故乡,总是让人魂牵梦萦。有时甜蜜,有时忧伤,甚至有时令人唏嘘、流泪。
别离的痛苦,悲伤的思念,午夜阑珊,时时夜不成眠。
在余光中眼里,故乡是绵绵的乡愁,在悠长的纷繁思绪中,乡愁化作了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活着的和逝去的亲人,都埋在了浅浅的海峡岸边。浩瀚无垠的海峡,化作故乡村边熟悉而温暖的河流。

和诗人甜蜜而温暖的回忆不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故乡远没有这么浪漫温情。
几日前,老家的一个兄弟梵打来电话,问我在石油系统是否有熟人,能否帮忙疏通一下关系,他想在老家开个加油站。
这些年,梵在广东东莞合资企业打工,说起来也算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十年前我去深圳拍片,曾经去东莞看他。他请我去他台湾的朋友那里喝茶。

彼时的东莞还是一片欣欣向荣。街面上有很多台湾人的店铺,他们售卖茶叶,还有祭祖的纪念品,梵也托台湾的朋友帮我买过书。
那些年,是东莞的黄金时代。
因为距离不远,很多深圳人也去东莞买房,就像曾经因为女儿患白血病,撰写微信公众号文章吸引几百万打赏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罗尔(很多人说罗尔是骗子,但他女儿确实身患白血病,就在打赏事件之后不久就因医治无效而离世),也在东莞投资买了房。

可惜,我们经历的黄金时代总是那么短暂。这几年,曾经名声大噪的东莞逐渐开始走上下坡路,很多经营多年的企业关门离开了。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的转型和调整,面对无法把握的未来,很多企业突然变得茫然一片,外部环境不再友好,压力阵阵袭来,他们只好选择脱身抽逃。
两年前爆发的疫情,对于东莞这个加工生产基地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不期而至的疫情管控,交通受阻,物流不畅,原料和成品无法及时到货,生产和销售就无从谈起。
“很多工厂都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新买的机器就在那里放着,生产线白白浪费了”。一年前,说起东莞的现状,梵痛心疾首。因为企业运营时断时续,他每个月只有几千元的收入。
两年前,疫情爆发时有专家预言,病毒只会在冬天肆虐,天气一热就会自然消退。而今,海南、四川的疫情又起,几乎遍地狼烟,似乎在狠狠抽打专家的耳光。
对于梵来说,他想回家开加油站,实则迫不得已。
“深圳的疫情一起来,现在那里都不敢去,从那里回来就要被隔离……东莞前段时间到处封路,道路用铁皮堵上,拉个货都能转晕,不知道从哪里才能转出去。”
在外寻不到前途,心中可资盼望的,似乎只有熟悉的家乡。那里有熟悉的乡音,有馨香可口的饭菜,还有朝思夜盼的亲人。
但家乡的路途未必那么平坦,家乡的人未必那么可亲,家乡的空气也夹杂着刺鼻的粉尘。朝阳早已不再灿烂,落日不再迷人,可能早就蒙上了厚厚的黑色尘土。
就像网上热传的那个沸沸扬扬的二舅,虽然身体残疾,他还要自食其力,自己照顾八十多岁的老母。他所住的老宅,也许历史悠久,但沉疴已久的历史也是摧残他生命,压得他无法自由呼吸,他终生摆脱不了的沉重负担。

也是几个月前,在老家县城上班的亲戚就对我说,县委书记刚刚调走了。他之所以离开很多人觊觎已久的书记大位,也是没办法的事。半年多来,县里公务员的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每个月财政局领导都要四处求人,借支款项,不能让公务员断炊。虽不断炊,但工资常常从月初拖到月中,又从月中拖到月底。
我老家地处华北平原,是陇海铁路和京九铁路交汇处,交通、物流极其方便,而且距离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非常近。一二十年前,很多沿海地区的企业纷纷到我们那里投资设厂,我们当地也有几个上市企业,怎么疫情爆发才两年就困窘到如此地步?
我有点想不明白。
几年前,黑龙江某县电视台记者就因为工资拖欠不得不到澡堂搓澡挣外快养家。我老家不是东三省老工业基地,人口流失不严重,也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官员腐败似乎也还在百姓可容忍的限度内,也还没有发现有动辄上亿的巨贪。
几年前,老家的房地产开发还如火如荼,到处一派勃勃生机,马路双向六车道,绿化赏心悦目,二三十层的高楼鳞次栉比,直逼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如今,席不暇暖,似乎就开始江河日下了。
反腐风声鹤唳的日子,有些官员倒下了,包括我们县曾经的书记。他被抓的时候,同学群里纷纷传扬他贪污的天文数额。事过两年,他咬出上百人的同僚,却依然还在被隔离审查。

即便这样的贪腐官员糟蹋了不菲的国家财政,地方政府这么多年的卖地收入也可以抵挡一阵,至少支持得起公务员的工资,断不至于到了马上断炊的地步啊?
也许,这里面埋藏了很多我们不知晓的秘密。财政数字背后有很多五彩斑斓的泡沫,甚至经不起微风,还没曾触地,泡沫自己就破了。
很多年前,经济还处于上升期,前呼后拥的泡沫掩盖了不堪的现实。很多人到我们那里投资设厂,然而有些人很快就失望而归。
企业刚开始投产,甚至还没有正式运营,工商、税务、城管、卫生、消防各路人马就陆续赶到,提出各种条件,每一个条件背后都意味着接下来花费不菲的请客送礼。
有门路的,开得起的,留下了。开不起的,只好自己卷铺盖走人。大浪淘沙,剩下来的企业,不是三头六臂,就是长袖善舞。
开办企业手续繁琐,需要协调的社会关系繁琐复杂,需要打点的各路财神形形色色,如此劳神费力,有人也许会想,这还不如开个饭馆省心。
其实未必。
在老家开设饭馆,都是熟人熟脸,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流行赊账消费,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此更是驾轻就熟。一个饭馆经营多年,往往并非因为经营不善关门,而是像被恒大欠账拖垮的企业一样,都是因为债务而被逼上了倒闭的绝路。
饭店做的风生水起的,不是饭店隐形的老板本身就是官员,就是背后有深厚的官场资源支撑。
华中理工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毅在其专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和阐释》里,为我们生动展示了基层百姓企业经营的艰难困境和生存之道。
深谙经营之道,在官场游刃有余,和官员交情颇深的人精老罗开个饭馆尚且需要挖空心思,四处公关,像我的老乡梵这样常年在外打工,对老家官场形同世外的“准外地人”来说,开个投资巨大的加油站,难度之大,在我看来,几乎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差不多。
仅仅办理手续一项可能就会耗尽他全部家当,要了他半条命。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完了全部手续,顺利开业了,如何对付那些留守乡村的恶势力的骚扰也会让他伤尽脑筋。
城乡天然存在的自然和文化差异,因为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而人为制造的各种社会不平等,使很多生活在乡村社会的百姓自出生始就处于被剥夺的弱势地位,很容易使他们的人格、心理、意识和思想发生扭曲,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日常行为。
不可否认,乡村默守的,还是一套约定徐成的传统社会法则,隐形的暴力法则对百姓的日常生活依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很多老实本分、胆小怕事的乡邻不同,有些人借助各种势力恃强凌弱,横行乡里,盘剥百姓。经营企业,需要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应对这些社会边缘势力。
很多农村青年并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他们可资凭赖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或者突破社会规则的勇气,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急于实现梦想的不安分野心,很容易让他们走上不法之路。
十几年来,我亲眼见证了自己老家的很多青年因为参与赌场、非法集资,或者其他形式的犯罪而身陷囹圄。他们或者期望快速发财,急于摆脱贫困的经济现状。或者结交身份不明的道上朋友,希望改变软弱无助的社会形象,却因为无知一不小心就遭受了牢狱之灾。
对法律和社会的无知,自制力的缺乏,底层生活积压的怨气和愤怒,他们做事很容易失控,突破法律的界限,伤害到他人的人身和安全。
即便没有结成团伙的三三两两的个人,如何对付他们,有时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很多年前,我老家村子里有人结婚,请了外地的一个唢呐班子助兴。婚礼前一天,唢呐队正在兴高采烈地演奏,突然冲出来两个年轻人,对唢呐队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拳打脚踢。
也许,那个毛线帽子曾给村里的两个年轻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们或许被带毛线帽的人侮辱伤害过,毛线帽由此勾起了他们痛苦的感受,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就像中国近代史里屡见不鲜的案例,有人看见了金发碧眼的洋人就怒不可遏一样,他们要发泄报复的快感。
事后得知,打人的年轻人是我们本村的,他们因为看不惯被打孩子头上戴的那顶毛线帽子,觉得他太洋了。
所谓的“洋”,其实就是城市生活的“时尚”。我们村两个年轻人之所以对“洋气”这么深恶痛绝,其实是对城市时尚生活的仇恨。城市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地位的卑微,人格被随意践踏的残酷现实,改变现状的软弱无力。
某个无足轻重的细节伤害到他们的情感,就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于是他们急于找到一个城市生活的象征物进行报复。红色高棉强迫金边市民离开城市,历史上很多残酷的大迫害,大体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文化上的因循守旧,在传统习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老家结婚几乎完全沦为了一桩以质论价的买卖。男方需要买房、买车,拿出几十万的彩礼钱,一场婚姻可以透支一个平民百姓一家十几年的未来。
回老家创业,在世俗中生活,必须面对来自传统社会的各种压力。更不用说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亲戚朋友们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每个场合都要准备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份子钱”。这还不包括孩子升学、过生这些数不胜数需要出钱的场合。
撇开所有这些社会因素不谈,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这个时候回老家创业,也很可能是一条凶多吉少的不归路。
这些年外部世界似乎越来越穷凶极恶,各方似乎都在为与世界脱钩做准备,国内经济受到的影响显而易见。
疫情爆发以来,各地财政收入日渐急促,2021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财政盈余,而今年至今,已经全部赤字,四川、河南人口大省更是出现三千多亿的财政赤字,以至于总理都不得不召集几个财政大省要钱。
我们老家以农业为主,并没有什么产业,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单一,主要还是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如今全国财政一片吃紧,首先保证的是那些急需用钱的地方和部门,哪还有多少盈余往我们那地方转移呢?
老家地方政府发工资之所以出现困难,正是缘于此。我相信像我老家这样的情况绝非个案,全国各地比我老家财政困难的地方不胜枚举,有些地方没有我们老家那样有利的地理位置,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营收渠道有限,开发房地产的卖地收入也少的可怜,而供养的财政人口比例可能比我老家还高,他们的困难多大,可想而知。
如果地方经济萎缩,百姓收入下降,面对一个市场日益低迷的未来,回老家创业还有没有什么前途呢?
更何况,在“别让XXX跑了”的鹤唳风声中,这些年眼见的很多人移民海外,新加坡一下子多了几十万大陆移民,取代湾湾成了亚洲金融中心,人们对内地的市场前景还有多大信心呢?
更不用说,我们那个主要靠转移支付支撑的地方财政体制。
很多时候,故乡,只能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停留在沉沉的美梦中。而现实,往往如同冰山,坚硬冷酷,一如往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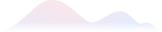
撰文 | 蒋效中
编辑 | Ke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