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尔塔萨提出,1922到1930年十年间,巴特有一个“从辩证到类比”的神学认识论上的转向,这一观念原为学界普遍接受。陈家富老师致力于澄清,巴特后来并没有摒弃辩证神学方法,而是将之与类比方法并用。而且,对此两种方法的同时协作运用。并非首见于巴特的安瑟伦书,而是在1924年的《哥廷根教义学》中就此存在。因此,尽管将安瑟伦书的论述视为巴特神学方法论的分水岭这一观点甚至得到巴特本人的认肯,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声称,安瑟伦书中有任何前所未见的新发现和神学方法论上的突破。这是陈家富老师文章的主要结论。在我们看来,陈老师的文章遵循“忠于思想而非语言”这一原则,对学界,特别是汉语学界,长期以来的误解具有纠偏的价值。
原文载于鄧紹光、赖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101-122。推送时已获作者本人和发表单位授权,特此感谢陈家富老师和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從辯證到類比?
一個對卡爾巴特神學知識論的探討1
陈家富
1
引言
本文嘗試重新考察卡爾巴特(K. Barth,1886-1968)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間神學知識論的發展,並對學術界稱巴特這段時期的神學方法為「從辯證到類比」(from dialectic to analogy)的論題提出質疑。我們將發現,巴特從《羅馬書釋義》第二版(1922)到《教會教義學》第一卷(1932)期間,辯證神學一直是他運用的方法,換句話說,巴特的辯證神學方法論並沒有被他摒棄。
「從辯證到類比」已被普遍接受為描述巴特神學發展的用語,意指巴特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期間,在神學方法論上出現一個徹底的轉向。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標誌着以辯證神學來對抗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此可說是巴特的第一個決裂(first break)。及後在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開始教授基督教教義學,亞於一九三〇年在波恩大學(University of Bonn)教授安瑟倫(Anselm)的神哲學,在一九三一年出版討論安瑟倫的小書就標誌着巴特的第二個決裂(second break)。這個決裂也就是一般被稱為從辯證神學轉到類比神學方法的分水嶺,而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教會教義學》首卷亦遵從這種類比神學方法而展開。總而言之,巴特神學的發展被認為是經歷了兩次的轉向:一是從自由神學轉到辯證神學;二是從辯證神學轉到類比神學。
首先提出上述這幅有關巴特神學發展圖象的學者是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他指出,巴特的思想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辯證的階段,二是類比的階段。
就正如奧古斯丁經歷兩次轉向,第一個是從大量的錯誤轉到真實的上帝和基督教裏,而另一個(在較後時期)則從早期著作中的宗教新柏拉圖主義轉到真正的神學中,而在巴特中我們亦發現兩個具決定性的扭轉點,第一個是從自由主義轉到徹底的基督教,它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在《羅馬書釋義》中表現出來;第二個是從哲學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使他最終到達那真實和自我證立的神學中。這個轉向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事實上是一個掙扎,差不多經歷十年的時間而約在一九三〇年終止。2
雖然巴爾塔薩辯稱巴特第二次的轉向並非一個突然的決裂(十年的掙扎!),但正如他所提出,我們仍會發現,一九三〇年是巴特神學發展的商高潮。在巴爾塔薩心目中,這個高潮就是討論安瑟倫書中的「信仰類比」(analogia fidei)概念,亦即是巴特神學的知識論轉向的核心,而這個轉向亦即是「從辯證到類比」。
……自從在他(巴特)神學從辯證到類比的偉大轉移……巴特已詳細和完整表連出他自己的觀點,當中是毫無疑問和清晰的。表達他思想改變的第一本著作是他討論安瑟倫的上帝存在論證,他自已稱呼這部作品是他從第一個階段分離出來的真正宣言。3
我們或許會問,為何巴爾塔薩堅信「從辯證到類比」是巴特神學發展的真象呢?筆者相信,除了巴氏對巴特原著有仔細的研究外,似乎巴特本人的自身理解與巴氏不謀而合亦不無關係。在一九三九年,亦即是論述安瑟倫著作出版後的八年,巴特以「在本世紀我思想如何轉變」為題來論述他神學思想所經歷的路程。他說:
在這幾年,我已驅除一種哲學性,即是人類學……基礎的最後殘餘部分和基督教教義的闡析。事實上,標誌着這個道別的真正文件並非在一九三四年直接反對布魯納(Brunner)並經常被人閱讀的《否》(Nein!),相反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討論安瑟倫有關上帝證據的書。在我云云的書中,我以為這部是寫得最滿意的一本;……4
在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巴特自己亦同意論述安瑟倫的書是他神學方法論的分水嶺;不單如此,巴特對巴爾塔薩的分析亦在一九五八年的再版前言中加以正面評價。
相對來說,只有少部分的評論者,例如巴爾塔薩,能發現我對安瑟倫的興趣,在我來說絕非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或(假設我對聖安瑟倫的歷史詮釋或多或少是正確的)留意到它影響我多少或正融入我思想的路線當中。他們大部分都不能看見我在論述安瑟倫的書,若非是那唯一的鎖匙,也是其中一把理解整個思想進程的鎖匙,它影響我的《教會教義學》亦愈來愈多,使它成為唯一對神學適當的東西。5
我們可見,巴特自身似乎亦完全同意巴爾塔薩的分析,以致學術界普遍完全接納巴氏對巴特神學方法的分期觀點,認為巴特的神學發展確實存在兩次的「決裂」,而在後一次轉向中,巴特的「信仰類比」(analogia fidei)完全取代了前期以《羅馬書釋義》所代表的辯證神學,亦即是在一九三一年(論述安瑟倫著作面世)之後,辯證方法再沒有被巴特採納為他神學方法的工具。巴爾塔薩的論題不單影響着德語神學界,6 連英語世界似乎亦不加批判地接納了巴氏的分析,六十年代的多倫斯(T. F. Torrance)*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Thomas Forsyth Torrance
(30 Aug 1913 – 2 Dec 2007)
多倫斯是首位在英語世界研究巴特神學早期發展的人。7 他考察了巴特從辯證時期到所謂「過渡到《教會教義學》」時期的神學內容。雖然多倫斯注意到巴特在哥廷根(Göttingen)和明斯特(Münster)時期的神學發展重要性,但他仍接納巴爾塔薩的論題,即安瑟倫的討論是巴特神學從早期過渡到成熟期的轉捩點。
差不多沒有疑問的是,他(巴特)有關《信仰尋求理解》研究的寫作與出版是代表他思想的決定性轉捩點,因為它標誌着他從辯證思想到《教會教義學》的最終完成……它肯定對巴特的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因為在《教會教義學》的寫作中,在及後時間他立刻將自身投擲此書在重要地方的影響,主題(subject-matter)、形式和方法的連結是被關注的。在這部耀眼和極之重要的小品中,巴特對神學方法的基本本質得到厘清和具體化,他在當中嘗試抓住神學中的科學與準確命題的問題,並信仰與理性、客觀與邏輯內在必然性之間的內在關係,這些都能建構神學的整個結構。8
多倫斯聲稱,在研究安瑟倫的書中,巴特發現一種新的做神學方法,以致辯證法被這種方法取代。同時,這種對早期神學方法的揚棄,亦標誌着建構一種新神學基礎的完成,而《教會教義學》亦有賴於這基礎。故此,這部小書不單可說是巴特神學方法的轉捩點,它更是開展一條新神學路徑的起始點。
本文旨在對上述這種理解巴特神學方法的圖像提出批判性的考察,而筆者會集中討論有關巴特的所謂「第二次決裂」的問題,亦即從辯證神學方法論轉到類比方法的過渡問題。本文會討論四個相關的問題。(1)辯證方法與類比法是否必然相互排斥?(2)巴特在哥廷根時期的教義學採納了甚麼神學方法?(3)巴特在討論安瑟倫的書中是否存在新的發現?(4)《教會教義學》首卷中是否存在辯證方法?
2
巴特《羅馬書釋義》的辯證方法論
對巴特而言,神學方法決非一個次要的問題,尤其他在自由神學的訓練下,有關神學知識論的討論可說是他神學生涯一開始就要掙扎的課題。神學知識論可理解為有關人類對上帝認識的可能性之探索,當中包括神學語言性質的問題、人類認知範圍的討論、上帝與人的本體論與知識論差異等問題。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可說是從宗教的領域內對康德的知識論的一種反動,而巴特早期的辯證神學亦受康德式的思想影響頗深。9 在自由神學的理解下,上帝再不是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的認知對象,因為在康德的哲學中,人的知識只局限於感知世界(sensible world),越過此經驗領域,沒有任何對象能被直觀(can be intuited)。因此,我們不能聲稱對上帝的知識是客觀的,因為「上帝」已經是一個遠離我們知識象限外的超越存有,所以,有關上帝的知識只能是「主觀性」的。「主觀性」並非意指個人的愛好,而是指一種存有的實存模態,這種模態是由宗教經驗所引導的。「虔誠的自我肯定性本質就是:存有的意識絕對依賴……與上帝關係中的存有」10 由此,上帝知識的研究也就成為人類宗教經驗與存有實存模態的研究。巴特正是受上述這種神學框架所教導。

Der Römerbrief 罗马书释义
Karl Barth ,1999 16. Aufl.
Press: Tvz Theologischer Verlag
Subtitle: Zweite Fassung 1922,
眾所周知,巴特與他神學老師的決裂,是由於他們簽署了一份宣言,這份宣言象徵着他們認同於凱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的戰爭政策。巴特當時完全不能理解這班神學教授的立場,但有一點巴特是堅信不移的,就是這班教授所提出的自由神學是再沒有任何前途了,11 因此,巴特需要重尋神學的方法,基本上他認為自由神學忽視了上帝的「他性」(Otherness),上帝是「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他並非我們世界和心靈裏的對象。巴特認為,整個自由神學都走錯了路,以為神聖知識的主體是人的宗教意識。相反,巴氏堅持,神學知識的主體永遠是上帝自身。「上帝在天上,而你卻在地上」正是《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主題。12
在《羅馬書釋義》中,巴特不單強調上帝與人的「無限本質上的區別」,他還以辯證的思想去處理上帝和人的關係。
那個與我們相遇的否正是上帝的否。我們所欠缺的正是能幫助我們的,那驅禁我們的正是新家鄉,那否定所有世上真理的亦正是那根基。因為準確來說上帝的否是完整的,它亦是上帝的是。13
上帝是從辯證的途徑去認識,他的是與否是相互依存。就我們來說,我們難以判斷哪個是上帝的是,哪個是上帝的否。這個陳述的基本原則是想指出,上帝和世界是有距離的,這是一種本體論上的距離,上帝和世界之間並無任何的連續,上帝並非我們世界事物的總和,上帝超越這一切,亦即是說,上帝並非內蘊於世界中。就這而言,巴特強調上帝的不可知性(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上帝是不可知的。那麼,我們怎樣言說上帝呢?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位自我啟示的上帝嗎?在這段辯證神學時期,巴特啟示論是相當富爭議性的。
在歷史裏,耶穌作為基督只能被理解為問題或神話。作為基督,他將父的世界帶來,但處於這個具體世界的我們卻對這另一處世界一無所知,並且亦無能而知。但從死裏復活卻是一種轉化……復活就是啟示……在復活中聖靈的新世界碰觸到肉體的舊世界,但這種碰觸就好像切線碰觸圓形一樣,即是根本沒有碰過它。14
巴特確實提到上帝的啟示,但復活作為啟示是「非歷史性」(ahistorical)。「復活並非在歷史裏的一件事件。」15 巴特的意思是,我們不能將復活理解為在歷史中眾多事件中的其中一件,它的意義是不在歷史理性的範圍之內,故此,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啟示的行動仍然是非直觀的(unintuitable)。用麥郭馬(McCormack)的說話表達,就是上帝在啟示中以遮掩自己來彰顯自己(God unveils Himself by veiling Himself in revelation)。16 可見,基督論和道成肉身論在這時期還未成為巴氏神學知識議論的基礎,他只強調上帝的他性。
其次,巴特有意將自由神學的基本前設重新反省,將他們的企劃作一個完全的扭轉,在人類的知識領域中,上帝是「完全的他者」,人不能宣稱已經抓住上帝,上帝的啟示雖然是「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但這仍然是一個奧秘,啟示並無碰觸這個世界,人完全不能憑藉歷史理性去認知誰是上帝。在這個知識論的意義下,巴特是一個康德主義者。17 康德辯稱我們客觀知識的合理基礎是由於客體是可直觀的,所以,在康德的知識論框架中,上帝是不知的,因為上帝是一個不能被直觀的上帝。巴特似乎亦基於這個框架去考慮上帝知識的可能性,他認為,若上帝是非直觀性的(unintuitable),那麼,唯一真正認識的判准就只有上帝自身成為可被直觀,但有一個兩難會出現,就是若上帝使自身成為可被直觀,則上帝把自己成為一被造物,而最後此被造物亦將成為我們人類認知活動的客觀對象。所以,原本是認知活動主體的上帝,最後卻因着要被直觀,而成為認知活動的客體。據麥郭馬分析,巴特的解答是不完整的。18 一方面,巴氏強調上帝的非直觀性,為要保護上帝與世界的截然分開;另一方面,他又為人類對這非直觀的上帝所可能有的知識而掙扎。這個問題開始於《羅馬書釋義》第二版,而巴氏就嘗試透過道成肉身論在哥廷根的教義學中解決。19
另外,在《羅馬書釋義》中還存在另一個神學知識論的困難。問題是倘若巴氏認為上帝是「完全的他者」,我們又怎樣知道上帝的存有是他者的存有呢?倘若巴氏堅持人不能直接認知上帝,他又從何得知上帝是「完全的他者」呢?就算這是一件有關信仰的事情,我們仍要問,這個信念背後的知識論根基何在。換句話說,若巴特指出他這種神學方法是辯證的,我們要問辯證法的必要條件是甚麼?潘能伯格(W.Pannenberg)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示,據他理解,巴特在《羅馬書釋義》的上帝是世界和人類的否定,意思是當我們接受巴氏的上帝觀時,我們其實是透過對有限存有物的否定來思想上帝(thinking of God through the negation of the finite beings)。從積極的意義來看,雖然上帝和世界關係是在辯證中,但上帝的存有仍依賴世界去給他界定(縱使這是一種否定的界定)。20 若潘氏的理解是正確的話,巴特的方法論仍然「從下而上」(from below to above),從對世界的否定去思想超越的上帝。
由此可見,在《羅馬書釋義》中,上帝和世界的概念並非一種完全斷裂的關係,反而兩者存在着一種頗吊詭的關係。上帝不能抽空地思想他的「他性」,「他性」有賴於對世界的否定而構成。雖然世界和上帝在此並無一種類比的關係,但至少讓我們明白,要思想上帝,是不能離開對世界的觀念來思想的。
3
哥廷根教義學的基督論
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巴特首度在哥廷根大學教授基督教教義學的「預備性部分」(prolegomena),他將課程定名為「基督宗教的課程」(Unterricht i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我們將會發現,巴特在這時的神學方法論有重大和關鍵性的突破,因為基督論的出現成為上帝啟示的基礎,而一直在《羅馬書釋義》未完全發展的道成肉身論亦正式展開。並且,在哥廷根的教義學中,我們不單察覺一個較有系統的神學框架逐步完成,更重要的是,巴持有意將早期的辯證法和類比法帶到一個互相補足的階段,以致兩者不單不會相互排斥,而且在基督論的基礎上得以同時並存;不單如此,我們發覺,巴特最早使用類比法是在哥廷根大學的教義學中,而非討論安瑟倫的書。
在教義學的首部分,巴特清楚將教義學理解為「對上帝之言的科學性反省,上帝之言乃由上帝在啟示中說出,並由先知和使徒記載在聖典中,現在是和應該是在基督教教導中被宣講和聆聽。」21 這個對教義學的扼要陳述可理解為上帝之言的三個形式。第一是一種永恆形式,指到在啟示中的上帝之言;第二是一種歷史形式,指的是聖典;第三是現時的形式,具體表現為基督教宣講。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巴特所強調的是三者都聯於同一源頭,就是由上帝自身所說(Deus dixit)。
與《羅馬書釋義》中啟示的永恆臨在觀念不同,巴特現在所強調的是「上帝自身所說」是等同於歷史人物耶穌基督。意思是,上帝言說的主體既是在歷史之外,但亦同時在歷史之中。
上帝言說是意指此時此地,或那時那地偶發的事實是教會在這些獨特的著作中找到啟示的見證,並在見證中找到啟示而並非意外。偶然性是在啟示的本質中。上帝言說指到一獨特、一次完成和偶發的事件,當中這些獨特的著作而非任何可能的作品更能帶出見證。22
當中歷史的耶穌成為在歷史中上帝之道的主體,上帝在耶穌基督裏言說,故此,《羅馬書釋義》中的「沒有碰觸這個世界」就被「存活在世界中」所取代。其次,巴氏強調所示的偶然性,意思是人的語言有資格成為上帝啟示的人類語言,因為聖典與基督教的宣講同樣成為上帝啟示的客觀載體和上帝之言的其中兩種形式。因此之故,不單一個歷史人物能成為上帝的啟示,連人類的語言同樣可成為上帝自身的載體,因為正如巴特所強調,上帝之道是透過和在人類語言中表現其現在的形成(God’s Word is, through and in our language, in the present form)。23 雖然巴特指出人類語言和上帝之道之間類比關係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但他並沒有放棄辯證法。原因是啟示的主體仍是上帝自身、上帝言說,上帝是那位對他構成知識的主角,換句話說,人沒有能力越過上帝而對上帝能構成任何的知議,因此,上帝與人之間仍然存在知識論和本體論上的距離,教義學作為一種「科學性反省」是指出沒有一套教義學能有資格作為上帝的最後說話。人之言決非神之言,《羅馬書釋義》中的辯證法仍是主調。可見,在上帝的判斷中,辯證法和類比法得以同時協作。24
在第五部分中(在討論上帝言說和人學之後)巴特第一次提出三一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給友人圖內森(Thurneysen)的信中,巴特聲稱被三一論所佔據:
「存有的三一論(A Trinity of being),不單是經世三一論(economic Trinity)!三一論教義的全部內容!若我能親手找到這條正確的鎖匙,則萬事皆妥。」25
三一論是解答「誰是上帝?」或「誰是啟示主體?」的問題,亦即是啟示可能性的主體性基礎。
啟示是上帝的自身啟示,意指啟示的內容並非另一個上帝,相反,啟示的內容和啟示的主體是分不開的。當我們論及上帝啟示時,我們並非提及一些我們真實或可能經驗上的對象,這決非是一件人的事件。26 正如巴特認為,啟示的內容是「唯獨上帝、完全是上帝、上帝自己。」27 倘若我們離開了啟示的內容,就不能認知啟示的主體,相反亦然。故此,在三一論的視域內,上帝之道作為啟示的客體是不能與啟示的主體相分離的,啟示客體的存有是等同於啟示主體的存有(The being of revealed object is identical with the being of revealing subject)。因此,巴特所講的「存有的三一論」,是指內在三一論(immanent Trinity)與經世三一論(economic Trinity)是分不開的,前者着重三位格在一體中的關係,而後者則重三位格在創造和救贖中的工作。因此,上帝的整個存有都啟示給我們,他的隱藏性並不涉及存有自身,而是理解為「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在歷史中的上帝永遠是deus absconditus(隱藏的上帝)。28 同時,巴特指出在上帝啟示的語境中類比思想的可能性,雖然啟示的主體是上帝自身、而沒有任何人的理性或宗教經驗能與之等同,但人卻能回應上帝的自我啟示,方法是與上帝的存有和行動進入類比的關係中,巴特說:
當面對上帝所作的,我們是在自已存在的領域中作出相應、平行與類比的做法。我們的理性活動獲取一種更強或更弱的獨特理智和實踐取向……但這些全部只能在啟示的影象中進行。29
當巴特談到啟示的內容時,他堅稱,耶穌基督是主,耶穌是等同於啟示的主體。但倘若我們將《羅馬書釋義》遺留下來的問題重提出來:耶穌基督如何在時間中作主體而沒有損失任何的神性?巴特似乎會用一種辯證的方法回答:上帝是以地上的形式出現作為啟示的主體,但他並非變成地上的形式(God is the revealing Subject in the earthly form, but He does not become the earthly form)。耶穌作為啟示的內容是等同於啟示的主體,意思是上帝在耶穌基督的隱藏肉身中非隱藏地啟示自身(God unveils Himself in Jesus Christ in a veiling flesh)。巴特就從以上的背景中發展他的道成肉身論。
當巴特討論道成肉身論時,他劈頭的說話是:
上帝在基督裏。在其神性的不能排除的奧秘中(被每個攻擊可能性所圍繞),他是被釘的那位,他只能透過他自身在基督的死而復活中被認識,在歷史中,在時間裏,他能真實、準確地並充分地與人在相處中被認識。30
所以,我們能從耶穌基督身上認知上帝自身,因上帝決意完全在這人身上啟示自身,但這並無表明在啟示中上帝變得微小,上帝仍是啟示的主體,從辯證的角度看,上帝在耶穌此人身上揭示自身給我們。「隱藏一定是完整的,神聖的隱藏一定是整全」31 同時「有限能承載無限」(finitum capax infiniti)這路德宗的基督論方程式亦為巴特所接受。
總而言之,在巴特的《哥廷根教義學》中,我們發現,巴特嘗試解決《羅馬書釋義》中所遺留的問題。基於他將基督論作為神學知議論的基礎,我們可透過耶穌去認知上帝。更重要的是,巴氏指出,我們的語言可作為上帝之道的表達,人的語言和上帝之言有類比的關係,但同時巴氏並無放棄辯證法,上帝仍以隱藏的肉身去開顯上帝自身,因此,「無限本質差異」仍是《哥廷根教義學》中的思想。我們可用麥郭馬的說話來總結:
當中知議論義涵是,現在上帝似乎已完全進入到一種主體一客體的關係中,這關係指導我們對這世界事物的認議。上帝完全進入一種直覺的世界(world of intuitability)。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巴特只能透過上訴於神聖能力的實踐去連結非直覺性與直覺性間的鴻溝而得以保存直覺性,但現時上帝……已成為可被直覺了(God has become intuitable)。32
4
巴特論聖安瑟倫:一個方法論的轉捩點?
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可進入討論安瑟倫的問題。巴爾塔薩想指出的是巴特討論安瑟倫的書是巴氏本身神學方法的轉捩點,亦即他認為在此巴特有新的發現,但我們將會發現,安瑟倫的書中內容其實早已見於哥廷根的教義學中。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一九三〇年初,巴特應邀到波恩大學教授系統神學。當時,士高(Heinrich Scholz)亦應邀到波恩演說,內容是討論安瑟倫的上帝存在論證,是為一九三〇年夏天。巴特自己清楚指出,士高的詮釋引發他對安瑟倫詮釋的方向和興趣。33 因此,第一:巴特基本上沒有任何意圖和計畫要在安瑟倫的書中展示或陳構他自己的神學框架,極大可能是對士高的一種回應而已;第二:這是一本討論安瑟倫的書,雖然到最後或許它能告訴我們有關巴特的神學多於安瑟倫的神哲學,但它始終是一本研究安瑟倫的書,主角並非巴特本人。基於以上的歷史考慮,我們再進入理論性的問題:究竟巴特在此書中有否神學方法論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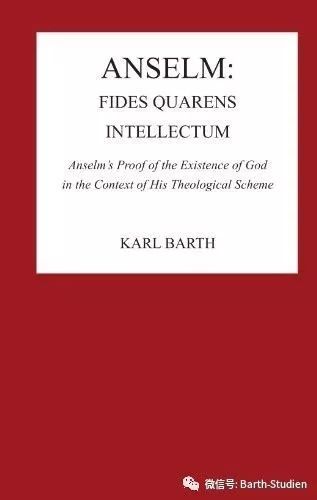
Anselm:Fides Quarens Intellectum 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
Author: Karl Barth,
Translator:I. W. Robertson,
Publisher: Pickwick Publications (April 1979)
這本書原初的題目是《信仰尋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ctum),信仰是首位,理解奠基於信仰。簡單而言,對上帝的理解永遠是一種對信條(Credo)主體的「再思」(Nachdenken),故此,我們的神學知識本質也就是一種對教會信條的「後驗反省」(a posterior reflection)。理解(intellectum)可理解為三種不同的範疇:(1)人的認知是「理知」(ratio);(2)信仰的對象是[信仰理知」(ratio fidei);(3)上帝之道是「真理理知」(ratio veritatis)。34 安瑟倫認為,理解得以完滿,只有當認知者的理性與對象內涵的理性達致一種融洽的關係。因此,據巴特的理解,安瑟倫的神學框架並非要去展示一種對上帝存在的理性「證明」,相反,人是無法運用自身有限的理性去論證上帝的概念,沒有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上帝的知識是無法獲得的。
每一個神學命題都是其對象的不完滿表達,雖然就我們而言,每一種嘗試(那怕是最高層次和最完美的)在思想或言說中重新產生那道都是不完滿,但基督真正的道對我們的言說就並非不完滿的表達。直接說,只有上帝自身具備上帝的概念,我們所有的只是諸對象的概念,當中沒有一項能與上帝等同,哪怕是最有價值的描述都只是一些相對的價值。他是我們能夠言說關於他的那位,而並非僅是完全的他者,縱使唯獨他自己是真正和真實,獨特而在範疇中他只被自己所認識。35
巴特的意思是,每一個神學語句都是條件性的,條件是以一種辯證的方式出現。上帝須在我的思維中展示他自身,以致在思維中的上帝能與上帝之道得以符合,但同時,上帝之道仍然是整個認知事件的主體。簡單而言,我們之能想像和言說上帝是基於上帝首先對我們言說,但我們又不可能永遠無誤地言說上帝,因為上帝知識的主體永遠是在上帝那邊。基本上,這種辯證思想亦曾在《羅馬書釋義》中出現,故此,理解是一種辯證的概念。另一方面,神學語言的可能性仍被巴特所重視,整個神學語言都是上帝所賜的禮物,上帝「展示」自身給我們去認知他,他「提供」適當的語言(上帝之道)給我們去言說他,所以,上帝使用我們人類有限的語言去描述他,整個過程的可能性全在於信仰的背景下進行,因此,巴氏強調信仰尋求理解。他說:
整個事件不僅依賴上帝給他恩典去正確地思想他,而且上帝還進到他的系統中成為思想中的對象,即是他「展示」自身與思想者並在過程中修正思維以致能達致一種「進到事物本質中的理解」(intelligere esse in re)。唯有如此,基督教知識的恩典才得以完成……這種認知,這種認知(intellectus)……是一種信仰的認知(intellectus fidei)。意思是,它只能包括對信仰對象的一種積極默想……最後,它到達的目標就是恩典,事情就是目標的觀念和人達致這目標的努力,亦即是在最後的分析中這是一個禱告和對禱告回應的問題。36
我們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在討論安瑟倫的書中確實存在類比思想,但同時巴特在書中亦高度重視辯證方法;第二:這種將類比和辯證方法同時協作運用,並非首見於安瑟倫的書,在一九二四年的《哥廷根教義學》中已存在,因此,我們不能聲稱,巴特在討論安瑟倫的書中有任何前所未見的新發現和神學方法論上的突破。因此,根頓(Colin E.Gunton)在評論巴特這本書時是有誤導性的,他說:「沒有它(討論安瑟倫的書),我們將缺乏重要的資料去理解巴特為何認為神學是一種理性的追尋和他將甚麼給予其理性。」37 正如我們在本文第三段指出,巴特在哥廷根的教義學中已非常重視神學的科學性格,其用意是突顯上帝自身提供及保證我們神學語言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耶穌基督是上帝啟示的對象,而人類神學語言的客觀性亦建基於他,因此,教義學作為一種科學的追尋是要求我們對上帝有理性的思想和認識。
5
《教會教義學》中的辯證法
一九三二年,巴特將《教會教義學》的「預備性部分」(prologomena)出版,與哥廷根的教義學相似,巴特以上帝之道的教義作為整個教義預備部分的內容,但今次他將上帝之道的教義放在三一論的語境中討論,而三一論的教義所指向的內容是關於啟示的問題。所以,我們先要處理三一論的教義,然後才考察它在神學知識論中的問題。巴特認為,三一論和啟示論是分不開的,當我們處理上帝的啟示時,其實我們是在處理上帝自身,同時上帝彰顯自身在啟示中,因此,巴特指出「上帝啟示自身。他透過自身啟示自身。他啟示自身。」38(God reveals Himself. He reveals Himself through Himself. He reveals Himself)巴特這句簡單的神學命題就清楚地將過往教會傳統中有關三一論的異端加以反駁,他強調,啟示的主體是等同於其客體及效用,所以在啟示中的上帝是指上帝作為啟示者(revealer)、啟示(revelation)及啟示性(revealedness)。而且,巴特強調,上帝的存有與上帝的行動亦是分不開的,上帝的存有是在他的行動中彰顯出來,在他行動中,其存有得以彰顯,故此,上帝的存有與行動是相互等同的,帶來的結果是我們若離開上帝在世界中的行動,我們將不能認識上帝的存有,同時上帝的存有亦在行動中完全彰顯出來。總括而言,上帝在啟示中是主體、客體與效用。
在有關神學知識論的討論中,巴特指出在啟示的語境中,我們需要回答三個問題:(1)在他啟示中的上帝是誰?(who is God in His revelation)(2)他做了甚麼(what is He doing)(3)他產生了甚麼效用?(what does He effect)雖然巴氏注重三者的相互緊扣的關係,但它們並非在同一水平上。「誰」的問題比「甚麼」的問題永遠在神學的探索中佔有優先性。39
有關上帝是誰的問題(它是三一論處理的問題)是需要保存的,而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有關上帝的「甚麼」,而這問題卻要在「誰」的前設中被理解。40
巴特認為,傳統神學上較喜歡跟隨的模式是詢問我們怎樣認識上帝?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甚麼?而誰是上帝的探問是最後的。41 因此,據巴特的理解,無怪乎三一論往往成為神學上次要的問題。巴氏清楚指出,除非上帝自身定義「上帝」這詞的意義,否則,人類不能正確言說它,所以,神學追尋的對象首先應是此追尋的主體,即是所有關於上帝的反省永遠是對上帝已經啟示自身此事實的一種「反思」(Nachdenken)。42 這種神學方法論的觀點想指出的是,任何有關對上帝的知識都不應該是「先驗」(a prior),而相反應該是「後驗」(a posterior)。「誰」的神學詢問能規限和陳構神學企劃的內容和範圍,而三一論就是回答「誰」的神學詢問的答案。
三一論是能在根本上區分基督教上帝觀之為基督教的,並區分基督教啟示觀之為基督教而與所有其他可能的上帝觀或啟示觀相分別的教義。43
因此,有關誰是自我啟示的上帝的回答是:就是那位上帝他啟示自身為父、子與聖靈的那位,這三種上帝存在的模態(Seinsweisen)也就是啟示中的主體、客體與效用。
在名為「三一論之根基」一節中,巴特強調「上帝啟示自身為主」這一神學命題。44 首先,上帝在啟示中的主權意指上帝是那位在啟示中的絕對主體。45其次,其主權意涵其自由,上帝不受任何東西所制約,上帝是自由的,意思是上帝是自決的,他有絕對的權威與自我自律去決定如何啟示自身,但他的啟示並不以一種抽象和形而上學的形式出現,相反是以具體的方式臨在。
……所有這些將能完全具體出現,只有當我們注意到我們現在所具備的並非主權的抽象啟示,而是主的具體啟示;並非抽象的上帝,而是上帝自身,他在自由中言說成「我」而被「你」所接受。46
上帝的啟示是一件事件,當中「我-你」的相遇出現。「上帝那種為我們的存有就是啟示的事件」。47 第三,巴特重視在其啟示中的上帝是向我們自我隱藏其存有的上帝,因此,啟示的上帝(Deus revelatus)亦是隱藏的上帝(Deusabsconditus),意思是上帝在其隱藏中彰顯自身,而其隱藏性亦在啟示中彰顯出來,上帝是以這種辯證的方式啟示他自己,故此,人與上帝的存有亦在此張力中,雖然是這樣,上帝的奧秘並無在啟示中減損分毫。48
可見,辯證法的元素仍在《教會教義學》首卷中出現,就算上帝的啟示成為我們神學反省的對象,上帝作為啟示的主體仍得以保存;其隱藏性在其啟示中亦沒有失去,因上帝的自由和主權在啟示中得以保存。故此,上帝仍是透過和在一個隱藏的肉身中不隱藏地彰顯自身,這亦是在哥廷根教義學中的主題。
6
總結
從以上各節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巴特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期間,辯證法一直出現在其重要的神學著作中;其次,辯證法與類比思想首見於哥廷根的教義學中,並以基督論作為基礎使兩種方法得以同時存在。因此,討論安瑟倫的書在神學方法論上並沒有重大的突破,因為重要的元素已經在哥廷根的教義學中出現。因是之故,巴爾塔薩描述巴特的神學方法為「從辯證到類比」的論題是站不住腳的。49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陈家富,香港出生,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曾任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宗教与神学)、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 (宗教学,哲学)、香港浸会大学文学士 (宗教研究)。学术兴趣:近代当代基督教思想、欧陆宗教哲学、宗教与环境伦理学、宗教与动物伦理、蒂利希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田立克:边缘上的神学》、“Life as Spirit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 ”(de Gruyter);编著:“Paul Tillich and Asian Religions”(de Gruyter)及多篇学术论文。(部分摘自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官网)
巴特研究
往期阅读 Editors’ Choice
陈家富|兩種類型的辯證神學——兼論劉小楓的漢語神學構想
陈家富|人性與基督:巴特的基督論人觀與耶儒對話
林子淳 | 論巴特思想中的觀念論痕跡與可能的出路
陳家富 & 賴品超 | 漢語神學對巴特神學的接受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公号邮箱:
编辑:Lea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