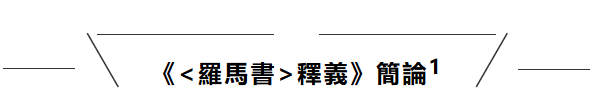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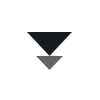


与其卷帙浩繁的、教义神学时期的代表作《教会教义学》不同,巴特在辩证神学时期的代表作《<罗马书>释义》对普通读者来说,其影响之深远可名列前茅。《<罗马书>释义》初版在瑞士印行,第二版则在德国印行。“我面对的基本上只是主题之谜,而不再是文献之谜。”巴特曾在第二版序言(XIX)中如是说。这体现出《<罗马书>释义》颇具争议的写作特色,并且在背后隐藏着巴特的如下追问:“忠实原文字句何用之有,如果这个忠实是以对话语的不忠为代价?”(509)。本文是张贤勇老师根据他为《<罗马书>释义》中译本所作导言改写而成。张老师认为,本书是一部巴特自抒胸臆的著作,应将其归为圣经注释中学术标准最高的神学、考订类。巴特以信仰批判宗教,用福音扬弃教会,从现实关照历史,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我们应寻求理解巴特,同时进而理解他所设法解明的上帝话语。
一般认为,《<罗马书>释义》从第一版到第二版,既体现了巴特从早期自由主义神学时期至中期辩证神学时期的思想断裂和变迁,也揭示出巴特神学强调上帝之上帝性和以基督论为中心一以贯之的根本神学进路。第二版更是充满表现主义的修辞手法和思想特色,不仅是一篇批判立场鲜明、反思意涵深厚的辩证神学作品,更是一部反映一战之后时代精神的文学佳作。
本文原载于:鄧紹光、赖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41-67。推送时已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推送,特此鸣谢!
//////////
一 《<羅馬書>釋義》的寫作
卡爾·巴特(1886-1968)的代表作,一般首推《教會教義學》。巴特曾勸告過那些自以為是的批評家,要他們先去通讀了他包括《教會教義學》在內的著作,取得發言權,然後再下結論。2 可是,巴特孜孜不倦地寫了近四十年還沒完成的《教會教義學》,3 又有多少人有耐性看完呢?E. L. Mascall(E.L.穆司卡)就批評說,如此龐大的用以解釋上帝之道的神學,豈不是要嚇退或纏住讀者,讓他們讀不成上帝之道(此處指篇幅相對要小得多的《聖經》)?況且,巴特晚年對完成這部著作,似也意興闌珊。面對巴特浩瀚的著作之海,我們常人,大都也只能取一瓢飲。這種實情,巴特自己也清楚,因此,就有若干種教義學的綱要本和選萃本的問世。4

E. L. Mascall
巴特的成名作是《<羅馬書>釋義》。這書是巴特在瑞士阿爾高州的薩分維牧會期間寫成的。牧會十年間,巴特講了五百多篇道,每篇都經認真預備,寫出完整講章。主日證道外,他還負責主日學、堅振禮輔導班和探訪。5 他日後回憶說,到薩分維才首次意識到,改革宗教牧人員作為傳道人、教師和牧師的職責何等重大。此書初版,由瑞士一家小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在德國印行時,巴特已在哥廷根任教,有一些書評推波助瀾,此書的名聲愈來愈響。巴特此後的生涯,基本上是在四所大學度過:哥廷根(1921-1925)、明斯特(Münster,1925-1930)、波恩(1930-1935)、巴塞爾(1935-1962)。晚年,他在巴塞爾正式退休時,已年逾七十五周歲,仍老當益壯,退而不休,時常還要開講座、舉辦研討班。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巴特在巴塞爾家中安然去世。巴特執教幾十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在著述方面,巴特也大可以著作等身自豪,他生前發表的著作,已達六百多種。6 但是,就著作的影響深遠以及對普通讀者的入門便利而論,《<羅馬書>釋義》無疑名列前茅。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巴特開始寫作《<羅馬書>釋義》時,思想上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十九世紀以來德國文化基督教傳統的刺激。從大學時代起,他就一直崇尚、服膺施萊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開創的這一傳統,所以對他父親恪守的比較保守的傳統常思超越。他父親因病遽然去世,據傳他彌留之際的遺言,是「要緊的是愛主耶穌,而不是科學,也不是教育或批評。這需要同上帝有種實在的聯繫,為此我們必須向主上帝祈求。」這番話,對巴特當有不小的震動。隨後幾年中,巴特雖仍處在施萊馬赫等人的影響下,已開始反思自己走過的路。其次,宗教社會主義的影響。他對社會主義理念的認識,也有發展變化,從早年的滿懷擁護,到後來的有所分辨,這也同他這一時期開始遠離自由派神學路線有關。一九一一年,巴特在<耶穌基督與社會運動>(Jesus Christ und die soziale Bewegung)一文中宣稱:「耶穌就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就是當代的耶穌。」7 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他在題為「福音與社會主義」的講章中仍說:「我看社會主義的訴求是實踐福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我也相信離開福音他們無法實行。」可是,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卻寫到:「上帝的國就是上帝的國。……新耶路撒冷同新瑞士或革命的未來國度毫不相干……」第三,對注重《聖經》的改教運動神學傳統的復諦。作為一名普通的牧師,在證道中向信徒傳達甚麼樣的消息,這是巴特和圖尼森等年輕的教牧人員不斷面臨的現實問題。講解《聖經》固然不錯,但如何講解呢?巴特與年輕同工在牧會中,深覺學不敷用,決定在神學上提高自己。巴特一度想[重]讀康德,圖尼森則建議吃透黑格爾,結果都在研讀《聖經》中找到了出路。研經也是一條神學再思和反思之路,不是在「現代」神學的框架中來看《聖經》,而是敞開自己,誠信聆聽,讓《聖經》向自己說話。《<羅馬書>釋義》就是巴特在重讀《羅馬書》的過程中記錄下來的心得。

Heinrich Bullinger
促成這一變化的,自然還有其他的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巴特對昔日崇敬的德國老師在戰爭中的表現甚感不滿等等,8 但這些外在的因素,恰恰證明這一階段巴特經歷的思想危機,從根本上來講,是內在的。可是,巴特為甚麼偏偏選中《羅馬書》呢?其中也有原因。首先,巴特的希臘文掌握得比較好,研讀原文《聖經》從《新約》入手自然更方便些。其次,《羅馬書》在《新約》中的地位很特別。有人這樣說過:「《羅馬書》在基督教歷史上所起的作用,表明它是保羅著作——若不說整部《新約》——中最重要的一部……事實上,通過檢視歷代對《羅馬書》的闡釋方法,幾乎可以寫出基督神學史。」9 其實,歷代不少人寫《羅馬書》注釋,也不單是因為此書在保羅著作中,甚至整部《新約聖經》中,屬教義結構比較完備者,可以據之構造《羅馬書》中的保羅神學,還因為「此書是一部各人可以從中自覓教義、並且同樣能夠找到自己教義的著作。」巴特的外祖母是十六世紀蘇黎世改教家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的後代,像路德、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一樣,布林格也講過《羅馬書》。10 巴特的同代人中,最早歡呼《<羅馬書>釋義》初版問世的布魯納(Emil Brunner,1889-1966)也好,一開始對巴特此書下嚴厲批評的K. L.史密特(Karl Ludwig Schmidt)也好,甚至同巴特關係一直很好的威廉·陸迪(W. Lüthi),後來都分別出版過各自的《羅馬書》注釋。巴特寫作《<羅馬書>釋義》之前,他的老師和長輩中,已有不少人出版過《羅馬書》注釋,比如席臘特(Adolf Schlatter)和庫特(Hermann Kutter, 1863-193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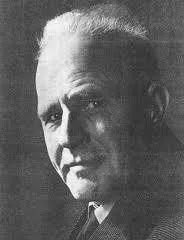
Emil Brun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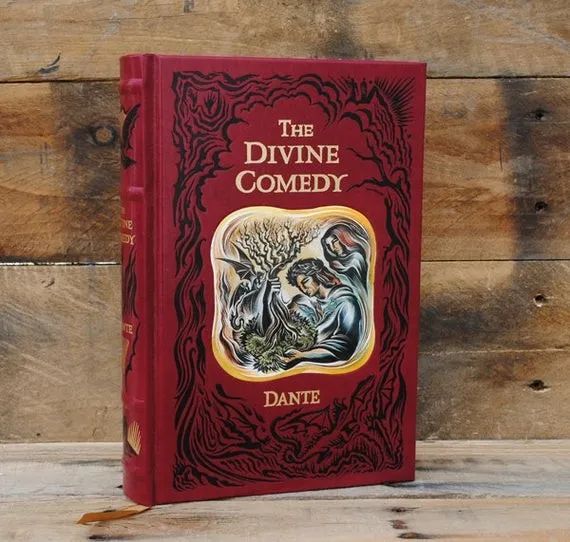
The Divine Comedy

二 《<羅馬書>釋義》的特色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近年推出的《<羅馬書>釋義》中文譯本,據德文本修訂版(第二版)譯出。13 據巴特自己講,第二版完全是新寫的,細節暫不說, 就是比較一下前後兩版的綱目,也會發現改動確實挺大。兩版大體結構相同,都分十六章,但第二版除去一首(第一章前半部)一尾(第十五至十六章)保持初版的章節名稱,其餘或多或少都經改寫,改動主要有三:第一類純屬德文語言修辭方面的;第二類是明確表達初版中比較含混的詞句;第三類則牽涉到實質性內容的改變,在討論巴特思想發展過程時,尤須注意這類變化。14
從初版問世到推出全面修訂的第二版,其間三年不到。從初版到二版,巴特思想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轉折,或說思想發生了一個飛躍,人生道路也有所改變:從「鄉村小教會的牧師」成為「大學神學系的教授」。15所以,現在一般人評論巴特《<羅馬書>釋義》,多是依據第二版立論的,對於我們瞭解巴特後來的神學思想,二版當然顯得更為重要。巴特自己在<再版前言>裏說:「再版和初版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應由拙著本身作出詳盡的回答,而這類問題往往是無聲的。奇怪的是批評界竟然對本書初版的真正缺陷一無所知……」(XIII)事實上,巴特將初版推倒重寫,已經表明對此書初版缺陷的自覺超越,雖然日後他沒有將對初版的不滿意之處和盤托出。
在我看來,巴特《<羅馬書>釋義》是部自抒胸臆的著作。《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評宋劉敞《七經小傳》說:「宋人說經,毅然自異於先儒,實自敞始,遂開一代之風氣。然敞學有根柢,故能自為一家之言。」移來考鏡巴特的《<羅馬書>釋義》在現代解經史上的地位,大概雖不中亦不遠。西方歷代的《聖經》考釋,無異汗牛充棟,就是最近十年間的新着,數量上也得超過《皇清經解》正續編的許多倍。東西方的《聖經》注釋(Commentaries),數量雖大,基本可分三類:神學、考訂類;述義、教牧類;蒙引、靈修類。16 第一類,從學術標準上看,應屬最高,這類注釋主要根據原文,在不同古代抄本、譯本、異讀和詮釋之間,常考訂異同、別白得失,著者一般提供自己的《聖經》譯文,以明權衡取捨。這種注釋的讀者,大都是神學教授和《聖經》學者。第二類的讀者,主要是教會裏面的教牧人員以及研讀神學的學生,這類注釋有時涉及原文字義,但對歷史上互殊的眾說,一般不作過多的辯駁,而是依據久孚的定論,對教義作些引申解釋,可作查經和避證道之助。第三類注釋,篇幅一般不大,但最為暢行,其特點是提供各卷經文的背景材料,依據若干種譯本,疏解經文的難點,適合普通讀者的讀經需要。三類中,有時會有交叉和重疊。不過,總的來說,在漢語《聖經》注釋方面,真正體現《聖經》研究學術水準的第一類,包括中文的創作以及從西文翻譯的,似還相當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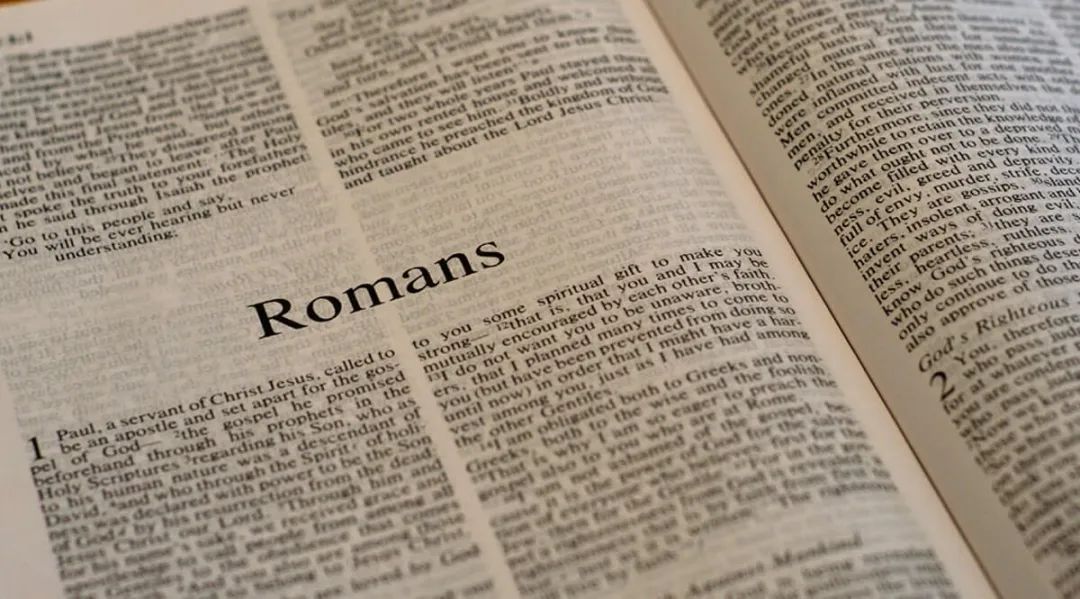
那麼,巴特自抒胸臆的《<羅馬書>釋義》,應當歸入哪一類呢?我以為當列入第一類。但這種看法是可以爭議的,而當年恰恰是這種爭議,使《<羅馬書>釋義》的聲譽鵲起。按巴特初版前言中的話 ,「這本書是帶着發現者的喜悅寫成的,保羅洪亮的聲音對我來說過去是全新的,現在還是全新的,恐怕對某些人來說也是全新的。」(頁XII)《<羅馬書>釋義》初版問世後,學院派的《新約》教授往往批評作者的別出心裁或「自抒胸臆」,也即認為它新得出格,既非傳統、嚴格意義上的《聖經》注釋,也沒遵循嚴謹的歷史—考證方法。對此,巴特有所答覆。第一,他明確表示:歷史-考證的解經方法,誠然是為理解所作的準備,但在這一方法與古老的靈感說之間,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因「後者的道理更偉大、更深刻、更重要」,「它揭示了理解活動本身」(<初版前言>XI)。其次,他在第二版前言中也坦陳:「作為理解者,我必須深人到這樣的地步:我面對的基本上只是主題之謎,而不再是文獻之謎。」(XIX)第三,巴特當年在馬堡師從的於利歇爾(Adolf Jülicher)教授,為當時《新約》研究泰斗,嚴守《聖經》學者的家法,用巴特的話說,「急於將我趕到實踐神學這片平緩的河穀草地上去,他希望我不要附上校勘注釋,而我則沒有完全如其所願。有些段落我認為必須避開大多數學者必定手持的繩套,這時我才作校勘注釋。而對某些自己顯然不甚了了的東西我就沒有插嘴。」(XXV)巴特這裏謝本師的態度也很明顯,他對校勘注釋這類《聖經》學者的看家本領並不外行,雖然自己側重挖掘《羅馬書》的神學思想,但並沒無視《聖經》研究的成果而橫生別解。於利歇爾的看法和用意,也十分清楚,在他看來,昔日學生巴特的這本注釋,算不上第一類的注釋,神學和學術工夫欠佳,最多只能歸入第二類的注釋中去。平心而論,此書初版寫作對象既非神學教授,也就無須仿傚神學教授的寫法;而且這是巴特自抒胸臆的神學著作,硬將之套入教牧或靈修類,自然也不妥當。在巴特看來,於利歇爾等《新約》學者,頗有些死於句下的味道,他打心眼裏就不佩服。他的釋義寫作接近尾聲時,曾給馬堡的老師臘德(Martin Rade)去過一封信,其中提到自己正要完成的這本書,並稱這本書實非於利歇爾、尼波嘎爾(Niebergall)輩所能想見。17

Adolf Jülicher
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無論初版二版,在解經方面都受到不少批評,有些批評確能搔到癢處。巴特不斷修訂此書,一方面也反映出這種現實狀況。至於他後來沒在修訂版基礎上再動大手術,實有多方面原因,例如:大學教學任務繁忙,開始教義神學的寫作計畫,出版《<羅馬書>釋義》目的已達等等。18 日後,巴特還講過《以弗所書》和《約翰福音》等,《聖經》研究同教義神學研究,在他實相輔相成。巴特對《羅馬書》並沒忘懷。四十年代初,巴特在巴塞爾成人教育學院開設過一個學期的《羅馬書》,留有一份相當完整的講義。19 但是無論是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還是在四十年代初的《<羅馬書>講義》,甚至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巴特對《羅馬書》某些經文的解釋,雖遭他人的嚴厲批評,他仍然堅持,深信自己的理解不錯。這裏可以舉《羅馬書》十三章1-7節為例。這可能是對各國政府來說在整本《聖經》裏最中聽的經文之一,也是讓相當多的基督徒頗感困惑的經文。
有意思的是,巴特將這段經文(再加上羅12:21)放在「巨大的消極可能性」標題下(500-571),而且特別告誡說,這段經文當與整本《羅馬書》聯繫起來理解,對全書無把握的人,也不可能讀懂這段經文。巴特從《羅馬書》十二章2節的「心意更新而變化」說起,提到個人不得不面對的國家、法律、教會、社會等權勢,他們固然要求承認和服從,我們則須思忖:究竟應滿足,還是當拒絕其要求?「選擇前者,顯然就是選擇了合法原則。選擇後者,顯然就是選擇了革命原則。」(502)世人難道真的只能依違於合法性原則與革命性原則之間麼?巴特的答案,頗有些出人意料:[非革命」與[非合法」。巴特單刀直入破題:
巨大的消極可能性!說[巨大」,是因為在此不僅僅是面對近處的人在個別的態度和舉動中進行表態,而是面對個人極近於「全」的「多」在總體立場上進行表態。說「消極」,是因為這種表態的動機和意義確實不是「無條件接納國家為道德力量」(Jülicher),也不是「為所有國家權力的神性本原大唱讚歌」(Wernle),而是,即使在此也是對人的抨擊,抨擊人的「志氣高大」(羅12:16),抨擊人普羅米修斯式狂傲。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人類的種種秩序,不是必須在某一種此類秩序中實施的人類行為(「公民義務」,Jülicher), 而是人不破壞這些秩序,是人面對這些秩序的無為。(502)
接着,巴特掉轉頭談何為現存秩序和統治者:「現存秩序意味着:人又虛偽地認為已經澄清了自己本身的問題;人又怯懦地縮回到安全地帶,不敢直面自己存在的奧秘;人又愚蠢地祈求稍緩片刻再對自己執行死刑。」(503)他認為,從約翰《啟示錄》時代起到尼采,從再洗禮派到安那其主義者,並非反對政府裏的敗壞,而是向統治者存在的權力提出根本性挑戰。「法權至高,邪惡至大。」20 因為「人沒有在別人面前客觀地擁有公義的權利,他給自己披上的「客觀性」外袍愈是寬大,他給別人造成的不義就愈是嚴重。」(504)巴特質疑道:「哪種合法性的根源不是非法的?」巴特矛頭所向不僅是反動派,也同時針對革命者:「說到「為惡所勝」,革命者比起保守者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帶着「不」字的他更逼近上帝。……惡不是對惡的回答。受到現在秩序傷害的正義感不會因與現存秩序決裂而得以重建。「要以善勝惡」!」(506;參見503、505)他最後總結說:「要認識上帝乃是制服現存不義的勝利者。這便是回歸的意義所在。這便是《羅馬書》第十三章的意義所在。」(506)至此,我們才明白他說的「非革命」與「非合法」究竟意味着甚麼。

Oscar Cullmann
現代解經家對巴特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解,有所批評。《羅馬書》十三章1節中exousia(和合本譯作「在上有權柄的」、「掌權的」)何所指?21 眾說紛紜。改教家中梅蘭希頓(Philip Melanchthon)和加爾文認為,是指維護公民權益的行政長官(civil magistrates);而馬丁·路德等人將之同時理解成[靈性上的領袖」(spiritual rulers)和「世俗的統治者」(secular princes);巴塞爾當代聖經學者庫爾曼(Oscar Cullmann,1902-1999) 則主張,exousia指的是[國家政府背後不可是的屬天靈力」,甚至有政柄和屬天靈力雙重含義。22 類似庫爾曼的解法,據Fitzmyer(費茨瑪)說,Dibelius(迪貝留斯)早先用過,後來放棄,巴特等人則傾向於這種解釋。應當指出,在《<羅馬書>釋義》中,巴特並沒有將exousia本身看作屬天的靈力,23 他只是在解釋《羅馬書》十三章6節時說,恰恰是「官員、官府、現存制度的官方代表」這些人作神的差役,但是,「他們全部的存在,全部的權力以及他們在你們面前獲得辯護這全部古怪現象都在大聲宣告一點:人的不義和作為目標的上帝世界。」(517)此前,巴特明確說過,對掌權者的順服,在倫理上純屬消極概念,卻是相信上帝的人避免以惡報惡、為惡所勝的不二法門,最激進的革命不只是反叛,而且本身也是「對現存事物的辯護和強化。」24 所以,在巴特看來,反對叛逆,並不意味着擁護現存秩序,信仰上帝的人須注意的是,「叛逆者一不留神倦入的爭執是上帝的秩序和現存的秩序之間的爭執。」接着,巴特列出了對這段《羅馬書》解釋最具創意的一個公式:
若將現存的秩序如國家、教會、法律、社會、家庭等等的總體設為:(a b c d)
將上帝的本原秩序對這總體的揚棄設為括弧前的負號:
-(+a +b +c +d)
那麼顯然,革命作為歷史行為即使再徹底,也不能視為在括弧前對人類秩序的總體實行全面揚棄的神性負號,而是充其量只能視為這樣一種可能成功的嘗試:揚棄括弧內的現存秩序作為現存秩序擁有的人性正號。於是得出以下公式:
-(-a -b -c -d)。
在這一公式中必須注意,括弧前巨大的神性負號很快就會出乎我們意料地將括弧內人擅自以革命方式搶先改設的負號重新變成正號。換言之,鑒於神人之間的局面,有事物經革命的演算法在崩潰之後會以新的形式捲土重來,而且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508)
應當承認,像這一類至今讀來仍覺神采飛揚的文字,於利歇爾之流當然無法想見,斤斤於文獻之謎者,也難以認同這種法度中翻出新意的《聖經》神學。可是,巴特這本釋義的特色,恰恰是要追問:「忠實原文字句何用之有,如果這種忠實是以對話語的不忠實為代價?」(509)25單憑這一點,我們就不難體會《<羅馬書>釋義》對現代《聖經》研究的貢獻是何等的實在。

三 《<羅馬書>釋義》的神學要點
前面為了說明《<羅馬書>釋義》的特色,引入了對《羅馬書》十三章1-7節的分析,這種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對《聖經》原文個別詞句的理解,而牽涉到對《<羅馬書>釋義》中所反映的巴特神學思想的闡述。讀者至此已不難領會巴特對政教關係的看法要點。眼下不能就這個問題展開深入探討,不僅限於篇幅,前已點到為止即可,更因巴特對政教關係的思考,並非《<羅馬書>釋義》的重點。關於信仰與政治或者教會與國家的關係,他後來另有文章詳細論述過。26 下麵想從神學思想方面,進一步探討《<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所傳的若干關鍵資訊。
1 以信仰批判宗教 讀完全書,讀者會有一種十分強烈的印象,就是覺得作者對宗教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不錯,事實正是如此。巴特所用批判的武器,恰恰是信仰,或者像他所譯的「忠信」(希臘文pistis:德文Trecu Gottes)而不是不信,更不是無神。27 在談到《羅馬書》的主題時,巴特寫道:「無論說「因上帝之忠信」還是說「因人類之忠信」,其實所指相同,其信為一。……人類的信仰是對上帝之「不!」表示接受的一種敬畏,是以空穴為指向的意志,是激動地在否定中堅持不懈。在上帝的忠信和人類的信仰相會之處,人的義顯現出來了,義人得生了。」(18)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標誌,在巴特看來,只能是在基督裏,此外同上帝建立的關係,其「中樞就是奴隸的不義。」(21)又說如有一種信仰不滿足於耶穌基督復活以後的空墳墓,那麼這種信仰實是非信仰。(參見35)28 巴特眼中的宗教,正是建立在對上帝的誤解之上的「人性之義」——
因為這種誤解……於是,典型的「宗教的」(特殊的、與一般生活相悖的)生活產生了;它帶有一種浪漫的不可信性;在蔑梘它的人面前,無論怎樣能言善辯都不能使它變得可信。於是,先知的神性之義演變成了法利賽人的人性之義,然而人性之義就意味着不虔不義。……暫時,演變成了法利賽人的先知還在愈來愈高地建造他的巴比塔——貪得無厭地向上帝提要求,自信對上帝有把握,享受着上帝;然而,在他的日復一日的生活這層簾幕後面已經理伏着上帝忿怒和正義宣判的永恆之日。他是身居高位,但已墜落下來。他是上帝之友,但已成了上帝最痛恨的敵人。他是義者,但已受到正義的審判。(39)
自以為義者,無論顯得多麼虔誠,都是對上帝的僭越,是上帝之國的絆腳石(53)。歷代多的是為上帝大發熱心的人,他們誤以為自己能為上帝作些甚麼,結果卻喪失了唯一得救的機會。(64)在歷史文化領域,煞有介事的宗教也帶來嚴重的後果。(272)巴特認為,強調世人在上帝面前的無能為力並非否定人類的積極方面,因為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們的主題、歷史的真正主題既非否定亦非肯定人本身,而是認識人與他所不是的上帝、與他永恆的關係中的疑難性」(67)另一方面,宗教可能性的範圍中也存在着疑難性,人完全受這疑難性的支配;同時,「在宗教的可能性中,無「服從」、「復活」、「上帝」可言……」(231)因為「宗教的意義在於死亡」,(261)還「證明罪孽統治這個世界上的這些人的力量:連宗教的人也是罪人,恰恰是宗教的人更是罪人。」(261)巴特的宗教觀後來或稍有變化,他的信仰觀卻始終不曾動搖。
2 用福音揚棄教會 與宗教批判相關聯的,是本書中也頗為突出的巴特獨特的教會觀。《<羅馬書>釋義》中巴特對教會看法的表現(尤其是9-11章),雖不像後來《教會教義學》時期那麼系統和完整,也已相當清晰了。29 這一時期,他基本上把教會同宗教聯繫起來考察,而用來衡量宗教與教會的,仍然是信仰。他認為:「信仰乃是一切宗教的真理,乃是一切宗教純粹的和彼岸的開端。……無論在甚麼地方,信仰都不會成為某種生活史、宗教史、教會史或救贖史中的一個階段。」(111)在談到亞伯拉罕因信稱義時,巴特解釋說:
亞伯拉罕不是作為宗教意義上有別於外邦人的上帝之友,而是作為未行割禮的信仰者接受割禮的記號的。他不是作為宗教意義上的篤信者,而是作為一個未經體驗便開始注意上帝的法庭和恩典的人成為「宗教個體」的。他不是作為在教會意義上適合於並奉召擔任神人之間的仲介者,而是作為未加入教會的局外人成為這一神人聯盟中的人的代表。……割禮、宗教和教會是指示性的標誌和見證,並非積極的內容;只要在其消極性和消亡性上理解和肯定割禮、宗教和教會,便是如此。(115)
把握外在性標誌和見證的人,很容易感到篤定滿足;而信仰卻是在危機中激發出來因為對拯救的信仰,正「產生於熙攘和雜亂,產生於未被拯救的世界侵襲到人內心深處的困惑和迷惘。」(143-144)而恰恰是教會,不是塵世,將基督釘在十字架上。(407、422等)
巴特對教會的批判,也是他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他一方面高舉對上帝(或者毋寧說對死亡復活之基督)的信仰,另一方面又傾向於祁克果、歐弗貝克和社會主義,要這樣一個人對宗教和教會的自我陶醉與麻木不仁視而不見、對身邊世人的苦情充耳不聞,又怎麼可能?因着對復活的基督的信仰,所以主的門徒不是信教者,而是蒙恩者(210,比較218關於使徒與教徒的區別)由於是個人直面上帝的認信,所以,恩典只能從上帝那裏直接領受,無法在集體主義(哪怕以基督的名義結成的群體)中吃大鍋飯:「恩典意味着:上帝將人的存在作為一個整體歸於自己,為自己所有。恩典是上帝對一個不可分割的個人行使的權利。正因為恩典構成了個體的嚴重危機,所以恩典是個體全部此在和如此在中的真理。」(221)30 這種批判,以前也有人作過,《<羅馬書>釋義》中便反詰:「為甚麼他拉噶慈那樣,要求從毫無希望的教會和神學移居到略勝一籌的俗人世界中去?」(223)31 巴特認為,教會是同基督福音兩相對立的,大大小小的教會都在追求幻影(382)。
教會是多少稱得上是全面和果斷的嘗試:使神性人化、物化、暫時化、世俗化、實用化;這都是為了人的幸福,這些人的生活並非沒有上帝,但也沒有活生生的上帝(瞧瞧那些「宗教裁判長」!)一言以蔽之:教會嘗試使那些難以理解的、但也不可避免的道變得易於理解。……福音意味着揚棄教會,正如教會意味着揚棄福音。(346)
「讓教會成為教會」,可以概括他後來對教會的思考,這也同他告別孤獨大師祁克果有關。愛之深者責之切,即便在批判,他對教會的感情,也決不比張口閉口讚美教會者淡漠。對自外於教會的人,巴特則說,聆聴和宣告福音者,不會站在教會旁無動於衷,而是設身處地以投入的態度站在教會之中(348),因為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教會,雖說從教會出發又無法前行。(352)教會應悔改,真正成為神跡的教會、信仰的教會、上帝的教會。(387)巴特對教會持雙重性的理解,因此區別以掃的教會和雅各的教會。(參見356以下)
提到巴特的教會觀,我想起樁往事。巴特和布魯納是二十世紀瑞士改革宗教會中最著名的兩位神學家、兩人有幾十年的的友誼,私交一直不錯,雖然巴特寫過那封布魯納當頭棒喝的《斯乎不可!——答布魯納》(Nein!Antwort an Emil Brunner, 1934),戰後兩人多次見面,彼此的成見,不見得比各自門弟子間的門戶之見更深。赫舍林克(I.John Hesselink)一九六〇年拍攝的兩人合影,流傳很廣,32 因為這張照片確實相當鮮明地突出了巴特和布魯納的個性。巴特同布魯納的神學思想在早年相當合拍,後來分歧不小,兩人晚年在教會觀問題上差別尤其明顯。33 巴特在開始撰寫《教會教義學》時,思想已有較大轉變。34 布魯納早年在青年會服事過,五十年代初在日本講學兩年,其間深受日本「無教會運動」的影響,著文演講,向西方極力鼓吹這種教會的改革,對當時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聖公會人士把持信仰與聖事講壇的情況大為不滿。然而,頗為奇怪的是,在世界範圍內的福音派圈子內,巴特似乎遠不如布魯納吃香,這大概同巴特對基要派的抨擊不遺餘力有關。以前有人討論「文化基督徒」問題,最後直接引用了布魯納《基督教的上帝論》(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英文版的一段文字,35 大概想藉重布魯納的權威,來說明神學同教會密不可分的關係,卻不一定很清楚布魯納其實並不能隨便對付,其他的暫且不說,就引文中的「教義學」和「教會」兩個詞而言,是並不能因為已將之放入自己的籃子裏,就都可當作菜的。漢語神學界普遍鑒別力的提高,或當有賴於日後「比較教義學」的引入。36
3 從現實關照歷史 我們還應當進一步思考的,是巴特在此書中闡述的對所處時代及其危機的認識。在論到歷史與現實的時候,巴特說:「歷史可以有一種效用。過去可以和現實交談。因為在以往和當前之中存在着共時性,共時性治癒了以往的啞和當前的聾,使它們能開口和聽見。」(132)他甚至說:要理解《羅馬書》,就應讀各種世俗的文獻,尤其是報紙。「因為,思想如果是真實的思想,就是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思想。……正是作為辯證的思想,思想才符合它的目的,即探尋生活的深度、關聯和現實,導致對生活意義的澄悟,使賦予生活意義成為可能。」(448)與此相關的,還有他對《羅馬書》十二章11節的譯解,他主張應讀成「服務於時代」而不是通過所譯的「常常服侍主」。巴特開始寫作此書時,歐洲還在連天烽火中,所以對於戰爭的問題,他特別作了闡述。(494以下)直面危機,洞察歷史,不忘恩典就是出死入生的危機。(225,參見553-554)
巴特一生中一直都保持着注重現實的特點,無論是他後來在德國擔任神學教授時參與認信教會的構建,還是總結十九世紀基督教神學思想,37那都是關心當代現實的表現。從《<羅馬書>釋義》來說,它不是一本躲在書齋裏的(新約)學者的《聖經》注釋,也不是一個得過且過的鄉村牧人的消閒作品,而是一個視野寬闊,具有很強的時代使命感和教會責任感的基督徒聆聽上帝之道後對時代發出的呐喊。在這樣的呐喊聲中,我們自然也能聽出巴特其他的神學見解,例如對原罪論(參見162頁以下)、基督論(148頁以下等處)、預定論(163)、人論(174等處)、恩典論(180;第六章,特別是182-185,221以下)的看法以及巴特倫理學思想的表述,——這些我們在閱讀原著時不難體會,——但針對我們今天的現實來說,這裏提到的三點,仍然是特別清晰、未曾陳舊的資訊。注釋《羅馬書》的人多矣,包括巴特當年的老師於利歇爾,但其中大部分人的著作,今又安在?把《聖經》研究只當作一種技術性的學術工作,那麼這種工作被人超越就是早晚的事。巴特的《<羅馬書>釋義》不以版本考證和字句校勘見長,而是以神學思想性的詮釋成一家之言,結果是至今讀者不斷,他人難以超越。其中的道理,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四 巴特神學的方法論意義
巴特是位堅定獻身神學的學者,他說:「我從未想過要去從事神學之外的工作,問題是在於何種神學?」(《<羅馬書>釋義》<再版前言>XIV)他也常常批評將神學研究哲學化的傾向,但這決不意味着他對哲學一竅不通,或者說他自己絲毫不受哲學的影響。恰恰相反,他若沒有早年對康德等人的迷戀,以及隨後對祁克果等人思想的開發,也就不會有日後《聖經》和信仰所作的宗教和哲學批判。巴特的神學著作,一般來說並非系統神學,他不講究體系井然,即使在結構上特別精心結撰的《教會教義書》中,自相抵牾、前後矛盾之處也不一而足;這也是他晚年的自評。38 他在一封信(1060年3月5日)中對女婿說,他雖然講授並撰寫「教義學」,但從根本上來說遠非教條式的人。39 巴特的這種特點,在《<羅馬書>釋義》中也反映得相當明顯。
我在前面說過,《<羅馬書>釋義》是巴特自抒胸臆的著作,同時示意:這種著作只有在學有根底者才比較牢靠,否則,會偏向癡人說夢。《<羅馬書>釋義》的自我抒發性成份,在巴特一生的神學論述——包括 《教會教義學》——中從未缺席。作為出色的教義神學家(或謂同布魯納相比,更有系統),40 巴特對《聖經》的注重,也少有與其媲美者;論者甚至覺得巴特有極端聖經本本主義(excessive biblicism)的嫌疑。這一點對漢語神學界來說,格外值得重視。絕大多數漢語神學家所據以生存的土壤,絲毫不缺乏《聖經》養料,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就有天然的、牢靠的《聖經》根基。以《聖經》為本本,將串珠經文當作神學論述、沒受過且不屑於接受《聖經》考證學的訓練、喜歡對自己「顯然不甚了了的東西」插嘴,難道不是漢語神學界常見的景觀?這些方面,《聖經》學者所受出格的誘惑,當遠小於系統神學家或教會史學家所受的誘惑。我們受誘惑犯過失時,巴特只能作提醒對照的鏡子,而不是我們推卸責任的支撐依據。我們大多數人所受的神學教育,與巴特當日所受,已不能同日而語。家學淵源,題目過窄,可以不談。但是,在大規模工業生產影響下,今日的神學教育,無論中外,都架設起了標準化的流水線,這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如此普及神學教育,是好是糟,是進步還是墮落,是向本真復歸還是被世俗異化,大概也是見仁見智。據我觀察,師(傅)(門)徒關係蛻變成(老)師(學)生關係,言傳身教大體已是罕見古風,老師不知學生姓甚名誰,平時相見如同路人,不知不覺已成時尚。老師為完成課時而教,學生為取得學分而學,至少已不是個別現象。同當年巴特、布魯納、圖尼森輩拿得起、放得下——進大學講課、入堂會牧養,——相比,今日的神學畢業生多的是高不成低不就。
神學研究不僅需要實踐,也需要思考。標準化的流水線製造不出具有個性的通用人材,也培養不出普遍認可的專家。當年批評巴特的於利歇爾、尼波嘎爾等人,在各自專業中稱專家至少沒問題,反觀今日的神學教授們,可能不少連專家的底線都達不到。豈不可歎!漢語神學界的情況並不比歐美更好,比較而言,天主教還略勝一籌。中國大陸基督教的學術工作不提也罷,——要提也多是細線串豆腐!——香港的情形也不容樂觀,記得《道風》登載過兩位《新約》教授的批評與反批評,41 讀後覺得在不太沉重的書評後面有顆沉重的心。
關於巴特神學研究方法論的評價,雖然早有人覺察並表示看法(例如潘和華[Dietrich Bonhoetffer]*),但並沒引起足夠重視。直到巴特的學生以及教授傳人奧特(Heinrich Ott)發表了《現實與信仰》第一卷《潘和華的神學遺產》42之後,才引起較多神學界人士的注意。奧特在書中是以敘述潘和華與巴特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為契機,從方法論上來批評巴特神學的。43 他認為,巴特《教會教義學》的方法無非是從基督論的系統原理演繹出其他一切,在基督論上巴特又不像潘和華為奧秘留有餘地,而最關鍵的缺點,是巴特沒有採納阿奎那《神學大全》中那樣的對話(Quaestio)方法來展開神學論述,雖然世人因《教會教義學》的內容廣博的特點,常將它同《神學大全》相提並論。在方法論上,奧特是同巴特分手的。
《教會教義學》誠然像《<羅馬書>釋義》一樣含有自我抒發性成份(奧特的批評是個旁證),巴特卻也並不像有人描寫的那樣,駕駛一部「神學推土機」(a theological bulldozer)旁若無人朝前開。44 巴特《教會教義學》之所以寫得篇幅龐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其說是自律不夠,不如說是過於在乎他人,因為他確實是在立論過程中批駁一切已顯未顯的謬論,實際上也是在同前人、時人,以及後人進行着「隱形對話」。所以,認為巴特不懂對話,似也太過。巴特遠不是「孤獨的思想者」,他關注現實,就不能不同現實中的人物對話,而且為了現實的緣故,他研究歷史,因此自然要同既往的人物及傳統對話。在這些方面,巴特還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榜樣。我們先看傳統。關於巴特與歐洲思想文化傳統的關係,已有不少人作過探索。巴特去世一年半之後,哥廷根大學的教義史專家Ernst Wolf(恩斯特·沃爾夫)就指出,巴特的神學應是經典神學(klassiche Theologie),巴特的著作應當享有魏瑪版路德文集那樣的地位,遂有編訂出版巴特新文集(GA)之議。這是從對後人來講的角度所說的經典神學,從繼承前人的角度同樣可以稱之為經典神學,且不說巴特代表作《教會教義學》是一種「神學大全」式的建構 ,他的其他著作也表明他接受的思想傳統之宏豐。從《<羅馬書>釋義》來看,或許可以藉用巴特書中一起提到的幾個人,來說明他思想所受的影響:「加爾文的無情、祁克果辯證的勇氣、歐弗貝克的敬畏、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對永恆的渴望、布龍哈特的希望……」(255)仔細分析巴特的思想,就無法忽視祁克果的影響。巴特對祁克果的解說,也是用生命同祁克果的精神的對話。

Søren Kierkegaard
另外一個巴特終生與之對話的傳統人物,是施萊馬赫。施萊馬赫早年是巴特崇敬的目標,巴特中年以後同他分手,卻告而不別,施氏仍是他超越的目標。一九一二年,他稱施氏為「一場新宗教改革的英明領袖。」巴特早年對施萊馬赫的興趣,一直持續到晚年,一九六八年他稱,神學家不僅應當研究施萊馬赫,還須帶有極大的敬意研究他。有人因此說,巴特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還是論施氏的,而學術界一般公認,巴特是施萊馬赫以來基督(新)教中最重要的神學家。45 此外,對巴特思想影響較大的人物,還有一些,比如音樂家莫扎特。說到巴特同當代人的對話和交流,例子就不勝枚舉了。這裏舉一個特別的例子。巴特對潘和華的影響,是神學界比較熟悉的,但潘和華對巴特的影響呢?從常理推論,應當會有,雖然查無實據。在芝加哥指導我讀基督教倫理學的一位教授,曾指出巴特有名的「關係類比」,係藉自潘和華的《創世紀》一至三章注程中對「神的形象」解說。46 實情果真如此,還是其間也摻雜着信義宗神學家彼此維護的想法,尚難斷定。但毫無疑問的是,巴特與潘和華的相交,包括神學思想上的交鋒與對話。當然,我們仍可以說,《教會教義學》中的論述方式,是論戰性而不是對話性的,但這時所說的對話,概念上已狹隘化了。
理解巴特這樣人物的思想其實不易。歐美文化傳統相近,交流起來尚且不能無隔,巴特真要進入漢語華土,困難更在德語神舉界之外的神學同行對他的理解與接納之上。47 但是,雖然困難,還是要設法理解。《<羅馬書>釋義》中文譯本的出版,是尋求理解的良好開端。巴特代表作《教會教義學》的中譯可能會遙遙無期;據我所知,至少在東亞,就巴特這部巨著的翻譯而言,日本和韓國已遠遠走在我們前面。當然,翻譯巴特並不是我們的目的,尋求理解,理解巴特,同時並進而理解他所設法解明的上帝的話語,才是我們應當特別關注的。在這點上,巴特頗有自知之明。他晚年多次提到過一首兒童讚美詩在自己神學視野中的地位。這不是簡單的返老還童或返璞歸真,而是曾經滄海之後的一種洞察和徹悟,若做比較,我想《神學大全》的作者托馬斯·阿奎那晚年棄稿封筆的境界,庶幾近之,雖然巴特臨終時桌上還攤着一篇未寫完的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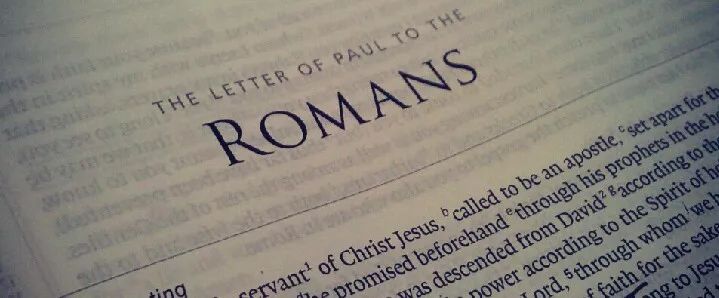
往期文章
瞿旭彤|普遍與特殊:從蒂利希與巴特一九二三年的爭論看兩人神學立場與進路的差異
关注我们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