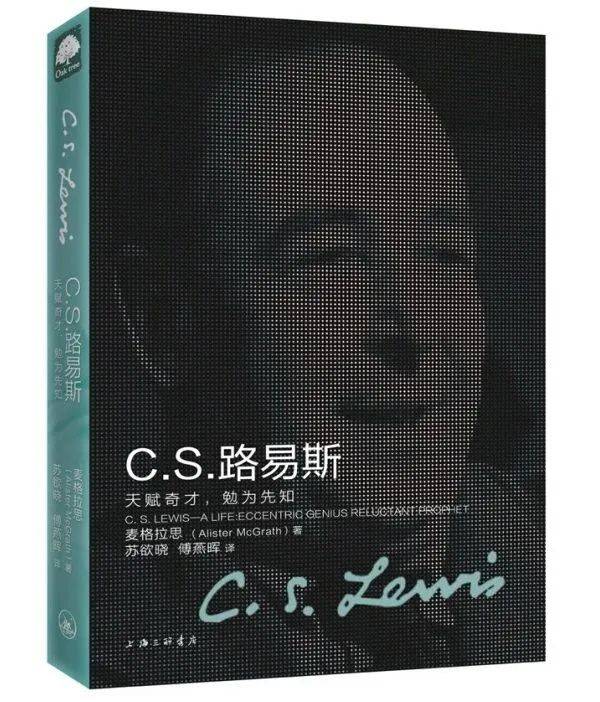路易斯对于文学该如何进入、如何理解的认识,与当代文学理论的主流观点相去甚远。就路易斯而言,阅读文学——尤其是阅读更古老的文学——对基于“时代势利症”之上的某些欠成熟的判断是一桩重要的挑战。欧文·巴菲尔德已经教导过路易斯,要对那些宣称当下必然较过去优越的人心存怀疑。
路易斯在《论读古书》(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1944)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路易斯在该文中论道,熟悉过往的文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立足点,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拉开一段批评性的距离。这样,他们就得以“用自己合宜的眼光去看待当下的各种争议”。
阅读古书能让“清新的历世历代的海风不断吹拂我们的头脑”,从而使我们免于成为“时代精神”的被动俘虏。
“新书尚处试验阶段,一个外行人没有资格对它进行判断。”既然我们无法阅读未来的文学,我们起码能阅读过往的文学,它对当下的终极权威构成一种强有力的隐含的挑战,我们起码要认识这一点。因为或迟或早,当下总要变成过去,而当下观念所具有的不证自明的权威也将被腐蚀——除非这权威是建基于这些观念本身所固有的美德上,而不仅仅是其年代所处的位置。
路易斯指出,当人们意识到20世纪新兴的各种意识形态时,那些“在许多地方生活过的人”就不容易被“他本村本土的当地错谬”所欺骗。路易斯宣告,学者即是“在许多时代生活过的”人,因此能够挑战那种下意识地认为当下的判断与潮流具有内在决定性的先入之见:
我们需要对过去有一种密切的认识。并不是过去有什么魔力所在,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研究未来,但又需要某种东西作为现在的参照,来提醒我们,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假设,许多在未蒙教化的人看来确凿无疑的东西,无非只是当时的风潮。
路易斯坚持认为,要理解古典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有必要“搁置大部分的回应,抛掉大部分的积习”,而这些积习都要归因于“现代文学的阅读”——比如,不加怀疑地假定我们自己的处境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路易斯用了一个熟悉的文化典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出国旅行的英国游客,就像E.M.福斯特(E.M.Forster)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Room with a view, 1908)这类作品中不惜笔墨揶揄嘲讽的那些人。
路易斯叫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出国游历的英国人:他深信,自己的英国文化价值远远高过除自己之外的西欧的那些蛮夷之辈。他不是去搜寻当地文化,享受当地美食,容让自己的预设接受挑战,而是只跟其他的英国游客交往,执意要找到英国食物,看到他的“英国性”,把这个当作他不惜代价要去维护的东西。他就这样随身带着自己的“英国性”,“又将它原封不动地带回家”。
还有另一种游览异国的方式,与之相对应,也有另一种阅读早期文本的方式。这一次,旅游者吃着当地的食品,喝着当地的美酒,“以当地人的眼光而不是游客的眼光来观看异国”。路易斯论道,其结果是这位英国游客回到家中,“见识增长了,思考、感觉”的方式与从前不同了。他的旅行扩展了他的视野。
路易斯在此要说的是,文学提供给我们一套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它打开我们的眼睛,为价值判断与反思提供新的视角:
我自己的眼睛不够用,我还要透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在阅读伟大的文学时,我变成了一千个人,却同时还是我自己。就像希腊诗歌中的夜空,我用一千双眼睛去看,但看的人还是我自己。
对路易斯来说,文学帮助我们去“用他人的眼睛来看,用他人的想象来想象,除了用自己的心,同时还用他人的心一同去感觉”。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现实想象性的再现,从而挑战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观感。
因此,阅读文学即是潜在地让自身接受可能的改变:将我们自身敞开在新的思想面前,或者迫使我们重访那些我们一度以为理应拒绝的东西。恰如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在每一件天才的作品中,我们都认出了被我们拒绝的思想:它们又以某种令人陌生的威严回到我们面前。”
路易斯因而强调,文本影响我们,它也挑战我们。若一直坚持文本要符合我们的预设以及思维方式,那就等于强迫文本嵌入我们自制的模具中,从而剥夺了它更新、丰富或改变我们的任何机会。
阅读文学作品意味着“完全进入[其他人的]意见,从而也就是进入其他人的态度、感受和全副的体验中”。它意味着柏拉图所说的“心理教育”——一种“对灵魂的扩充”。
路易斯认为,所说的是什么,要比是谁说的更重要。他认为,构成文学“批评”的要素是领悟作者的意图、接受作品,以及由此经历到的一种内在的扩充。
我们看到,这个观点在他的《〈失乐园〉序》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篇文章十分精彩地呈现了弥尔顿史诗的背景,并详究其意义。
路易斯有力地论证了一点,即诗歌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诗人而是诗本身。剑桥学者E.M.W.梯利亚德(E.M.W.Tillyard, 1889~1962)则提出与此截然对立的观点。梯利亚德认为,《失乐园》“实际上说的是弥尔顿在写这首诗时真实的心灵状态”。
这就是30年代那场著名论争的缘起,它常被冠以“个人异端”(The Personal Heresy)之名。这场复杂的论争简而言之就是,路易斯赞成一种客观的或非个人化的观点,认为诗歌讲的是“在那里”的东西;而梯利亚德则捍卫一种主观的或个人化的观点,认为诗歌讲的是诗人内心的东西。路易斯后来将这个观点称作“主观主义的毒药”。
对路易斯而言,诗歌的运作不在于将注意力引向诗人,而是引向诗人之所见:“诗人不是一个要求我去看他的人;他是一个说‘朝那儿看’,并指向那儿的人。”诗人因而不是一处“场景”(spectacle),以供观看,而是“一副视镜”(set of spectacles),透过它可以观看事物。
诗人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以不同方式看事物的人,他指点的事物若非借他指点,我们或许就注意不到。或者还可以说,诗人不是一个要人朝向他去看(to be looked at)的人,而是一个要人透过他去看(to be looked through)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上述这一切:路易斯对文学阅读的理解是,它是一个想象及进入他者世界的过程,它有能力照亮我们真正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路易斯时常将自己奉献出来,为那些涉足于这趟朝圣之旅的人当旅途向导。
[本文摘编自麦格拉思《C.S.路易斯》,上海三联书店]
关联阅读
欢迎关注备用号:
↙ 点击阅读原文,进店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