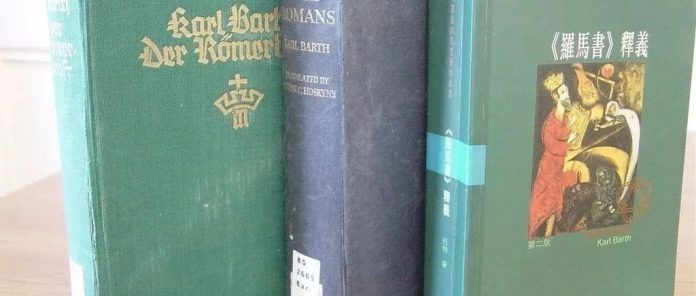编者按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聚焦于这部经典之作的神学百科全书性。在洪老师看来,巴特既批判倚重史学的释经学,又批判臣服于现代价值的系统神学、以及侧重策略与技术的实践神学。如此种种,导致福音神学教育陷入一种总体性的危机。 与之相对, 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展现出一种以神学家面对上帝时的生存奠基为定向的神学百科全书性,这意味着《圣经》所见证的、作为生命意义的基督复活要成为释经的目标、教义的基础、以及实践的聚焦。对数字化时代的神学人类学与终末论探索而言,巴特近百年前的这一批判性思考所蕴含的复调特征、透视主义和终末导向仍具有巨大价值和启发意义。
本文原载于《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2018年第26期。推送时已获作者本人和发表单位授权,特此感谢洪亮老师和《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编辑部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引言:《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对话结构的三个层面
在过去的七年中,针对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文本校勘与研究迈入一个崭新階段。2010年,经过荷兰学者Cornelis van der Kooi和Katja Tolstaja 的共同校勘,瑞士苏黎世神学出版社正式推出《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学术考证版[1],位列卡尔·巴特全集出版计划第四十七卷。在此前后,学界 (尤其是德语学界) 对这部二十世纪神学经典的历史研究日益聚焦于其文本内在的对话结构[2]。与此相对应,瑞士实践神学家图爱森 (Eduard Thurneysen) 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文本形成史的意义[3]及其对辩证神学运动的理论贡献[4]得到重新评估。对当前国际辩证神学研究而言,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已经浮现,那就是《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绝非一个能用“作为他者的上帝”或“人与上帝之间质的无限差异”这类教科书式的标签来涵盖的单面文本,它是一个夹杂着多重声部的多面文本,折射了魏玛共和国初期众声交错的文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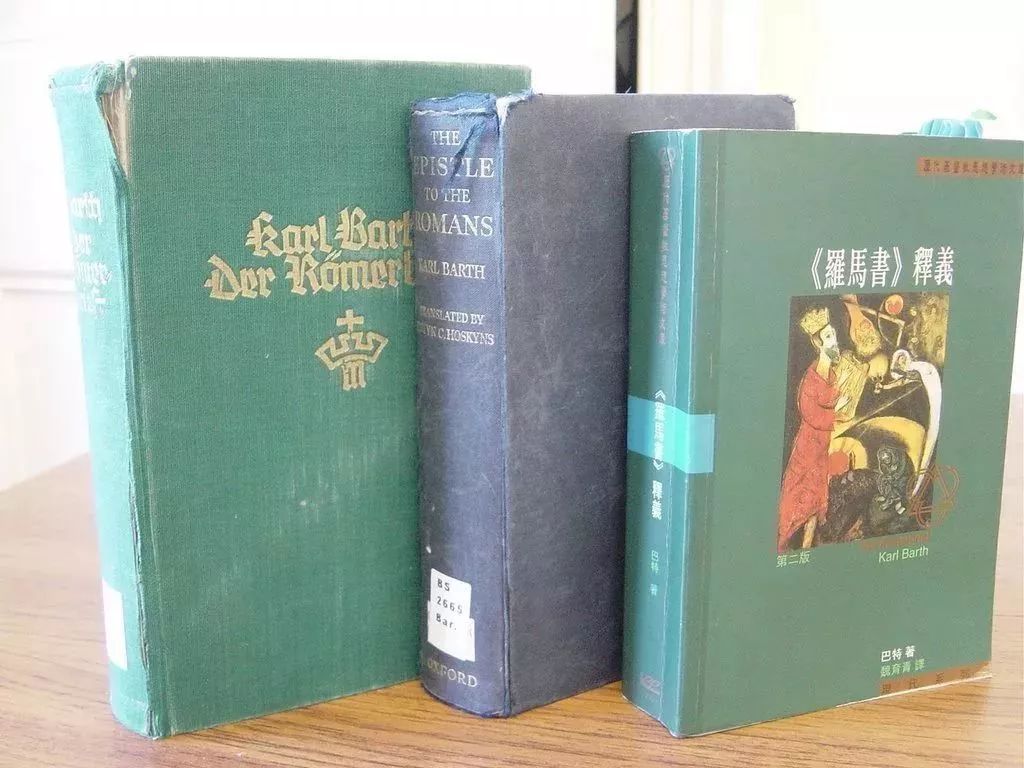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个多声部文本所蕴含的对话结构。首先,当时针对《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出现一些书评[5],有赞许的声音,但批评性书评居多。巴特觉得自己被误解,要在第二版中进行澄清和回击,除了在第二版前言中集中回应[6]之外,巴特在正文中对他的批评者们进行了大量不指名道姓的影射,他的手法是首先以讽刺性笔调模仿对手的学术观点,然后进行谬误推理,最后击倒对手。这种手法导致《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成为展现各类流行学术观点的万花筒与哈哈镜,从当时如日中天的宗教史学派[7]到新康德主义[8],从宗教社会主义[9]到人智学[10],从托尔斯泰的道德哲学[11]到希腊化时期的神秘宗教[12],从苏维埃主义[13]到无政府主义[14],各类观点一一粉墨登场,然后一一中枪倒地。2010年问世的《罗马书释义 (第二版)》学术考证版添加了大量脚注,目的就是要澄清巴特的这些论争对象。
其次,《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草稿逐字逐句都经过实践神学家图爱森的修改[15]。这一点巴特在第二版前言中已间接提及,他强调,自己在写作期间与图爱森密切交流,断言任何专家都不可能分清哪里是他的思想,哪里是图爱森的思想。不过,任何事情都会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借助巴特档案馆里大量未发表的书信,今天已经可以澄清两者合作关系中的诸多细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区分清楚哪里是巴特自己的看法,哪里是图爱森的观点。当巴特1920年深秋开始写作第二版时,他在每一章写完后都会立即邮寄给图爱森,后者则负责对文稿进行把关,他时常会建议巴特在正文中加入一些他构思出的文段,巴特对这些文段进行微量修改,然后直接移用[16],直至1921年初秋完稿。与此同时,图爱森同时在写一本关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他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些观点放进自己的书里,这本书在1921年7月正式出版之后,巴特反复读过多遍,十分重视,《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的一些重要文段以及概念,比如“生命”(Leben)这个概念,就是在回应这本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17]。图爱森的这本书吸收了不少巴特此时的思想成果,但它反过来又启发了巴特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新的拆解和表述。可以说,两部著作合在一起才构成1920年深秋至1921年初秋这两位神学家之间对话的完整版,才是一块完璧,《罗马书释义(第二版)》这部著作记录了两者之间的部分对话,并隐蔽指向其姊妹篇《陀思妥耶夫斯基》。

最后,《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包含了为新教神学学科体系重新奠基的思想抱负,实现的方式就是借助对保罗书信的创造性疏解与流行的释经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模式展开争论,并最终彻底取代它们,建立真正的释经学、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在新教神学内部进行跨专业对话的这种学术追求造成了《罗马书释义(第二版)》身份的多元性,需要记住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原本是关于保罗书信的释经著作,却被当时的新约泰斗尤利歇尔(A. Jülicher)归为实践神学类书籍[18],而它在之后的神学史编纂中又被视为系统神学的经典,这种奇特的多重身份与巴特在这本书中同时向这三个学科开炮密不可分。巴特既想释经,又想谈神学理论与实践,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意图客观上营造出三个学科围绕保罗展开对话的思想氛围。如果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对话特征的这三个层面叠加在一起,阅读和理解这部著作的难度就会变大,因为读者(尤其是今天的读者)并不处于这个多层面的对话语境之中,如果使用比喻的话,可以说读者是一个远处的路人,看见一群身份各异的人正在激烈争论,但想立刻听清他们争论的内容却是不容易的。
本文的关注点是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试图处理的“神学百科全书性”问题,也就是其对话结构的第三个层面。巴特在走上教授岗位之后,不同时期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述[19],然而,在创作《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时,思考神学学科问题的巴特是一名瑞士乡村牧师,没有博士学位,是德语专业性神学学术的圈外人,巴特的这个特定的社会身份与处境在其相关思考中得到反映: 他此时聚焦的核心不是以大学院系为骨架的神学学术的专业发展,而是其最后的根基何在,如果神学学术与教育仅仅跟文化、历史和教养有关,不能见证上帝之道,揭示普通人的生命意义,那它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让教义史家哈纳克感到懊恼和震惊[20]的思考方式显示了《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激进的草根性,要么百分之百地忠于上帝,要么百分之百地背叛他,这种不容妥协的“非此即彼”赋予了这部著作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和价值,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当时会被很多神学教授[21]拒绝,却受到大量神学生甚至是文科生的青睐。那么,巴特此时是如何在与当时的释经学、系统神学以及实践神学的争辩中去思考“神学百科全书性”的? 下文首先依次简要分析巴特此时心目中“真正的”释经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内涵,最后概括并评价他对“神学百科全书性”的理解。

Friedrich Gogarten, Eduard Thurneysen und Karl Barth bei der Gründung von “Zwischen den Zeiten” 1922 auf dem “Bergli”.
一、历史考证释经与专注圣经“实事”的释经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第二版)》蕴涵着一个“解释学宣言” [22],这个宣言针对的目标是在当时的圣经研究中已然成为主流的历史考证方法。在《罗马书释义》第一、二、三版前言以及第一版前言的六个未刊草稿[23]中,巴特通过对历史考证方法的批判间接阐发了一种聚焦于圣经“实事”的批判性释经学。“实事”对应的德文词汇是 Sache,它的含义非常丰富,既可以表示物品、事情或对象,也可以指主题、内涵、目标或意图等。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巴特用这个词来指称圣经所聚焦的内容。对于批判 (Kritik) 一词,巴特的理解是康德式的,批判并非批斗,而是设立界限,当巴特呼吁历史考证方法要“更具批判性”[24]时,他的意思是圣经学者要在自我批判中去认识这个方法的价值以及局限所在。这个方法虽然能够为理解圣经作语言学及史学意义上的准备,但尚未触及理解活动的实质,历史考证方法的学术性 (Wissenschaftlichkeit) 只能保证它针对圣经文本所说的一切具备可证伪性(Verifizierbarkeit),但保持这种可证伪性并非理解活动的最终目标,因为理解圣经的关键在于理解者要与圣经的实事建立休戚与共的内在联系。
“面对一份历史文献,判断对我来说既意味着以实事来衡量文献中的所有词语和词组,因为若非一切都是假象,文献显然要谈论一个实事,也意味着将文献中的一切已有的答案与显然与之相对的问题 反向联系起来,然后再将其与一个涵盖所有问题的首要问题反向联系起来,更意味着在唯一能被论述, 因而事实上也唯一被论述了的内容的光芒中来诠释首要问题的内涵……作为理解者,我必须深入到这样的地步,我面对的几乎只是实事之谜,几乎不再是文献之谜,我几乎忘却自己并非原作者,我对他 的理解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能让他以我的名义发言,我自己以他的名义发言。”[25]
与圣经的实事建立内在联系,这意味着理解者要进入实事本身所包含的问答结构之中。圣经的实事并非僵死不动,相反,它持续向读者提出“首要问题”,并给出最后答案,想要真正理解圣经实事的读者必须首先承认,这个“首要问题”概括了他自己所有的生命问题,而圣经所提供的最后答案就是这些生命问题的谜底。圣经实事所蕴含的问答结构支配着个体生命所蕴含的问答结构,个体生命的问答结构见证着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可逆转的支配与见证关系是超越历史的,当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前言[26]中说,保罗固然是古人,但他宣讲的信息却针对所有世代中的所有人时,他就是在强调保罗所呈现的这种支配与见证关系的非历史性。作为《罗马书》的“原作者”,保罗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并承认,这种支配与见证关系对读者自身也完全适用,这就导致他不能作为一个保持距离的旁观者描述并重构保罗的思想世界,而是要充满激情地与保罗为伍,与保罗对话,视保罗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保罗的答案为自己的答案,因为两者的问题和答案尽管古今有别,但同样都是对圣经实事问答结构的见证,具备内在的“共时性”(Gleichzeitigkeit)[27],读者与保罗之间因为这种共同见证而生发出的忠信关系 (Treueverhältnis)[28]一方面克服了他们的古今之别,另一方面也勾销了他们的角色差异,作为一个忠实于保罗的人,读者能够以保罗的名义发言,甚至可以深化并展开[29]他对圣经实事的陈述,读者如果不能与保罗建立起这样一种忠信关系,那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诠释保罗。
巴特为释经学设定的目标不是以客观描述的方式解答“文献之谜”,而是感同身受地呈现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与个人生命的问答结构这两者之间不可逆转的支配与见证关系。这个释经目标显然迥异于巴特时代大多数保罗研究的目标。在巴特写作《罗马书释义》第一、二版期间,德语世界的保罗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当时成为主流的宗教史学派的保罗研究,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保罗神学的观念来源中犹太成分和希腊化神秘宗教成分的所占的比重,其次是以及称义论和救赎论在保罗思想中的理论位置[30]。这一类研究的主要代表是新约学者A.Schweitzer[31], W.Wrede[32], W.Bousset[33]以及古典学家R.Reitzenstein[34]等。第二类是以A.Jülicher[35], O.Pfleiderer[36], H.Lietzmann[37], C.Holsten[38]和H.J.Holtzmann[39]等为代表的保罗研究,他们从典型十九世纪自由派神学的核心概念“宗教”出发,一方面关注保罗的宗教经验, 他的虔诚人格和反对律法的自由性宗教伦理,另一方面则要区分保罗的神学和宗教,认为他的神学只是其宗教经验的理论化产物。在这两类主流保罗学派之外,也有像A.Schlatter[40]以及 J.T.Beck[41]这样与历史考证方法保持张力的学者,巴特对他们的研究保持了适度关注[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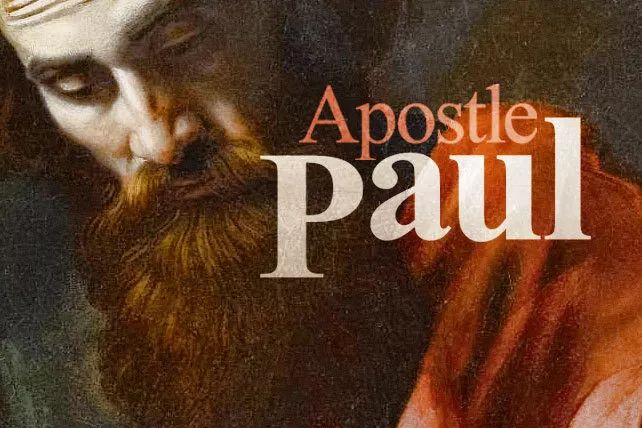
对于以上两类主流的保罗研究,巴特都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学者们把保罗当成一个与己无关的研究对象,要么认为理解保罗就是要重构出他的思想根源,要么认为理解保罗就是要揭示其现代意义,他们都没有和保罗建立起忠信关系,用巴特的话来说,他们缺乏理解和诠释的坚韧意志[43]。与他们不同,加尔文具备这种意志,他在自己的保罗书信注解中首要关切的并非保罗时代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间距,而是与保罗之间的交谈如何集中于圣经实事本身,这也就是说,如何与保罗并肩携手,共同呈现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与个体生命的问答结构之间不可逆转的支配与见证关系。巴特在此的意图并非抬出加尔文,贬低严肃的史学研究,他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圣经文献的历史考证研究如何在具备史学内涵的同时也具备神学内涵,这也就是说,圣经研究的目标不能只是在文献史意义上提出不同的底本假说,而是要更进一步,揭示圣经实事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44]。当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前言中明确强调自己更喜欢圣灵感应说(Inspirationslehre)的时候,他的意思并非要再次返回到新教正统主义(protestantische Orthodoxie),按他自己的讲法,他知道“问题没有这么简单”[45],他希望的是重建圣经实事对诠释者的约束性,不是诠释者凌驾于圣经之上,而是反过来,圣经的实事高于诠释者的诠释意图。在巴特看来,同时代的圣经历史研究颠倒两者之间的恰当关系,错过了圣经的实事。
二、“危机神学”与基督的复活
圣经实事蕴含“首要问题”以及最后答案,对此时的巴特而言,这个问答结构的核心是基督论。可以用两节经文来概括他的理解。《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中耶稣在去往凯撒利亚的途中问自己的门徒:“众人说我是谁?”这是巴特眼中圣经的“首要问题”,《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中耶稣向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谁跟从我,谁就不会行于幽暗之地,反要得着生命之光。”这是圣经的最后答案。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以基督论为中心,是基督的自问自答[46]。在巴特看来,基督的这个自问自答涵盖了人对有限生命的一切疑问和暂时解答,而人对自我的一切认识最终指向这个发生在基督之中的上帝的自我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圣经的实事与哲学的主题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只在于,神学家在哲学家们称为“本原”[47]的地方发现了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耶稣基督,真正的系统神学应专注于基督的复活,《罗马书释义 (第二版)》的神学核心是基督论,而这个基督论的核心则是基督的复活。《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同样关注复活问题,但着眼点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到来的死人复活如何成为盼望的对象[48],而第二版强调的是上帝的正义[49]在基督复活之中得以展现。
“唯有通过他(指耶稣),上帝的正义才变得不难理解,变得不易误解了: 它是雄踞于人类以及历 史之上真实的秩序与权柄。”[50]
基督的复活,上帝的正义,巴特试图联系起这两个概念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基督的复活不是上帝恩典的随意派发,而是其正义的贯彻,上帝的正义与司法意义上的赏善罚恶不能简单等同,它展现的是上帝全新的复活与创造之力。上帝的彼岸正义高于一切人类的此岸正义并构成后者的绝对危机。
“基督的恩典所及之处,人即使矜持怀疑,也参与了对古往今来万事万物之转折的宣告,参与了复活。”[51]
如果人的正义自以为义,拒绝这一带来根本转折的全新的复活现实,那么这个危机就意味着上帝的永恒弃绝,如果人的正义承认自己被基督的复活现实所批判,那么这个危机就意味着重生的机会,它照亮人类正义的有限价值,使后者成为对上帝正义的类比 (Gleichnis)。所谓的“危机神学”包含两层意义:首先,在基督复活中展现出的全新现实揭露了世界现实的陈旧,其次,必须做出抉择[52],承认这个陈旧的世界现实的确处于绝境,以便从上帝那里绝处逢生,否则将面对永远的沉沦。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危机神学”的双重内涵支撑起其罪论、教会论与宗教批判,也动摇了称义论(Rechtfertigungslehre) 在传统新教教义学中的核心地位。不是人如何通过虔敬自律而称义,而是上帝如何在基督复活这一终末论性质的事件中表明自己的正义,这个正义无与伦比,因为它来自彼岸,是意在拯救的神性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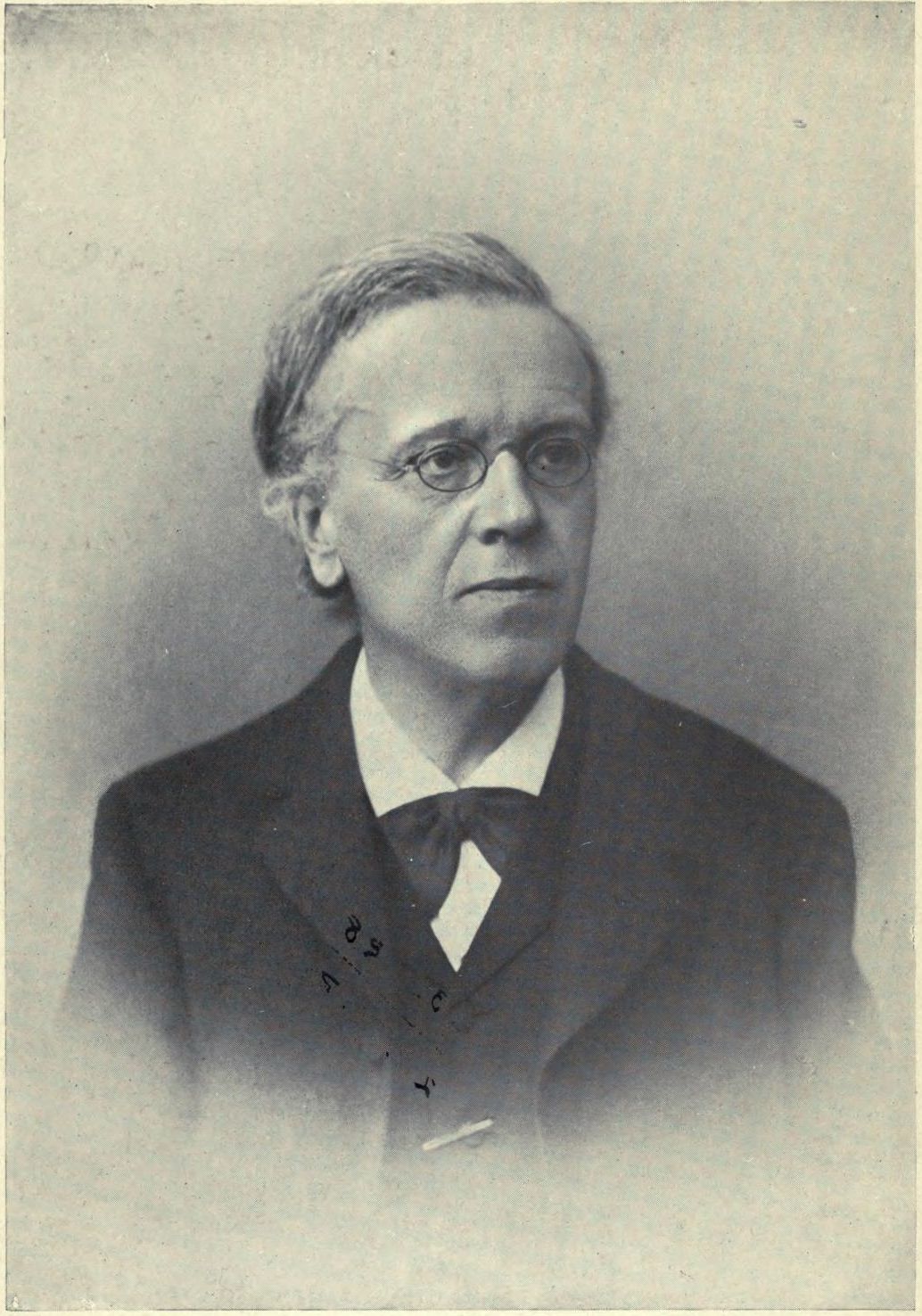
Franz Overbeck (1837-1905)
巴特虽然从释经学角度质疑宗教史学派的史学方法,但从教义学角度接受了该学派的一个基本的学术结论:新约与原始基督教所宣信的核心与康德以降的新教神学所强调的道德人格毫无瓜葛。与此同时,巴塞尔大学教会史家欧文贝克(F.Overbeck)问世于1919年的遗著汇编《基督教与文化》[53]对巴特震撼极大,从这位尼采的昔日友人那里,他学会了把现代基督教与原始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差异解读为前者的自我迷失或者说堕落,正是带着这种鲜明的价值评判,巴特加入到宗教史学派在世纪之交对里奇尔(A.Ritschl)主义的批判浪潮之中, 但又超越了他们。众所周知,J.Weiß在1892年写出了《耶稣对上帝国的宣讲》一书,指出新约中耶稣宣讲的上帝国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里奇尔学派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构想出的不断进步的市民道德共同体,而是暗示世界末日到来的“弥赛亚-终末论”[54]。W.Bousset在同样写于1892年的《耶稣与犹太教对立的宣讲》中虽然强调耶稣面向世界的亲和与同情,但同样认为耶稣对上帝国度的宣讲源于一种“对世界末日和世界审判这些终末之物的期待”[55]。史怀哲 (A.Schweitzer)对宗教史学派一贯有所保留,但他在出版于1913年的名著《耶稣生平研究》中不仅认为耶稣的上帝国宣讲是终末论性质的,甚至其在尘世的所有作为都具有终末论性质 或者说弥赛亚意识[56]。以上三位重量级学者尽管从史学角度揭示了里奇尔主义从康德伦理学角度对上帝国概念的误读,但又都从教义学角度承认了这种误读的必要性,因为唯有通过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律,原始基督教的终末论才能和现代基督教世界的自我理解重新建立联系, 唯有如此,彼岸的终末才转化为“此岸的力量”[57]。在巴特看来,他们的里奇尔主义批判并不彻底,因为他们虽然揭示了上帝国的终末论性质,却无法摆脱里奇尔对这个概念的伦理诠释, 终末论元素对他们而言仅仅是基督教中具有前现代性质的“残余”[58],失去了其原本的颠覆性意义。终末论不能被现代基督教世界的道德称义论抵消,恰恰相反,它要成为后者的绝对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强调,终末论要成为教义学的核心[59],如此才能保证教义学从基督的复活和上帝的彼岸大能中获得其内在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所指向的目标当然不仅限于基督教的道德化,同样也包括基督教的政治化,比如宗教社会主义[60]。

对基督复活的专注使系统神学不再聚焦于圣经的实事如何与现代精神沟通,而是聚焦于两者之间深刻的沟通障碍,因为显现于基督复活之中的上帝大能来自彼岸,日日新苟日新, 现代精神所推崇的人道能力来自此岸,每况愈下,朝不保夕,前者是新酒,后者是旧瓶。与对历史考证方法的批判一样,巴特在此的意图绝非简单地拒绝现代精神,而是要敦促受现代精神熏陶的新教神学进行自我批判:如果神学的对象是上帝,那么启蒙以降的现代人是否时刻把他放在神学的中心位置?当他们谈论上帝的时候,想的是否只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两个问题为巴特后来的史学著作《十九世纪新教神学史》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框架: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在技术、科学与政治领域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这导致十八乃至十九世纪主流新教神学高举人类中心主义,对神学问题进行国家化、道德化、学术化、内在化与个体化[61],而“危机神学”则意在重新恢复上帝的中心地位。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巴特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阐述这个上帝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侧面,即上帝的自我启示及其可认知性,众所周知,在《教会教义学》第一卷第一部分中,三一论被确立为上帝自我启示的认识论结构[62]。从《巴门宣言》[63]开始至二战结束,巴特以盟约神学(Bundestheologie)[64]与反抗权(Widerstandsrecht)[65]为基础,逐渐开辟出这个上帝/基督中心论所蕴含的政治神学维度[66]。《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处理这个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在包罗万象的生活实践这个背景中来理解上帝的中心地位。
“思想如果是真实的思想,就是对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对上帝的思想。”[67]
三、生活图像的透视主义与实践神学
思想是否具备真实性,这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触及到生活与上帝之间的关联,思想上帝就是思想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主宰地位,思想生活则是思想它被创造主和救赎主上帝所统治。 在巴特看来,以上帝为中心的“危机神学”绝非脱离日常生活实践的抽象玄思,而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理论[68],因为它抗议现代生活的各个实践领域与上帝隔绝的独立性[69],要用基督复活所展现的上帝大能来照亮现代生活的全部困境与复杂性,深度与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诸多生命哲学尽管出发点不同,但目标类似,因为大家都要在全方位剧烈变革的二十年代为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找到新的解释原点。在哲学家海德格尔尚未写出其《存在与时间》的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注意到巴特的“危机神学”与生命哲学的这种内在关联[70]。巴特找到的这个解释原点不是后来对布尔特曼(R.Bultmann)产生巨大影响的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 概念,而是此岸生活与彼岸上帝之间的透视学关系:如果生活是一副立体图像,那么上帝就是位于该图像之外的透视焦点 (Fluchtpunkt), 图像的所有线条都指向这个焦点,如果焦点消失,图像内部的线条关系就会紊乱。这个思想最初被实践神学家图爱森提出[71],巴特将其引入《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危机神学”之中。
“没有什么自在的生活,而是只有一种与上帝相关的生活,只有受上帝审判,得上帝应许的生活: 以死亡为特征,但通过作为永恒生活之希望的基督之死而获得资格的生活。”[72]
巴特认为,在生活实践的各种具体关系内部,无法看见生活的全景,唯有从生活之外,超越于生活的某个焦点出发,才能够透视整个生活的图像,这个焦点就是对生活给出审判并应许的上帝,人的全部生活处在他的审判和应许之下,没有任何一根生活图像的线条可以脱离与这个焦点之间的联系。前面已经指出,上帝在其大能中的审判与应许意味着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危机,这个危机体现于具体生活实践的各类矛盾与问题之中,生活的意义不是借助各种手段去摆脱这些矛盾和问题,而是要借助它们去进入这个总体性危机,因为只有在这个危机或者说焦点之中,生命的来源与归宿,生活图像的全景才会真正显露出来。巴特为释经学制定的目标是呈现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与个体生命的问答结构之间不可逆转的支配与见证关系,这个目标是关于生活图像的透视主义在圣经诠释层面的落实:圣经实事中基督的自问自答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危机,这个危机浮现于每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解答之中,把握圣经的神学内涵意味着看到个体的生活图像对这个危机或者说神性焦点的依附关系。那么,这个关于生活图像的透视主义如何塑造了巴特对实践神学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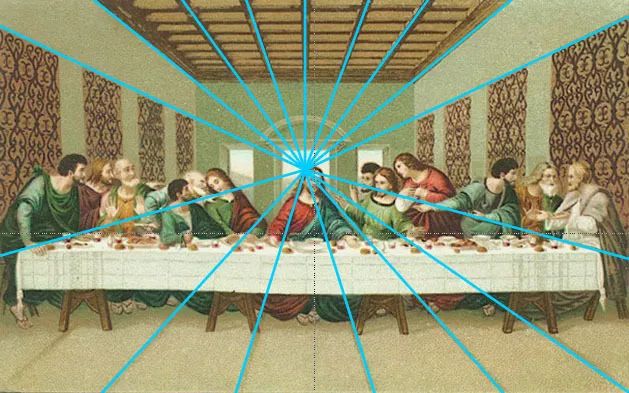
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序中,巴特称实践神学流连于“平缓的河谷草地”(sanfte Auen),回避真正的神学任务必然要面对的雄关险隘,这个针对实践神学的“臭名昭著”的评价至今还让德国的实践神学家耿耿于怀。巴特的这个评价究竟针对当时的哪些实践神学家? 作为一门独立的神学学科,德国的实践神学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其标志性著作虽然是 K.I.Nietzsch 出版于1847至1857年这十年间的多卷本《实践神学》[73],但晚近研究则一致公认,真正确立了第一个实践神学理论范式的人是Nietzsch的老师施莱尔马赫 (F.Schleiermacher)。早在施莱尔马赫出版于1811年的著名的《神学研究简述》[74]第一版中, 实践神学已经被定义为神学之树的树冠,它从哲理神学这个树根中汲取养分,被历史神学这个树干所扶持,目标是发展出可以引导信徒灵魂和带领教会发展的艺术规则,以便在日渐独立的世俗文化语境中保存并且完善教会。与此相应,牧灵(Seelsorge)的首要功能是恢复并提升信徒被遮蔽了的良知自由,推动起重新被整合进教会这个社会团体,不再提出牧灵要求。施莱尔马赫深受启蒙精神熏陶,认为教会是由受上帝之道直接引导的独立个体所组成的, 教会区别其他社会团体的特殊性在于,连接其所有成员的纽带是虔敬意识 (Frömmigkeitsbewusstsein)。教会并不独立于社会文化语境之外,恰恰相反,它要在由虔敬意识引导的宗教实践中显示出自己是这个语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施莱尔马赫创立的这个沟通教会与社会的理论范式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自由派实践神学家那里得到贯彻与深化, 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代表比如O.Baumgarten[75],P.Drews[76]以及 F.Niebergall[77]都认为实践神学的中心是社会中的教会,但与施莱尔马赫不同,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强调社会这个概念的经验性内涵。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经历巨变,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和世俗化既催生出了全新的社会经验(比如新的交通与通讯手段带来的速度体验),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比如劳资纠纷和社会分化)。在自由派实践神学家们看来,这些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与教会存亡息息相关,只有直面这些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围困的信徒的灵性需求,采用时新的经验科学的方法 (比如宗教学和心理学) 分析并解决它们,才能重新接近那些被世俗力量夺走的信徒,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必须注重策略与技术。在巴特看来,这个潮流正逐渐使实践神学丧失神学内涵,沦为翻译社会经验的工具与手段。从他和图爱森发展出的生活图像的透视主义出发,巴特抨击自由派实践神学的平面化思维,认为他们只看到了紊乱的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本身,却忽略了它们位于彼岸的焦点,他们眼中的生活失去了神性深度,一切都被归纳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生活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它的问题不可解决,在于它从上帝这个彼岸的焦点看到自己深陷危机,只能仰赖救赎。对巴特而言,只有借助这个透视主义视野,实践神学才能防止自己沦为臣服于现实生活种种经验诉求的传声筒,从而保持其神学品质。牧灵和宣讲所应关注的终极目标不是如何消除危机,而是如何更深刻地展现生活的根本性危机。在自由派实践神学家眼中,巴特的理论范式彻底打破了施莱尔马赫试图在教会与社会之间努力架设的桥梁,再次凸显了圣经实事与现代精神之间深刻的沟通障碍。
四、神学学科的统一性或“神学百科全书性“
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对释经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的批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此前的一九一八年,在为《罗马书释义(第一版)》撰写的六个未刊前言草稿中,他已开始向這三门学科开炮。巴特在草稿中强调,自己并非孤军作战,与他同声共气的是“整整一代青年牧者和学生”[78]和“足够多的非神学家”[79],大家都想以另一种方式阅读圣经,以区别于被十九世纪神学统治的大学神学院系,因为后者把圣经视为记载远古虔敬意识的“经典文献”[80],对其进行了诸多“光彩耀眼且富于穿透力”[81]的历史语文学研究,但这些“神学学术活动”[82]在面对“圣经的意义”[83]时却暴露出“非实事性、形式化、非本质性、不专注和无爱心”[84],不只是释经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面临类似的问题。
“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渴望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理解、宣讲以及教学能够更具实事性、内容性和本质性。”[85]
对此时的巴特而言,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的突破口是找到一种更贴近圣经意义本身的读经方式,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考证方法相比,这种方式应“更具实事性、更着眼于内容和实质、更专注并更富于爱心”[86],能让圣经再次对“陷入外在与内在撕裂状态的人类”[87]开口讲话,唯有在此基础之上,“今日之神学”[88]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对《罗马书》的解读固然属于释经学范畴,但它牵涉到的问题却绝不仅仅是圣经诠释的方法论,而是包含了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在内的整个神学学科统一性的奠基。在三年之后写就的《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序言中,巴特重新对这个基本关切作出表述:
“他们的学生将来在教会中的前途如何?这的确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不仅涉及实践也具有高度实事性的问题。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得不年复一年登坛宣讲,应该并愿意理解和诠释,但却常感力不从心,因为大学教给我们的只是著名的‘对历史的敬畏’,说虽然好听,但这其实意味着拒绝进行任何一种严肃的、充满敬畏的理解与阐释。”[89]
理解保罗意味着跨越历史藩篱,承认“他作为上帝国的先知与使徒针对所有世代的所有人宣讲”[90],沟通他和“所有世代的所有人”的根本基础并非精致的史学“移情艺术”[91],而是包括保罗在内的所有人与圣经实事问答结构的见证关系。上文已指出,圣经实事问答结构的核心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它揭示彼岸上帝的正义,构成此岸世界的危机,在巴特看来,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疑问与探索指向这个关联彼岸的危机,按照图爱森的透视主义语言来表述,这个高悬的危机是一切生活图像的透视焦点,唯有从此焦点出发,才能把握到生活图像的全貌。在此,“圣经的主题与哲学的总和合二为一”[92]。脱离这个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透视关系,巴特提出的所谓“时间与永恒之间‘质的无限差异’”[93]难以被恰当理解,因为他的着眼点并非时间与永恒之间二元论式的的僵硬区隔,而是此岸生活如何在与彼岸焦点的动态张力中“成像”,失去彼岸焦点的此岸生活只是混乱而无意义的线条堆积。呈现作为危机的彼岸焦点对此岸生活图像的建构性意义,这是青年巴特眼中确保历史理解、教义反思与实践想象具有真实性与深刻度的唯一基础。
十九世纪神学总的问题性在于,圣经学者倚重史学,系统神学家臣服于现代价值,实践神学家关注策略与技术,三者形成强大合力,使整个神学学科为“历史-心理学”[94]的虚构与偏见所蒙蔽,最终偏离其根本对象,在此前提之下,二十世纪初的新教神学陷入全面危机:释经学无法揭示圣经实事的问答结构,系统神学无法触及基督复活所包含的批判潜能,实践神学在平面思维中日益浮浅,三者画地为牢,彼此隔绝。在巴特看来,释经、教义和实践所组成的这种偏离目标且相互割裂的神学学科体系最终使德语主流神学界丧失基本的判断力,混淆了超越的上帝国与一战同盟国意识形态所鼓吹的民族国家利益。新教神学如果想要重新出发,那么释经、教义和实践三者之间必须打破藩篱,重返使它们陷入共同危机的唯一对象,即被圣经所见证的作为生命图像意义焦点的基督之复活,正是这一对象奠定了三者所组成的神学学科的内在统一性或“百科全书性”。区别于潘能博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以广义科学理论(Wissenschaftstheorie)[95]为导向的神学百科全书性,《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强调的打通学科界限的百科全书性立足于生活图像的彼岸奠基,具有鲜明的生存主义色彩,巴特此时的首要关切并非神学学科的理性品质,而是其全方位转化生命的实践价值,正是这一点让当年的巴特在彷徨求索的学生群体中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马克思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业》一文中曾说,一位学者取得的专业成就,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内就会过时[96],这是现代学术的命运。巴特神学是否过时,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如果“过时”一词所指不是某项学术成就的内在价值,而是外部世界对它的关注程度, 那么韦伯的讲法就有其合理之处。巴特逝世于1968年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年份,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德国新一代的系统神学家们就已开始批评巴特不懂终末论[97]和“启示神学”的反智倾向[98],重新发掘历史对于理解启示概念的意义,与此同时,被巴特批评为人类学中心主义的神学代表施莱尔马赫思想在德语学界经历了复兴,他试图连接教会与社会的文化理论范式重获肯定。在圣经研究领域,曾被危机神学激烈抨击的宗教史学派重获生机,这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以O.Keel为代表的图像学(Ikonographie)[99]在七十年代的兴起,它掀开了古代近东研究、旧约研究以及广义宗教学的崭新篇章。在德语实践神学领域,学术新生代如K.Wegenast等推动的“经验转向”(empirische Wendung)[100]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巴特,认为他的实践神学范式忽视了信众的信仰经验与现实需求,片面强调宣讲危机,这是教义学对实践科目的专制与压迫,巴特在二十年代初期所反对的一切似乎在他去世之后又以新的面貌和强劲势头重生了。
学术风潮的变化无常符合《论语》对川流的描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如果重审《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百科全书性”只是为了做一个“巴特主义式”的表态,即只有巴特一个人才是对的,其他所有人都弄错了,重温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就像巴特本人在第二版前言里所强调的那样,“问题没这么简单”[101]。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对于当前及未来世代针对“神学百科全书性”的理论反省而言,《罗马书释义(第二版)》都堪称伟大的典范,它的典范性根源于青年巴特的深刻信念,那就是神学思想必须立足于充满变动与危机的生活世界,要去那里寻求奠定自身统一性的基础:“正是着眼于生活,思想才必须踏上交错的道路,步入无尽的远方,正是而且唯独是在生活诸多线条所构成的那种让人迷惘的、万花筒般的运动性与紧张性中,思想才能真确地反映生活”[102],才能成为对上帝的思想。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洪亮
德国图宾根大学神学博士,师从系统神学家莫尔特曼,二零一五年十月毕业,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于二零一六年三月在Neukirchener出版社面世,先后获得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学年最佳博士论文与博士考试奖,二零一七年度德国新教神学协会恩斯特伍尔夫双年奖与二零一七年度曼弗雷德劳滕施莱格神学希望奖。现任职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系统神学科助理教授,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为巴特、莫尔特曼、实践哲学、法律与宗教。目前师从圣安德鲁大学系统神学家施威博,继续撰写教授资格论文,主题涉及“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与朋霍费尔论责任的根源”。
相关文章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编辑:Imaginist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声明:本公众号欢迎各界人士通过微信文章打赏或其他形式对“巴特研究”公众号进行捐助,也欢迎与期待您与我们的合作机构或相关基金会签订协议。期待您的来信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