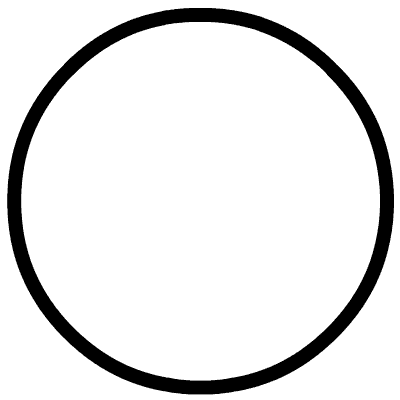 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 自闭症家长/教育者学习、成长和分享、互助的心灵家园。欢迎给我们投稿并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如需转载请附上我们的二维码。


近日,联合国在官网公布了2020年世界孤独症日宣传主题:向成人期的过渡衔接(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今年联合国的孤独症日宣传主题聚焦孤独症人士的阶段性衔接,特别是向成年期过渡衔接的重要性,同时也向社会表达了孤独症人士向成年期过渡转衔中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年前,我们的编辑兼心理咨询师大黄蜂接待了以琳阳光班的三个大孩子,尝试了解他们的成长困境、焦虑障碍、心理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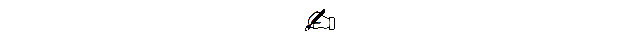
采访:大黄蜂|图片:《少年的你》
看了这几年的访谈记录,我做过一对一咨询的圈内大孩子(十五岁以上)已经超百位,让我没有多少乐观情绪反而越来越悲观,孩子们是笑着或恋恋不舍地离开,但留给我的除了各种心疼,更多的是无奈。
我确信这并不是一股正向、阳光的能量,它指向过去——孩子们已经走过的路和家长已经无力也无法修正的那些遗憾,以及未来——随着家长们日渐衰老、能够提供的呵护可能越来越少,孩子们即将独自面临和承担的那些焦虑。
其实,如果严格按照咨询师职业伦理而言,我这些想法几乎可以认为是部分越界操作,因为“圈内”的孩子,包括“阿斯”,都不直接作为职业心理咨询师的服务范围之内(即使智商完全正常、情绪稳定、语言行为得体),他们的档案应该归属于精神科医生,而我们只能配合做好辅助性心理疏导。
然而,很多在接受了心理专科医院或者在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医生咨询后的孩子们,还是在家人、老师的建议或坚持下,向我求助——我想这是“圈内”家长之间一种天然的信任,也是我作为一个典型谱系妈妈的一种职业幸运,因为养育了有类似情况的孩子,相对比其他同行,我可能更容易走近和走进孩子们的心。
如果孩子背后或身边的家长们,有足够高的参与度和配合度,我们会在咨询室外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一起探讨方法思路和调整方向,双管齐下,咨询效果相对比较明显。
有些孩子的表达理解能力受限,全程都需要父母陪在身边进行咨询。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咨询,我都是通过对话、绘画或者游戏方式当面沟通,提前或之后与父母单独交流确认。还有一些孩子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认为我就是一个喜欢聊天,喜欢自己,只是偶尔会莫名其妙地问三问四的阿姨。也有一些孩子干脆拒绝其他人陪伴,或者即使是语音电话交流,也不许旁听……
然而,我咨询过的孩子们中能明确表达自己的困惑、主动提出需要心理咨询并有针对性进行探讨的,有且只有一个,那是一个想主动为自己摘掉“阿斯”帽子的大孩子。而其他孩子,都是父母家人或老师同学发现异常后“引导”他们向心理咨询师求助的。
孩子的情况千差万别,相信家长老师们之所以考虑心理咨询可能有用,前提是这个孩子的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比如谱系中等功能或以上),而且有一定配合度。从咨询的孩子中,我发现他们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情绪不良和行为不适、人际关系困扰以及认知偏差。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只有一个:因为焦虑、恐惧等,导致情绪无处安放而无所适从。
我在青岛以琳的辅导室,接待了阳光班的三个孩子,他们整体的能力在同龄谱系中至少是接近正常人四分之一部分的。认知水平、语言理解和表达都很不错,能脱离父母过寄宿生活的适应性也很好。
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与我交谈,几乎都是没有真正主题的,当我介绍自己的身份和可能做出的帮助之后,W在引导下以和我分享生活经历为主,Z在交换过很多信息之后总是想把我拉进有关方妈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题黑洞”,Y一直在反复描述公交车上发生的她最喜欢和最讨厌的故事——实话实说,这就是谱系孩子咨询的一个常态缩影。

受访者:W(男,17岁)
W与我分享了他在青岛游览过的地方,最喜欢的啤酒博物馆和前段时间邮轮行的晕船感受,义卖中的畅销产品,以及他为家人们到山东旅游所设计的路线,还说了因为更换老师产生的失落和最喜欢的班主任——暖男叶老师。他总结了老师温暖、以身作则、情绪很稳定的品质,说了自己作为班长的一些挫折和应对方式(不是全部告诉老师,而是自己想办法试着变换方式处理)。
在谈到学校生活感受的时候,W表示在以琳一年多的学习生活让他非常开心,尽管也有不愉快发生,但足以被更多的快乐抵消。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大家朝夕相处,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照顾,这和之前他在学校受到排斥的情况完全不同。放假回家后,他会同家人分享在青岛的见闻,或帮家人做事、走亲访友,以及到处看看,但是没有与之前同学聚会的计划——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是我问他答的形式。
W有两次主动的提问,一是确定我在阳光班听课的那天是周几,二是询问青岛有没有华德福学校。对于心理咨询师而言,第一次约访只是收集一些基本信息和资料,但这次我却了解到W的一些经历和对重要人物、事件的感受,已经非常有收获。
总而言之,W目前的心理状态很不错,因此我也没有继续了解他之前在学校经历过的挫折。在此也想向W的父母、老师们建议,不要再提及W那些想主动忘记的曾经,也尽量不要勉强、劝说他与之前的朋友同学约见——他可能是在主动疏离那些人,毕竟见到他们,就会想到过去。
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W的自我认同感已经建立。他表现出的信心和阳光,家人和学校老师们功不可没,可能后期的重点就是试着培养他的工作能力。

受访者:Z(男,17岁)
通过半小时的接触,Z的表现和状态很让人忧心,我甚至觉得他明显在退步,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休息好,还是因为氛围过于放松,Z从行为到情绪和想法,一直在“飘着”:他坐在沙发上,不是想脱鞋,就是抠鼻、搓眼各种小动作不断,最关键的是他一点都不关注我说了什么,而是想方设法把话题转移到他最关心的方妈妈的故事方面,不管我谈论什么话题,他像没听到一样,要么不回答,要么直接打断——自顾自地痴迷在他从手机里、网络上或者道听途说的各种信息中。
三年前我曾见过Z,那时高功能的他不是这样固执和逃避,也没有这么多的不合时宜、需要不断提醒,以及不断重复的小动作,似乎当时的他比现在更关注外界——这让我不禁怀疑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会让他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因为Z此时此刻的神态和行为,和那些网络成瘾的孩子如出一辙,他们窝在沙发上或盘在床上头不抬、眼不看。Z认为我是他暂时的搜索引擎,或者一个不怎么按输入出牌的工具而已。而在阳光班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他一直被各种干预,即使是青春期前后的一种退化,也不至于这么突出。
在咨询结束后,通过向老师了解情况,我心中的疑惑似乎有了一点眉目:Z是走读,在阳光班的学习生活是朝夕制。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要求,阳光班对个人生活要求、各项教导和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定不一致。Z的兴趣面有限、在家很多个人事务被分担,家人给他的自由时光多、顺着他性子的时候也多,而Z又恰恰处于青春期前后比较自我的阶段,所以发生前面这些情况似乎就“顺理成章”了,毕竟孩子越大越会钻空子。但愿我的这些主观臆断会被事实推翻。
不知今后有没有机会与Z的父母当面交流,职业的敏感性提醒我,除了谱系青春期心理变化的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家校共育时教养方式的不一致,导致衔接的“空挡”被聪明的Z发现,并过度利用。

受访者:Y(女,16岁)
Y是被哄出辅导室的,在对话期间,关于某些公交车的特定品牌和她与某路公交车间发生的故事,她反复提到了不止五次,在这期间我们也聊到了同学交往和城市旅游等几个话题,也都被她滔滔不绝的回忆挡了回去。
Y似乎还活在过去,她的倾诉里有很多愤怒和不甘,她曾经喜欢在她最喜欢的品牌公交车上拿相机抓拍,得罪了好多司机,有几个人对她威胁谩骂甚至报警,她自己已经上了各种监控的黑名单,而且随时会被传讯——具体发生过什么我无从知晓,因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受进行表述,但从Y忿忿不平的表述中,我感到了很多不安和恐惧。
我甚至觉得这个公交事件就像是祥林嫂家被狼叼走的阿毛,她的所爱被夺,还要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正如祥林嫂从始至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阿毛有监护不当的责任,Y也从没有真正认识到她冒犯别人在先,不尊重隐私权,公然对着别人拍照确实属于不当行为。
而这些事情发生后,她所看重的那些人,从老师、同学到父母、家人,几乎每个人都在责备或批评或警告她。然而在Y的认知体系中,自己就是单纯喜欢做某件事情,觉得拍照片就是给自己看的,这和他人无关,更谈不上侵犯隐私——很多孩子看问题,会习惯性地把自己从世界和他人之间割裂。
对Y而言,“被警察局备案”应该是比被司机和乘客当面指责谩骂更具危机性的事件,她在被司机恐吓、甚至差点被殴打之后,就已经怕得要命,后期家人又一盆冷水泼上来,说她已经上了黑名单、随时有可能被送进警察局,就完全被自己人吓唬地进了死胡同里,走不出来了。

Y在描述爸爸对她说被警察“约访”时,Y的左手拳头握得紧紧的、右手拍打着自己胸口、脸涨得红红的、额头冒着小而细密的汗珠,这是典型的创伤性事件“闪回”时的生理反应。
在被问及与父母的关系时,Y叹了口气,提到儿时,她说自己的爸爸经常拿“别人家的孩子”教育她。因此我估计警察找过Y的父亲,请他配合多加管束教育Y。但到处的监控器上都已经有了Y的黑记录、时刻准备抓Y,多半是Y的父亲为了提升警察的威慑效果顺口而出的夸张说辞。可他这样做时就应该想到,把Y吓成这样,她可能许久之后还无法释怀——父母把焦虑在无形中传递给孩子而半点不自知。谱系的孩子心思多么单纯,理所当然会把父母的话当真,心里不安的程度有多么深、惊恐的时间就有多么长,真的无法想象。
无可否认,Y的焦虑有部分来自于她在人际关系上的天生短板,尽管她口齿伶俐、言语流畅、思维也比较条理,但她与正常孩子心智年龄的差距,至少在三岁以上,但更大的诱发成因可能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特别来自父母的“二次伤害”。
本来还有位每天觉得身边都是坏人、动不动就要报警的P需要访谈,但因为有别的安排没有如期进行。在我观摩阳光班课程的时候,我就坐在P的旁边,在稳定状态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各种反应都在线的孩子。然而这样一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却频繁有被迫害的妄想性行为,让我忍不住脑补,他之前在毫无个别化支持系统的学校里,曾受到过的诸多伤害。

我经常拿纪伯伦的“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劝导所有孩子的家长,可在接触了这么多谱系之后,我却想和家长们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先天的生理特点造成了孩子们能力弱、敏感度高、社交缺陷明显,要把他们养育长大,家长们真的要做足了必修课。
从阳光班的孩子身上,我明显地发现:他们都是单枪匹马闯荡过普校、混过NT小社会的。我在普校陪读两年多,能想象出“手无寸铁”的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冷落白眼和各种形式的欺负经历过多少,人格和尊严就会被践踏过多少。以P为例,他的安全感那么少,才会让他在其他孩子感到放松、老师有爱的环境中,还时时刻刻有被迫害的焦虑和担心,并且有控制不住报警求助的冲动。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过了所谓的“黄金康复期”,家长认为孩子能力差不多,就盲目乐观送进普校的做法,真的会后患无穷。
如果家长们无法看到孩子的真实需求,而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引领孩子,对孩子逼迫(对生活或学习的环境适应,特别在灌输知识、抓学业方面)、忽视(根本不关注或处处溺爱包办)、束缚(各种各样的规矩要求,而半点不给孩子自由选择机会和自由空间),就常常会导致出现假性亲子和谐或者亲子间反目为敌等情况。前一种情况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一套背后一套,是典型的两面派;后一种情况的孩子,则是当面锣对面鼓地直接“争战”。
谱系的孩子没几个会与父母争战,因为这个世界他能爱和重视的人实在太有限了,因此只能与自己争战,于是就出现比较严重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甚至产生精神性疾病症状。
而家长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和时间都是朝着提升孩子的社会适应度,数年下来,反而青春期前后的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差。“两面派”们的日子最终也不好过,他们会成为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接纳的人,因为老师、同学、同事会觉得现实中的他们,与其父母描述的太不一样了,而父母则会认为,他们眼中的孩子和别人转述的根本不是同一个。
正视现实、接受差距,扬长避短、逐步调整,才是正途。有足够的了解、接纳、支持以及及时的肯定与帮助,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像W一样阳光的生活,积极正面的看人、看世界和对待自己的成长……

另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必然是“我们的”孩子,似乎只有圈内人才能真正无偏见地懂和爱孩子。不少AS和高功能孩子在十几、二十岁时,因为在学校里无法应对人际关系,或者之前多年累积的情绪压力爆发而导致“崩溃”,出现了精神障碍疾病的反应症状,有些直接被送进医院,从精神科医生那里得到一纸比如分裂样疾病的诊断,用药或直接住院处理,极少有医生会从头到尾地追溯孩子的成长史,深入了解谱系孩子发育的特点和需求,更不用说帮助孩子规划未来。
而养育谱系的我们,则有着真正的感同身受。为家长们着急、为孩子谋划,因为每个孩子的过去可能就是我们孩子的现在,每个孩子的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孩子的将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谱系家长之间的相互扶持,越来越多的爱心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动力和更持久的热情,创造出更具实质性的帮助。
孩子们需要各种支持,家长们需要抱团取暖。谱系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们撑起的一片天。
方老师4月2日





4月2日 21:00

喜欢我们,就设置为星标吧
在订阅号列表一眼就能找到我们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精彩推送了
(方法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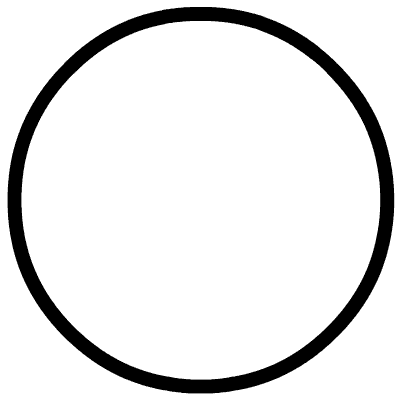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入以琳报名信息栏目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入以琳报名信息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