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特在其著作《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所讨论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一辩证被广为关注,但有趣的是,大多数讨论却集中于巴特在《教会教义学》中对此辩证的再度提及,而忽视了它在《罗II》中的核心地位。注意到此讨论的相对缺失,曾老师在文中不仅厘清了这套辩证背后的神学与哲学对话:从康德主义出发的不可能性到克尔凯郭尔(文中译作祁克果)式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而且条分缕析地论述了《罗II》中的七重不可能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分析这一辩证与巴特后期神学发展的关系,曾老师意欲表明,《罗II》在巴特神学中具有其独特性,而巴特后来对于“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一辩证的拒斥与重拾,恰恰说明了巴特神学自身的连贯性与自我修正性。
本文原发表于《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第29期(2020年6月)页121-155,已获得发表期刊和作者授权,特此感谢《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和曾劭恺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摘要
巴特第二版《羅馬書釋義》(以下作《羅II》)於1922年出版時,即因嚴肅挑戰了當時德語神學的主流範式而成為時代經典。關於《羅II》的二次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其中不乏探討其辯證法的著作;巴特筆下「不可能的可能性」之辯證,亦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特別是其於《教會教理學》(Die Kirchliche Dogmatik)III/3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此辯證在《羅II》中的功用,在德語及英語學界卻幾乎被完全忽略。本文旨在闡述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之辯證之於《羅II》的重要性,顯示其為貫穿該著作的核心主題,支撐整部釋義的神學架構。巴特這套取自聖經的辯證,與長十九世紀(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哲學與神學進行對話與辯論,交織成複雜的神學架構。本文文末從《羅II》文本的詮釋轉移至巴特後期神學的發展,探討巴特於《教會教理學》III/3重拾「不可能的可能性」之辯證後,如何用它來平衡他基督中心本體論當中的救恩論客觀主義傾向,以避免「基督一元論」的聯想與指控。簡言之,若欲明白《羅II》在巴特整體神學發展當中的獨特性,掌握「不可能的可能性」之辯證在這部著作當中的核心意義,乃不容忽視的關鍵。
關鍵詞:巴特;羅馬書;不可能的可能性;(新)康德主義;祁克果辯證法
Keywords: Karl Barth; Romans; Impossible Possibility; (neo-)Kantianism; Kierkegaardian dialectics
「不可能的可能性」:再思巴特第二版《羅馬書釋義》辯證法
曾劭恺
一、
引言
卡爾·巴特(Karl Barth)《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以下縮寫為《羅II》)於1922年出版時,即因嚴肅挑戰了當時德語神學的主流範式而成為時代經典。[1] 儘管他生涯中曾經數度修改神學方法與內容,但此早期著作至今仍是許多神學家的靈感來源。關於《羅II》的二次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其中不乏探討其辯證法的著作;巴特筆下「不可能的可能性」之辯證,亦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特別是其於《教會教理學》(Die Kirchliche Dogmatik)[2] III/3與IV/1當中所扮演的角色。[3] 然而,此辯證在《羅II》中的功用,在德語及英語學界卻遭到嚴重忽略。韋伯斯特(John Webster)曾簡略地提出,「不可能的可能性」是理解《羅II》當中「從恩典進入到人類歷史與行動的至要移動」(“the imperative movement of grace into human history and activity”)的關鍵,但至今仍少有學者注意到此辯證對於這部著作的重要性。[4] 麥考馬克(Bruce McCormack)鉅著《卡爾.巴特的批判實存辯證神學》論及《羅II》的章節多次提及「不可能的可能性」,但在探討這部巴特早期著作中的主要辯證主題時,卻對其置之不理。[5] 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雖注意到「不可能的可能性」在巴特早期神學的獨特性,但他僅提出「『不可能的可能性』這獨特的範疇,首先帶有爭辯性功能,宣稱自由派神學… 認為… 隨時皆可能者… 為不可能」。[6][7] 雲氏並未以文本細讀法分析這辯證如何支撐《羅II》的整體神學架構。
本文旨在闡述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之辯證之於《羅II》的重要性,顯示其為貫穿該著作的核心主題,支撐整部釋義的神學架構。明白巴特於此時期賦予此辯證的意義,亦有助於瞭解他在神學生涯不同階段中的發展與改變。我們將會發現,巴特這套取自聖經的辯證,與長十九世紀(Long Nineteenth Century)的哲學與神學進行對話與辯論,交織成複雜的神學架構。[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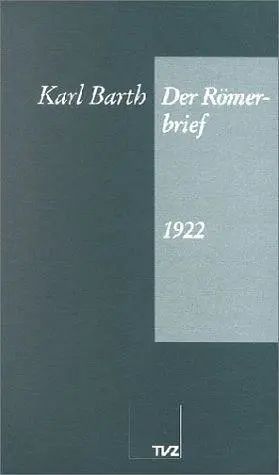
作者: Karl Barth
出版社: TVZ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副标题: Zweite Fassung 1922
出版年: 1999 16. Aufl.
二、
「不可能的可能性」: 神學與哲學背景
01
「不可能性」:康德主義的出發點
麥考馬克如此闡述「巴特在整個《羅II》階段中所處理的基本難題」:「神如何能夠使祂自己被人們認識,其之為啟示之主體的存有,在自我傳述的過程中卻未曾改變?」[9] 此核心神學關注,與巴特前一個思想發展階段(1915-1918)乃是一致的,在該時期「巴特一貫地預設:(一)康德知識論(在其觸及對於經驗實在性的知識上)的有效性,及(二)康德對形而上學批判的成功」。[10]
巴特的目標在於重建上帝對於人類理論理性的可知性。如麥考馬克所言,「在某個觀點上,巴特所有的努力,皆可被視為藉由康德克服康的嘗試;不是退縮到他身後,也不是尋求繞過他,而是前行穿過他」。[11] 他成熟時期的神學會以道成肉身為核心發展所謂「基督中心」本體論與認識論,但在《羅II》時期,他仍在自由派神學的影響下,視道成肉身為不可知的古典形而上教義。[12] 《羅II》所論述的啟示,乃是以基督復活這非歷史性及非時間性的事件為核心。

图片截取自The Center for Barth Studies官方视频
巴特在《羅II》中強調,只要世界仍是世界,那麼,上帝自我啟示的經世之工,在今世始終是不可能發生的;儘管上帝的揀選已使啟示變為可能,但啟示的可能性在時間、空間、可直觀的現象界中,仍始終不具任何可能。換言之,巴特以「不可能性」表達了康德為知識論所設的限制。
在此限制下,巴特在《羅II》採用一套神學方法,與康德超驗法(transzendentale Methode)的思維模式相似(馬爾堡新康德主義者視此為康德哲學的核心)。這是巴特在其後神學生涯的每個階段中都會繼續使用的方法。[13]
在《羅II》中,巴特訴諸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揀選論所表述的上帝主權,建構啟示之在體可能性(ontische Möglichkeit)的設準(Postulat),並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以下論述。他主張,信徒向著罪死(羅六10-11)乃是可驗證的事實,而這事實只能在基督復活的亮光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由於復活是非歷史性、非時間性的事件,所以它是信徒能夠藉以信靠上帝揀選的唯一嚴格意義上的啟示事件。換言之,揀選與復活對巴特而言乃是以信心接受的設準,超乎理性或經驗的論證;若無此設準,那麼,信徒向著罪死的後驗事實,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在此時期似乎仍將人對神的知識視為信心範疇的知識,與康德所謂的純粹理性(reine Vernunft)知識仍有一段距離。這意味巴特此時尚未成功跨越康德在「信心」與「知識」之間構築的藩籬。[14]
02
不可能的可能性:祁克果式的辯證
在《羅II》當中,人認識神的不可能性,基本上是康德批判哲學所造成的難題,但並不只如此。麥考馬克指出,「在啟示中所賜下對上帝的認識之所以會是個難題,在巴特看來,是由於兩個因素:一邊是人類認知的侷限,另一邊是神的揀選」。[15] 「人類認知的侷限」誠然是康德的批判哲學對現代德語神學所帶來的一大難題,但麥考馬克此處並未注意到,「上帝的揀選」所帶來的乃是巴特筆下的「可能性」,這與「人類認知的侷限」所構成的認識神的「不可能性」形成一種祁克果式的辯證。
事實上,就連「人類認知的侷限」都不僅僅是康德批判哲學所帶來的難題:在康德的第一批判中,純粹理性的侷限並非罪所構成,但巴特在《羅II》中卻強調,神與人之間的本體及知識論鴻溝,乃是人類墮落的後果。麥考馬克過於強調康德對早期巴特的影響,忽略了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為巴特帶來的啟發,特別是祁克果在《哲學片段》談到神與人之間「無限本質的差異」(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時所涉及的「罪的純理性影響」(noetic effects of sin)。[16] 巴特在1963年追憶道:「直到1919年,祁克果才嚴肅而更加全面地進入了我的思想,就是在我《羅馬書》第一、二版之間的關鍵轉折點…。使我們感到特別引人入勝、心曠神怡、受益匪淺的,乃是他那不屈不撓的批評…。我們看見他用其抨擊一切抹滅神與人之間無限本質差異的臆測。」[17]
路許克(Werner Ruschke)正確地指出,神與人之間無限本質的差異,乃是《羅II》的「基礎辯證」(Grunddialektik):「我們知道神是那位我們不認識的,是那位我們不可能認識的,因為神是神。」[18] 換言之,《羅II》的辯證特色乃源於「人類沒有臨近神的可能性」這神學難題,亦即人不可能獲得對神的知識,因為對於世界而言,神是「絕對祂者」。[19] 此辯證一方面是對康德的回應,一方面也抨擊黑格爾及士萊馬赫的觀念論思想,關於後者,筆者已有著墨,在此不贅。[20]

Søren Kierkegaard(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
巴特在《羅II》主張,歷史開始之前,人類的確曾處於墮落前的景況,享受與神共處的「直接生命」(das unmittelbare Leben)[21]。他在《羅I》稱此為「初源」(Ursprung),這在《羅II》仍是關鍵詞。[22] 人類從那初源墮落了,而這正是人無從認識神的核心肇因:人的墮落,使得神的自我啟示在人的主觀方成為純理性(noetisch)的不可能性。在此意義上,巴特在《羅II》所論述的「不可能性」其實更加接近祁克果,儘管他無疑亦受康德的啟發:對康德而言,人類墮落的影響主要屬乎道德理性的範圍,而非理論理性或純粹理性。
03
可能性、不可能性於祁克果筆下的辯證
雲格爾曾正確指出,祁克果的著作是巴特早期神學辯證法的重要來源。可惜的是,他並未詳述巴特筆下「不可的可能性」與祁克果的關連。[23] 由於麥考馬克在許多方面對雲格爾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當代英語學界通常提及雲氏對巴特早期辯證法的論述時,不會用太多篇幅處理,而會著重討論麥考馬克的觀點。稍早提及,麥考馬克否定了祁克果對早期巴特的影響,他聲稱「沒有任何好的理由,認為巴特讀過《哲學片段》或《非科學的結語》──至少在出版《羅II》之前的這時期沒有」。[24] 然而,麥考馬克並未為此觀點提出任何具體證據,而他處理巴特與圖奈森(Eduard Thurneysen)的通信時,完全沒提到巴特1921年1月22日的信件。[25] 巴特在其中明確指出,他撰寫《羅II》第五章的書稿前閱讀了《哲學片段》。[26]
麥氏承認,我們「很難確切知道巴特讀過祁克果的哪些作品、何時讀過它們」。[27] 他甚至同意,「毫無疑問,祁克果式的用語及概念,在《羅II》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8] 然而,他仍舊認定祁克果從未直接影響巴特在《羅II》時期的思想。麥考馬克引用拜因特克(Michael Beintker)對巴特辯證法的研究,聲稱「產生《羅II》特有的辯證型態所需的大部分概念要素,都已經在巴特透過他兄弟亨利[Heinrich]的《初源哲學》[Ursprungsphilosophie]接觸到祁克果之前,就已經成形了」。[29]
特爾臣(Sean Turchin)對此觀點提出了有力的反駁:
麥考馬克聲稱「一些特定的思維模態」已然成形,以此解釋《羅I》到《羅II》的戲劇性轉變,這造成一個問題,亦即他所指的究竟是哪些思維模態。假設這些「思維模態」乃建基於新康德主義,那麼我們是否應該相信,祁克果僅僅提供巴特一套與巴特特有的神學體系缺乏任何實質關聯的術語?奇怪的是,巴特在《羅II》的序言中歸功於祁克果,稱祁克果提供他恰恰這套「系統」,亦即建立在祁克果「無限本質區別」之概念的系統。新康德主義真的是這套反映祁克果思想的神學系統的靈感來源嗎──這套巴特自己承認借自祁克果的系統?[30]
”
在較新的研究成果中,除了特爾臣外,芭特爾(Cora Bartel)也有力地指出了祁克果對巴特早期神學的影響,儘管芭特爾並未處理麥考馬克的論點。[31] 然爾,特爾臣及芭特爾皆未發現「不可能的可能性」這祁克果辯證法在《羅II》中的重要性。
如稍早所述,雲格爾已注意到巴特筆下「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十分獨特的修辭。事實上,「可能性」與「不可能性」早在數十年前已是祁克果研究學界廣泛討論的課題,而巴特的用法與祁克果十分雷同。[32] 儘管我們無法確切得知巴特是否直接引用了《致死的疾病》關於「可能性」的論述,但他在《羅II》行文中使用「致死的疾病」一詞,似乎暗示他當時可能已經讀過這部著作。[33] 再者,《非科學的結語》當中「不可能性」的概念,實已暗示了其與「可能性」之辯證,而特爾臣已提出有力證據,說明了《非科學的結語》對巴特早期神學的影響。[34]
麥考馬克忽略了「可能性-不可能性」之辯證在《羅II》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它在《羅I》當中未曾出現的事實。若他注意到了這點,可能他對於祁克果是否為巴特在寫作《羅II》時提供了一套新的思維模式,會有不同的看法。
巴特在《羅II》將「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這出自共觀福音的神學真理視為「不可能的可能性」這辯證的決定性基礎。[35] 這與祁克果《致死的疾病》(1849)托名作者「反克理馬克斯」(Anti-Climacus)的論述同出一轍。後者稱「在神凡事都能」的真理為「真盼望與真絕望」的「決定性事物」。[36] 反克理馬克斯寫道:「唯有當一個人被帶到最徹底的極端,以致在人而言,任何可能性皆不復存在時,決定性的肯定才會臨到。此時,問題就在於他是否願意相信在神凡事都能──亦即,他是否願意信。」[37]
正如巴特在《羅II》稱宗教為永遠無法觸及神的「人類可能性之顛峰」(見稍後闡述)[38],反克理馬克斯亦提出,「有時人類想像力的創意足以構成可能性,但在最後關卡,也就是當信心的行動成為關鍵時,唯一的幫助乃是:在神凡事都能。」[39] 相似地,「救恩在人而言乃萬事中最無可能者;但在神凡事都能!這就是信心的爭戰,它瘋狂地為可能性爭戰。」[40] 我們稍後將發現,反克理馬克斯在人類不可能性與神之可能性的辯證框架下論述信心與救恩,在《羅II》辯證中產生深刻的共鳴。
祁克果筆下,反克理馬克斯對於「可能性」的論述與另一位托名「約翰尼斯.克理馬克斯」(Johannes Climacus)在《非科學的結語》(1846)所闡述的「不可能性」相輔相成。在一段論及「可能性」的簡短篇幅中,克理馬克斯如此評論道成肉身的弔詭:
「歷史性的事件,就是那位神、那位永恆者,在時間當中的某個特定瞬間,以一個殊相之人的身份臨到了。在這個案中,這歷史性事件的特徵,將思辨轉化為一個令人愉悅的幻象,因它並非單純歷史性的,而是唯有違反自身屬性方能成為歷史的某物。」[41]
”
雖然《羅II》的基督論仍規避道成肉身的教義,但巴特在其中論及基督非歷史性、超歷史性的復活為啟示的核心時,誠然呼應了祁克果此處所述的基督教之弔詭:「它並非單純歷史性的,而是唯有違反自身屬性方能成為歷史的某物」。祁克果托克理馬克斯之名指出,此弔詭對於人類理性會顯得「荒謬」──祁克果的用意在於使用克理馬克斯的非基督教觀點來間接表達基督教的真理。[42] 拉斯穆森解釋托名克理馬克斯筆下「荒謬」一詞:「儘管『荒謬』在其日常含意中所指涉的『愚昧』及『可笑』從理性的角度而言清楚明白…,但這用語在更大規模的對話中暗示,克理馬克斯設計了這整個交流,以致『荒謬者』成為雙關語,暗指理性對於弔詭者的聾聵。」[43]
克理馬克斯主張,那絕對的弔詭不可能被直接地理解,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可能性」的概念。[44] 他與反克理馬克斯有一顯著的差異:反克理馬克斯筆下的「不可能性」在乎人類的侷限,而「可能性」則在乎神的全能(「在神凡事都能」);但克理馬克斯論及「可能性」時,卻前後一致地意指人類在其有限的能力範圍內可行之事。巴特提出「不可能的可能性」,則是正反克理馬克斯之間的辯證,結合了二者的用語。例如,巴特稱哲學與宗教為人類的可能性,又稱信心、稱義、救贖、啟示為人類的不可能性,這些在人而言不可能之事,皆因神的大能而變為可能,因為在神凡事都能。
克理馬克斯用「可能性」指涉人類的能力,寫道:「可能性作為理解,恰恰是往後退卻的步伐藉之踏出的理解,在其中信心來到了盡頭」(英譯:“…possibility as understanding is precisely the understanding by which the step backwards is taken in which faith comes to an end”)。[45] 他解釋道:「…基督教是那絕對的弔詭…,正因它摧毀了一個本為虛幻可能性(用異教的類比來說,就是神在永恆中的「成為」),並將其化為實存,而這就是那弔詭…。」[46]

宗教是人類想像能力範圍內的可能性,在其中「神完全可以與人合為一體」。[47] 但克理馬克斯說這可能性──巴特稱其為人類「最高的可能性」[48]──被絕對的弔詭摧毀了,這弔詭性就在於道成肉身的事件「會在現實中發生於一名個別的人」。[49] 簡言之,對克理馬克斯及巴特而言,以基督教之弔詭為對象的信心,在人類理解能力範圍之內乃是不可能生發的。
巴特主張,唯因在神凡事都能,人對基督的信心才成為「不可能的可能性」。不可能性與可能性之間的辯證,乃巴特在《羅II》中表述其神學思想的巧妙方法,用以描述神的揀選如何克服人類罪惡的純理性影響,最終將神自我啟示的主觀面變為可能,儘管在人而言這可能性在今世始終是不可能的。本文以下篇幅將探討「不可能的可能性」如何構成《羅II》的整體神學架構。這辯證的基礎原則正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50]
三、
《羅II》的辯證結構:七重「不可能的可能性」
在開始探討「不可能的可能性」辯證時,我們首先應當留意,這詞彙在《羅II》始終是指神用以克服人在罪中之全然無能的全權恩典行動。如上所述,這辯證要表達的乃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聖經教義。[51] 如此,啟示、救贖、揀選等上帝行動並非客觀、在體性(ontisch)意義上的不可能性,而是人在墮落景況中的主觀、純理性(noetisch)不可能性。
巴特在《羅II》中一共提出七重墮落人類能力範圍內的不可能性,可按其邏輯關係整理如下:
(一)啟示:人對神的認識;
(二)啟示:人作為亞當的自我認識;
(三)啟示:人對危機(Krisis)的認識;
(四)救贖與稱義
(五)基督的復活
(六)人對基督的信心
(七)揀選
除了上述第一個不可能性之外,其餘六者皆為一系列在邏輯上相互連貫的上帝行動,每一者皆將前一重不可能性變為不可能的可能性。第一個不可能性則囊括了其餘六者。巴特在《羅II》所處理的主要難題是:我們既以上帝自我啟示的可能性為後驗的設準,那麼這不可能發生的事,如何變為了可能?巴特對此難題的解答,關鍵在於他在羅馬書文本基礎上所建構的預定論,誠如詹森(Robert Jenson)所言:「預定論是《羅馬書釋義》的核心,亦是其基本結構模式最精簡的表述。」[52]
01
第一重不可能性:啟示──人類對神的認識
巴特主張,神對人的自我啟示乃無庸置疑的後驗事實,而啟示之可能性乃他神學的起點。例如,「神的聖言交託」於猶太人(羅三2):巴特認為,這意味神將自己啟示於猶太人,所以對他們而言,「那未識者[Nicht-Gekannte] 如此就可能成為知識的對象[Gegenstand von Erkenntnis]」。[53]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巴特論及啟示的可能性時,他的「起點」並非「一個將其自身呈現於人類認知者因而可被認知的『客觀實存』之經驗世界的存在的(非批判性)預設」。[54] 在康德批判哲學的侷限下,巴特認為神在人之純粹理性的限度內是無可直觀、無可感知的。對巴特而言,上帝啟示的可能性乃不證自明的神學設準。借用《哥廷根教理學》的詞彙來形容《羅II》的論述:啟示的可能性乃「後驗」的既成事實。[55]
然而,巴特在此並非迴避康德的批判哲學,否定神被人認識的不可能性。上述可能性始終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一個因神的大能而變為可能,但在人而言卻始終不可能發生的真實可能性:「因著他們[猶太人]對那不可能者的追憶,他們自己就是上帝立於可能性之範域的[後驗]證明,[此可能性]並非諸多可能性之一,而是… 不可能的可能性。」[56]
但啟示的不可能性究竟何在?對此問題,巴特的觀點其實與康德有相異之處。對康德而言,人不可能以神為純粹理性知識的對象,乃是由於本體與現象之間的鴻溝,而非人類的墮落。康德認為人類墮落的影響並不在於純粹理性,而在於實踐理性。[57] 相較之,巴特在《羅II》強調,人類理性無法認識神,並不只因人類認知受限於時間與空間的超驗形式;歷史時空成為人類理性的牢籠,乃是人類墮落的後果。神的啟示對於人類理性的不可能性,乃出於人的罪:「對我們而言,神是未知的,且始終是未知的;我們在這世上無家可歸,且始終無家可歸;我們是罪人,且始終是罪人。」[58] 巴特在《羅II》中甚至以墮落來定義「人類」與「歷史」:「『人類』一詞指涉未蒙救贖的男女;『歷史』一詞意味侷限與敗壞;『我』這代名詞代表[神的]審判。」[59] 因為「我」這主體是墮落而有罪的,所以它無法以神為認知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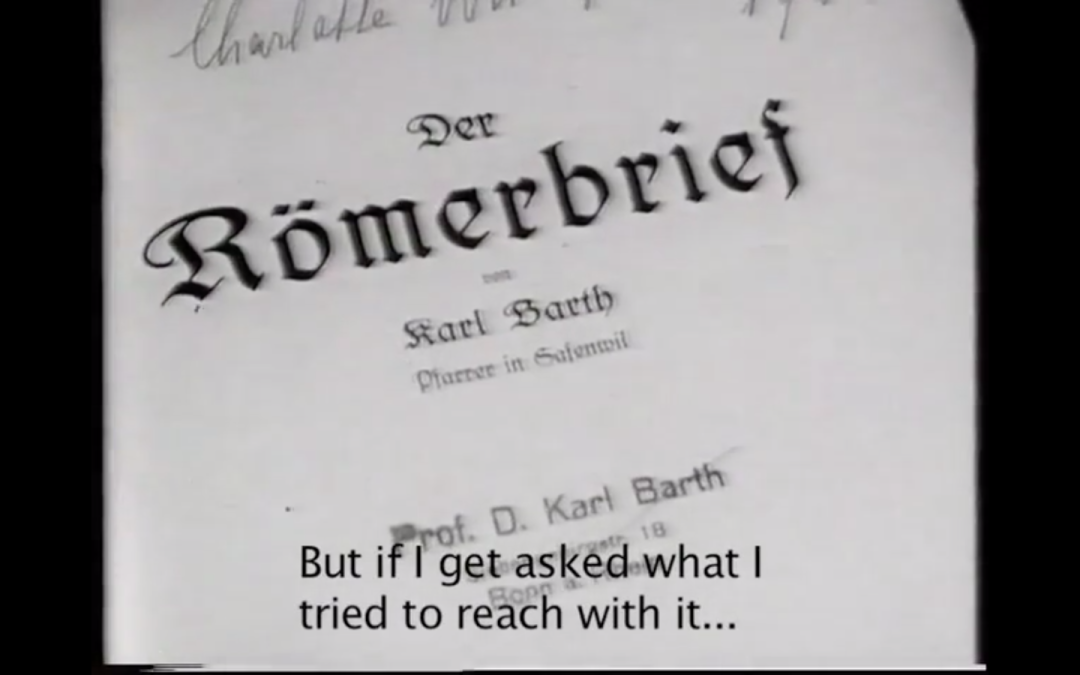
图片截取自The Center for Barth Studies官方视频
巴特以康德主義的思維主張「我們唯一能認識的世界,是屬於時間、事物、人類的世界」,並區分「創造」與「自然,亦即『世界』」。[60] 自然世界乃「我們能夠觀察」的,它指涉「可見的歷史,[此歷史]僅僅是進程」。[61] 巴特認為,「世界」乃墮落的產物。相較之,創造則「超乎我們的觀察」。[62] 那「一去不返… 的永恆創造之瞬間」屬乎墮落前的狀態,人類在其中尚未落入不捨晝夜的歷史洪流。[63]
墮落之前,「神與人曾是一而非二」;神與人存在於「生命的一體」中,[64] 即德意志觀念論與浪漫主義所謂神人之間「直接的生命[das unmittelbare Leben]」。[65] 在此「直接的關係」中,人對神的認識不需任何中保/中介(Vermittlung),因為神對人而言是可直觀(anschauen)的。[66] 巴特稱此墮落前狀態為人之「初源 [Ursprung]」,雖已逝而不返,至今卻仍不斷「在我們裡面喚起我們與天地之主同住的回憶」。[67]
時間的洪流始於人類「原初」的墮落,這事件發生於「時間開始之前」,摧毀了神人之間的直接關係。[68] 死亡也由此入了世界,這不只是個別的肉身之死,更「是由永恆過渡到時間的記號,這當然不是在時間內發生的,而是原初歷史中的過去式事件」。[69] 由於罪與死,「現在一切都是具體而間接的」。[70]
此處巴特用「具體」一詞駁斥源於黑格爾的觀念論傳統。黑格爾用「具體」(konkret)指涉殊相與共相的終極一體性:精神在其絕對的階段中,具體地與歷史現象合一。巴特則堅持,具體的歷史進程,乃墮落的產物;此進程中的間接性,並非神與人之間真正的復和。在世界上,人不可能認識神,因為墮落之人所能認識的客體皆限於時間與現象,而神並不在其中。簡言之,神的自我啟示對於人類主體而言是不可能的,因為「啟示」意味神使人認識祂。
此「不可能性」,很可能是巴特借用祁克果以反駁黑格爾的修辭。史督華(Jon Stewart)指出,克理馬克斯所論述的「不可能性」,乃是「對某種黑格爾主義的絕對認知觀點的批評」:「任何有限、殊相的個體達到永恆的認知,乃是不可能的,因這意味全知性」。[71]
巴特在此所處理的難題,並非人如何能夠認識神:對他而言,從這問題出發,導致了十九世紀新更正教神學的潰敗。自從與自由派決裂後,他就一以貫之地堅持,神的自我啟示乃後驗事實。在《羅II》中,他主張神學所要探索的問題是:神既已啟示祂自己(啟示對巴特而言始終涵蓋人類這方的主觀面,亦即人對神的認識),那麼人對神的認識如何從「不可能性」變成了「不可能的可能性」?這就是接下來六重「不可能的可能性」所要回答的問題。
02
第二重不可能性:啟示──人作為亞當的自我認識
在探索神自我啟示的可能性時,巴特借用了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中的著名辯證:「若無對自我的認識,就沒有對神的認識」、「若無對神的認識,就沒有對自我的認識」。[72] 巴特亦認為,墮落之人既不可能認識神,那麼亦無從認識自我,亦即自我認識為「亞當」:「亞當」之名指涉「墮落而遭監禁的受造物」。[73] 一個人若要得著對基督之復活的信心,就必須先認知基督之死,但人若不認知自身的危機(Krisis),就無從明白基督之死。人的危機就是作為亞當,站在神的忿怒與審判底下。
巴特筆下「危機」一詞並非全然負面,而是以類似黑格爾的辯證模式指涉上帝否定性的恩典:人的罪否定神與祂的創造,而神藉由忿怒與審判、棄絕與刑罰,否定了人的罪。如此,「危機」乃「對否定的否定」,這「棄存揚升」(Aufhebung)的過程帶來揀選與復活。人對此危機的知識,也因此以作為「亞當裡」的罪人之身分的自我意識之覺醒為前提。
巴特認為,此意識覺醒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亞當在歷史… 的平台上並無存在」。[74] 人類認知的對象侷限於時間與空間,而真亞當的存在是非歷史性的。人類理性所能認知的亞當,是已然墮落入歷史時空的亞當;「亞當在變成必死之身前是什麼」,既然「在定義上是非歷史性的」,就不可能由人的理性所認知。[75] 「我們歷史性的知識乃… 受限於… 亞當之死。」[76] 換言之,「全人類從他們與上帝之聯合的非時間性墮落」在其自身對我們而言是不可知的,儘管其現象已「由他們將真理監禁於不虔不義」的事實所「顯明」。[77]
因此巴特問到:「我們明白『墮落──從神那裡墮落』之含意的能力從何而來?」[78] 巴特的答案乃基督的復活:「[從神墮落]的亞當並非處於他歷史之無關係性中的亞當,而是處於他與基督之非歷史性關係中的亞當。」[79] 我們能夠「建構任何關乎亞當墮落的概念理解」的途徑,就是將「基督從死至生的高升」存於意念當中。[80] 這是因為「透過亞當而進入世界的罪,正如在基督裡向世界顯明的義,是無時間性而超驗的」。[81] 換言之,基督的復活是人類能得知亞當非歷史性之墮落的唯一途徑。
基督相對於亞當在知識論上的優先性,不只建基於純理性的因由。就在體性而言,亞當亦無獨立於基督的存在:「亞當並無獨立、實證肯定的存在…。他唯當煙消雲散時方得存在,而唯當他在基督裡不復存在時方被肯定。」[82] 第一位亞當是「將要來的第二位亞當的預象,如同祂的光所照出的影子。他作為構成基督邁向勝利的背景的『瞬間』而存在,在那場景中世界與人類從墮落被轉化為義、從死至生、從舊至新。」[83] 簡言之,亞當只有在基督的復活中才被揭示為亞當。在基督復活之外,人類無從自我認識為亞當。
03
第三重不可能性:啟示──人對危機的認識
問題是,對基督復活這事件的信心,解釋起來其實極其複雜。首先,基督的復活本身就是無時間性而非歷史性的,因此它自身對於墮落之人而言已然不可認知。不但如此,巴特甚至主張,復活事件自身都是不可能發生的。[84] 再者,人對復活的知識必然是間接的,這不只是由於復活的非歷史性,也因為它是棄存揚升的過程。基督的復活是「對否定的否定」的結果。[85] 用路德的用語形容之,它是「死亡之死」。[86] 基督的死亡之為恩典,「乃因它的否定是肯定性的」。[87] 明白基督的復活,就是明白基督之死所否定的否定性。
最初的否定,就是「透過罪,死亡作為危機進入了世界」。[88] 這「終極的危機」是一個至高的「否定」,威脅著「一切的存在」。[89] 它並非生發於神原初的創造,而是出於神作為「賜下律法因而在律法之上者」的「忿怒」與「審判」。[90] 然而它又是神恩慈的介入,令世界不致全然離棄祂而滅亡。因此這危機是「神忿怒的記號以及祂臨近的拯救的訊號。不論如何,死亡是神的命令──『停下來』──而我們無法悖逆它。」[91] 換言之,拯救的過程不只是基督的復活,也包括起初的否定:救恩是整個棄存揚升的過程。人對復活的知識,也因此必然涉及對危機的理解。

《罗马书释义》手稿,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問題是,「我們對 [此危機] 的肯認以及理解它的能力從何而來?我們認知到世界是世界的可能性,以至我們因而藉由將它相比於另一個對我們未知的世界而如此侷限它的可能性,究竟從何而來?」[92] 神被認識為不可認識的神,乃單單「在終極而無所不包的危機的亮光中」變為可能的,但「這領悟與認知乃超乎我們知識的可能性」,它雖奇妙地變為可能,但在其自身卻仍是「不可能之事」。[93]
巴特在此以他《羅II》時期的一貫方法,從後驗事實出發,亦即人對危機之知識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問題並非人對危機的知識是否可能,而是:此在其自身始終不可能之事如何已然變為可能?
但我們在此必須先退一步問:巴特因何認為這知識在其自身是不可能的?此不可能性的因由與人類自我認識為亞當的不可能性同出一轍:亞當的墮落是非歷史性的。死亡透過亞當非歷史性的墮落進入了世界。「死亡是罪惡的另一面」。[94] 在此他所指的並非肉身的死亡,而是奪去受造物真實生命的死亡,這真實生命「就是人們與神的關係」。[95]
人不可能認知這真實的危機,因為它超出了人類單純理性的限度。儘管罪與死的種種今世現象充份地將神的忿怒顯明出來(羅一19-21),罪人卻無法認識神為「未知者」。[96] 這並不意味宗教是不可能的。反之,宗教是「人類可能性的顛峰」。[97] 儘管如此,宗教作為「至高可能性」,卻是「我們 [與神] 不可見的關係最徹底的分離」。[98] 亞當「滿足於較低的諸般可能性」時,夏娃將人類最高的可能性呈顯於他:宗教就是「明白善與惡、生與死、神與人的慾望」。[99] 宗教所造的神明不是真神,因為宗教之神不是不可能的可能性,而是人類在世上可直接認知的對象。巴特於此尖銳地駁斥士萊馬赫的名言:「宗教根本不是『與無限者和諧共融』」。[100] 巴特呼應祁克果,宣告宗教無法逃避「我們站在其下的致死的疾病」。[101]
宗教最極致的價值,就是幫助人類面對死亡,但宗教始終無法揭示死亡的真實含意,亦即危機,因為正如先前所述,死亡作為危機,既是神的審判,更是神的恩典。人類的危機在於,人並非單單被神棄絕,而是處於祂的「雙重預定」之下。[102] 宗教所面對的死亡,卻僅僅是「神的『不』,在其中祂的『是』被隱藏起來」。[103] 宗教佯稱人可以得知善惡而獲得生命,但事實上分別善惡樹所帶來的知識,導致的卻是死亡。如此,「宗教是個無底深淵:它是驚怖。」[104]
倘若就連宗教這人類至高可能性都無法使我們認知到人類的危機,那麼對危機的知識就誠然不可能了。如此,究竟是什麼使這不可能性變為可能的?巴特的答案又是基督的復活。的確,若不明白危機,就無從理解基督的復活,但反之亦然。在基督的「復活當中,那可被驗證之否定──亦即我們之被埋葬──的整體嚴肅性與能量,皆被揭示而生效」。[105]
唯有基督的復活將死亡揭示為恩典:死亡以審判的姿態,藉由亞當的罪進入了世界,基督卻藉著死亡審判並治死了死權。「死亡不會是恩典,假如它透過一系列的負面之事使人類的可能性倍增,這些負面之事包括苦修主義、『回歸自然』、默觀崇拜、神祕死亡、佛教的涅槃、布爾什維主義、達達主義等。」[106] 宗教的失敗,就在於它倍增人類的可能性,卻始終無法觸及那不可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恩典之為恩典,在於它乃負負得正的危機:「恩典不會是恩典,假如領受它的人不處於審判之下。」[107] 唯有「在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亮光中」,我們才「可能認知」死亡為危機,亦即明白死亡既是審判亦是拯救。[108]
04
第四重不可能性:救贖與稱義
換言之,認知死亡為危機,就是認知危機為救贖。但救贖作為「從亞當到基督的移動」[109]、「『此處』與『彼處』的聯合」[110],又如何可能呢?對巴特而言,神人之間無限本質的鴻溝就意味,「這世界因為是我們的世界,所以是罪已進入其中的世界」,而「在這世界當中,在這地上,在這天底下,沒有救贖,沒有直接的生命[kein unmittelbares Leben,亦即人與神的直接、不需中介的關係]」。[111] 簡言之,只要世界仍是世界而神是神,救贖就無任何可能。
《羅II》救贖論的強烈終末導向,在此值得一提。巴特主張,救贖的不可能性在今世意味,「救贖只能發生於將來的那日,當新天新地出現時」。[112] 然而,救贖在今世並非不存在,儘管它絕非簡單、直接地存在。救贖在今世乃辯證式的可能性,而非簡單的現實性:「藉由祂的死,祂宣告了我們的救贖的不可能之可能性,並且彰顯祂自己為從非受造之光而來的光、上帝國度的先鋒信使。」[113]
我們必須注意,在《羅II》當中,基督之死本身並不構成救贖。[114] 它是對否定的否定,但雙重否定僅是棄存揚升的前二個階段。基督之死在其自身並不是非時間性、非歷史性的,因此它只能成為救贖之可能性的先鋒信使。只要人類仍在這世上,
…我們就沒有可能將一件時間內的事物投射於永恆,或將永恆侷限於時間的範域。相似地,我們不可能將我們行為的某個片面從它的人類處境抽離出來,並宣稱它在神審判座前被稱為義,正如我們不可能將某個元素從上帝的義抽離出來,並在此抽離狀態中認為它能夠被舒適地植入人類行為的結構當中。[115]
如此,正如救贖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稱義的可能性也始終是不可能的。儘管稱義的可能性已在今世被開啟,但它的實在性之所在卻仍處於歷史時空之外。「神的義是個浩瀚的不可能性…。我們沒有任何可誇的,不論過去或將來,不論在那『瞬間』之前或之後──它並非時間內的瞬間──在那一刻號角將吹響,人赤身站在神面前,在他們的裸露當中,他們將被神的義袍所遮蓋。」[116]
巴特在此使用宗教改革的神學用語,排除了羅馬公教天特會議關於「內注之義」的教導,以在神學上維護神人之間無限本質的差異。在哥廷根-明斯特(Göttingen-Münster)時期的一封書信中,巴特稱此差異為「天地之間的巨大加爾文主義距離」。[117] 然而,《羅II》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辯證,與巴特成熟時期所採用的宗教改革「同時性」(simul)的神學文法仍有差異。在《羅II》時期,巴特仍未建構「與基督聯合」的救恩論以及位格內-非位格(enhypostatic-anhypostatic)的道成肉身基督論,因此巴特無法將「義的歸算」描述為在基督裡的既成現實。《羅II》的救恩論及救贖論有極強烈的終末導向,以致稱義與救贖在其中只能被形容為「未然」,卻無「已然」可言。
相較之,罪的現實性是直接可知而不具辯證性的:它是「可能的可能性」。[118] 「在罪中的持續」,對於「新造的人」而言的確被基督的復活所「排除」因而變得「不可能」,而這說法絕非只是「比喻」。[119] 然而,它也不是既成的現實。罪的不可能性是絕對屬乎終末的,因為基督的復活是絕對非歷史性的。因此,跟隨基督的人在今生持續犯罪,並非「同時為義人與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的弔詭。罪在今世是可知的既成現實,毫無弔詭可言;救贖與稱義在今世則非既成現實,而是弔詭的不可能之可能性。[120]
這與巴特在《教會教理學》III/3-IV/3稱罪為「本體論的不可能性」與「不可能的可能性」形成鮮明對比。[121] 在《羅II》之後,巴特幾乎不再使用「不可能的可能性」一詞,而當他在III/3再次使用這辯證時,他已將基督的救贖視為萬世以先已然永恆成就的客觀本體現實。他甚至不再跟隨祁克果而稱基督神人二性為「弔詭」:「神成為人並且是人,並不弔詭或荒謬。它與神的概念並無矛盾。它使這概念圓滿。」[122] 反之,「人欲變得如神一般,誠然是弔詭而荒謬的。它與人的概念相矛盾。」[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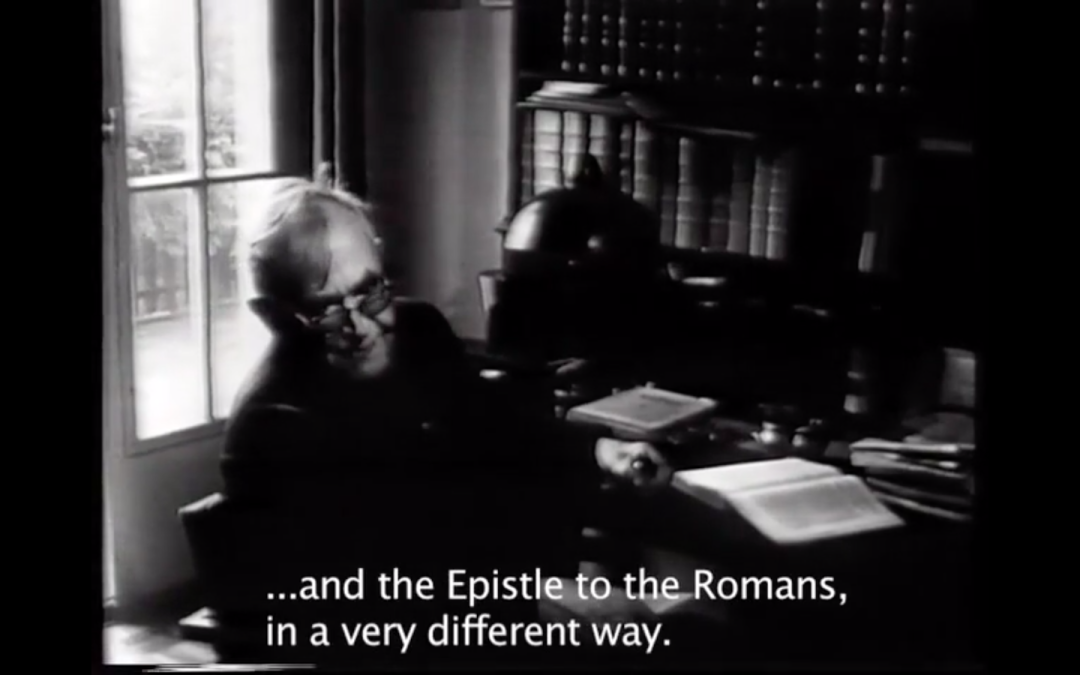
图片截取自The Center for Barth Studies官方视频
相較於上述巴特成熟時期的客觀主義救恩論(objectivist soteriology),「不可能的能性」以及救贖與稱義之「未然」在《羅II》中反映一種強烈的終末導向的救恩論(eschatological soteriology)。由於救贖與稱義在今世始終不具可能,所以基督之死只能是此二者之可能性的宣告,卻不能成為此可能性的因由,甚至不能成為此可能性的適切啟示。嚴格而言,只有基督的復活才是救贖與稱義的因由與啟示,因為基督之死屬乎歷史時空,復活則超乎歷史時空。[124]
05
第五重不可能性:基督的復活
基督的復活使啟示、救贖、稱義等不可能性變為可能。問題是,復活在這世上,亦是不可能的。巴特不僅主張人不可能認知基督的復活,更指其為三大人類不可能性之一(另二者為人對神的認識,以及「『此處』與『彼處』的聯合」)。[125] 如此,復活又如何從不可能性變為了不可能的可能性?
巴特處理此問題的方式類似祁克果對道成肉身的論述,採取了在體性-純理性之區別。在體性的答案相當簡單:「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126] 純理性的層面,則涉及《羅II》的超驗法。簡言之,復活必須具有可能性,否則啟示之可能性的後驗事實就無從解釋;基督復活所帶來的新生命,在現今亦非單純地不存在或不可能,而是作為不可能的可能性,可經歷地「壓迫著我在罪中的堅持」,成為「對我的時間性存在與思想與意志的批判」。[127] 新造之人並非形而上的幻想:「我是實際地[in der Tat]向罪死了。」[128] 「我們能夠在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亮光中肯認那將來之日的能力與意義,亦即新造之人與新造的世界的日子」,乃是「因為我們已然感知了」恩典、公義、新生命在現下的不可能之可能性。[129]
也是在基督復活的不可能之可能性的亮光中,死亡被揭示為恩典、危機為福音的大能、十字架為拯救。「我們與復活的大能相遇…:不可能性變成了可能性。」[130] 如此,基督的復活就啟示了死亡之死以及新生命。基督的復活儘管超乎時間與空間因而無可感知,但藉由信徒可驗證的新生命,我們就知道基督的復活必須是可能的。
在《羅II》當中,基督的復活並非邏輯推論的結果,而是(新)康德(主義)的超驗論證當中的設準,用以解釋新生命等後驗的不可能之可能性。對巴特而言,基督的復活並非神學反思的結論,而是其預設之出發點。
那麼,究竟是什麼事件,使得基督的復活變成人類理性可能認知的對象?回答此問題時,巴特自始至終未曾逾越康德劃下的知識論界線:啟示事件必須在某種意義上發生於人類感官可直觀的現象界中,亦即屬乎歷史時空的世界。巴特稱,既然新生命是在舊人被治死時開啟的,那麼基督復活的真理就必須透過祂的死來明白:
我們是新造之人的真理…乃在其出發點上方可被我們理解。而這出發點對我們而言就意味舊人的結束。這是此真理當中唯一能被我們看見的層面;唯有在基督的十字架當中,我們才能理解祂復活的真理與含意。[131]
”
當然,如稍早所述,十架本身並不具啟示性,因為從永恆之神而來的啟示必須是非歷史性、非時間性的永恆事件。基督的復活如此,十字架則不然。然而,神對人的啟示,必須以歷史時間為媒介,才可能被人感知。巴特在《羅II》中主張,十字架是神命定的歷史媒介,用以折射復活的亮光。他將復活與十架喻為太陽與陽光:「在深谷底下聳立著雄偉的橡樹」,其「頂端的枝椏」遮蔽了太陽本身,但「陽光於清晨照耀著我們,我們就看見別人都看不見的:我們見到將來之日的太陽,於是喜迎歡呼:『主,願祢來!』」[132]
但正如稍早所述,十字架乃是負面的。在其自身,它不過是死亡、軟弱、暴力、不義的記號。倘若復活之光要穿透十字架的遮蔽而被人看見,那麼唯有信心的雙眼方得見這光:「唯有在基督的十架當中,我們才能理解祂復活的真理與含意。我們只能相信那位新造的,而且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只能相信我們真的是相信的。」[133] 巴特此處的修辭無疑刻意帶著濃厚的祁克果色彩。[134] 復活的純理性不可能性,乃是在信心凝視基督十架時,方變為不可能的可能性。
06
第六重不可能性:人對基督的信心
然而,人對基督的信心又是另一重不可能性。這是因為基督作為死在十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穌,並非啟示的適切媒介:
耶穌作為罪人站在罪人當中;祂將自己全然置於世界當得的審判底下;在祂將自己所置之處,神只有在被質疑時才臨在;祂取了奴僕的樣式;祂走向十架與死亡;祂最高的成就,是負面的成就…。然而,恰恰在此否定中,祂就是人類進程的每項可能性的成就…,因為沒有任何可想像的可能性,是祂沒有從自身剝奪的。在此祂被肯認為基督…。在祂裡面,我們在地獄的深淵中凝視神的信實。[135]
在此巴特尚未發展迦克墩模式的基督論。主導此處論述的,乃是康德批判哲學的原則:巴特在《羅II》中仍堅持,耶穌作為歷史時空中人,不可能直接等同於神的啟示。他克服康德難題的方法,則是祁克果式的辯證:「我們對那新的日子的眼見,始終是間接的眼見;在耶穌裡,啟示乃弔詭,不論它如何客觀而放諸普世皆準。神之信實的諸般應許在耶穌基督裡已得實現,並非且永遠不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因為在祂裡面,這真理乃是在其終極的隱藏性以及至為深奧的隱密性中顯明的。」[136]
毋庸置疑,上述辯證有深刻的路德十架神學背景:「在祂[耶穌]裡面,祂[神]全然隱藏祂自己,為要將自己唯獨顯明於[人的]信心。」[137] 神的信實並非人類感官所能感知。[138] 唯獨信心能夠認知神的信實。巴特用祁克果的著名修辭,主張信心「始終是朝向未知的黑暗的一躍」,因為「在耶穌裡的啟示… 必須是對祂的不可測透性最徹底的隱藏」。[139] 「信心」並無「任何必要的前提」──信心不接受任何證據或推論──反之「信心就是自身的起始、自身的前提」。[140] 因此,「對所有的人而言,信心同時是簡單又困難的;它對所有人而言皆是討厭的…;它對所有的人呈現同樣的羞恥以及同樣的應許;對所有的人而言,它都是朝向虛無的一躍。而它對所有人皆是可能的,唯因它對所有人而言同樣不可能。」[141] 簡言之,人對基督的信心是不可能的,因為「拿撒勒人耶穌,即肉身中的基督,是歷史上諸般可能性的其中之一;但祂又是具有一切不可能性的特徵的那個可能性」。[142]
然而,人必須藉由對基督的信心方能認識神,而人對神的認識既已成為不可能的可能性,這就意味不可能成就的信心亦已變為可能。這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巴特的答案在於「上帝信實的不可能之可能性」。[143] 如稍早所述,在《羅II》當中,「不可能的可能性」必然指涉神的作為。在人自身而言,一切之事唯有可能(例:宗教)與不可能(例:信心),並無任何辯證弔詭可言。但神的作為卻創造出不可能的可能性。「上帝信實的不可能之可能性」,意指「在信心的弔詭中,神的信實已然足夠;因為藉由它,我們站上平穩的地面,並帶著確據前行」。[144]
但神又如何憑著祂的信實,喚醒罪人的信心呢?揀選論在《羅II》中的重要性,就在於回答這最為核心的問題。
07
第七重不可能性:揀選
「揀選」在《羅II》被定義為神在人類主體中喚醒信心的行動。神是「全然的祂者」,而神的行動在這世上始終是不可能的。[145] 「揀選之可能性唯有在應許的形式中,人方得與其相遇。」[146] 神的「應許」乃「在一切指向真理,亦即指向神蹟、聖靈、不可能性的事物當中被理解」。[147] 換言之,墮落之人作為理解的主體,唯有在不可能之可能性的形式中方得與神揀選人的行動相遇。
正因揀選的可能性在今世始終保留著不可能性,所以棄絕與揀選必然是一體兩面。揀選的不可能性意味棄絕的可能性,而巴特在《羅II》中定義後者為神任憑人不信祂、從人收回信心之恩賜的行動。「不可能的可能性」在此就成了「雙重預定」的同義詞,但這僅僅適用於侷限在歷史時空當中的墮落世界。在終末論的意義上,「棄絕的可能性」已經被神「永遠地克服了」。[148]
因此麥考馬克指出,「在此生涯階段中,巴特的揀選論運作於兩個獨特的層面」。[149] 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描述之(這些術語在《羅II》中反覆出現),在歷史與時間的終結,亦即永恆的終末層面上,棄絕乃屬乎過去的瞬間(Moment),它被定立(gesetzt),僅僅是為了永遠地被揀選的行動棄存揚升(aufgehoben)。在這層面上,棄絕被定義為神將人類侷限於時間歷史之困境的行動,而揀選則是神藉由基督的復活對墮落歷史時間的否定,此雙重否定的棄存揚升過程,就將人類提昇至永恆中。揀選在此意義上乃以普世為對象。詹森解釋:「雙重預定的兩個面向之間的關係…,無非是我們已經套討過的時間與永恆之間的關係的另一種形式;因為時間之有別於永恆,其含意即在於棄絕,而永恆相對於時間,其意義則是接納。在時間當中,我們都是被棄絕的;在永恆當中,我們都是被揀選的。」[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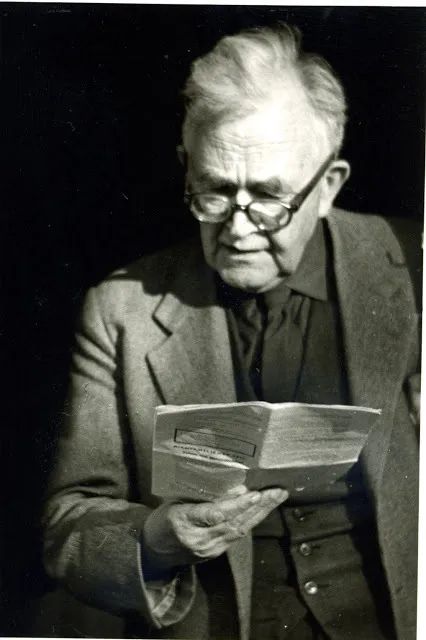
正如基督的死與復活不是等量的對偶,雙重預定在永恆終末的意義上,亦「不涉及任何平衡關係,反之…,它乃揀選勝過棄絕、愛勝過恨、生命勝過死亡的永恆凱旋」。[151] 麥考馬克稱此為「從普世棄絕邁向普世揀選的移動,發生於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當中」。[152]
相較之,在歷史時空的層面上,揀選則指涉「神在我們裡面喚醒信心,因而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153] 在此意義上,揀選事件乃不可能的可能性,而棄絕的威脅在終末之前始終不得消除。神有主權在任何人一生當中的任何一刻揀選或棄絕那人。儘管在永恆終末的層面上,揀選勝過了棄絕,但「在時間的每個瞬間當中,這勝利對我們皆是隱藏的」。[154] 哥克爾(Matthias Gockel)因而評論到,《羅II》最突出的「重點」乃「神聖預定」,這受困於世界之「人對神的認識的唯一基礎」。[155]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就連在歷史時空的層面上,巴特亦未曾將雙重預定描述為神的「絕對喻旨」(decretum absolutum:此為改革宗正統術語,指神在創世以先以不可改變的旨意,將人類二分為蒙揀選、遭棄絕的族類)。巴特反駁古典改革宗神學的預定論,聲稱雙重預定的真諦「並不關乎這人或那人,而是全人類。人類並非被它二分,而是被它結合為一體。在它的臨在中,他們都站上同一條線:因為雅各始終亦是以掃,而在啟示的永恆『瞬間』當中,以掃亦是雅各」。[156]
如此,「永恆的『雙重預定』這無可避免的教義,並非對神之行動的量的侷限,而是質的定義」。[157] 雙重預定對巴特而言,並不關乎哪些人被揀選、哪些人被棄絕。某人或許此刻蒙揀選,下一刻即被棄絕。
既然神賜下的信心乃不可能的可能性,這就意味「啟示永不可能被延伸至時間的平台上,以致它被理解為人們具體擁有的產權」。[158] 因此,「基督徒的確據」其實是一個「單單在神學家們的幻想中」存在的概念(巴特在1936年以基督論重新詮釋揀選論之前,一直不接受「得救確據」一說)。[159]
綜上所述,《羅II》所提出的雙重預定在歷史時空的層面上,無非是啟示在今世作為不可能的可能性所導致的信與不信的辯證。由於人的墮落及神主權之恩,「人們不得不在一條路上繼續前行,這條路以『雙重預定』為終點」。[160]
然而就連在歷史時空的層面上,雙重預定都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被理解為等量平衡的雙邊關係:「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人」(羅十一32)。巴特認為在這節經文中,「『雙重預定』的終極含意意欲使自身得以被知曉」。[161] 他聲稱,這節經文對雙重預定的定義乃「整卷羅馬書的關鍵」。[162] 根據他對這節經文的詮釋,雙重預定在永恆終末的層面上意味,神棄絕全人類(「眾人」)的目在於揀選全人類;在歷史時空的層面上,雙重預定則關乎啟示的不可能之可能性,此辯證關係彰顯於「眾人」實際的信與不信。
揀選在今世的不可能之可能性並非等量平衡的雙邊弔詭:「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163] 神的可能性,永遠強於人的不可能性。儘管神主權的揀選始終不能成為我們囊中之物,但教會仍蒙召以信心見證神藉之揀選人的信實,堅定地盼望主的日子臨到,將今世一切的負面之事棄存揚升,使眾人永遠得蒙神的憐恤。[164]
結語:
《羅II》與巴特後期神學發展
以上的論述以「不可能之可能性」的辯證為核心,重構了《羅II》的神學框架。儘管巴特著書不久後就發現《羅II》有許多不成熟的表述及神學上的漏洞,但年輕時的創意與想像力不但至今仍繼續啟發許多神學家,甚至他自己在生涯的不同階段中,都一再回到這部早期作品尋找靈感與題材。《哥廷根教理學》著名的實動主義(actualistic)揀選論,即是以《羅II》揀選論的歷史時空層面為基礎。[165] 儘管巴特在哥廷根-明斯特時期不再區分雙重預定的永恆終末及歷史時空二層面,但他仍視羅馬書十一32的內容為預定論的核心定義,主張揀選乃棄絕的目的。[166]
《羅II》與《哥廷根教理學》在方法論上最重要的差異之一,反映於後者幾乎隻字未提「不可能的可能性」的事實。《哥廷根教理學》明確地在道成肉身基督論及聖靈論的基礎上拒斥了此辯證,宣稱人在基督裡因信認識神的「可能性」是「可以藉由聖靈在任何時刻成為現實」的,而這意味「我們不該說啟示的有條件性… 等同於神的不可知性,亦即對上帝真實、充份、滿足的知識之不可能性與非現實性」。[167]
在此後的神學發展過程中,巴特會繼續採取哥廷根時期的路線,主張教理學是真正神學性(theologische:不只是歷史或社會研究,而是以神為研究對象)的科學(Wissenschaft:以實存對象為研究課題的知識學問)。[168] 這與巴特所理解的祁克果「非科學性」信心觀大相逕庭,也使得他在《羅II》以後的神學思想愈發遠離唯信論的指控(不論這指控對於《羅II》或祁克果是否公允)。自哥廷根時期開始,巴特就不再形容神的自我啟示及人對神的知識為不可能的可能性。

反之,當他於《教會教理學》III/3再度使用「不可能的可能性」一詞時,這辯證所暗示的非理性之弔詭被用於形容罪、惡、死亡,亦即「虛無」或「非者」(das Nichtige:指涉無有、什麼都不是)。巴特在IV/1解釋道,「不可能的可能性」乃是一個「在邏輯上荒謬的公式」,只能用以指涉「在其自身必然荒謬者」,亦即「罪」這違背人類受造天性的荒謬事件。[169] 道成肉身及揀選並非弔詭或荒謬的,因此不當以「不可能的可能性」形容之。[170]
儘管巴特後期神學愈來愈明確地拒斥他早期所理解並使用的祁克果辯證法,但他仍一次次回到《羅II》尋找靈感與題材。在1936年《神恩典的揀選》一書中,他首次以道成肉身的基督論詮釋揀選論,而他重申了《羅II》的一些重要見解:他主張羅馬書十一32提出了聖經對雙重預定這教義的核心定義,而此經文將棄絕與揀選描述為棄存揚升的過程。[171]
巴特1936年開始發展的基督中心揀選論,在1942的《教會教理學》II/2有更完整成熟的表述。這套以基督為中心的本體論強烈地聚焦於基督在客觀上已然成就的工作以及全人類及世界歷史皆「在基督裡」被命定(bestimmt:在黑格爾研究中通常譯為「規定」)的客觀本體事實,而此間濃厚的黑格爾主義色彩使得巴特的本體論被指控為「基督一元論」。
他在IV/1反駁這項指控時,再度從《羅II》找到了靈感。[172] 倘若II/2較為側重神在基督裡揀選人這由上到下的向量(即英語巴特學者常提到的downward vector)以致引發「基督一元論」的聯想,那麼IV/1-3涉及道成肉身、罪、稱義的復和神學,就更加強調神的揀選與人的信與順服之間的實動雙向呼應(Entsprechung)。[173] 與《羅II》相似的一處在於,IV/1-3十分重視揀選之於今世與終末的區別:人類的存在(Sein/Dasein)在今世的歷史現實中,始終處於基督裡「從上而來」(von oben)的揀選及亞當裡「從下而來」(von unten)的雙重命定之下,唯有到了終末,人的實存才可能全然擺脫亞當歷史的命定而全然呼應基督裡的揀選。[174]
在IV/1-3及《羅II》當中,救恩之實現的強烈終末論導向,皆可解讀為巴特用「棄存揚升」的邏輯詮釋羅馬書十一32的結果。[175] 如稍早所述,這種詮釋早在1936年就已是巴特基督中心揀選論的重要基礎,而IV/1-3濃厚的歷史主義、實動主義、終末導向,卻是在III/3重拾「不可能的可能性」辯證後才發展成熟的。
在IV/1-3中,人的罪與不信被形容為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羅馬書十一32當中「已然」及「未然」的雙重向度:神對全人類的「憐恤」乃基於祂在基督裡已然客觀成就的永恆揀選,但在歷史現實中,這憐恤唯有「在他們未來的實存當中… 擁抱他們」,而這就意味「眾人」的「不順服」雖已然被克服(它是本體上的不可能性),又仍待被消除(它是實動上的可能性)。[176] 在《羅II》中,神以揀選為基礎而施行拯救的工作被描述為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如稍早所述,這辯證亦體現羅馬書十一32當中的終末向度,儘管此處仍嚴重缺乏救恩之「已然」。
由此可見,巴特於晚期著述中重拾「不可能的可能性」辯證,並非心血來潮。反之,上述對比顯示了巴特神學發展的不同時期之間的連貫性以及自我修正。正視「不可能的可能性」辯證在《羅II》中的重要性,不只提供詮釋這部巴特早期著作的框架,亦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掌握他後期的神學發展。更重要的是,這方面的研究能幫助巴特的讀者更確切地認識他神學思維的辯證特色。「不可能之可能性」的辯證向我們揭示巴特神學的蛻變過程當中一套一以貫之的基本的思維模式:這辯證詞彙在《羅II》之後並非單純地被遺棄,而是暫時懸置,並在1950年代以更加成熟的型態重新出現。


曾劭恺 (Shao Kai Tseng) ,加拿大籍 ,出生于中国台湾 ,2017年入选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本科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B.S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双主修物理及德文。大学毕业后转入基督教研究专业,先后获加拿大维真学院(M.Div., Regent College)、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Th.M.,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MSt, DPhil, University of Oxford)。兼任学术期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A&HCI、Scopus等)编辑委员。著有英文专著Barth’s Ontology of Sin and Grace (Routledge, 2018)、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VP Academic, 2016)、《牛津手册》系列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 专书论文等。主要学科为基督教思想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巴特研究、汉语神学、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研究、黑格尔研究、加尔文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研究、奥古斯丁研究等。 其专文 “Barth’s Actualistic Ontology” 被收录为普林斯顿经典课程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eorge Hunsinger 教授主授)之指定阅读教材。
——摘自百度词条
#往期阅读#
编辑:Lea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