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会计学士,普渡大学电脑硕士,富乐神学院MA in Theology。现为“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主任,专为神国推广文字与文化异象,栽培并牧养文字工人。著作《在永世抛掷一个身影》一书获2012年汤清文艺奖。另有散文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散文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小说曾获大陆“冰心文学奖”、台湾“宗教文学奖”等。著有文字事奉系列《故事的呼唤》等六书。灵修书《在永恆中,读你》、属灵牧养书《向生命的礼物说Yes》。散文集《莫非爱可以如此》等五本。杂文集《爱得聪明,情深路长》等三本。短篇小说集《在爱的边缘》等五本。并有《莫非爱可以如此》、《在永世抛掷一个身影》等有声书。

【对话背景】二鱼:我和莫非在北京相识,后来又在香港相遇,逐渐熟悉,每次见到莫非和她的先生杜老师,都笑容满面。详谈起来,才知道她们的蒙召和辛酸。从小爱好文学的莫非,出生于台湾,后赴美国读书、工作。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福音文学展开。究竟什么才叫福音文学?或者说如何在文学里见证福音?

二鱼:
可以简单聊一下你当年创作的题材吗?
莫非:
一开始我是写一些散文。但因为是因著呼召进入,便观察现有的华人基督徒文字事奉有哪些作品,发现小说较少基督徒写,而且是对非信徒的小说,于是便开始学习写小说。那是一个摸索的痕迹。因为前人的脚印稀少,同时代投入的人也不多,完全是个人在黑夜中的大海中浮沉,努力想要飘到灯塔的岸边。自然,很多是生涩的作品。
二鱼:
有人说不像十八九世纪,现在全世界的福音文学都难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莫非:
没错,基督徒写的人本来就少,也因为基督徒作者一直挣扎在结合信仰进入自己的文字中,写出来的作品也是信仰和文学有点像油和水,融合不起来。我们缺少信仰的土壤来生出成熟含信仰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十八、九世纪有丰富的信仰土壤,甚麽样的人文艺术都可以开出灿烂的花朵。
现在的基督徒有些有成熟的文学文笔,但是生命不到位。有些有成熟的属灵生命,但是文笔不到位。这是为何创文对一些成熟的笔,不断提供属灵牧养,也对一些不成熟的笔,提供一些文字课程培训。更对所有有心想写的人,引进西方基督教文学比较成熟的作品,开启华人作者的视野,丰富创作的题材和方向。

二鱼:
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十八九世纪的欧美本来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以能很自然的融入进故事和人物。现代的很多宗教,思潮,心理疗愈已经很大程度替代了教会的作用,比如冥想,新纪元等。
莫非:
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所说的信仰土壤,比较能够产生伟大的信仰作品。异教从古到今都有,不是现代才发生。只是不同的异教。所有的宗教都有重叠的地方,都有信仰的对象、敬拜的仪式,也有信仰的法典。但是,因为神学的不同,会让你故事的人物决定和走向很不一样。故事不一定要设置背景在教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或托尔斯泰,并非如此。
二鱼:
但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基督教文化中,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很多文化在替代了教会,人们精神出现问题首先不是找牧师,而是找心理医生,找某某大师。
莫非:
所以呢?
二鱼:
所以在表现福音对人的改变,和其他文化对人的改变之间的区别上似乎更难。比如一个心理抑郁的人通过心理医生得到了疗愈,也可能通过教会得到疗愈,这个区别是有的,但文学表现起来似乎更难,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是没有的,不是吗?
莫非:
有次我和人讨论写文章中是否要提上帝?或任何和基督教有关的内容:教会、十字架、基督徒、圣经….如果不提上帝,会不会我们做福音预工把土地都准备好了,反而被佛教或其他宗教给收割走了?
二鱼:
嗯是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觉得应该提吗?
莫非:
如果一篇文章未提“上帝”,就容易被佛教或者新纪元等来收割,就表示这篇文章里面的眼光、人生观、道德观等等有其信仰眼光不清,或者属灵生命不深的问题。
因为老实说,虽然“温暖、光明和爱”,各家宗教都会讲一些,但这些并非是基督教信仰的全部。我们信仰的丰富还包括救赎、饶恕和公义等等等等。即使谈爱或光明,也有层次、深度和走向的不同。
在我“创作的思想架构和题材”中,曾提到一名基督徒创作者若是能把上帝的创造,人的背叛,神的干预和救赎等《圣经》故事,深深地嵌印在脑海中,又让上帝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就无须时时在文字或艺术中提到神或十字架了。正如一个人无须总是提到自己有父有母一样。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本源。
在我“以基督的眼光看世界”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作家在本质上就是一名观察者,写作的目的,便在呈现所看到的世界。我们的信仰会让所看出去的世界,有次序、有原因、也有结果。
这也是为何,一个相信上帝掌管世界的基督徒,和一个认为世界中一切都出于偶然的非信徒,对文字绝对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一个相信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基督徒,与一个相信神是人所创造的偶像的非信徒,文字中也会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一个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作者,和一个认为人必须宿命的作者,故事发展更会呈现不同的结局。
也因此,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谈到罪恶感与忏悔。有美国安尼‧迪勒的《溪畔天问》,对大自然有种敬畏尊重的态度来书写。或者美国厄普代克著名的《兔子五部曲》,描写一个人在生活中出走又回归……等等内含信仰价值观的作品。另一方面来说,也会有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后现代英雄过的是完全没有责任感,虚空轻盈到让人不可承受的地步。或像张爱玲写出世纪末华丽或倾城倾国的爱。还有大陆作家余华的《活著》,呈现大时代处于浩劫时,只要活著本身就是一切的答案。
光就书写大自然,安妮;迪勒和写《湖滨散记》的梭罗,就大有所不同了。在我们基督徒笔下,对爱情永远不相信缘份和宿命,而是靠著信仰来学习饶恕和付出的功课,这已划分了基督徒的笔和佛教徒的笔走向不同。
所有生命的本质和经历,出发点不同,动机不同、看一生不同(佛教都是空)、盼望不同(不是转世或靠下辈子),结尾不同,即使不写“基督徒”在脸上,也不会被误认为佛教徒。除非读者自己对各类信仰太不清楚,分不出是道是佛或是基,那就需要靠媒体性质和作者身分来帮补了。在甚麽样的背景(context)呈现出这样的文字,作者是甚麽身分,都是隐性但有效的线索。但这和我们努力下笔的文字又无关了。
所以回到你这边的问题,救赎外表看似相同,但是怎样救赎,为何救赎,救赎后的人生观有何不同,却是大不一样。这是为何文学不能只描写表象,要有很多内心视野的展望,才能呈现生命不同在哪裡。
二鱼: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年代的土壤和今天不同,我赞同您的看法,但在今天,福音作品不提上帝,而仍能让人感受福音的美好,似乎很难,有这样的中文作品吗?
莫非:
就看你怎麽定义带有信仰价值观的作品,如果要做到窄义带福音的作品,往往文学价值都被打折扣了。所以往往是用福音中的故事原型,然后放到文学架构中来呈现。张晓风用中文文学中的典故来带出信仰中的某个片面,写出好几个剧本,〈自烹〉、〈和氏璧〉、〈武陵人〉、〈严子与妻〉、〈第五牆〉、〈第三害〉,都是很好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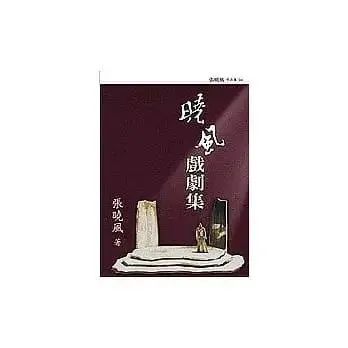
二鱼:
举个例子,按照好莱坞理论,电影里有上帝的角色,有英雄的角色,泰坦尼克号的上帝角色就是杰克,英雄角色是露丝,杰克为露丝生命,也拯救了她,这是电影学院的说法,你认同吗?
莫非:
当然不认同。这就像文学中的”Christ Figure” 基督形象人物,和我们信仰中的基督完全是两回事。张晓风的戏剧不是这个层次。

二鱼:
后来,你从自己创作,到开办创文,教很多人一起写作,两者哪种更激动人心呢?
莫非:
当然是成立创文,首先,创文的起源是来自“洛城写作团契”,不是我一人成立。然后,创文的主要宗旨就在“成全他人的笔”。因为当初我走上写作的路是来自文字事奉呼召,是在成立创文前20年。那时,以为就是自己写,不断地写,是神对我文字事奉呼召的心意。但是,经过20年的个人创作,愈来愈发现这需要一群人来完成。就像一滴水跳入大海很快就消失不见。但是若有一群人一起写,便如一股清流可以成为一股力量。
二鱼:
每次看到你和杜老师都热情洋溢,你们私下有疲惫忧伤的时候吗?
莫非:
当然有,是人,都会有挣扎啊。就像《天路历程》,每个人的信仰路都有高低起伏,你看到我们的热情洋溢,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是我们热情所在。文字事奉是我们夫妻共有的负担和呼召,只要谈到这个异象,30多年如一日,总让我感到燃烧。
二鱼:
有灰心后悔的时候吗?创文做起来确实很难。
莫非:
倒是没有。因为一直是在神的带领下摸索,在神工作的地方工作,比如说办文学奖,虽然募款和后台行政很艰难,但是,看到好作品参赛就很被鼓舞。像保囉,宣教受过那样多的苦,又是船难,又是被人误解等,但因为了解神的心意,就只看到神要成就的心意,不太会去看难处。所以没有灰心后悔,只有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感到困惑。然后就会去求问神,往往神也会赐下线索,经文,让我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有甚麽样的遭遇。就像以利亚被神带到何烈山,然后就告诉他之后将要发生的事,以及他要被差去为神做甚麽。当你能窥见神国奥秘时,只会感到兴奋,不会有其他。
二鱼:
感恩,愿我也能如此。
莫非:
你会的,只要开放自己的生命,让神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