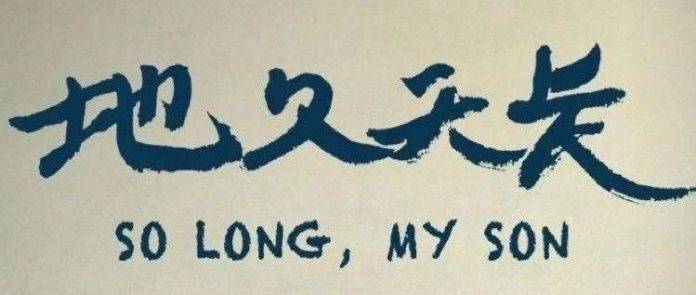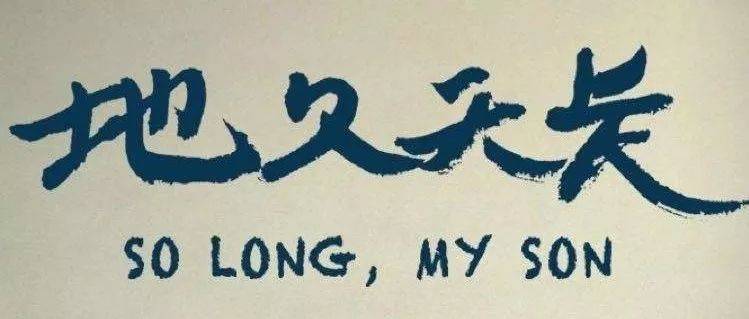
1
王小帅导演的影片《地久天长》,虽然以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为社会背景,但其真正主旨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而是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生活与生命态度的呈现,来一般性地呈现出人在关系困境和存在困境之中的伦理性抉择。
女主人公王丽云被强制堕胎,留下后遗症不能生育。独生儿子刘星在与朋友李海燕之子沈浩玩耍的过程中意外溺亡。是沈浩出于孩子气的任性,推倒了刘星,客观上造成了刘星之死。男女主人公难能可贵的品格在于:在承受了丧子之痛而自顾不暇的同时,不仅没有对李海燕有迁怒和怨恨,反倒对她的孩子心存善意。虽然自己的心在滴血,却仍顾念和爱护那作为“祸首”的孩子,不愿他幼小的心灵在战兢惧怕惊惶中受煎熬。
按王小帅谈自己创作此影片的初衷,本意是要通过孩子感受世界的视角,来呈现大人们担当苦难的坚韧以及他们不计较他人过犯的宽容与慈悲心肠,由此来凸显一种“温情与善意无价”的人文关怀。
摆在男女主人公面前的,是两个严峻考验:一是在生活苦难和心灵苦痛中如何作善恶抉择;二是如何在这无常的人生中,去放下或胜过“永远失去”的伤痛。
2
人生确实无常: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风险之中,我们一生都在被某种不测所追赶。即使让我们受苦的直接因果链,可能追溯到某种不义的制度,但一个正义的制度却不能保证我们从此就与人生苦难绝缘。
不管我们的生活是否美满,伫立在我们生命道路前方的,总是那个黑压压的死亡阴影。如果死后我们没有未来,那么,本质上我们就没有未来——在生死别面前,谁若失去,就永远失去;谁若孤独,就永远孤独。死亡,让我们没有未来。
人的一生,总的来说都是残破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的生活际遇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存在形态本身:罪恶与死亡,总像幽灵一般对我们如影随形。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了走向死亡的程序,正所谓“出生入死”。死与生,仿佛就是我们生命形态中的一体两面。然而,死,终究是对生的吞灭,是迫使人与所爱的人分离。李安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主人公“派”这样感叹:“我的父母,我的兄弟,理查帕克,最后都离我而去了,到头来我相信人生就是不断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都没能好好的与他们道别。”
人生代代无穷死。似乎除了告别与送别,生命旅程别无它物。关于生死之别,很多人心中的悲伤和遗憾,似乎只是死亡来得太意外太突兀,让我们没有机会好好告别。似乎若死亡可以来得更从容,让我们更有预备,我们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3
影片呈现了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王小帅说自己的用意是:“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为此,影片的焦点不是要呈现苦难和解释苦难,而是要呈现一种对苦难的坚韧担当。
对王丽云夫妇来说,他们的“在一起”,同甘共苦、相依相守,如他们所说,彼此都为对方而活,这就是他们担当苦难的重负人生的动力和勇气来源。

然而,人与人的“在一起”并不具有某种天注定的恒久性。作为丈夫的刘耀军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背叛过妻子,他对妻子的爱并不必然具有一种永不止息的恒久特征。作为天性柔弱的妻子,丽云对丈夫有一种心理依赖。她在苦难中的刚强需要有丈夫的陪伴做精神支撑。虽然她也曾感受到,这份支撑在她心里似乎不够坚固有力,不足以真正安慰她与子分离的伤痛和心碎。所以她曾留下遗书,准备与世诀别。
影片回避了更尖锐地呈现出人心在现实中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困境,没有把人在生活之内的绝望推至极致。所以,王丽云自杀未遂,刘耀军也胜过了试探,没有在背叛妻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丽云有重新承担人生的勇气,来自于丈夫的不离不弃。
然而,即使丈夫胜过了另一份爱情的试探,但,死,终有一天会把他们分开。一旦谁先离去,那个被撇下的人,坚韧地生存下去的根基又将何在?又或者丈夫真的移情别恋,那么王妻子活下去的根基是否就将坍塌?
导演回避了一条不断探问和追寻人生命根基的道路,而选择走向一条能够托起温情和希望的路线:让丈夫陪伴在妻子身边,也让那个离家的养子回来。在彻底的黑暗与绝望与幽微的光明和希望之间,影片选择了呈现后者。
然而恰恰是这样有意要呈现温情和希望的出发点,使得影片离那些在生活之内绝望得彻底的人有一些远,也离人类精神层面上的真实绝望有一些远。这也使得影片的境界始终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徘徊,而没有往形而上的方向进发,以至于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作为文艺片的精神质素。
4
如果世上有一些痛失爱子的女人,恰好又遭遇丈夫移情别恋或撒手人寰,她们只想选择“放弃”,而不愿选择“放下”,我们又能给出何种理由去劝说她们放弃对人生的放弃?
或许有这些理由来劝说她们:虽然你丈夫离弃你了,但你还可以再找丈夫。虽然你孩子死了,但你还可以再生孩子。就算不能再生了,还可以领养孩子……总之,只要你还活着,人生就向你敞开无限的可能性。
或许还有一套要女人追求自立自强的道理,要她们不要做男人的依附者,不要在家庭、丈夫和孩子的身上去建构自己生命的意义,不要为了他人而活,而要为自己而活。这种道理要女人有这样的“人间清醒”——就算你选择和某人在一起,至少也要让自己可以离得开他。不要让任何人在你生命中重要到不可缺失。否则,你就可能被他的离开所摧毁。只有在精神上独立,在情感上不依附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成为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才能胜过失去任何人的伤痛。他们若离开,你们的孤独和伤痛才不至于无法治愈……
本质上,这是一条爱得有所保留的道路。惟有爱得不那么深,分离才不会那么痛。
在李玉导演的《观音山》里,失去了丈夫,又失去儿子的孤苦女人常月琴,对观音山上一个寺庙师傅说:自从三个青年来到她家里租住,她就变得很快乐了,但是这种快乐仍让她感觉恐惧……
“以前我很快乐,我有孩子,我有先生,然后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师傅说:你没有完全放下。女人说:我不想放下。

她不想放下,因为她无法让自己对儿子的爱有丝毫保留和克制。她的痛,不仅在于一种被撇下后的孤独,更在于她拒绝让自己的爱因儿子的离开而消减。如果除掉痛的代价是爱的消泯,那么,她就宁肯自己一直痛,也不愿放弃爱。深爱,决定了她心中的死别之痛,不能被治愈。爱,就是要在一起,而且要永远在一起。为此,一个以深爱家人为生命志业和灵魂归依的女人,宁肯忍受心中长久的离别和撕裂之痛,也不愿对逝去家人的爱消减半分。
她说:“人不应该永远孤独的……”
确实,人不应该是永远孤独的。人需要与某个“他者”建立彼此相爱的共同体关系,才能心得深切满足,才能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完整。独立,并不是人本体性的存在状态。人会渴望自己活在一种爱的关系中,与“他者”永远相连。人内心渴求永恒的真相,其实并不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独立”地永远存续,而是想和自己所爱的“他者”永不分离。
影片的最后,暗示常月琴从观音山上跳崖。她曾对那三个带给她短暂快乐时光的年轻人说:“孤独不是永远的,在一起才是……”
既然死拦阻了她与儿子的团聚,如果她也走向死亡,是不是就可以和他团聚了?
很多人都说常月琴说反了,事实应该是:在一起才是暂时的,孤独才是永远的。因为他们相信:死亡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永别,死亡的背后没有相聚。
5
区别于《观音山》里常月琴的是,《地久天长》里的王丽云在生活之内并没有走向彻底的绝望。虽然生活让她遍体鳞伤,但只要还有爱人的陪伴,似乎今生就可以活成永远,或地久天长的样子。似乎在不完满之中仍然可以有某种完满,似乎面对破碎的人生仍然可以走向内心的升华。那就是,与自己那有限而残破的人生达成“和解”,对必然要降临的死亡的看淡和超脱。
在飞机上遇上强气流的时候,她自嘲似地对丈夫说:“真可笑,我们居然还怕死。”

这句感叹或许可以做这样的解读:我们这样含悲忍苦的人,既然对人生不再有什么期待了,就应该平静地接受生死的“命数”。既然“命运”交给我们一副烂牌,那么我们不应该是直接扔掉它,而是尽力把它打好。我们不爱这“命”,但我们仍没有资格放弃。如果在苦海中浮游是给我们的“命定”,那么,只要还有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人,我们就能够勉力在其间苦中作乐。只要“命”让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活着承担一切苦痛的“责任”。
至于在苦痛的重压之下,为什么非要活着不可?很多人都认同作家余华所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对他们来说,既然已经活着了,或者说既然还活着,那么,就姑且活着吧。生也好,死也罢,都随遇而安了。死生有命。或生,或死,似乎都不应该太介意了。
不介意死与不眷恋生,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然而爱的本质必然包含着对生的看重和宝贵。若爱,就必然会对死亡所带来的毁灭充满了悲哀和伤痛。若爱是永不止息的恒久,只要“死”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还在,这伤痛就无法真正被医治和痊愈。从这个意义来说,看淡生死,实质也不过是爱的衰微和寡淡。
若不再活在爱中,是背反于人的存在本质的,那么,让人以消减甚至根除爱的方式去除去心中的痛,这如同是在以一种“人将不人”的方式去对人进行“医治”?
所以,有人不乏悲情意味地问:“那些生活中留下来的伤痕真的能够被抚慰吗?还是只能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逐渐遗忘和掩盖?”

6
我们在生活之内的一切盼望,终将成空。当死的毒钩向我们自己伸过来,迫使我们不得不遥望死亡背后的未知黑暗,并为此而凄惶无助的时候,谁能应许我们一个有盼望的未来?死,会把那些想永不分离的人粗暴地分开,让他们各自都显出自己生命本体中的无助、软弱和孤独。他们活着时的“在一起”,只是掩盖了这种孤独,而不是解决了它。
死,最终会剥夺我们生活中一切的盼望,会揭露我们想一直忽略和逃避的存在本相:在这个广袤的大地上,我们如迷羊找不到回家的路,如孤儿不知道父亲在何方。我们拼命向同类伸出双手,渴望彼此相扶,使我们得以在大地上站立得稳。然而,很多人在看清前行方向之前,就被迫如飞而去了。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像大树扎根于土壤的深处,而像无根的浮萍漂浮在水上,也像飘零的风絮飞扬在空中。
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战胜“死亡”这个敌人,那么,面对一生都在环绕我们的死亡波浪,人还有什么盼望?面对分离的伤痛,如果我们不要心硬和心死,那么,我们的悲哀是否可能被“盼望和喜乐”所代替,我们的忧伤之灵是否还有得安慰的可能?
人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在他的生命中到底失落了什么,才会沦落到被流放在这会地动山摇的大地上,承受这样无根可寻的漂泊,还要被死亡和毁灭的权势不停地追赶?
有这样一个关乎永恒失落和永恒归回的故事,自两千年前,从中东的耶路撒冷开始流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对被上帝造出来,本与祂同在的夫妇,因为失守了祂的话语,而被赶出美丽的伊甸园。从此,人类在罪与死的重负之下呻吟叹息哭泣。
死亡,是人类离开上帝的代价。人与自己存在根源(上帝)的关系断裂了,彼此之间也有深渊相隔,就像树枝从树上断掉了。树枝既已断,就不再有生命汁水的供养,就注定了走向枯干的命运。
那些断掉的树枝,想彼此靠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为彼此提供生命的汁水和养分,然而不管它们怎么相濡以沫,也不能摆脱共同走向干枯的命运。它们为彼此终将分离的命运而哭泣,却没有为自己与树的分离而哭泣……树枝们为彼此不能永远在一起而悲伤,面对着必要走向枯干和入土的命运,它们唯一的盼望是:可以一同埋葬。这是它们所能设想的彼此永不分离的唯一形式。然而,除非它们是一起被连结在树上的,它们就不可能“永不分离”。

与生命树隔绝之后,我们就失落了乐园。等候我们的“永远”或“地久天长”,就只是绵绵无尽期的孤独。如有人所说的:“错觉的天长地久,其实只是一无所有”。在坠落大地的过程中,不管树枝吟唱出了什么美丽之歌,那都只是它为自己的安葬所鸣的哀歌。
我们可以永不分离吗?永活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吗?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的儿子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人的悲剧性就在于,一边渴望着与所爱的人永不分离,渴望永活,一边又坚定地拒绝相信人类有永生的可能性。不信,让人牢牢地困囿于没有死后盼望的绝望和黑暗中,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