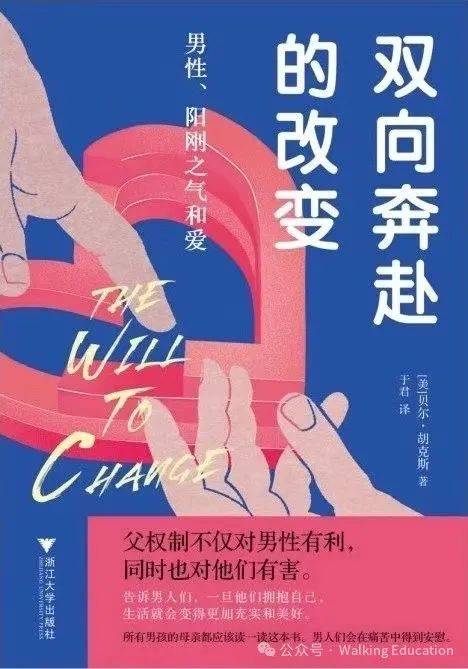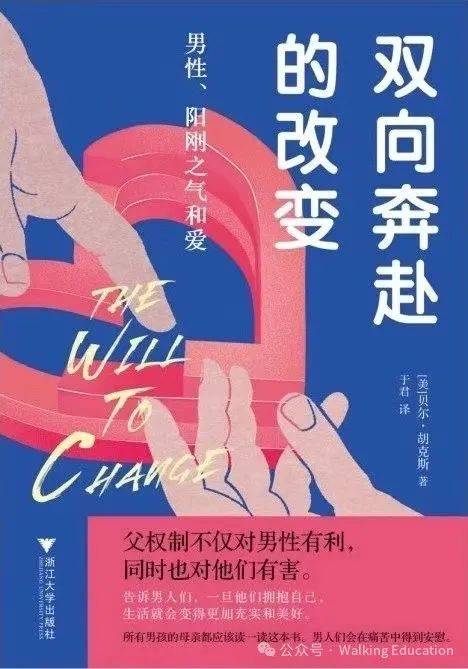
认识贝尔.胡克斯,完全是一桩恩典。因为在朋友圈偶然见到道明兄推荐的《教出会思考的孩子》,我第一次读到了女性写的论“批判性思维”的书,因着这本书,我第一次知道贝尔.胡克斯的名字。虽然朱莉在她的书里只是短短地引述了胡克斯的两段话而已,却让我的思想遭到触电般惊醒。
然后,就开始找她的书来读,先是《关于爱的一切》,接着是《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再后来就是这次出来旅行随身携带的《双向奔赴的改变》。
我越来越有一种很强的感受,以前我们批判华人社群的反智主义,于是教会在90年代有了改个宗神学进入之后,似乎一下子给信仰打开了格局,让人不得不去思考信仰的真谛,再后来就是开始反思建制的重要。
其实,传统家庭教会不是没有神学, 没有建制,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和建制蒙上了太多的经验主义、情感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阴影,这就难免会让新一代的牧者群体在走上牧养之路后,不得不重新为教会在中国这片土地扎根,枝繁叶茂,寻找那活水的泉源。
问题是,我们对付反智主义的方式,往往是以理性主义的专断完成的,我们对建制的渴求,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长期以来盘桓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上的家长制。这种家长制,在我读《双向奔赴的改变》时,有了一个至少对我而言全新的对应词汇:父权制。
说来,一个男性,忽然开始对女性主义作家感兴趣,甚至开始反思父权制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的确是有一些不太理性,不太正经,但我越是读这本书,越是不断被胡克斯澎拜的激情和启发人心的思考所折服,因此,我诚意向所有还没有读过她的书,还不了解女性主义为何物的朋友们推荐此书。

究竟什么是双向奔赴的改变?我的理解是,男性需要认同女性保守父权制伤害,同样的,女性也需要理解男性饱受父权制压迫。
胡克斯开篇即如此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没有人教导男人爱的艺术,他们就没有爱的能力。如果没有人教导男人他们的灵魂很重要,呵护灵魂是生存的首要任务,他们的灵魂就会永远处在分裂的状态。如果所有男人都在寻求情感能力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心灵滋养,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好。男人需要女性主义思维。有远见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明智的、包含爱的政治学。大多数男人难以改变的地方是他们的情感生活。女性一直相信可以通过付出爱让男性获得拯救,可是女性不能为男孩和男人做他们必须自己做的事情。
她和父权制这种思想怪兽缠斗三十年之久,依据她的观察看出,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男人没有地位,没有特权,他们没有享受到天上掉馅饼的优厚待遇,没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福利。
对这些男人来说,支配妇女和儿童可能是体验父权制的唯一机会。这些男人遭受痛苦,他们的痛苦和绝望无休无止。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痛苦程度,而是进行掩盖和假装。他们在一个不希望男人改变的社会中痛苦深重,这个社会不希望男人重拾阳刚之气。
更严重的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女性拼命地追寻男性之爱。男人一旦敢于爱我们,在父权制的文化看来,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男人”了。鲁迅曾有诗云:“怜子如何不丈夫?”恐怕先生当年勇敢地承担起男性之责,会被不少人视为是懦夫之举吧?
这个世界都在教导男孩不应该表达感情,受此世界所困,青少年男性找不到可以宣泄悲伤的地方。青少年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他们经常曝光符合周遭世界的伪善。
所以,胡克斯认为,为了尊重和真正保护男孩的情感生活,我们必须质疑父权制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改变之前,我们必须创造一种亚文化,一个避难所,在那里,男孩可以学会做有个性的自己,而不必被迫盲从父权制的阳刚之气愿景。我们必须足够重视男孩的内心世界,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建构他们的权利,使他们的身心健全能够得到持续的赞美和肯定,使他们获得和给予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男孩需要爸爸,在无数个反面教材面前,父爱是一个难以兑现的誓言。母爱博大深厚而直观:我们抱怨是因为我们享有太多的母爱。父爱呢?父爱对很多人而言,是一种稀缺宝石,有待我们去发掘,其价格弥足珍贵。
因此,只有一位身心健全的父亲才会真正疼爱自己的孩子,才能拥有圆融性的态度,向儿子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觉得尴尬。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我还记得小时候,当问到父亲一个他也不明白的问题时,他恼羞成怒,似乎在说:“看,我不知道你问题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我应该踢你的屁股!”当然,我几乎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再向父亲追问答案。也许他应当耐心地对我说:“孩子,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一起探索就知道了。”
温德尔.贝瑞也说:如果在童年时有幸被宠爱我们的成年人所包围,那么我们的健全性就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对他人和我们的关系的归属感;它是一种无意识的群体意识,是人们共同拥有的群体意识。也许,只要我们活着,这种单一的圆融性和群体归属感的双重感觉就是我们个人的健康标准……我们似乎本能地意识到,健康是不可或缺的。
男人之所以非常暴力,芭芭拉戴明认为,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在表演一个谎言,所以对自己卷入谎言而感到愤怒,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挣脱。他们的愤怒其实是掩盖精神苦痛或烦恼的遮羞布。
父权制的文化并不在意男性情感是否得到满足。父权制传统教导男人在情感上应当禁欲,教导他们如果没有情感就更有阳刚之气,如果他们偶然有了感情,感到了伤害,就应当把 它们压制下去并且忘记,尽力让它们消失。
男人若受到伤害,整个文化对他们的回应是:请不要告诉我们你的感受。我们构建了一种文化,男人的痛苦无声无息,他们注定要生活在情感麻木的状态中。大量的男人记不得最初的心碎和心痛的时刻:那一刻他们被迫放弃了感受和爱的权利,而接纳作为父权制男人的地位。
我们的文化让男性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因此必须向他们灌输父权制思想,教唆他们使用暴力,并以此为乐。新闻报道的多是暴力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听不到关于男性和爱的消息。只要男人支配者女人,男女之间就不可能有爱。爱和支配可以共存,是父权制告诉我们的最有力的谎言之一。
只有我们的价值观发生转变,男性暴力才能真正结束。这种变革必然是基于爱的伦理。为了创造懂爱的男人,我们必须爱男人。父权制的文化不允许男人单纯地做他们自己,并以他们独特的身份为荣,他们的价值总是由所做的事决定。然而,男人不必证明他们的价值和实力,从出生那一刻,仅仅是存在就赋予他们价值,赋予他们受到珍惜和宠爱的权利。
除非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流行文化,在不赞同父权制的前提下肯定和赞美阳刚之气,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看到广大男性对其身份性质的思考方式发生变化。
到底什么是父权制?胡克斯说,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政治体系,它坚持认为男性天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有天然的优越性,尤其和女性相比,还具有统治和支配弱者的权利。男孩就应当以暴力为乐,男孩不应表达情感。为了向男孩灌输父权制观念,我们强迫他们感受痛苦,并否认自己的感受。父权制的文化捆住了我们的手脚。
父权思想不一定是男性,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固守父权制的思想和行为。最常见的父权制暴力形式是发生在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间的暴力。在强迫男孩遵从父权制标准方面,单身母亲往往是最残忍的,坚持让她的男孩“做个男子汉”的单身母亲并不反对父权,她在行使父权意志。在父权文化中,男孩很早就知道母亲的权威有限,她的权力仅仅出自对父权的维护和尊重。 许多母亲将怒气撒在儿子身上,来表达她们对成年男人的愤怒。这些不健康的亲密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教导男性和女性什么是亲密关系。只要母亲依然主要承担育儿的责任,我们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学习如何亲近子女,并与子女分享这种知识。
胡克斯主张,父权意识给男性洗脑,让他们相信对女性的统治是有益的,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我们集体承认父权制造成的损害和所带来的痛苦,否则我们无法解除男性的痛苦。父权制作为一种制度,剥夺了男性获得圆满的情感幸福的机会。父权制的力量一直使男性处于恐惧之中。
男性面临的危机不是阳刚之气的危机,而是父权制阳刚之气的危机。 这种父权制的阳刚之气坚持认为,真正的男人必须通过理想化的孤独和离群索居,割舍亲情来证明他们的阳刚之气,但是女性主义的阳刚之气告诉男人,他们可以通过与他人联系的行为,通过创建社群而变得更具有亲和力。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是由孤独的人组成的。即使身处偏僻的小屋,梭罗坚持每天给他的母亲写信。
尽管性别角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文化仍然是一种父权制文化,男性至上主宰着一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男人可以把失业当作是度假,那时他们可以做自我实现的工作,可以进行自我疗愈。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职场男性几乎不能阅读或写作。
绝大多数的女性主义者并不讨厌男人。她们为男人感到遗憾,因为她们看到了父权制是如何伤害他们的,而男人却依然固执地奉行父权制文化。
我们关于爱的著作应该是重振男性雄风,而不是让它成为父权制统治的抵押品。我们这些试图终结父权制的人可以打动真正的男人的心,不是要求他们放弃阳刚之气或男性气质,而是要求他们允许其内涵的改变,要求他们不要忠于父权制的男性特质,以便为男性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再成为高高在上或随意施暴的同义词。
为了给男人创设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我们必须首先用伙伴关系模式替换支配者模式,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视为所有有机体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与之共同沐浴在爱的海洋上,不再担心冷漠和孤独,体验一种无所畏惧的完全的爱。我们需要打开心门,张开双臂,站在他们的立场,随时准备拥抱他们,在他们努力寻找心灵回归之路,下定决心准备改变的时候,奉献上我们的爱,来庇护他们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