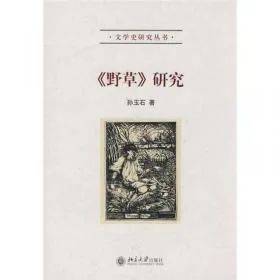
我脑海里常常晃动着几个画面。
没办法
“看哪,我又被他们强奸了……”一个女人,披头散发,逢人就说。
“你喊人了吗?”
“喊有什么用呢?没办法。”
“没喊过怎么知道没用?”
“你听到谁喊过呢?我反正没听到过。”
“那你反抗了吗?”
“没有,反抗有什么用呢?没办法。”
“好吧。那你还抱怨什么呢?既然反抗不了,就主动选择享受吧。调整心态,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放你个狗臭屁,我又不是妓女!”
“可是,妓女还能得到钱,被强奸,连钱都没有。”
“你是在嘲笑我吗?混蛋!”她有些恼怒了。
“不。我是在嘲笑自己,你怎么知道我就没被强奸过呢?”
“哈哈,看来不光我一个人这样,那我就舒服点了。”
……
“看哪,我又被他们强奸了……”
“看哪,我又被他们强奸了……”
“看哪,我又被他们强奸了……”
其实,我看不清这俩人是男是女。
口炮党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以上是照抄鲁迅先生的名文《范爱农》。老实说,我是站在范爱农一边的。依我看,发电报非但无用,而且主张发电的人中,定然有不少“表演艺术家”。
会叫的狗不凶,极凶的狗不叫,直接咬。
吴冠中说:“一百个齐白石(的社会功用),比不上一个鲁迅。”我总想接一句:一百个鲁迅,比不上一个……
赶紧打
这好像是我亲历的一件事,但我并不确信。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西安土门一带的市场上瞎晃荡,猛听得两个南方男人在对骂,其时人群已经聚集成一个密密匝匝的大圆环了。
“操你妈,敢睡我婆娘,不想活了吗?”
“我们你情我愿,你能把我咋样?”
“真你妈的不要脸,自己有婆娘,还搞别个婆娘!”
“哪个叫你婆娘妖娆儿呢?你他妈栓不住自个儿婆娘,还有脸往外说!”
“操你妈,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狗杂种。”
“有话好好说嘛,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教书匠模样的人决定出来评理。
那二位谁都不理睬他,骂得更带劲了。教书匠也只得放弃劝说,悻悻离开了。
……
四十分钟过去了,两个男人还在骂,跳着脚、指着鼻子骂,骂得五彩缤纷、波澜壮阔,关键是,修辞绝妙。
“都他妈给我闭嘴!娘们唧唧的!这他妈就不是个骂的事,是个打的事嘛——赶紧打。”一陕西络腮胡终于忍无可忍,厉声喝道。
这一声断喝有如雷震,震得那俩小男人魂飞魄散、面如土色。回过神后,飞也似地钻出人群,跑掉了。
我特别喜欢陕西男人,楞!多年来,每每想起那部络腮胡,耳边就飘出一句戏文——“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人被逼到生不如死的时候,就该打。但是,如果敌人是只老虎,你还敢打吗?
人都怕死,除非你不怕死。
死生间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痛彻心扉。
十字架下,是震耳欲聋的狂笑:“你不是神吗?咋不救自己呢?”
这狂笑的人中,有多少是吃过耶稣的饼和鱼的?有多少是被耶稣救治过的?有多少是几天前他进耶路撒冷时夹道欢呼他的?——同样的震耳欲聋。
“你们所做的,你们不知道。我免了你们的罪。”耶稣说。
“哈,哈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狂,还赦免我们,你不觉得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吗?你这个失败的小木匠!”他们说。
“成了。”耶稣说。
耶稣既怕死,又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死了,就成了——成全了人的活。
他又复活了,于是有人相信自己永不再死。
这地上本没有路,抬头看天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