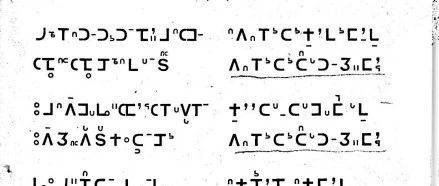柿花箐去來記
張宗南
八月十日(星期四)。昨天已同王弘道君約好了,今晨他在東門的城門口等我們,所以一清早崔博士同我就把隨身帶著的行李運到大東門,見到了王君之後,又一同去小東門的豫豊馬店。和我們一路上柿花箐的那批馬幫就歇在這個馬店里,他們是由尋甸運木板來的,放空囘去,所以王君同他們接洽順便帶我們到柿花箐去,我們在馬店等了一會,祁育真女士也來了,我們在十一點就徒步先行,因為馬幫那時還未完全準備好。向北進行,走了兩里,馬匹也都由小路到了,祁女士騎上馬去,這是一匹只有木馱鞍的大馬,祁女士高高的坐在馬鞍上,像騎着一匹駱駝似的,她小心抓住木架,馬走的很慢,所以她覺得還相當舒服,祁女士所騎的是唯一的可騎的大馬,其餘三匹都是小馬,崔博士卻無法騎。最後,只好為他選了一匹驢——一匹比較老實的驢子。他費力的先爬上一塊石碑,馬夫把驢子牽在碑旁,我站在驢旁準備為崔博士推上他的身子去。剛準備上去,驢子一動,馬夫把牠緊緊拉住,崔博士剛一跨足,驢子就絕不合作地跑走了。沒有辦法,崔博士只好同我們一起步行,望着祁女士一人高高坐在上而微笑。
走了五里路之後,迎面來了一隊運木板的馬匹,祁女士讓不及“說時遠,那時快”狹路相逢,祁女士被撞下馬來,幸而跌在旁邊的泥土上,並未被馬隊踩踢。我們趕忙奔前去扶她,發現她的臉色慘白可怕,一面呻吟着,一面摸着胸,我立刻跪下一條腿子,讓她靠椅着,她緊緊地抓住崔博士的手搖頭,嗯嗯地哼着,說不出話來,我立時感到情形的嚴重。過了幾分鐘她左手貼着胸斷斷續續地說着:“胸痛的很……我來了……給你們添麻煩……”差不多在泥地下躺了二十分鐘,才慢慢地扶她起來,髮夾都鬆散了。她摸着髮夾的時候才發覺後腦上多了一個大疤。她仍繼續步行前進,我望着她那尚未恢復的慘白的臉色以及散在肩頭的兩條長編,真有說不出來的感動。我同崔博士扶着她慢慢地走着,她說最難過的還是覺得好像有一口氣,悶在胸里不能出來。
又走了一里之後,她就完全自己走了。路上不是高低不平的亂石,就是泥漿水塘有時還要跳溝,坡雖小,路太濘滑,也太崎嶇了,走了兩個多鐘點才見到普吉。此處離昆明僅十五里,崔博士一直喘着氣,紅着臉,祁女士因為爬幾個坡的原故,總算把那口悶氣吐出來了,臉色也好多了,大概是那口氣太沉重了吧。
普吉是幾個村子的,一共有兩百多家,住的都是漢人,我們並未進村,只有遙望着那些密集的紅泥墻而已。
過了普吉之後,王君先走了,因為從沙朗到廠口之間常有匪人出沒搶劫旅客。所以他預備先到沙朗去請鎮公所派自衛團丁護送。我們慢慢地仍在後面走着,過了一坡又是一了。到坡沙朗之時,他們兩位實在累乏不堪了。沙朗離普吉一般人說是十五里,實際或許有二十里。
在將要到沙朗的三里中,完全是亂石堆砌的下坡路,很是陡險。到了坡底時,崔博士之腿已無法步,勉強又復前進,偏偏又走錯了路。因為馬隊都在前面,老早已看不見了,好容易走到沙朗的大村,才知道鄉公所在東村。
沙朗一共有大村東村西村三所,全是漢化了的“民家”,他們和大理一帶“民家”的語言是相通的,當我聽到田野中播送出來的那些山歌時,就立刻憶起五年前在洱海月夜裏的隨波而去的調子。
從大村到東村的途中遇到了四個兵士,全副武裝,很是整齊。通話之後,從知道他們四位即是來護送我們去廠口的自衛團丁,他們說王君和馬夫都在前面等我們,那時已有兩點半了。從八點之後什麼都未進肚,既餓且渴,心中都覺焦躁,滿以為到了沙朗可吃點什麼,又挨個空,只得勉力前進,在一個茶館門口遇到了王君。
這個小茶館門口只有三戶人家,只好在一個挑担上買了些老鼠啃過的甜糕糖餅之類,和着茶吞下去一些,祁女士一看見些陳年的甜品,就不覺得餓了,只喝了幾口茶而已。
離開沙朗走了四里之後,才覺得這個地形越來越可怕了。我們在嶺上走着,兩旁都是矮林,路既險峻,又多歧道,有人藏在我們兩旁也看不出來。出事之後,逃避極易,那幾個“民家”的團丁,到了此時都把鎗握在手中,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我們靜靜地在當中走着,這樣緊張的戒備之下走了四里,遠遠地看到有幾個背鎗的人在前面,我們的心都跳起來了,那幾個團丁說他們都是廠口的團丁。走近一看,才見到有五個戴大笠帽的便衣巡查,那時從沙朗來的四個民家兵要回去了,因為還有七里路到廠口,可同那八個巡查兵一路走。我們給這四個兵一點酬謝,他們再三地客氣后才收下了。
王君的意思,我們今天頂好歇在離廠口五十里的清水塘,那是一個苗村,我們都可以在他姊夫家裏,並且他的馬已由柿花箐拉到了清水塘。可是崔博士和祁女士實在太乏累了,祁女士摔跤之後還未復元,崔博士在出發之前,手臂和後腦的病都剛好,他的左腿從前曾受過傷,所以和王君商量的結果是他們去清水塘歇,我們同馬伕在廠口歇,明天早晨他把罵準備好了之後在路上等我們。
廠口完全都是漢人,我先去保公所訪保長,請他為我們介紹宿處。他請我們到他家裏去住,他肩上肩着一條長凳引我們到他的家裏。
宿處是在樓上的鐘堂裏,相當寬大。張保長臨時為我們打鋪,打掃塵埃。崔博士和祁女士實在太累乏了,一上樓就躺在床上休息着。
我去買了一斤牛肉,十個雞蛋,四兩豬油,一把掛麵,本來還想買點麵粉做個餅子,預備明天在路上吃,可是沒有一家有現成的麵粉。人民們平時的食品都是洋芋同包谷,麵粉是奢侈品,要吃的時候,臨時用手磨的。
晚餐是炸醬牛肉麵,我們在一個矮棹子上飽餐一頓,圍着火同張保長一家談談,就一會上樓去睡了。
八月十日(星期五)早餐後出發,一夜的休息,大家精神都好的多了。慢慢地前進。因為今天不跟馬幫走,走累了自己就休息着,路上買了些梨和煮熟的玉麥,飢渴的問題也解決了。走到將近撒旦之時,前面來了一個短瘦的穿着白麻布衣衫的背鎗的人,遠遠地就向我們一鞠躬,原來他是從清水塘來接我們的。他說王先生已到十里坡去了,叫我們就在撒旦等着,過一會十里坡的馬就會來的,再一同前去。今天就在十里坡歇,那地有一所小學和教友都準備着歡迎我們。
我們到了撒旦,見已有兩匹馬來了,一匹馱物,一匹騎人,原先的馬伕就讓他先走了,把行李卸了下來。
下午兩點十里坡的馬匹到了,我們三個人一人騎一匹,崔博士騎一匹頂肥壯高大的,祁女士騎一匹頂矮小的,我騎了一匹較頑劣的。
崔博士上馬真是相當困難,他欲先爬上一個泥堆等着,把馬牽了挪去,用兩個人拉住馬,讓他完全不動,靜的像一個木馬一樣,然後左腳踏蹬,再由我幫忙把他的右腳送上馬背去,等到坐穩了,那真是頗為“穩重”。崔博士自己也說:“我上馬困難,一上了馬就摔我不下了。”
出撒旦不數里即上坡,這一帶全是松林,地勢頗險,因為接近苗區,匪徒絕跡。我們在松林裏騎着馬,黃沙綠葉之中,徐徐前進,頗富時意。這個坡很長,一共有十里,所以我們今天去的地方,即名為十里坡。
還未走完松林,就聽到有學生們團體歌唱聲和軍號聲,精神為之大振。我不知道翻過最後一坡之後,將會遇到什麼奇蹟。
我的馬一直走在最前面,所以先翻過山坡去了,遠遠地望到有幾十個穿白衣的學生分着兩排站着,前面還有幾面國旗。他們一見到了我,就先吹起軍號來,我在馬上威風凜凜的走着,像是檢閱十萬大軍似的。到了他們面前時,就有人發口令“敬禮”,於是都把右手舉起,軍號同時吹了起來,我也自然地舉手答禮,雖然我頭上和那些學生一樣無帽子。走完隊伍,就有三位中年苗胞站着,都上來和我握手。
祁女士那時在馬上向學生一一答禮,最後是崔博士,他騎着馬走近旗子,正於用右手放在帽邊上之時,那匹高大的青灰馬忽往斜路奔跑,就這麼一頭兩頭:“說時遲,那時快”崔博士給摔下馬來了。幸而是“慢慢跌下”所以他也能“快快爬起”,衣服上塗了不少的黃泥,也顧不得那些急急走近歡迎的行列,點頭答禮。我怕他摔傷了,很不放心地一直回頭望着他,問他之後,他搖着手說:“沒有什麼”,又看見他從袋裏摸一個剛才摔破的梨子,一面咬着一面走着前進。
學生們成軍行排着隊跟我們來,一面吹着“起床號”,好像特別為“崔博士下馬”後再起而奏的音樂似的。
我們到了十里坡的小學了。小學課室很大,裏面足容六七十人,課室外貼着一張綠紙,寫着“歡迎中華J 督J H 崔博士、張幹事、祁幹事”並附苗文,課室前面有一個可以作為籃球場那麼大的平壩,學生們可在上面體操運動。
我們在教室隔壁的張老師的屋內休息,大家都很興奮這麼熱烈的歡迎,這麼許多的學生……真是“戲劇化”得很,而戲劇中最出色的部分還是“博士下馬”。
十里坡全是苗人,這個小學設立剛只一學期,現有五十一個學生,來自附近七八個苗村。教員張德新先生就是苗人。下午全校學生在草場上舉行歡迎會,排着隊唱自編的歡迎歌,崔博士當場向他們說了一篇話。歡迎會完了,學生們在草場上踢着自製的麻線球,我也參加他們去踢,又教他們球的各種玩法和幾個遊戲。我和祁女士還教他們唱了幾個歌,學生們學的很快,只教幾遍都能唱了。
晚餐在他們的課室裏吃,有鵪鶉和炒雞棕菌,非常豐富。米飯是紅色的,吃起來也比白米香些。晚餐後舉行歡迎禮拜,附近村子臨時來參加的教友也有十多個,擠滿了一教室,差不多有一百人,先讓張老師用苗語講幾句話,就領大家唱國語的讚美詩。室內點了許多松香和松光,滿室的光明和煙,大家似乎都能唱,唱的很響,很整齊。這些苗語讚美詩的拼音字,都是西國傅教師製的,並非是原來的苗字。我望着那麼多緊張誠懇的臉,真是感動,尤其是望到那個在白天橫着鎗向我們鞠躬的矮瘦的苗人,他給松光的煙熏皺着眉,閉着眼,可是仍舊張大着嘴在拼命的唱,有些老年人的鬍子給松光照映着,鬍子在上下動作,他們的歌聲從鬍子裏發出來。
唱完了一個之後,由王弘道君用苗語禱 告,接着是崔博士,祁女士和我的演講,我不知他們都懂,但是都相當的安靜,除了偶然有幾聲嬰孩啼叫之外再就是我們的講話和松枝燃燒的聲音了。
講完之後,王弘道君用苗語把我們講話的總括地解釋一次,“抑擺零止座”,最後張老師向大家說着,這意思是唱第一百零三首,他們仍是唱的苗語,就是那首“起來,全世界的罪奴……”,他們唱的太令人感動,我們三人也加入唱了起來,在十多只松光中,我們都沉醉在這首聖歌里了。
八月十二日(星期六)。我們一共十六個人,五匹馬,四條鎗,在清晨從十里坡出發,浩浩蕩蕩的前進。苗家的鎗法是有名的,所以挨近苗區的匪全被清剿了。我們有這些“英雄”們伴着,心裏頗為泰然。不過路太崎嶇了,不論是下坡上坡,都很陡險。我每次回頭看到崔博士在馬上那個紅着臉緊張的樣子,心裏真是感動。他已經五十歲了,又這麼胖,從來不會騎着馬過這麼大的山,當然非常吃虧。此次為了幫助這許多深山的苗胞,他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完成這個旅行。
行三十里,我們在馬街休息,吃着帶來的熟洋芋,又買了點米餅,切兩盤羊肉,吃的非常痛快。大梨每個一元,太便宜了,不過味不頂鮮美。馬街全是漢人,街上站滿了看我們的人,成年人一色的都掛着煙容,孩子們都掛着鼻涕。
吃畢又走。我們在路上處處要擔心自己的馬,因為這幾匹馬挨的太近,就會打起架來,幸而有幾個徒步的苗胞,他們隨時可為馬“解圍”。我的馬最討厭,總是選着危險的路走,不會多走幾步平坡,總要向面前的陡坡跳。到了離柿花箐還有十五裡的東村時,我的馬不走正中的石板路,偏要走旁邊的泥溝,前腳摔到一個很深的泥溝里去了,馬身立刻矮了下去,我急想跳,哪知牠也往上一躍,結果我給摔在地上了。不過並沒有摔傷什麼,只是右手中指被石頭碰破了,出着血。我又上馬,對崔博士和祁女士說:“上帝是最公平不過,決不偏持那個人,我們三人一人摔一次,第一天摔了‘女士’,第二天摔了‘博士’,第三天當然應該摔我這個‘韓事’了。一人摔一天,從昆明摔到了‘柿花箐’”。大家笑了起來,我也忘記我那出血的手指了。過了東村之後,走了一節平路就上坡。這個坡非常陡,馬走幾步停了下來,再走幾步,又停了下來。坡高七八里,是生平第一次遇到的陡坡,崔博士說這是“天下第一坡”。
上了坡頂,又聽到歌聲和軍號了。我們預先都下了馬,以免崔博士那匹青灰馬見到了這麼熱烈的歡迎會,又“受寵若驚”奔騰起來表演“博士下馬”。歡迎的學生有八九十個,都是一律的白衫,吹着號,唱着歌。他們行注目禮,並沒有舉手。
柿花箐也只有十六家苗胞,這是苗村當中比較集中的了。這裏有一所完全的小學並且還辦了一班初中,由王弘道、王有道兩兄弟負責,這兩位昆仲都是苗胞,他們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王有道先生十五歲時進武定縣的沙鋪上(註:灑普山)內地會所辦的小學裏讀書,不過那個學校,只准他們講苗文S J 。後來到了昆明,仍沒有機會進學校,只做了一年接電話的工作。不過在這一年當中,看到了昆明的一切情形,並且痛恨自己沒有上學的機會,就立志要來為苗胞辦學。剛開始辦學的時候,他們弟弟弘道君祗有四歲。他教八個學生,完全盡義務,自己一面耕種,一面教書。後來學生漸漸多了,到今日有道先生已有四十四歲了,除了柿花箐的小學已成為完全小學,共有一百二十個學生之外,還在進行辦初中。在滇中其他的苗區裏,也由他發動辦了七個初級小學,其中六個小學的校長都是他們的學生,十里坡小學的張校長是他的同學。這八個小學一共有四百多學生,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苗胞,還有些夷胞和少數貧困的漢人。
學生們多數是從外村來住宿的,自己帶了糧食來,學費是初小每年糧食四升,高小每年糧食六升,初中每年一斗,教員們的束脩很低,王氏昆仲差不多全是盡義務的。
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昨夜到柿花箐,因為都疲憊了,所以沒有開會。今晨天剛亮就舉行清晨禮拜。到了午飯後又有禮 B 。村子裏忽然熱鬧了起來,聚會的時候在一個大課室裏緊緊擠着兩百左右的聽眾,散了會都在坪子上曬太陽。夷胞的婦女們穿着紅紅綠綠的衣服,非常美麗。可惜我們的話多半的人聽不懂,尤其是那些女同胞們,在聽講的時候呆坐着,在坪子裏只能陪着我們笑笑。
祁女士教些女孩遊戲,有一個初中一的叫做張梅君的學生,很快的就學會了,她是一個夷胞女孩,長得很清秀,人也很聰明。
午後的會議是崔博士報告中華J D教H的工作等,苗胞們提出來幾個問題。第一、大家公推王弘道負責苗村宣道工作,可否請總會給予深造機會。崔博士當即答應盡力給予深造的機會,並同意王弘道暫時為滇中苗區的宣 教師。第二、教友們將在柿花箐自建 J 堂一座,請總會捐助一架風琴,崔博士也立答應了這個請求。第三、請求總會印苗語及夷語普天頌贊及S J 。崔博士允代向成都華英書局接洽。第四、希望滇中七縣能設一診所,為苗夷邊民治病。崔博士的回答是盡力去辦。他們提出的請求很是具體切實,崔博士的回答也很使他們滿意。
晚上讓我演講,教室內坐滿了人,總不下二百,我先問他們願意聽那方面的演講,他們商量一會之後,有一個六年級學生站起來說:“請張幹事告訴我們抗戰為什麼一定可以勝利”。這個問題真使我高興,因為這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當然我所講的更能給他們較深的印象,我就很緩慢很通俗的一句一句講着,講到淪陷區敵人的殘暴行為時,大家都傷感的望着我,有兩個竟掉淚了。講到國軍英勇的戰門和必勝的理由時,大家都興奮起來。我的演講剛結束,十里坡的張老師立刻站起來要大家唱松花江上的歌,於是室內充滿悲感的氛圍。唱完之後,我對他們說,這不是難過的時候,我們要起來把敵人打出去,我們來唱義勇軍進行曲吧,“起來,不願——”這麼雄壯,這麼激烈,從松光照映着那些健康而真摯的臉上,我望到了新中國前途的曙光。
八月十四日(星期一)。今天來了更多的人,有些消息得到的慢,所以今天才從數十里外的村子趕來。早禮拜都是祁女士做的,上午十一時是領洗禮拜。祁女士和幾個女生忙着把教室佈置一下,用樹枝和野花紮成一個美麗的 S 字架,還用竹葉在遮布上釘了“學效J D ”四個大字。給大家一個嚴肅敬重的印象。領洗儀式一切都是在極壯觀的空氣中進行。先由崔博士講解領洗的意義,接着用一碗水來施洗,一共有三十個苗夷的信徒受洗。
午後我去王有道家閉坐。他的家和普通苗人家庭一樣,灶房裏堆了些雜物,用三個石頭擱成的灶上燒了一大鍋白菜,旁邊還有好幾個鼎鍋。我問王先生這些是什麼,他說今天宰了一隻羊。真是太客氣了,我怪他們不該為我們如此花費。他說:“這一點點意思,我們慚愧得很。”他說的不是客氣話,而是真正代表他內心的意思。
他說他有一個理想,希望在他死去之前能夠看到苗人自己有一所完全中學,並且還辦起了大學。他說大學即使不能辦成,至少要看到苗人中有四人從大學畢業出來,一個學醫,一個學教育,一個學農業或畜牧,一個做M 師。他苦悶了二十四年,含辛茹苦,今天的成績實在不可埋沒與輕視。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小,誠懇的盼望着中華J D 教H 去幫助他們。他盼望能夠送他的弟弟王弘道去讀S 學,至於王弘道的家庭生活,已由衆教友答應輪流去為他家作工來維持。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晚間我又被請去演講,講“愛”的意義。
八月十五(星期二)。今天一早吃午餐,全程送我們半里多路,分手時有好幾個流着淚,尤其是那位盲目的夷人李浩然先生竟大哭起來。他說:“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了,我們的心是分不開的”。對的,我們的心怎會分開?
今天的路長,坡高。沿途是夷村,不見苗民,行十里到黑山,再十五里到沙木里杜,再七里到貝子田,再八里到羅囊。這些夷村多則十數家,少則五六家,據說也都是教友。內地會的M 師從前曾來傳過道。由羅囊再十里到後街,我們就在後街午餐,吃點洋芋和饅頭而已。同行的苗胞都吃涼粉。離開後街,不久,遠遠地望見幾條鎗,大家都有點提心吊膽,怕是匪人,才知道是楊柳塘來接的五位苗族青年。他們在此已等了兩個鐘頭了,請他們各食梨一枚解渴。
我們同行的人更多了。不幸得很,烏雲漸漸近起來,雨來了,到牧羊壩子時已都淋的透濕。幸而不久即晴,又復前進,牧羊壩子距後街二十五里,到楊柳塘只有十里。學生們在離村兩里的地方排隊接我們,和我們一同回村。
楊柳塘有十五家,此地也有一個小學,有學生四十六人。
晚餐後,小學里擠滿了人,大家都很累,為了不使他們失望起見,我去同他們講話。有一個老婦人聽到我動勉學生要用功讀書,體貼父母的苦心時,她大哭起來。
八月十六日(星期三)。上午舉行歡迎會,到一百五十六人,我們三人都簡單的講了一篇,後由一位佈道員王先生翻譯。午後有六十六個信徒受洗,他們同柿花箐的一樣,已等了好幾年,沒有人來替他們施洗,今天都是從數十里甚至百餘里以外的村子趕來的。
楊柳塘的教友今晚又宰了一隻羊招待我們,同時他們自己也藉此聚會,非常熱鬧。夜間,教室裡又坐滿了人,臨時又請我去演講,我所講的內容是關於抗戰和普通的常識。
八月十七日(星期四)。今天早晨離開楊柳塘,回昆明所走的都是平路,不過在平路上最討厭的是來往的駝木板的馬幫太多了,讓來讓去頗為費力。祁女士離大灣之後半里下坡時滑了一跤,臉色立刻白起來,閉着口說不出話,過了好久才把她扶起來,慢慢上馬。祁女士真是“有始有終”,離開昆明那天摔一跤,回到昆明的那天又摔一跤。馬到花次溝,原擬在此換塔馬車,因時間過遲,馬車已都走完了,只得吃頓午餐後又到黑龍潭,從黑龍潭就可坐公共汽車了。汽車在離昆明五里之地忽然損壞,不得不下來又臨時喊了一輛運黃沙的馬車,坐了上去,到大東門時已經黑夜了。旅程就告此一段落。
——載《邊疆服務》
1945 年第 8 期第 34-4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