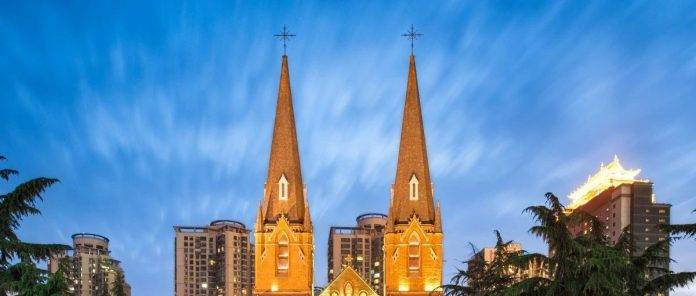第九次读书会
“耶稣基督在他自身内受有了我们;如果我胆敢这么说的话,我们,比基督自己的肉身,更真切地是他的身体。”这是博絮埃(Bossuet)的惊人之笔,尽管他小心地加以限制:“任何有着爱德与基督徒合一的精神的人,都能理解我的意思。”他继续说道:“基督在自己神圣肉身中所行者,便是那他将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者的真正模式。”博絮埃将此基本原则和大胆的言说方式,归因于自己对教父的恒常研习。例如,奥斯定教导我们,“基督身上的一切,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举止,甚至他的肉身,都是基督徒生活的象征,都是这位既独一又普遍的属神之人的‘圣事’。”在奥斯定之前,奥利金便极精确地阐明了基督个人性的身体和祂“真实”身体——也即教会——间象征性功效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圣事性共融的“真理”,最终的果实,是与教会合一:在教会的心中,圣言(Word)回荡,因为教会的确是逻各斯(Logos)真实的临在。中世纪时,奥利金思想的要素,在各个方面得以重现。William of St. Thierry,尽管带着他特有的轻微差别,也像其他人一样区分了基督的三重身体,而又紧接着说,事实上,尽管我们可以三种方式借着信仰深思、凭着虔敬依附基督的身体,但这一身体在根本上是一。因此,从悬在树上(指十字架)的肉身到教会,“有着无间的连续性”。
按:William of St. Thierry是熙笃会的成员,与伯尔纳铎并称,特别着重于爱,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会更加地注重理智。这里提到“以三种方式借着信仰深思、凭着虔敬依附基督的身体”,但没有具体说哪三种方式,也没有说哪三重身体。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文本,指的是基督在世的肉身、基督复活后的光荣身体、还有他的奥身,或者说他的真实身体,也就是教会。这个身体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从悬在树上(指十字架)的肉身到教会,“有着无间的连续性”。“无间的连续性”不仅在于身体的一致,也在于历史上的一致。依照一种通行的解释,正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当基督把圣母托付给若望,并把若望托付给圣母的那一刻,或者说当他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的那一刻,教会就成立了。在历史上,在时间上,它也有着无间的连续性。当然在奥秘的层面,在根本上,这个身体的连续性就更为密切一些。
奥斯定教导我们,“基督身上的一切,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举止,甚至他的肉身,都是基督徒生活的象征,都是这位既独一又普遍的属神之人的‘圣事’。”奥斯定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天主教传统共同认可的。中世纪后期的一本灵修名著,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也就是在一切言行上都以基督的在世生活为榜样,这些在世生活都指向祂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受难之后的复活。
刚刚我们触及到一个问题的边缘,或者说,是一系列问题的边缘,在本书的范围内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能让它们为神学家们所注意,也就够了。然而,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审视神学史上系统化的努力,它们所要强调的基本观念绝不能被当成或多或少的无据思辨或者对信仰没有实际影响的意见之争。因为,教会圣师关于祭台圣仪的教导,为教会当局在她的礼仪中,在圣体祭献的行动中,在这一行动的仪节(rites)或轨范(formulæ)中,强有力地推行开来,以教会权威的全部分量证实了它。
按:一个问题的边缘,或者一系列问题的边缘,就是在更具体而细微的层面探讨的教会与圣体圣事的关系。圣体圣事塑造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细节,吕巴克在这里没有进行细致的探讨。这一段讲,神学的确有思辨的成分,或者说有争论disputation的成分,但是神学不仅仅是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在根本意义上,它起源于生活而又复返于生活。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起源于教会对崇拜天主的需要,就是礼仪,而又复返于教会实际的崇拜天主的行动,还是礼仪。所以它的开端和终结在某个层面上都是指向礼仪行动的。因为礼仪,就其本质而言,便是对天主的崇拜、敬拜,一种完全无功利性的、全身心参与的行动。
“遍及普世,基督徒的祭献是一;因为作祭献的基督徒是一,所献给的天主是一,借以祭献的信仰是一,献上的是一(for the Christian by whom it is offered is one, and there is one God to whom it is offered, one faith by which it is offered, and one alone who is offered)。”这是“教会的祭献”,“整个教会的祭献”,无论牧者还是百姓,无论在场还是缺席。而它的目的,仍是合一(unity),因为它是为了教会而祭献,为了一个更大的、更团结(united)的教会:为了整个世界的救赎(pro totius mundi salute)。安布罗斯礼仪的前言如此说道:“神恩无可言喻的奥秘带来救赎。”“经由圣神的灌注,众多的祭献变成一个基督之身,这也正是为何我们这些领受圣餐共融的人能够结为一体(The offerings of the many become by the infu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he one Body of Christ, and that is why we who receive the Communion of this holy bread and chalice are knit into one sole body)。”
按:这一段还是引用教父们的话,或者说天主教会的官方训导来说明合一的道理。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特别是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因为从这句话来看,可以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作祭献的基督徒是一,我们都是归属于基督的。所献给的天主是一,我们共同献给的都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不是犹太教纯然超越的天主,也不是伊斯兰教一位的天主,当然也不是自然宗教只能够模糊地把捉到的无名之神。借以祭献的信仰是一,信仰是天主所赐的超性之物,并且我们依靠信仰来补充自己理智的缺陷,在黑暗中认识耶稣基督,并借由耶稣基督来认识天主。献上的是一,献上的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做祭献时,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什么东西献给天主,这是附加性的,我们首要的是在重复耶稣基督当年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我们重复他的行动。基督用一种奥秘的方式,基督借着教会把自己祭献给天主,或者同义反复地说,天主借着教会把天主祭献给天主。在祭献的过程之中,需要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需要我们在心神上与天主合一,需要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但这个是附加的,而且这种 “附加的”必须要因着“首要的”带来的效果,才能够真正地得到实现。前面吕巴克说,教会祭献的目的是合一,因为它是为了教会而祭献,为了一个更大的教会。我们可能会把吕巴克说的这个教会当成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可见教会,有形的组织实体,罗马大公教会。但是吕巴克后面接着引用了教父的话,教父们共同肯认的道理,“为了整个世界的救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教会是奥秘的,等同于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际上会有一种努力,让天主教友和新教友共同举行圣餐,会有支持的,也会有反对的,会有更审慎的,也会有要我们最好先展开行动,然后再来具体地、细致地深化理论的。双方的确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们所给出的意见也都是比较坚实的。我们暂且不涉入这里面的争论。单纯地说,在圣神的灌注之下,在圣餐的共融之中,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能够结为一体。因为天主合一的力量永远大于人分裂的力量。
讨论部分:
1.我有一个题外话。吕巴克写悬在树上,怎么理解呢?是生命树吗?(从悬在树上(指十字架)的肉身到教会,“有着无间的连续性”。)
2.对,可以关联着《创世纪》中的生命树来谈。有两种解释,一种比较朴实,是直接性的隐喻。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用木头做成的,就是把树直接等同十字架。也有一种奥秘的解释,把它等同于生命之树。悬在树上的肉身,是基督受难、垂死的肉身。十字架在当时是羞辱的记号,但是天主把它转变为生命之树的象征,生命的象征。与此同时,在这种羞辱之中,恰恰显出了天主的荣耀。天主荣耀的工作方式和我们以为的荣耀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我们可以想想堕落,堕落是因为人不听从天主的命令,服用了知识之树、“智慧”之树的果子。但最终要靠生命之树救赎人类,把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走出的扭曲之路,重新纳入到生命之中,让真正的智慧在生命的轨道中展开。
3.悬在树上,包括后面的祭献,让我想到了比较宗教学的一个典故,跟这个神学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蛮有意思的。据说传教士给北欧民众传教时,由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跟北欧的奥丁神话有很大的相似性,北欧民众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形象。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最高神,曾经也悬挂在树上,深受自己长矛的刺伤。奥丁自己被当作奥丁的祭品,自己献给自己,在无人知晓的大树上,同样描绘的是自我祭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智慧、奥秘。
4.这也不算题外话。在基督宗教诞生之前,其他民族的神话和秘仪传统或多或少都跟基督宗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此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就是比较宗教学的外在视角,把它解释为基督宗教是人所设立的,在设立过程之中,它吸纳了各个传统之中,或者说正好那些传统流传到地中海地区,为它所吸纳的那些东西,然后混杂成了一个自己的东西。
另一种解释,从基督宗教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早期护教士经常采用的护教法,在基督诞生之前的其他传统都在为他做准备,都在为他开路。犹太宗教当然是最大的准备。但是这种准备也以零星的方式、分散的方式出现在其他民族之中。
我个人肯定站在后一种立场上来看待问题,而且我会认为第一种立场有一些问题说不通。比如人不会为神话myth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宗徒,包括其他的门徒,几乎都是非常惨烈地殉道而死,被石头砸死,倒钉十字架而死,他们殉道的见证,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信仰不是一个由人的理智从头脑中借着不同的材料拼凑而成的混杂的主题,而是真正地能跟生命合一的,他们真正地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了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这是殉道者的见证性的论证。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论证方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比较宗教学的外在视角也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对基督的想象、对早期教会的想象投射入历史的真实之中,而他们这种还原性的、历史性的做法,恰恰有助于拨开迷雾,能让我们少以自己的臆想掺入对历史真实的解读。
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教宗弥撒的仪式尤其引人注目:
在罗马教会中,共融圣事的仪式应当包含对教会合一清晰有力的表达,这点尤其重要。因此,就有了“Fermentum”的传统习俗,即把主教弥撒中所献之至圣圣体,送到那些在祭台上献弥撒的司祭那里去;因此,也显出了圣哉仪(the rite of the Sancta)——在高唱“上主和平”(Pax Domini sit semper vobiscum)时,将前台弥撒所剩下的被祝圣过的圣体片放入本台弥撒的圣体盒中——的意义。如是,在罗马所有的教堂内,在过去与现在所举行的每一次弥撒礼仪中,都是同样的祭献,同样的圣体圣事,同样的共融礼。如是,为了明明白白地显示出,从祭台上(from the altar)被分开与分发的饼与在祭台上(on the altar)被祝圣的饼是同一个,可以把一块圣体片留在祭台上。
出于类似的象征性理由,教宗在举行完弥撒后,会保留一些被祝圣过的酒,然后大执事先将它们倒入圣爵,再把圣餐带给会众。至少,这是Louis Duchesne所理解的,他将此仪式追溯到八世纪,尽管,正如M. Andrieu所设想的,一开始可能只是便宜行事。
按:这里还是在讲共通性的问题。在罗马所有的教堂内,是一个空间的意义。在过去与现在所举行的每一次弥撒礼仪中,这里有一个时间的跨度。这个罗马可以扩展到普世的,无论空间上多么广远无界,无论时间上多么往来不息,它们都只是同一场祭献,同一个圣体圣事,同一件共融,以一种极其密切的方式完全交融在了一起。这样的交融,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种实在性的显示,一种圣事性的显示,它是真的。
倘若这些古代的仪式,不再能为我们在参与日常弥撒时描画出教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合一,在牧者和百姓间的合一(这合一本就是奥秘合一的象征,而祭台祭献则是奥秘合一不断更新的纽带)。在礼仪中,也绝不缺少能让我们记起圣体卓越功效的祈祷。想一想圣灰节后周五共融圣事结束时的祈祷:
按:这里提到古代仪式的象征意义。我们今天不再有一种圣事性的看待世界的观点。我们只能把眼前的这个看为这个,不再能够通过这个看到它所折射出的另外一个更加崇高之物。与此同时,这个更加崇高的层面没有完全泯灭了现实层面中这个东西的确切含义,而是把它提升了。吕巴克接着说,在礼仪之中,也绝不缺少能让我们记起圣体卓越功效的祈祷。下面举了一些祈祷文,让我们体会到教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合一。
上主,求你垂怜,赐给我们你爱的圣神,以使这些你以同一天粮喂养的人,能在心灵和信仰上成为一体。(Spiritum nobis, Domine, tuae caritatis infunde, ut quos uno pane caelesti satiasti, tua facias pietate concordes.)
又或者,
上主,我们祈求,慷慨赐与你的教会合一与和平的恩宠。我们此刻所作的祭献,便是这恩宠奥秘的记号。(Ecclesiae tuae, quaesumus, Domine, unitatis et pacis propitius dona concede, quae sub oblatis muneribus mystice designantur.)
讨论部分:
1.有一个比较值得讨论的问题。圣体圣事在宗教改革里面争论最大。在天主教跟新教的争论里,针对弥撒的性质,有所谓的真实性探讨。如果天主教一定要坚持祭献的真实性,那么像加尔文,或者另外一些改革派,比较抨击的是,这样看待祭献,那祭献便是反复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由此推理出弥撒根本就不是一种仪式,只是一种纪念活动。时代变化了,大家思维方式不一样了,如何理解弥撒的献祭是一个真实的仪式,而又能够跟耶稣基督的献祭等同?
2.我觉得你刚刚的问题其实是多层的。第一,加尔文宗认为,一次献祭已经够了,不需要天天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加尔文宗特别在意天主的主权,就认为这样是对天主的一种侵犯,一种亵渎。不过,我们可以回想起早期教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关联着人的道德生活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每次心思不正或者说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而且这种情况比圣体祭献更让耶稣基督心痛。因为这是我们以自己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而教会后来所做的重复耶稣基督之前那一次一劳永逸的祭献的其他祭献行为,都是耶稣基督作为主动的实行者,他乐意为救赎全世人的罪把自己钉了十字架。
第二,思维方式的变化,“纪念说”可能更切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阐明为什么天主教一定要坚持真实性。用天主教的眼光来看,论证包括圣经、教父们普遍的观点以及一些神学上的思辨和推理。我个人认为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根本上,在于天主教思维跟新教思维的不同。天主教看待世界的眼光极度丰富,有一个丰富、满溢、超越的维度。而新教相对来说,更专注其一,而不顾其他(sola)。坚持身体的真实性,它同时是纪念,对过去的纪念,但也是现在的一个圣化行动,更是对未来天乡的预尝。里面包含了多种维度,而这又跟天主教对天主恩宠的理解、对天主恩宠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天主的恩宠极为丰富,允许人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去把捉它,去领会它,去让它渗透。同样,天主教会也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性的宝藏无限丰富,而恩宠的无限丰富搭配本性的无限,能够把它们分别地加以提升,这种种分别又能够汇成一个其大无外的、但是又包罗万象的综合体。这些可以在直观地在建筑上、在大教堂上看出来。第二个问题,思维方式的变迁是梵二之后,在天主教会内,两大神学学派的争论焦点。公会议一派认为我们一定要跟随时代,时代怎么变化,我们就怎么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把福音传下去。而共融派,也就是吕巴克所从属的一派,他们认为福音真理优先时代的变化,时代变化永远只是暂时的,人不能随从这个时代的变化,一定要随从耶稣基督的真理。人对世界的一种圣事性的认识确实在衰退,但毕竟还有一部分人能够这么来观看和理解世界。类比地说,比如哪怕身处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少部分人也应该坚持自己心目中一定不移的伦理标准,做一个高尚的人。时代风气也许不能作为一个最终的衡量标准。
3.基督在历史时间当中的那一次被钉十字架,是超时间的。发生在时间当中,但本身超越时间,是永恒。对于我们在时间当中的人来说,它就是时时刻刻的、永远的。
4.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终那个时刻,神学上有个称呼,叫逾越。在那一刻,他正好由时间逾越到永恒,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进入了永恒,从此便具有了永恒的效力。如果它不具有一个永恒的效力的话,教会维持不下去,恩宠也不会降临到跟耶稣远隔两千多年的我们的身上。从永恒的层面来看,后面教会所举行的一次又一次祭献,跟耶稣基督的那一次祭献,是不断地重叠,不断地合一。很难用语言去表述它,因为任何语言都是在时间中说出的,有一个先后的维度。此刻我们在时间中的人,此刻就已经在永恒之中了。因为等到我们到时间的终末,就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逾越,由时间进入永恒一样。在终末,我们由时间进入永恒的那一刻,时间同样是完全被收纳进永恒之中的。所以我们的行动,都是合一性的行动,共融的行动。
5.好几年前,我在深圳碰到一位驻香港的荷兰大使。他退休之后经常在深圳住,一天望好多弥撒。他说这个世界不能停止弥撒,中国早上八点,美国是晚上八点,如果每个教堂做弥撒,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这个世界都没有停止。弥撒是耶稣对我们的拯救,不断与我们共融。
6.新教很注重的是祷告和读经。祷告时,时间和永恒相连;读经时,就是上帝跟我们说话。这是不是一种合一共融呢。
7.以一般意义而言,这肯定是一种合一共融,但不如圣体圣事那么彻底。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圣体圣事的优越性,这个关联到天主教对圣事真实性的肯认。读经是天主对我们说话,祈祷是我们对天主说话,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圣体圣事中,天主直接把整个自己给了我们。他给予我们一个天主,我们所有人分有的也是同一个天主。我们每个人领受那一小块饼的时候,每一小块又是同一个天主。奥斯定的话,当你吸收我时,不是我成为你,而是你将被转化成我,圣事圣体共融性的力量,被转化成耶稣基督。另外的一方面,不管是读经,还是祈祷,人都会掺杂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志意。比如,我们可能对圣经的理解不一样,那就有破坏共融的危险,但领圣体时候,要求我们倾空自己,单纯地领受。
8. 有些关于圣体圣事的观念,可能与天主教经院哲学和新教的形而上学有关系。圣餐变体说,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体本体论相关。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待到新教兴起的时候,已经不为他们所接受。天主教的思想资源与新教的思想资源有所不同。天主教认为圣体是实体的转变,所以是真实的。新教保留了理念上的形式,否认了实体性形式。
9.补充一点,以上是从哲学、形而上学的角度谈论的。从历史的角度,天主教确实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素朴的实在论,而路德接受了唯名论的观点。但我们也可以从巴尔塔萨等二十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的角度看,这与他们对道成肉身的体认有关,对物质较为积极的看法。另一方面,在基督宗教看来,信仰真理是和谐一致的。耶稣在世时,有一个真实的身体。耶稣死后复活,同样有个光荣的身体。终末时,我们复活也有一个身体。所以在圣体圣事中,同样有个真实的身体。教会警惕纯粹属灵的看法,因为它蔑视大地、物质、肉身,贬低了人,贬低了天主的创造,进而贬低了天主。不过,新教内部确实派别众多。比如,马丁·路德虽然不支持天主教会的变体说,但他主张的同体说也承认圣体圣事的真实性。确实不宜讨论单数的新教,应该以不同的派别分别地来展开讨论。
10.文本里面的一个落脚点其实是偶像崇拜。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疫情期间有圣体游行,很多新教徒以为这是偶像崇拜。在时代背景下,这个局面有些尴尬。
11.这个如果硬要说时代背景的话,它是一种世俗主义。世俗主义不会在意你们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分别,不会在意你们是否偶像崇拜。你说的是基督宗教内部、新教对天主教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背后的理论根据是不同的。很多新教朋友认为拜圣体是偶像崇拜,也会认为敬礼圣母也是偶像崇拜。在这些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经过比较艰难的努力,才能达成一致和共融。个人比较欣赏二十世纪天主教神学。因为二十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无论是巴尔塔萨,还是拉辛格,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基督中心论的倾向。以基督为中心,更容易展开不同宗派的对话。
教会的典礼遍布着同样的思想,从共融赞到天主经与和平颂,以Florus of Lyons的话来说,便是,教会内,人人相互给予和平之吻(dat sibi mutuo omnis Ecclesia osculum pacis)。如果过去世代的礼仪学家向我们展示出的,今天被看为太过微妙而令人困惑,我们仍需承认,即便他们采用了最为怪异和任意的寓意式释义,他们也和他们的弟兄释经家一样,是从信仰的类比(the analogy of faith)中取得灵感。因此,Amalarius和他的后继者Rhabanus Maurus,这般解释司祭在主持圣礼时在圣爵上划十字圣号的举动:圣爵的四面为司祭所一一触碰,以显示基督的身体将整个人类重新带入合一,将从四面而来的人汇入一身,因此而成就了大公教会的和平。依照同一基本而又重要的主题这种简单的变体,还可找到许多其他例子。在主祭时,司祭不是两次为教会的合一作出祈求吗?
罗马礼的这些祈祷,以及其他拉丁礼中相应的部分,重复了古代礼仪所言说的东西。我们关于最初几个世纪官方祈祷的证据实在是太少了,但最近发现了一段极富价值的残篇。它来自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布道,几乎与St. Cyril of Jerusalem著名的教理讲授(Catecheses)处于同一时期。它详尽地描述了弥撒礼,在其中我们发现,司祭在整场弥撒的最高潮,热切地祈求所有参与这场奥秘合一的人之间的契合与归一(union and concord)。
巴西尔礼,另一种东方礼,在同一庄严的时刻,以几乎相同的词句,说出同一件事:“愿我们这些分有同一饼酒(圣体血)的人,能在同一圣神的共融中彼此契合。”同样的渴求在古老的亚美尼亚礼的呼求圣神祷词中回响:
“我们祈求你,上主,遣发你的圣神,临在我们和这些礼物之上,圣化这饼和这酒……愿祂使我们这些分享同一饼酒的人,一体无分。”
或者在St. Eustace礼中,和平之吻前的祈祷:
仁慈和宽大的上主,我们同声向你泣求:赐给我们和平,以使我们能在神圣的亲吻中互赐和平……使我们成为你一体同圣的子民,将我们彼此相连以拯救我们,让我们唱起你的赞歌。
在西方,“宗徒宪章”的比喻,将我们带回三世纪初。很有可能,它描绘了直至二世纪末罗马教会的功能。在东方礼中,有同样的祈求:
上主,请将你的圣神降在这一团体的祭献上。聚集它,联合它,降恩给所有在它之中欢悦的圣徒,以使他们充满圣神。
同样,这也是除新约记载外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感恩祭形式的主题,可在《十二宗徒训诲录》didache的第九、第十章读到。然而这一奇妙的祈祷,类似于犹太人的饭前祝文,真的是感恩祭祈祷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出色的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如此之多感恩祭祈祷的基础,而且它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在Serapion of Tmuis——亚他那修的友人,四世纪时的埃及主教——的《礼典》(Euchologion)中找到。单单为了这个理由,它便值得在此征引:
正如这块面饼,(起初的麦粒)散落群山间,而又被聚集归一,因此,你的教会将从地极被聚到一处,形成你的王国……上主,请纪念你的教会,从四方收拢它,圣化它,成就你的国度。
这是那些为基督所聚集一处的人的渴望,基督的圣神充满了他们的心。不仅是教会向天主献上基督,当元首的祭献跟随着肢体的祭献时,也是基督向天主献上教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只要他肢体中的一支为他作出见证,基督便如同依弗大献上他的独生女(参看民长纪/士师纪第11章)一般献上教会。无论是官方宣布的殉道者,还是那些在受苦中相信自己是天主和基督真正的捍卫者的人,这一点都真确无误。Saragossa的殉道者,在向行刑者交付自己时,作出了宣言,很少有比这一宣言更能感动人的句子了,全幅庄严,却又如此单纯:遍布东西的大公教会,我需要你,请纪念我。(In mente me habere necesse est Ecclesiam catholicam ab oriente usque in occidentem diffusam.)
这是真正的祭献,祭台上的祭献为它作准备。因此,真正的感恩祭式的虔敬,并非个体主义式的虔诚。它“对一切无益于教会之事,无所挂怀”。它以一种包卷万有的姿态,在单纯热诚的意向中,将整个世界都纳入怀抱。它让我们回想起圣若望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在建立爱的圣事时自己所作的评论:葡萄树的寓言(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新的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为合一所作的祈祷(愿众人都合而为一),通往爱的至高标志的道路(指殉道,“人若为他的朋友而死,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真正的感恩祭虔敬,正是在这些事上奠定了思想和决心。如果没有兄弟般的共融,无法想象擘饼的行动:在共融中擘饼(in communicatione fractionis panis)。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在古代礼仪及延续至今的东方礼中,呼求合一的祈祷是呼求圣神降临祈祷的高峰。呼求圣神降临,如同整场祭献,却又以更为清晰的方式,展露出圣神的记号。这一位圣神,既预备了基督的肉身,便同样会介入圣体圣事,以造成基督的奥体(指教会)。他现身于厄里亚的祭献之中,如吞没的烈火,将人性中的渣滓燃烧净尽,除去对圣事之合一德能的阻碍。正如基督的圣神降在宗徒身上,不是要将他们在封闭的圈子里联为一体,而是为了在他们内点燃普世仁爱的火焰,因此,当基督每一次交付自身、将天主四散的孩童聚集归一时,圣神便会重临。我们的教会是马尔谷的楼房(upper room,宗徒行传1:12-14;2:1),最后晚餐不断地更新,圣神不断降临。
讨论部分:
1.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在摩尼教传统里,也讲到合一是战胜魔鬼的大前提。吕巴克所讲的合一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维度。就是说,以敌我区分的立场,我们有需要战胜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2.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如果以更为深层的角度去看,恰恰很对。只要你把这里的无产理解为彻底意义上的神贫,这恰恰也是早期方济各会走的道路。因为人如果能抛弃所有外在的财产和内在的财产,外在财产是指财物,内在是指知识,就能够更好地爱近人,因为这些东西是引起纷争的源头,财物跟财物相争,知识跟知识相争。现实来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从终末论的角度,我们不是梦想一个乌托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想象一种全凭人类的行动主义。终末的合一,归根结底是基督所带来的。第二点,摩尼教的合一是一种精英主义式的合一。在教会这里,合一是无分的,恰恰不是知识上的、道德上的优越性,然后这些优越的人组成一个团体。没有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越。所有人都是有各自的优胜之处,所有人都彼此分担各自的贫弱,所有人共同组成基督的身体,共同效法基督。另一方面,你提到,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是对诺斯替主义常见的批评,他们敌视物质,敌视这个世界。他们是以敌视、怨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动力。吕巴克完全相反,我们当然也有敌人,就是魔鬼。但魔鬼无形不可见,我们绝对不能把敌人等同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具体的近人。近人恰恰是我们要爱的对象。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近人。在这个意义上,吕巴克不是以一种敌我区分来展开行动,而是优先地,从合一的角度去看待这种共融。这敌人可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可能是来自外界的魔鬼。但不管怎么样,不是近人,也不是这个世界。
3.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合一本身就是一种分裂。举一个例子,有敌人的状态下,整个国家的人才能够团结起来,有外人的状况下,本来有矛盾的朋友也可以合起来,然后共同对抗这个人。但是吕巴克所讲的合一,是爱的合一,爱则天下无敌,不是以对抗的视角来实现的。比如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要合一,往往状况是什么呢?我以天主教跟世俗社会对立,以天主教跟新教对立,会一直讲,我们要团结起来,要延续我们的传统,旦我发现,自己有时候很难跨出这个维度,往往是一种恨的合一。
4.我们可能是一样的,在早期,我也有对抗性的思维方式。但是,正因为难,才要去做;正因为转变思维方式太难,才值得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