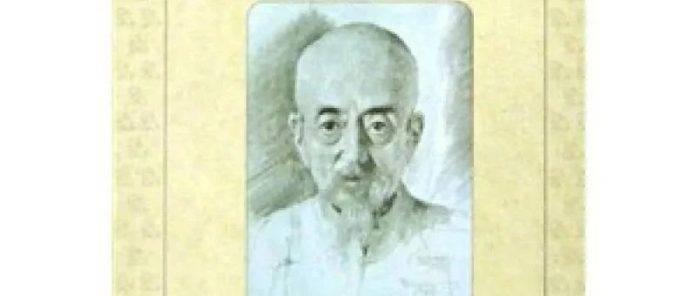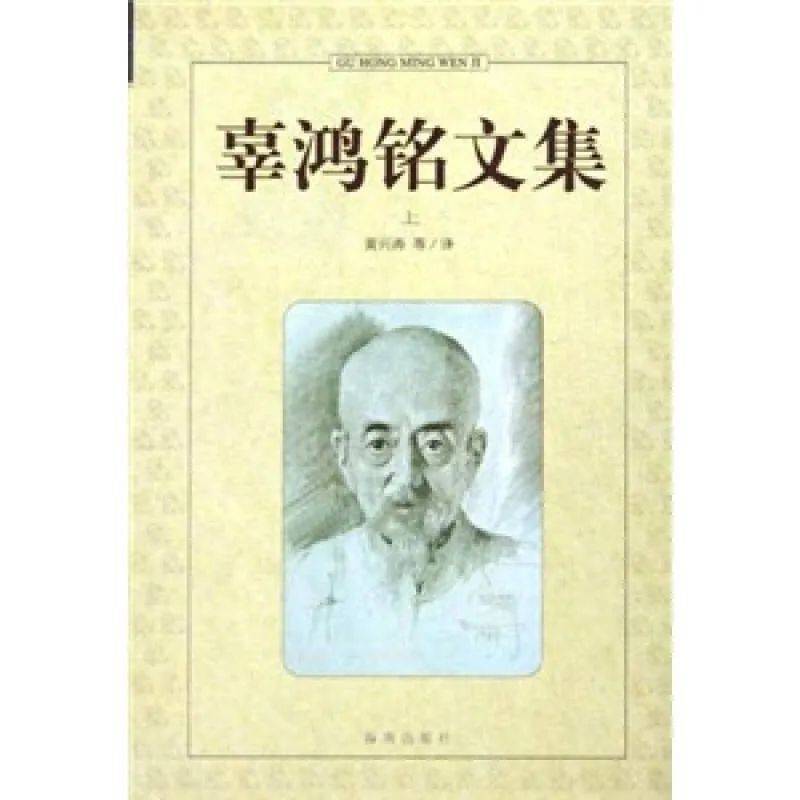
在清末民初,辜鸿铭怪得并世无两,因此评论他的人自然就不少。论者明显分新旧两个阵营:旧阵营的,比如罗振玉就盛赞他,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外务部左丞辜君传》;新派人物中的激进者,如鲁迅,在批评世道乱象时只提到辜鸿铭的名字,根本不屑于论述辜为何不堪。那意思是,辜鸿铭的反动是众所周知的定论。
辜鸿铭为何非要逆潮流?在我所见的回忆文章中,辜在北大的同事温源宁的论断可谓泼辣。
温源宁说,辜鸿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与众不同的只在于,他是个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儒家思想、他的君主主义,他的辫子,对于他消耗在纯粹的享乐中的生活,只不过是些装饰。他那苍白憔悴的躯体,并不是用脑过度的结果,而是欲望、机谋、耽美色和无节制地追求与众不同的愿望共同的牺牲品。
“一个真实的辜鸿铭,和我们现今每天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辜鸿铭之古怪只在于他是个天生的叛逆。他脾气倔犟,他以对立为生。大众接受的,他拒绝。大众喜欢的,他厌恶。大众崇拜的,他鄙视。与众不同是他的乐趣和骄傲。因为剪掉辫子成了时尚,所以他偏要保留。如果别人全都留着辫子,他就会成为剪辫子的第一人。关于他的君主主义,情况也完全一样。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由于他希望成为例外。共和主义成了风靡一时的东西,因此,他就痛恨共和体制。他夸耀君主主义,就像花花公子夸耀他的领带。其实,从才智和精神方面称辜鸿铭为花花公子,倒也未必就不准确。就像花花公子夜以继日把时间花费在穿着打扮上,辜鸿铭则是为了与众不同而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殚精竭虑。”
按温源宁的意思,辜鸿铭专以作秀为荣,毫无原则可言。
但据同样是辜鸿铭的同事胡适的回忆,辜并非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辜鸿铭曾亲口给胡适讲过一个故事:袁世凯时代,安福系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选票。一位姓陈的人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但“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
胡适当初提倡文学革命时,辜鸿铭曾撰文反对,文中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胡适对辜鸿铭的回忆自然不会有什么溢美之词,所以我宁愿相信胡适的意见——辜鸿铭不是为作秀而作秀。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给辜鸿铭当了20多年上司的张之洞曾评价他的这个下属“知经而不知权”。所谓“知经”,就是过于教条主义;所谓“不知权”,就是不晓得与时俱进。这样的人,要说他没有原则,实在说不过去。
我读过两卷本的《辜鸿铭文集》。老实说,我没觉得他思想上有多深刻。不过,我几乎可以在他每一页中都读出两个字——自尊。
最典型地体现了辜鸿铭自尊心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拜访他的故事。在毛姆事后写的访问记中,辜鸿铭对一个远道而来的访客表现出的倨傲让人吃惊。
因为在拜访辜鸿铭前毛姆在礼数上有些不周,所以见面后毛姆就对辜说了很多恭维的话。即便如此,辜鸿铭并不想原谅毛姆。“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学博士,”他说,“那儿以后我又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是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虽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语调来发表这些评论的,但是很明显,一点点不同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不悦。
“可是我们也有过对人类社会思想界多少产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呀。”毛姆说。
“你是说休谟和柏克莱?可是我在牛津的时侯,那里的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如果他们思考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的话,他们宁愿放弃。”
“您研究过当代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吗?”毛姆问道。
“你是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辜鸿铭的评论很是尖酸刻薄。
“我发表过二十本著作,”辜鸿铭说,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地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可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辜鸿铭愤愤地说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辜一边用手捋着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当毛姆起身准备告辞的时侯,辜鸿铭却没有要他走的意思。最后他不得不向他告辞,这时,辜鸿铭决定送毛姆一件礼物——一幅辜手书的书法作品,那同时是辜的诗作。
“你写的什么?”毛姆请教道。
辜鸿铭的眼里飘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辜鸿铭回答道,“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毛姆后来找朋友翻译了辜鸿铭送他的诗。搞怪的是,他送他的居然是情诗。
作为一个弱国的国民,辜鸿铭不过是借倨傲来表现自尊心。但倨傲并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反倒徒增人的耻笑罢了。
我为辜鸿铭感到心酸。
突然想到,辜鸿铭不就是孔乙己的升级版吗?
突然想到,当今中国还有不少活着的辜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