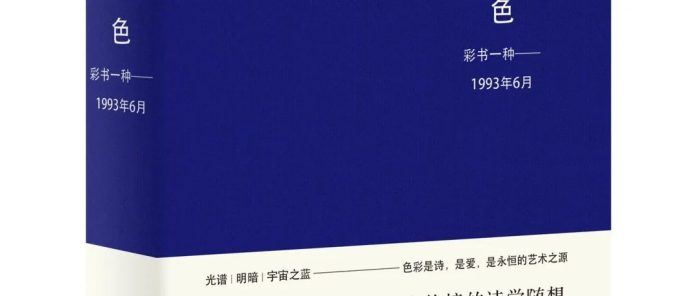读着这本快意与机智并举、博学和戏仿兼擅的书——德里克.贾曼《色:彩书一种》,深感有一段时间没读到过这么反叛的文字了。但这是我所悉知的,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以前既是学着如此写,也常像他一样行,当然没有像他那么玩格:酷儿、同性恋、爱滋病等,并用各样的方式如写作、电影、演讲来彰显这些异举,并使这些异举戴着权利的桂冠,而成为时尚之骄子与英雄。
我得诚实地说,若非江文宇译了这本书,我根本不知贾曼为何许人。但读了他这本书,查阅了一些其它资料,且看了他死前所导演的“反电影”《蓝》——只有一个克莱因蓝的屏幕,其余皆是他及另外的人之旁白,以至该电影在网络上播放,弹幕上有人说像“广播剧”——也读过一些《慢慢微笑》的章节,与他经营花园的照片等,此人在我的阅读序列里竟然立体与鲜活起来,与第一眼看到这名字的完全抽象自有不同。这就是说,阅读也能增加些许位格性的理解,虽然真正的位格来自生命的相交,从至高者那里而来的爱。
他坦承自己有个教名迈克尔,不过他对这个成为他们族群习惯的信仰,虽说并不隐藏,但其轻看调侃却是溢诸纸墨,并将罪包装与彰显得特立独行,却让那能拯救人生命的十字架,觉得使人厌弃。如在《白色谎言》一章里,作者说:“从中可见,众神皆白;而圣约翰发明了基督教的天堂,身着白衣的天国万军敬拜那只羔羊,于此之前数个世纪,希腊人和罗马人则在庆祝萨图恩节——12月17日,忧郁的萨图恩,像奥西里斯和后来的基督一样,是一位白神,白中受敬拜,……”(德里克.贾曼《色:彩书一种》P24,江文宇译,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下引本书只注页码)。在此译者用了个很节制的注释来加以评说:“《启示录》中多次描写天堂万军敬拜羔羊,远多过《圣经》其它部分,原文逻辑可能因此称约翰‘发明’了天堂,但这一种十分罕见的说法”(P39)。这只是贾曼自己的信仰坍塌,完全只成为其知识与生活背景的必然。
一:博学戏仿的多面手
这个世界有的人饿死,有的人撑死;有的人为生存而战,有的人则生活无忧,却用特立独行的办法来为自己“找死”——人人必有一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这死并非终局,是否终极沉沦是有选择的——贾曼大约可以说属于后者。我无意唐突贾曼及其喜爱者,因为特立独行成了这个世代很多人高蹈与标举自己,且以自己为神的“独门绝技”。我为何如此说呢?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无论是成就还是作派,都比贾曼差得远,但骨子里面的价值观却是相同的。以我的血性与罪身来讲,我天然喜欢贾曼这些做派,巴不得踵武其后,但幸好我得到他弃之如敝屐的信仰。换言之,按我取死的身体的本相,常常都在发生各种起义,不!没有什么义可起,而是罪在我身体与灵魂里叛乱。
但即便如此,我也要说贾曼的《色:彩书一种》,实在是我读到的关于色彩之随笔小品里,截至目前为止最好的一种。他喜好色彩,其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作为画家的经历,无疑使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敏锐及专业积淀。对颜色作物理、化学乃各种光谱合成与分析之研究,自然也是件好玩的事,不过不属于贾曼认知色彩的方式。他当然没有将世间所有的色彩都谈论一遍,因为他这书并非色彩大全。但他论色彩,也的确是极尽上下古今之能事,举凡与颜色有关的物事,都用诸种稀奇古怪的人物、事件、用典来新人耳目。他所胪列的多是西方的物事——只是偶尔齿及中国与日本,如中华白瓷、皇帝的黄袍等——因此对他的目标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多慧心能解。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也有不少障碍要去逾越,故译者除了极尽曲折传达其妙外,还要有相当的背景注释工作要做,才能使读者不致坠五里烟海。
贾曼从儿时皇家空军尼森小屋发霉的墙上,涂抹的颜料及其色彩变化,就似乎与各色打上了一辈子的交道。从区域性上来看,他不仅注重色彩,而且注重“色彩之地理”(P6),于是那不勒斯黄、安特卫普蓝等,逐一呈现在他的笔下,好像每座城市不是人流、市政、交通之组合,倒是色彩之炫耀竞丽。不过,他谈色谈光,虽也引莱昂纳多.达芬奇、牛顿、歌德、维特根斯坦的著述——“要知道正是莱昂纳多向着光迈开第一步,紧随其后的是牛顿,一位声名狼藉的单身汉,带来了《光学》。二十世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又写了《评色》。色,看上去天生就有点酷儿有点弯!”(P131)如果你还看不出他的戏仿,我将译者的注释直接端出来,“此处‘天生’与‘弯’在原文是一词(bent)双关;‘弯’指同性恋取向。”(P137)——不过这种外表的理性,其实是为了传达通过炫博而来的戏仿之野心。换言之,他通过掉书袋,来完成对掉书袋的戏仿与解构,这是一种别致的随笔写作格局与气派。
如谈白色,其标题为“白色谎言”,此白色自非全系物理意义上的白色。这种做法贯穿到他所谈的关于色之诸领域,即他所谈的颜色,固然关乎绘画及相关诸色本身,但更多是社会学、民俗学乃至风俗史的色彩联袂展览。除了前面所引的所谓“白神”之说外,他还说“太初有白”,“白往回延伸。白是在大爆炸中被创造出来的吗?那爆炸本身是白的吗?”(P22)这里面的戏仿既有对《圣经》语式的戏仿,亦有对大爆炸宇宙理论的仿作,不特如此,还是对建筑师柯布西耶建筑阳台之乳白、作家吉卜林的“白人负担论”、诗人金斯堡的《白裹尸布》、同性恋的“酷儿白”等的持续推演。接下来他紧跟着说:“现在只有蠢人或很有钱的人才穿白,穿白你就无法混入人群,白是孤独的色彩。它排斥那未洗净的,有一种偏执的特质,我们这是在拒斥着什么?洗白,是要下苦功的。”(P33)你一看这就不是画家在谈论白,而是社会批评家用历史与现实的眼光,在打量白色如何在各色人等及生活中的使用,以及如何被人们议论。
有创意的形式,在贾曼的书里也不时闪现,其对颜色的处理甚至与文章的结构有关,算是出人意表之举。贾曼自己就擅长园艺——“我儿时对花卉的热情,被他(指父亲——引注)认为是娘娘腔”(P30)——是可以在邓杰内斯核电站旁边建一座美妙花园的人,因之写绿这一章就以《绿手指》名题。尤为称奇的是,他在书中数处使用英国童谣,可见其对童谣有特别的喜好,而这次他用英国传统儿歌《十只绿瓶子》,来架起这篇文章的写作结构,直到最后“那就没有绿瓶子挂在墙上面”。从十只到最后一只,“每只绿瓶子”所谈的关于绿颜色的事物,既有差异也有关联。如写第七只绿瓶子时,他说到自己最初的记忆就是关于绿色的记忆,四岁时父母就知道他迷失于绿,但“我的手指是何时变了绿?”从而回忆起他那些阅读与游历的细节,说到一颗南瓜的大叶子让其入迷,仿佛好莱坞大片里埃及法老的扇子,“电影业延生于好莱坞——这也是一片绿林”(P147—148)。稍懂英文的都知道好莱坞的英文字面意义为“冬青林”,这便他玩文字游戏的又一例。
前面说过他模仿《约翰福音》首句之“太初有道”,来一句“太初有白”。其实作者在此书中有多处戏仿《圣经》,不劳遍举,再举一例以概其余。他提及描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锦葵紫旬”:“紫踏步前进,堇腼腆退缩。/粉生锦葵紫生紫生堇……”(P289),译者注时说:“此处措辞戏仿《圣经》家谱写法,比如《马太福音》第1章第2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P299)。戏仿不可怕,戏仿背后只把圣经当成知识背景,而不当成翻转生命的绝对真理,那种未曾被对付过的自傲之心,才是我们的问题之所在。
二:重新命名的译者
贾曼的笔触佻达机智,不无炫博戏仿之笔,其行文跳跃腾挪,常有诗意在其间流荡,不要说跟论文相比,就是与一般议事衡人的文章相较,亦让人不易理出其间的头绪。幸好遇到一个尊重他的创作,却也极认真对待翻译的译者。怎么判定译笔是否认真呢?当然最好是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很在行,再来评骘,比较恰当。我英文的理解力相当有限,远说不上在行,固不能评说作为源语言的贾曼原作。且就译作本身,结合译者详细准确的章末注,借他人之框架来做一番言说。
对《色:彩书一种》的汉译,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有出于提携后进之用心的好评:“周正考究、知所分寸、体贴原著——居然带着不可觉察的诗意——这就是江文宇的译笔。眼下他所翻译的《色》,为贾曼所写,一个颓唐而深谙享受的英国人。而我所能看懂的只是中文。以我的谬见,好译者并非看在外语水准,而是字字句句考验汉语。今日的汉语早已不妙,是故这位八零后新晋译者的文本,足堪惊喜。”
我不认为译者真的完全达到了这样的水准,但我认同陈丹青先生所说的外语译成汉语的看法,对译者来说“字字句句考验汉语”。我认为好的译笔,不特深入源语言的能力强,且目标语言尤其考验译者的水准。尤其目标语言是自己的母语,更是考验一个译者在对源语言的把握之下,对自己母语的敏锐,以及默然会心的能力。我有一个偏见,一个人的母语不行,却吹嘘其外语能力,我总是感到有个大大的问号要审判他。为了说明实际情形,我顺着陈丹青所言之“周正考究、知所分寸、体贴原作”的诸方面,来做些举例性的说明。
“周正考究”,在我看来,可谓之大方雅正,细究上下文,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使作者的原意犁然自现。首先,我认为译者在选择译笔时,其随文赋形的能力,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周正考究相匹配的用心。什么是随文赋形呢?这就像小说人物之创作,农民的声口与知识分子的声口肯定迥异,否则不符身份。在贾曼所引中世纪拜占廷时期一位哲人兼炼金术士摩利埃努斯《瑰园》,其中关于“灰”的诗句时,他译为“勿轻死灰,盖其乃为汝心之权冠也,恒忍万物之烬也。”(P116)在译柏拉图主义者、天主教神父费奇诺为洛伦佐所写的诗时,亦用文言:“吾侪奉献苍青以祀朱庇特/青金石曾得蒙此色/盖其朱庇特之权能可御/萨图恩之黑胆液故”(P240)。这些都是匹配人物与事件的恰当做法,类此尚有佚名之《古英语诗歌》(P118)与布莱克的《绿有回声》(P158),以及《黑艺》一章之眉题“呜呼冥冥吾魂”(P307)。这与贾曼本人所用的一些粗鄙之语言,译者之翻译大为不同,这都是为匹配人物与上下文原意所做的特定“赋形”。
周正与考究,常常是联在一起的。关于此书翻译中的“考究”之处,可举之例不少,只举一个“罐木灰”,便可明了其间的考究与认真。我一看到“罐木灰”,第一直感就是出现了错别字,是否应为“灌木灰”。后又觉得似无“灌木灰”一说,疑是否为“草木灰”之误,急翻译者的注释,其注释如次:“罐木灰(potash):一般译作‘草木灰’,其主要化学成分是钾碱(碳酸钾)。该词英文直译自荷兰文‘potash’,字面意思都是‘罐灰’,因该物最早是靠在罐中焚烧木材获得;后由此名衍生了化学元素‘钾’(potassium)。原文该词与下文‘陶罐’(pot)呼应。”(P123)此种小考证,方能对游戏且炫博的贾曼笔触,有更深的领会,同时我们也获得了一些在知识脉络上的融会贯通。
这样的考究,涉及到翻译的准确性,甚至出现重新命名的情形。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把动物交给亚当,“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2:19)。人命名的能力包括一切创造力,都是上帝所赐的。那么译者将源语言的名物,用什么样的名称进入目标语言,就本书来说,从英语到汉语的转换,不是简单的语言变化问题,而是一种“文化命名事件”。比如关于天青、群青的译名,以及将violet误译为紫罗兰的问题,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小事。其实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涉及到名实问题,也涉及传达的准确与否,更涉及到“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中文“紫罗兰”的历史,已有人说是从明代《草木花诗谱》中的“紫罗襴”演变而来,后经于日本的引用,又从日本返回中国,但这里面的传播链条,以我目前所读到的文献而论,却并不明晰。但将violet误译为紫罗兰的人,却是像贾曼一样的文艺多面手,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绿手指”一样的莳花高手,晚年出有花卉散文集《莳花志》的周瘦鹃。他年未弱完时遇着自己心仪的女友周吟萍,却因人力原因交臂失之,其英文名为violet,而周瘦鹃便以“紫罗兰”名之。同时大办特办《紫罗兰》刊物,写与紫罗兰有关的诗歌,终使这个误译习非成是到人之不觉。
而文宇在译文之注释里,对violet做了一个重新命名的小考证:“锰堇(manganese violet):俗译‘锰紫’。现代汉语一般将‘堇’(violet)误译作‘紫罗兰’,并进一步将之与‘紫’(purple)混淆;俗以‘紫’为上义词涵盖堇、紫、锦葵紫等各种不同概念。本书原文有大篇幅明确区分这几种不同色彩及其多种相关表达,故本书所有‘violet’及相关词汇,全部严格以‘堇’译,如传统所谓‘紫外(线)’(ultraviolet)在本书译作‘堇外(线)’。”(P13—14)像这样的重新命名,尚有关于蔷薇与月季之别的注释及其考证(p17—18),可以说能给读者较多的求知乐趣。
所谓重新命名,并不表明译者顺着自己的性子胡来,而是严谨求真之必要,以我的知识储备而论,认为译者是在竭力做到此点。不特如此,译者既体贴译者,亦体贴读者,举两个注释以概其余。一方面译者纠正作者的误写误用。如贾曼在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诗作时,误将整理的学者查尔斯.卡恩(Charles H.Kahn)写作可汗(Khan),译者纠正之并给出其引用之诗作更准确的出处。另外译者体贴读者,举一例即可见一斑。关于贾曼“我骑着我的驴”,熟知圣经的人,当然可以想到耶稣基督之骑驴进圣城,但下面这样的注释,却对读者了解贾曼跳跃隐藏的文意有很好的帮助:“驴(donkey):俗称‘驴凳’,指一种前端有挡板的小凳,其挡板处可以支起画架,整体外形似驴。此处措辞及上下文或有暗指耶稣基督君王之姿却谦卑骑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参《圣经.马可福音》第11章。”(P16—17)
译者的译笔极其用心,注释也相当给力。就像我前面所强调的一样,若你在网络上看贾曼《蓝》,对照着这本书里写蓝的那一部分来看,照着译者仔细有分寸的注释,必定更能明白贾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在表达些什么。但万事不会完美,以我的能力,看出译者有两三处可商。首先关于“一展伟大红旗在招扬”(P80)。量词在汉语表达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外国人固不容易学,就是中国人用起来也常会滋误,此处应为“一面”。二是“耗资极盛”(P102)亦无如“耗资极大”、“耗资极多”,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与语感。三是在谈日本俳句诗人与谢芜村的诗作,兼及英译与日语的不同时,译者说“与日本原诗稍有迥异处”(P271),迥异乃极有不同处,与稍有恰好意义相反,要么是稍有不同处,要么是颇有迥异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
三:用忧伤与怜悯去看见
一般人读了贾曼这书,肯定会得到比较嗨的快感,因为他不仅写得酷,而且他的行为诸方面也出格得让人酷(哭)。在书中他常常不惮强调乖僻的诸种爱好,而且粗言糙语,不时涌现。表面上看,这完全是人的表达自由,这一点哪怕在专制的世界里,也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谁能反对言论自由呢?但我们总要思想如此说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写作本身的目的,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索一样。
希翼得人的点赞,在信息洪流淹没的世代脱颖而出,难免异举以鸣高,惊视而回听,并且视出人头地或者名垂青史为重要之事。这种重要性,在很多人看来,重于自己的生命,更重于自己的得救——悲哀的是有不少还不知道自己需要拯救——有许多人为现世名或身后名,不停的奋斗、努力,切望用此与永恒相连,不知这是那早已注定的虚空。与那些福音从未到过或者说浇灌得浅的地方之人相比,欧美的“贾曼们”有一种更深的悲剧性在里面,他们的先辈及他们如今,得神恩是何其浩大,但他们却轻看而远离。他们并不明白离了神,欧美算不了什么的道理。
要读懂贾曼的书,必须要有比较深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背景,才能明白,好在译者于这方面给作者与读者,都作了极好的补充与桥梁作用。下面这段话,写得不错,也极能表达出贾曼在知识上对他所在族群的信仰是了解的,但他并不相信。在论及红这种颜色时,贾曼写道:“红海是治愈的海,穿越它会带来一个转变、一次洗礼。出埃及的过程其实是逃离罪的过程。那些对罪没有意识的人,红海带给他们死亡;但那些达至彼岸的人,就在荒漠里重生。”(P72)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对神的顺服造就人。否则你就极难明白,同样一个人,为何有下面这样的言语:
“至于那绿康乃馨,哈夫洛克.霭理士曾说确信,酷儿们偏爱绿胜过其他任何色彩。他们曾否偷偷套上女孩子们脱下的翡翠洋装?找个满脑子鸡巴的小伙子,递给他一张色卡,看他选哪个颜色……普里阿普斯就选了根绿的。为何所有戏剧演员的休息室都叫‘绿室’?而且你们知道吗,耶稣曾着迷于约翰,而约翰则是绿色福音宣教士。或许有个简单的答案:有太多年轻人盯着那些曾让希腊人沉迷的裸体绣绿铜像看,盯了太久。”(P152)
基督教并不是禁欲的宗教,是希望你的欲望有正确表达亦即分别为圣的宗教,因为圣经的话语已经启示出要我们如何行。可是悖逆的人偏行己路,即便他们的先辈乃至同辈人中都曾有不少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其后代或同代人中亦有很多人拜偶像,《列王记》与《历代志》早有许多的前车之鉴,但后车之覆却似乎不可遏止,滚滚而来。贾曼这段话里对耶稣与约翰的亵渎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他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历史,亦没有任何传统及文化根据可言。译者在此得体地指出:“此句关于耶稣与约翰的表达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说法,在英语文化中亦无任何根据可查。”(P165)
这个世代的人,哪怕是肉体很自由很饱足的英美人,都需要救恩,更需要我们从神而来的怜悯。或许你会说,你一个活在专制下肉体很不自由的人,却来怜悯那些自由且生活无忧的人,不是你的阿Q病发作了,就是你得了很深的精神病。我要说,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之所在,福音可以使贫穷的变得富足。贾曼说自己写这本书时,已经时日无多,“若有什么是你视为珍贵,却被我忽视的——你自己写在页边吧。”(P82)下面这段话,就是我写在他这本书页边的,权作本文的结束。
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说:何必为人生的片断哭泣,我们整个生命都催人泪下。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好,很切近现实,但还不够入骨。入骨的说法是,若是没有永生,世上没有比命更薄的东西。因为那至高的审判者告诉我们,若不在永生里,一切都是虚空。
2021年12月21至22日于成都,同日改定。
德里克.贾曼《色:彩书一种》,江文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想参加12月26日下午在成都东玉龙街屋顶上的樱园译者签售活动,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