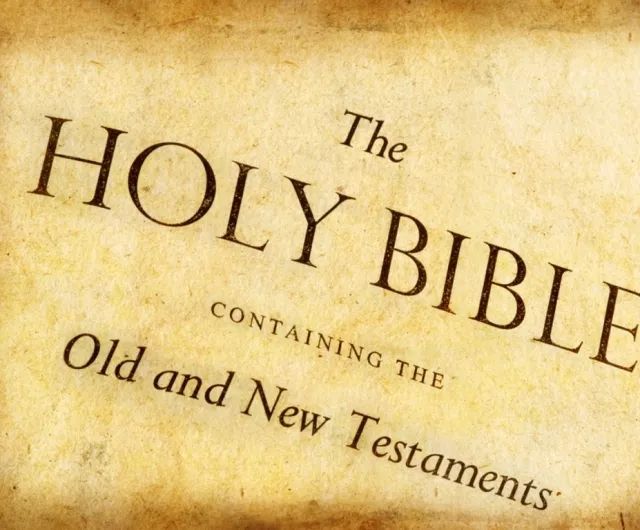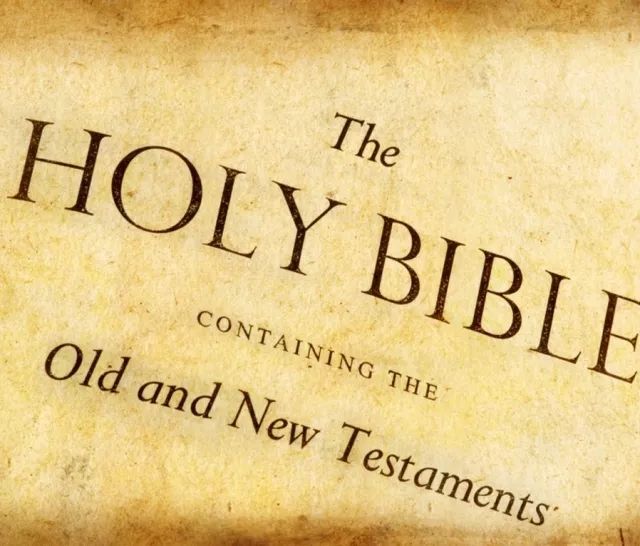编
者
按
《人写的书怎么会是神的话?》一文原发表于《基督教学术》2014年第11辑(总第44辑)第78-95页,推送时已获作者授权。本文意在尝试对“圣经作为人写的书何以成为神的话”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首先回溯圣经正典形成的历史,指出为耶稣做见证使得形形色色的圣经书卷获得共同的衡量标准和统一性。借用巴特对该问题的思考,作者描绘了圣经——透过人对神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的见证——成为神的话的动态图景。同时,作者认为,巴特忽略了神在道成肉身这一特别启示事件之后的作为,从而提出,“教会实践的历史对人的传承的检验其实也是一种神的拣选。”但是,就巴特对神主权行为的坚持强调而言,说巴特有这样的忽略,是有待商榷的。也许,作者在此文中想要强调的,并非神在道成肉身启示事件之后的作为,而是由于这一行为,教会及其实践的历史、以及圣经所获得的特殊地位,而这特殊地位也可理解为神在启示事件之后的不断作为的体现。
人写的书怎么会是神的话
卡尔•巴特圣经理论的应用和再思
[内容摘要] 圣经上的话作为人说的话是经不起历史研究和科学的检测的,但是基督徒却要宣称圣经上的话是神的话。在启蒙运动后的今天,这种宣称是否能继续成立?本文将通过回顾基督教圣经的成书过程来探讨其性质,并运用巴特圣经理论来回应现代理性对圣经权威性的挑战,最后指出巴特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圣经的正典化 圣经的权威性 巴特的圣经理论 神的话
自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信仰便受到各方面的挑战。 挑战之一便是对其经典可信度的质疑:基督徒们如何能说这本书,或这一辑人写的书,是神的话呢? 这一挑战促使许多正经八百的基督徒投身对圣经文本真实性的科学的、历史的考察中。 其中某些人由于急于为自己所委身的宗教辩护,声称为圣经中所记载的内容找到了蛛丝马迹的历史证据。 且不说这一类言论不免导致的圣经主义——将受历史局限的人所纂写的文字绝对化——和基要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事实上,考古和历史研究常常告诉我们,那一类言论,即使是正确的,也远不能证明基督教经典字面信息的可信性:圣经中所载常常并不完全与历史相符;那里面的信息也非绝无仅有——类似内容在同时代别的非犹太-基督教宗教文化群体的典籍中也能看到;而当我们深入研究圣经本身的文本时,又会发现不同的篇章常常会包含不同的对神的理解,不同的神学上的看法 … 基于所有这一切,基督徒们还怎么能说他们的经典是神的话呢?
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在此过程中,本文将首先追溯基督教圣经正典化的历史,并且通过回顾这一经典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它的性质。 由于本文的主要目标不是进行历史的考察,而这一部分又只是为了接下来的神学思考打基础,在此将主要借用李•马丁•麦克唐纳德(Lee Martin McDonald(在《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Biblical Canon)一书中所取得的成果。 在这个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将着手回答这样的一辑书如何能被称作神的话。 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将着重介绍最重要的现代意义上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看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又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基督教圣经的形成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及其经典的历史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建立在书本上的宗教。 根据基督教圣经对其救主耶稣基督一生的记载,他不是像孔夫子那样的学者——他似乎从来不写东西;他也似乎从不打算要制造一部经书——他不像默罕默德那样要求追随者将他认为对的东西记下来;他的信息既简单又直接——“来,跟从我,”因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基督教开始于与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个人接触,信他名的人就成为了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团体,公元一世纪的教会,并没有什么“基督教的”经典——新约,不过,他们还是有犹太文化的传统和典籍,而这些将成为基督教旧约的来源。 然而,对他们来说,具有规范作用的不是,或主要不是,这些犹太的典籍,因为这些文本尚不能被定义为一套确定的正典。 “公元前两个世纪直至公元一世纪的‘犹太教’在关于哪些文本是神圣的这个问题上尚未统一看法。 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关于哪些著作应被视为神圣的,在以色列内外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The 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Biblical Canon,53) 事实上,耶稣自己的话,(无论是使徒所转述的,还是被记录下来的,)对于他最早的犹太群体中的追随者来说才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他们则凭着对这一位被钉死在十字上、却在第三天复活的耶稣的信心来选择他们的犹太经典。 而正是出于对这些耶稣信奉者的这一行为的回应,犹太群体中不相信耶稣的人开始着手将某些特定的犹太文本作为他们标准的经书。(Formation,62)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对犹太经书进行犹太教正典化的过程中,关于弥赛亚的文字被大大削减。(Formation,61)
在最早的教会中,由使徒、先知和教师传承下来的耶稣基督自己的言行较之犹太的传统有更高的权威性。(Formation,71,74-76) 这种传承主要是通过口头的形式进行的,虽然有些犹太典籍很早(约公元35至65年)就已成书。 的确,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写在纸上的东西远不如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对耶稣的活的见证那么可靠和有感染力。 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之交小亚细亚希尔拉坡利斯(Hierapolis)的主教派皮阿斯(Papias)就说:“我不指望书本上的信息能像一个活着的人亲口说的话那样能给予我帮助。”(Formation,71)
但是,从二世纪中叶开始,被写成了文字的典籍,由于较之口传信息有着相对确定的形式,开始在基督教群体中获得主导地位。(Formation,72) 这也很自然,因为口头的传承依赖于人的记忆,而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变得模糊,最早和耶稣有个人接触的那些人(使徒)相继去世,而救主并没有照他们预期的时间再来。随着教会的扩大,成文的教导较之口头的信息当然能得到更有效而稳定的传播。 而这一时期异端的出现,更是促使教会寻求更为精确和确实的信息传递方式来将其各群体的教导和实践维护在正统的范围之内。(Formation,73-74)
随着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等记载耶稣生平和教导的文献的出现,其中某些书卷在教会的实践中赢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权威性(虽然还不能说就是正典),也更多地在团契生活中被引用。 在这里,著名的圣经历史学家汉斯•冯•堪朋豪森(Hans von Campenhausen)特别指出,仍旧是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而不是成本的福音书或使徒的书信在教会中有着相当于经典的地位。(Formation,76) 他的这一看法可为坡利卡普(Polycarp)写给腓利比教会的一封颇具影响力的信所证实:“那么,‘让我们,(像他自己所要求地那样,像使徒和先知那样)带着敬畏满怀崇敬地服侍他’——是使徒将福音带给了我们,是先知预言了我们主的再来。”(Formation,80)截至200年,在教会广泛认可的堪为经典的基督教文集中,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但是,“耶稣本人的权威仍然是二世纪末教会中最重要的权威,虽然那时候遗留下来的他的教导大都只在成文的福音书里找得到。”(Formation,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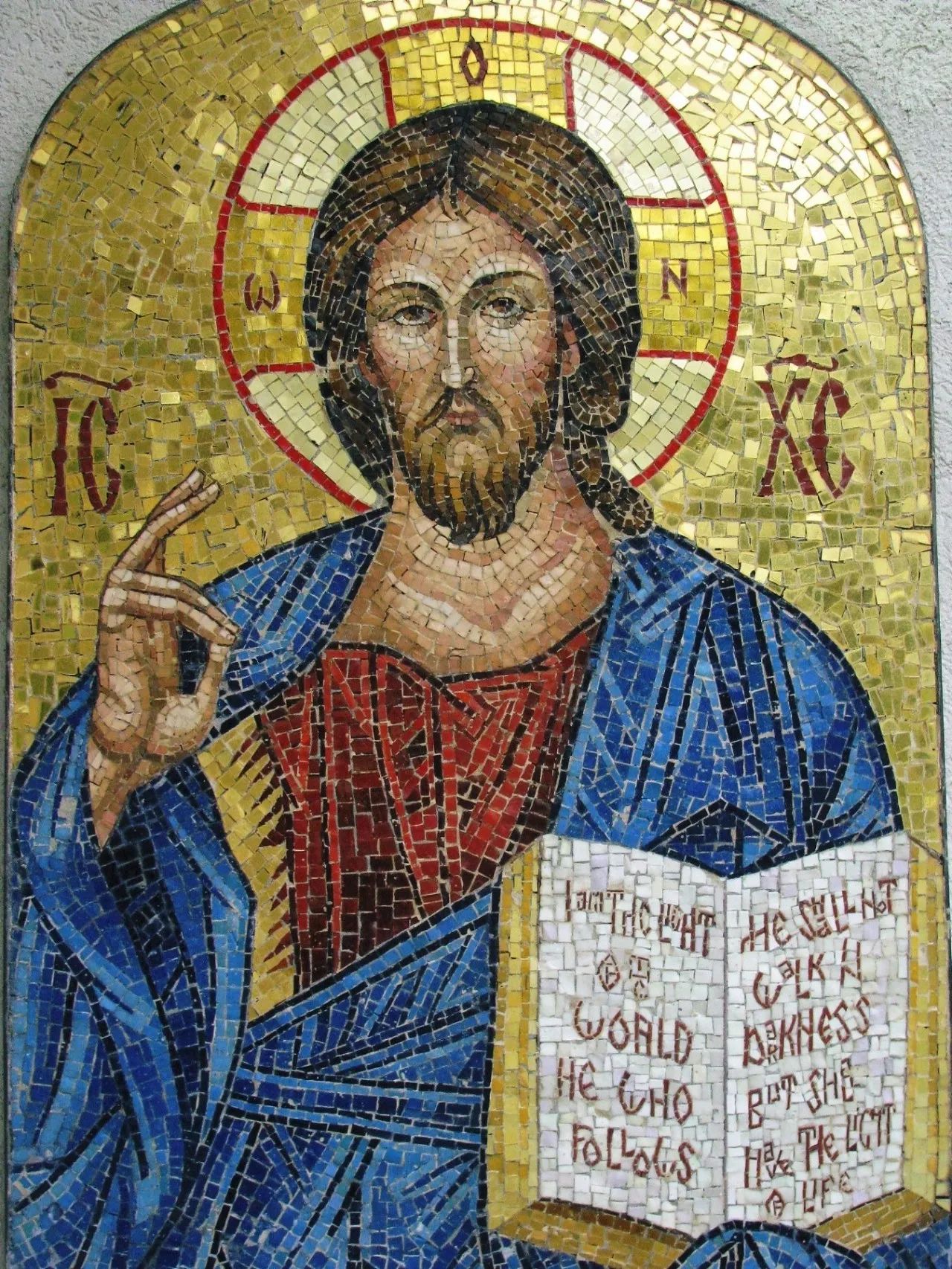
基督教史学界通常认为,艾瑞纽斯(Irenaeus)(著述于170至180年)标志着“从早期的对传统的信赖…到新时期有意识地将正典标准化的过渡。”(Formation,92-93) 他是列出基督教“正典”之第一人。 但是,由于艾瑞纽斯的初衷主要是批驳灵智派异端进而维护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确立一套固定的文集,他的所谓“正典”不是一份经典的书单,而是对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陈述:
教会虽然散布全世界,甚至达到地极,却从使徒和他们的门徒那里领受了[统一的]信仰:它相信独一的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主;它相信一位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拯救我们成为肉身;它相信圣灵—-他借着先知宣告神的性情、主的到来、由童贞女所生、主的受难、从死里复活,以及神的儿子在蒙爱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里升天。 他也借着先知宣告他将在父的荣耀里从天上显现,“将万物聚集为一”,并且使全人类的肉身得到全新的复活…(转引自Formation,93)
艾瑞纽斯为他的“信仰正典”的正统性辩护、以及驳斥灵智派所谓继承密传真道的说法的依据是,他的“正典”是从源于使徒、又经由教会主教代代相传的教导所领受的。下面这段话可谓颇具代表性:
蒙恩的使徒,即已奠定和建立了教会,就将主教的职位授予利奴手中。 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信中曾提到利奴。 阿耐克里特斯(Anacletus)接替了他;[后来,]主教职位又派给了克莱蒙特。 克莱蒙特由于曾跟随过蒙恩的使徒们,跟他们很熟,可以说使徒们的讲道仍然在他耳中回荡,而他们的传统对他来说也历历在目。 … 厄瓦里斯图斯(Evaristus)又接替了这个克莱蒙特,而他自己又被希克斯图斯(Sixtus)接替,这是从使徒传下来的第六代。 阿尼色图斯(Anicetus)由叟特尔(Soter)和厄娄特里尔斯(Eleutherius)接替,后者是从使徒传下来的第十二代,现在正执掌着主教的职位和传承。 始于使徒的教会传统和对真道的宣讲正是按照这样的秩序通过这样的传承临到我们的。 这充分证明,从使徒时代至今只有一个赐人新生的信被保留在教会中并且作为真理被传下来。(转引自Formation,95)
艾瑞纽斯相信,“倘若使徒们真知道什么隐藏的奥秘,是他们惯于密授给‘完全者’而不叫别的人知道的,他们应该会特意把它们传给他们授予领导教会权柄的那些人。”(Formation, 106)艾瑞纽斯拒斥灵智派异端对希伯来圣经的抛弃,从而首先造出“旧约”和“新约”的字眼,坚持说两者对基督教信仰都有规范性并且明确称他们为“经典。”(Formation,94,96)虽然今天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艾瑞纽斯的正典源于使徒,许多人仍然认为,它大体上反映了教会中长期接受的信条。(Formation,99)而且,艾瑞纽斯所列的新约圣经得到当时大部分教会的认可,虽然直到四世纪晚期才有大公会议决定新约所涵盖的文本。 当时地方教会各自决定所采用的经典,约定俗成的看法逐渐形成。 毫无疑问,那些最能满足教会需要的典籍渐渐具有了权威性。(Formation,99,100)
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进行了对基督徒最后一轮全国范围的逼迫。 这次逼迫的特点是,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交出他们的圣经以被烧掉。(Formation,106-107)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基督徒选择交出非正典的文本,仅仅为了应付掌权者的命令。而对我们来说,这也提示了他们对哪卷书是正典、哪卷不是已经心里有数;只是在众教会中尚没有统一看法。(Formation,110)
直到313年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基督徒才得以自由地敬拜他们的神。 和其他的罗马皇帝一样,君士坦丁高度重视帝国中的统一和“和谐”(整齐划一)。 在皈依基督教后,他便将解决由异端所带来的教会争端视为己任。 可以理解的是,这位罗马皇帝青睐主流教会所持守的信条、并且希望所有其他教会都来遵循。 他叫尤西比斯监督制作五十本圣经(应该包括旧约和新约)以供新都君士坦丁堡使用。(Formation,114) 所以,至少肩负这一重任的尤西比斯应该对这套典籍该包含哪些书卷有所关注。 说到底,直到四世纪末,今天新约所包含二十七卷书中的大部分才得到普遍认同。 但是,即使到那时,也没有教会全体将我们的新约的所有二十七卷书采纳为正典,甚至还有教会使用这二十七卷以外的书卷。
罗马天主教会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通过1546年天特会议确立其圣经的“全部”:
本次大会接受的书卷…如下:旧约,摩西五经,即,创世纪、出谷纪、肋未纪、户籍纪、申命纪、若苏厄书、民长纪、卢尔德传、列王纪四书、两部编年纪、第一和第二厄斯德拉—-第二部又叫尼西米记、多俾亚传、友弟德传、艾斯德尔传、约伯传、达味150篇的圣咏集、箴言、训道篇、雅歌、智慧篇、德训篇、依撒依亚、耶肋米来、以及巴路克、厄则克耳、达尼尔,十二小先知书,即,欧瑟亚、岳厄尔、亚毛斯、亚北底亚、约纳、米该亚、纳鸿、哈巴谷、索福尼亚、哈盖、匝加利亚、马拉基亚;两部玛加伯书,上和下。 新约,四福音书,依据玛窦、马尔谷、路加、若望;由传道人路加所写的宗徒大事录;宗徒保罗的十四封书信,致罗马人的、两封致格林多人的、致迦拉达人的、致厄弗所人的、致斐理伯人的、致哥罗森人的、两封致得撒罗尼人的、两封致弟荗午的、致弟铎的、致费肋孟的、致希伯来人的;宗徒伯多禄的两封书信、宗徒若望的三封书信、宗徒雅各伯的书信、一封宗徒犹达的书信、宗徒若望的默示录。【John H. Leith, ed., Creeds of the Churches: A Reader in Christian Doctrine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3rd ed.,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1982), 402-403. (书卷名称采用思高本译法。)】
显然,这个书单里好几卷旧约书卷在今天新教通用的圣经中都找不到。 其实,新教之父路德甚至还怀疑雅各书、希伯来书、犹大书和启示录这些新约书卷的正统性;而希腊东正教会的旧约书单比罗马天主教的还要长。
这一对基督教正典形成历史的回顾让我们看到,正如巴特所说的,圣经“只是非常相对地”定型了(Church Dogmatics【下面都简写为CD】,I/2,476)。 如此看来,在探究这套书卷的神性,即,它是不是神的话,之前,恐怕我们不得不先质疑它的统一性:像这样一些松散地绑在一起的书卷怎么能被当作一个整体呢? 就算我们承认其中每一卷书的神圣性,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讲的是同一位神呢? 有些旧约圣经学者不就抱怨说,何必一定要在希伯来圣经中寻找耶稣呢?
我们的问题由回顾圣经正典化的历史而产生,而答案也隐藏在这段历史中。 回头再看看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教会本身的产生,就是源于在犹太文化背景下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复活的信息所带来的力量;她随着这一强有力信息的传递而增长,并且通过对这一信息的理解和宣讲不断精确化而逐渐明确自己的身份。 在这一过程中对这一信息的书面记录开始沉淀并成形。 从一开始,为这一信息定规的就是耶稣本人的生命和教导。 由此,形形色色的圣经书卷获得了共同的衡量标准和统一性:所有这些书卷都是为一个人和一件事做见证——有的为这个人的到来和言行提供社会和文化的背景,有的叙述了这个人在地上的一生以及他的死和复活,有的回顾了他的教导,有的宣讲他的再来;虽然这些见证的内容不同,但所见证的对象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

正如我们前面简短历史回顾所指出的,对于最早的那些生活在犹太文化背景下的基督徒来说,是耶稣的信息赋予了他们的犹太传统以意义,而他们和耶稣所共处的这一传统又使得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耶稣的信息。 基督徒不能否认其他人有权对律法和先知书做出别的阐释,但是,是这个关于耶稣的主题使得它们成为基督教正典中的文献。 质疑对希伯来圣经的基督化阐释其实是质疑耶稣这个人的可信性。 由于在某种意义上是耶稣这个人的“真实性”赋予这个传统以意义而促成了“旧约”的成型,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个人出现之前的希伯来圣经来验证这个人的自我宣称的合法性。
二、这样一套书怎么可能是神的话

那么,这些七嘴八舌的人的见证,就算是指向同一位神,怎么会是神的话呢? 就圣经是人的话而言,它不可能是完全无误的。 巴特对这一点直言不讳:“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见证人,跟我们一样是会犯错也不时犯错的人。”(CD,I/2,507)他甚至说,作为一部由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著述和编纂起来的典籍,圣经本身不可以是神的话。 但是,由于它收集了关于神过去对人的启示的记忆,收集了神过去对人说的话,它应该引导我们期待类似事件在将来还会发生;当神使用那些人的话、并借着它们说话时,过去的人对神的话的陈述就可以成为神的话。 怎能如此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须先了解巴特的“神的话”的概念。
为了使圣经之为神的话成为可能,巴特首先指出,我们断不能把神的话想象成像人的话那样有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形式:“神的话既不能被描述成、也不能被定义成一个东西。”(CD,I/1,136)相反,这话是灵性的(即不是物质的),首要的是,“它”(也许应该是“他”)是神的第二位格,圣子;而这一位圣子又完全地且仅仅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人而同时保留着原有的神性,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CD,I/1, 119) 巴特承认,圣经和教会对基督信息的宣讲是神的话的另外两种形式,但是它们之为如此乃是派生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他们之源于在耶稣基督里成了肉身而被启示出来的活着的神的话的基础之上的。
在耶稣基督里,神向人说话,而神的这一言说是神自己自由的、并且有目的的行为。这样的神的话被巴特诠释为一个事件,启示事件。
没有什么言语仅仅是被说出来、而不说给任何人听的。言语总是针对特定的听众,并且期待他们的聆听和理解。 类似地,神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对特定的人,用特定的方式,说特定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的真义从来不能被我们解释为一般性的笼统的道理,也不可能被我们复制。(CD,I/1,140)圣经的文本相对确定地保留了神过去的启示的内容,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用人的字句遮蔽了神的话,所以,它必须不断地被神自己的活着的话检验。(圣经主义者将人过去对神的话的领受和表述绝对化并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会使人关于神的话的记忆变得干枯,使它无法领受神本来可以不断给予它的新的生命。)
但是,神说话还是为的要人听见。 虑及神说话一贯所具有的目的性,巴特总结出其中的一些共同点,认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特定的言语:
1)因为神说话和人说话不一样,是真实的没有后悔的,“无论神对我们说什么,…都是作为主的话被说出的。”(CD,I/1,141)
2)因为万物都是因着神的话而有的,而人又是照着神的话要成为肉身这一意象造的,所以,无论神对我们说什么,“它都是在造物主和被造物这样的关系之中被说出的。”(CD,I/1,142)
3)由于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被我们破坏,造物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包含着对我们现状的批评,也还有他在批评之外要重建这种原初关系的意愿。 所以无论神对我们说什么,他的话都是一个和解者进行新造的言语。(CD,I/1,142)
4)在神作为我们的和解者的言语里,神应许他自己要来实现和完成那在创世之时就被确立、又在他和解的工作中被更新的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神的话最终是我们救赎者的言语;他将一如既往地做我们的主。(CD,I/1,142-143)
神的言语既然出自我们的主、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和解者和救赎者,它就是为的要创造、维持、和解、以及挽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此,神的言语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神向着我们的作为。而在神的言语和它所带来的果效之间没有间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9)——神的言语就是神的行为。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1:37)当神自己在特定的情境告诉一个特定的人“神与我们同在”时;这个人不再只是他自己——他被神抓住了。(CD,I/1,149-150) 要是一个人根本不知道神的话的能力,他就不能夸口说他知道神的话。
不仅如此,在神的话选择成为人的样式之后,成了肉身的道表明神在他自己神圣的自由里向着人所做的一个决定。 既然神是自由地对人说话,那么他就是作为活生生的一位说话,所以,“离了他自己,”他所说的“就从来不能被认识、也不会是真的”(CD,I/1,137)——神自己是他话语的主;他自己决定他的话要怎么说(CD,I/1,139)。 通过描述神的话的位格性,巴特杜绝了任何人宣称掌握了神的话的企图,也严禁任何人将神的话约简为人的体系——无论是语言的、概念的、社会的还是神学的。
然而,在他自己的话里,神向我们说话——对我们来说,神仍然是个奥秘。 作为对特定情境中的人、通过特别的方式所说的、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免不了采取一种属世的形式;但是,这个形式对于神的话来说本来是不合宜的,所以,在包含着神的话的同时,它也因为它的属世性遮蔽着神的话。 而且,当神的话成了肉身、又住在我们当中时,他是住在一个被罪辖制、又对神充满敌意的地方。 所以,这只能是神自己所行的神迹,也是他自己的奥秘。(CD,I/1,165-174)
当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属世的形式了解到属神的内容时,我们其实无法知道到底这一形式遮蔽了些什么、又遮蔽到什么程度;这样我们就只知道神的话被揭示的一面(而不知道他被遮蔽的那一面)。 也有可能,我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属世的形式里包含的属神的内容,或者我们不再满意于既有的、对它的了解;这时,神的话确实是向着我们被遮蔽了,但是,在这种被遮蔽的状态下我们又确实知道他是不可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神的话原本的特性——一个绝对的奥秘——又被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知”是实在的正面的“知”。 在我们认识神的话的时候,他是被揭示了,却也是被隐藏了;而在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时,他是被隐藏了,却也是被揭示了;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已有的认识而要去追求更认识他,以致我们只能爱上他;而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却也其实是认识他,在我们的不安中我们也当得着安慰和安息,所以我们只能敬拜他。 无论如何,我们只能惊异于这道的奥妙。(CD,I/1,174-181)
而且,当神在他自己的话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时,他不只是要我们得到他的话,他希望我们在信心中接受他的话。 但是,能真正接受神的话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神的启示若要照着它的本意得以实现,神自己就必须是这一事件最后的终极的基础。 “话语的主也是我们聆听的主。”(CD,I/1,182)所以,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无法保证真正听到神的话。 即使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确实听到了,在我们听到的时候,神的话也还是个奥秘,也就是说,他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CD,I/1,181-186)

巴特将神的话等同于神的儿子,又将他诠释为神自由的行为和他自我启示的事件,似乎是完全剥夺了我们任何将基督教圣经说成是神的话的权力。 但是,拆毁了这殿,巴特却让它得以三日内在神的手中被重建起来。 神的话不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属性”。(CD,I/2,513,530) 既已从人用人的字句网罗他的企图中释放出来,真正的神的话便得了自由,可以自由地使人的话为己所用。 基督教圣经不是这一启示事件本身,但是它可以参与到这一事件中来,从而成为它所当成为的,只是不是靠着它自己的能力、乃是在乎行这事的主的欢心。
基督教圣经之所以能有分于这一事件,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一事件的产物、从而已经参与了这一事件。 神已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启示了他自己,而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话。 使徒们参与过耶稣在地上的生命,是他的生死和复活的第一见证人,也就是这一耶稣事件和神的言说的见证人。 他们后来通过口头的面对面交流又把这个活见证传给了在他们之后的信徒。 相对于他们活生生的见证,基督教圣经则是对这一活见证的书面的记载、收集和整理,于是也是对使徒见证的见证,从而也参与到见证耶稣这一道成肉身神的启示事件中去。 既然是见证,它就不是所见证的东西本身;圣经不是活着的神自己的启示本身,它只是一个见证,指向它所见证的;它是人对自己所领受的神的启示的传达,而人的传达本身不是神的话。 但是,作为“渴慕、等待和盼望这一位以马内利、又终于在耶稣基督里看到、听到和摸到它的人的话,圣经宣称、证实和传扬了[这一位以马内利],”这一神的言说;不仅如此,“通过它的宣讲、证实和传扬,它应许它也适用于我们,尤其是我们。”(CD,I/1,108)
在回忆神过去的启示时,圣经应当在我们心中唤起对将来启示的盼望;虽然这样的回忆不能攫取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启示、这样的神的话(就是神自己),虽然前人领受了这一益处不能保证后人也领受——神的话不是一件物品可以一次性地被人领取、然后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并且是直接从神领受,但是神过去给人的恩典应当鼓励我们期待,今天神仍然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确,神的话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对特定的人说的;它出自一位主、一个创造者、和解者、救赎者,而这一位也想要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创造者、和解者和救赎者。既然出自这样一位的口中,这样的神的话带着能力,他将听到他的人抓在自己手中。当神的话借着基督教圣经成为他所当是行他所当行,当我们通过圣经听见这一位主向我们个人说话,当我们因此不再是以前的我们,圣经就成为神的话了。当圣经为神的启示做见证,从自己指向神的话的时候,它就“不再区别于”神的话了,它就成为神的话的合宜的载体,它就是那“临到我们、自行向我们传达、俯就我们”的神的话。(CD,I/2,463)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谈论神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谈论它的力量、它的大能、它的果效,它所带来的改变。”(CD,I/1,152)神的话的能力和果效是对它的真实性的实际证明。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对这种果效的人为模仿,(比如,严格按照圣经的教导进行的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证明。 “神自己的言说在圣经中人的字句中发生,…这完全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这是“神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CD,I/1,109)只有当人的经典安于自己的本分,承认自己只是为神的话做见证的,而不自称与神的话同等或者掌握了神的话,这时它才能够成为神的话。 当圣经允许神的话享有他当有的自由,就卸下了它自己本不能承受的重负,从而也得了自由。
的确,我们要承认,人的话无法捕捉或模仿神的话。 神的话,既然“离了神自己就永远不能被认识也不可能真实,”就不拘于我们的经典:“神自己自由地掌控着圣经的字句。他可以使用它,也可以不使用它;他可以这样用它,也可以那样用它;他也可以使用圣经以外的别的字句”——我们的正典“只是非常相对地”定型了。(CD,I/1,137)神可以通过圣经说话,但是,他也可以通过任何其它他认为有用的东西说话,比如一个人,我们的敌人,甚至,像巴特说的,一条狗。 神的话不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属性”;只有神能决定它是不是神的话。
我们姑且同意这种说法,但对于我们来说,现实的问题是,圣经的重要性何在? 它与其它可能成为神言说的媒介的事物有何不同呢?如果圣经并不具有神性,我们又在何种意义上称它为“圣”经——巴特自己并不拒绝这种说法——呢? 巴特认为,圣经在教会中(并且通过教会在世上)所应当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威性,还是要归结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进行自我启示的事件:“回忆神过去的启示,发现正典,相信先知和使徒的话所带来的应许…从而相信使徒传承的真实存在,这是…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圣经是神的话。”(CD,I/1,109)圣经不是本质地或必然地是神的话,但出于神的欢心,使徒的人的话事实上成为了“神的话的代表。”(同上)。使徒们和我们一样,是有罪的、会犯错的人,而且几乎肯定地,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如我们多。但是,作为神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的第一手见证人,“和所有其他人相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处于一个绝对的永远特别的位置。”(CD,I/1,145)当然,神的话不能、也不应当被弄成笼统的道理,但是作为阅读圣经的人,“我们可以、也应当…研习一些一般的概念性的材料,那些明显地重复…神向这个人或那个人所说的话的材料… 我们显然没有其它方法提醒我们自己或他人记得神的话,”(CD,I/1,140)并且因此盼望它以后再来。 只是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应当总是记住这些材料根本上的“人性”,永远不要将他们与神的话本身的丰富和具体的完全性混淆;我们应当不断地让圣经带领我们超越圣经自己。
当我们阅读对神过去的启示的回忆时,我们期盼神将来的启示,但是,神现在对不对我们说话呢?我们怎么能知道神现在是不是在对我们说话,神的言说的事件是不是正在发生,我们所读的圣经上的人的话是不是正在成为神的话呢?巴特的回答是,很不幸,我们现在不能知道,只能相信。“声称圣经是神的话,这是一种信仰的告白”;“我们不认为它是对我们对于圣经的体验的描述”——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灵魂蒙了多大的光照,我们的心多么被敞开,或者我们的“己”是多么彻底地被破碎;“我们认为它是对神在圣经中的作为的描述——不管我们在这种联系中体验到什么或没有体验到什么”(CD,I/1,110)。因为不管我们的灵魂蒙了多大的光照,它都被光照得不够,不管我们的心多么被敞开,它都被敞开得不够,不管我们的“己”是多么彻底地被破碎,它都被破碎得不够。无限的神在我们有限的领悟力之上;最终,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个奥秘:只有在认识神的话被揭示的在场的同时也知道他之被遮蔽,我们才能算是真正领会了他的在场;但是,神的被遮蔽并不能真正地被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不能对它进行正面的言说,因为一旦对神否定性的领会成为关于神的断然的言说,这种否定性的领会自己就变成了肯定性的命题——我们不仅不能说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无论怎样我们都是在撒谎,在假装知道,大言不惭地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真的只能相信,我们真的只能把自己弃绝给神,让我们被他抓住,然后他就认识(造访)了我们,我们也认识了他;当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时,我们就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而这种同在非我们所能把握,只要我们一企图把握它,它就成为了过去而不真的在了。当我们回忆这种同在时,我们企盼它将来再来;但是,我们不能说它现在不在:因为当我们回忆和企盼时我们在相信着——要不然我们怎么会企盼呢? 而在我们的信心中他就在了——否则我们怎么能信呢?但是,这信非我们所能言说而只能相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是靠着信活着(罗马书1:17)。
三、进一步的思考

通过将基督教经典诠释为人对神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的见证,巴特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圣经如何成为神的话的动态的图景。但是,现在再回头看一看基督教正典形成的历史,我们发现,对圣经形成的人为历史的探究只能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是建立在拿撒勒人耶稣这一事件之上的,而不能立即告诉我们这一耶稣事件是神自我启示的事件——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历史材料至多能告诉我们,在基督教团体里,也就是说,对那些相信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的人来说,这部经书所享有的权威性有着稳固的基础。统观巴特关于圣经如何成为神的话的繁复论述,我们发现,他的整个论证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之上,即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道所成的肉身,是神的话在人世被启示出来,在他里面,神充分又独特地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心意。 但是,这一基督的信息正是现代读者所质疑的圣经主题。如果从一开始使徒们所相信和传讲的拿撒勒人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或神的道所成的肉身,如果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复活只是使徒们的幻觉或编造,巴特,还有我们,怎么能说这一基督教的文献、这一对一个失败的历史人物的人为见证,是神的话,或者可以成为神的话呢? 这里似乎我们非得对圣经经文所提供的信息做一番历史的考察不可了。
我们大概不能指望巴特给我们提供什么历史的证明。我们不能证明,我们只能相信。 许多新教传道人大概都会这样说。这也可能是巴特自己会给我们的回答。如果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凭着狂热的坚持就能把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相信成为确实的真理?就像中国人的俗话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 对于这种唯信主义——究其实是人的自我称义——巴特只会坚决反对:“信仰不能简单地抓着圣经不放,好像它用的力气越大…神的话语就越会来到…”(CD,I/2,512) 那巴特又能给我们什么更好的答复?如果我们坚持寻求关于圣经所见证事件的历史证据,巴特大概要说,我们只能从这一事件的在历史中产生的果效寻找这样的证据:基督教正典形成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它不只是人的历史:
因为神的启示催生了为它做见证的圣经,因为耶稣基督唤来了旧约和新约的存在,因为圣经记录的是对一个特别的呼召和特别的命令的特别的聆听,所以它能够成为正典,它能够一次又一次成为“活的”正典,公示神的启示、呼召和命令,即神向我们说的话。(CD,I/1,115)
对于巴特来说,这一历史是神的话的能力和果效的彰显,或者(如果你想这么看)是对圣经所说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自我启示的真实性的唯一可能见证。这一事件的历史确定性应该激励我们盼望它将来会再发生,但是,只有在它真的发生时,我们才会真的知道,也才会知道它是真的。现在,我们只能祷告。但是,对那些鼓起勇气祷告的人,这一事件已经是真的了,因为若不是他们被这样的见证吸引,若不是他们已经被它的能力抓住——这样的能力超出人所能为只能是从神而来,他们又怎么会想要寻求它呢? 也许,出于人的礼貌和善意,你不会马上拒绝一个传道人的邀请,但是若非你是真的被那从上头来的力量抓到,你的善意无法长久。巴特不会否认,我们有权否认这样的“证据”的有效性、而坚持它完全出于人意。他承认,圣经的字句和读者之间可能永远存在着“偏差”,以致“圣经上所说的对它的读者或听众来说并不显得真实,对他不起什么作用,而他从他那一方也不知道如何能从中获益。”(CD,I/2,468-469)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说“这个读者无法恰当地理解圣经”(同上)——要是一个人不知道神的话的能力和果效,他就不能对它进行论断。巴特对圣经的“神性”的论证面对现代人对它的挑战确实显得有点脆弱;但是,神的能力正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通过解开人的字句对神的话语的束缚,巴特确实带领我们避免了许多与现代文明之间不必要的纠缠,也阻止了基要主义者对圣经进行教条化的归约,使得圣经得以呼吸新鲜的生命:信仰不是接受一些概念性的命题。但是,巴特的诠释是否与圣经正典形成的历史相符呢? 说得直白一点,他会如何对待艾瑞纽斯的“信仰要义”?这一“要义”与圣经正典的形成密切相连,对基督徒身份的确认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那些基于教会的信经不也是人对圣经信息的概括吗?要是巴特处在一个异端四起的时代,他将如何回应?也许巴特会说,艾瑞纽斯的“信仰要义”、大公的信经都是教会基于圣经的宣讲,最终来源于那活着的神的道,因此要不断接受神自己的道的检验。这都没有错。但是,如果那些书面的文字压根没有任何神圣崇高之处,从中总结出的要义又有什么意义?我们用人的语言进行的信经的诵读,难道与我们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信心完全无关紧要吗?不是说我们不只要心里相信、也要口里承认吗?
巴特的圣经理论秉承了他神学中一贯的行为主义、以及坚持人的因素和神的因素完全断裂的风格。 这确实有利于消除人的自义,也催促人更渴慕神的恩典。但是,他对人的因素在神的作为中近乎彻底的否定在实践中极易导致犬儒主义,而他对人的权威的消解又极易在教会中造成无政府状态。 我同意,圣经是人对神的言说的见证,是人对所领受到的神的启示的转述,它的确是人的话。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圣经不是神的话,而只有在神使用它对人说话时才成为神的话,就对它作为基督信仰的正典的地位过于相对化了。就圣经是人对神的话的转述来说,它也应该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言说在先,就没有接下来的人的领受和转述。虽然人的领受会有偏差,人的转述可能走样,但是,圣经的正典之所以为“圣”经,不应只是因为其成书时间较早,更是由于它是经过教会实践的历史考验和筛选下来的对神的道的传承,而这种筛选其实是神的道在世间万象和芸芸众生中的一般启示对特定的人群所领受和传承的神的道的检验。巴特完全否认有所谓在耶稣基督之外的一般启示,难免忽略神在道成肉身的特别启示事件之后的这一层作为;教会实践的历史对人的传承的检验其实也是一种神的拣选。圣经虽然不是“神”经——像阿拉丁神灯似的法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是“圣”经;世物能称为“圣”,“holy”,“sancta”,乃是因为它们是蒙神拣选、又被神祝福的,如圣日、圣礼、圣徒。也许,巴特要说这种拣选和祝圣需要不断地发生。也许,历史的考验和筛选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就圣经的正典较之后来关于神的道的论述经历了更长久更严酷的筛选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就讲述成了肉身的神的道而言,圣经具有最高的含金量。如果因为圣经与生俱来的人的因素、而放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无异于否认神在圣经成书过程中的作为。当然,人对神的道的领受和转述需要不断地接受神的道本身的检验和校正,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11:29),我们相信,神自己会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

参考书目

-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Doctrine of Word of God, 2nd ed., (Edinburgh: T&T Clark, 1975).
-
Boone, Kathleen C. The Bible Tells Them So: Discourse of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 (SCM Press, 1990).
-
Bromiley, Geoffrey W..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
Holcomb, Justin. Christian Theologies of Scrip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Dempsey, Michael. “Biblical Hermeneutics and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The Revelatory Presence of God in Karl Barth’s Theology of Scripture” in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Fall 2007, Vol. 37, Issue 3, pp. 120-131.
-
Leith, John H, ed.. Creeds of the Churches: A Reader in Christian Doctrine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 3rd ed.,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1982).
-
McDonald, Lee Mart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Biblical Canon, (Nashville: Abingdon, 1988).
-
Runia, Klass.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Holy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作者简介

成静,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学士,耶鲁神学院道学硕士、神学硕士,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系统神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现任教于福建神学院。
往期文章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公号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辑:Vanci
校订:然而、巴特研究、语石、Shooki、Lea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