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的方言常让外地人听不懂,那时全家住在成都时,当地的弟兄姊妹根本听不懂我和父母用方言交流,甚至曾经被人听成了日语,这可着实笑坏了我们这一家子尧舜禹的邻居。
于是我在外地公开场合和父母聊天总直言不讳,什么这家冒菜的味道不很理想啦,那家菜场的菜卖的太贵啦……我就这般被方言保护着,体会到一些”言论自由”,甚至有些放纵。
以致于我回了老家还带着这个习性,在一家面馆评价着家乡的味道,老板接了我的话茬儿,我当场愣住,而后平复着安慰自己:幸亏评价还算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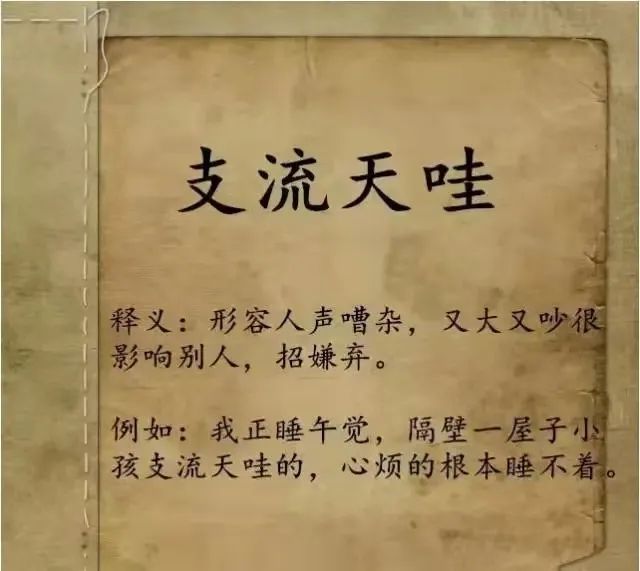
我们老家的方言特有意思,整个县各个村庄的口音、用词都不太相同,像是对亲属家人的称呼。例如“大大”二字,大部分地区还是理解其为称呼父亲的方式,但有的地方会用其称呼姐姐,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我们村用其称呼哥哥。
还有一些不同的,我们县大多称呼奶奶这只是用乡音称呼这两个字罢了,而我们则会叫“娘娘”,倒是和川渝地方的“嬢嬢”意思有些相近。而外婆这个词我也不会叫“姥姥”,而是直接叫“婆婆”;外公也比较特殊,叫“外爷”。
并且,一般情况我们在辈分上下关系上,通常会在本来的称呼上加个“老”字。比如说“姨”,若是我父亲或是母亲的姨,我就会叫“老姨”;还有父亲的奶奶,我就会在“娘娘”的基础上加个老,因此会叫“老娘”。
而妈妈的外婆,若是以此类推,可能只能叫“老婆”了,但因为我们这里老婆的叫法也是这样,因此我会叫她“老婆婆”。而我的老婆婆在我生命中,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自我有记忆起,我就常去老婆婆家,那时我的外公外婆都已过世,而他们的四个儿女中,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只有一个小儿子,也就是我舅,也已经出去工作打拼了。
因此老婆婆独自一人住在外公外婆的房子里,那是个独户的院子,倒也不小,里面有三棵枣树,两棵大树,一棵小树,小树立在西屋门口的小坡上。
下面是一大片空地,老婆婆在里面种了月季花,无花果树,小葱,番茄等等,种类很多。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作物有两个,一个是草莓,一个是葫芦。
那时外婆外公的孩子们,只有母亲是在本村出嫁的,因此我常常出没在这里。我痴迷于在草莓丛里翻找着,想尽法子要找到几颗老婆婆摘完后漏下的果子(即使摘下来也总是给我吃的)。
并且我翻找的时节不分春夏秋冬,直至秋冬季发现那里没了那一小丛叶子,就以为院子里的草莓从此灭绝了,到了第二年,却还能吃到。

还有葫芦,那是一种流行文化的象征,没错,就是我们的《葫芦娃》。那时我最爱的动画片就是葫芦娃,于是闹着想要一个“七娃”的葫芦玩玩,老婆婆便在院子里添置了一串挂在竹竿上的小葫芦。
农作物的对面有三座屋子,一间是许久未住人的东屋,我不太敢进去;紧挨着的是一间小小的厨房,再过来就是一间充满回忆的柴房,一般家里的蜂窝煤会放在那里面。
在往里面其实还有半个院子是空地,但那时我不常去那里,记忆也就模糊了。只记得那里养过鸡,因为熊孩子总是去欺负面善安静的母鸡,作为一家之主的大白公鸡自然要撑起一片天来保护自己的配偶。
于是它以熊孩子为敌,每次见面必追逐一番,直到母亲看不下去,将那只漂亮的公鸡抓来吃了。那是我吃鸡肉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毕竟是头一次吃掉自己恐惧的对象,味道都变得不太一样了。
童年许多时光都在这个院子里度过,连做留守儿童的日子里,我也常常离开爷爷奶奶家去找老婆婆。那里给我的温情,是其他地方若所没有的,甚至在这里起床走远路上学的感觉,也比住学区房就近出发更觉幸福。
只可惜这样的时光不能给我多少享受的机会,我还是跟着父母离开了村庄。那时我曾在村子里做过不久的留守儿童,属于调皮到不行的那种孩子,常让大人们觉得头疼。
村里的大喇叭里那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常常失踪,爷爷奶奶满村找,却不想我藏在农田里的某处,或是某个同学家的饭桌上。
就这样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总该是要带到城里收一收野性的。于是我那个暑假,几乎没有出过几次门,住在一个学校里,磨炼着自己想念乡野的心,磨练着自己想念和老婆婆两个人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一个人的日子是孤独的,这毋庸置疑,许多人知道,却不说明。也是危险的,我们都该知道,但总是忽略。那是一个秋天,大雨连绵着下了十一天,好像要用自己软化所有的硬土。
老婆婆一个人在家,去了柴房,要搬些蜂窝煤到屋里烧炉子。却不小心滑倒了,摔断了腿。于是她开始了自己最不自在的那几年,似乎她当年躲避日本人的时候还要难受。
那时我跟着母亲从城里回来探望她,走进了拥挤的病房,只见一个绿色窗台的白色房间里安置了一个机械式的病床,老婆婆就躺在上面。那个床是可以动的,用来让她躺着舒服一些。
我走近她,见她在流泪(她常在躺下时眼角流泪,不知是因为眼睛涩,还是因为心里苦),于是我帮她擦了,就像以前一样。
小时候只是以为老婆婆只是因为伤口疼痛才这样,但是长大后才多了一些理解,她的疼痛不止身体上的,还有这许多年来心中的苦闷、懊悔和孤独。
她对我说,觉得自己快要去世了,我认为她错了,于是把玛土撒拉介绍给了她,想让她因为这个人的寿命不要害怕。也不知道,那时候老婆婆会怎么想玛土撒拉这个人,会是羡慕?还是同情?

老人家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即使在她受伤以后,也分别两次在我家住着,因为那时亲人之间也会轮流接待行动不便的老婆婆。她是在我家离开的,而两次之间隔了整整五年。
老婆婆经历过许多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历史事件:她曾为了躲避日本人而在各个村子,山区里奔走,甚至有过在外面堆满木柴的窑洞里藏了许久,那时她的丈夫(我的”老外爷”)是八路军。
她也给我说了一些可怕的故事:那时在村子里嚣张的坏蛋们大都是日伪军,这就是中国本土的“皇军”,他们因为找茬而砍了村民的头,还因为本土的迷信,做人血馒头吃……
直到我看到鲁迅先生写的人血馒头,我才明白,没有读过书的老婆婆,从这样一个故事背景之下活下来,就成了一本无字的书,一本活着的书。
我从她这里听了许多过去的事,关于我祖先的事,曾几何时,还因为自己的”红根红底”,觉得自豪。
尤其是听到老外爷险些做了县长时,激动的不得了。但忽然想到,若是这样,父亲或许就娶不了母亲了,这样的话,享受做县长后代的那个人也就不是我了,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庆幸的念头。
老外爷在拒绝了县长职位后不久,便因肺结核去世了。老婆婆膝下有四个女儿(大女儿便是我的外婆),却没有一个儿子。就这样,她顶着压力,撑起了这个家。
那时,我也常义愤填膺,因为她也会和我谈论一些,和我的老姨们之间的矛盾。
她讲到最让我愤愤不平的就是那个欺哄她”五保”保金的女婿,也就是我的老姨夫之一。他告诉她,自己会把每年的钱”贴心地”替她领着,然后等着老婆婆离世后买棺材用。
老婆婆让我了解了许多过去的事,让我对那个时代常常向往,她也让我知道了许多真相,无论是关于亲情的、历史的。
虽然她没有读过书,但是仍教导了我许多知识。她给我讲述着自己的一生,让我知道了一部分的现实。
老婆婆在最后的日子里接受了福音,这一点来说,她也很幸运(有限的词汇中最适合的一个)。那时我还和她住在一个屋子里。
只是最后几天的时候,老婆婆无法控制自己的呻吟时,无法忍住大小便时。我这个没良心的家伙竟想着远离她,便把一切照料她的担子都丢给了母亲……
我发现自己本能性地嫌弃着这个从小照看我的老人,虽然我内心也因此十分痛苦,但是我不再陪她聊天,不再听她说话,不再想着法子让她舒服一些,甚至睡觉也跑到其他房间去躲避她。就是我躲避老婆婆的那个夜晚,父亲陪着她到了凌晨,她就走了。
我的老婆婆,一九二二年到二零一二年,享年九十岁,我曾经心里最亲近的,又自私得嫌弃的老人。从亲情上来说,我是一个失败者。
当我在葬礼的那些日子遇到那个老姨夫时,我义愤填膺,却愧疚不已,因为我想着自己最后几天的态度,只觉得自己像这个骗子一样。
我逃避着自己的亲情,因为我的私欲总是大过血浓于水,为了让自己不陷入不愉悦,便把感情从中抽离出来。像许多成了陌路的亲属们一样,我曾这样硬着心肠,让自己成为了现实中的一部分。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次回想那个院子,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院子,墙壁只是砖头活搭起来的墙头而已,大风一吹可能就倒了。
门也不过是一个木板钉起来的木栅栏,常常有野狗钻进来,到院里偷食。还有那半个院子,原来那里常常会长出高高的野草,没有人去处理,也就无人问津了。
还记得老婆婆家门外有一排石头组成的座位,那似乎已经垒起来许多年了。老婆婆常带我去那里,坐下和人们聊天,这似乎是她不多的娱乐环节了。
我还记得许多有关老婆婆的故事,她给我讲的故事,我们之间的故事,那个院子里曾经有过的其他故事……这么多场景早已有些模糊了,但那时的感觉却越来越清晰。
渐渐的,记忆开始混乱,平淡的显得那般美好,痛苦的早已云淡风轻,深刻的事还未来得及回忆,思绪便这般被略过去了。
于是我将最明确的印象写下,最铭心的感受记住,免得被大脑一笔带过,曾经最重要的人,都被多余的故事充斥着,快要吞没了。
202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