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本期推送选取由李秋零老师翻译的潘能伯格论“上帝的主体性与三位一体学说”一文,并对文章略作编辑处理。在本文中,潘能伯格注重比较巴特与黑格尔关于上帝主体性及三一学说的论证,并试图指出两位思想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内在关联。在潘能伯格看来,巴特思想部分接近黑格尔思辨神学的思维路径,尽管巴特在具体问题论证上受到不同思想家的影响,但事实上,巴特也同黑格尔相类似地从上帝的主体性中引申出三位一体,作为包含在它里面的规定性的展开。最终,潘能伯格指出,上帝的统一性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先于位格的三重性,它仅仅存在于三个位格的共同性中。只有如此,上帝才是真正的无限者,既内在于世界,又超越世界。
潘能博格对巴特与黑格尔两位大家之间思想关联的这一解释主要出自主体性理论或者自我意识理论的视角,这不仅符合于他对近现代神哲学从宇宙论到人类学转向的基本判定,而且也符合于他对施赖尔马赫以来主体性理论或自我意识理论的自觉继承。但是,这样的解释进路忽略巴特神学和黑格尔哲学所不自觉或自觉承继的亚里士多德以来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传统,忽略了巴特三一论和上帝论对上帝之为上帝的上帝性的特别强调:上帝不仅仅是自我意识或认知的主体,更是在从以色列历史到耶稣基督历史中自我启示的、与人同在的、盟约的和行动的上帝,创造的、和解的和救赎的上帝。
原文发表于《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7年春,第6期,页9-30。本文推送时已获发表期刊和译者本人授权。特此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李秋零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文章正文长度约10500字,阅读时长约20分钟。
新春临近,预祝各位友人新春愉快!
近
年来,卡尔·巴特的神学一再被当做主体性及其自律这一近代主题的一个变种。[i]这样的观点具有某种挑战性,因为归根结底,卡尔·巴特恰恰是以上帝至高无上的名义来反驳“近代主体性所说的自律性”的。[ii]但尽管如此,这样的反驳是在巴特从自律之人的主体性向唯一自律之上帝的主体性的转变中,借助于可以追溯到康德主体性哲学的材料实现的。在这里,巴特也没有简单地使人的主体性问题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毋宁说他断言,上帝的主体性是建构人的主体性的条件。[iii] 巴特在他的《罗马书注释》第二版及其“危机神学”阶段就已意识到,上帝不可以仅仅被想象为世界和人的对立面:“如果上帝还是与另一物相对立的某物,例如一极或者对极,是与否,如果上帝不是完完全全自由的、独在的、优越的和胜利的,那他就是非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上帝”。[iv]虽然这句话的表述,起初所针对的是以此岸和彼岸的宗教对立图式来论证关于上帝的言说,但是,它也同样切中了巴特的《罗马书注释》自身的框架设想。T. 伦德托尔夫(Rendtorff)在此正确看到,“已经瞄准了那个超出《罗马书》的主题”。[v] 巴特意识到,不能从与世界的对立出发来设想上帝,因为这样一来,上帝依然在对立中依赖于这个世界,从而甚至不是被设想为上帝。巴特起初试图通过肯定与否定的结合来公正对待这一事态,他称这种结合为辩证关系,它借助自己的肯定和否定而与这里保持为非直观的、“本身当然不可称谓的真理”发生关系,这真理“处在中间,且只是如此才给予肯定和否定这两者以意义和指称”。[vi] 但这样一来,上帝的真理当然还没有被设想为在自身之中自由的和优越的。巴特直到1924年,在他开始自己的哥廷根(Gottingen)教义学讲演课后,还在为这一任务费心劳神。此间,他的努力特别集中在三位一体学说上。1924年4月20日,他在给图尔内森(Thurneysen)的信中写道:“倘若我在这里掌握了正确的锁钥,那就简直是万事大吉了”。一个月后,他报告了已找到的答案:“我把三位一体理解为上帝在其启示中的不可取消的主体性问题……”。[vii] 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三位一体学说,才避免了一直仍在对世界的依赖性中设想与世界有别的上帝,因为上帝作为父,首先不是在与世界的对立中,而是在与子的关系中被设想的,以至于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扭转了,被理解为通过上帝三位一体的自我关联而可能的,在这一自我关联中预先形成的。由于三位一体学说论证了上帝及其在基督里面的启示相对于世界的独立性,所以它早在1927年就在《基督教教义学》(即教义学导论)中得到探讨,被当做关于上帝之言是神学认识论原则的学说的基础。巴特对基督教布道是上帝之言的要求所做的分析,首先导向了“原初的”启示事件,这事件在历史的层面上,既不是作为事件、也不是作为上帝之言而能被认识的(页81)。启示作为上帝之言的现实性,只有从上帝自身出发才能得到论证。为此,巴特早在1927年就求助于坎特布雷的安瑟尔谟(Anselm von Canterbury)的本体论上帝证明,这证明作为从概念出发对存在所做的证明,是上帝的自我证明(页97以下)。但是,上帝的这一自我证明蕴含在三位一体之中;借助于三位一体,由下到上、由人到上帝的道路,教会布道是上帝之言的论证过程,都与上帝在其启示中的主体性相适应而被扭转了(页126 – 127)。巴特1927年从“上帝说”(页127以下)这句话,1932年在《基督教教义学》中从“上帝启示自身为主”(Ⅰ/1,页323以下)这句话,发展出三位一体的规定;他还称后一句话为“三位一体学说的根源”(页324)。在这两个场合,上帝包含在启示概念自身中的三重身分,即启示者、被启示者和启示活动自身,是三位一体学说的基础。在此,对于巴特来说重要的是,这种三重性不仅仅处在上帝对人所做的启示之中,而且已经处在上帝的永恒本质之中,因而是“内在的三位一体”。巴特早在1927年就极力强调这一点,因为若不然,我们在启示中就会与真正的上帝毫不相干(页157)。因此,内在的三位一体是巴特构思上帝在其启示中的独立性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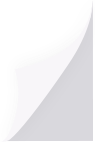
△Karl Barth’s Church Dogmatics Original Publication Dates from postbarthian.com
由于这一构思,巴特已非常接近19世纪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的思辨神学。思辨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归还了三位一体学说——针对18世纪的知性批判所造成的三位一体学说的解体——在上帝观中的中心地位。就连巴特也承认,黑格尔以他对三位一体学说的“更新”,“孤寂而又专断地推进了神学”,而且是在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敌对”中。[viii] 但是,尽管巴特赋予三位一体学说以对神学来说在整体上奠基性的功能,他事实上依然接近于黑格尔和思辨神学家,因为在那里和在巴特这里一样,三位一体学说是与启示概念紧密相连的,而且是在建立在上帝三位一体的自我展开之中的上帝自我启示的严格意义上。而在第三个与此相关的点上,巴特也接近于黑格尔和思辨神学,这就是他把坎特布雷的安瑟尔谟的本体论上帝证明当做对上帝在其启示中的自我证明的描述来使用。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接近,巴特却把黑格尔的思维看作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在黑格尔及其神学后继者那里,关于上帝及其圣灵的言说难道不是归根结底意味着人和人的精神的神化吗?无论如何,黑格尔的真理自我运动对于巴特来说是“与人类主体思维的自我运动同一的,而既然人类主体的思维总是在思维时保持为自身,所以它也就与这一主体的自我运动相同一”。[ix] 在此,巴特肯定是过于轻易地接受了黑格尔对科学认识的要求,即“把自己交付给对象的生命”,[x] 以至于哲学家“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袖手旁观了”。[xi] 因此,巴特也没有充分估价黑格尔那尚需要讨论的扭转,即把有限的主体扭转为作为绝对主体的上帝,没有充分估价这一扭转与他自己的思维运动的平行性。这大约要归因于基尔克果(Kierkegaard)对巴特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巴特自己在1963年说,由于基尔克果的“起床号”,由于基尔克果把上帝与人的无限质别尖锐化了,对他来说已不存在向黑格尔的“复归”了。[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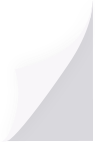
△Photo of G. W. F. Hegel (1770-1831)
虽然基尔克果的观点把巴特引向了对黑格尔的一种片面人类中心论解释,巴特却一直在细节上承认他自己的思维与实证神学家们的立场的渊源关系。有一位受到黑格尔影响的神学家,巴特把他列为自己的先驱,这就是依萨克·奥古斯特·多尔纳(Isaak August Dorner)。巴特在1927年《基督教教义学》前言中把他列入自己神学先祖的目录。在这部书的正文中,多尔纳主要是与三位一体学说相关联而被提到的,而且是作为“少数新派神学家中的一位”;在巴特看来,这些新派神学家认识到,在梅兰希顿(Melanchthon)那里已出现的对三位一体学说的忽视最终被引向“通过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道路”(页198)。在这方面,巴特明显地联系到多尔纳1886年的一篇文章《德国神学及其在当代的教义学任务和伦理学任务》中的一段表述;巴特在自己的《十九世纪新教神学史》中也引用了这段表述。在那里,多尔纳指责了施莱尔马赫对三位一体学说的“冷漠的、甚至是否定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可以追溯到梅兰希顿;多尔纳还说道,如果没有“内在的三位一体学说”的思想,就连“维护释罪原则的福音力量和纯洁性也根本不可能”,[xiii] 因为释罪的信仰正是取决于由三位一体学说所保证的上帝的至高无上性。与此相似,多尔纳在其《基督教教义体系》(1886年第2版)中强调指出,由释罪信仰所建立的人的品格“只有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才找到其客观的和绝对的论证”(页401)。
关于多尔纳这一思想的贯彻,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他把上帝的统一设想为“绝对的品格”,从而不愿意让三个三位一体的“位格”成为同等意义上的位格。作为替代,他更乐意说“上帝的三种存在方式”,它们“在其产品中,即在神性的品格中并没有消失,而是永恒地持存”(页431 )。巴特有过明显类似的表述。在《教会教义学》中,巴特--虽然没有引用多尔纳的原话--肯定了多尔纳的命题,即上帝是一个唯一的品格,而且这被宣布为“从三位一体学说得出的一个结论”(《教会教义学》,Ⅰ/1,页378)。必须把唯一的上帝理解为主,“理解为位格,也就是说,理解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自我,具有他所特有的思维和意欲”(同上)。这样,上帝就在其启示中与我们相遇,并且是作为启示自己的主,虽然上帝在其启示中区别为启示者、被启示者和启示这三种“存在方式”,但他依然是主。因此,巴特在默不作声地追随多尔纳时,把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统一理解为一个思维着和意欲着的自我的统一。这一自我,一方面和在多尔纳那里一样,被理解为存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三重性的结果(页378),但另一方面,又被称之为三位一体学说的根源,在处于启示之中的上帝自身里面,这一根源被称作是“言说的上帝的位格”(页320)。事实上,如果说在巴特看来,三位一体学说应该表示上帝在其启示中的主体性,那么,上帝作为主,其自我也许就构成了这一主体性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三种存在方式当然就可以被理解为这一自我自己展开的要素了。这样,无论如何强调三种存在方式的同等神性,也几乎无法再避免把父设想为神性自我的原初形态,设想为“他的其他存在方式的缔造者”了(页414)。此处起作用的趋势--一种不情愿地要求使其他两种神的存在方式失去可能的趋势--是,父不知不觉地成为唯一神性自我的原初形态;至于这一趋势的难题,多尔纳看得比巴特更清楚。只有在能够和多尔纳一样把唯一上帝的品格理解为三种存在方式的结果,而不是理解为其基础的条件下,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巴特的基本思想,即把三位一体学说展开为上帝在其启示中的主体性的表达,并使上帝的主体性已经构成三位一体的“根源”,而不是构成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成问题了。

△ August Johannes Dorner (1809-1884)
由于把自己的三位一体学说与上帝是主体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巴特也就比多尔纳本人更接近黑格尔以及在黑格尔思维中达到顶峰的思辨上帝观。只有通过把上帝设想为三位一体的,才能把上帝设想为主体、设想为自我意识,这一思想在近代神学中可以追溯到莱辛(Lessing)。在其《人类教育》第73节中,莱辛解释说,上帝的意识应该被设想为永恒地集中在作为一切完善性之总和的自身之中的。但是,上帝表象什么,也就创造什么;因为在上帝那里,表象、意欲和创造是一回事。这样,上帝也就永恒地创造着一个与他相等的、完善的存在,即子;而子由于其完全的相等而在同样完全的和谐中与上帝是一回事。谢林( Schelling )在1802年赞扬莱辛的这一思想“也许是他全部著述中最具思辨性的”。[xiv] 这一思想在黑格尔的上帝观中得到了其经典的完成。黑格尔从上帝是精神、是主体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属神生命的三位一体结构。在其《宗教哲学讲演录》手稿中,黑格尔写道:“上帝是精神,是绝对的活动,是纯粹的活动(actus purus),也就是说,是主体性,是无限的品格,是他与自己本身的无限区分,是对自己来说对象性的、对自己来说客观的神性,是子,是生产;但是,这一区分开来的,是包含在永恒的概念之中、即包含在作为绝对的主体性的普遍性之中的”。[xv] 因此,从精神是主体性或者自我意识的概念[xvi] 出发,产生出自我区分;尽管如此,主体在这种自我区分中与自己依然是一回事。早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经写道,绝对的本质作为精神“本质上是自我意识”,从而“就其概念而言是可启示的”,也就是说,对其自身来说是可启示的和显而易见的:“它的那种对象就是自我,但自我不是异己的东西,而是与自己不可分离的统一,是直接的普遍者”。[xvii]
这样从精神概念引申出属神的三重性,在西方神学中可以一直追溯到奥古斯丁(Augustinus)。如果说,奥古斯丁在这一问题上还考虑到三位一体教义陈述的世俗解释的话,坎特布雷的安瑟尔谟就已经迈出了从精神概念引申出三位一体规定的步骤。巴特对他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所看到的从三位一体的迹象(vestigia trinitatis)引申出三位一体的作法持批判态度,与此相对立,他早在1927年就强调,三位一体学说乃是“耶稣是基督或者救世主、是主这一认识的展开。理解、阐述和论证这一学说就是由此出发的,而不是由其他任何地方出发的”。[xviii] 难道巴特在这里不是坚决要摆脱思辨的三位一体学说吗?再仔细地看一看,这一对立就不像乍一看那么强烈了。因为就连巴特也不是首先从注释性的断定出发,因而也就是从耶稣与父的历史关系出发,而是借助启示概念的内在逻辑来阐述三位一体学说的;在这一概念中, 可以区分开主词、谓词和宾词,或者启示者、启示和被启示。[xix] 在巴特看来,这里所涉及的是上帝在其启示中的自我客体化,据此,上帝亘古以来就“不是没有他者存在的”,而是“只有通过借助他者、甚至在他者之中拥有自己才拥有自己的”(《教会教义学》,Ⅰ/1,页507)。事实上,这不就是黑格尔在从精神或者自我意识的概念中引申出三位一体时,所阐述的那种主体性结构吗?毫无疑问,这种引申的形式在巴特那里并不存在;但是,他根据上帝的主体性概念所做的论证的结构,难道在事实上不类似于黑格尔的结构吗?至于巴特是从作为三位一体学说基础的启示出发的,与此并不矛盾;因为即使在黑格尔那里,上帝三位一体的自我客体化也是与启示概念紧密相连的:“……这种自我展现属于精神自己的本质。一个不可启示的精神并不是精神”。[xx] 毋庸置疑,区别还是存在的。黑格尔已经在三位一体内部、在上帝对自身而言可启示的意义上使用了启示概念,而巴特则是把启示概念留给了道成肉身和在耶稣基督里面发生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已经不仅仅把世界的和解,而是还把世界的创造理解为上帝的启示活动:“精神作为精神,在本质上就是启示自己,它就连世界也不创造,相反,它就是永恒的创造者,是这种永恒的启示自己,是这种活动”。[xxi]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神的创造行动的启示意义对于人来说,只有借助于上帝与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统一才是可启示的。尽管如此,在这些各不相同的说法中,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启示概念延伸到了上帝三位一体内部的生活和上帝在创世之中的启示活动的差异,这暗示着,世界的创造被看作是神性本质自我展开的一个必要因素。事实上,黑格尔在其1827年的宗教哲学讲演中就能够说:“是创造者,这属于他的存在,属于他的本质。--如果他不是创造者,他就被理解为有缺陷的”。[xxii] 在这个地方,巴特产生了他对黑格尔观念的--如他自己所说--最严重的“疑虑”:黑格尔用一种人能够洞见的必然性取代了启示的自由。“在启示中,所涉及的不再是上帝自由的活动,而是上帝必须像我们看到他在启示中发挥作用那样发挥作用。他必然要启示自己”。[xxiii] 尤利乌斯·米勒( Julius Muller )对黑格尔提出的主要指责就已经是:“精神的本质被这个体系片面地理解为思维,而这一思维又被理解为必然的过程”。由此,“世界成为上帝的自我实现,……而无限生命的伦理规定性则成为这一实现过程中的要素”。[xxiv] 米勒已经从这一批判--巴特在自己的《十九世纪新教神学史》的黑格尔部分赞同了这一批判--中得出结论说: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一种“逻辑的泛神论”,其结果是对恶的违背神性得出了错误认识,既取消了上帝的自由,也取消了人的自由。即使鉴于黑格尔实际上的陈述,不能把强加上这样的所谓“结论”完全视为有道理的,但对逻辑必然性在黑格尔关于神的自我展开过程的描述中所起的支配作用提出的主要指责依然存在。[xxv] 即使考虑到黑格尔试图把必然与自由理解为辩证同一的,这一指责也依然存在。
当然,黑格尔给上帝的现实性和上帝活动的过程强加上思想的逻辑规定性次序的必然性,这是一个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这种批判所针对的却不应该是,黑格尔根本上是试图在思想中--这总是意味着:在人的思维形式中--把握上帝的现实性。巴特并没有摆脱做出这种反应的诱惑。他特别赞扬多尔纳,说他把启示概念从黑格尔对思维的片面强调中解放了出来,使它隶属于信仰,尽管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的开端是应该肯定的。[xxvi] 尤其是,巴特反对黑格尔,赞同基尔克果关于上帝和人之间有无限质别的命题。当然,巴特此时并没有陷入黑格尔批判过的哲理神学对手们的观点;这些人宣称不能认识上帝,从而在事实上绝对地设定了有限的现实性。但是,巴特为自己拒绝在思维中把握上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信仰的决定对他来说成了神学从上帝出发进行思维的尝试的基础。为了论证这一点,巴特认为只能求助于一种如上所说的具有神学勇气的行动,即“根据上帝的确定性来理解人的自我确定性,而不是相反”。[xxvii] 由于他把将属人的主体扭转为上帝的作法当做一种裁定的事情,他也就把自己严厉批判过的近代神学的主观主义和人类中心论推向了顶点。巴特借助于三位一体学说把上帝设想为独立于世界的努力,并没有能够克服转向这个主题时的裁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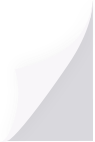
△ Photo of Karl Barth (1886-1968)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黑格尔依然比巴特高明。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两人对本体论上帝证明共同的高度评价上。黑格尔和巴特二人都断定这一论证是上帝的自我证明,从而是唯一适合上帝的至高无上性的。但是,黑格尔认识到了本体论论证在其出发点问题上的困难:“构造作为最完善本质的上帝的概念是必需的吗?”黑格尔认识到了安瑟尔谟论证的弱点,这弱点就是,安瑟尔谟采纳这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从这一概念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是把它当做某种仅仅偶然给定的东西。因为这样一来,关于上帝的思想连同其存在的断定,都成了某种偶然和任意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全部努力都集中在证明思维上帝的必要性上面,或者--如黑格尔所说--集中在超出有限者、上升到无限者的思想的必要性上面。黑格尔是通过他的整个体系做出这一证明的,他到处都通过辩证的反思指出,借助于有限者在其一分为二中的有限性,无限者或者绝对者就已经得到了思维。这样,本体论上帝证明的出发点就被确保为一个不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思想。与此相反,巴特对安瑟尔谟做出诠释的命题是:本体论证明的出发点是由信仰预先规定的;这一命题使上帝观退回到了个人信仰行为的纯粹主体性上面。
黑格尔要求以思维来认识上帝,而巴特针对黑格尔的要求所做的保留,除了退回到信仰决定的有限主体性上面,还造成了其他后果,即再也无法认清被用来展开这样的信仰立场的思想形式。这样,巴特接受了黑格尔从上帝的主体性概念引申出三位一体学说的作法,尽管这与他对黑格尔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描述属神的自我展开所做的批判根本无法统一。[xxviii] 而尤其是,尽管巴特的上帝观自以为是不依赖与世界的任何关联,但它在事实上却仍然依赖于在世俗范畴中解释的对世界和人的经验,因为巴特的上帝学说排除并越过了整个实际上的世界经验和自我经验的领域,其目的是以上帝为开端,而不是通过反思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有限性间接地获得上帝至高无上的思想。黑格尔是这样做的;本来,巴特自己在《罗马书注释》第二版中所说出的洞见也是这样要求的:“如果上帝还是与另一物相对立的某物,……如果上帝不是完完全全自由的、独在的、优越的和胜利的,那他就是非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上帝”(参见注4)。巴特在这里所说的,正是黑格尔关于真无限的思想。据此,仅仅在与有限者的对立中设想的无限者还不是真正的无限,毋宁说,真正的无限者和绝对者必须既与有限者对立,又在自身中扬弃这种对立和有限者的世界。因此,它在一切有限者中都必须是可证明的,但仅仅是否定性地可证明的。这就是黑格尔对传统的上帝证明形式的批判:不是有限者的存在证明作为其第一因的上帝的存在,而是有限者的非存在--其非独立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指出这一事实,乃是从有限者上升到无限者的思想,这是一种并非首先在哲学论证中、而是首先在宗教意识中完成的、在哲学思想中只是事后才完成的上升。这样的上升乍一看是人这种有限主体的作为。但是,只有作为上帝自己在人里面的作为,它才能够是向上帝的上升。黑格尔在反思人“上升”到上帝这一概念的矛盾情感时,完成了与日后巴特所设想相类似的扭转,即扭转人的主体性为上帝的主体性。但是,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向上帝至高无上性的扭转,恰恰是因为他并不是以一种信仰决定为开端,而是以对有限现实的有限性的反思为开端。与此相反,巴特虽然早年的开端另有所指,但自二十年代中以来却借助于纯粹的信仰决定来论证向上帝至高无上性的转变,其目的是事后重新把世界和人引入上帝的统治。他的这种方法依然停留在信仰决定的主观主义和神学与非神学地孕育的人和世界的经验的对立中,以至于上帝至高无上性的思想必然使他转向他律。
尽管这一切,由尤利乌斯·米勒提出、并为巴特所接受的对黑格尔关于神性本质在逻辑上必然的自我展开的思想所做的批判,仍有其合理的内核。只不过,批判的合理所指,不能是黑格尔借助于思维设想了上帝。只有这种情况在黑格尔那里如何发生的方式,才能是指摘的对象。在我看来,做出这种指摘的契机当然是实际上既定的,也就是说,是黑格尔借助于绝对主体自我展开过程的思想把人的思维规定的有限性纳入了上帝的绝对现实性。在这种意义上,指责黑格尔让上帝屈从于人的认识、屈从于人的思维,当然是有道理的。
黑格尔断言神的自我展开的逻辑必然性--从而也断言了世界的创造及其和解的必然性--,必须以上帝的概念为前提条件;上帝的自我展开被断言为必然地从这个概念得出的。这就是主体或者自我意识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主体的概念与概念之概念,即他的逻辑学的顶点,是同一的。因为黑格尔认为,概念在其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诸要素中展开自己本身,进而成为判断和推理,最终成为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理念。每一个概念之所以是普遍的,乃是就它表述了它所把握的特殊者的普遍本性而言的,特殊者作为普遍者与其特殊性的统一,永远是一个个体。这些逻辑规定性在判断的逻辑形式中分离开来,而在推理中又联结起来,但此时却是作为有差异的整体。尽管这一切,概念始终是某物的概念,不仅仅是主观的思想或者表象,而是事物自身的概念,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就其实现而言,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所说的理念。
我只是顺便提出一个问题:概念是否在实际上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有差异的结构中展开自己本身;或者说,这是否只是由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概念所包含的东西的反思而发生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黑格尔是否借助于概念的逻辑,真正在逻辑进程中达到了一个原则上新颖的、终结性的阶段;因为反思揭示,我们离开了现象就不能思维本质的概念,离开了结果就不能思维原因,离开了整体就不能思维部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使针对那些范畴,概念的诸般规定性以新的方式已经在追求反思从它们那里所强调的东西,但这种反思却依然还是一个重新外在于概念之概念的、诠释学的活动。它并不简单地是概念自身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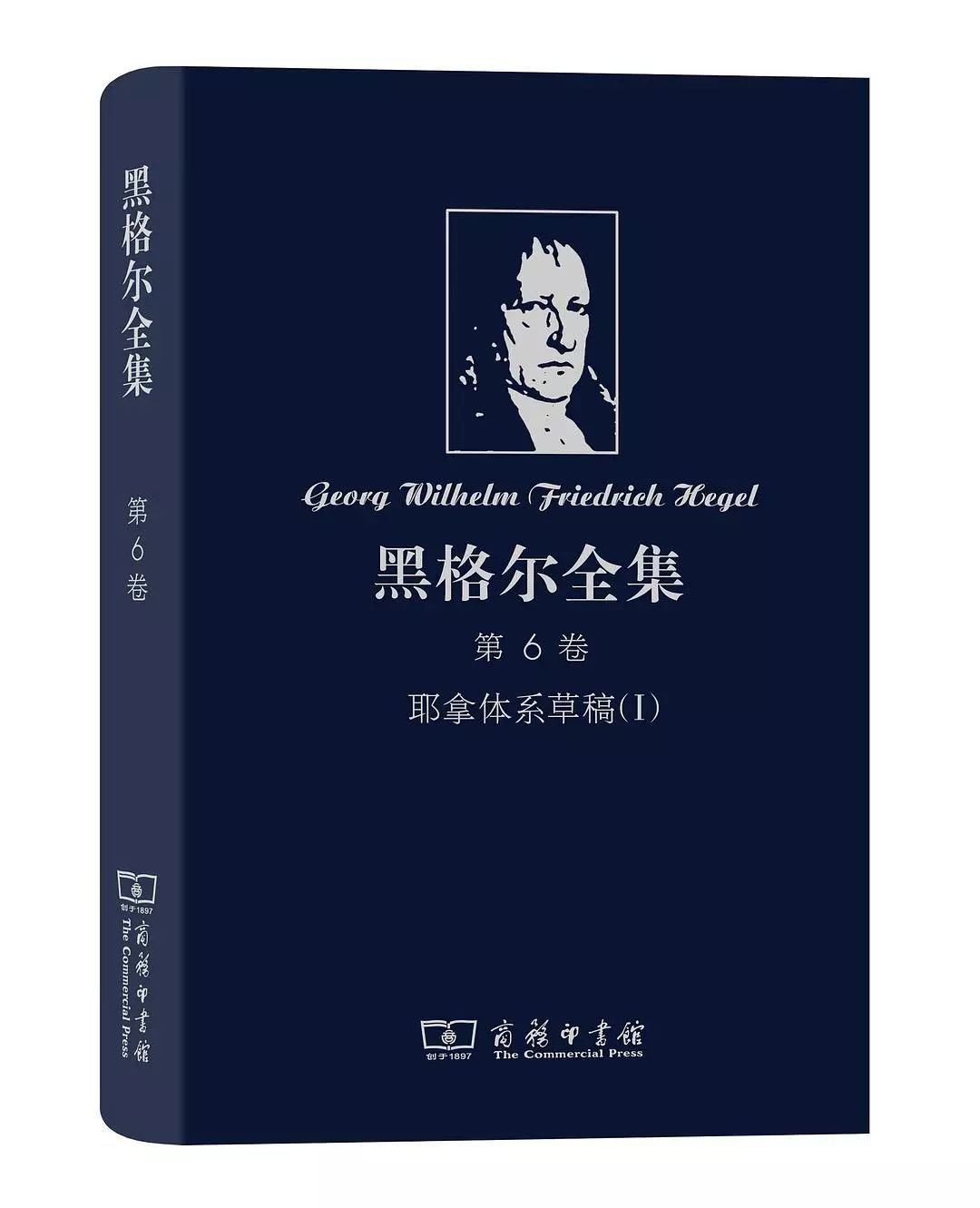
△黑格尔.《黑格尔全集 第6卷》. 郭大为, 梁志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但是,只有在概念阐释自己本身这种见解中,黑格尔才能宣布主体的结构与概念的结构是同一的:“概念……无非就是自我,或者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自我是作为概念获得存在的纯粹概念自身”。[xxix] 因为自我既是普遍的,就它延展到自己经验的全部可能内容而言;同时又是一个特殊者,并在两方面的结合中是个体性的品格,是这个个别的自我。从黑格尔关于概念与主体结构相同的命题中,毫不勉强地就得出必须把绝对主体的活动描述为绝对者概念的自我展开这一结论。由此可见,只有对主体与概念相等的整个情结进行批判,才能正确地批判黑格尔关于上帝在逻辑上必然自我展开的观点。
黑格尔把本体论的上帝证明,即从上帝的概念出发证明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解释为上帝的自我设定,这是一种以主体与概念相等为预设基础的诠释[xxx]:“概念就是在自己本身里面实现自身、给予自身客观性的过程,是仅仅存在于异在的形式之中的目的”。[xxxi] 只有联系到作为主体的上帝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条件,上帝自我展开的思想才是有意义的;只有从这一前提条件出发,上帝的自我展开才能被理解为一种从其预设的主体性中必然得出的自我展开。因此,主体的概念应被设想为先于其展开的,为的是从它出发,这一展开可以被描述为必然的。但是,恰恰主体这样先行于自己那随后能被解释为自我展开的展开,表现为把有限的思想规定--即理由与结果的先后相随--纳入了神的现实性。基督教神学一直是这样理解上帝的永恒性的,即上帝在唯一的临在中是他所是的一切。但是,这一上帝永恒性的思想,与包含在作为主体的上帝自我展开的思想中的上帝是自因(causa sui)的观念,是无法一致的。但是,随着作为主体的上帝自我展开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也自动地产生了这样一种过程的逻辑必然性的断言。
当然,对黑格尔的这一批判也适用于巴特。巴特也同样地从上帝的主体性中引申出三位一体,作为包含在它里面的规定性的展开。在这里,如果把上帝三位一体的分化设想为上帝活动的产物,那么,把上帝逻辑上已经“先于”这种分化设想为主体,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相对于此,巴特拒绝黑格尔从上帝概念中引申出三位一体、拒绝黑格尔所要求的神性自我展开的必然性,也很少会有什么用处。这种证明对于他的论证结构自身来说依然是外在的,因为三位一体的规定并不是从以诠释的、历史的方式获得的对原始基督教关于上帝是父、子、灵的说法的断定发展出来的,而是仅仅在它们从“上帝启示自己为主”这句话--从而也就是从上帝在其启示中的主体性--引申出来之后,才在事后借助于此得到了证实。事实上,这里有一种深刻的嘲讽,巴特本人恰恰陷入了由他极其激烈地批判过的黑格尔上帝学说的观点,因为他显然没有为自己做出足够的辩解,何以没有触及到论证风格中的必然性,他的出发点是以论证的方式还是通过一种信仰决定意义上的决断获得的。
选择从主体概念中引申出三位一体规定性的可能,出现在黑格尔的三位一体神学反思自身中,即出现在他从联结父与子的爱的共同性出发对神性统一所做的解释中。[xxxii] 在此,位格的多重性不是刚刚引申出的,而是原来就有的,而且只有在它里面上帝的统一才是实实在在的。在此,属于三位一体诸位格的,充其量是主体性,而不是通过相互的奉献把他们彼此联结起来的爱的统一。尽管如此,此处所涉及的也不是三神论或者二神论,因为只有当父与子的位格彼此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仅仅在第三者、即联结他们的灵中拥有自己的存在时,他们才存在,但在这里面又没有任何独立的东西,只有父与子的共同性的精神。只有从这样的相互奉献出发,三位一体的诸位格才有其独特的位格性。[xxxiii] 因此,必须把位格性与主体性区分开来。虽然在黑格尔看来,就连主体,即确知自己本身的自我,在自己的它物中也与自己本身同在;但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在自己的它物中认识到它自己的表现,从而也就认识到它自身。与此相反,位格性还没有从自身出发拥有自我。自我之所以是位格,只是出自一种超越自我的生命内容,只有它,才说明了自我真正的自我性。因此,耶稣之所以是位格,只是出自他那来自父的宣布和阐述上帝统治临近的使命。从他对父和对自己的使命的奉献中,耶稣拥有了他作为子的位格性。我是位格,这只是因为我真正的自己在我的自我中作为这一自我的规定性表现了出来。这一也适用于人类学的事实,在三位一体的诸位格身上原初性地、典型性地清晰可见。他们恰恰不像多尔纳和巴特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唯一的神性位格主体的“存在方式”。古典的三位一体学说所赋予共同的神性本质的,除了三个位格之外,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位格性;倘非如此,三位一体学说就会或者成为关于唯一有位格的上帝的“有神论”观念的多余附庸,或者成为上帝主体性的内在分化的隐喻。在西方三位一体学说的历史上,这一发展已经由奥古斯丁对教义的心理学说明肇始,由经院哲学盛期的心理学上帝学说继续发展,在近代的托马斯主义中达到其高潮。但是,根据古典的三位一体学说来看,这一道路是一条日益成问题的歧路。唯一有位格的上帝的有神论思想,事实上会被看作是人的自我的投影,就像对黑格尔绝对主体学说的无神论反驳所表现的那样。三位一体教义的上帝观恰恰表现了对这样一种抽象有神论的扬弃。虽然,就连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是一个唯一的上帝,而且这一上帝也不是非位格的。但是,他每次仅仅以三位一体的诸位格之一的形象是位格,因为三位一体诸位格中的每一个,都不仅只有以自己与其他两个位格的关系为中介才拥有其位格性,而且也只有如此才拥有其神性。子之分有神性,只能通过他以灵为中介而与父发生的关系。对于子来说,父与唯一的上帝是同一的。但是,就连父也只有通过子、在颂扬父与子的灵的统一中才拥有神性。也许,把唯一的神性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意义上的位格,这必定被判定为基督教有神论的异端。[xxxiv] 这一上帝观或者导向仅仅在世界彼岸的上帝的观念,或者导向上帝的一种自我展开的观念,在后者的一贯形式中,世界成为神的自我实现的条件。[xxxv] 这后一种观点至少有下述优点,即它并不把上帝留在一个对他的无限性来说招致毁灭的抽象超越性中。就像巴特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上帝还是与另一物相对立的某物”,事实上他就不是上帝。但是,上帝的至高无上性是不能从他的主体性出发得到论证的,而三位一体学说也不是这样超越世界的主体性的展开。[xxxvi] 上帝--用朋霍费尔(Bonhoeffer)的名言来说--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此岸的”。虽然一个世界的存在根本不是上帝的神性的条件,但是,一旦有一个世界存在,上帝的神性就存在于他在世界的现象中的内在性里面。并不仅仅子的神性取决于他与父的共同性,就连父的神性也取决于他与子的共同性;二者都只有在把世界更新为上帝之国的灵的统一中才是上帝。因此,上帝的统一性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先于位格的三重性。它仅仅生存于三个位格的共同性中;它之所以是有位格的,乃是因为三个位格中的每一个都是唯一的上帝。这也适用于诸位格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对神性的诸位格来说,唯一的上帝也是表现在其他位格之中的。他们就是这样相互颂扬的;只有如此,上帝才是真正的无限者,既内在于世界,又超越世界。
注释:
[i] 最早出自 T. Rendtorff:<上帝的彻底自律:卡尔·巴特的神学及其结果>,Theorie des Christentums,1972,页161 – 181;在此期间,这一命题又由于 W. Groll 关于 Barth 与 Troeltsch 之间关系的研究(《恩斯特·特洛尔奇与卡尔·巴特--矛盾中的连续性》,1976 )而得到证实和精确化。此外,在 Rendtorff 编纂出版的《自由之实现》( 1975 )中,它还和教会教义学的各种不同主题一起得到了探讨。
[ii] R. Weth 就是这样认为的。Weth/Gestrich/Solte:《国立大学里的神学?》,1972, 页46。但尽管如此,也是 Weth 借助于“基督学的自律”这一术语,与近代人类学的自律相对立,但又“批判性地相对应”,刻画了 Barth 的地位(页49以下)。
[iii]最近,T. Rendtorff通过他对教会教义学洗礼学说的诠释指出了这一点:<教义学的伦理意义>,Die Realiesierung derFreiheit,1975,页119以下。关于这一问题,注(1)中所提到的 W. Groll 的著作也在说明Barth 的开端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iv] K. Barth:《罗马书注释》,第2版,1922,页213。
[v] T. Rendtorff:《基督教理论》,1972,页168。
[vi] K. Barth:《上帝之言与神学》(讲演集Ⅰ),1924,页171。
[vii] K. Barth:《全集》,第5部,第4卷,页245和页253 – 254。
[viii] K. Barth:《十九世纪新教神学史》(1974),第2版,1952,页371。
[ix] K. Barth:同上书,页375。
[x] G.W.F. Hegel:《精神现象学》,Hoffmeister 版,页45。
[xi] G.W.F. Hegel:同上书,页72。
[xii]《新教神学》,第26期,1963,页340。
[xiii] I.A. Dorner:《论文集》,1883,页28以下,特别是页30。
[xiv] Schelling:《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演》,1803,第8次讲演。
[xv] G.W.F. Hegel:《宗教哲学讲演录》,Lasson 版,第4卷(绝对的宗教),页57。
[xvi] Hegel 称自我意识为那种精神运动的“永恒例证”;同上书,页61。
[xvii] G.W.F. Hegel:《精神现象学》,Hoffmeister 版,页528 – 529。
[xviii] K. Barth:《基督教教义学》,1927,页141。
[xix] K. Barth:同上书,页127;参见《教会教义学》,Ⅰ/1,页312以下。
[xx]《黑格尔全集》,纪念版,第16卷,页197。
[xxi]同上书,页198。
[xxii] G.W.F. Hegel:《宗教哲学讲演录》,Lasson 版,第4卷,页57。
[xxiii] K. Barth:《新教神学》,1947,页377。
[xxiv] J. Muller:《关于罪的基督教学说》(1838),第1卷,页552;第2卷,页195。
[xxv]在这个问题上,请参见作者的《上帝观与人的自由》,1972,页106以下。
[xxvi] K. Barth:《新教神学》,页524,参见页529。
[xxvii] K. Barth:《基督教教义学》,1927,页108。
[xxviii]单纯引入唯意志主义的联想(如上文注19之后所引用的陈述)也不够,因为 Barth 由此当然不能否认:上帝只有在子的他者中才拥有自己本身,这亘古以来就属于上帝的父性。至于上帝乐意这样,在此并不意味着还可能是另一种样子。逻各斯是上帝之子,乃是出自本性,而不是根据神的意志决定才如此。
[xxix] G.W.F. Hegel:《逻辑学》,Lasson 版,第2卷,页220。
[xxx] 预设这一事实,在这里只是应该被当做先行于设定的东西,它相对于设定并且为了设定而表现自身为这样的东西;而且不能马上在 Hegel 的反思分析的意义上把它解释为在自己这方面被设定的、从而追溯到一个主体的设定的东西。至于它通过设定而表现为一个先行于设定的东西,只不过是设定在它里面的折射。
[xxxi] G.W.F. Hegel:《宗教哲学》,Lasson 版,第4卷,页39,参见页37。
[xxxii] G.W.F. Hegel:《宗教哲学》,Lasson 版,第4卷,页57( Hegel 的手稿),参见页71( 1824 年的讲演)和页75( 1827 年的讲演),以及页61(参见页72,特别是页81 )。J. Splett:《 G.W.F. 黑格尔的三位一体学说》,1965,页149 强调了爱的思想和与 Hegel 的精神概念紧密相连的“把爱扬弃在认识中”的“基本决定”之间的张力。他正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把神性位格的多重性扬弃在一个唯一的位格中,是否与此有联系(页150)。当然,Hegel 没有意识到爱的思想与自我意识“永恒例证”意义上的精神的思想之间的张力。他并没有自觉地把爱的思想隶属于精神或者概念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在感受的领域里,把爱当做概念的逻辑结构的表述来探讨,就像1824年和1827年的宗教哲学讲演笔记(同上书,页71和页75)以及与 Hegel 的《哲学全书》第159节相对应那样,然而,在Hegel 的宗教哲学讲演手稿中(页57),爱的概念在描述概念自身的逻辑结构时,是与精神处于同等级别的。但恰恰这一点也表现出,Hegel 没有意识到爱的思想与自我意识的独白式结构的结构差异。因此,正文中的阐述(例如我的《基督学基本特征》所已经包含,1964,页183 - 184 )用 Hegel 从爱的思想出发对上帝的统一所做的论证--连同他对三位一体诸位格的位格性所做的辩护,这里涉及到三位一体诸位格的统一--来反对在 Hegel 本人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论证趋势。
[xxxiii]当然,根据 Hegel 自己的观点,位格是主体的概念已经以三个三位一体的“位格”为基础,这三个位格中的每一个都通过在其他位格中与自身同在而实现自己为具体的位格。因此,F. Wagner 是这样解释 Hegel 的思想(《宗教哲学》,Lasson 版,第4卷,页75)的:“且不说三位一体诸位格的位格共同性,就他们的逻辑结构来说,他们是个体性的品格”(《费希特和黑格尔论上帝品格的思想》,1971,页249)。W. Kern (《神学与哲学》,第49期,1974,页82 – 83)指责说,这一解释“径直……通向一种三神论”;Wagner 之所以避免做出这种指责, 只是因为根据他的解释,作为品格的主体性概念同时也是个别的,并且“作为个别性是普遍的”(页246),以至于在个别性的逻辑概念中,包含着 Hegel 不仅能把三位一体理解为普遍的概念(或者主体),而且同样能够把它理解为三个位格的统一的理由(页247)。与此相应,作为个别性的品格的逻辑结构与其实现不同,可能处于具体的位格、主体之中(页250- 251)。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绝对者的绝对者,就必然如 Wagner 事实上为《精神现象学》作辩护所断言的那样,是非位格的(页257以下)。 绝对者不是位格, 充其量是品格的结构。与此相反,Hegel 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已经把绝对者设想为主体,从而也就是“有位格的”。即使没有这里依然缺少的三位一体内部的位格差异,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已经完成了决定性的、 克服 Fichte对上帝品格的批判的步骤,主体被理解为不是通过它自己的它物所限制的(从而是有限的),而是在它物中与自己本身同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从绝对者的主体性通向绝对者内部诸位格的多重性的另一步骤,作为对在自己的它物中与自己本身同在的主体的结构的阐述,是 Hegel 所追求的。但事实上,Hegel 在关于如何在诸位格的相互关系中获得具体品格的描述中(Lasson 版,第4卷,页75),展开了一个超越他的主体哲学的思想,这就是,诸位格的身分只是从那些事后被称之为“位格”的东西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才建构起来的。在此,诸位格的位格性的根据恰恰不再是:“且不说它们的位格共同性,就他们的逻辑结构来说,他们是个体性的品格”。若不然,就会像W. Kern所指出的那样,在实际上出现一种三神论,或者--鉴于三个位格与唯一绝对者的主体性的区别--一种四神论。在这个地方处于 Hegel 的思维之中的张力,超出了他的绝对者即主体的观念,理应开放性地、而不是强制性地获得一种仅仅以抽象为代价的统一思路。毋宁说,这里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把 Hegel 在意识所指称的内容和事实上对于意识来说已经成为内容的内容之间所做的区分,运用于他自己本身。
[xxxiv] J. Moltmann 与自己的十字架神学相联系,援引上帝、父、子、灵之中的诸位格的区别,批判有位格的上帝的有神论思想,称其为“一个投影到天上的位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972,页234)。由此,他在实际上是用古典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这种学说只知道上帝的品格是三位性,而唯一神性的本质自身则不是位格--的上帝观,来反对西方基督教中自奥古斯丁的心理学三位一体诠释被原则化以来通过安瑟尔谟的独白而发展的基督教有神论。当然,由于 Moltmann 把这一对立扩展到一神论本身(页230以下),他为自己招来了主张一种三神论的指责(参见 K. Rosenthal:<关于当代研究三位一体学说的说明>,KuD 22,1976,页132 – 148,特别是页 146 以下)。恰恰是在古代教会神学的意义上, 三位一体学说应该被理解为一神论的基督教形式。它必须被直截了当地解释为彻头彻尾的一神论的形式,--对于基督教信仰与犹太教的上帝观以及与伊斯兰教的上帝观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奠基性的任务。三位一体学说是彻头彻尾一神论的,因为它并不仅仅以柏拉图的方式( platonisch )把上帝设想为与多对立的一,从而也不是在与世界的纯粹对立中设想上帝,以至使世界或者至少使物质作为上帝的对立者,赋予它一种实际上是神性的身分和原初性。虽然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包含着上帝与世界的对立,但它马上就超越了这一对立,并且只有如此才最终既维护了上帝的统一性,也维护了上帝的无限性。在基督教有神论中,三位一体上帝观的这种独特性是从属于西方关于一个唯一神性主体、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的自我展开的神学和哲学的,上帝有位格的统一在这里显得比三位一体的诸位格更为原初。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不同,基督教的一神论却陷入了有神论转化为泛神论或者无宇宙论的二重性。相比之下,使三位一体学说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一神论的条件这一任务,又重新提出来了。
[xxxv]在其他关联中,我本人也用自我实现的范畴来说明神的作为。但在这方面,首先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被描述为上帝的“自我实现”,其次,这一情况之所以发生,乃是鉴于这一范畴表示着出发点与结果的一种同一性。它由此而恰恰挣脱了上帝自我展开的唯心主义观念。
[xxxvi]与此相关的,还有把经院哲学的“纯粹现实”(actus purus)概念重新解释为绝对主体的纯粹活动的独特做法。
译者介绍

李秋零 / 教授
李秋零,1957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博士。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2年毕业后赴联邦德国,先在弗莱堡歌德学院学习德语,后到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哲学,1985年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院)任教至今,并于1991年在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李秋零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神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学术专著,并翻译出版5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文字逾1000万,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康德的全部学术著作翻译为汉语,即《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340余万字)。李秋零教授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此外,李秋零教授多年来也致力于潘能博格神学思想作品的翻译和介绍。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官网:http://isbrt.ruc.edu.cn/index.php?type=yanjiurenyuanview&id=2472
往期文章
曾劭愷|巴特《哥廷根教理學》的主體–客體辯證: 宋明儒學與歐陸神哲學批判比較
鄧紹光|潘霍華與莫特曼對巴特上帝的主體性的批判
瞿旭彤|普遍與特殊:從蒂利希與巴特一九二三年的爭論看兩人神學立場與進路的差異
瞿旭彤 | 比自由神学更自由:试从巴特对神学实事性和科学性的探讨看其神学与自由神学的差异
关注我们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编辑:语石
校订:巴特研究、Imaginist、Lea、Vanci、Kimeikei、伶利、Iris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