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亚伯拉罕·凯波尔的定义:原始阶段的宗教,很难与政治、法律、经济、艺术、科学等如今划分为“社会生活”的事物截然分开。

注: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 1837~1920),荷兰政治家、新加尔文派神学家。
就好像襁褓中的龙凤胎,仅凭外表,尚难以区分他们当然不同的性别。这种难以区分,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持续到青春期之前。不过青春期一开始,他们就会分开,从此沿着不同的路径,独立走向各自的成熟。
这一定义与意象不光针对宗教与政治,也可应用于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经济等关系。譬如,在一个宗教甚至还不能与巫术分开的国度,却希望它的宗教能率先和政治分开,不啻于要求尚未断奶的孩子去行使公民权。这并非不能是“巨婴国”的可能定义之一。
若仅以政教关系为例,则需要进一步指出:原始形态的政教关系,和终极形态的政教关系,一定是也理应是大一统的政教合一。但在从统一到统一的漫长历史路径中,政教则理应分开,也一定会分开。
就像未有天地之先,三位一体的上帝本为一统;无有天地之后,上帝与选民又成一统。但在天地之间、时间之内,巴别塔下被天使变乱的口音,不能统一;各按海岛邦国居住的诸族,不能统一;多样化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不能统一。
而历史证明,任何强行统一的尝试,都会打着“历史终结”的旗号,实质上退回到未有历史之先。貌似最美观的理性设计,一次次把人带入非理性的血海深渊。
虽然如此,仍要指出,从政治学或基督教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最理想的政体的确是君主制——只要这个君主是上帝本身。正如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C.S.路易斯曾说,甚至奴隶制都是很好的——只是人间无人配当奴隶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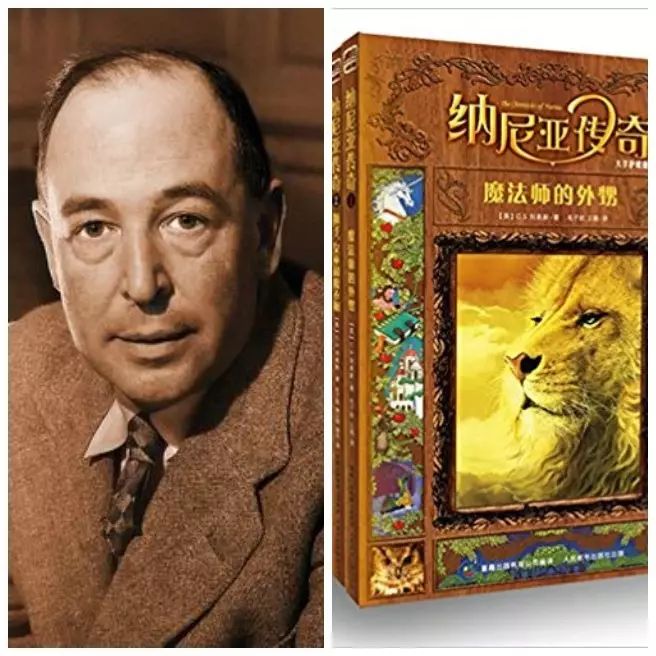
注: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知名作家、护教家。著有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等、神学作品《返璞归真》、《四种爱》、《人之废》等。
即或你不能接受基督教人论中“人性全然败坏”的前提,但由此推导出的“权力必须被制衡”的结论,想必可以并且已经得到你的承认。这也正是宗教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指出政教必须两分(我们先不谈此两分是“分离”还是“分立”),否则单一的绝对权力必然带来双方的绝对腐败。
如果政教不能两分,则只可能有三种形态的政体:一种是中古之前的欧洲,天主教会控制政府;一种是直到如今的俄罗斯,政府控制东正教会;一种是自古以来的原教旨伊斯兰国家,政教直接合一。
至于“政教合一”带给你的印象,究竟是“神权政府”还是“强权政府”,就要看你本人的认知体系和默认前设了。正如在数学意义上,从左右两边逼近的零,涵义并不相同。或者说同为无神论,但犹太背景的无神论和中国背景的无神论,“无”的涵义也大不相同。
但无论你的分辨力和分辨率究竟如何,“政教合一”与“政教两分”的明显不同,还是非常容易识别的。
而政教两分的概念,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历史上,都来自圣经和教会。
在旧约历史中,亚伯拉罕身为族长,却要给大祭司麦基洗德奉献并受他的祝福,已经显明政教两分原则。摩西虽为先知和领袖,但仍有大祭司亚伦为辅弼或曰制衡。纷乱的士师(军事领袖)时代之后,扫罗、大卫相继称王,但王室从来都不能僭越宗教权柄,撒督的祭司谱系和拿单的先知序列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虽有弱势时被恶王欺凌之危,但以利亚等指斥君王的先知和耶何耶大等除灭僭主的祭司也一直不绝如缕。被掳回归之后,行政长官尼希米、所罗巴伯和宗教领袖以斯拉、约书亚的并立,再次显明政教关系在神意历史中的应然走向。
到了耶稣和使徒年间,罗马这一亘古未有之强权的出现,使得政教关系成为新约也需要阐述的重要主题之一。
其首要原则,就是两千年来不断被引用或误用的耶稣名言: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当归给上帝。
这句话明显确立了“政教两分”原则。保罗和其他使徒在进一步的阐述中,明确了政府具有“刀剑的权柄”,即外交、军事、治安、行政、税收等公共事务的权柄属于政府;而教会具有“属灵的权柄”,即人的灵魂、良心、信仰等宗教事务的权柄属于教会。政府和教会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所以两者应该以既制衡又互助的关系共同却又分别承担上帝赋予他们的不同使命。
不过早期教会对此的认识显然不清。从君士坦丁开始,教会越来越依附帝国。东西教会大分裂后,东方教会(东正教)延续了这一路径,直到如今。西方教会(天主教)则幸运地经历了罗马城的陷落,“罗马陷落犹如耶路撒冷再次陷落,促使人们思考普世帝国与大公教会的真正关系,第一个成果就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世界之城 ’学说的提出,而后世加尔文的政教分立观是此双重世界观的更新和完善(王怡)”,同时见证了诸蛮族的皈依,从此教权在乱世中一跃成为无所不包的大一统式最高权柄,甚至对各国国王都可生杀予夺。于是教廷开始加速腐败,最终催逼出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自始至终的主要动机固然都是为了恢复纯正信仰,但支持他的各位选帝侯就不能不考虑趁机摆脱教皇的巨大政治经济诱惑,正如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很难说有比企图合法离婚更充分的理由。但这些历史的芜杂仍足以显明隐秘的神意,其中一点就是:统一已死,多元当立,时候已到,政教两分。从此各个宗派兴起,民族国家林立,欧洲特别是西北欧开始向世界输出秩序,将人类带入文明。
而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和教会内部,政教两分的具体实践又进行了不同方向和程度的探索。
探索的结果主要有两个。简言之,今日所谓“政教分离”,不过是新教中重洗派的口号,并不能代表其他宗派的立场。而真正深刻影响了荷兰、瑞士、苏格兰、英格兰、美国等国家和教会的改革宗(加尔文宗、归正宗),其政教观应当被正确地描述为“政教分立”,其具体含义正如改革宗纲领文件《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第23章《论政府官员》一节所述:
国家官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亦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然而国家官员如同保育之父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份的各方面,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并且,耶稣基督在祂的教会中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它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作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利的行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致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侮辱、暴力、诅骂和伤害;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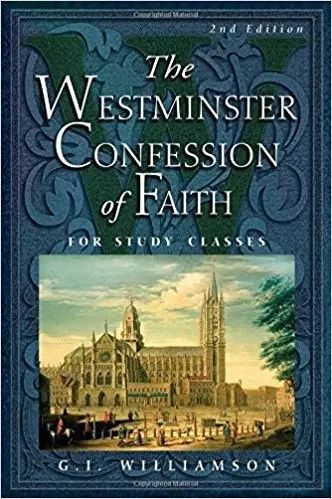
所以,同样的“政教两分”,各宗派的强调重点相当不同。重洗派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翼,他们的政教观更强调“分”。相对而言,以改革宗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政教观,更强调的毋宁说是“两”。强调“两”就隐含着“分立”,强调“分”则预示着“分离”。
重洗派的“政教分离”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浸信会,以至于他们的教会观也是“独立制”,即便本宗派内部的不同教会也应尽量疏离;改革宗的“政教分立”思想则影响到以长老会为代表的诸多宗派,长老会的教会观也是启蒙了邦联制和联邦制的“区会制”,强调在独立基础上的彼此自愿联合。
容易看出,改革宗的观点恰是在大一统的天主教和大分裂的重洗派中间,比天主教“左”,比重洗派“右”,比天主教“分”,比重洗派“合”。对应到宪制与政体,则可以说天主教对应君主制,重洗派对应民主制,改革宗对应共和制。
不过需要承认,如果说右翼的改革宗曾经深刻影响过早年(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那么左翼的重洗派就曾经并且正在影响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美国,这和二百年来世界整体左倾的趋势是一致的。1960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近年的约翰逊修正案,貌似明确了“政教分立”,实际上是确定了“政教分离”,特别是与基督教分离。直接的后果不过是高举起政治正确的、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方向,从此基督信仰被驱逐出公立学校,即便基督徒也不能在学校里祷告。从此政治议题被赶下教会的讲台,牧师甚至不可以对本教会的会友发表基于圣经的政治观点。
所以,川普在2017年5月4日的全国祈祷日签署的宗教自由行政令,不过是对早已偏离“政教分立”真正精神的美国法律的一次归正。行政令中说,现在的政府政策是“保护和积极促进宗教自由”,现政府将让美国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以身作则”,“把发声的权利还给我们的教堂。”——仅从文本意义上,这的确是对从使徒到威斯敏斯特的圣经政教观的回归。

“政教分立”还可借用凯波尔的另一段话来说明:
当政府允许教会在自愿的原则上按它们自己的能力成长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就很顺利。这不是沙皇俄国式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政府,不是罗马教庭那样要求政府屈服于教会,也不是路德宗的法学家们对公民在承认信仰上的要求,更不是法国革命式的无宗教立场。唯有一种自由国家里自由教会的体系才是加尔文主义所尊重的。政府的主权与教会的主权共同存在,相互制约。
身为神学家和政治家的凯波尔,后来在他担任荷兰首相期间就践行了这一理念。“共同存在、相互制约”,才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教两分原则的正确解读和实践方式,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中,这一原则已经并将不断证明,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假扮上帝的强行一统和架空上帝的自由散沙,永远是两种最糟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