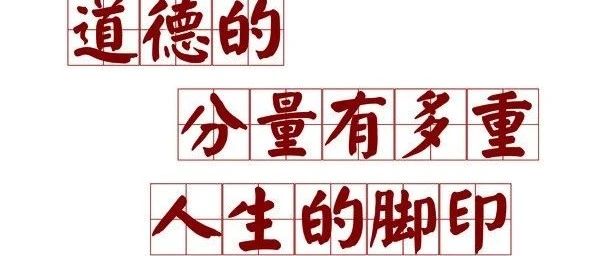《列子》记载一则寓言:一王者夜夜梦作苦工,劳倦不堪;一工人夜夜梦为王者,其乐津津。此王愿和工人互换生活,但工人拒不接受。
王日间所享受乃肉体物质生活,其夜间梦境虽虚,却是内心或说心灵生活,此生活虽虚假,但内心感受却是真实。正如同为饮酒,但有人欢乐,有人忧愁,酒虽同但人心却不同,外相似而心迥异。
人生有三态:一为幸苦忙碌而不知为谁,到头一场空;二为沉溺于物质生活中醉生梦死难自拔;三则能将心放在恰到好处,但有待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去参究领悟。
宋人讲过另外一个小故事:一解差押送一和尚,途中和尚将解差灌醉后易服逃脱,待解差醒来,身上穿着僧衣,一时糊涂竟大叫“和尚犹在,而解差却走失了”。
可见,若一味地侍奉肉体,自我很快就会迷失,亦可说此人心已迷失。因此,有志者首先将心放对地方,心若安排妥当得救,再来整理外面,才有所谓的主人意识,既人格。
先秦诸子各派大致都在讲这方面的道理,人人都想立功名获财富,但若把自己的人格丢了,这个人就彻底完了,何况人格本来也不会抹杀功名和财富。因此若失去人格去争功名利禄,心就会无安放之处。
心若要有安放之处,首先要有敬畏之心,世界各大宗教尽管不同,但都教导人应有谦逊敬畏之心,若将自己当作自高无上的主宰,必导致狂妄自大。
其次,就是不能将人物化,其结果人对人无情无义,只知道彼此利用,没有宽恕之心, 此人对物之乱用结果。
再次,为人之道,即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在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最透彻,一个“仁”字足以,
最后,对己,不懂得己难懂对人之道。《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生是一门大学问,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很多时候人们并未从这所大学校毕业,而是请长假或休学。人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层;
第一,职业,古今涵义不同,“职”人人都有,父有父职,子有子职;有“职”必有“业”,慈是父业,孝是子业。近代社会职业偏向生产谋利,不同于古代之“职业”。准确地说,现代人有“职”,但“业”很少。不管怎么说,先求一职而生活,故为第一层。
第二,闲暇人生,即我们常说的业余生活,生活之乐趣大多都给予自由闲暇中,而非职业工作中,不论人品贵贱,都可以在闲暇中尽情自我,但因个体职业不同,所以自由活动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玩物尚志,但闲暇并不等同于玩物,而且历史上很多所谓的丰功伟业亦都出自闲暇生活,反而很少在职业中产生。
因此,每一人固然需要一职业谋生,但也要学会合理利用闲暇人生。正因为它不为工作规范所约束,所以更应该人人留有这样的时光。也有人称它为艺术人生,工作人生基本相似,但艺术人生却是个别的,若不注重此艺术人生,乃为人生一大憾事。
第三,理想人生,不管是职业人生,还是艺术人生,毕竟都是眼前现实的人生,若长期陷在眼前现实中,容易厌倦堕落。若要救此弊病,须在现实人生外有超现实的理想人生,甚至职业和闲暇都应该受到理想人生的指导。
现实人生多物质,理想人生则是精神。前者关注当下,后则充满想象,没有想象的人生难免会心生厌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羡慕的优秀职业人反容易抑郁,甚至自杀,一方面可能闲暇人生被剥夺了;另一方面又没有所谓的理想人生。理想有属于个人的,也有群体的,如民族理想,亦大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虽不靠谱,但却极有蛊惑力。
第四层,最后一层是道德人生,或真理人生。不论理想还是现实,人生都必须道德。人生甚至没有职业、没有自由、没有理想都可以,但不能没有道德。所以,我们讲人生、讲真理,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遇,都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即良心让人放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