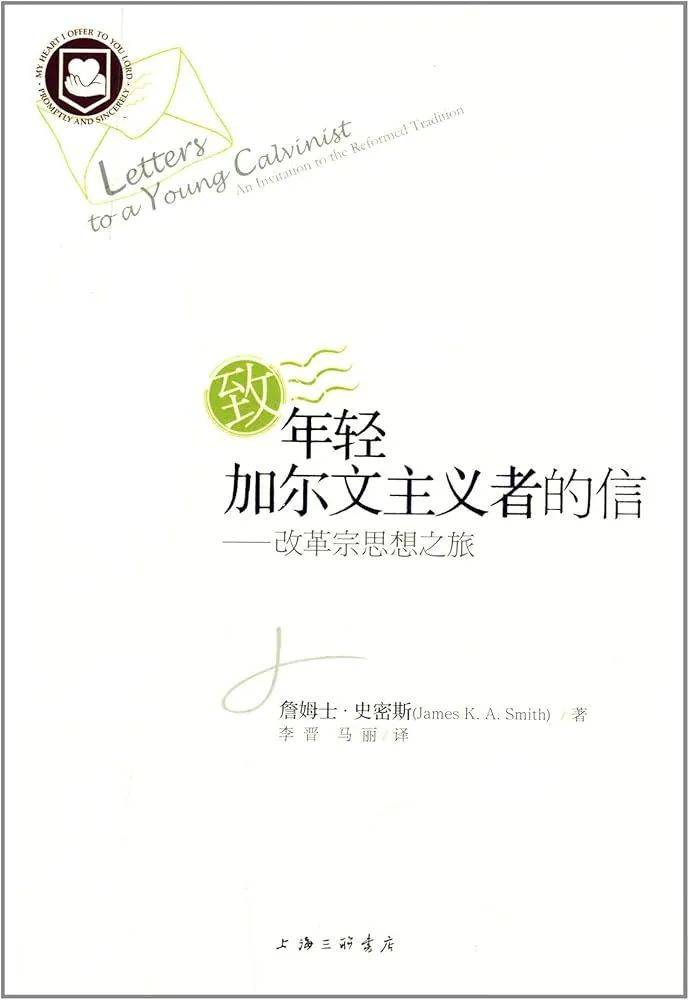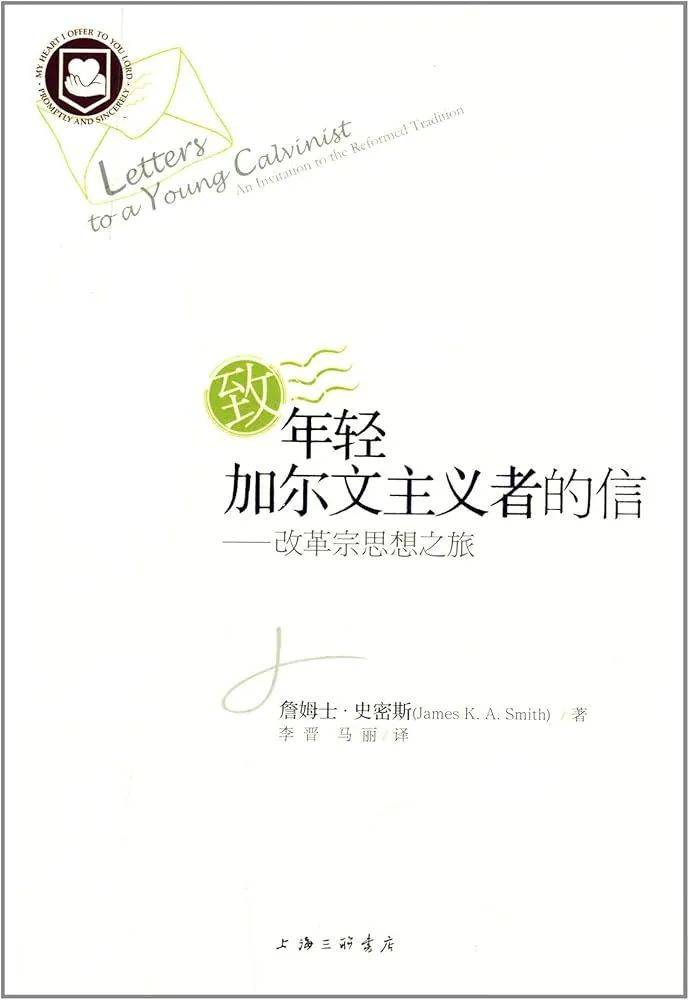我期望你会渐渐感受到,加尔文主义首先不是一个神学体系,而是一种灵性,一种敬虔,正如清教徒所说的那样。(我记得这是巴刻在他一本非常精彩的书《敬虔的追寻:清教徒的基督徒生活观》中描述的。)改革宗传统不是一种知识框架,使我们成为“聪明”的基督徒(让我们瞧不起其他“愚笨”的基督徒)。这传统也不是一种让人羡慕其一致性和神学之美的神学复合体。它首先、也是首要的,在于表述出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呼召人作他的门徒。
如果加尔文主义不能产生一种生活方式,以便让上帝的恩典可以在一群人的生命见证中活出来(这是一群先品尝到上帝那将要降临之国滋味的人),那么,这种加尔文主义就一文不值,它只不过像“鸣的锣、响的钹”(林前 13:1)一样。
如果有一种加尔文主义,它没有回答《海德堡要理问答》中的第一个问题:“在生与死当中,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那么,这种加尔文主义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溺爱我们、向我们讲甜言蜜语的神学框架。我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加尔文主义不能转化为一套信仰实践,不能使我们拥有鲜明的特征,以证明我们是一群独特的、为上帝所收养的“儿女”(我们互为弟兄姊妹),那它就不值一瞥。
正如我先前说到的,我感到《威斯敏斯特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以及《比利时信条》之间存在差别。后一类的(欧洲大陆的)信条具有一种存在性的精神,似乎渗透到我的灵魂中。相比之下,这是更有逻辑性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所不具备的。
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威斯敏斯特的神学家们,而是为了强调我之前所说的一点,那就是改革宗传统的大公性。你一旦有机会,一定要通读一遍《海德堡要理问答》,再去阅读《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然后告诉我,你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感觉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我不是要你像在奥普拉(Oprah)脱口秀节目中作客那样告诉我什么。我的意思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读,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确会有一些不同。最后还要告诉我,你发现的差异是什么。
让我来给你一些提示:《海德堡要理问答》借着阐明《使徒信经》来清晰表述必须被相信的福音。然而,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并没有出现《使徒信经》(我知道有些《小要理问答》版本附上了《使徒信经》,但并不是作为核心内容加进去的)。
为什么这一差异值得注意呢?我认为这一差异指向我们最近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海德堡要理问答》把《使徒信经》放在要理问答的核心位置,把《使徒信经》作为对福音的一种简洁、忠实的总结,这表明该信经把传统作为一种上帝的恩赐来接受,也因此将自身置于大公教会中(当然,这也正是《使徒信经》本身所宣告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这等于是将我们自身视为一种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受惠于与历代圣徒相通,并且因此与那些我们之前的信徒成为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要比我们这一群人大得多(遍及全世界的信徒都认信这一信经)。我认为,这一属灵情感非常重要,却显然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缺失了。
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也解释了我先前所暗示过的。让我尝试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我希望不会太有争议性。请对我有些耐心,让我来详细地表达清楚。
我们这样说吧:对于你正在收听的加尔文主义的广播节目,你正在阅读的那些书籍,以及你经常参加的那些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聚会,我要说,他们都是威斯敏斯特加尔文主义者。我当然不是说这本身有什么不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传统只是改革宗传统的一支,它有独特的重点和所珍视的关切。这一支传统特别清晰地阐明了改革宗信仰对于福音的理解,但是我认为在这一脉中,可能存在非常重要的缺失。
事实上,它所缺失的正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核心关切(更不用说奥古斯丁了),那就是对于教会的强调。或者,用我们过去讨论时用过的术语来说,就是威斯敏斯特一脉减弱了改革宗传统的大公性,因此,这一种加尔文主义仅仅阐明了那种范围狭窄的、经过提炼的救恩论。它的这种关切基本上能与各宗派背景分离开来,然后植入到形形色色的宗派(和非宗派)土壤中。所以,你才会看到我之前指出的那种奇怪现象:连像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那样的地方,也能成为加尔文主义活跃的中心。
现在,如果我们只用加尔文主义来指以 TULIP 为架构的救恩论——即只关注个人灵魂(“选民”)的得救——那么我承认,连浸信会也会采用这种救恩论立场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的确一点也不稀奇,因为我觉得这种救恩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最前后一致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圣经所描绘出来的图画(大家公认该救恩图画足以颠覆人的惯常思维)。但是,改革宗传统并非只是关于救恩论,因为宗教改革并不仅仅是修复救恩的教义。
以加尔文为例,对他而言,宗教改革不只是要使有关个人救恩的教义归正,也是要使教会论归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一个机构。在这方面,加尔文所关注的是教会敬拜的归正,因为他认为教会对门徒身份的理解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们都非常重视教会的结构以及堂会之间的关系。他无法想象会存在某种“自主自治”的堂会,如我们在浸信会系统和非宗派教会中所看到的那样。
确实,在他过世之前,由于对曰内瓦信徒生命牧养的特别关注,加尔文实际上确认了某种类似主教制的教会结构(这在他的《基督教要义》1543 年版中有清楚的阐明)。但是,至少宗教改革的一个贡献就是对教会治理结构(即教会的组织形式)的理解,改教家们认为这是从宗教改革所强调的事情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因此,对于改革宗传统而言,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怎样“做”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去敬拜,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加尔文还认为,福音的意义不仅超出个人得救,而且也超出教会治理,其意义一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归正。如果主是万物的主,那么基督就对万物拥有权柄(西 1:15-20)。非常有趣的是,对于加尔文而言,这一点并没有转化成对神权政治的偏爱。事实上,他在日内瓦的改革很有影响,显然塑造出了后来的民主历史。【具体可见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最近的一本书《权利的变革》。】但我们要留到其他时间再来讨论这一点。
在此,我所有的强调都归于一点:改革宗传统远远超过“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因为它的内涵超出个人得救的范畴。改革宗传统不只是救恩论,它也有教会论;不仅是教会的教义,而且是更新了的教会的具体活动,并将崇拜作为所有活动的中心。改教家们最根本的关切,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会采取何种样式。教会既是宣讲福音的场所,也是基督门徒成圣的地方。他们不认为教会敬拜仅仅关乎品味或偏好,他们也不认为教会组织只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此,他们一定想不到“有关恩典的教义”这一果子会脱离改革宗敬拜和教会治理的土壤。相反,改教家们看到一种敬拜的逻辑性,那就是敬拜是从人对罪和救恩的理解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那么,一个浸信会的神学院是怎样变成一个加尔文主义的温床呢?(不要马上向你的朋友们广播这一点)我猜想,改革宗传统的“威斯敏斯特化”,也许以某种方式移除了改革宗传统那幅广阔的图景。这个广阔的图景在我所说的大陆信条中依然保留着。而且,正因为改革宗传统(或加尔文主义)这种威斯敏斯特版在美国流行,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一些浸信会和非宗派的教会(这些教会都倾向于反对信经和圣礼)认为,他们可以吸收加尔文主义,而同时又不影响到他们的敬拜方式或教会治理。
我并不想在这一点上冒充行家。我只是想说,在我自己迈向改革宗传统的朝圣之旅中,虽然一开始勾起我兴趣的可能是救恩论,但一直维系着我的虔信的,却是改革宗传统更广的方面(其教会论和与文化的交遇)。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上帝以拣选论作为诱饵,待我上钩之后,他又把我拉进了教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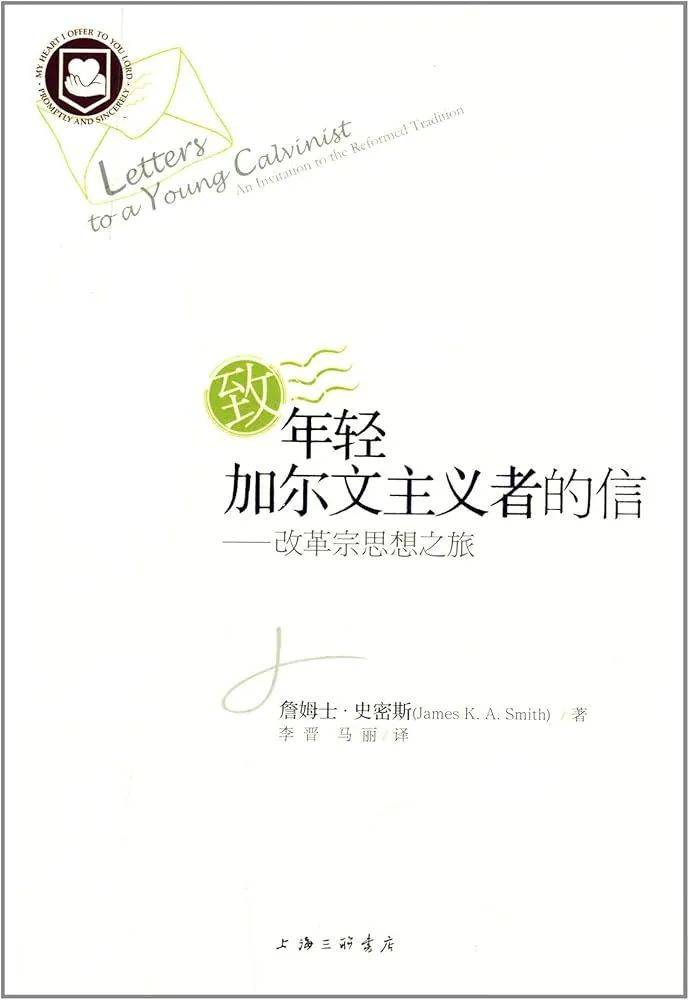
摘自:詹姆士·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李晋、马丽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购买链接:《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