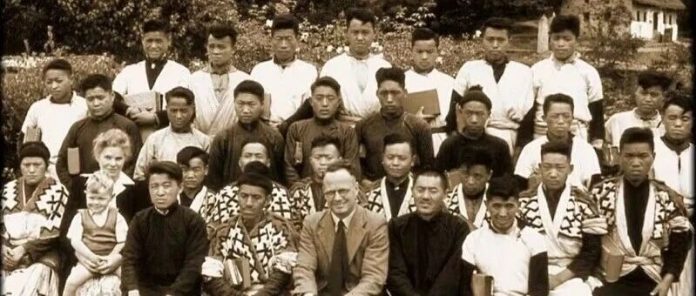關於阿卯在安順地區初接觸福 音的故事,我們許多人都能講出個大概來,但未必能講的更加詳細。或者,有的人講的比較詳細,但是每個人所講的內容又是有一些地方是不相同的。
許多的前輩記錄下了自己所了解的歷史故事,我們從他們的筆下了解了這段歷史的梗概。而且,歷史的敘述中也會因為所看資料的問題,呈現出不同的故事。有時故事的主人公會出現不同,有時某些橋段是添加的。對於阿卯來說,口傳歷史也是一種不斷在變化的故事。阿卯歷來善於講故事,而講故事,有時為了更加引起別人的共鳴或為了其他原因,在原本的基礎上又會添加了一些本沒有的事,這就使得”原生故事”變的更加撲朔迷離。再加上人的記憶有限,一代一代下來,其所述之故事總會有所改變。
近日看某著名大學的音樂系學生寫的有關阿卯基 督 教音樂的碩士論文,在對阿卯於安順初遇黨牧歷史的描述中,就感覺作者沒有好好閱讀文獻資料,把去昭通見柏牧的四人和在安順初遇黨牧的幾人混為一談。縱使是一篇對音樂的研究(其實這方面也研究的不咋地),但也應該注重細節問題。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可能我們大多數人,對這段歷史還不是那麼了解。我想這位作者也是在其他人的文章裡看到了,所以就借鑒過來了。
離那段歷史越近的文字資料,越接近真实的历史。那些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依然還是我們可以依靠的一筆豐富的財富。而且,透過不同作者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的研究比較,更能讓我們了解到貼近歷史的原本。在歷史發生的過程中,不同親曆者從自身角度對同一歷史的描述都會呈現出不同的看法。比如阿卯自身所口口相傳下來的版本,就會與傳教士所述的有所不同。而這不同,就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歷史的豐富性。對於當時的漢族人來說,他們深入苗區所能了解到的,可能又是另外的有差別的故事。
最近在閱讀清末民國時期有關”阿卯於安順得道”的諸多記載,甚是有趣。這些記錄者,有的是阿卯自己,有的是傳教士,有的是國人的漢族佈道者們。礙於各自了解的程度不一,他們筆下的故事也是會不一樣。不過,相比較於49年後的資料,它們顯得更加的寶貴,其一就是敘述者離那段歷史更近,所知道的應該較貼近歷史原本。比如某位不知名的作者者1907年在《通問報》上刊登的文章,對阿卯在安順遇到黨牧的歷史,就描述的比較詳細。
在國人開始重視邊疆佈道後,許多的沿海地區的人也來到邊疆落後地區,從而接觸了阿卯。在他們筆下,也為我們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記錄。當然,有些時候,由於作者了解的還不夠,所以難免一些錯誤。比如一位前往邊疆佈道的女佈道者周舜華女士,她在1918年的《興華報》上,就曾經對自己所聞的阿卯接受福 音的歷程有過一個簡短的介紹。
她說:……於一千九百零四年,有大隊苗人,往貴州省之內地教 會,至唐先生處,求彼至滇省傳道,唐先生因有多數要工未畢,需在貴州服務,乃囑彼至滇省之昭通縣,因該處亦有內地教 會……
周舜華曾在雲南佈道,她接觸過該地的苗族人,了解到了一些基本情況。她所說的唐先生,大概指的是黨居仁。雖然所述內容有些地方有差別,但可知她也在去了解這個地方的基本情況。對於黨居仁、柏格理等人來說也是這樣,他們都是一步步地去了解他們的禾場的情況的,這是一個基本功。诸如邵次明、陈铁生等中华国内布道会人员、中华基 督 教协进会的调查人员、以及边疆布道团、边疆服务部等的人员都曾深入过滇黔阿卯社会,为我们留下些”只言片语”。
在阅读中英文资料时,笔者也看到它们之间所描述的相同之处。对于英文文献来说,内地会一方的人所记载的更为详细,如Samuel. R.克拉克和党居仁两位。
從清末民國的文字資料中,我們可以填補更多缺少了的細節,從而了解到更多阿卯初信時的更多故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段歷史時期,處於偏遠山區中的阿卯,正在被國人所熟知,自己也在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阿卯於安順初遇福 音,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具有非凡意義的歷史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