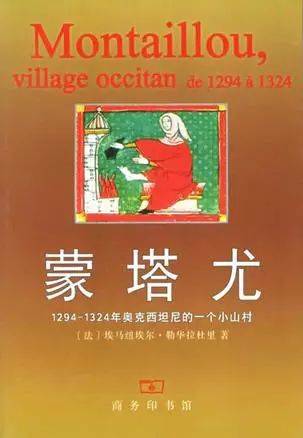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所谓一个时代在文化成就上的代表就只有单一的“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精英文化运动,并没有触及底层民众。新文化史所考察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数。伯克认为,“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另一些文化。因此,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研究的是一个小磨坊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研究的是一个小山村的居民。
其次,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都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

最后,新文化史重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伯克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早在1975年,纳塔莉•戴维斯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也“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通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他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都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占主流的还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以寻求历史的规律、客观地解释历史与社会为宗旨。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计量史学即是例证,它在美国表现为“克利奥学派”(cliomet rics) ,在法国是“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计量史学家们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研究模式,决定对历史研究进行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重要转折。标志这一转向的是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和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兹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表现出来,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格尔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存在的。因此,研究文化的任务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仪式、精神旗帜、观念、宗教等象征物的表达符号。
此外,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结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后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完善而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任何既定的状态中每一个要素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由与它相关联的并卷入这一状态的其他要素决定的,因此,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都是在结构中被赋予的。20世纪60、70年代,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固定于一种作为文化的词语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始终潜在地变化着。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被解构,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建构”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才存在。正是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发展起来了。
新文化史起源于法国。在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仍旧占着主导地位,他们继承年鉴学派开创的总体史的写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运用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但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反感,他们运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拓了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等新的领域,促成了心态史的繁荣。一批历史学家也经历了伏维尔所说的“从地窖到顶楼”的大转变。心态史可以看作是新文化史发展的第一阶段。阿尔方斯•迪皮戎在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中,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罗贝尔•芒德鲁在《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中,增加了对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的考察。此后,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巫术活动从被接受到遭到镇压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勒高夫在《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这篇名作中分析了“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探究了背后反映的人们心态的变化。乔治•杜比在《三个世界》中,探讨了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表象”三个概念。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利用时任帕米埃主教的富尼埃审判异端的审判记录,揭露了一个小山村居民面对爱情、婚姻、死亡的态度和宗教信仰。但这些历史学家并未把心态看作是完全独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相反,他们仍认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研究尚未脱离结构史的范畴。
70年代后期,孚雷和莫娜•奥祖夫主持对法国书籍史的研究,他们不是研究伟大的著作,而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和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达尼埃尔•罗什在巴黎七大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研究18世纪巴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80年代开始,皮埃尔•诺拉组织120位来自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撰写法国记忆史,出版了7卷本著作《记忆的场所》。在本书的序言中,诺拉写道:我采用新方法来写法国的历史,如果把法国定义为一个实体,那不是别的,完全是象征物的实体。这一系列著作和研究表明法国的新文化史已经脱离了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结构史”。
最终使法国新文化史彻底脱离心态史传统的是以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四代历史学家。80年代后期,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开始批评“心态史学”,他们认为心态相对于文化仍然过于狭窄,并不能涵盖人类精神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于是,他们明确指出文化与心态在概念上的区别,声称“社会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他们反对把心态看成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来看。因此,夏蒂埃提出,历史研究要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
与此同时,新文化史在美国学界也爆发出了强劲的势头。1984年,维多利亚•伯奈尔与林•亨特应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编写了一套“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系列”丛书。他们推出的第一本著作是林•亨特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到1999年,该系列一共出版了34本相关议题研究的著作。1994年,就在这套丛书出版10周年之际,以林•亨特为首的历史学家召开了以“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为主题的讨论会,在该次会议上,与会学者重新思考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并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进行文化研究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两年后他们又召开了“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历史学与社会学”会议,《超越文化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一书就是该次会议的成果。在本书的序言中,林•亨特指出,自文化转向以来,历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们把文化和社会的范式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文化史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法美学界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表明它已经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一流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探索的研究者,许多新文化史研究者也在著名高校获得了教职。但同时,新文化史研究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在西方史学界,一些历史学家已开始了对它的省思。林•亨特在1999年即已看到了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渐渐落幕。彼得•伯克在2004年的论著中更是写道:“新文化史也许将到达它生命周期的终点。”
正是由于新文化史是一场国际范围的史学运动,它并不局限于美、法等国,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在积极地简绍新文化史的著作,并有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新文化史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中国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气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国际范围内新文化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台湾学界也在不遗余力地引进和消化新文化史著作,蒋竹山在明清社会史和医疗史的研究领域有意地采用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参考阅读:
1.林·亨特《新文化史》,台湾,麦田出版,2002年。
2.陈恒编:《新文化史》,《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