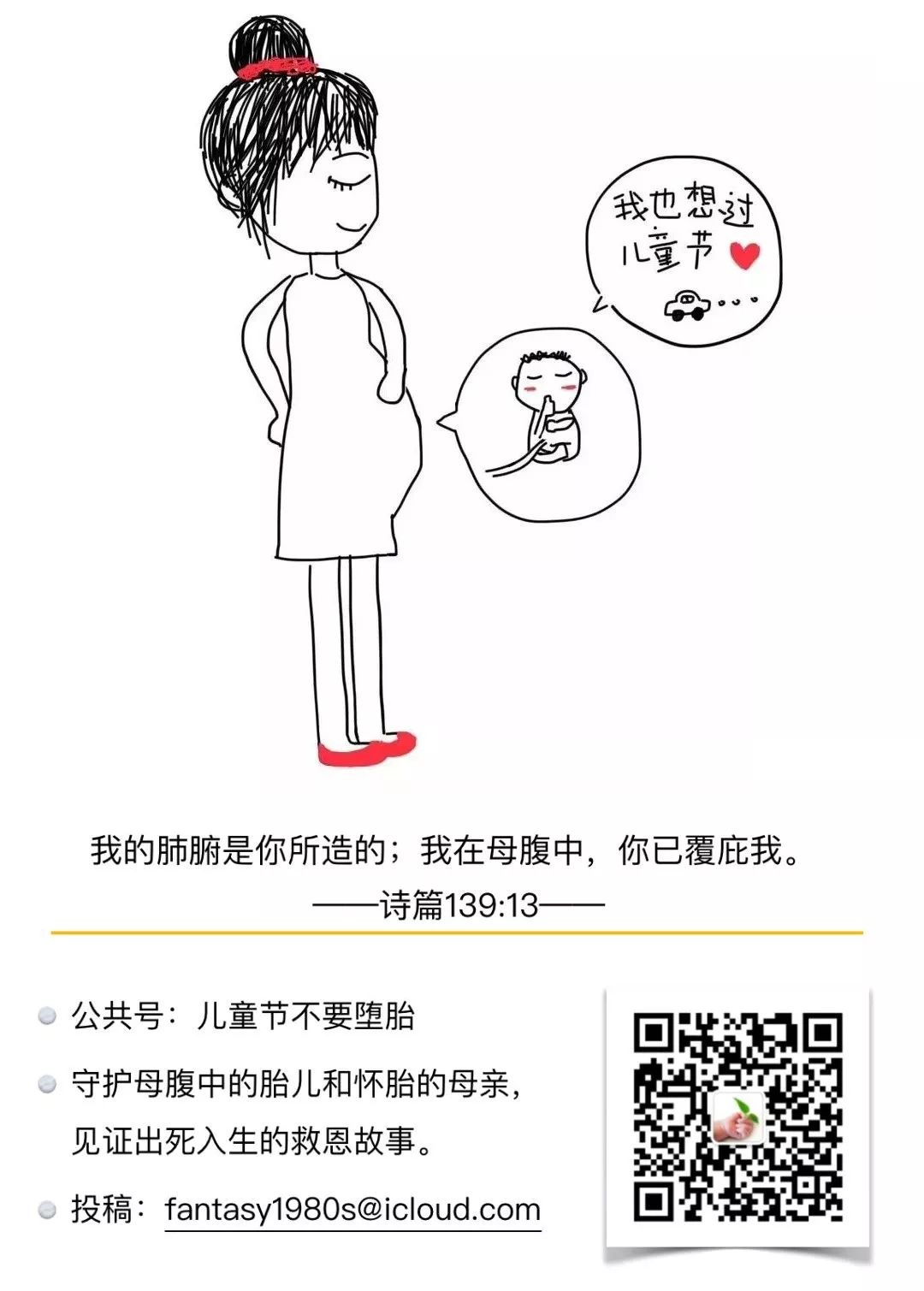朱厄尔斯·格林曾经选择了堕胎,并一度相信,只有堕胎能帮到那些面临困境的母亲,直到某天她再也无法说服自己……
第二章:最终选择生命
朱厄尔斯·格林
圣诞节之前的三周,我发现自己第一次怀孕了。然而,听到这个消息的感觉,可不像拆开一份早到的礼物,而更像是九岁那年,我发现妈妈藏礼物的地方,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我当时仔细地、悄悄地、慢慢地打开了用闪亮的红色纸包裹的长方形大盒子:我做梦都想要的帕克儿童显微镜和科学仪器就放在里面。我打破了本来的规则,提前发现了我想要的礼物,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有点太早了。
当我发现17岁的自己——未婚,吸毒,高中辍学——意外怀孕时,我并没有觉得堕胎是选择之一。事实上,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准妈妈了。我停止了吸毒,并且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名字是《未成年人怀孕》。我开始读这本书,为成为父母做准备,而且安排了第一次产前检查,并打电话给当地的公共援助办公室,学习如何申请医疗救助,为抚养我的孩子做好准备。
然后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每一个我深爱,并且信任的人都希望我堕胎。我感到窒息,感受到他们的无情,感到孤独,感到被困住,感到被抛弃。
我从电话簿中拨打的第一个号码不是堕胎诊所,而是播放的一段录音:“当您的第二次例假没有按时来到的时候,您的宝宝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然后我听到了一串微小而迅速的胎儿心跳声——“砰,砰,砰,砰,砰”。接下来,这段录音讲述了堕胎的恐怖,并讲述了一位两个孩子母亲的故事——她奔向堕胎诊所,然后在那里流血而死。我拒绝去想这样的结果,我被吓坏了。但我的心变得冰冷,我的信心崩溃了。
我让我男朋友带我去堕胎诊所。抽血、咨询、付钱之后,是脱下衣服进行手术的时候了。我跑出了办公室,希望能拯救我的宝宝。两天后,怀孕九周半的我做了堕胎手术。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不是手术过程,而是心理的冲击。在术后的两天中,我一遍又一遍收听那个支持生命的电话录音,录音中的心跳变成我内心痛苦的咒语,我随时都能听到那个:砰,砰,砰……然后戛然而止。
就在我堕胎几周后,我试图自杀,最后在青少年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月才康复。心灵是一个黑暗的泥沼,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很容易失去立足点并跌入裂缝中,灵魂陷入困境。
在我自己的创伤性流产经历的短短几个月内,也就是在我从精神病院出院数周后,我发现自己出现在当地的一个去往华盛顿特区公交车游行中,主题是支持堕胎权。游行后不久,我开始志愿为孕早期堕胎的女性做诊所护送(不是我堕胎的诊所)。
我盲目地把自己拴在与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完全相反的立场上,这使我免于进一步的内心动荡。我尝试说服自己堕胎没有错。当我向一间堕胎诊所求职的时候(我曾在那里做过志愿者),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到为什么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一名优秀的堕胎诊所工作人员。那篇文章中,我分享了自己堕胎经历(完全没提到内心所有的矛盾,胁迫,情绪漩涡),还分享了我对于争取堕胎选择权的热情(我在华盛顿游行过!)以及我为何认为这些经历,能够让我成为堕胎诊所工作的最理想人选。这篇文章真的很有用,我被录用了。
我完全接受了曾经伤害我的观点——选择堕胎在某种意义上与女性平等有关;生下孩子,为不想要或者“不合时宜”的孩子制定收养计划(而不是杀死他/她)对孕妇来说是一种负担;如果堕胎是非法的,无数妇女将死去。
在我里面那种对堕胎经历,对失去的孩子的渴望,慢慢地发生压抑、遗忘、忽略和扭曲。让我逐渐成为一个刚硬倔强,且内心封闭的堕胎权倡议者。
在我为堕胎诊所工作的五年里,我做过除医生和护士外的几乎所以工作。我甚至每天早早来到诊所清扫门外的地上散落的雪茄烟头,周日去帮忙粉刷员工浴室的架子。我的书法作品挂在接待室的墙上:“去投票吧!选择支持堕胎权的官员!”。我热切地接受新的挑战,当时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高压灭菌器技术员。高压灭菌器看起来像一个超大号的微波炉,作用是给手术仪器消毒。高灭菌器的技术操作人员,其实就是“高级”清洁工,清洁沾满鲜血的金属仪器。
高压灭菌室的另一个作用是:为被流产的孩子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数点并重新拼接被堕胎的孩子的身体各部位,以确保堕胎是彻底的。如果孩子的任何身体部位留在子宫内,都可能导致感染。那些罐子连着抽吸器,每次堕胎手术后,连接在抽吸器上的罐子就会与抽吸器分离,然后通过墙壁上的小窗户送到灭菌器操作人员那里。
在高压灭菌室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每一个装有流产婴儿器官的透明玻璃罐里,我都像看到了我失去的孩子。我开始做噩梦,这些噩梦渐渐不只是关于我失去的孩子,我还经常想到流泪的孩子,关于我每天工作的诊所里那些因堕胎死去的婴儿,以及各地因堕胎死去的婴儿。那些没有四肢的小婴儿,总是惊扰我的睡梦。但即便如此,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愿望(我已经杀了我的孩子)扭曲了我的思想,让我相信,如果所有这些与我共事的坚强、能干的女性都认为堕胎是无罪的,那我也必须能够相信这一点。
一天晚上,在高压灭菌室的工作结束后,我晚上作的关于死去婴儿的噩梦变得非常可怕,所以我决定去见诊所主任,和她谈谈我的感受。当她告诉我 “我们在这里做的就是结束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简单而清楚。这个事实没什么可讨论的。要想在这里工作,你就需要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我用力压抑住内心的不快,压抑住被刺激的良心,几天后我决定,接受我们在诊所所做的事——结束一个生命——求神帮助我吧,然后我又回诊所工作了。我不断地回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不久前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开始思考试管受精和代孕,这两个不自然而奇异的过程。我身边有一个熟人,她同意为她的朋友做代孕母亲,并和我分享了这个过程的细节。
我开始慢慢质疑在实验室里创造生命的正确性。我的朋友加入了一个代孕互助小组,并告诉我其中一位代孕母亲的合同中包含这样的内容:为一对不孕的夫妻代孕,对她怀的孩子进行基因检测。当结果显示孩子出生时患有唐氏综合症时,她拿到了代孕合同写到的全额报酬,然后她去堕胎了。
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的“觉悟时刻”!我的心态完全改变了,我终于(终于!)明白了:堕胎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每一次堕胎都如此。怀孕现在成了一种商业交易:幼小无助、正在成长的胎儿是一种可以随意制造、出售、购买和抛弃的商品——多么可怕和让人发指的事实——而我多年来一直是这种野蛮“产业”的一员。我哭了。我开始祷告。我现在就是支持生命了。我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在确认自己的站在支持生命一方后的几周内,我开始为这项事业奉献我的时间、才能和财富。我加入了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生命组织。我的第一次守夜祈祷是在我第三个儿子出生的医院外,也是一间堕胎诊所。我们一起散步,一起祈祷,我还唱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我们平和地祷告守望,为考虑堕胎的孕妇提供希望、支持和真正的资源,这些经历也让我相信改变对于堕胎的想法是正确的选择。
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但也是最更新我生命的事情。我希望并祈祷那些听到我过去的痛苦、可耻细节的人能够相信:这种转变是真实的,而且完全可能。
在堕胎诊所周围,我们平安地,充满祷告地存在着,给予共情的关怀和实际的资源,以及对怀孕母亲的支持,并为诊所里工作人员的内心转变的献上祷告。他们不是敌人,他们内心不全是恶的——真正的敌人是堕胎,它是邪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