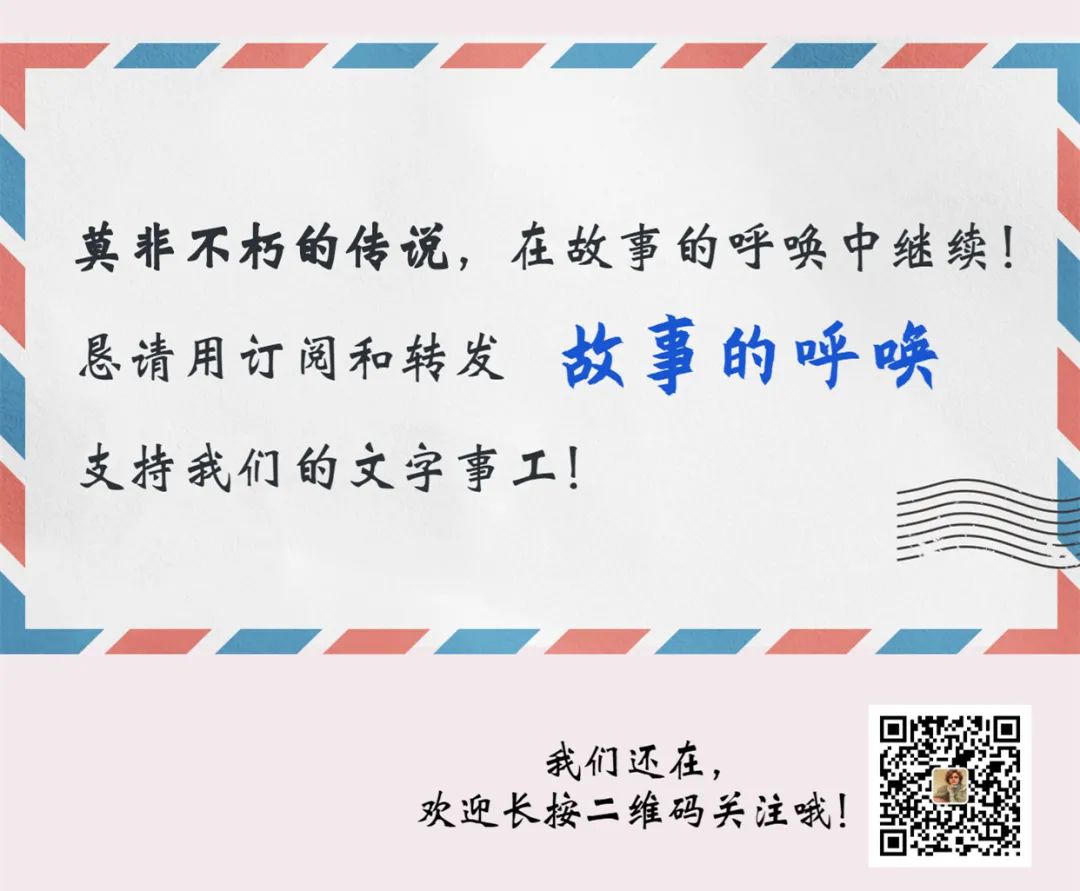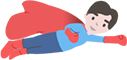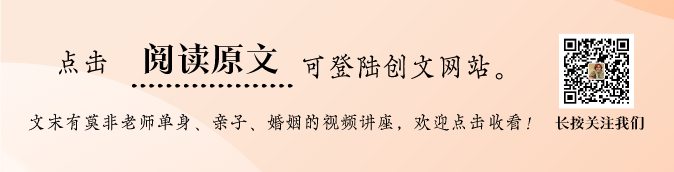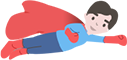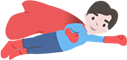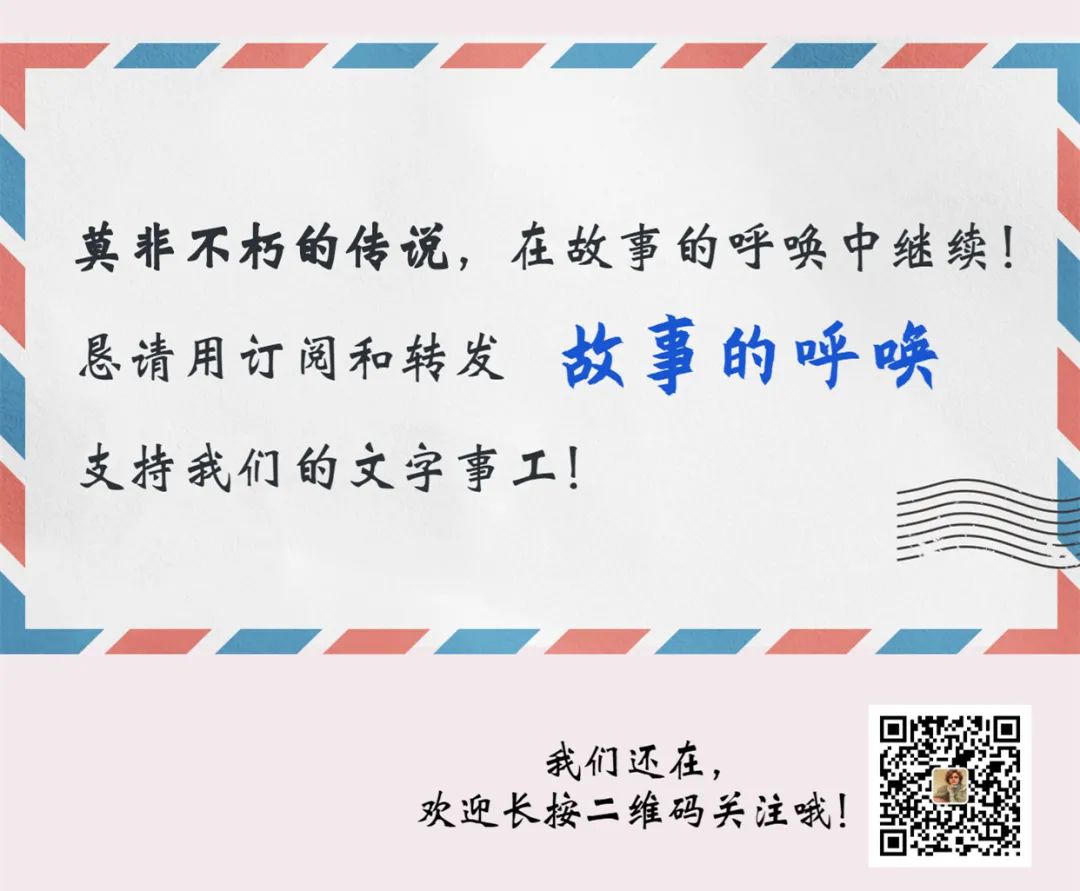
▼
一个父亲,透过短短的一句“来,跟我来”,将“未来”指给小女儿,提供更宽广的世界,让她的宇宙从未被盖过顶。父亲节到了,你最清晰记得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作者丨莫非
主播&后期制作丨溟帆
“来,跟我来!”那是一个中秋月夜。所有空军眷属都被接至机场,在俱乐部开晚会同欢。当众人正为抽奖而全心投入之时,蓦地,父亲由后轻敲我肩,转身,见父亲示意我跟过去。我偷偷跟出,上了父亲的吉普车。
父亲将车驶至机场内另一头的高尔夫球场,牵我走上那沾满露珠的果岭。四面空间一片开旷,只有远处跑道头的红灯微微闪亮。夜凉如水,父亲弯下身半拥着我,一手为我指向天边:“看!圆不圆?”天边挂着的,正是一盘皎洁明月。
不久,一架飞机徐徐飞起,飞向高高的明月,飞向远远的天边。那年我小学五年级。
又是某次踏青,爸爸载着一吉普车的小孩或来到山上,或去至大河边。在孩子的喧闹中,父亲十足一个孩子头,带着头上山下水,玩得兴味十足。然后,总有某个时刻,他会拿着照相机,示意我跟过去。然后在树下、或石头上,照尽各个角度的相。
镜头中,常是一个黑瘦梳着长辫的丫头,被父亲指挥着或望天,或望向远方,或假装若有所思,其实脑中常是呆地一片空白。或者,便是舒服地躺卧进父亲怀里,一脸娇憨,停格在相机按下的那一瞬间。
“来,跟我来!”总是父亲在说,声音极轻,语气中带点神秘,不欲为他人知,是一个偷偷的邀请。每次,我亦都能心领神会,很有默契地谁也不张扬,悄悄起来,跟随父亲而去。
有时是一个眼光,有时是一个手势,又有时,是一个声音,深深沉淀到我心底的熟悉回声:“来,跟我来!”我的马上起来同行,带有许多信任与不尽期盼。我甚至从未想过要问:“跟你去哪?”他亦从不解释。
一场舞蹈的开始,是不需要原因的。就像爱,无需解释。
有时会想,“父亲”两字,在女儿心中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印象?有人心底飘过乌云,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有人眼睛亮起,脸上浮起一片温柔。而我形容父亲,总觉写不尽,又怕写不好,会亵渎了心中的感觉。所以,我总是写了又写,重复捕捉“父亲”在我生命中同行的各种足迹。当然,那不容易,因为这也是自我描摹的一种努力。
我在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父亲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定义着自己。那是一种十分个人的“基因译码”。
当然,这样的牵系,父亲不知道。在那个时代,谁也不懂亲子关系的理论。父亲又自小离家进军校,并无健全家庭模式做参考。然而,在我与哥哥的成长中,除了有几年父亲在国外,其他时间他是一路出席,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位“男性”启蒙。
仍记得我初中新接触异性,是在一些教会活动里,懵懂又兴奋。每次郊游之类的活动,事先若征求他同意,他从不禁止,认为有些社交机会是好的。但每当出发的清晨,我尚未睡醒,他便一屁股坐在床边,开始“审问”:“去的人都有谁?是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一片关心又不敢显急切之情,常让眯睡着眼的我觉得好笑。
现在,却让我敬畏,尤其是在自己女儿进入青春期之后,该松该紧,如何拿捏?
回忆中自小至长,与异性接触方面,我从未被设限,那给我一种受尊重与被信任之感。然而父亲的谆谆询问,又让我觉得他关心,也在询问中了解了他的期望与关怀,使我在与异性互动中自有分寸。现回想,那是一种比阻止,比放任,更要下工夫的爱。既明知船迟早要出港,与其禁止,不如护航。他是在提心吊胆中一点一点地“放”。
反观哥哥,小时皮,大些反而变得内向敦厚。小学时新年总在机场过,那时候的联队长是司徒福,夫人老被我叫成“石头妈妈”。每次“石头妈妈”发压岁钱,哥哥都怯生生地不敢上前,还要我再跑上去,帮他也要一份。
进入中学,他也走进异性的烦恼。但仍胆怯,于是我成了他的代言人,帮他打电话给小学同班女生,免得被对方妈妈接到,会被凶回来。去教会,一散会他便推着单车准备走。神父或哪个同学试着留他,他都腼腆一笑:“下次吧!”低着头上车便走了,只有我留下嘻嘻哈哈。
于是,很多人说我们家生反了,男生像女生,女生又像男生。父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觉得这样下去对哥哥不大好,便开始介入,亲自教哥哥筹办一次小学同学会,到郊外踏青。
从开始的找地点、计划时间表,到打电话召集,父亲一步步带着哥哥做。甚至,连到了野外,怎么上山时拉女孩一把,一些绅士礼节小动作,全一一传授。
哥哥在其中学会了怎样策划、做领袖、与人沟通,眼见着一个活动就此渐渐成形。却没想到当天清晨,倾盆大雨。哥哥一早由被窝中爬起,望见窗外阴雨连连,知道野外郊游无望了,便又转头,钻进被窝就睡。
然而,父亲马上叫起了他,告诉他:“你是负责人,一定要去火车站告诉每个来的人,活动取消了!”哥哥只好冒着雨赶去“彻底负责”。领袖是怎么产生的?那一天,我目睹哥哥辛苦地踩着脚踏车,渐渐踩上他成为一名领袖的路。
也因而哥哥由当初的害羞内向,变至后来昂然带领两百人干活的主管。在这后面,有一只“父亲的手”在推动。
高中时,我考上台北一女中,父亲工作亦“刚好”调至台北,因而陪了我三年。
在那三年中,我随时有需要,他就生病了送药,没钱了送钱。一个电话之遥,拨通时,永远是从容、全神贯注的关爱之声,从不记得父亲有任何不耐之情。那是一种完全的回应,面对面、人对人,正视相对,而非忙碌夹缝中的一点“应对”。
周末,有时若不南下回家,父亲就带我出去打牙祭。上哪去?我决定。于是有时小摊、有时上馆子。吃面,端上来的大碗,常是往父亲面前一放,小碗给我。然后父亲开口更正了:“对不起,大碗是我女儿的,小碗才是我的!”然后我不好意思地换过来,便开始埋头苦干。这成了父女间共享的一个笑话。
父亲偶也带我去看画展,初次见识刘墉气派十足的山水国画,就在国军文艺中心。父女同行的文化活动不少,音乐会、舞展、画展,每次都装模作样地评头论足一番。多年后,我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一次云门舞集来美访问表演,又只有咱们父女俩有兴趣同行去看。那次的舞码(指一个或一组完整的成品舞蹈)是《流浪者之歌》。看完,父亲终于初次讲了实话:“跳的是什么啊?实在是看不懂!”我回:“我也是,但不能说,说了就太没气质!”
因父亲一辈子受军校教育,他是武官,而非文官,所以他读的书不算多。最熟的是《三民主义》与《国父思想史》,就靠这两本书,他行走天下。但他在自己有限的环境下,不断地力求超越。日后的英文与卡耐基人际关系训练等,都是他自己苦修的,工作上缺什么补什么。
去接触文化,完全是因他有颗开放的心,认为凡好的都可以沾一点。尤其是对女孩,沾染一些“可以培养气质”。所以父亲自己虽没什么人文背景,但他为我提供的,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空间。
高中在台北读书,好几次回台中,是父亲开吉普车。那时没有高速公路,都是黑暗中从一个又一个的乡镇、田野穿过。一路上,我讲东讲西,要不表演电视广告,叽叽喳喳地嘴没停过。面对车前黑暗,笑言暖语说亮了一车,也撒了一地星辰。父亲不但百听不厌,而且还常会问:“你的小脑袋瓜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好似对我每翻出新的一面,他只有不断的惊喜。那种欣赏,没有使我轻浮,反而使我沉淀;使我知道我有些珍贵本质,是不需靠外表包装,也无需用手段来笼络人心的。这为我日后的两性互动,提供了一层“底”。认识到这世界上有一种两性关系,是建立在接纳、尊重与欣赏上的。任何与这种关系相斥的,就走调了,便不足取。
好似一直是这样的,父亲的膀臂,像大海一样宽广,他为我导航东,又为我导航西,一路推送,但从不颠覆。他从未曾收起双臂,控制我的左右。
现见多了父女模式,愈来愈发现父亲,是把“未来”指给女儿,为女儿塑造性格的一个关键人物。不幸地,有的父亲指出的,是一个传统,僵式为人妻母便到此为止的“狭窄”视野。而父亲为我指向的,则是一个“宽广”的世界,像他为我指向月亮。让我觉得此生,没有什么不能做,没有什么不能“是”,我的宇宙从未被盖过顶。
这使得日后择偶,任何会限制我天地,让我觉得婚后人生只剩两人头上那丁点天的,我便窒息,便欲逃。直到遇上这一位,能为我提供无限宽广发展空间的男人,我才停歇了寻觅的脚步。
现回想,父亲虽不懂心理学理论,亦无知于父亲会影响女儿日后的择偶取向,但他有爱。他是凭着人性中最天生自然的父爱,摸索出一条路来牵引我。
重要的是,他想牵引,不只想在我的成长中出席,他还渴望护航。这怕是许多父亲从未想到过的父爱彰显方式。
就这样,“来,跟我来!”一次次,他在我的成长路上提携,带着我一步步、更深地走入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我脚步较稳了,自自然然地,便由我的生命路上让开。然后,像共舞时扶在我背后的手掌,轻轻一推,我舞出了两人的圆圈。似初出江湖的小船,摇摇摆摆,但帆里鼓胀着风,是父亲一口、又一口气的祝福,吹向渐行渐远的女儿……
“来,跟我来!”这是父亲可以送给女儿最大的礼物了。而我,何其幸运!
▼
课程推荐

▼
作者简介
▼
网络书苑

▼
感谢支持
▼
转载说明
▼
书籍推荐
▼
莫非视频推荐
从养育、放手,到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