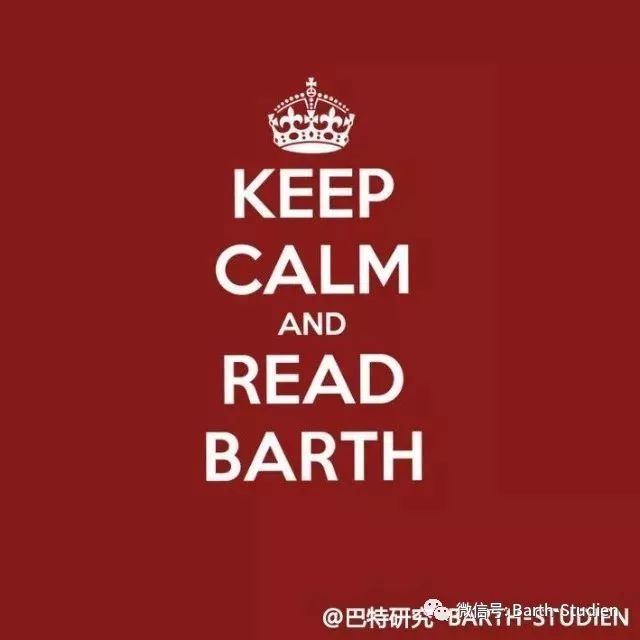堕落之后神的形象|成静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文章是成静老师对尼布尔和巴特罪观与人性论的比较。在详细解读尼布尔《人性与人命》和巴特《教会教义学》中的相关论述后,成静老师认为,二人的观点表面上差异极大,实际上有诸多原则上的相似之处。二人都认为,神的形象对人的存在是本质性的,不能将人的这一本质特征简单对应于人的某一特定官能,人的堕落不改变被造的原初完美,但是,人的现存确实已完全败坏。尼布尔强调,罪是腐蚀(corruption),不是拆毁(destruction),神的形象以及“原初的完美”仍然遗留在已堕落了的人里面,人不能卸去保证它正当运作的责任。巴特所理解的“神的形象”,暗示着神与人的约、以及耶稣基督的人性,于是,耶稣的死有可能表明,神性生命的“爱的共存与合作”在人的存在域里已经完全被毁了。至于二人之间的分歧,成静老师认为,尼布尔坚持人的灵性的自由,而巴特则把一切实在的意义交付给神。
随后,成静老师从尼布尔和巴特的政治表现中进一步观照二人思想的联系与差异。二战前后,巴特对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始终如一的中立,既强调神的最高恩典,又看重神人相遇的具体性,因而在德语世界取得巨大影响力。尼布尔则一边承认人类共同的罪性,一边在历史中区分善恶的政治,却难以做出相对恰当的道德选择。对巴特从神的作为出发的人学和伦理学的高度和气概,成静老师尽管文笔内敛,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由衷的赞美和感叹。
本文原发表于《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评论》第44期,2016年,第341-369页,推送时已获期刊和作者授权,深表感谢!文章正文长度约15000字,阅读时长约20分钟。
内容提要
卡尔•巴特提出在人堕落以后起初被造时所有的神的形象就完全失效了。这是巴特神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键性的前提。本文主要研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对巴特这一立场的批评—-尼布尔认为巴特这样的立场将使得人逃脱在其历史存在境遇中寻求现实的相对的善的责任。尼布尔坚持,在人堕落以后他原有的神的形象不是“失效”了而是“败坏”了;人起初被造时所有的原初的义仍然遗留在堕落了的人里面,而这个原初的义应当促使人在此时此地尽量寻求善。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巴特和尼布尔的罪论做一番比较,指出两者之间在某些原则上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尽管如此仍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很深的差异。在对于巴特和尼布尔的人学及其伦理学意涵进行一番理论考察后,本文将进一步追踪两位思想的巨人在他们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于现实政治的参与,并指出他们的思想理论的差异可能导致的实践行为的不同。
关键词:卡尔巴特,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神的形象,罪。
在罪人的身上,“神的形象不仅是…除了一些残余就都被毁坏了,而是完全被取消了(vernichtet, annihilated)”,“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Church Dogmatics, I/1,页238)[1],巴特在1932年出版的《教会教义学》第一卷第一 部中如是说。在那里,巴特是在反驳艾米尔•布汝讷(Emile Brunner),后者把神的形象当作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接触点,为人领受神的启示提供条件,使人认识神成为可能。巴特在与布汝讷关于自然神学的论战中发出的尖锐声音在神学界造成巨大反响,它不仅向传统的神学认识论提出挑战,而且也引出了一系列神学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与巴特同时代的美国神学伦理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巴特神的形象“取消说”的质疑。 尼布尔认为,这样的罪论和人学将对道德教诲的实施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他在1941年出版的《人性与人命》(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第一卷“人性论”中说:
像巴特那样的神学,由于片面强调所有人的罪性的终极的宗教事实,大有破坏一切相对的道德判断之势,正该被疑有危及历史中相对的道德成就之嫌。(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I, 页220)[2]
尼布尔也承认,堕落后的人没有能力实现基督教爱的理想,但是,他仍想要维护人类历史中由那一超验的目标驱使的追求相对的进步的意义和必要;而且,尼布尔看到,人虽然有罪,却仍然会有为做错事而懊悔的时候,所以他相信,在人堕落之后,人里面神的形象虽然被毁坏了,但不是被彻底消除了。而且,尼布尔(和布汝讷一样)认为,要是真像巴特所说的那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认识神和为着神的能力,他将不必再对神负责,要求这样的“人”遵守神所颁布的诫命也是不合情理的。
尼布尔对巴特的批评中肯吗?巴特的神学里还有可供基督教伦理学生存的空间吗?他们中间哪一位的人学更忠于基督教正典的教导,对信徒的生活更有帮助呢?他们中间的矛盾真是那样不可调和吗?本文首先将对尼布尔《人性论》中关于“神的形象”的论述做一番介绍;鉴于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一卷第一部中并未展开对“神的形象”和人的堕落的全面思考,我们将主要结合《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一、二部(出版于1945年)和第四卷第一部(1953)来了解他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并通过对两位神学巨匠的思想的对比,考查他们各自的利弊得失,以资今日之借鉴。
一、尼布尔关于“神的形象”的学说以及“原初的义”
在尼布尔看来,基督教关于人的看法包含了人的存在中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1)人是有限的,人纠缠于自然和历史世界中的各种必然和偶然之中,这意味着人的脆弱和人对无限的永恒的神的依赖(NDM, I, 页3);2)当人把这样的有限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思时,他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他的自然的历史的存在,这一点指向人内在的对无限的导向(orientation),指出人的灵性的自由(NDM, I, 页3-4);3)而现实是,人不满足于他的有限性,不愿意倚靠神,企图自己寻求一种安全感,从而为自己争取一种虚假的无限性(NDM, I, 页178-179)。尼布尔把第一点称作人之为被造的特征,第二点是神在创造人时放在人里面的祂自己的形象,而第三点则是人的罪。
“如果人坚持说,他是自然之子,不应该假装比动物—-他当然也是动物—-有什么强,他就默认了,无论如何他是一种倾向于、并且能够这样假装的奇特的动物。”(NDM, I,页1)就这样,尼布尔开始了他关于人的存在所处的种种悖论的描述。在接受了基督教关于人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被造的老生常谈之后,尼布尔指出,这一有限的被造有着超验的对无限的视域的导向:如果人仅仅是一个有限的个体,他就没有能力对自己的存在进行一种整体的把握、从而认识到它是有限的—虽然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死的,只有人对这一点有意识、并且因此感到不安(NDM, I, 页181-182);在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时,人表明他自己不是一种简单的有限体。人的自由就在于此:他不仅有“在自然过程所呈给他的各种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越他的整个存在、从而“选择他的最终目标”的自由。(NDM, I, 页163)在这里,尼布尔认为,他找到了人身上的神的形象,并视之为人的灵—-由此,尼布尔与希腊化的基督教划清界线,因为后者往往把人所有的理性和语言的能力作为神的形象(NDM, I, 页13)。[3]
可是,尽管人向往无限,但是,在他自己里面他无法达到或实现无限:在他的超验的导向中,人无法把自己从他所处的自然和历史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虽然他被赋予选择自己目标的权力,但是,可供他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更让人恼火的是,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但他并不很清楚界线到底在哪。这就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NDM, I, 页182-184))这种不安是人的罪得以产生的“内在前提”,它引诱人犯罪,虽然它不必然导致罪。(NDM, I, 页182-183)
关于人的无助,尼布尔所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人“没有能力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NDM,I,页164)。和其他有自我行动能力的被造物不同,人在灵性的自由里面,可以站到他和历史的纠葛之外,从而看到它是有限的;但是,人又比其它被造强不到哪去,因为他逃不出这一命运,也不能赋予它效力—-任何他能赢得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在人自己的自我超越中,他的有限性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但是囿于他的有限,他的自我超越并不能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在尼布尔看来,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除非引入一个“超越他的能力所能超越的世界”的“意义原则”(NDM, I, 页164)。这一原则要“超越他的能力所能超越的世界”,乃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已经有过太多将人所掌握了一些原则提升到终极高度的尝试:一个国家的生死荣辱、自然的因果律、理性的融贯原则,等等;但是,国家并不永世长存,而且国家利益的绝对化已经表明是极具破坏性的,自然的因果律又与人的自我超越和自由相悖,而人的生活和历史中都充满了矛盾超出人的理性的组织能力之外,等等。不仅如此,将进行自我超越的自我加以绝对化的企图本身就与这种超越相悖。(NDM, I, 页165)总而言之,“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恰恰因为他里面那些被称为‘神的形象’的特质,不能被按照人的形象所造的神满足”(NDM,I,页166);他所具有的神的形象,他的自我超越,引导他去寻求超越他自己的世界的神;“人只有在神的特性里才能找到他的真正的标准,”但是,、作为被造物,他“不能也不应该追求当神”(NDM, I, 页163)。
尽管人性和人的存在处在这样一种悖论的光景之中,它并不是在被造之初就是邪恶的;的确,“如果人知道他自己是坏的,他又怎么能‘在本质上’是坏的呢?”(NDM, I, 页2)相反,尼布尔认为,与人的被造性和灵性的自由相对应,人已经被赋予了一种与人性、及其存在的辩证性相符的“原初的完美”。首先,与人作为被造的特性相应的,是一种“自然法”,“它…定义了人的各项功能的正常行为、他的各种冲动之间的规范的和谐、以及在自然秩序的限制之内的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规范的社会关系”(NDM, I, 页270)。但是,律法只有作为对自由的规范才有意义,可是,自由就其本义来说是超越规范的,所以,这样的“自然法”对于划清“对在自然秩序中作为被造的人的明显的要求[和]他作为自由的灵的特殊要求”之间的界线,只有“暂时的有效性”(NDM, I, 页271)。
进一步,与人在他的灵里面的自由—-即人被赋予的神的形象—-相应,尼布尔提出基督教的信望爱三德。尼布尔认为,这些德行是“对自由的基本要求”(NDM,I, 页271)。有限的人,当他反思自己在自然的偶发和历史的变迁中的有限的存在时,不由得焦虑,所以,他需要相信一位超越历史的神来为他提供历史的意义和他存在的安全感。(NDM, I, 页183、271) 盼望是“信心的一种特定形式”,它“处理关于未来的问题”(NDM, I, 页271)。而且,具有自我超越的灵的人,不能满足于禁锢在他有限的自我里面,从而他渴望一位他者。但是,虽然人具有共同的本性,又彼此依赖,但在论到每一个个人的灵的特别性时,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彼此分离的;鉴于这两方面的因素,人不得不彼此以爱相连。“在爱中,灵与灵在每一个体的最内在本质的深处相遇。”(NDM, I, 页271-272) 这种爱也要以对神的信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人会过分忙于他在外面世界的事务,以致无暇顾及自由的属灵世界;他会被关于他自己的焦虑和操劳占据,以致懒得再去管别人的事。(NDM, I, 页272)总之,与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天主教神学不同,尼布尔强调,基督教关于信望爱的教导不是基督宗教提出的超常要求,而是由人存在的特征所决定的,它们的缺失有损于人存在的根本。
不幸的是,这一与人的辩证存在相符的原初的义虽然应该、但是并没有在人的身上实现。尼布尔指出,当人的存在境遇被错误地诠释后,它就败坏了。作为有限的灵性存在,人对无限有所领悟,但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它;由于知道自己的有限、却又不知道这个界限到底在哪,所以,当人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焦虑时,便被引诱将自己等同于他所面对的全体:神的形象的不当运作导致对神的否认。(NDM,I,页181)由于他的超越的灵性让他看到的悖论的境遇使他感到不安,人不愿意接受他自己的有限性,而这种不情愿促使他企图为自己寻求一种安全感,这导致他对神的反叛:他不信神,而信他自己。(NDM, I, 页190) 再者,一旦自我把它自己放在他的导向的中心,他就不可避免地使他自己的利益优先于他人的利益,从而待人不公。(NDM, I, 页192))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当人被这种焦虑骚扰时,他急于为自己寻求解脱,于是他索性将他身上的神的形象掩盖起来,假装不知道他有超越的能力,将自己交付于世界的琐事。(NDM, I, 页185)在第一种情况下,人的罪以骄傲为特征,第二种,纵欲(sensuality);作为人的幻觉这两者常常彼此相联。(NDM, I, 页185-186)
然而,尼布尔想要强调,神的形象以及“原初的完美”仍然遗留在堕落了的人里面。“罪是人的真正本质的堕落(corruption),但不是破坏(destruction)。”(NDM, I, 页269))如果尼布尔想要宣称神的形象仍然存留在人里面,这听起来似乎还是有理,因为无论是骄傲者的错误导向,还是纵欲者的逃避企图,都不是对人内在的自我超越能力的完全抹杀。事实上,两者都是对他的这一自由的运用和表达。人性的本质的结构,那使得他是他所是的,不会因此被摧毁。但是,人的本质特征并不自动地带来对这一特征的遵从。面对人昭彰的罪恶,我们从哪里能找到那“原初的完美”在这样一个罪人身上的遗迹呢?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在此,尼布尔引导我们去看一个罪人的懊悔:
“没有人—-不管他是多么深陷于罪中—-能将罪的可怜视为正常。 对于之前的蒙福状态的一些记忆似乎萦绕在他的灵魂里;他已经触犯的律法的一些回音似乎回荡在他的良知里。任何为罪的习性披上正常的外衣的努力都多少暴露了一个不安的良知的疯狂。人真的和本质上所是的和他已经成为的之间的对比是明显的,即便对那些不明白这一对比存在于每一个人里面并且位于人自己的意志之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NDM, I, 页265)[4]
只要神的形象仍然遗留在堕落了的人里面,他就不能卸去保证它的正当运作的责任。既然那些基督教的德性是为人的基本要求,人就不能简单地对之视而不睹而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不过,因为罪人已经失落了它们,它们现在对他来说成了律法,谴责着他的错误,光照他的罪,却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些德性。(NDM, I, 页273)这一律法已经被写在了人的心板上并且彰显为我们的良知。(NDM,I,页273-274)而对于尼布尔来说,这良知就是“罪人的义”(NDM, I, 页274)。
那么,尼布尔是不是就这样放弃了基督教关于人性在堕落后的完全败坏(corruption)的说法呢?没有。那又怎么没有呢?在这里,尼布尔首先拒斥了基督教传统中可能存在的对堕落的时间性的解释。堕落不是一个划分在其之前的原初的纯净的人的存在和在其之后的人的败坏状态的历史事件。相反,尼布尔认为,它“象征着人的生命中每一个历史时刻的一个方面”(NDM, I, 页269);在这一刻,人的原初的善与他现行的恶“垂直地”关联(同上)。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把它定位在个体的人的某一特定官能上,他将劳而无功。在此,尼布尔将罪人的光景比作一个生了病的机体:
在一个生了病的机体中,健康在哪里呢?显然感染的部位可能是机体中的某一特定器官,而其他部分都是相对健康的。但是机体中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会影响到整个机体。所以,整个机体都病了。但是,只要这个机体还有生命,它就多少拥有健康。疾病带来的疼痛本身就是对这种隐藏的健康的佐证;因为疼痛揭示了,机体的正常和谐已经被打破,所以,它是健康对疾病的控告。[但是]要在有病的身体里划出残留健康的所在,却是不可能的。(NDM, I, 页276-277)
尼布尔说,从这一类比可以推出,虽然我们不能保护人的任何官能不被罪玷污,人的存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是它的义—-对神的降服、与邻人的协作—-的余留的明证,因为人的生命如果完全不符合任何基本的规范就会彻底毁灭。虽然尼布尔无意于维护人的任何官能的正常性,他并不放弃寻找“原初的完美”在人里面的“落脚点”。回到他对人的懊悔现象的观察,尼布尔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一原初的完美的线索:在罪人感到悔恨的时刻,他为他之前所犯的罪遭到良心的谴责,而这标示着他之超越他之前的状态的时刻,在此,我们看到自我“关于原初的完美的意识和记忆显出来了”。(NDM, I, 页277)
但是,尼布尔承认,不安的超越的自我关于原初的完美的意识和记忆,并不是对那一完美的“拥有”。(NDM,I,页277)的确,自我此时对其之前的不端行为的批评并不能保证他以后就能行为正直。其实,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不断地成为限制他下一个行为的历史因素,因为他现在的超越的要行义的想法不可避免地是他包含了之前的不义行为的计算的结果。也许这次他可以比上次做得好,但这不能保证他完全符合“原初的完美”的神圣原则的要求。既已错误地转向了他自己,这个已经扭曲的自我无法找到回头的路。因为无论何时它要从头开始,他都无法不关注他自己;结果,“从这个焦虑的有限的没有安全感的自我出来的每一个思想、情绪或行为都带着罪污”(NDM, I, 页278)。懊悔总是在事后发生,而它也没有能力预防任何以后的不端行为。“[我们]允许人所有的原初的完美的残余[不应该]被错误地等同于执行‘公民正义’的能力,这一能力和其他人的能力一样明显地被罪腐蚀了(corrupted)。”(NDM, I, 页26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错误总是因为无知或疏忽而犯下的呢?尼布尔坚决否认:人对自己的软弱从来不是毫无意识,神的形象一直都在要求我们遵从它;其实,罪总是一种[人]要掩盖他[自己]的软弱、对超越的自我的要求充耳不闻的企图。(NDM, I, 页181、278)“所以罪既是无意识的,又是有意识的。”(NDM, I, 页250)它是无意识的,因为“它来自于意志的一种缺陷,由于这个原因它不是完全深思熟虑的”(NDM, I, 页242);但它又是有意识的,因为它从不是“意志单纯的突发奇想”(同上),因为原初的义存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知道什么不该做。那么,在这同一个人里面就有两个自我了:超越的具有神的形象的自我和罪性的想反叛前者的自我?尼布尔回答说,不是两个自我,而是一个自我有两个方面:这个自我一时仅仅和世界打交道;另一时对世界和它自己都加以反思。尼布尔援引保罗关于他自身里面属灵的律和罪性的肉体之间的冲突的哀叹,声称:“这个从自我超越的角度来看将罪性的自己不看作自己而看作是‘罪’的‘我’,和那个从罪行的角度看将自己的超越的可能性不看作自己而看作‘律法’的‘我’,是同一个‘我’”(NDM, I, 页278-279)。
尼布尔认为,原初的义在这个有罪却自由的人的终极自我里面的残留,应当成为规范他的自由的律法,告诉他什么不应该做。虽然完全实现律法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但是由于灵性的自由仍然存留在他里面,他不能推卸他自己对它应负的责任。他对出于自己的意志的不端行为的悔恨,暴露了他对自己的罪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是在原初的完美里被造的,现在这一原初的完美虽然在历史中看不到,却仍然存留在历史中的人里面。(NDM, I, 页280)所以,尼布尔建议说,我们应该不断地关注在我们的超越的自我中残留的原初的完美,并且在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努力争取相对的有条件的善。宣称神的形象在堕落了的人里面已经完全被取消(annihilation)、不正当地无视人在灵里面仍然保有的自由—-他还是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他仍然是道德责任的主体;而否认人里面的原初的义将成为人推脱自己对这一自由的基本要求当负的责任的借口,拦阻他去争取他本来可以实现的历史中的相对的善。
在对尼布尔关于人性和人的存在的神学建构有所把握后,我们接下来将转向巴特所阐述的新教人学,看看尼布尔对它的批评是否中肯,还有,尼布尔所关注那些问题是否只能按着他所提示的路径解决。
二、巴特对“神的形象”的诠释以及神与人的约
巴特是在一个宏大的创造论(《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的框架里面阐发他的神学人学的。处在这一创造论的中心的,是神出于祂自由的爱而创造人和世界的理念。在神的爱中,祂不满足于祂所创造的他者的仅仅存在,而进一步与他立约,希望他成为这个约的伙伴(CD, III/1, 页96)[5]。于是,“就其所是和性质来说,[这一]被造是命定了、被预备了也被装备了要做[这样]一个伙伴”(CD, III/1, 页97)。在神创造的巅峰是人的出现,他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神就歇息了。对巴特来说,这一安息日的事件象征着神与人同乐,人从一开始存在就被呼召参与到其中:“神…在人之中欢欣,正如在祂自己的形象中欢欣”(CD, III/1, 页99)。
那么,在这里“神的形象”意味着什么呢?在此,巴特领我们去看创世纪中第一个关于创造的叙述,并通过解释“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来阐发他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巴特首先要我们注意“让我们”这几个字:这一说法首先向我们提示了神自身中的复数性,虽然不是马上就和三位一体连上,但至少说明神自己里面有着我你之分。对巴特来说,更重要的是,神向祂自己所做的这样的言说蕴含了神在祂自己里面取得的共识,并且提示说,设立一个外在于神的立约伙伴是在“确认和荣耀祂自己内在的本质”(CD, III/1, 页183)。巴特由此推出,在神自己的所是里面,有“一个爱的共存与合作”(CD,III/1,页185、196),而人被造是为了“代表”这样一种神性的生命形式:他先是被造成为神的立约伙伴;其次神自己里面的交互关系也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只有在和其他人的联系中人才是人,而人之为人的这一基本特征首先体现在人被造为男女二性(CD,III/1,页185-187)。巴特认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而紧随其后的“[按照我们的]样式(likeness)”意指人存在的形式只是神自己里面的形式的复制或模仿,而不是原版。(CD, III/1, 页183-184、 196-197)
而论到什么是神的形象时,巴特又带我们发现保罗将耶稣基督称为“神的像”的说法(和合本,林后4:4,西1:15)。这个耶稣不是仅仅“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而就“是”神的像。耶稣是如此地为着神,也为着他人,“以致非他人所能企及”(CD, III/2, 页222)[6]。即使撇开我们的罪不谈,耶稣和我们之间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只有他是“从一开始因着他的存在”就为着他人的(同上):他正是通过放弃在天上的宝座,而成为人,并取了奴仆的样式的(腓2:6,7),而他也是因着神托付他的代表人拯救人的使命而如此的—-耶稣之为着神决定了他之为着人。 神起初造人,就是“为着耶稣的缘故,以耶稣为图景,为目标,从而也是在他里面又照着他造的。”(CD, III/1, 页203)既已宣称“耶稣的人性在于他之为着人”,巴特推演说,“人的人性在于他之被置定为与他人共处的所是。”(CD,III/2,页243)与他人共处,这是神在按照耶稣的人性置定的人性的基本形式。
巴特坚持,只有认识了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人,自然在他看来,只有认识了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什么是人的罪。
但是,神向着祂的被造的这一意愿已经被人弃绝了。人在他的骄傲里拒绝相信神,并且远离神—-虽然神在基督里已经永远地拣选了他,并且爱上了他—-从而侵犯了神的权威。(CD,IV/1, 页414-415)[7]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为神为人而活,他以为他可以单单和自己在一起,以为他是自足的,可以做自己生命的源头、标准和主宰。可是,他这一番折腾并不能真正改变神所置定的人性的正当形式,结果只是他自己与神为敌陷入可怜的自我矛盾的光景。“堕落的本质…即在于人无用的自信(fiducia)。”(CD,IV/1, 页480)
所以,巴特说,在人堕落以后,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已经被“完全取消了”。这是巴特人学的必然结论,如果照巴特所说,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是人的存在里面的神的形象。耶稣的死应该向我们展示,神性生命的“爱的共存与合作”在人的存在域里已经完全被毁了。如果这样,巴特将如何回应尼布尔对他的神学做出的批评呢?巴特凭什么要他的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他是不是不鼓励我们在此世追求相对的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看一看巴特是如何描述堕落之后的人的光景的。
当我们走近巴特的罪论时,我们首先发现巴特和尼布尔之间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虑及虚无主义的威胁,巴特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小心,在描述罪的破坏性时不要“过了头”。(CD, IV/1, 页484)巴特一方面肯定了尼布尔所强调的,堕落了的人应该仍然保有他原初被造时作为人的特性(nature)和能力(CD, IV/1, 页482-483、492),而神对他的诫命应该仍然有效—-“圣言总是对人的审判,它的真理是他的存有的真理,即便在他堕落的光景(status corruptionis)里也是如此”(CD, IV/1, 页482),更重要的,巴特指出,“堕落而远离”神的人“并不能真正逃脱神”(CD, IV/1, 页480)—逃脱的意思是,“他再也不能听见神对他说话,神不再知道他也找不到他,他与神再也没有任何关系”(CD, IV/1, 页482)。的确,“虽然神和人的约已经被…堕落的人完全破坏了,但是,因着神恩典的大能的作为,它还没有被逆转或挪去或毁掉(ausgelöscht,destroyed)。”(CD, IV/1, 页481)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巴特用来描述“神的形象”所遭遇的破坏的词是“vernichten (annihilate,取消)”,而不是“zerstören(destruct,拆毁)”或“verlieren(lose,丢失)”。其实,巴特在回顾基督教关于“神的形象”的概念的历史时,批评了宗教改革中对堕落后神的形象的“丢失”、“废除(aufheben, abrogate)”或“拆毁”的宣称;他说,圣经中关于创世的叙述并不支持“一个原初的理想的人的”观念,也就谈不上“对这种理想状态的废除,或对‘神的形象’的部分或全体的拆毁”(CD, III/1, 页200)。这也许可以向我们提示,鉴于对巴特来说神的形象不是一个所有物,也不存在拥有它的单个的人(因为它不可能被个人拥有),他用来描述堕落后神的形象的“vernichtung(annihilation,取消)”一词在此的主要含义应该是其法理的意义“失效(invalidation)”,这与巴特提出的神的形象是服务于神的约的宏大叙述契合,也是诸如“拆毁”或“丢失”等指向本体的词所缺少的。更重要的是,尽管在堕落了的人性中神的形象已经失效,神性的“样式”,“人与之间的伙伴关系”仍然存在(CD, III/1, 页200;IV/1, 页493):即使作为罪人,人还是彼此联系,他也不能斩断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只是现在这些关系都不那么愉快。[8]事实上,巴特说,“神和人的团契以及交往的历史…真的是从人的堕落开始的。因为虽然它包含人对神的意图的完全忤逆从而给人招来羞辱和审判,但正是这样神坚定了祂的意图,把人当作一个‘你’来称呼,并且使他成为一个要对自己负责的‘我’…”(CD, III/1, 页200)
那么,巴特是不是放弃了改革宗传统对人的彻底堕落的境况的坚持呢?绝对没有。巴特认为,人的堕落的严重性只能用神差遣祂的儿子救赎我们这一事实来衡量;巴特说,因为罪我们欠了神一笔债,而我们自己无法还清。(CD, IV/1, 页484)因为在罪中,人已经单方面破坏了他和神之间的约,是神被得罪了,只有神的饶恕,才能重建原初的义和秩序。(CD,IV/1,页484)的确,任何人为的与神和好的企图只会再次暴露人想要代替神的野心和冒昧。神的饶恕是神恩典的彰显,但是,人因为自己的骄傲违背了神恩典的旨意;可是,神没有因此收回祂的恩典,虽然由于人的敌意这一恩典现在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罪人既不能用他的好行为或坏行为促使神给他恩典,也不能改变其形式,因为恩典之为恩典,乃在于它超出人的掌控—-否则,它就不是恩典了。我们只能相信神的恩典,即使它是以审判的形式出现的,并且恳求神的赦免。但是,这信不能以神的恩典为目标,因为一旦人意图以信心为获得神恩典的手段,信心就成了行为,从而像人的任何其它行为一样败坏。所以,因信称义的“因”当解作“因循”而不是“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虽然也“因着信”。我们因信领受神的恩典;在信心中,我们本该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审判和神的恩典;但事实上,罪人总是忍不住不时地把信变成一种行为,一种为自己寻求安全感的行为,从而他在“信”里对神的降服总是不完全的,他得救的唯一希望最终只能在乎神爱的恩典和神自己的信实,如巴特所说,“神和人之间的约已经被人的堕落完全破坏,并且就人而言没有修复的可能,”尽管“作为神的恩典的全能的作为,它没有被逆转或挪去或毁掉”(CD, IV/1, 页481)。不错,虽然我们没有能力相信,却也只能相信,并且只能相信神。
不仅如此,由于发生在耶稣里的人与神的和好,在于人的境遇的全面转变,巴特推论说,在人对神的反叛中,整个人,他的所是和他的行为,肯定都已经陷了进去:“人是他所做的。而他又做他所是的。并且在他的所是和行为的循环中他活在对神的背逆之中—-反反复复从罪到罪。”(CD, IV/1, 页492)人通过他的行为建构他之所是;由于他的罪行,这原本被造得好好的人(good man)成为一个坏人(evil person):在实践中,人的罪恶的生命和他单个的恶行是同一的(CD,IV/1,页499)。
巴特坚决反对,在堕落之后还有什么善“残留”在人的主体里面:罪人并没有丢失神所造的好的属性,[9]但是作为主体的一位他不能称这个为自己的功德。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尼布尔以人会懊悔为证说明在超越的自我中还遗留有“原初的完美”。但是,巴特在谈到懊悔时,却侧重于说明,人会懊悔,并不等于说人就能凭着所谓与生俱来的良知(或自然法)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人的懊悔经常会伴有人的自怜,而这种情感的存在往往成为人为自己开脱(亦即自义)的借口。(CD, IV/1, 页360)由是观之,像尼布尔那样以懊悔夸口,恰恰暴露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自义。这似乎并不直接针对尼布尔关于懊悔是人心中遗留的善的表现之说。巴特反对称懊悔之心为遗留于人里面的善的凭据,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撇开神在造人时所赋予他的好的属性,人所能称为善的当是他主观发出的行为,而懊悔不是人主动的行为,而且,懊悔之心也不能代表一种自我改善的能力,人不能靠它宣称自己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有什么可嘉奖之处。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懊悔是一种“情感”,发生在人“直接的自我意识”里面,它不同于发生在“间接的自我意识”里面的自我反省这样的有意识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以“懊悔”夸口。
要真说有什么“善的残留”,巴特说,那只能是神自己的“恩典的心意”,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并且不断地把我们建造成“祂恩典的对象”(CD, IV/1, 页494)。“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和合本,罗11:29)。既然由于神的心意,人应当是、又决定性地是这样的一位,人在神的面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是这样的一位;巴特认为,在这里用“残留”这个词来说人所是的好就“太,太弱了”(CD, IV/1, 页494)。另外一方面,就人自己而言,他之“为”人“已经彻底变坏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可供善立足的]常在点存在于[罪恶的]表象的流中”(CD, IV/1, 页494)。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神和人之间的约已经被人的堕落完全破坏,而就人而言没有修复的可能,但是,作为神的恩典的全能的作为,它没有被逆转或挪去或毁掉”(CD, IV/1, 页481)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质的置定是彻底的,两边都无“残留”的余地。
可是,如果这样,巴特如何能要求他的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呢?在这里,巴特的解决方法与尼布尔的相似:罪人还是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首要地是因为“他作为罪人的存在…不是既定的,而是…[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又被回答”(CD, IV/1, 页493)。[10]他通过他的行为建构他的所是,并没有什么外力迫使他犯罪—-他不是“笼罩在他头上的命运的受害者”(同上),他没有理由犯罪,在罪中,他与自己为敌。当神要求人顺服时,神并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祂并没有要求人成为什么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应该是他所是—-祂所爱的人…”(CD, IV/1, 页488)
但是,巴特又怎么回应尼布尔说他对人的堕落的极端宣称妨碍人追求他本该也可以达到的相对的善呢?巴特会完全否定这样的问题的合法性,因为“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和合本,可10:18b)。(CD,III/4,页4)[11]善恶是神定的(CD,IV/1, 页450),合神心意的就是善的,不合神心意的就是恶的;而神永恒的心意已经启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亦即,祂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做祂的立约的伙伴;而祂也要求我们选择祂,像耶稣那样顺服祂。所以,巴特的伦理学强调,我们不必追求善,我们只要追求听神的话(CD,III/4, §52),而巴特又指出,神的话是活泼的大有功效的,它总是在特定的境况中向着特定的人发出(CD, I/1, 页140),也赐给人顺服的能力(CD,I/1,页149-156)。可以说,在尼布尔关注量的相对的善的地方,巴特在乎的是质的具体的善。
三、谁是对的?
经过这一番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尼布尔和巴特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神的形象对人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CD, III/1, 页185),而且我们不能将人的这一本质特征简单对应于人这一行为主体的某一特定官能,并且两个人都坚持被造的人性的原初的好,即使是人的堕落也不能改变这一点,然而人的现存已经完全败坏,等等。尽管如此,在一些关键点上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虽然两个人都认为所谓“神的形象”不能单指人的存有的某一特定官能,但是尼布尔从分析人的主体存在的结构出发,认为“神的形象”指的是人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指的是人的灵性的自由,而巴特在坚持两人的共同点上走得更远, 他力图杜绝任何神恩典的赠予成为可为人左右的人的拥有物的可能,于是他在神对人的拣选的框架里,从分析圣经文本出发,把“神的形象”诠释为以爱的共存与合作为特征的神性生命在人的存在中的显现—-最终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巴特和尼布尔一样,看到人一方面是宇宙中的被造物,另一方面又与神相关,但是,对于巴特来说,这种关联不是系于人性中某一恒常特征,而完全在于神自由的爱的心意—-神把人置定为祂的立约伙伴。虽然两个人都声称人的这一超越特征即使在罪人中也仍然存留(CD, III/2, 页221),但是,对巴特来说,这不是由于一个既定事实的不可侵蚀性,而完全在于自由的神的信实(CD, III/1, 页200):在巴特看来,神的心意比任何既有的实体都更可靠。
由于巴特提出“神的形象”当指一种以爱的共存于合作为特征的神性生命,所以,“单个的人不能算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CD, III/1, 页290)。从这一点看,巴特的人学其实先天地带有入世的伦理维度[12],因为为着他者是神在开始造人时就规定了人存在的基本特征。而尼布尔的人学则尚未完全脱离近现代人本哲学的思维套路,虽然他对人的存在的分析要极力将现代人从人本主义的自我中心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他从坚持堕落后的人残留的原初的完美出发号召人追求眼前的相对的善,其形而上的基础稍嫌薄弱。
当然,至于究竟什么是神的形象,在教会历史上也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很难下一个绝对的结论。但是,也许我们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谓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应该关乎人的整个存在,而不应该企图将它定位于人的某一特性或官能。根据创世纪,神说的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而不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形象放在人里面(或上面)”。这告诉我们整个造人的事件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进行的,不存在一个先前造好的人,然后神再把祂自己的形象打在他上面,也不存在一些先有的人的素材,然后神再把这些人的素材塑造成祂自己的形象(这也许可以用于神对已经造好的人的生命的塑造,但是神用泥土造人,不等于神把泥土捏成祂自己的样子)—-这不同于神把自己的气息吹入泥土所造的人里面。在这一点上,巴特的解释似乎更符合第一段创世叙述(创1:1-2:3)中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之说,而尼布尔指出的人的自我超越的特性则更适用于解释第二段创世叙述(创2:4:14)中提到的神向泥土造的人所吹的那一口气。而且,若所谓“神的形象”单指自由的灵性,那么一切有这种灵性的被造(比如,天使)就都有“神的形象”,但是,《圣经》上只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巴特意义上的“神的形象”要以神所赋予人的一些官能,例如,语言和思维的能力、主体的能动性,为条件。
除此以外,巴特用新约中耶稣是“神的像”的字句来解释旧约中“神的形象”有待商榷。因为他的这一言论首先未加考察就简单地把新约希腊语中的“εικων”等同于旧约希伯来语的“tselem”,虽然“εικων”是“tselem”对应的希腊语翻译,而且两者在英语里都被译为“image”(德语,Bild),但是,新约中提到耶稣是神的像和旧约中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语境相去甚远:因为耶稣是神的“像”,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看见神自己,但是看见了耶稣就等于看见了神;而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应该是指神赋予人某些祂自己的特征,这并不等于说在堕落前的亚当反观自己就好像看见了神。“像”比“形象”有更高的明确性和可视性:“像”是对其所指的事物的直接直观的反映,而“形象”则涉及对其关涉的事物主体性的总体的把握。在这里,中文和合本圣经将一处译为“神的形象”、而另一处译为“神的像”,是很有见地的。
而巴特和尼布尔关于堕落之后的神的形象的看法都是各自对神的形象和罪的诠释的自然结果。至于尼布尔对巴特关于堕落后神的形象的观点的伦理学批判,在这里,也许对尼布尔和巴特的两个人的神学都有所学习、并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的朋霍费尔的意见可供我们借鉴。面对尼布尔在《人性和人命》中对巴特的罪论的批评,朋霍费尔表达了对巴特的同情:
“在[一]战前我们活得离神太远了;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全能和公义。我们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良善的民族,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努力过于自负,我们对我们在科技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进步感觉过于良好,并且我们把这种进步等同于神的国的到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觉得太幸福了太满足了。然后,巨大的幻灭来到了。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无能和软弱,我们突然从梦中惊醒,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愆,我们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13]
不过,对于关于巴特的罪论的消极后果的指控,最有力的反驳当来自巴特神学本身—-巴特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作为出发认识罪,不仅全面彻底地揭示罪的种种特性,更重要的是,他在毫不留情地指出人无望的处境的同时,带人看到出路,这条出路不是人自己的某种可能性,而是神预备的恩典之路。不管人的罪有多大,神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胜过了它;罪只能作为那被神“摈弃、咒诅和排斥”的而存在,它是“绝对的不可能”。(CD, IV/1, 页409-410)而且,如但尼尔•米格里沃(Daniel L. Migliore)指出的,巴特的罪论提出,人的罪不仅在于想要和神一样,也在于无视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和救恩,自甘碌碌。[14]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理由懒惰。大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巴特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就没有停止与纳粹势力作斗争,直至1935年他被吊销教职,不得不离开德国。即使在他回到瑞士以后,也毫不含糊地坚持,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15]
彼时,尼布尔身处纳粹势力影响之外的美国,要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影响现实政治当然有诸多便利,可是甚至在1941年6月法国等西欧国家沦陷之后,他虽然认为,美国应该在战备资源上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却反对美国直接参战[16]。直至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于次日正式加入反法西斯的阵线。而地缘和文化历史渊源与美国都很接近的加拿大,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就对德宣战,并于1940年6月对意大利宣战。司格特•鄂尔温(Scott Erwin)指出:1938年至1945年间尼布尔一直在思考基督徒应该如何一方面承认人类共同的罪性,一方面在历史中区分善恶做出相对恰当的道德选择。[17]但尼布尔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表现出的优柔寡断是不是正暴露了他从分析人的此在出发的伦理学缺乏巴特从神的作为出发的人学和伦理学的高度和气概呢?
当然巴特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强调,神学是教会的工作,并且呼吁同僚专心研究神学,“就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18],但巴特所言旨在拒斥世俗政治对神学和信仰的影响,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宣讲的唯一根据和指导,并非要基督徒和神学家不问世事。巴特虽然强调一切从神出发,从耶稣基督出发,但他并非无视人此在的具体环境,相反,他非常看重神人相遇的具体性:人要在此时此地以实际行动回应神恩典的作为。所以,伍尔夫•克汝特克(Wolf Krötke)认为,“巴特的神学在与人的实际存在相关联时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征”,[19] 而巴特又终极地把他的人学和伦理学建立在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和作为的基础之上,是以他的人学又“显示了人作为神的伙伴和神的形象在其被造的关系中所享有的丰富的可能性”。[20] 事实上,克汝特克见证到,巴特从神出发建立的人学使得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至少在德语世界极具影响力。[21]
当然,巴特从不忘记强调神人之间无限的质的区别,强调人根本的堕落,这只使得巴特直言不讳地反对“所有将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置于某种理念形态、概念或系统之下的人为的意识形态”。[22]所以,在战后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上,巴特一视同仁地对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拒绝偏袒任何一方。而尼布尔在二战后支持美国反共,甚至认为,教会也应该加入其中,而当世界基督教大会采取巴特的建议在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中保持中立时,他极不乐意。[23]那时,他是不是又忘记了自己曾经坚持的人类的普遍罪性的原则呢?
注释
[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I/1, trans. by G. W. Bromiley, (Edinburgh: T&T Clark, 1975).
[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人性与人命:一个基督教的解释》), vol.1, intro. By Robin W. Lovi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3] 布汝讷所持的这种便是观点。他认为神的形象有“形式上的”和“质料上的”意义的区分,人形式上的神的形象是指人有语言能力,是理性的要承担责任的主体,而质料上的神的形象指的是人和神、和人之间爱的关系。罪所破坏的是质料上的神的形象,却不能抹杀形式上的神的形象。见Emil Brunner, “Nature and Grace”(〈自然与恩典〉),载Natural Theology(《自然神学》),Peter Fraenkel译, (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2), 页23-24、31-32。
[4] 斜体由本文作者添加。
[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III/1, trans. by J. W. Edwards, O. Bussey and H. Knight, (Edinburgh: T&T Clark, 1958).
[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III/2, ed. by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trans. by H. Knight and G. W. Bromiley, etc., (Edinburgh: T&T Clark, 1960).
[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IV/1, ed. by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trans. by G. W. Bromiley,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8] 欧力仁在〈巴特的神学人学〉一文中说,巴特在1934年反驳布汝讷时认为“人类堕落之后,[神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而到了1945年写《教义学》三卷一册时,他发现根据创世纪1:26,“人类不是被创造而成为(created to be)上帝的形象,只是按照(created in)该形象被造而已。…人类根本未曾拥有过该形象…[从而]无所谓失去。”(载欧力仁、邓绍光编,《巴特与汉语神学II—-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道风书社,2008,页274、275)。我认为首先,将巴特所说的“annihilation”说成“荡然无存”是不准确的,其次,区分人被造“成为”神的形象和人“按照”该形象被造,至少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巴特在《教义学》三卷一册中甚至有人“是”神的形象的字句(CD, III/1, 页184)。
[9] 或者更准确地说,巴特认为,罪人不能改变神对人之所是的置定:人还是当为着神,还是处在和他人的相互联系中,还是具有身体的灵魂,还是存在于有限的时间段中,等等(CD, III/2)。在这里,也许汉语比英语更有利于说明问题,对应于英语的“good”,汉语有“善”和“好”两个词,也许我们可以用“善”专指主观之德,而“好”主要指客观事物的正面属性,虽然也不排除“好”可以指人的德行。中文和合本圣经也说,神看祂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创1),而“良善”是圣灵所结的生命的果子(加5:22)。
[10] 在这个问题上,赖品超在〈从佛学看巴特的罪观及人性论〉一文中还提醒我们,即使是基督教传统所说的“原罪”巴特也倾向于把它称为“原初的罪(Ursünde)”而不是“承继的罪(Erbsünde)”,“以此否定任何对罪的宿命论的或自然主义的理解。”(载《巴特与汉语神学II》,页506。)Allen Jorgenson在〈卡尔•巴特对罪的基督论处理〉(“Karl Barth’s Christological Treatment of Sin,”载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苏格兰神学期刊》),54.1[2001],页451)一文中对这一点也有提及。
[1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III/4, ed. by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trans. by A. T. Mackay and T. H. L. Parker, etc., (Edinburgh: T&T Clark, 1961).
[12] 如Andy Alexis-Baker在“Theology is Ethics: How Karl Barth Sees the Good Life”(〈神学就是伦理学:卡尔•巴特如何看待幸福人生〉)一文中强调的,巴特的神学通过揭示人是谁(即被神拣选为立约伙伴)和人存在的目的(为着神也为着人)告诉人该做什么。见Scottish Theological Journal(《苏格兰神学期刊》)64.4[2011],页425-438。
[13] 转引自Josiah U. Young,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Reinhold Niebuhr: Their Ethics, Views on Karl Barth and Perspectives on African-Americans”(〈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他们的伦理学、对巴特的看法和关于非裔美国人的观点〉),载Peter Frick编, Bonhoeffer’s Intellectual Formation(《朋霍菲尔思想的形成》)(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8),页289,注30。
[14] Daniel L. Migliore, “Sin and Self-loss: Karl Barth and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Sin” (〈罪和自我迷失:卡尔•巴特和女权主义对传统罪论的批评〉),载Walter Brueggemann & George W. Stroup编,Many Voices One God: Being Faithful in a Pluralistic World (《一个神多种声音: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保持忠心》),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8), 页149。
[15] Scott R. Erwin, The Theological Vision of Reinhold Niebuhr’s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Battle and Above It”(《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美国历史中的讽刺〉之神学异象》),(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页70。
[16] Erwin, 页68-69。
[17] Erwin,页53。
[18] Karl Barth, Theological Existence To-day: A Plea for Theological Freedom(《今日神学的存在:呼吁神学自由》),
R. Birch Hoyle译,(London: Hodder& Stoughton, 1933), 页9。转引自吴国安,《启示与历史—-从〈教会教义
学〉卷一看巴特的历史观》,载《巴特与汉语神学II》,页151。
[19] Wolf Krötke, “The Huma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in Karl Barth’s Anthropology” (〈卡尔•巴特人学中人的人性〉),Philip Ziegler译,载John Webster编,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rl Barth (〈剑桥巴特指南〉),(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页173.
[20] Krötke, 页173.
[21] Krötke,页171.
[22] Krötke,页73.
[23] Erwin,页102-105。
作者简介
成静,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学士,耶鲁神学院道学硕士、神学硕士,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系统神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现任教于福建神学院。
往期文章
寺园喜基 | 战争中的日本基督教会:关于接受德国神学的第一波、第二波
瞿旭彤: 比自由神学更自由:试从巴特对神学实事性和科学性的探讨看其神学与自由神学的差异
曾劭愷 :巴特與自由神學:回應瞿旭彤教授「比自由神學更自由」一文
郭偉聯:巴特神學中的三一上帝啟示與信仰的類比:雲格爾的詮釋之神學意含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Lea、Vanci、imaginist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