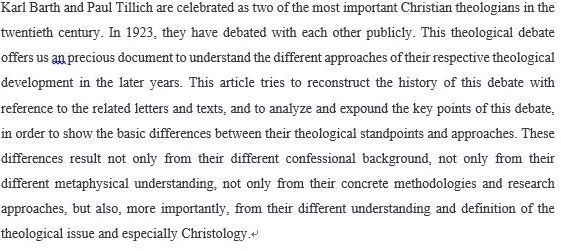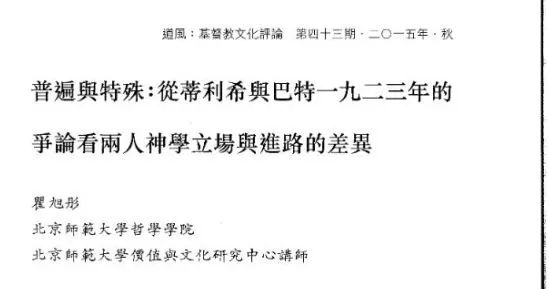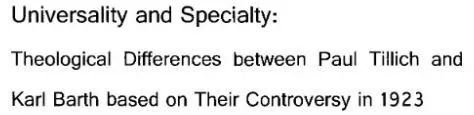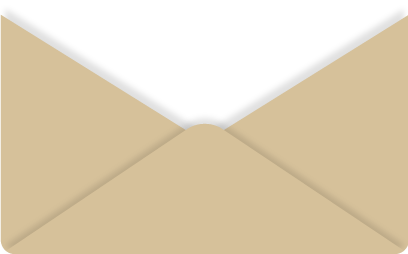编者按
同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巴特与蒂利希有过多次思想交锋。上周推送的杨俊杰老师的《蒂利希的“时候”和“时候意识”:论蒂利希的巴特批评的历史神学之维》一文就巴特与蒂利希的历史观差异进行了比较,并且提到,蒂利希对巴特历史观的批评,与二者在基督论方面难以调和的差异直接相关。这种差异在瞿旭彤老师的此篇文章中将进一步得到说明。以巴特和蒂利希一九二三年的论战为线索,瞿老师耐心细致地梳理分析了二者在神学立场与进路上的差异,生动再现了两位神学大家相互肯定又针锋相对的精彩对话。蒂利希坚定地批判巴特偏执于否定,并非真正的辩证神学;巴特沉着回应,反问为何必须以蒂利希所理解的“肯定”为辩证的辩证扬弃。蒂利希“善意地改良”,建议回到肯定性悖论;巴特无一例外地予以拒绝,并指出其出发点有误。相比巴特对蒂利希的认真研读,蒂利希对巴特的理解却不够深入,因此,蒂利希的指责被瞿老师形容为“误解性批判”,但也正是在此处突显出蒂利希神学的特色与力量。二位神学巨人的思想碰撞火光四溅,从中我们也可窥见错综复杂的现代神学面貌。
本文原发表于《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5年总第43期。推送时已获期刊和作者本人授权,感谢《道风》和瞿旭彤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文章(包括信息量相对较大的脚注部分)长度约19000字,阅读时长约18分钟。
Tillich
Barth
中英文摘要
巴特與蒂利希堪稱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二位基督教神學家。 兩人在1923年曾展開公開的神學論戰。這場論戰為我們理解兩人日後神學發展的基本進路與根本差異提供了寶貴的文本資料。本文試圖回顧此次論戰的緣起,梳理和闡述論戰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並參照之後的相關文字或作品,分析和總結兩者在神學立場與進路的根本差異。筆者認為,兩者在神學上的差異不僅來自他們各自的宗派背景,不僅來自他們所推崇的不同哲學與形而上學,不僅由於具體的方法論和研究進路,而且更是由於他們對神學實事(特别是基督论)的不同理解與規定。
一九二三年,不管對巴特(Karl Barth)個人而言,還是對二十世紀辯證神學運動和之後基督教神學思想史而言,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年。[1] 該年一月,辯證神學運動機關刊物《在時代之間》(Zwischen den Zeiten)創刊。在刊物出版當月,巴特先前的神學大師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在自由神學機關刊物《基督教世界》(Die Christliche Welt)公開發文,批評新興的辯證神學運動。巴特隨即加以回應並與之論戰。[2] 這場論戰既標誌着巴特神學和辯證神學運動的獨立與成長,也意味着他們與自由神學的公開決裂。但是,對未來神學發展更有指標意義的不是巴特與哈納克之間的這場論戰,而是同年底巴特與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和辯證神學運動同道中人[3]蒂利希(Paul Tillich)之間的一場論戰。[4] 巴特與蒂利希均是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基督教神學家。[5] 兩人在早年的這場論戰為我們理解其日後神學發展的基本進路與根本差異提供了寶貴的文本資料。本文試圖回顧此次論戰的緣起,梳理和闡述論戰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並參照之後的相關文字或作品,分析和總結兩者在神學立場與進路的根本差異。
一、論戰之緣起
一九二三年,《神學報》(Theologische Blätter)主編施密特(Karl Lugwig Schmidt)邀請蒂利希撰寫一篇關於巴特等人的論戰文章。不過,此邀請並非出於一時興起,乃是因為蒂利希「早就」答應要寫一篇這樣的文章(349)。蒂利希雖對巴特(及其《〈羅馬書〉釋義》[Der Römerbrief]第二版)讚賞有加,[6]並引之為同道中人,但其實「早就」有所不能贊同,[7] 由此才會對施密特表示,「早就」有意撰寫文章與巴特展開爭論。[8]
據現有材料,蒂利希所說的「早就」至少可追溯至他在一九二二年初與巴特在哥廷根(Göttingen)的兩次長時間交談。據巴特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寫給圖爾奈森(Eduard Thurneysen)的信,[9] 此次見面出自希爾施(Emanuel Hirsch)的安排,[10] 他和蒂利希原屬同一學生社團,[11] 雖比巴特和蒂利希兩人年輕,但早在一年前就已成為哥廷根大學教席教授。[12] 這次會面,巴特還曾與蒂利希單獨談話,兩人坦誠相見,「願意思想和期待彼此的最好」,並且熱烈交流。[13] 對巴特來說,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蒂利希「『反對正統的怨恨』及其歷史神話學」。[14] 此外,蒂利希還談及有條件者和無條件者,以及歷史中的「無條件的『神律』(theonomen)階段」。[15]
上述說法得到蒂利希本人的證實和補充。也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蒂利希致信友人弗里茨(Alfred Fritz),講述他的哥廷根之旅。此行是「第一等級的提神,一次從神學『行省』出發的旅行:從柏林進入神學的中心」。[16] 在三人進行的第一次談話中,蒂利希同意希爾施對巴特的批評:巴特關於基督、復活和終末論的系統並不連貫一致,其思想源自布魯姆哈特(Johann Christoph Blumhardt),可被稱為「超自然主義」(Supranturalismus)。[17] 與此同時,希爾施認為,蒂利希的思想相較而言是連貫一致的和異教的。此外,巴特神學過於否定歷史-批判法,可能會消解「科學的嚴肅」,因而比蒂利希「真誠的異教」更危險。[18] 在蒂利希與巴特兩人單獨進行的談話中,[19] 主要話題是歷史哲學。這次談話明顯體現出兩人的對立:巴特是「超自然的終末論者」(supranaturaler Eschatologe),對歷史毫無興趣,而蒂利希注重「『神律』時代」(“theonomen” Zeitalter),對歷史饒有興趣。最後,兩人達成共識,巴特應「理性化其超自然的說法」(supranaturalen Formeln),而蒂利希則應「通過超自然的均衡其理性的[說法]」;巴特想作為一名《聖經》神學家(Bibeltheologe)宣講甚麼是無條件者的本質,而蒂利希則願作為一名文化神學家(Kulturtheologe)進行宣講。[20]
哥廷根大学
此次哥廷根會談堪稱現代神學思想史的重要篇章。巴特和蒂利希這兩位之後的神學巨人對彼此的理解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均可追溯至這次會談所表達出的不同立場、取向與進路。如叔斯勒(Werner Schüßler)指出的,希爾施在一九二二年就已看出巴特與蒂利希神學思想發展的不同進路與發展,並將兩者歸屬於不同的思想類型:巴特神學是「超自然主義」的,因而是「非科學的」,而蒂利希神學則是異教的,因而是「非基督教的」。這也是一方為甚麼主張聖經神學、另一方主張文化神學的根本原因。[21]
此後,據圖爾奈森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寫給巴特的信,蒂利希儘管在基礎方面與巴特有相當多的一致之處,但還是不想從巴特知道甚麼,因為他認為,巴特的態度中有「某種毫無行動的-懶散的東西」,巴特神學將會結束於「超自然主義和敬虔主義」。由此,圖爾奈森提醒巴特,對蒂利希要持有一種有所保留的態度。[22]
二、蒂利希的贊許與批評:從批判性的悖論回到肯定性的悖論
在一九二三年的公開批評文章中,蒂利希開宗明義地表示,「不太情願」與巴特等人的思想展開「論戰(Auseinandersetzung)的嘗試」(351)。[23] 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他因為非常肯定他們所做的批判性否定,並且認為,應該在教會內繼續推進。然而,正是為了更好推進這樣的批判,蒂利希認為,要防止對手利用巴特等人立場的「弱點」來阻止這樣的批判。由此,蒂利希「敢於」展開論戰的嘗試,試圖在認可巴特等人批判性否定的同時,指出其批判性否定之所以得以可能,乃是出於肯定(Position,又有「立場」之意),這一肯定乃是否定得以可能的基礎(Boden)。
由此基礎出發,蒂利希認為,必須辯證理解無條件者和有條件者之間的關係。他之所以要認可巴特等人的批判性否定,乃是因為這種否定有助理清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種直接的、非悖論性的、沒有經過持續和徹底之否定的與無條件者的關係,不是與無條件者的關係,而是與有條件者的關係,這樣的有條件者提出自己是無條件者的要求,其實卻成為偶像」(351)。[24] 那些應該表達悖論的東西和詞語,比如宗教和《聖經》、基督和上帝,都有可能成為偶像,由此處於持續的危險之中。
與此同時,蒂利希認為,不應僅停留於否定性批判。巴特等人所強調的否定性辯證和危機神學必須以一種肯定為前提,而這種肯定自身不再是辯證的。否則,辯證的自我揚棄就陷入無限,沒有止盡。這種並非內在辯證的、對辯證肯定的真實揚棄必須從無條件者那裏尋找。由此,蒂利希提出他的核心觀點和對巴特的最大提醒:要從批判性的悖論回到肯定性的悖論。一旦如此,就可以自由和辯證地看待所有的肯定。一切都是辯證性肯定的因素,一切都處於審判與恩典的統一之下。肯定性恩典是否定性審判的前提,「若是沒有與恩典的統一,審判就是自然過程」(353)。
接着,蒂利希從如下三方面省察他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上帝與自然的關係、上帝與精神的關係,以及上帝與歷史的關係。就上帝與自然的關係而言,蒂利希認為,不應該像巴特等人那樣拒絕談論創造的秩序,[25] 全然否定人從自然出發認識上帝的可能性。蒂利希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辯證地看來,一旦談及審判、非理性或死亡在世界、自然或生命中顯明出來,那麼,那些對世界、自然和生命的相應肯定都已是預先設定的前提。第二,自然的非理性所顯明的,並不僅是世界的絕望處境,而且是上帝值得敬拜的無限尊榮。最後,朝着天上的飛鳥、田野中的鮮花看去的目光所見到的,絕不僅是審判,而且有創造生命的恩典。當然,蒂利希也承認,審判和恩典是悖論地統一的,只對信仰的眼睛顯明。倘若只看到恩典,而不看到審判,這是[自我]神化的理念論(vergottender Idealismus),即試圖直接和悖論地把握無條件者和有條件者在自然之中的統一。[26] 倘若不顧與恩典的悖論統一,只把有條件者在自然中的摧毀看作自然過程,這是有魔性的實在論(dämonischer Realismus)(353-354)。在蒂利希看來,這兩者都是不應該的,而且都遠離啟示。為了說明這些,蒂利希特地強調了他對三一論的理解。三一上帝向外的做工是不可區分的,這些做工始終都同時出自聖父、聖子和聖靈。這也就意味着,創造的秩序和拯救的秩序是相互屬於的,創造和拯救中所展現的恩典行為是不可區分的同一個行為,「創造朝向拯救,被設定為以拯救為序,拯救已在創造中被先天地賦予」(354)。[27]
就上帝與精神(Geist,或譯為「靈」)的關係而言,蒂利希認為,人的精神也屬於創造。辯證性肯定不處於審判之下,並非人類困境的表達,而是真理。人的精神能夠宣揚這一真理,因而是啟示的場所。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由恩典與審判的統一所承載。在人的自律(Autonomie)中,始終既有啟示,也有遮蔽,始終既有神性,也有魔性。神性者與魔性者之間的鬥爭,聖靈與非聖之靈之間的鬥爭,創造原則與毀滅原則之間的鬥爭,正是精神歷史最為深刻和隱藏的內容。
蒂利希認為,危機神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以最大的能量反對宗教的非悖論的絕對性訴求。他甚至認為,巴特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所寫的每一相關文字都是在摧毀偶像崇拜(355)。但是,蒂利希指出,辯證性的自我揚棄不能揚棄此一否定的基礎,即宗教性的肯定(die religiöse Position)。「在所有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文化中,都存在顯明源初(Ursprung)的[……]、在信仰之眼中啟示恩典和審判的現象」(355)。在蒂利希看來,這正是文化和宗教的「深層意義」(Tiefsinn)。這一深層意義不能被對象性地和直觀性地看到,只能在是與否的統一中辯證地和信仰地看到(355-356)。[28]
就上帝與歷史的關係而言,歷史也是有條件的,因而不能把歷史設定成無條件者。如同自然和精神一樣,歷史是陷入困境的人之似神性(Gottähnlichkeit)的場所,處於憤怒之下。但是,這樣關於危機的判斷只有在肯定立場上才是可能的,而這一肯定立場本身並不處於這一判斷之下。在蒂利希看來,在歷史之中,否定性悖論的肯定性根基最為清楚地顯明;因為危機的宣講是歷史,而其內容是歷史性的內容。「凡是這一消息得以宣講的地方,就是啟示在歷史之中的場所。[……]在歷史之中自我實現和承載歷史的啟示,是非直觀的」(357)。
巴特等人拒絕這一思想,並沒有看到危機神學的肯定性根基,但又被迫在歷史中尋找關於危機的宣講得以奠基的一種肯定。「這一啟示的地點就是基督。在基督論上,肯定性悖論與否定性悖論之間的對立達到決定性的解決」(357)。巴特等人在歷史中劃出「一件一次性的歷史性事件」(Ereignis),在這一事件中,歷史被設定是被揚棄的,並且被設定了一個絕對的新。在基督裏所發生的,完全地發生於人之彼岸,但卻發生在歷史人物拿撒勒的耶穌身上。這一發生是「單純的客觀的歷史事實」,雖發生一次,但卻是一勞永逸的(357)。[29] 蒂利希認為,巴特這樣的觀點表明,批判性悖論的神學在尋找自身批判基礎的過程中成為肯定性的荒謬神學,並且由此放棄自身的前提。在他看來,巴特等人必須承認,「這一經驗事實是指向在此事實中非對象性地顯明的無條件者的指引(Hinweis)」。「信仰也不是對荒謬的肯定之工,而是成長於非直觀性的啟示史的立場之上,這一歷史隱蔽地貫穿歷史,並且在基督裏找到了它完全的表達」(358)。
在從上述三個角度批判巴特等人的神學之後,蒂利希最後總結道,其神學有其正確之處,即「反抗那些對無條件者的非悖論性的、直接性和對象性的理解」(358),但未注意到,其自身還有一個本身不再是危機的前提,即創造和恩典。只有穿過危機,才能悖論性地言說這一前提,而且必須落實到自然和精神、文化和宗教來言說它。與上述三一論神學框架相應,蒂利希認為,對這一前提的言說有如下三種方式。第一,從創造的角度看,這一前提是永恆的源初(Ursprung)與根基(Grund und Abgrund),通過各種處於是與否中的受造者非直觀和非被給予地向信仰顯明出來。第二,從拯救的角度看,這一前提是永恆的拯救,它只向信仰顯明,作為隱蔽的、在基督裏的、藉着完全的象徵力量展現自身的拯救史,非直觀和非被給予地穿過歷史及其各種創造。第三,從完全的角度看,這一前提是永恆的完全,是非直觀的應許;在這一應許中,源初的雙義性、神性者與魔性者之間的鬥爭在上帝裏的永恆統一中被揚棄。由此,批判性悖論的神學,不單單是辯證地、而且真實地將自己置於悖論之下,從而成為肯定性悖論的神學(358)。
三、巴特的「反批判」[30]:基督就是那肯定性的悖論
在巴特做出回應前,圖爾奈森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向巴特寫信說,撰寫上述文章的蒂利希如同一頭獅子,試圖在神學競技場內宣告自己的即將出場。在圖爾奈森看來,蒂利希神學帶有「大城市氣息」(Großstadtgewächs),不僅罕見地造作,而且缺乏《聖經》基礎,試圖逃避啟示。因此,他對巴特的回應甚為期待,希望巴特儘快出手,讓蒂利希這頭獅子安靜下來。[31] 在稍後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巴特寫信給戈加滕(Friederich Gogarten)說,「我當然無一例外地拒絕了蒂利希的改善建議」。[32]
在公開發表的回應中,如同蒂利希的開場白一樣,巴特一開始也表示,「不太情願」公開地與蒂利希交談。原因之一在於,他和蒂利希雖在各方面都有不小差異,但彼此還算接近。[33] 因此,巴特不太樂意於在不相干的眾人眼前演一出戲,講述自己與蒂利希的差異。[34] 不過,既然蒂利希已公開發表文章,他也不應保持沉默,而是做出回應。[35]
首先,巴特表示出對蒂利希主要觀點(批判性否定應以某種肯定立場為基礎)的理解,並且認可他批評和指正的權利。但是,巴特接着明確指出,蒂利希的出發點有問題,即他認為巴特等人沒有看到危機神學的肯定性根基,就好像他們必須等待他的啟蒙一樣。蒂利希以為巴特「沒有聽說過的新東西」,對巴特來說,其實至少數年以來並非一無所知(359-360)。
接下來,巴特試圖理解,蒂利希為甚麼自以為找到了「瑕疵」或「漏洞」。在巴特看來,蒂利希其實並未嚴格停留於神學的實事,並未讓神學成為神學,並沒有從神學的問題出發,而只是從某種文化哲學的問題出發。[36] 巴特認為,倘若蒂利希承認其前提是「外在的」、「典型的非神學的」,[37] 蒂利希完全有理由拒絕巴特對其前提的抗議(361)。
儘管彼此有着迥乎不同的進路和出發點,巴特還是嘗試比蒂利希自己更好地理解蒂利希的文章,[38] 考察和改善其對肯定性悖論的理解和規定(361-362)。蒂利希認為,巴特等人把批判性否定絕對化了。在巴特看來,蒂利希之所以這樣指責,乃是因為,蒂利希只是偶爾閱讀過巴特等人的作品或者見過他們本人,[39] 就懷疑他們偏執於否定,並且還自以為找到了危機神學的「致命弊端」(362)。[40]
與蒂利希的觀點恰恰相反,巴特針鋒相對地指出,「對(作為肯定的)辯證的辯證揚棄肯定是、而且始終是辯證的」,而不是不再是辯證的(363)。在此意義上,巴特所理解的「危機」,不是蒂利希所理解的「持續且徹底的否定」(351)或者「禁止」,而是「警告」或者「提醒」(364-365,即提醒不要忘了危機)。在具體情況下,「危機」也可能意味着肯定和誡命。由此,巴特反問蒂利希,為甚麼辯證的辯證揚棄必須是蒂利希所理解的「肯定」,「為甚麼它就應該完全不能是指引,而且不是指向某種他者、而是指向那個他者、指向『真實揚棄』的指引」(364)。[41] 巴特認為,倘若蒂利希不能證明這個必須和這個不能,那麼,他就看不出自己為甚麼有必要接受蒂利希的指導,因為蒂利希並未說到問題的要害。
由此,巴特轉向談論問題的要害,即被指引所指向者,也即蒂利希的核心要點「肯定性的悖論」。巴特認為,蒂利希沒有講清楚甚麼是「由無條件者而來的真實揚棄」,並對此提出多項質疑。在巴特看來,以為不靠外力就可通過己力擺脫困境,這很可能只是「哲學的謊言」。巴特同時也對蒂利希的「無條件者」概念提出質疑。[42] 倘若一旦認識到無條件者是肯定性悖論的前提,就可理解「上帝」一詞所可能導致的偶像崇拜式理解,就可認識到這種理解的微不足道,那麼,蒂利希為甚麼還要禁止神學家使用「上帝」一詞,而且這種禁止並非神學家所應遵守的誡命。[43] 不過,最讓巴特感到沉重的、感到「陌生」和「不能理解的」乃是,在蒂利希的方法中,哲學或形而上學多過神學,蒂利希所講的肯定性悖論,不過是一個X。[44] 即使巴特在具體觀點上可能對蒂利希有所認同,但是在根本的方法和進路上,他並不認同蒂利希的思想,認為它作為神學是「不值得信賴的」(367)。
由此,巴特開始批評蒂利希根據上帝概念所展開的對上帝與自然、與精神、以及與歷史關係的討論,並提出三點具體反對意見。第一,巴特認為,蒂利希文章充斥陳述句(Indikative),以此指向大量的對上帝與世界或人之間關係的非悖論性規定。但是,肯定性悖論強調的首先是悖論,而不是上帝與世界或人之間的統一。其次,蒂利希關於審判、恩典和啟示的說法,恰恰與其所反對的對「上帝」一詞的偶像崇拜式使用一樣,表達了「對基督教思考和言說的粗野化」。肯定性悖論強調的不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不能以蒂利希這種想當然的確信方式隨意談論審判和恩典。第三,巴特反對蒂利希對上帝與世界和人之間關係的普遍化,認為這是一套「關於信仰和啟示的寬泛且普遍的套話」。這樣所談論的上帝不是「路德和基爾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的上帝」,但類似「施萊爾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和黑格爾的上帝」(369)。巴特認為,作為神學家,在談論肯定性悖論時,也就是說,在談論上帝的悖論時,應避免蒂利希的「直接」、「輕鬆」和「慷慨」。因為上帝的悖論不僅與「不可直觀的」有關,而且與上帝自身的自由意志有關。與蒂利希不同,巴特所理解的啟示「不是某種普遍地、以陳述句形式規定的、只需等待人來發現的關係,不是某種隱秘的被給予狀態,而是一種特殊的、單單由上帝所開啟的,單單由我們去認知(在我們被上帝認知之後)的發生(Geschehen),一種從位格到位格的事件(Ereignis)」(369)。
路德(左上),施莱尔马赫(右上)
黑格尔(左下),基尔克果(右下)
正是在上述對於肯定性悖論的理解上,巴特與蒂利希分道而行。巴特認為,這也正是蒂利希在其思想中發現所謂漏洞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巴特看來,肯定性悖論首先不是神學科學認識的客體,而是不受人的思想與認識所支配的主體。[45] 兩人這樣在進路和出發點的差異與對立,特別清楚地體現在基督論和與此相關的對啟示的理解上。[46] 對巴特而言,「基督就是那肯定性的悖論」,「基督就是那拯救史,拯救史自身」。而對蒂利希而言,「基督就是某種在完全的象徵力量中或多或少始終而且到處發生的拯救史的[具體]呈現」(370)。巴特認為,蒂利希對肯定性悖論之悖論的規定是不完全的,忽視了上帝的自由與愛;蒂利希雖正確反對了「人神」(Menschgott),即從人到神的偶像崇拜,但有可能陷入最嚴峻的反對「神人」(Gottmensch,即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具體而特殊的啟示)的危險之中。在巴特看來,對「受洗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學家」而言,而不是對普遍性的世界、宗教、文化和人而言,這啟示可用陳述句形式表達出來,即「根據《聖經》見證和教會認信,『有』(es gibt)一個合格的(qualifizierte)、作為那拯救史的那場所的歷史」,這就是那獨特的肯定性悖論,它「不單單是不可直觀的,而且首先是上帝獨特的、位格的、真實的(要理解為具有一次性和偶發性特徵的!)自由與愛的行動(371)。
由此,肯定性悖論或者啟示本身也是悖論的和辯證的。一方面,由於上帝自身的主權,由於啟示發生的一次性和偶發性,這樣的啟示雖在歷史中發生,與經驗事實密切相關,卻是不可直觀和不可對象化的,不能通過可直觀的歷史關聯找到,也不能通過抽象得來。另一方面,這一啟示是上帝尊榮在其過去的、具體特殊的卑微中的啟示。在此語境中,巴特旗幟鮮明地徵引改革宗的基督論傳統(以及迦克墩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的基督論傳統),為的是明確表明他與蒂利希所遵循之基督論傳統的差異。巴特所遵循的傳統認為,耶穌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穌,兩者雖可區分,但不可分離。而蒂利希所遵循的傳統則不僅試圖區分耶穌和基督,而且借用象徵理論將之分離,「通過啟示否定這一[道成肉身]歷史的單一資質」(singuläre Qualifikation),即否定這一歷史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並且由此出發「通過啟示宣稱所有歷史的資質」(373),即強調所有歷史都可能成為上帝的啟示。
在回應的終結部分,巴特試圖理解蒂利希作為神學家所展開的「謎一般」批判。他揣測到,一方面,蒂利希可能始終還觸動於現代人對宗教大法官的攻擊(374),帶有強烈的護教動機,而不太重視宣教。另一方面,蒂利希「對正統的怨恨」導致他很難正確理解(特殊的)肯定性悖論,即《聖經》所見證的和教會所認信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特殊啟示。當然,巴特也承認,蒂利希的文章整體而言不僅態度友好,而且充滿認可。巴特希望自己的回應也同樣如此。但是,蒂利希試圖糾正危機神學的漏洞,恰恰攻擊了對危機神學來說至關重要的決定性要素。對巴特來說,神學不是沒有前提的,而這前提也不是普遍的「神律」。「不單單是上帝,不單單是基督教,還有教會,[不僅僅是神聖的普遍教會,而且還有我們所屬的個別教會],是神學的前提」(375)。由此,巴特得出最終結論,他與蒂利希之所以發生衝突,乃是因為他「對神學之真理概念與教會、正典、聖靈這些概念不可消解之關聯的指引」(375)。
四、蒂利希的回應:對精神處境的反思
在讀到巴特的「反批判」後,蒂利希只想「快且短地」加以回應。同時,他也指出,他與巴特展開對話的目的「完全是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分開」(376)。
蒂利希的回應着重於談論其哲學-神學工作的精神處境,他首先贊同巴特從精神處境出發理解其思想的努力,並且明確指出,他的哲學-神學工作,包括他對巴特等人的肯定性與否定性批判,正是對宗教大法官及其隨從的反抗。[47]
由此出發,蒂利希認為,若從普遍的角度看,巴特神學以真理概念、正典、教會和聖靈為前提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緊接着指出,問題在於,這樣的普遍性看法對「我們的精神處境」而言究竟意味着甚麼。在現有處境中,我們不可能想當然地按照《聖經》的詞語與教會的言說直接言說上帝,不可能直接地說出其中的本質性意義。我們必須間接地言說無條件者。我們也不可能直接地把(具體特殊的)耶穌基督當作肯定性悖論加以言說。耶穌基督之名有可能會被濫用。假若基督之靈與耶穌基督之名是同一的話,那麼,褻瀆耶穌基督之名就會受到詛咒,而宗教大法官就是對的。
改革宗神学家加尔文
與巴特所持守的強調特殊啟示的改革宗基督論傳統(以及迦克墩大公會議的基督論傳統)不同,蒂利希主張,應從強調普遍啟示的邏各斯和基督之靈出發從事神學。[48] 因為(普遍的)基督之靈才是肯定性悖論,並不會窮盡於耶穌基督這樣特殊的經驗現象之中。而且,神學從未宣稱過,肯定性悖論有着絕對的偶發性。神學講得更多的是邏各斯,[49] 神學應該跟隨邏各斯的道路,[50] 並竭力搞清楚,邏各斯也存在於文化和宗教的創造與危機之中。由此,宣講肯定性悖論,試圖顯明在文化和宗教的創造與廢墟中上帝的蹤跡,並非錯誤的偶像崇拜。蒂利希認為,這樣的神學進路可被稱為「文化哲學」,因為朝向終極者的指引在此並不局限於《聖經》的詞句與教會的言說。「這樣一來,我們的處境驅使作為神學家的我們不是神學家,而是文化哲學家」(377)。落實到具體的聖靈論理解,蒂利希所理解的普遍的基督之靈不一定局限於《聖經》與教會之中,它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從具體的自然事物、文化作品或宗教活動中,即使相關言語、敍述和圖像可能帶有大法官的印記,更強有力地吹向我們。這樣一來,在他看來,巴特那樣在具體意義上綁定於正典和教會的所謂「聖」靈就迥然有別於真理與愛之靈,而且可能嚴重阻礙通往在基督裏完全直觀悖論的道路。巴特這樣的聖靈論理解,這樣直接地宣講具體的悖論反對文化與宗教的各種形式,正是「我們處境的不忠」(378)。
由此,蒂利希特地向巴特表達了他的兩點具體擔心。首先,巴特等人使用辯證的方式可能會導致「一種極其肯定、極其非辯證的超自然主義」,上帝與世界關係的是與否可能會變成在面對世界時一種簡單的否,並有可能反而成為「一種更為肯定的、非辯證的是」(378)。其次,巴特所援引的改革宗神學嚴格區分世俗與神聖領域,不僅將文化生活世俗化與抽空化,而且面將宗教生活原始化,已完全遠離宗教改革的意圖,並且違背所處處境。與此相反,蒂利希同樣旗幟鮮明地表明,他所處的傳統是德意志-路德宗傳統,這一傳統強調,必須不斷地嘗試,通過由神律而來的自律來克服世俗的自律。在蒂利希看來,巴特所提到的施萊爾馬赫和黑格爾也處於這一傳統之中。
對蒂利希的上述回應,巴特並未做出進一步回應。[51] 據圖爾奈森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七日寫給巴特的信,蒂利希的這些說法實際上最多只能理解為「腳注和起到警戒作用的貢獻」。就實事本身而言,沒有任何東西會得到改變。[52]
五、論戰之餘緒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蒂利希在柏林地方報《福報》(Vossische Zeitung)的「時代思想家」(Denker der Zeit)專欄發表文章,[53]繼續批判巴特。以此篇短文為標誌,巴特和蒂利希這兩位偉大神學家從此徹底分道而行,走上各自的神學發展道路。[54]
如同之前的論戰文章一樣,蒂利希首先讚揚,以巴特為代表的神學運動是當今德國新教神學最為重要的運動,其《〈羅馬書〉注釋》是「新教神學發展的里程碑」。[55] 在關於歷史背景的第一部分,蒂利希認為,除了宗教改革思想外,布魯姆哈特父子也是巴特神學思想的重要來源。[56] 這兩位先知性人物強調上帝自身的作為,認為上帝與世界的關係無需以教會和敬虔為媒介。[57] 受此影響,巴特認為,任何屬人的運動,無論是教會的,還是非教會的,無論是敬虔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基督教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在上帝之前都沒有任何神聖性而言。一切均處於從永恆而來的、臨駕於時間性事物之上的審判中。正如我們在一九二三年的公開文章中所看到的,蒂利希對巴特所開啟的這一批判頗為讚許,認為辯證神學運動「始終都還是當今新教神學最為強大和對最近未來而言最為重要的因素」(188)。
與在一九二三年強調巴特神學的基督論理解略有不同,蒂利希在關於系統思想的第二部分首先着重闡述巴特的上帝觀、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人的自律、文化和宗教的批判性理解,然後闡述巴特的啟示觀、以及由此導致對敬虔與信仰的批判性理解。在蒂利希看來,巴特深受加爾文宗上帝觀的影響,強調上帝完全的力量和超越世界的榮耀,極力反對在自然和歷史中直接直觀上帝的可能性。世界處於罪之中,處於審判和危機之中,接受審判的是一切時間和時間性事物,特別是人的自律、文化和宗教。自律被巴特理解為人的自我榮耀和人的如下努力:在自己的形式中生活,並且試圖在上帝之前成為甚麼。一切文化也都處於危機之中,文化的最高貢獻不過是在確定其自身界限。宗教則只是人的一種可能性,是人試圖走向上帝的一種努力。就其根本而言,宗教屬於人的自律,是人自我榮耀的形式,基督教作為宗教也不例外。與上述上帝觀相應,巴特認為,啟示是既不需要任何護教努力的奠基,也不能被任何爭論所反駁。它是一次性的、偶發性的和特殊的,不能從普遍性出發加以把握。啟示打破自律,以上帝的可能性取代了人的可能性,這對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可能性」(188)。由於這樣的啟示觀,巴特認為,敬虔是信仰,而信仰則是跳躍和冒險,是來自上帝的、而非出於人的不可能的可能性。
在展開具體批判的第三部分,蒂利希首先指出,辯證神學的意義和力量來自於它對新教原則的持守,即「唯獨因信稱義」(Rechtfertigung allein aus dem Glauben)。蒂利希的批判要點與一九二三年的批判類似,即「不可能只宣講和聆聽上帝的否,而不宣講和聆聽上帝的是」(191)。通過對信仰、宗教和啟示這些概念的考察,蒂利希展開了對巴特的批判。其一,由於信仰或不信仰者是具體的個人,信與不信的對立不存在於超越之中,而存在於人的現實之中。其二,不能像巴特那樣片面地只從否定的方面理解人的宗教,宗教不僅是人的可能性,而且能成為對上帝之可能性及其啟示的信仰的回答。其三,不能像巴特那樣斷裂地理解啟示,否則啟示將成為「固定的時間片段,歷史的碎片」(192)。在蒂利希看來,巴特神學的這些缺點或「錯誤發展」(192)可能會被正統派利用,以之來支持他們僵化的教義。
一九三五年,被迫流亡美國的蒂利希造訪美國芝加哥,與當地神學家多次交談,極力表明自己不是巴特派神學家。[58] 為了加以公開說明,蒂利希用英文發表《「辯證」神學有甚麼錯?》(What is Wrong with the “Dialectical” Theology?)一文,在英語世界公開表達他對巴特神學的批判。這篇文章基本觀點是:巴特的辯證神學不是辯證的,而是悖論的和超自然的。[59]
一九四〇年,蒂利希在評價巴特新書的書評[60]中指出,無論巴特本人承認與否,此書呈現出巴特思想的轉折點,即巴特開始把納粹當作政治現實來加以反抗。在蒂利希看來,巴特神學之所以之前不斷受到攻擊,乃是因為其中的「超驗主義」(Transzendentalismus),即徹底區分上帝與世界、宗教與倫理、上帝國與歷史。[61] 但在本書中,特別在第四部分,巴特採取了新立場,由於納粹既是政治實驗,也是宗教性的拯救機構,「教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中立地面對今天的政治問題」(325)。此外,蒂利希還簡要提及這一轉折對巴特神學思想可能具有的深刻影響,即在巴特神學與宗教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區別就不再是神學的,而只是政治的(326)。[62]
六、一些暫時性的分析與總結
在梳理和分析上述一九二二年面談、一九二三年論戰和一九二六年書評等之後,[63]本文試圖在結尾處總結性地闡述巴特與蒂利希對彼此的理解、以及兩者在神學立場與進路上的一些根本差異。
首先,就兩者的相互關係而言,蒂利希與巴特並非朋友,而是相互保持距離、並且彼此尊重的神學對話伙伴。兩人在各自並行的神學發展歷程,對彼此有着一定程度的關注。這一點在巴特那裏體現得更明顯,他直到晚年仍在研讀蒂利希《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第一卷。[64] 而蒂利希對巴特的認識和批評則較片面,他特別強調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對巴特是神學思想(尤其是其上帝論)的影響,特別強調巴特神學是不辯證的、只是偏執於否定的超自然主義或超驗主義。這表明,蒂利希對巴特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於辯證神學和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時期(特別是1919年的《〈羅馬書〉注釋》第二版)。
第二,正如在一九二三年論戰中巴特所明言的、蒂利希所確認的,兩者的神學差異是宗派性的,巴特秉承經由路德和基爾克果改革宗傳統,蒂利希則延續德意志-路德宗傳統,親近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傳統和黑格爾的哲學傳統。[65]
第三,蒂利希對施萊爾馬赫和黑格爾的親近也與其形而上學立場緊密相關,即強調創造(然後才是拯救和完全),強調上帝與人(或者無條件者與有條件者)之間肯定性的源初統一。由此立場出發,蒂利希認為,要辯證地對待否定性的差異,即無條件者與有條件者的分離。[66]
巴特神學也有着自身的形而上學前提,只是與蒂利希神學所具有的迥然不同。總而言之,巴特神學的形而上學立場則是後現代的,即認為,源初統一已徹底喪失。由此立場出發,巴特神學強調上帝與人之間的絕然差異。
第四,落實到具體的對辯證的理解,蒂利希的辯證強調,儘管有否定,但以源初的肯定為先,源初的肯定是否定的前提。而巴特的辯證則是強調,源初的肯定已不再可能回復,面對否定,只有因着上帝自身在拯救中不斷重新建立的肯定,否定才能不斷被克服,而且對否定的克服不是普遍的,而只是偶發的,只能不斷走在從已發生啟示到已應許啟示的狹窄道路上。
與此相關,蒂利希的辯證強調的是普遍的方法與原則,而巴特的辯證則強調的是特殊的、神學實事自身所具有的辯證。[67] 儘管巴特和蒂利希神學採取的都是三一論框架(創造、拯救與完全),但由於對神學實事的理解不同,一個強調普遍的啟示,一個強調特殊的啟示,導致兩者對辯證的理解迥乎不同。
第五,由此,巴特神學與蒂利希神學的差異,不僅僅來自不同的宗派背景,不僅來自哲學背景和形而上學的差異,不僅僅由於具體的方法論和研究進路,而且更是由於對神學實事的不同理解與規定。[68] 基督論正是其中的主戰場。蒂利希強調邏各斯和基督之靈,強調基督的象徵力量,強調啟示在歷史和文化之中的普遍性。巴特則強調耶穌是基督,基督是耶穌,強調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特殊啟示,強調這一啟示在具體歷史和具體文化的特殊性、一次性和偶發性。[69]
第六,與上述基督論差異相應,巴特強調神學的聖經性和教會性,因為上帝在耶穌基督的特殊啟示是《聖經》所見證的和教會所宣講的。而蒂利希則強調神學的文化性和宗教性,因為上帝有可能通過文化和宗教中具有象徵力量的現象進行啟示。與此相應,巴特的教義學與詮釋學採取從特殊到一般的進路。而蒂利希的系統神學或宗教哲學則採取從一般到特殊的進路。
第七,由於巴特與蒂利希在神學立場和進路上的根本差異,兩人在對待宗教社會主義運動上也有着迥乎不同的態度。對蒂利希而言,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是他的原則性決定。而對巴特而言,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歸根到底只是他的「一種實踐上的政治決定」。因為在巴特看來,他對基督教信仰的認信是排他的,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歸屬並不意味着他「對社會主義理念與世界觀的認信」。[70]這再一次表明,蒂利希將宗教社會運動視為巴特神學思想的決定性來源是一種誤解。
第八,正如蒂利希對謝林的誤解性批判一樣,他對巴特的誤解性批判恰恰反應了他自身神學的特色與力量。正是出于這樣的哲學與神學誤讀,蒂利希神學走上了自己獨特與開放的發展道路,逐漸成長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和宗教哲學家之一,在曆史與啓示、宗教與文化之間建立了一條不可忽視的偉大神學思想橋梁。
作者简介
瞿旭彤,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 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eles)、德国古典哲学(Martin Heidegger)。德文专著《巴特与歌德》(Barth und Goethe: Die Goethe Rezeption Karl Barths, Neukirch: Neukircher Verlag, 2014)先后荣获德国福音神学协会Ernst Wolf Preis(2015)、德国海德堡大学国际青年学者Manfred Lautenschläger Award for Theological Promise(2017)。 发表有多篇中德英论文。
往期文章
杨俊杰|蒂利希的“时候”和“时候意识”:论蒂利希的巴特批判的历史神学之维
成静|从罪对人身上“神的形象”的影响看尼布尔和巴特的人学和罪论及其伦理指导
寺园喜基 | 战争中的日本基督教会:关于接受德国神学的第一波、第二波
瞿旭彤: 比自由神学更自由:试从巴特对神学实事性和科学性的探讨看其神学与自由神学的差异
曾劭愷 :巴特與自由神學:回應瞿旭彤教授「比自由神學更自由」一文
郭偉聯:巴特神學中的三一上帝啟示與信仰的類比:雲格爾的詮釋之神學意含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公号邮箱:
编辑:Lea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然而、Vanci、imaginist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