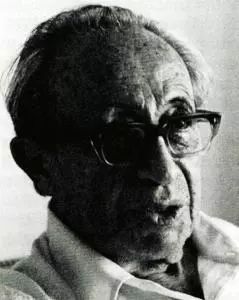编者按
作为一项跨学科、跨文化、跨传统的研究工作,李泉老师此文从现实议题出发,探索巴特与牟宗三分别在基督教和儒家政治伦理传统中的责任观念与主张,从责任的源头与实践两个维度比较二者责任伦理观的异同。巴特认为,责任的源头是上帝的神圣律令,牟宗三则将焦点从超越的上帝转向内嵌于人的良知;巴特坚信,责任的实践就是学习回应耶稣基督,而牟宗三则坚持以自省为中心的道德实践。李泉老师认为,这是极端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与儒家理想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他看來,除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不同思考路径之间的对立,分处欧亚的两位思想家同样坚决捍卫符合人性的体制,提出将行动与责任联系起来的独特责任观。在他们的责任理念和社会关怀之间,还存在着值得挖掘的关联,以期回应当代的思想与政治处境。
原文发表于:《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评论》第49A期,2018年冬特别号,第115-140页,已获作者和发表期刊授权,特此感谢李泉老师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推送时文章已略作修订。

牟宗三

巴特
回應聖者的自由權利:
巴特與牟宗三論責任倫理
李泉
一、導論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處境下的政治倫理學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議題是:誰來為晚近以來的人類悲劇負責?事實上,普通民眾集體責任意識值得嚴肅和深刻的反省。[1] 這個在東方世界中浮現的問題,已經迫使很多西方思想家重新審視現代政治生活的思想和倫理基礎了。對那些追隨以賽亞•伯林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由於人們被某種政治性宗教迷惑造成的。例如,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在《黑彌撒》一書中,將二十世紀某主義的興起和集體責任感的缺失歸咎於那些追求人類完美的烏托邦工程,他們主要是由歐陸啟蒙主義哲學驅動的。[2] 他所擔心的是,現代人很容易迷失在救贖政治的幻想中。因此,為了保全一種健康的政治生活,有必要在公共領域中拒絕任何類型的目的論倫理學。儘管這樣針對倫理價值的工具主義態度會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但我們無法回避自由主義者們提出的挑戰,那就是是否可以找到一種更好的倫理思考的方式,既可以保全政治責任的倫理信念,又可以避免由於盲目追求烏托邦而造成的悲劇?
本文的目的是從比較文化的視角出發探索具備這種潛力的責任倫理觀。具體而言,我們將考察兩位來自不同倫理傳統的思想家,他們分別是基督教神學家卡爾•巴特和現代新儒家思想家牟宗三。我們將系統比較他們將倫理信念和行動聯繫起來的獨特的責任觀念。之所以選擇這兩位思想家進行比較研究,是基於兩個原因。首先,他們分別是現代基督教和儒家倫理傳統的傑出代表。[3] 其次,他們各自在其一生之久的工作中都致力於探索一種特定類型的政治倫理觀念,使其可以與他們所信守的宗教或道德傳統相匹配,即人類的倫理責任應當被理解為是在處境性關係中回應聖者的自由權利。這種意義上的責任觀不僅包括了行善的意願,也是成為善者的呼召。更為重要的,成為善者不是由某種狀態或抽象原則界定的,而是一個通向純粹道德主體的自由過程——對巴特而言,這一過程指向作為上帝律令的耶穌基督;對牟宗三而言,則是儒家傳統中的聖賢。可以說,兩位思想家此處共通的思考徑路使得他們的責任倫理觀對我們的目前探討的議題仍有啟發與借鑒意義。
作為一項跨學科的研究工作,本文旨在比較基督教和儒家的政治倫理傳統中的責任觀念與主張。這就需要考察哲學、倫理學與政治學中相關議題的文獻——尤其是關於責任的性質及其對人們公共生活重要性的研究。下文中我們首先簡要回顧幾位現代責任倫理思想家的學說,以期為隨後的比較分析提供研究背景並說明這項研究的潛在貢獻。
二、現代視野中的責任理念
在一段發人深省的論述中,神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言:“在人們的各種道德資源中,最為重要的是指明他們擁有一種通向善的義務感。這種道德感本身並不包含道德判斷的具體內容。作為一種行為準則,它只訴諸個人根據自身所能形成的善與惡的判斷來行事。”[4]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現代語境中,責任的理念非常明確地指向了人類道德的本質,因而常常成為闡釋道德的形成、抉擇與行動的關鍵詞。
在很多人眼中,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為現代責任理念提供了最重要的表述方式。康德道德哲學的特色在於堅持責任倫理的理性特質。他認為人類作為理性的行動者,不僅僅是由欲望和偏好所驅動的動物,其道德的發展取決於他們敬重(respect)普遍而超越的道德律令並用來引導和糾正欲望的能力。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一書中,康德以善意(good will)即一種僅從義務出發來行動的意志作為道德行動的開端。正如他寫道的,“義務就是出自對法則的敬重的一個行為的必然性。”[5]
在他看來,首要的道德律令便是“在任何時候都要按照你同時能夠意欲其作為法則的普遍性的準則去行動。”[6] 為了將行動準則一般化,我們必須同時對自己和他人承認:人永遠不應該僅是達至某種目的的手段。當每個行動者都如康德所期待的,在他們所有的自我立法行為中遵守上述準則,那麼所有人將成為目的王國的成員。[7] 此處,尊重的情感尤其值得關注。雖然康德承認一個行動者在實踐中敬重道德準則是重要的,但是作為一個理性主義的道德哲學家,他卻選擇將其視為一個理性的概念並堅稱:“意志直接為法則所規定以及對此的意識就叫作敬重,以至於敬重被視為法則對主體的結果,而不被視為法則的原因。…敬重的對象僅僅是法則,而且是我們加諸我們本身、就自身而言必然的法則。”[8]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會產生質疑,如果從有意義的公共生活和倫理傳統中分離,單純的理性主張能否足以支撐起對普遍原則和對他人的尊重並激發我們的道德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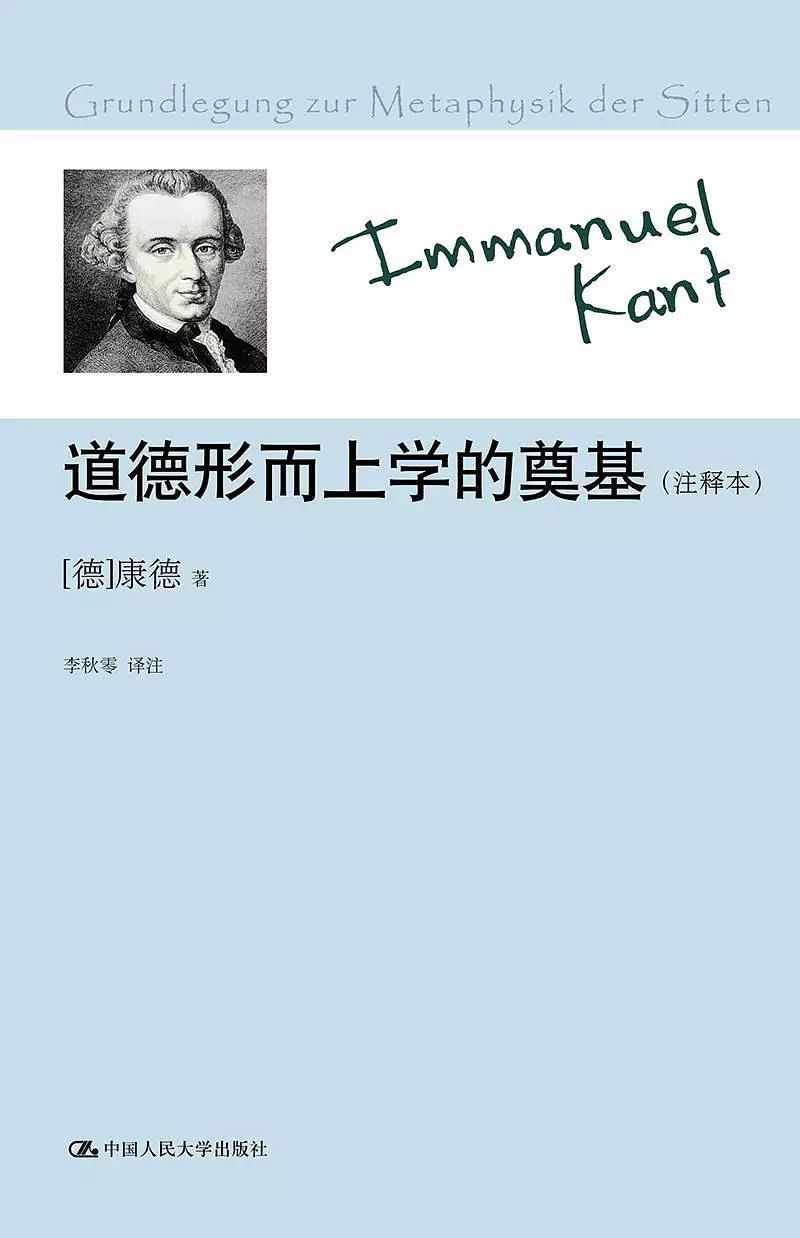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作者: [德] 伊曼努尔·康德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注释本
原作名: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译者: 李秋零
出版年: 2013
因此,其他現代思想家儘管堅持康德式的責任準則,但會更加強調其社會屬性。 例如,迪特裡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將責任解釋為代表性行動。[9] 他寫到,“責任作為一種代理問題(deputyship)根本上最清楚地反映在一個人代替他人的直接義務性行動中,比如作為一名父親、政治家或是教師。”[10] 在他的基督教倫理學中,責任的觀念必須以已經代替我們行動的基督的行動為中心。因此,基督徒也必須如此行動,同樣教會也需要對社會承擔責任。有趣的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儘管採用了更具世俗色彩的術語,卻也有著類似的洞察。在論及政治生活中的責任意識時,韋伯認為政治家基於其職業的特殊性質,必須不僅要根據絕對的道德準則,而且也要依據當前行動的未來影響來進行決策。[11] 不同於康德,上述兩位思想家皆賦予了社會角色之於責任分配的重要意義,以此表明我們可以為他人承擔責任,即代表他人並為著他人行動。[12]
對這種意義上的責任主張而言,或許最重要的闡述來自神學家理查德·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他為此提供了一種本體論的解釋,即人類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對話性存在的生物(homo dialogicus):
我們試圖通過我們部分的活動來理解自身的完整性;當下我們將自己所有的行動看作是回應(respond)他者的方式。為了投入對話,為了回答面對的問題,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攻擊,為了回應指令,為了迎接挑戰——這些都是我們人類共同的經驗。[13]
尼布爾洞察到,自我存在於回答和回應他者之中,因此他者是自我形成的必要條件。正是由於自我存在的這一特點,責任理念才有助於呈現出我們整個生命活動的本質。此外尼布爾更指出,在與他者的回應性關係中,自我既不是與規則打交道,也不與原子式的個體打交道,而是與一個互動系統中的成員進行溝通和交往。尼布爾的這些洞見使他超越了康德的視野,將倫理學定位在個人對上帝屬性和行動的回應性反思上,進而成為基督教社群道德生活的關鍵。正如他精闢地寫道:“責任表明——上帝作用於你的所有行動。因此對你的所有行為的回應也就是對上帝作為的回應。”[14] 儘管尼布爾處理基督教信仰的人類學方法常常受到挑戰,但他此處所提出的關於責任的對話性結構卻影響深遠。作為一種倫理思維模式,它提供了一種處理個人終極關懷與其對共同體責任間關係的重要方式,並使其成為了塑造責任性自我(the responsible self)的核心議題。
當代關於的責任理論整合的工作是由一種深刻的危機意識引發的。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發現,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科技進步極大地拓展了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支配力量,同時也暴露出此前道德生活的基礎和來源並不充分的缺陷;因此過去的倫理學說已不足以解決我們這個世代所面臨的道德問題。[15] 他認為,為了填補傳統道德或宗教信念衰退後留下的空白,倫理學需要搭建起新的原則,即認識到區分善惡的絕對標準是對存在而非虛無的肯定。通過這種方式,約納斯試圖將倫理價值的正當性論證從上帝轉向根植於目的性和自由訴求的人類有限的存在本身。[16]
Hans Jonas
(German,10 May 1903 – 5 February 1993)
不同于約納斯通過關聯於人類力量的責任準則來建構規範倫理學的方案,基督教倫理學家威廉·史維克(William Schweiker)傾向於將責任與在上帝面前保持道德整全的律令聯繫起來。利用古典和現代的思想資源,史維克論證說責任關聯於一種我們通過批判地反省自身所關心的事物而改變自身生活樣式的特殊能力。他據此構建起責任的準則來指引我們在價值領域選擇回應方式時的決定,那就是,我們的所有行動和關係都是為了尊重和增進在上帝面前生命的整全(the integrity of life before God)。[17] 按照史威克的理解,現代術語中的整全一詞忠實地傳遞了公義(righteousness)作為善的總和的聖經理念。一方面,個體生活在道德意義上是正確和善的,是因為在對公義上帝的信仰中得到了重整,並且這一個體在尊重和改善生活方面積極行動。另一方面,社群只有在尊重和改善人們生活的整全和公共利益時才是正義的。總之,在上帝面前尊重和增進生命的整全是衡量責任生活的絕對標準。[18]

追寻生命的整全
作者: William Schweiker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Theological Ethics and Global Dynamics : In the Time of Many Worlds
译者: 孙尚扬
出版年: 2011
這些整合責任倫理的理論性工作從比較研究的功能和對象兩個方面啟發和支持了我們現有的研究。首先,責任不能僅僅理解為描述某種知覺或思辨活動的個體性術語。它需要同時包括對個人和道德群體的認識和批判性反思。然而,自康德以降闡明這種活動普遍屬性的道德哲學主張的代價也是明顯的,即訴諸人類普遍道德經驗的解釋時常常會稀釋掉特定傳統中關於智識與道德的深厚智慧。為此,我們這裡選擇的是對道德共同體在其邊界內所持洞見的深度解讀。我們相信,這種針對不同傳統的仔細比較不僅是一種全面理解責任問題的可取方式,而且能夠觸及不同的道德傳統是如何理解責任的來源與行動這兩個關鍵問題的;相比之下,這些議題在那些關於責任的普遍性主張中經常被忽視。
其次,上述倫理學家探討責任問題時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徑路:以人為中心或以上帝為中心。這種不同的終極關懷取向為理解當下比較研究對的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事實上,兩位思想家——巴特和牟宗三——根據他們各自的傳統分別持有上述兩種極為不同的立場。例如,巴特的倫理學堅決捍衛耶穌基督作為上帝律令這一立場。他認為,基督教責任理念的獨特之處在於這個術語真正揭示了自我回應他人的方式是以三位一體的上帝與人類之間的聖約關係為原型的。據此我們便可期待,比較視野中的兩位思想家能夠從基督教和儒家兩種立場來拓展我們的道德視野。
三、責任的源頭
責任的源頭指的是在人性中或超越人性的能夠塑造責任意識與行動的根本性力量。對巴特而言,我們責任的源頭是上帝的神聖律令(divine command)。前文中康德依靠普遍性道德律令建立的責任倫理學為此提供了思想背景。在倫理學中,康德代表的是一種基於規則的義務論(rule-deontology),強調相比於行動結果而言順服道德準則本身的重要性。巴特一方面讚賞康德對順服的強調,[19] 另一方面則拒絕順服的對象是普遍準則。他警告康德式的準則概念根本無法描繪上帝審判與救贖行動的鮮活內容。為此,他轉而強調上帝律令相對於每一個人類具體處境的獨特性;相應的倫理義務只能以一種在特定處境下採取特定行動要求的方式,而無法通過一般性的規則得到認識和遵行。因此可以說,巴特提出的倫理學類型事實上是一種基於行動的義務論(act-deontology)。[20] 正如羅賓·洛文(Robin Lovin)發現的,他在其責任倫理學中拒絕康德的主要原因,是試圖推翻所在時代建基於康德,隨後由自由主義神學家們繼承的主流神學體系,並試圖重新發現與上帝相遇的純正含義。[21]
不僅如此,我們認為巴特之所以會採取一種基於行動的倫理路徑來理解責任問題,更重要的原因來自其神學倫理學體系的論述架構本身。作為基督教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的宣導者,巴特堅信對人類處境的任何真切理解都必須源於有關上帝自身的現實,而不是相反。沿此思路,為了描述神聖律令的具體內容,他建議把律令作為上帝宣稱(claim),決定(decision)和審判(judgment)的類比分別加以理解。[22] 首先,作為上帝的宣稱,神聖律令見證了上帝的旨意,並要求我們透過自己的意志和行動來順服。但是,上帝這項權力的來源是什麼?我們又為何要服從他?巴特回答說,上帝宣稱的有效性源於他恩慈的意志。憑藉這樣的意志,上帝會永遠採取主動,為我們與他的關係負責。換言之,上帝要求我們順服,不是由於具有壓倒性的權勢或者具有本質上的善,他甚至不僅是我們完全的滿足。現實是他已經把自己交給了我們。他這樣做,取代了我們的位置,並接納了我們的所有。這是上帝宣稱的基礎和權威所在。[23] 因此,上帝的宣稱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宣稱都擁有更大的權力,要求我們真誠地承認他公義和憐憫的作為,並呼召我們自由地順服。不同于康德,巴特在這裡提醒說上帝的恩典不是抽象地轉向我們,而是決定性地通過耶穌基督即道成肉身在我們中間的上帝自己來實現的。
言說上帝的宣稱,耶穌基督是其中的關鍵。巴特強調說,作為神聖宣稱的內容,耶穌基督自己就是福音,他自己便是“上帝要把自己獻給我們的意志的抉擇與行動”,是上帝向我們彰顯恩典的唯一途徑。[24] 換言之,作為要求我們順服的律令本身的上帝意志完整地體現在耶穌基督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他裡面神聖的道成了肉身。這意味著他已經承擔起與我們聯合的責任。當上帝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時,他已經把我們有罪的人性帶入到他的神性中。由此我們才能意識到:自身的存在雖然被本能的罪惡遮蔽並處在死亡的審判之下,卻意外地向天開放,得到從上而來的光照和釋放;我們不是被上帝拒絕,而是在滲透萬有的愛而特別是耶穌基督對我們的犧牲中得到了與他的合一。在在巴特看來,這些陳述不是純粹的道德願景或理想,而是我們人類存在的無條件和普遍的真相。無論我們積極還是消極地回應,上帝宣稱的仁慈現實都已經在耶穌基督的行動中實現了。
上帝的律令不僅意味著神聖的宣稱,也是他在耶穌基督裡所做的神聖決定。巴特認為,上帝律令的第二個維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自身存在以及與他關係方面一個更為宏大的事實。他指出,人類存在的一個基本現實是,我們的生活是由自己意志和行動中一系列連續的決定構成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整個人生和其中每一階段的方向。因此可以說,我們作為上帝的被造物是通過這些決定而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在這些決定中,我們才能見證上帝神聖的行動。[25] 因此,上帝的主權必須回應這更具體的現實。上帝的宣稱必須通過擴大其範圍來解決這個事實,即它能夠並且必須衡量我們整個生活以及每個時刻所做的決定。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上帝神聖的宣稱可以同時被理解為他神聖的決定。
巴特據此認為,正是上帝在他的律令中所表明的這種事先的決定,確立了分辨我們行為善惡本質的標準。[26] 我們自己的選擇,無論是善的還是惡的,是順服的還是悖逆的,本質上都受到由神聖決定這一概念所表明的關係性事實的支配。他進一步解釋說,當這種透徹的現實得到承認時,我們可以立即做出兩個推論。一方面它意味著上帝在永恆中已經通過耶穌基督為我們建立了分辨善惡的標準。除他以外,我們找不到任何可以負責的對象。另一方面,不論我們在他眼中是否正義,都不是我們自己所做的結論,而是他根據在永恆之中的旨意和在我們生命中每一刻的行動所表現出來的神聖決定所做出的。[27]
最後,耶穌基督是神聖審判的基礎,因为他憑藉自己死亡和復活的行動清晰地界定了上帝審判的目的:上帝審判我們,以便使我們在他的主權下得到永生。[28] 巴特通過區分咒詛和寬恕勾勒出這個悖論性的事實:
當我們進入他的審判時,我們是完全邪惡的;當我們離開時,我們完全潔淨了。在上帝的同一個審判中,我們既是完全罪惡的(semper peccatores)也是完全公義的(semper iusti)。罪得赦免的事實是,這兩個預設不彼此排斥,他們相對而立,但不是辯證的平衡,而是以第二個為優先;另一個事實是他們的順序是不可逆轉的,上帝從不從善中創造惡,而是從惡中創造出善;再一個事實是,完全的公義是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被我們聽到和認識的判詞。這便是上帝在審判中的恩典。[29]
於是神聖的審判本身就成為了信心的呼召,而我們的信心也成為了對神聖呼召的回應。因為信心是我們事實上承認,上帝已將公義替我們成就了。這是我們接受上帝公義的權利。[30] 因此,作為上帝審判的結果,信心引導我們獲得了重生,使我們能夠遵循上帝的律令,做他看為好的事。通過信心,真正的責任感最終成為了我們自身的現實。通過信心,我們被賦予了負責任的態度,並且能夠樂意地為上帝審判所預定和應許的永生做好準備。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確信不是出於自身道德本性而負責,而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裡恩典的審判所帶來轉變的結果。自此,我們作為道德主體的身份得到了確立。正如巴特總結說:
我們負起責任是因為聽到了復活的主的聲音,我們有責任繼續聆聽這個聲音。作為聽到這個聲音的人,我們在上帝的審判中被認真對待,為此我們必須認真對待自己。正如沒有其他真正的責任,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真正的嚴肅性。[31]
簡言之,一旦責任的源頭明確了,責任性自我的地位便得到了捍衛,道德成長之路才會真正呈現出來。這裡責任的概念敏銳地捕捉到了我們人類狀況的根本性現實。我們生活在與上帝的對話性關係之中,我們被他預定並呼召成為他的盟約夥伴。無論我們是誰,我們做什麼,這是我們存在本身的普遍、客觀和具體的現實。作為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神聖宣稱、決定和審判的對象,我們毫無例外地生活在他對我們道德存在的超越意志之下,確立我們道德生活的善惡標準,並從根本上轉化我們的生命本質。因此,當被視為是與上帝立約關係中的回應性時,責任理念便展現出其終極的源泉是耶穌基督。
牟宗三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闡釋了儒家的責任倫理,同樣與康德形成了鮮明對照。對康德倫理學而言,道德的最高原則針對的是道德主體根據他的個人意志自由運用實踐理性的行為。正是這種自我立法的能力指明了人類作為道德存在的特質。由於倫理學需要說明個體能夠為其自身行為進行立法,它因此必須將自由意志設定為道德行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自由意志是用來說明我們具備實踐理性的道德主體之所以可能的一項純粹假定(postulate)。牟宗三儘管欣賞康德對道德選擇中主體責任的重視,但同時堅持認為作為必要條件的自由意志絕不是一項假定,它其實是我們深層道德意識的呈現。為此,他專門發展出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這一概念,作為探究儒家實踐理性的門徑。作為一種直覺,智的直覺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具體化原則(principle of cognitive presentation),其作用是被動地接受和呈現道德律令。另一方面,智的直覺也可以視為存在論意義上的實現原則(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actualization)。此時,智的直覺是積極的和創造的。[32]儒家倫理學的關鍵任務就是運用智的直覺來考察作為道德本體的良知(innate knowledge of good)的獨特性質及其在指導道德實踐方面的深刻意義。
對牟宗三而言,存在論意義上的良知就是處於實現過程中的創造性原則。因為一項道德律令如果是普遍的和超越的,它的存在論基礎良知就必須作為創造的源泉而存在。在他看來,這是儒家思想與西方的哲學傳統的明顯區別:
道德即依無條件的定然命令而行之謂。發此無條件的定然命令者,康德名曰自由意志,即自發自律的意志,而在中國的儒者則名曰本心,仁體或良知,如此說性,是康德乃至整個西方哲學中所沒有的。”[33]
為此牟宗三借用“性體”這一儒家傳統概念來表達良知的客觀維度。他解釋說,性體作為絕對和普遍的存在,並非由於它是柏拉圖式的範疇概念,而是因為它就是實體本身或終極存在。它雖然實現在人的道德實踐中,卻不受其限制。可以肯定的是,它本身創造和維繫著整個宇宙,從而成為眾生的源泉。不僅人類及其道德生活,而且一草一木乃至一切生物都受到它的潤澤。牟宗三用“涵蓋乾坤”來指稱這一宇宙的創造原則。借助作為實現原則的智的直覺,明智的個體便可認識到其宏偉工作的範圍和影響,進而決定跟隨和效法它。這就涉及到“心體”的工作,即我們良知的主觀維度。[34] 綜上所述,良知不僅在道德實踐中呈現自身並得到理解,也在同一過程中培育著我們的人性使其成為道德的存在。正是這項洞見使得一代代儒家深信,為了從良知的創造性工作中受益,我們必須努力尋求性體與心體的合一。正如牟宗三洞察到的,當遠古的詩人在《詩經》中驚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時,他恰恰表達了這種令人嚮往的深刻體驗。[35]
儘管如此重要,性體和心體尚不能涵蓋良知的所有活動。對良知的全面理解還需要包括對“悅”的認識。悅作為一種心智活動,意味著對某種東西有興趣,同時接受和擁抱它。比如,當我們的良知進行立法時,它便隨即和自發地悅納自己的成果。牟宗三強調說,悅可被視為人類良知的一個特定功能,它在我們的生存境況中扮演了趨善避惡的動力角色。[36] 缺少它關鍵性的工作,人性就會被困在物質享樂的無盡欲望之中,既不能提升到道德的層面,也無法用理想和價值來表達自己。這就是人性的困境,也是對我們人類存在而言惡的確切含義。[37] 與此相對,善則是我們擺脫這種困境的努力,將意志引向其完全和最終的源頭良知上。這便是悅的功能。[38] 可以說,悅的概念被牟宗三特別地指定為一種與康德敬重概念相平行的儒家理念。二者的區別在於,悅的活動本質上是清晰、可觸及和活躍有力的,而敬重則缺乏這些特點。牟宗三把康德這種概念上的弱點歸咎於他把我們的善意誤解為一個抽象主體,從而扭曲了其存在屬性。[39]
鑒於我們良知的本體論特徵,牟宗三進一步解釋說,我們從智的直覺中獲得的知識既不是概念性的知識,也不是透過康德意義上的認知類別獲得的知識。智的直覺並不是一種道德狀態的呈現,而是去實現這種狀態的努力。受到王陽明的啟發,他運用“覺”這一概念來說明上述反思性活動的性質。他認為,儘管人類無法完全掌握良知的真諦,我們卻可以通過在具體處境下踐行善行的方式不斷追求。而在這項操練道德的工夫過程中,無論是一般性的規則還是律令都無法確保我們可以獲得道德進步。牟宗三為此引用古代聖人舜的例證來概括這一反思性活動處境化的實踐特徵:“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同樣,在孔子的生活實踐中也存在著一條類似的成聖之路。孔子盡其一生來追求仁。但他沒有以分析和抽象的方式,而是在“具體清澈精誠惻怛”的生活方式中去踐行仁的精神。[40]
在這些典範性的個案中,牟宗三確信良知常常以看似矛盾的方式呈現並發揮作用:它既是具體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內在的又是超越的。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轉化我們的人性,將其提升至聖人境界。由此可見,他在根本上與巴特共用了一種處理倫理問題的基於行動的義務論路徑。但與巴特不同的是,在牟宗三的體系中,道德完善的動力源頭從超越的上帝轉移到了內嵌于人性中的良知。用他自創的哲學術語來說,這便是道德理想主義(moral idealism)的要旨。
四、自由的回應
本文比較的第二個維度是責任的實踐,即富有責任感的倫理行動議程。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指出,巴特將上帝的神聖律令作為人類責任意識的源頭。因此,責任概念有助於揭示我們道德存在的兩重相互聯繫的現實。首先,它指明了人類境況的一個基本現實,即我們總是在面對上帝,對上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出於自身的意志和行動在不斷地回應著上帝。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上帝的意志,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要受到上帝的質詢。無論我們選擇是否遵守上帝的命令,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要向上帝交代。[41] 可以說,這是對人類作為上帝所預定的盟約夥伴身份的客觀描述。不僅基督徒,而且在其他宗教和世界觀下生活的人也毫無例外地被納入其中。對巴特來說,人類這種責任狀態的普遍特徵恰恰是由耶穌基督的超驗來源所保證的。
巴特堅信成為一個富有責任意識的自我的過程,就是學習回應作為神聖宣稱、決定和審判行動者的耶穌基督的過程。因為他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野,使我們的自由回應成為可能。在他看來,這正是我們在上帝的恩典中發現的關於自由意志的驚人現實:
由上帝所成就,人類得以從罪中解脫出來,從而免于作為罪的後果的死。在不朽中,他們發現了自由的生活目的;在自由的目的中,他們發現了自由的意志。對於那些發現了這種自由的人來說,不管他們是否成功地踐行出來,所有的腐敗都化成了不朽的類比。在自由意志中,人發現了自己。他有著君尊的身份。他的尊貴不可估量,他的價值沒有窮盡;因為他擁有永恆而真實的生命。[42]
除此之外,當我們試圖審視自身的意志和行為時,責任概念也可以指涉我們道德反思的實踐。根據巴特的解釋,這構成了我們道德存在的第二重現實:
責任概念向我們展示了道德反思的意義,即省察我們的存在、意志和行動,以及上帝的命令與我們的存在之間的相互關係。這涉及我們對回應上帝的事實以及客觀上負有責任的事實的態度。這也預示著我們知道這一點,因而已經被告知我們的真實境況。但是,只有當我們在信心中聽到和理解了恩典聖約的資訊時,這一點才能真正被揭示出來。[43]
任何一種道德反思,如果能夠顯示我們的真實境況並引導我們承擔責任,就必須在信心裡透過聆聽和理解滿有恩典的上帝律令來進行。在此引導之下,巴特主張最重要的倫理行動應是在崇拜和禱告中回應上帝,其次是回應我們的鄰舍和社群,而崇拜和禱告作為首要的倫理行動為其他的行動提供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在這裡既不訴諸基督徒智識的優越性,也不主張基督教道德模式的排他性。對他來說,這樣的洞識並不專屬於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可能成為最先承認人類的責任是一個普遍現實的那個群體,那僅僅是因為他們真正認識到責任的源頭即在耶穌基督裡恩慈的上帝,以及相應的,他們當下的不負責任的實際狀態。[44] 基督徒的善意和善行都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轉向盟約中負責任的另一方耶穌基督。因為正是基督自己承擔了人類的罪惡,滿足了人類的需要,在他恩典的行動中成為各種權勢之下人們的最終解放者。
可以說,巴特終其一生都在尋求一種闡釋恩典與自由的神學。[45] 正如他曾在晚年坦言,“我試圖從聖經發展出來的神學從來都不只關心個人事務,與世界和全人類脫節。它的目標是:上帝是為了世界,上帝是為了人類,天國是為了今生。隨之而來的是我的整個神學總是包含或明確或隱晦但始終濃厚的政治成分…這種對政治的興趣一直伴隨著我到現在。”[46] 對他而言,基督教社群政治見證的基石就在其與在耶穌基督裡的上帝的盟約關係中。基於這些信念,巴特不僅積極參與符合正統基督教教義的進步政治的實踐方案,還為基督徒參與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實踐意義提供了豐富的神學闡釋。正是他這種對政治解放的信仰見證使神學家提摩太·戈林斯(Timothy Gorringe)確信,在任何情況下,真正的自由和恩典的神學同時也必然是反對上帝之外一切權勢的神學。[47]
對牟宗三來說,實現儒家道德真諦的唯一方式是進行以自省為中心的道德實踐。這涉及到反躬自省和修正偏差的勤勉努力。不同于康德關於自由意志的抽象思考,牟宗三強調儒家傳統的重點在於踐行。[48]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道德意識與行動只有在恰當回應我們在具體生活境遇中良知的呼召時才是有價值的。為此,我們有責任追求王陽明說言的“知行合一”,即道德行動與道德知識的統一。在牟宗三眼中,一代又一代的儒者求知的目的不僅僅是追求所謂的理論真理,更重要的是追求實踐中的道德智慧。據此他建議,我們作為道德的存在不僅能以思辨的方式運用理性,而且需要以實踐的方式運用理性。相應地,道德真理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客觀的論證和說明,還需要我們主觀的接納和實現。
這便是智的直覺中所謂“健”的活動。效法孔子的教導,牟宗三認為這項回應性的實踐是持續一生之久的在各種社會關係和處境下的操練。既然我們在善惡之間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選擇,因此道德的發展便意味著堅持不懈地通過對良知的肯定性回應來堅決拒絕後者。唯有如此,我們才可期待在批判和反省的過程中逐漸成長,直到能夠制定出實際而有效的道德律令來回應具體的生活境況。牟宗三將這一進程形象地稱為“隨波逐浪”。[49]
由此可見,真正的通向聖賢之路便是從我們人性的實際狀態提升至應然狀態的發展過程。相應地,責任的道德涵義也就不僅僅包括行善的意願,而是成為善者。在牟宗三的理解中,後者既不是由某種事態也不是由某個抽象的價值界定的;恰恰相反,它必須被理解為一個通向純粹的道德主體或聖賢的過程。如他所示,這其中包括了兩個關鍵方面:
“實踐主體”的呈露﹐則是以“繼天立極”的形態來撐開我們的生命﹐以德性的函量﹐智慧的圓融﹐來潤澤我們的生命。依是﹐根據實踐主體而來的﹐首先是個人的道德實踐﹐表現而為道德實踐﹐表現而為道德宗教的聖賢人格。其在文化文制上的意義﹐是樹立人間的教化﹐護持人性人道人倫於不墜。此為一本源形態﹐亦為一籠罩系統。此是“道”之統緒﹐簡名曰“道統”。其次﹐是集團的政治實踐﹐在現實歷史中﹐去表現道德宗教的聖賢人格所證實的“道”。它表現的方式﹐可以從其在現實歷史的演進中所發展至的“政治形態”來指明。[50]
簡言之,從個體方面來看,儒者的責任性實踐是對良知呼召的積極回應。在同一過程中,人性通過轉化和超拔自身得以發展成為真正自由的道德主體。[51] 在牟宗三的理解中,孟子關於修養工夫的教導反映出這一方面責任實踐的深度。從群體方面來看,儒者在操練責任意識時必須認真對待社會參與,後者將負責任的自我與生活世界中的其他人聯繫起來,從而界定了責任實踐的廣度。根據牟宗三的考察,這種堅持可以追溯到荀子的社會與政治主張中。他相信唯有在深度和廣度上同時踐行責任倫理,我們才能實現自身道德品格的成熟並真正選擇通向聖賢的自由生活方式。[52]
五、結論
本文中我們仔細比較了巴特和牟宗三的責任倫理觀在其源頭與行動方面的異同,指出他們分別代表著兩種基於行動的義務論的獨特形式:超越型和內嵌型。這是極端的基督教現實主義與儒家理想主義之間的差別,其中責任觀念分別是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得到闡述的。[53] 然而,除卻他們思考路徑之間的對立,巴特和牟宗三各自發展出的責任觀念又都呈現出一種鮮明的動態與對話特徵。對巴特而言,人類的責任意識得自於啟示。責任意識是動態的,這是因為啟示本身是上帝在耶穌基督中的行動。為此我們得到和解和救贖的良知才能透過上帝在歷史中的工作來瞭解他,回應他對我們在具體的處境中要立刻順服的呼召。對牟宗三而言,人類在肉體或心理層面的各種欲望是其道德完善的主要障礙。由於每種欲望都源於具體的環境中,因此克服我們自身邪惡的相應任務就必須保持活躍和勤奮。道德主體的責任意味著對良知的積極肯定和回應,而在與聖賢在歷史中的相遇則是啟發良知並踐行之的關鍵。
除了動態特徵,關於對話特徵的強調也顯示出兩種倫理系統的相似性。具體而言,真正意義上的道德責任需要被理解成是在一種與聖者的回應關係中培養出的自由權利。它是趨向一個純粹道德主體的過程。對巴特來說,耶穌基督即是上帝的神聖律令,對牟宗三來說,聖賢們的言行典範彰顯著這種純粹的人格。與巴特所建立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倫理學不同,牟宗三認為對仁的追求恰恰是在歷史中與儒家聖人神交的過程。這也解釋了他自己在知性和存在維度不斷與從孔子到王陽明的儒家聖賢們進行對話的努力。但不論是一個還是多個,由於所有這些道德主體都是歷史人物,他們便在一個活的道德傳統中真實地確立了人們富有責任感的生活樣式的潛力和限制。因此,與依靠那些模糊、抽象或普遍性的烏托邦目標來追求人性完善的做法不同,這裡自我責任意識的目標是在某種關係中得到清晰界定的。在巴特眼中,這種關係是縱向的。在牟宗三看來,這種關係更多是橫向的。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兩位思想家分別發展出了兩種關於政治責任的辯證形式,以便一方面保持道德願景的動力,另一方面克服烏托邦傾向。在巴特看來,這項工作對於對抗流行於德國自由主義神學和宗教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樂觀主義傾向尤為必要,因為二者錯誤地將上帝國混同於人類的內在靈性或政治解放。在牟宗三看來,這種努力對於避免以傳統中國聖王統治或現代中國專政形式的道德陷阱極為重要。因此,他們都堅信唯有在真誠回應責任源頭的呼召時,我們才能達至自由的境界,而這是任何形式的權勢都無法剝奪的神聖權利。
可以說,兩位思想家關於責任源頭的共通信念恰恰解釋了他們相似的責任實踐。那就是,闡述責任倫理的事業不僅僅是在學術象牙塔中進行的,而是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不斷整合理論和實踐的努力中成就的。我們不難發現,巴特和牟宗三各自在二十世紀的危機時代都付上了極高的代價,扮演了維護純正信仰傳統的關鍵角色。更加重要的是,儘管分處歐洲和亞洲,他們卻堅決捍衛著符合人性的政治體制,並借由闡述一套完整的責任倫理發展出在道德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之間的倫理性聯繫。我們認為,在他們的責任理念和社會關懷之間存在著值得進一步發掘的關聯,以便有效回應當代的思想與政治處境。兩位思想家的典範不僅令我們肅然起敬,更在提醒我們,什麼才是那些希望擺脫霸權、追求自由的人們的所應當珍視的,以及什麼才是在當代中國語境下進行責任倫理反思的目標與方向。
参考书目
注释
作者简介

李泉,香港城市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政治理论、知识社会学与廉政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作为:《治理思想的中国表达:政策、结构与话语演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往期相关阅读
寺园喜基 | 战争中的日本基督教会:关于接受德国神学的第一波、第二波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公号邮箱:
编辑:Lea
校订:巴特研究、Imaginist、语石、Vanci、Kimekei、伶利、Iris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