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论及巴特与自然神学,似乎只需想想巴特那篇回应文章的标题——“Nein!”(不!),就足以了解巴特对自然神学的批判是何等立场鲜明,掷地有声。作者关启文老师熟悉英美分析哲学和神学传统,又深受苏格兰巴特神学解释进路影响,故对巴特多有同情的了解和理解。他在文章中试图表明,巴特所坚持的启示路径与自然神学并无必然矛盾。围绕“理性与启示”、“自然与恩典”这一经典议题,关老师文章前半部分着力于巴特的洞见,肯定了巴特对于启示的强调,并逐一反驳了哲学上对于巴特的几种批评;后半部分则从自己的分析进路出发,着重阐发巴特强调启示对知识的“审判”这一模式的限制之处,从而提出虽然模糊却更有必要的“辩证”模式,即启示既审判知识也成全知识,从而寻求达成启示与理性的之间的微妙平衡。为一种“修正了的”自然神学留出空间,关老师认为这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
不过,巴特神学是否真如关文所言侧重强调启示对知识的审判模式、而非辩证模式,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原文载于鄧紹光、赖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7,頁139-176。推送时已获出版单位授权,特此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团队恭祝各位读者新春快乐,牛年吉祥!
巴特論自然神學:洞見與限制
文 / 关启文
導論
神學方法論是很重要但亦是很富爭議性的課題,它揭示我們最深層的假設和影響我們神學的內容。一個神學方法論的試金石是自然神學的地位,它是否必需?抑或它是可有可無,甚或有害無益?它與啟示的首要性能並存嗎?有普遍啟示(General Revelation)嗎?我們對這串問題的答案,直接影響我們對救贖論、宗教多元論、本土神學和自然法(Natural Law)的看法。當代神學大師巴特(1886-1968)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是眾所周知的,這篇文章會評論他的觀點,及探討一些引伸的問題。

傳統的自然神學
很多著名的西方哲學家都是自然神學家,他們都提出一些證明上帝存在的論證——內容雖不盡相同,但目標卻相當一致:
-
自然神學應以一些全然確定的語句作起點——它們起碼是所有合理性的人都接受的。
-
接着從這些起點以演繹法推演出「上帝的存在」為結論。
多馬斯主義不單相信理性可證明上帝,也相信理性可證明倫理的基本真理(自然法),當然像三位一體等神學真理是理性不能證明的,我們要倚賴上帝的啟示才可得知,然而啟示的可信性也是有理性根據的——如訴諸神蹟或預言的應驗作印證。1 多馬斯主義的精神在以下格言可見一斑:「恩典只是成全自然,不是摧毀自然。」(“Grace can only perfect, and not destroy nature.”)有人將多馬斯主義比喻為雙層建築,上層是啟示,作為基礎的底層卻是理性。
不是所有傳統自然神學的論證都宣稱是百分百確定的,如設計論證,但這論證的支持亦常宣告它實際上差不多是肯定的。在新教的自由神學中,則有一種以經驗出發的自然神學,如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不認為可用形而上的論證證明有上帝,但他相信人的心靈普遍存在一種宗教感,這常以一種「絕對倚賴感」的形式出現,他的神學起點就是這種人類的宗教意識。士來馬赫由於深受康德的不可知論影響,並不以為形而上的自然神學有可取之處,單從狹義的自然神學來說,他不是自然神學家。那為何將自由神學歸類為自然神學呢?一、他為宗教辯護的方式雖與前人不同(即不是訴諸外在世界的存在和秩序),但策略仍是「將啟示或神學建基於人的自然能力」,巴特將所有用這等策略的神學稱為自然神學,要注意這定義是相當廣泛的。二、士來馬赫的神學明顯有護教的目的,他早年的On Religion便是為了那些「有文化但鄙視宗教的人」寫的,為了建立與他們的接觸點(Point of Contact; Anknüpfungspunkt),他大量採納了當時知識界流行的哲學——富泛神論色彩的浪漫主義,這與亞奎拿接受亞裏士多德哲學的旨趣是一樣的。後期的自由神學不從人的宗教意識出發,而從人的道德意識出發(如Ritschl),這亦是為了與當時流行的哲學——新康德主義——建立接觸點。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November 21, 1768 – February 12, 1834)
自然神學的崩潰?
很多人都相信自然神學是再沒希望成功的了,原因有多方面。第一,很多以前廣泛被接受的信念(如道德的客觀性)也受到質疑,那以它們為起點的論證(如道德論證)也很自然受質疑。第二,現代世界觀對事實的詮釋與中古的大相逕庭,如亞奎那的第一路論證以自然界的運動做起點,再追尋運動的終極因,最後推論出不動的移動者(Unmoved Mover)。但牛頓第一定律(慣性定律)根本就認為運動是不需要解釋的。2 第三,近代哲學(特別是經驗主義)動搖了不少以前視為金科玉律的理性法則(如因果律、充足理由原則),但不少論證都依賴這些法則!第四,很多人認為縱然可成功論證到第一因、宇宙設計師等存在,這仍只是哲學家的上帝,而不是基督徒崇敬的上主。所以亞奎拿式的自然神學已普遍被摒棄了。
至於以內在心靈的體驗為起點的自然神學也是困難重重,士來馬赫無疑深受當時的浪漫主義影響,他強調心靈的自由與超越,及對文化與藝術的追尋,這些主題在當時或許引起不少共鳴。但在現代科技掛帥的社會,關於心靈與精神的長篇大論,最可能換來的是平常人的呵欠!在科學世界觀中,萬事都可用物理定律去解釋,心靈世界的位置更顯得微不足道,難怪很多學者的致力於將精神還原到物質,雖然這還未完全成功,3 但心靈哲學的主流已很明顯是唯物論,很多人相信隨着神經生理學和社會生物學的進展,能用科學解釋所有精神現象的日子指日可待。4 在這種大氣候中,實在不容易用心靈經驗去印證神的存在。
以上的困難未必不可克服,很多對自然神學的批評和對唯物論的偏愛,在理性上都有疑點,然而傳統自然神學的理想很明顯是難以達到的:有多少前提是所有理性的人都會接受、而又可全無漏洞地演繹出神的存在呢?在現今的多元社會中,這類論證在哲學、倫理與政治的範疇,也是難尋的!5 傳統的自然神學彷似高聳的大廈,但今天似乎已倒塌了!但究竟問題出在論證本身,還是那種近乎完美的要求?不少思想家認為只要調較一下對「論證」的要求,重建自然神學是可能的。他們指出一些高層次的科學理論也不能絕對證實,我們頂多可用歸納邏輯證明它的或然率較大,那處理神的存在的問題時,為何不用同樣的方法和要求呢?在當代史榮本(Richard Swinburne)便是建構這種歸納自然神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論證是開放及累積性的:我們要全盤考慮所有證據,且有心理準備新的(正反)證據會出現。史榮本便將各種證據小心分析及連結在一起,為有神論世界觀的合理性作出很大的貢獻。(此外澳洲哲學家科雷斯特[Peter Forrest]也有力地建構了另一個累積論證。)其實由六十年代開始,宗教哲學中經歷了自然神學的復興,每一個傳統論證都被不少哲學家翻新和維護,且有不少論證推陳出新:
·宇宙論證:戴維斯(Brian Davies)、米拿(Barry Miller)、冰尼(David Braine);
·設計論證:史榮本、戴維斯、比喜(Michael Behe);
·本體論證:彭定加(Alvin Plantinga)、多爾(Clement Dore);
·道德論證:奧雲(H. P. Owen)、亞當斯(R. M. Adams)、米曹(Basil Mitchell);
·宗教經驗論證:史榮本、奧斯頓(William Alston)、吉庭(Gary Gutting)、基爾文(Jerome Gellman);
·心靈論證(Argument from Consciousness):史榮本、亞當斯;
·宇宙起始論證(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克雷格(William Craig);
·知識可靠性論證:彭定加;
·人類原則論證(Anthropic Design Argument):史榮本、勒斯尼(John Leslie)、哥利(M. A. Corey);
·宇宙可理解性論證(Argument from the Intelligibility of the World):米納爾(Hugo Meynell)、博瓊漢(John Polkinghorne)。6
當然這些論證引起的爭議還未曾停止,但正如華德(Keith Ward)所言:「實在談不上哲學已推翻神的存在,我們現在不能有信心說不可能有證明神存在的論證。這此論證正在被提倡及嚴肅討論,宗教信仰的合理性的可能性被廣泛肯定……過去五十年中哲學界的理智氣氛已改變了……在哲學專業內,基督教信仰已不再只是被動……當這麼多英國的哲學教席現在由基督徒擔任,我們大可相信大勢已逆轉,基督徒不再需要感到是在逆流而上。」7 在美國基督教哲學的發展更加蓬勃,基督徒哲學家協會(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在一九七八年的成立是一個里程碑,二十年後的今天,她的會員已超過一千人,是美國哲學協會下面最大的興趣組別。
我們暫且不論這種新自然神學是否成功的問題。自然神學家的努力,似乎假設了自然神學的必要性,好像宗教不可缺少自然神學的支持,這個假設正是巴特要挑戰的。
自然神學的必要性?
為何那麼多人相信自然神學是必需的呢?或許是基於以下思路:
A)有神論是一種有認知意義的「真理」。
B)所有「真理」都要接受理性的檢視。
C)只有當我們能為所信的「真理」提供足夠的證據,我們的信念才是合理的。
更有些人相信:
C’)沒有足夠的證據便相信,不單不合理,更是不道德。
D)所以,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神的存在便相信神,是不合理(甚或不道德)的。
對持守以上(D)的結論者,自然神學實是洗刷不合理或不道德的罪名的必要工具。(D)不單是無神論者的攻擊武器,亦是很多基督徒思想家甘心背負的十字架。當然很多信徒事實上不是被自然神學說服才相信的,但問題焦點正是:這種態度是否不合理的迷信?答這問題時,不可忘記(D)的結論是依賴(A)—(C)的前設的,這些前設又是否正確呢?8
傳統的自然神學理性有資格審判宗教嗎?——巴特對自然神學的批判
巴特對自然神學的態度是一聲如洪鐘的呼喊:「不!」(Nein!)這也是他和布仁麗(Emil Brunner)討論自然神學時,回應文章的標題,他認為「否定自然神學意味着我們拒絕承認它是一個獨立的課題。」9 這種態度從他的基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s)可見一斑,這系列講座的目的正是促進自然神學,但有趣的是巴特被邀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鴨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主領基福特講座,但他稍微提過自然神學後,便對它雙字不提,而將全部時間放在解釋改革宗神學!10 可能正如他說:「若你真的抗拒自然神學,你根本不會注視這毒蛇,免得牠也注視你、催眠你、並最終肯定會噬你一口;而是第一眼見到牠便把牠擊殺。」11他 對自然神學的激烈批判和他對近代教會的發展的理解有很大關連,他「認為宗教改革後的神學歷史是一逐漸衰敗的過程——理性對啟示的反叛。首先是在十七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取代古老正統派的理性正統派,這逐漸導致啟蒙思想和宗教的全面理性主義。」12 當然巴特更認為這最終帶來了「文化抗議宗」(Culture Protestantism)和「德國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的運動,這兩者都以教會的名義效忠希特拉!13


Karl Barth&
Emil Brunner
在這處境中,我們較易明白巴特對布仁爾的憤怒,14 他恐怕布仁爾對自然神學的同情會為「德國基督徒」翻案;「或許我們不曾公允地對待那些可憐的『德國基督徒』?」15
的確巴特很多時會說一些完全否定自然神學的說話,他認為不論是「理性、良知、情感、歷史、文化及其成就與發展」,16 都沒有傳遞任何啟示。「只要我們用一根小指頭支持自然神學,必然的結果是否定神在耶穌基督裏的啟示……只要給它任何位置,你便走在引向自然神學獨霸天下的路上(縱使你可能無心如此。」17 對一些哲學家來說,這種立場似乎有以下涵義:
1)「唯獨恩典」意味着神完全用不着人的合作,人與神之間全沒接觸點。
2)巴特的神學是完全封閉,不可用理性討論的。若人拒絕接受它,根源正是人的罪和驕傲。
3)墮落之後,人的各方面能力都已全然敗壞。
4)啟示不能在人性中找任何接觸點,人性中也找不着甚麼去審判啟示。18
看起來巴特很像一個盲目的反理性主義者,但杜倫斯(T. F. Torrance)*認為巴特反對自然神學是有其深刻的理由,我們參考他對巴特的詮釋。19 杜倫斯明白巴特早期對自然神學的批評很易給人一種二元論的印象:極端地將神與世界對立,但他從巴特較後期的思想出發,認為他對自然神學的批評是建基於對神正面而合理的知識。20 甚麼是合理而客觀的知識呢?是符合客觀具體呈現的知識。所以真正對神的知識,只能建基於神在基督裏的具體啟示,這樣建立的科學化神學杜倫斯稱之為正面神學(Positive Theology)。若任何自然神學認為可抽離神實際的啟示,而獨立地獲得關於神抽象的知識,才是不科學、不客觀:「我們所有對神的自然知識,都遠不能表彰他的偉大,都錯過了他終極實在的特質。我們正是建其於對神的知識的實際內容,及其內蘊的理性方法,才斷定所有建於其他獨立基礎之上的思想運動,最終是不相干的。當它被用來作為正面神學的第二個或輔助根基時,這無可避免地製造混亂。」21 在神實際的啟示中,我們明白神的存有(Being)是不能和他的行動與話語(Act and Word)分割的,既然如此,自然神學企圖抽離神的行動與話語而認識神的存有,又如何能不墮進謬誤呢?再者,道成肉身正是神至高無上的行動與話語,那自然神學希冀在道成肉身的啟示以外認識神,豈不是緣木求魚?所以「除了那位單單結連於耶穌基督的上帝,我們別無上帝。」22 而自然神學只會在透過自然認識的上帝與在道成肉身中顯示的永活神之間,劃下鴻溝,這使我們不得不質疑自然神學。23
道成肉身也啟示了神永恆的三一本質,這使我們不能不質疑「那種並不最終導致三一真神的自然神學」24 神學的人性論也叫我們質疑自然神學,因為「自然神學從人的自然存在發出,而人的整個運動就是去發展他的自主是這運動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神學建基於「疏離了和有罪的人的自主性存在」而且「封神的自然知識的要求……不能與這種人的運動分開:抗拒神恩、肯定自我的運動,這只會發展為一種自然神學,是與透過神的啟示與恩典的行動而獲得的關於神自身的知識,背道而馳。」25 我們也不能忽略「唯獨恩典」(sola gratia)的知識論涵義,這宗教改革的主要思想正正否認我們能作甚麼去換取救恩,這也意味着,「真正認識神要求我們與神在認知上聯合,這不是我們透過自然的能力可達到的」,「神的恩典的運作……不是在我們自然的能力上補足我們的缺欠,而是將我們的生命安置在全新的基礎上。」26 所以自然神學不單表達了人類的自主性,也是在否認神滿有主權與自由的恩典。「唯獨恩典」表示我們作不了甚麼去認識神,不然這就不是真正的恩典,稱義和啟示是不可分割的。
哲學家的批評
巴特的思想實與重理性的哲學家南轅北轍,他招來的哲學批評不可勝數,主要的有:
1)自打嘴巴?
用論證去否定理性是自打嘴巴的,巴特由啟示的本質推論出「理性不可審判啟示」的結論,這不也是在使用理性嗎?用理性論證去否定理性是行不通的。
2)「啟示」的多元化
批評者或說:「我姑且接受理性不可審判啟示,但有那麼多宗教都宣稱自已有啟示,我如何分辨哪一個才是如假包換的啟示呢?」
3)道德上的批評
更有人認為犯了狂妄之罪的,正是巴特的信徒而不是他人:他們「混淆了他們的想法與神的想法」,他們「假定了他們相對且人性的禁止是絕對且神聖的。」27完全拒絕接受批評的封閉系統只會帶來偏見、狂熱行動和逼害。
4)理性的要求
哲學家多認為一些起碼的理性要求是不可少的,如以下三種一致性:
a)邏輯上一致:「理性與信心的事情分開,就算在理論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就算是有使用可被理解的語言的意圖,我們最少也要接受理性的一致性法則,沒有這法則意義便不能保存,無論是簡單的信徒或高深的神學家也不能例外。」28
b)與其他真理一致:所有真理最終不會互相矛盾的,所以啟示不能不與其他人類知識一貫,如科學定律。
c)與道德真理一致:「當我們被勸喻去敬拜一個行為惡毒或命令人行惡的神時,……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所謂啟示其實是由人的魔性衍生。若連這消極的標準也沒有,那甚麼都可接受為啟示。」29
對白蘭沙德((Brand Blanshard)來說,巴特甚麼要求都達反了,他封道成肉身的詮釋妄顧矛盾律,他的原罪解就則違背道德律!30
5)不切實際!
柏頓(Paton)也堅持:「在現代世界中放棄理性,等於自動放棄發言權。向理性宣戰,……會使我們與所有關心真理者疏遠,及為騙子與狂熱分子大開中門。」31
6)不美滿的人生
法維(Ferre)認為以理性去批評巴特的立場是徒勞無功的,但他認為忽略理性的體系是不完滿的:「用理性去批判『對理性的拒絕』,似乎也是循環論證!……但這個圓圈我們可滿懷信心地進入。它承諾會產生理智的圓滿而不是割裂;這為負責任的(而不是任意的)決定提供基礎;這是心智的馬車,是一個不斷前進的『良性循環』,所有思想的進展都要乘坐其上而前行。」這是因為「理性的圓圈容許我們對其主張不斷地作最廣泛的測試——這顯示了理性的本質,及理性的圓圈原則上不是『惡性』的,因為它不是不可糾正的。」32
巴特:後現代神學的先驅?
巴特的立場是否能被以上的批評輕易推翻嗎?也不盡然。以上第一個批評說巴特用論證去否定理性是自打嘴巴,這是對巴特的誤解,因他不認為他對理性的批評,是由一個抽象的「啟示」概念而推論出來的。他會堅持,他認識理性的無能,也建基於神在基督裏的具體啟示:「除了透過啟示,還有甚麼方法辨認出啟示就正是神對自己的見證呢?透過啟示辨認啟示就是說,因着啟示甦醒我們的信心,我們有能力辨認啟示。」33 再者,他也可將他的論證包裝為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若你接受理性,你的理性也會指出以理性審判啟示的困難,因為若萬有的根源存在,祂也是理性的根源,那如何能用我們被造物的理性去審判祂?若你不信任理性,那更不應用理性去審判神。所以,你始終不能說理性可審判啟示。」這只是假設性的推論,不代表巴特接受其前提。
多元「啟示」的問題較嚴重,但也不足以摧毀巴特的立場。要再次強調巴特不是由一個抽象的「啟示」概念衍生一種普遍的方法論,由始至終他談的是一個特定的啟示——在基督裏的啟示,是這個活生生的啟示事件(Revelatory Event)(而不是「啟示」的概念),從天而降、抓緊巴特。啟示的可能性和這啟示的真確性,在同一個啟示事件中被認知。這裏完全沒有「所有『啟示』都不可懷疑」的前提。當然巴特知道其他人未必會接受他的看法,但他已表白,對啟示圈外的人,他只能宣講,而不會用理性說服他們。無論你如何不滿意以上的回應,但邏輯上它們似乎不易推翻。柏頓也承認只要巴特的追隨者「完全一致地緊守立場,他的立場是攻不陷的。」他這個比喻也很傳神:「只要我們……堅拒踏出魔術圈之外,所有以理性之名迷惑我們的鬼魔的攻擊,我們都可安然渡過。」34 白蘭沙德也同樣「讚賞」巴特的策略是很「聰明」的。35
對比起來,神學家基列格(Richard Grigg)則似乎不大明白巴特的思路,他堅持以上兩種批評是成功的:「分析到最後,巴特未能清楚說明如何知道他宣稱他知道的……巴特說我們能知道這是啟示也是啟示的一部分,當然這答案只能將對人類理性依賴的需要推遲一步……我現在必然要問,我如何知道顯示事件Ⅹ是啟示的「啟示」真的是啟示。換句話說,我們要不是陷進……無窮後退,便是要在全無獨立理據的情況下躍進所謂啟示的封閉圓圈。至少在現代或後現代的世界裏,這必然被判定為一種違規——這規則是指神學家需要解釋如何能知道他們宣稱他們知道的。」36 最後基列格甚至說巴特的神學算不上是學術的神學!以上的批評正正顯示了神學家有時太被俗世的思潮所規限,巴特當然知道別人可進一步追問他知識的基礎,但他可以每一次都答:「是啟示。」他甚至可反問基列格如何證明「對人類理性倚賴的需要」,無論他如何作答,別人都可進一步追問他如何證明他的答案,無窮後退或盲目接受的兩難是懷疑論者質疑理性的論據,是所有人類知識面對的普遍困難,基列格卻以為這只是巴特的困難!傳統哲學對懷疑論的回應是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它是說我們最後可找到一些不可懷疑、不證自明的基礎(如感官素材、先驗知識),但後現代思潮就正正否認我們有一些不可懷疑、不證自明的基礎,那為何基列格在這個後現代世界仍然堅持巴特要遵守一種沒有人守得到的規則呢?更進一步將這種不合理的要求定作學術的標準,是否一種霸權主義呢?
至於「驕傲」的指控可發揮提醒的作用,但除非我們先驗地否定啟示的可能性,我們也不能說見證啟示者一定是出於驕傲。若一個人真的被神的啟示抓着,那他的責任只能是謙卑地將它宣告,他並沒有選擇的餘地。第二個道德的批評是巴特的封閉系統會帶來偏見、狂熱行動和逼害。這批評相當嚴重,但巴特的跟隨者會回應:愛正是他們信奉的基督的啟示的中心,這是不應帶來逼害的(但教會的歷史叫我們不得不警惕)。批評者會質問,一些極端教派又如何?理性若是批判膺啟示的利器,過分貶低理性會否帶來禍害?「瓊斯鎮(Jonestown)的可怕事件37清楚告訴我們,不作批判性的判斷便貿然委身信仰,是不負責任的。對那誠實求真的人,唯信論者提供不了援助,他提供的只是在現代宗教巴別塔之中的另一把呼喊聲。」38 這種說法有點誇大了:唯信論者也相信他能提供真理的——他只是相信他的真理源於啟示,而不是理性,認為巴特不能「對那誠實求真的人」提供援助,是否已假定了巴特主義不是真理呢?這不也犯了乞求論點的謬誤嗎?不錯,很多慘劇顯示宗教的錯誤可能會帶來災難,「批判性的判斷」的確需要,但問題是為何只有理性才可是批判的基礎?這不是又假定了理性能辨別真實與虛假的啟示嗎?這也似乎犯了乞求論點的謬誤。其實從巴特反抗納粹黨的實例看到,說唯信論者不能成為批判的基礎是不對的,某些情況下,以啟示為基礎使批判更堅決。
至於理性的要求又如何?有一點我是認同的:邏輯一致性的要求。有時一些神學家會宣告啟示是超越矛盾律的,甚至以「悖論」為榮,好像愈多矛盾的啟示便愈高超!我個人以為若放棄了矛盾律和一致性的要求,我們很難有意義地說話或溝通。一些神學家認為這是用邏輯去限制神,但他們真的認為神可以擁有互相矛盾的性質嗎?例如我們可否說「神是愛,但也不是愛」嗎?這一來我們的信仰仍然有固定的內涵嗎?其實我們沒有需要堅持神是超越邏輯的,因邏輯定律若有必然性,也是植根於神的本體。我們也可區分「悖論」與「矛盾」,前者只是看上去有矛盾,神學或者真的少不了悖論,如祈克果(S.Kierkegaard)*所言的神人(God-man)的絕對悖論,但它們不是真的有矛盾,39 就像兩條線,從上面看好像有交接點,但只要從側面看,便知道一條線在另一條之上,永不交接。我們有時不得不用悖論,是因為我們的視野和語言都是有限的。那當我們想描述終極實在(神)時,發覺我們語言的範疇不能完全稱職、捉襟見肘時,並沒有甚麼好奇怪的。禪宗的公案就透過不同的悖論打破我們思想的框框,認為這樣才可悟道。但最終說實在是自相矛盾是沒有意思的,否則我們在所有事情上說甚麼都可以,因為自相矛盾的語句邏輯上可推論出任何句子!所以神學家也應遵守矛盾律,雖然因着我們的有限性,有時要使用悖論。
不可忘記我們建構神學時也是要用矛盾律的,例如巴特說接受啟示為唯一起點的人不能同時以自然神學為神學的基礎,但為甚麼不能呢?因同時接受兩種思想是自相矛盾的!若我們不用理會矛盾律,那為何不將巴特主義與自然神學兼收並蓄呢?所以我同意這個白蘭沙德對巴特的批評:「若最好和最清晰的理性指引都不穩妥,那你的神學既然每一步都在依賴這種理性的使用,本身也是走在浮沙之上。」40 然而承認了這個批評並沒有動搖巴特的主要洞見,因矛盾律只關心你的信念是否一致,並不關心這信念從何而來:啟示?經驗?理性?——都沒問題。所以只要巴特的跟隨者不堅持啟示超越矛盾律,以上的批評並未推翻他以啟示為起點的合法性。
至於其他「理性的要求」則牽涉到神學與其他知識(科學、倫理等)的關係,關鍵的問題是:「啟示與其他知識應該有連續性嗎?」有三個主要答案:
1)成全模式(Fulfilment Model):啟示是成全由理性獲得的知識,兩者基本上是連貫的。
2)審判模式(Judgment Model):啟示並不用去「應酬」人類的知識,它反而像春雷乍舌的響雷,審判我們自恃的「知識」。
3)辯證模式(Dialectical Model):啟示在審判之中也同時成全。
巴特當然不同意成全模式,例如士來馬赫認為「信心」只不過是內在於人類心靈的能力的最高發揮,而「道成肉身」只是指人內在的上帝意識(God-consciousness)在耶穌生命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完美無瑕、全不間斷……但對巴特來說,道成肉身是絕對不可預料、「不合理性」的,錯非上帝的啟示,理性是萬萬不能推論到道成肉身的。巴特那麼強調啟示的超越性,因他深深感到成全模式的危機:太重連貫性會否定了啟示與理性的不連貫性,不合人心意的信仰便被任意剪裁,神學被消解為人學……,所以巴特呐喊:「神就是神,人就是人!」這不無道理,神的啟示又豈可被純粹是人的可能性所包容和限制呢?
而巴特很明顯是傾向審判模式的,這亦有可取之處,若啟示使一切事物(包括我們的「知識」)都原封不動,我們反要質疑它是否真的從天上而來。我認為巴特強調啟示對「知識」的審判,是饒有深意的。不少哲學家將「知識」分析為「被證立的真信念」,啟示的審判也有兩方面,第一,它揭示一些「真理」(如人的自主自足性)的虛幻。當代的詮釋學和科學哲學都指出,所有觀察都被理論滲透的,這不是說「甚麼詮釋都沒問題」,重點是沒有完全孤立的「事實」,每個「事實」總有一些詮釋的成分。巴特的要點可能在於指出,事物的意義即視乎世界觀,而「自然的人」(natural man)會在神以外找尋一個無所不包的意義系統,那啟示豈不應審判這種無神論世界觀及它對不同知識領域的涵義嗎?
啟示也同樣揭示出我們知識的證立的虛浮性。我們的證立是建基於有限的事物——都不是自明的,這便永遠給懷疑論留下攻擊的空間,然而知識的實在論仍然吸引,因為我們很難全盤否認知識。這樣看來,雖然我們擁有知識,但我們的知識並沒有絕對的立足點,是不能自證的,從理性的角度看,這情況始終有些不協調及張力。這種種問題卻在有神論世界觀中可解。假設一部電視突然有了自我意識,它且思索它為何可產生影象,它縱然可解開疑團之一二,但終極原理它是不能解釋的。只有那通曉電子學的設計師真正明白電視的能力的根源。同理,人的認知能力從神的智慧而來,知識的終極證立並不內在於人類的認知過程。
所以,巴特的思想雖看似和保守派的反智主義如出一轍,但分別在於他是洞悉現代精神的,當現代精神仍然強調所有知識都需要普遍的方法論和起點時(這是一種基礎主義),巴特已明白基礎主義的不足並言行一致地批判它,不錯,很多人都批評巴特的系統是一個循環論證:他的知識論源自他的神學,而他的神學又建築在他的知識論之上。但本體論又是否真的可以和知識論分開嗎?這種循環論證似乎是所有世界觀和哲學系統都不能避免,巴特只是清楚地將它顯示出來罢了。這種種都與後現代思潮對基礎主義的批評不謀而合,41 怪不得有人說巴特主義是後現代神學的開始。42 有趣的是他的神學知識論和當代宗教哲學中的改革宗知識論(Reformed Epistemology)有異曲同工之妙。改革宗知識論的主要提倡者有彭定加和勞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我們再看前面提過的前提:
C)只有當我們能為所信的「真理」提供足夠的證據,我們的信念才是合理的。
他們稱這類立場叫證據主義(Evidentialism),並指出它假設了基礎主義,然後再對基礎主義深入批判,43 他們的結論是基督教信仰不用接受證據主義的要求,即是說就算基督教信仰不是建立在普遍的理性與經驗上,也可以是合理的,因為假設了證據主義去批判基督教信仰,不單犯了乞求論點的謬誤(這點與巴特的精神相通),更是接受了一個哲學上不能維護的前設:基礎主義。彭定加近年使用他的哲學分析技巧,致力於寫作改革宗知識論的三部曲,44 第一本尖銳地批評多種現時流行的知識論,第二本建構一種新的知識論:正確功能論(proper functionalism),按彭定加的分析,知識是一些符合以下條件的真信念:
他且嘗試論證「正確功能」最終很難純用自然主義去分析,而認知機能的設計藍圖和可靠性亦與自然主義的進化論不協調,所以知識論的探索最終會支持有神論的合理性(這點與我上面的分析相似)。他的第三本書更進一步應用正確功能論於基督教信仰上,維護加爾文關於人的上帝意識(sensus divinitatis)、聖靈的內證(Inner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罪對「知識」的扭曲等主張。這些都與巴特的思想吻合,我不能肯定巴特會否接受彭定加的哲學進路,但我個人以為神學與哲學的進路未必矛盾,彭定加的努力顯示巴特的洞見是不容忽視的。

至於關於實用性的批評,巴特的信徒明言他不能和未信者說理,而只能向他宣講,他也大可承認他這種進路未必會很受歡迎,但這不代表巴特的思想就是錯了,持守真理不是應有付代價的心理準備嗎?巴特的跟隨者將別人的排斥視作信仰的十字架又有何不可?巴特便說:「我們在這裏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去獲取成功。」46
我總結一下巴特的洞見:
1)啟示在對神的認知中應有首要位置,去堅持關於神的知識一定要用理性由其他知識推論出來,其實已是否定了啟示的精義。
2)更進一步,所有關於神的知識都要透過特殊啟示去理解。
3)我們亦可從啟示出發,「審判」人間的知識。
以上很多批評都似乎不能摧毀這些主張,它們甚至可用哲學方法維護。但我認為巴特的立場也有限制,下麵詳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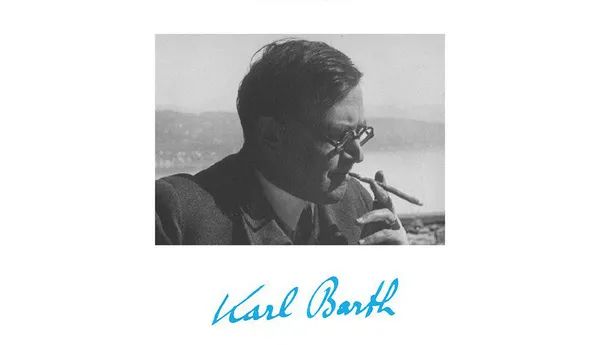
自然與恩典:連貫或斷裂?
我認同純粹採納成全模式是有危機,但純粹的審判模式也有不足。讓我們再思宗教的語言遊戲(religious language game)與其他語言遊戲的關係,縱然我們不需由後者推論出前者,但我們是否可以完全不用關心啟示與其他「真理」的一致性呢?是否任何與啟示不符的「真理」,我們都應審判它,並棄之如敝履?似乎不是。第一,我們真的一點兒獲得真理的能力都沒有嗎?這似乎極端了些,我們不用特殊啟示也知道痛苦的存在,假若有一種「啟示」否定痛苦的存在,說一切痛楚都不是真實的,那我們放棄的應是那「啟示」;更正確的說法是,我們辨別到這所謂啟示不是真啟示。全盤否定理性的能力,不單難以置信,更將自然與恩典完全對立,我同意布仁爾對巴特的回應:若自然的人真的與恩典完全脫裂,還能稱之為人嗎?可以叫他為自己的罪行負責任嗎?47 貝利(John Baillie)更加強調自然與恩典不可分割,48 甚至說人性也是神啟示的媒介。49 換言之,自然獲得的知識至少有部分也是難以否定的。第二,啟示是否真的像從天上擲下來的包裏——完全清楚和確定呢?似乎不是,所以我們的神學內容不能等同啟示,我們也要正視如何制衡神學家的錯誤和偏見的問題。當「啟示」與一些牢固的自然知識衡突時,或許我們需要質疑的是那「啟示」或我們對啟示的詮釋。其實這未常沒有好處,我上面提過唯信論者的確可以有批判性,但他只可以從自己的信仰出發,這可要付一個代價,就是無論其他「啟示」如何荒謬,他也不能用理性去批評。不錯多元「啟示」的理象不足推翻巴特主義,但始終對很多人來說,巴特的跟隨者不能提供啟示以外的人可接受的理由去選擇基督教的啟示。但假若我們不完全否定自然,我們就可用理性印證基督教啟示的可信性或優越性。
或者會有兩個批評。第一,我前面承認沒有完全沒詮釋成分的事實,那豈不是說並沒有中立的事實可以去仲裁不同的「啟示」嗎?不,事實與詮釋雖不可分,但這不就表示「事實」可無限地任意詮釋。以苦罪的問題為例,苦罪的意義在不同世界觀內不盡相同,但如上所說,全盤否定苦罪的存在是明顯不可接受的。第二,我既已肯定了恩典的自主性,那又豈可說啟示要在某程度上與自然「妥協」?若我們能辨清不同概念,這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啟示不需由理性推論而來,所以自然與恩典有不連貫性。但啟示的內容能否由理性推論而來,則是另一個問題。巴特將不連貫性高舉,似乎是過度反應了。啟示挑戰我們看事物的最終角度,及揭示我們的證立不是自足的,但啟示用不着全盤取代我們的知識。而且啟示可說明我們的知識和經驗,我上面提及當代自然神學的百花齊放,或許沒有一個論證可百分百證明神的存在,但每一個論證至少顯示有神論可解釋人生宇宙的現象:宇宙的存在及起始、宇宙的秩序與美麗、自然定律的精巧安排和可理解性,生命與心靈的出現、人類的認知機能、實存經驗、人際經驗、道德經驗、審美經驗、宗教經驗等等,這至少證明了啟示與人類知識的連貫性,也可說啟示在成全人類知識。但同時啟示揭示我們知識的脆弱,及我們反思及更新的必要,這或會帶來拆毀(審判),但重建後的知識大樓應比前更美麗、更穩固,這是恩典對自然的成全。我的結論是,純粹的成全模式和純粹的審判模式都不可取,辯證模式雖較含糊,但卻是必需的。
以啟示與道德的一致性為例。去全盤否定人的倫理知識是不可行的,若人一點倫理知識也沒有,全然分辨不到善與惡,那神為何要人負責任呢?假若人有一些倫理知識,那啟示應與其吻合。啟示誠然挑戰我們道德上的自足性,也賦予道德新的意義,但啟示總不會將善惡的界線完全泯滅,或將殘酷視為最高善吧?巴特不會反對吧?若不,那他承認了啟示也要符合一些基本的道德要求,即是說「啟示」不是絕對不可判別的!我相信啟示也是一方面揭示我們對善惡的終極意義的瞭解之偏執,並轉化我們的道德價值;另一方面啟示也超越(而不是取締)我們的道德。白蘭沙德認為對巴特來說,將基督的無罪歸入人類的道德良善的範疇,也是一種誤解。50 但他質問:「巴特是否真的感到無論是自然的愛與無私,或憎恨與惡毒,神在當中的臨在都是同樣稀少?」51 他又問:假若人對善惡的分辨真的那麼無能,那既然人間的美德可以是罪人的偽裝,為何人間的邪惡不可以是聖徒的偽裝呢?這些尖銳的問題顯示,啟示不錯可挑戰我們的固有道德概念(如「人不為已,天誅地滅」),但卻不能將它們連根拔起。
再以宗教語言為例,巴特認為人的概念是不能加諸神身上的,所以他反對神與人有存有上的相似(存有的類比(analogy of being),人的語言之所以能用在神身上,純是出於恩典,是啟示徵用了人的語言,只有透過信心接受啟示,我們才能肯定神與人的相似(信心的類比[analogy of faith])。52 若巴特正確,自然神學就算能成功推論出「神」的存在,這也只是哲學家的神、是偶像,決不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聖經》所啟示的永生神。以宇宙論證為例,假設我們證明了「第一因」的存在,但由於我們一直只是用我們的自然語言,那這「第一因」與世界的因果關係都只是限制在人所能經驗或想像的因果關係,但巴特認為神的創造是與我們能經驗或想像的「產生」、「造成」有質的差別,53 所以最終這[第一因」不能等同《聖經》的創造主,若你以這「第一因」為神去敬拜,你可是在拜偶像了!54 怪不得巴特認為「對自然人來說是『神』的只是假神」,自然人透過自然神學所認識的就是這個假神!55 我們看到巴特這裏又是將自然語言與啟示語言完全二分,但這很難解釋我們如何能明白啟示,巴特說得對,沒有任何人類經驗中的「創造」可等同神的創造,但這不表示人類經驗中的「創造」沒有任何方面與神的創造相似。事實上,巴特也有「啟示語言」成全「自然語言」的講法:「當我們用這些詞語在神身上,我們沒有取消它們的原本意義……我們其實在說出這些詞語的原本真理。」56 問題是:若兩種用法全無相似之處,巴特所言的又何以能發生?57 所以我比較同意布仁爾所言,存有的類比是不能完全否定的。58 59
啟示與封閉系統
法維強調的理性整全性是值得深思的。若巴特的跟隨者鄙棄所有人類的知識與經驗,那他獨尊的啟示便懸在半空,他的認知系統是割裂的,他陷在一個封閉系統內,他犯的錯誤(如對啟示的誤解)也不可能糾正。然而,這流弊的產生也是因為自然與恩典的對立,如上所說,將啟示放在中心的人可採納辯證模式,我們沒理由相信我們的「真理」會全盤被特殊啟示取替,至少特殊啟示的實際內容對很多方面的真理都沒提及。所以他亦可尊重知識與經驗,他雖否定啟示要建基於知識與經驗,但這種信心仍可不斷尋求理解,他讓啟示的光芒照在所有人類的知識與經驗上——審判它們、重新詮釋它們,若啟示是終極真理,在其光芒指引下所建構的認知系統不必然是割裂的,反而應該是完整、融貫和能滿足理性要求的。這個「信心尋求理解」的過程也帶出測試和糾正的可能:若一種「啟示」根本不能說明很多現象和經驗,那我們有理由反思這「啟示」的真確性,或質疑我們對啟示的詮釋。這樣看來,以啟示為出發點也未必會產生封閉系統。60
潘寧博(Wolfhart Pannenberg)*也認為系統神學不能逃避真理的問題,他正面肯定哲學神學的作用,認為這可建基於《聖經》的獨一神論及創造論,所以將哲學家的神與啟示的神對立是不當的。61 啟示的神也是萬事萬物的創造主,那在系統地解釋啟示時,可與萬事萬物的真理印證,這也可成為測試的過程:「系統地展示世界、人類和歷史如何在上帝裏找到根基、和解和圓滿,也是在處理神本身的實在……教義學作為系統神學同時採用主張和假設的方法,它提出一個世界、人類和歷史如何在上帝裏找到根基的模型,若這模型站得住腳,這就『證明』了神的實在和基督教教義的真理,及顯明它們是可以融貫地理解的。藉着這種展示的形式,它們亦得到印證。」62(這與米曹[Basil Mitchell]的進路也有相通之處。63)因啟示是超越的,它的豐富是永不窮盡的。因啟示是適切於每個時代的真理,我們要在每一個處境展示它的涵義。這樣看來,正因着我們要忠於啟示,我們不能將它變成一個封閉系統。以啟示為起點的神學也可以是動態、活潑的,接受巴特的洞見的神學家不用陷入理智的死寂,也可以展現法維所說的不斷前進的良性循環。64

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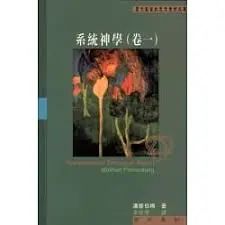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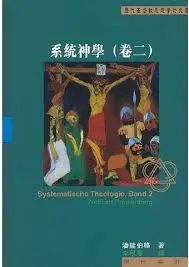
普遍啟示的必需性
以上的討論顯示,巴特的基本洞見:「只有透過神才可以認識神」(Through God alone can God be known),似乎是可以維護的(我不是說可以證明),堅持信仰一定要理性證明,是一種知識論的帝國主義,但將啟示與理性和經驗完全分隔和對立也不妥當。但理性主義者會質疑我這種折衷立場會陷入兩難局面:對「理性能否審判啟示?」這問題,無論答「能」或「不能」,都好像不妥當。從啟示的本質看,似乎是容不下人間權威的指指點點,若容許理性審判啟示,那啟示便失去了獨立的地位,也稱不上啟示。但若全不理會理性的要求,封閉系統的危險亦很真實,且流弊叢生。這兩者如何取捨呢?
然而這兩難的產生,只因為我們的「啟示」的概念太狹窄,及我們將特殊啟示與所謂「沒有神幫助的理性」(“unaided”reason)割裂了,「只有透過神才可以認識神」是不錯的,神的存有與行動、神的話語與道成肉身都不可分割,但神的行動與話語真的只限於基督事件嗎?基督事件在人類歷史中又是否真的只是數學的點,與歷史只有切線的關係?其實在基督裏的啟示起碼要在神對以色列人的啟示的處境中理解,道成肉身的確是神的最終極話語,但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已藉眾先知曉論各人,如巴爾所言:「神在基督裏自我啟示之前,有沒有任何關於神的知識呢?若我們正確地考慮正統的基督教原則(甚或巴特自己的原則),唯一的答案『有。』《舊約》提供了這些先前的知識。」65 當然我們也不用將《舊約》的啟示與在基督裏的啟示截然分開,因為在先知裏頭說話的不也是基督的靈嗎?(彼前1:10-11)或許如巴特所言,《舊約》啟示都要以基督論角度去詮釋,因《舊約》的啟示最終也要在基督裏成全,但這不代表它的願意可以忽略或沒有貢獻。當然《舊約》啟示仍然屬特殊啟示的範疇,但以上的討論顯示:「神只在基督裏自我啟示」這句話不能太狹窄地詮釋。何況成了肉身的道,神創造萬有不也具籍着他嗎?他也豈不是那照亮一切人的真光嗎?(約1:9)(奧古斯丁就相信神普遍地光照人類的理智,使我們保全[部分]認識永恆事物的能力。66)換句話說,基督是一切被造物與人類知識的本體根基,我們實不能將基督的重要性或工作規限在他在地上的三十多年。甚至有些神學家強調宇宙性的基督。67
若我們能肯定神亦能透過自然、理性與良心啟示——即是說普遍啟示是存在的,那以上的兩難題便可解決,因自然神學或理性的能力也是基於神的啟示——普遍啟示。布仁爾其實也和巴特一樣肯定啟示的首要性,但他認為《聖經》和基督教傳統同樣肯定普遍啟示的存在,所以他能一致地接受自然神學(但他強調自然神學內容既貧乏,也沒有救恩的功效。)。若布仁爾是對的話,巴特就面對一個難題:若他所肯定的特殊啟示也肯定普遍啟示和自然神學,那他否定普遍啟示和自然神學的立場也難自圓其說了!巴爾的書就企圖證明這點,他認為保羅的宣教資訊(徒14、17)、《羅馬書》首二章、耶穌的比喻、(舊約》的《詩篇》和智慧傳統都是支持自然神學的,在過程中他也嚴厲批評了巴特的釋經68和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的二分法。69 他這樣操作結論:「就算我們認為自然神學的元素在《聖經》中是相對地次要的成分,這些元素的功能依然非常重要。……原則上否定自然神學的神學會遭逢深刻的內在矛盾……事實上它們的原則逼使它們遠離《聖經》的真理。」70 我不能在這裏詳細討論這課題,我相信在這問題上,布仁爾比巴特正確,有很多《聖經》學者和神學家都同意自然神學有《聖經》基礎,71 歷史上基督教的主流傳統(包括巴特認同的改革宗和加爾文)也似乎某程度上接受普遍啟示和自然神學。72
所以我們不能排斥神亦透過自然、理性與良心啟示的可能性,巴特的追隨者或許認為這是將自然放於恩典之上,但這忘記了自然的創造也是源於自由的恩典,世上並沒有「沒有神幫助的理性」這回事!73 每一個正確的推理也是靠賴神的恩典托住,若不是神自由地創造一個穩定而可理解的世界,若不是神厚賜我們理解的心靈和思考的能力,一切知識與科學都不可能。所以當我們正確地使用理性時,這是自然,也是恩典,我們實沒有可誇、可恃之處。若理性也可用來判別「啟示」,這全因為墮落之後,神仍然保守我們的理性,預備我們去迎接神的至高啟示,既然如此,使用神恩賜的理性能力如何會危害啟示的完整性和首要性呢?74巴特的追隨者或者會指控我泯滅了啟示與理性的分別,但我只是重申普遍啟示與特殊啟示的分野,普遍啟示是指那些由於神創世和維持的恩典而可普遍被認知的真理,而特殊啟示是指《聖經》見證的救贖與啟示的歷程,在道成肉身上到達高峰,兩者都是神的主動、神的恩典,是不互相矛盾的。所以要求普遍啟示與特殊啟示互相吻合,不等於將自主的理性淩駕於啟示之上去審判它。當然特殊啟示也不能消解為普遍啟示,不然我們會重蹈自然神論和自然宗教的覆轍,反而後者要在前者的亮光中去詮釋,但這詮釋最終是成全而不是否定普遍啟示。這種立場既是特殊啟示所肯定,也是普遍啟示所贊同,所以並沒有「標準不一致」的問題。
墮落、恩典與自然神學
巴特的追隨者的另一個憂慮,是我可能忽略了墮落的深遠涵意,我要重申,我主要論點是,在啟示的範圍中,是容得下普遍啟示的可能性,但或許罪已抹殺了這可能性成為事實的機會,所以巴特的追隨者會強調「罪對理智的影響」(noetic effects of sin)。但這概念相當含混,這些影響到底是甚麼呢?「罪對人的身體與心靈都有破壞性的影響,這使人經常會有錯謬,無心之失、不妥善的教育、人生的混亂關係的影響、自私自利等等。……本來這些影響可透過不斷互相參照科學成果而減到最輕,但……罪對人性是帶來如此嚴重的傷害(因罪使人忘記他是被造物),所以他依然努力地壓抑神對他的啟示,這樣他便放棄了能證立每一個人類指稱的唯一起點,也理論上摧毀了知識的可能性。」75 若普遍啟示包括一種對神直覺的知識,我們的罪或許會破壞了這種能力,關於這方面「罪對理智的影響」,我們還需進一步的探討。76 但若以上就是「罪對理智的影響」,那我看不到它如何能使一個原來有效證明神的論證,變成無效,因為一個論證對確與否,是視乎前提與結論的邏輯關係,與人的態度無關。若從來都不存在對確的論證,自然神學的失敗也不是因墮落而來。所以原則上很難理解罪會摧毀以論證為主的自然神學。
巴特的追隨者仍然憂慮,若人能用自己的理性去認識神,那他豈不是可以在救恩上自誇他的功勞,這便與「唯獨恩典」的大原則違背。這論點有些混亂,首先要指出自然神學的知識不足以帶來救恩,就算人能用理性肯定神的存在,他仍然可以反叛這位神,自然神學的知識在這種情況只會令他難以諉罪。此外假設神透過一個人閱讀英文《聖經》去拯救他,那他用於學習英文的努力又是有助他得救的「功績」嗎?他能念英文,就與「唯獨恩典」的大原則違背嗎?似乎不是。同理,若人能用自己的理性去認識神,這未必有救恩的功效,而且也是神的恩賜,如何談得上是人的功勞,所以也不會與「唯獨恩典」的原則違背。至於認為自然神學家的動機一定是自然人的驕傲則明顯是以偏概全,似乎我們也可因着渴慕神或服事神而獻身自然神學。77
巴特與自然神學的和解?
我一直在論證啟示的首要性並不代表自然神學必然不可能,杜倫斯也似乎贊成巴特的洞見與自然神學未必不相容,他論到「唯獨恩典」時說:「就算在這裏巴特也不是否認自然神學的可能性或存在,他只是指出自然神學,因着神透過基督主動傳遞對他自己的知識,被架空、相對化和置於一旁。」78 他甚至說:「巴特能夠說自然神學被啟示神學包涵和發揚光大,因神的恩典事實上包括了上帝的創造的真理。在這意義上,巴特能詮釋及肯定亞奎拿的格言:『恩典不是摧毀自然,而是成全自然、使它完全。』他也可進一步論證,當神的啟示使已被埋藏和遺忘的創造的真理重見天日時,啟示的意義更被彰顯。」79 這種「已被埋藏和遺忘的創造的真理」與我談及的普遍啟示很相近。他甚至認為「自然神學……一定要安放在正面神學的全體之內,自然神學的探索也要與正面神學構成不可分割的整體。」80 而自然神學「會成為神學的科學之中必要的輔助架構。」81 在這過程中,啟示的內在合理性被展現,神學知識也得着正當的「證明」。他相信「巴特自身也指出,人的受造理性的真理,要放在恩典的處境中,顯出光芒和得着成全。」82,只是在決定性時刻巴特似乎退縮了。
事實上巴特在後期承認他早年過份強調神的神性:「我們將『完全的他者』孤立起來、抽象化和絕對化,將祂與可憐、可憫的人對立起來……這一來祂便顯得一直與哲學家的神,比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更相近。」83 巴特強調若真正尊重啟示,我們可見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實自我啟示為人的夥伴:「上帝是誰?祂的神性又是怎樣?啟示所呈現的上帝不是在真空中存在、只為自己生存的神聖存有,而是無論是祂的存在、說話和行動,他都顯為人的伙伴(但當然是絕對優越的夥伴),這正是啟示如實和真切地見證的事實。」84 而且正確認識神的神性,正是認識他基於他的自由、主權和恩典,在基督裏與人性聯合,所以神的人性也同樣重要:「正正是神的神性,(當被正確了解時)包含了祂的人性。」85 這種對神的人性的了解,使我們不能對人性、人的能力和文化完全悲觀:「神並沒有拒絕人!……這種透過神的人性而有的人的特性……亦延展到每一樣神作為人的創造主賜予人和裝配給人的東西,這恩賜——他的人性——並沒有因人的墮落而消滅,他的良善也沒有減少。」86 這種特性甚至延伸到「人類文化——無論是較高等或較低等的水準。」87 巴特甚至談及創造的光芒和特殊啟示以外「另一些真實的話語」,雖然他始終沒正式為自然神學翻案。88 我們也要注意,我一直也論證巴特的主要洞見和自然神學沒必然矛盾,而巴特也強調他的轉變也是基於對在基督裏的啟示的新瞭解,所以這種改變並非如漢斯·昆所言,會使他的系統崩潰。89 正如迦西墩信經所言,在基督裏神性與人性既不可混亂,也不可分離,巴特早年強調神與人無限的質的分野,和後期接納神是人的伙伴,其實都是反映同一個基督論的兩面,這與他從在基督裏的啟示出發的進路,並沒有矛盾。
這樣看來,杜倫斯對巴特的詮釋至少和後期的巴特有吻合之處,但或許「關於自然的神學」(theology of nature)比「自然神學」的名稱更貼切:從啟示開始,但接着在啟示的亮光中詮釋一切事物,我相信事物的詮釋不是無窮可塑的,有一些詮釋是不合理和牽強的,當啟示神學與理性神學並駕齊驅時,我們可看到啟示在成全而不是否定自然的真理。這也開展出批判思考的成分,「封閉系統」和「理性割裂」的指控也不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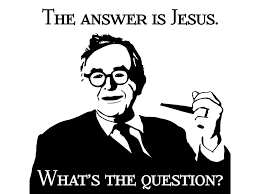
結語:自然神學的價值
「理性能否判斷宗教?」答案是:「能,也不能。」宗教也不能完全免於三重一致性的理性測試,(但這裏也要留下「宗教轉化我們的知識」的空間,因我們的「知識」也有不確定性。)在這意義上理性可判斷宗教。另一方面,信徒有從自已信仰系統出發的權利,他沒有必要從其他系統出發證明自己的系統,在這意義上理性不能判斷宗教。然而這信仰應不停開展理性神學或關於自然的神學(當然實踐也很重要),一種修正了或溫和的自然神學仍然可能,它亦很重要。麥奎利這樣論及合理的信心:信心「不是純然理性,但它可面對批判與糾正的理性的檢視和測試,而仍屹立不倒。信心不是理性的附從,也不單單是理性的擴充,但我們要顯示,它與理性相容,甚或被理性支持。」90 對他來說,自然神學是甚為需要的,因它可將神學家的世界與一般經驗的世界連接起來,若啟示神學完全「與世隔絕」,將會顯得孤立與奇特,一般人對神學的猜疑與輕視也不能消除。
回到巴特與布仁爾的辯論,布仁爾認為自然神學的好處在於可提供接觸點(如祈克果對絕望的分析),前面已論到,巴特的神學批評實不足以否定布仁爾的論點,然而巴特也有從實用角度回應,他認為最好處理非信徒的辦法,不是去建立接觸點,而是不用將他們的不信看得太認真。他的經驗也告訴他,當他直接從神的話語出發,聽眾的反應反而更佳。91 這回應不無道理,有時太重視福音的適切性和接觸點,會使我們忘記了福音資訊內在的權能和挑戰性。若福音只是迎合人需要的「消費品」,如何能叫人委身?若福音只是將我們已有的價值和信念用宗教術語包裝一下,又如何能給聽眾一些他本來沒有的東西?所以純粹成全模式在實踐上也是不足的,在美國很多強調適應文化的宗派近年便急劇萎縮。然而我們的處境與巴特的很不同,他身處的本就是基督教文化——這已提供了很多有形無形的接觸點。但基督教在香港和中國的社會與文化都占邊緣位置,所以自然神學的建立有更大適切性,我不是說基督教啟示一定需要自然神學去證明,但若我們如巴特一樣否定基督教與非信徒的接觸點,傳福音的使命和基督教本色化都會加倍困難。當然巴特的洞見也提醒我們要建構一種尊重啟示的自主性的自然神學,這個微妙的平衡需要保持。以布仁爾談到的「絕望」為例,對中國人來說,「罪」是很難理解的概念,若我們能將罪對人生的影響(如空虛、絕望)或對社會的影響(如不公義)說明,也可去除誤解,甚至透過人的絕望體驗等使人更易明白「罪」的概念,但這仍不可取代在十字架底下的痛悔,只有透過後者,我們才能充分明白罪所帶來的絕望。或許今天我們同時需要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的神學。92

注释
作者简介

关启文,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教授。(图片来源:香港浸会大学官网)
往期相关阅读
瞿旭彤 | 比自由神学更自由:试从巴特对神学实事性和科学性的探讨看其神学与自由神学的差异
周小龙 | 神学的任务:圣言或自然?——反思巴特与布鲁纳的“自然神学”争论
关注我们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