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哥廷根教理學》的主體–客體辯證: 宋明儒學與歐陸神哲學批判比較
Subject-Object Dialectic in Karl Barth’s Göttingen Dogmatics: Critical Comparison of Song-Ming Confucianism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of G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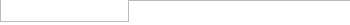
文/曾劭愷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wan/[email protected]
编者按
主客体之辩对于汉语文化及语境下的神学来说,并不陌生,人与“天理”、“道”之关系在儒家语境中的讨论,与近代意识神学对与主客体终极一体性的讨论进路非常相似。然而,如牟宗三先生与费尔巴哈的批判,通过主观主义寻求神学的出路,难免使得神学沦为人类学。“世界是世界,但神是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混淆,某种意义上说是十九世纪主观主义神学形态的失败,而汉语文化及其语境下,“道”、“天理”作为客体的他性被淡化,正与这种主观主义神学形态类似。曾劭愷老师认为,巴特《哥廷根教理学》中,对黑格尔及士来马赫主客体之辩的批判,是对重建神与人之间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尝试,旨在恢复上帝的绝对主体性、以及主体与受造客体间不可磨灭的区别,这对于汉语语境下的神学提供了可能出路。因此,巴特的主客之辩对于探求汉语基督教如何不失本质,以及避免汉语语境下的神学沦为人类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章原载于《汉语基督教文化学术论评》第21期。推送时已获得作者本人授权。在此感谢曾劭愷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摘要:本文旨在探討巴特《哥廷根教理學》(1924-25) 當中主體–客體辯證對漢語神學之意義。此辯證所處理的難題主要源自士萊馬赫及黑格爾所建構的主–客體終極一體性。東亞文化及語境與這種十九世紀主觀主義相似,傾向於淡化「道」、「天理」作為人類主體所認知之客體的他性。誠如費爾巴哈所揭露的,以這種進路所建構的神學,難免淪為人類學。巴特指出基督教神學面對此難題時所須達到的目標,值得漢語神學借鏡:確立上帝在啟示行動中的絕對主體性、祂在此事件中對於信徒作為認知主體的客觀妥實性與可知性,以及祂在此自我施予的事件中自始至終保有的自存性及超越性。
關鍵字: 巴特、哥廷根教理學、主體–客體辯證、近代意識神學、漢語神學
Abstrac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Karl Barth’s subject-object dialectic in The Göttingen Dogmatics (1924–25), whereby he tackles the kind of subject-object identification in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ology to which Hegel and Schleiermacher gave ris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elevance of Barth’s subject-object dialectic to Sino- Christian theology. Akin to the subjectivist theology that Barth challenges, East-Asian philosophy of which Confucian thought lies at the center does not posit in general a dualis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knowing as do Platonic-Cartesian traditions. As Feuerbach’s criticism demonstrates, such subjectivist methods would inevitably entail for Christian theology an anthropological essence. Barth’s proposal of the objectiv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Göttingen Dogmatics for overcoming this dilemma sheds light on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o affirm God’s absolute subjectivity in the act of revelation, God’s true objectivity and knowability to the human subject in this event of divine act, and God’s unchanging aseity and transcendence even in this self-giving event.
Key-words: Barth, The Göttingen Dogmatics, Subject-Object Dialectic,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ology,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 引言
《哥廷根教理學》(Die Göttinger Dogmatik) 在巴特 (Karl Barth) 早期著作中是一部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他於1921–25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擔任改革宗神學教授,此前從未真正接觸過改革宗正統的神學體系,僅於1911年閱讀了加爾文1559年版《基督教要義》。巴特初抵哥廷根時,採信義宗立場的神學系並未讓他主授教理學課程。他的主要職責是介紹改革宗思想,為此他開設了「加爾文神學」(1922)、「慈運理神學」(1922/23)、「改革宗信仰告白」(1923)、「士萊馬赫神學」(1923/24) 等課程。備課時巴特始接觸改革宗正統教理,儘管當時他尚未深入閱讀原典,僅從海勃 (Heinrich Heppe)、史懷哲 (Alexander Schweizer) 等人的二次文獻中窺探改革宗神學的樣貌。

▲A logo owned by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在此期間,巴特所讀到的改革宗神學對他影響甚深,特別是 (一) 關乎聖靈救恩之工的教義、 (二) 改革宗對迦克墩基督論的理解。改革宗正統的聖靈論與基督論為巴特的知識論提供了重要的新進路,以處理啟示的主觀與客觀可能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上帝始終是主動者,而這位絕對主體怎可能成為人類客觀認識的客體,卻不改其絕對主體性?再者,人如何在啟示事件中成為認識神的主體,卻始終是啟示行動的客體?這知識論難題乃《哥廷根教理學》的核心課題。
《哥廷根教理學》原為巴特於1924–25年間在哥廷根初授教理學課程時的講稿,1924–26初版書名為《基督教講義》(Unterricht i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仿效加爾文《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至今多數巴特學者研究這部著作時,都較為強調其濃厚的傳統改革宗色彩,而較少注意其中主體–客體辯證的十九世紀德語神學與哲學背景。
本文第一部份旨在介紹《哥廷根教理學》當中的主-客體辯證。巴特在此處理的難題主要源自士萊馬赫及黑格爾為回應康德對形上學及理性神學的批判而建構的主-客體等同性 (subject-object identification),以及費爾巴哈嚴肅對待此二者時對基督教所作的評論──基督教的本質就是造偶像。本文將指出,巴特在傳統改革宗的基督論與聖靈論中找到了基督教特有的辯證,並用其回應費爾巴哈的挑戰。
本文第二部份旨在探討巴特於哥廷根時期所發展的主-客體辯證對於漢語神學的適切性。主體-客體的辯證對東亞文化雖不陌生,但對許多漢語讀者而言,傳統西方哲學如此強調認知主體與客體的二分,與東亞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在東亞思想中,被認知的客體相對於認知主體而言並不具強烈他性 (otherness)。因此,對一些漢語讀者而言,巴特所處理的課題似乎不是漢語神學需要關切的,甚至有礙基督教融入東亞文化。
然而,巴特所面臨的挑戰已非柏拉圖-笛卡爾傳統的主-客體二元論及相應的知識論,而是在康德之後、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黑格爾 (G. W. F. Hegel) 等十九世紀思想家所帶來的所謂「神學的主體轉向」(theological turn to the subject),而這與東亞文化對主-客體關係的理解非常相似。正如巴特從費爾巴哈的批判中看見,十九世紀意識神學 (consciousness theology) 所論述的上帝對於人類主體而言已非超越的祂者,牟宗三先生亦發現,康德之後的西方哲學與神學所論述的上帝已不必然是基督教所相信的超越者,反而更接近「中國儒家的型態」,即對於人心不具絕對超越性的「理」或「道」。1
如此,巴特當年所面對的挑戰與當代漢語神學的處境其實頗具共通之處:東亞文化及語境傾向於淡化「道」、「天理」作為人類主體所認識之客體的他性,正如十九世紀意識神學或多或少將人類主體與上帝客體劃上等號,而誠如費爾巴哈 所揭露的,這種進路難免令基督教神學淪為人類學。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中或未解決他所看見的難題,但這部著作可貴之處在於指出基督教神學面對此難題所須達到的目標:確立上帝在啟示行動中的絕對主體性、祂在此事件中對於信徒作為認知主體的客觀妥實性與可知性、以及祂在此自我施予的事件中自始至終保有的自存性及超越性。
II. 教理學的課題:上帝話語
自從巴特《哥廷根教理學》於1985 年再版而引發關注,學者對這部著作的討論就主要集中於巴特如何將改革宗聖靈論、預定論,以及改革宗沿襲自迦克墩的非位格-位格內基督論 (anhypostatic-enhypostatic Christology) 納入他的思想,以回應康德對理性神學的批判。2 近年來,另有些學者探討了《哥廷根教理學》如何顯示巴特對改革宗正統的誤解甚或曲解,所關注的仍是巴特在此時期與改革宗正統的關係或糾葛。3 瑪爾嘉 (Amy Marga) 在較新的研究中討論巴特於哥廷根-明斯特(Münster)時期 (1921–30)如何處理羅馬公教所論述的「存有類比」(analogia entis),雖是新穎的課題,但仍專注於巴特與傳統神學的對話。4
學者在研究《哥廷根教理學》時正確地注意到,巴特在此時期所要處理的並非傳統神學所關注的救恩課題,而是近代哲學的知識論。然而,多數學者較專注於巴特如何回應康德,卻較少討論他如何拒斥十九世紀意識神學。
康德以後,士萊馬赫、黑格爾分別從神學及哲學的進路,將人視為認知的主體,探討人對上帝的意識 (Bewußtsein)。因著康德對理性神學的批判,士萊馬赫不再視教理學的研究對象為上帝所啟示的不變真理;黑格爾則將教義劃入「表象」(Vorstellung) 的範疇,以精神(Geist) 之自我疏離及合一的哲學「概念」重新定義「啟示」;高等批判更在文化人(die Gebildeten) 的圈子內使得傳統基督教所理解的「上帝話語」變為難以置信。在這些影響下,十九世紀意識神學規避了「上帝話語」或「啟示」的範疇,試圖以人作為認知主體來闡述人對絕對者或無限者的意識。然而,巴特從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對基督教之本質的批判中看見,十九世紀意識神學難免令基督教淪為偶像崇拜、神學淪為人類學。
如是,《哥廷根教理學》第一章的標題即為「上帝話語作為教理學的課題」(Das Wort Gottes als Problem der Dogmatik),其主要目標之一即確定教理學乃以自我啟示的上帝為主要論述對象,而非教會群體在各歷史時期所表達的宗教情感(士萊馬赫)、絕對精神以教會群體的型態在歷史上自我彰顯的表象(黑格爾)、信仰群體之信心中的上帝(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等。教理學若真能客觀地論述上帝,而非以人的主觀情感、意識、信心等為探究對象及內容,那麼這就預設了神已經啟示祂自己,成為了被人認識的客體:「若教理學能論述上帝……,那麼它無疑必須以上帝親密地轉臉向我們所說的話語為產生 [認識]的基礎,在其上找到最初始、首要、至高的主題,否則信心就是荒謬的。」5
在此,巴特立刻補上一句:「若非如此,那麼它 [教理學] 則或公開或秘密地站在費爾巴哈那一邊,將上帝視為信心的產物,而非視信心為上帝所賜。」6 在某種意義上,費爾巴哈對基督教的挑戰正是巴特在哥廷根-明斯特時期所要解決的難題。巴特在1928年出版的 《神學與教會》中寫道,費爾巴哈並非「只懂得批評與否定的懷疑論者」。7 在波昂 (Bonn) 任教期間 (1930–35),巴特更直言:「正確神學 的起點,正是…… 費爾巴哈的難題被視透且被取笑的那一點。」8
若要明白費爾巴哈所揭露的難題,就必須從士萊馬赫及黑格爾講起。巴特認為,「費爾巴哈的目的很簡單,但很龐大:他要嚴肅對待士萊馬赫與黑格爾,非常嚴肅地對待,就在他們彼此同意的那點上,即上帝的非客觀性」。9 這句話能幫助我們明白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當中以主體-客體之辯證來處理「上帝話語」這課題的背景與用意。
1. 黑格爾

▲Hegel portrait by Schlesinger 1831
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 15(『上帝的可認識性』)當中駁斥德國自由派新敬虔主義「對主體–客體關係的破壞」時提及,「黑格爾早就明白,[因這主體-客體關係的破壞],上帝主體將不再是面向我們的客體,而上帝的自我認知將等同於 [identish mit] 我們自己的認知 [Erkennen]」。10
巴特在此所指的是黑格爾的宗教哲學,本文將於此稍作說明。黑格爾區分「表象」(Vorstellung) 及「概念」(Begriff):表象性的理解僅止於感覺 (Empfindung) 的層面,而概念性的理解則是掌握(begreifen) 某事物的「理」(Rationalität)。在黑格爾的唯心論體系中,精神屬乎理性而非感覺,而既然宗教乃透過感官可感覺到的外在事物將精神呈現(vorstellen) 出來,那麼將人類對絕對精神 (Geist) 的意識提昇至概念層面的職責就屬乎哲學,而非宗教。
在《精神現象學》(1807) 中,黑格爾認為宗教的表象性形式必然造成人與精神間的疏離,基督教亦無可避免。11 然而,1827年的《宗教哲學》講義方為黑格爾成熟時期的宗教哲學,在其中他稱基督教為「終極宗教」(die vollendete Religion),並對宗教的功能有所改觀。在「終極宗教」(此著作第三部份)的標題下,黑格爾一如既往地將他的論述分成三個要素。
第一要素是「『上帝』這概念本身」:「在此我們思考上帝在其自身而言的永恆概念,就彷彿 [sozusagen]是祂在創世以先或世界以外的存有。」12 此處德文「sozusagen」一詞暗示,上帝「在創世以先或世界以外的存有」僅是個擬想。黑格爾一方面不滿於康德對理性的批判所設的限制,一方面又無法否認康德的批判哲學:至少在墮落的階段當中,人的意識主體無法以超越歷史時空的事物為認知客體。
黑格爾在此論及三一上帝的自存性。讀者或許較熟悉《精神現象學》著名的三一論:聖父是精神的本質,即本質之在其自身 (An-sich);聖子是此本質之為其自身 (Für-sich),即本質中的祂性(Anderssein);聖靈是此存有之在其自身與為其自身(An-und-für-sich),即精神在祂性中對自身的認識。聖父永恆自存的本質對人類而言是沒有意義的空洞詞彙,唯有歷史的三一上帝能成為人類意識的客體。在《宗教哲學》中,黑格爾仍用此三一論解釋內在於上帝的對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德文的Objekt 與 Gegenstand 通常皆被譯為『客體』,但後者更強調相對於認知主體而站立的客體,因此經常被譯為『對象』,以與前者區分之),同時又引進了奧古斯丁的思想來論述三位一體 (而非僅聖父)之在其自身:三一上帝在其自身的生命中即擁有對象性,能以自己為愛與認識的客體與對象,此客體性與對象性是自存的。然而,內在於三一上帝的對象性對於墮落的人類意識而言是不可能被認識的,因此,人所論述的三一上帝必須是透過「表象」進入歷史人類意識的自我啟示者(即《精神現象學》所提出的歷史三一)──這過程就是黑格爾所探討的「第二要素」。13
在此「第二要素」中,他解釋了基督教關於墮落及復和的敘事:墮落的敘事呈現精神之神人二性相互疏離的概念,而復和 (Versöhnung)的教義則呈現此疏離之棄存揚升(Aufhebung),14 也就是人類意識達到終極的自我認識,明白神性與人性的終極一體性,因而明白人類對精神的意識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識(換言之,人即精神)。
此復和之過程在基督裡並未完全成就:其普世的實現屬乎聖靈所建立的基督徒群體。這就是黑格爾所探討的「第三要素:群體、聖靈」。15 已得復和的意識 (das versöhnte Bewußtsein) 並非僅以絕對者(上帝)為認知對象。反之,此意識作為意識之主體本身就是絕對的,因為它是精神 (Geist) 的自我意識,是聖靈對精神之在其自身與為其自身(聖父與聖子)的認識。此意識進入並存在於屬靈 (geist-lich) 群體的意識當中。
一開始,精神與人類的復和歷史對於屬靈群體的成員而言「是客觀的,而現在他們必須自己實踐這歷史、這進程」;唯當「那主體自身實踐了這進程」才能「成為精神,因而成為上帝國度的子民」。16 將精神的客觀歷史內化為人類主體自身的意識,主要是由教會的教導與聖禮來達成。儘管教義及聖禮皆是外在的表象而非精神之概念,但教會能藉由教育的薰陶 (Bildung) 將教義所代表的概念內化於信徒的意識,使信徒在聖禮中「有份於神的臨在」──聖禮就是「神的自我感覺」。17 屬靈群體不只促成個別信徒與精神的復和,更將帶來普世的復和,以致實現哲學的至高「原則及真理──屬世者就是屬靈者」。18 換言之,全人類的集體意識終將完全等同於精神的自我意識:人即精神,人的意識與絕對者的意識終極而言乃是一體的。
在此,我們看見,康德對純粹理性的批判宣告了超越者的不可知性,而黑格爾在宗教哲學中建立上帝可知性的進路並非駁斥康德的批判哲學。對黑格爾而言,上帝之在其自身對人類而言是不可知的。然而,黑格爾提出了絕對精神作為被認知的客體與人類意識作為認知主體的一體性,進而提出上帝絕對者對於人類意識的可知性。這就是巴特論及黑格爾時所謂的「上帝的非客觀性」。
2. 士萊馬赫

▲An engraving of Schleiermacher from his early adulthood.
儘管在論述「上帝」時,黑格爾與士萊馬赫有許多爭辯,但在巴特眼中,二人的進路其實不謀而合,奠定了十九世紀意識神學的心理主義 (psychologism) 及歷史主義 (historicism)。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中評論道,正如黑格爾破壞了上帝與人類之間不可磨滅的主體-客體區別,士萊馬赫亦使「我們粗心大意地陷入那我與禰 (das Ich und Du) 相互融合的中立範域。19
士萊馬赫在康德所設的限制下,與黑格爾相似,不以超越的上帝為客觀認識的對象。巴特指出,「根據士萊馬赫,教理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基督教會群體以及某時期被視為有效的教義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就是研究基督徒敬虔感之各種狀態的文字表達的學科」。20
士萊馬赫成熟時期的基督中心論神學進路經常被形容為「從下而來的基論」(Christology from below)。這進路在思維模式上類似於康德的超昇法 (tranzendentale Methode):基督教群體所有成員所共有的宗教經驗乃有目共睹,而這後驗現象之起因的唯一解釋就是,基督必定擁有獨一無二的強大上帝意識 (Gottesbewußtsein)。
士萊馬赫在其教理學鉅著《基督教信仰》(1830) 中提出,教會教義其實並非關乎超越實存者的真理命題,而是「基督徒自我意識」(das christliche Selbstbewußtsein) 的表達,亦即「需要得救贖的感受[Gefühl]」。21 在基督論的標題下(§89),士萊馬赫訴諸教會論,將「救贖」定義為「強大上帝意識的傳遞」,此「嶄新的傳遞」乃透過「基督的出現以及此嶄新群體生命的設立」。22 此救贖乃創造之工的延續及完成:墮落之人及墮落世界壓抑上帝造物時賦予人的上帝意識,而救贖之工則由基督獨特而完美的上帝意識,透過聖靈的影響,重新將此意識傳遞給墮落的人。
雖然士萊馬赫在此一反其早期護教著作《宗教演講錄》(1801),主張教會之外無救恩,但他在《基督教信仰》中並未重新定義《演講錄》所提出的「上帝意識」,甚至不斷重申《演講錄》當中「感受」(Gefühl) 及「直觀」(Anschauung) 的關係。23 士萊馬赫從未明確揚棄他早期的基本立場:每個人的有限意識其實都是無限者之意識的一部份。人類意識對無限者的直觀所帶來的感受(即所謂『上帝意識』)並非以宇宙時空之外的超越上帝為對象;反之,那無限者就在每個人的意識當中。24
不論士萊馬赫晚期神學與《演講錄》有多少出入,毫無疑問地,他晚期的教理學並非以客觀實存的超越者為研究對象,而是教會群體意識的直觀感受。如此,教理學知識的主體以及客體就被劃上了等號:在教理學當中,人乃是以自己的意識為認識的對象,而非客觀實存的上帝。
3. 費爾巴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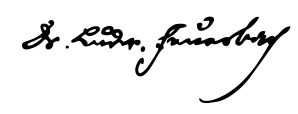
▲Ludwig Feuerbach’s signature
如上所述,巴特在費爾巴哈的批評中看見源自士萊馬赫、黑格爾之近代意識神學的致命傷。儘管黑格爾不斷強調精神的絕對性、客觀性、可知性,他在復和論當中所提出的主-客體之終極一體性讓費爾巴哈找到顛覆黑格爾唯心論的支點,將黑格爾的體系轉化為唯物論:既然宗教意識的主體(人)等於客體與對象(精神,那麼黑格爾「人即精神」一說大可顛倒過來,變成「精神即人」。費爾巴哈如此借力於黑格爾,再採納士萊馬赫早期在有限者及無限者之間所建立的主-客體等同性,於是在《基督教的本質》中斷言,宗教在本質上不外乎人作為主體,將自我意識投射於一個假客體作為對象,這客體並不具真實的對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指相對於主體而站立的被認知對象),而其實是人類自身的主體:「在以無限者為對象的意識當中,意識的主體乃是以他自己天性的無限性為客體。」25
換言之,神與人既是一體的(黑格爾),而人所意識到的神其實是人類的意識當中的神(士萊馬赫),那麼,費爾巴哈的結論就再自然不過了:「宗教,至少基督教,乃是人與自身的關係,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與自身的天性的關係(即他作為主體的天性)……上帝的存有不是別的,正是人的存有,或者說,是純粹化的人性,從人類個體的限制被釋放出來而客體化,以致被當成祂者來默想並崇敬……神性當中所有的屬性……都是人性的屬性。」26 費爾巴哈於是斷言,宗教的本質就是造偶像(人按照自己形象造神),而神學的本質其實是人類學(神學並非以神為研究對象,而是以人性為課題)。
III.巴特的主體-客體辯證:回應十九世紀意識神學
1. 《哥廷根教理學》的核心課題
巴特借重費爾巴哈的洞見,認為近代意識神學終將導致某種主觀主義,否定上帝的客觀實存及可認識性,使得神學淪為費爾巴哈所謂的人類學。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中開門見山地提出,教理學誠然「必須主要在信心的關係上探討神」(誠如意識神學所主張的),但「我們如果不要 [跟隨意識神學] 在第一步就落入費爾巴哈的懷抱,那麼我們在此關係當中就必須將神當作主體」。27
更確切地說,「信心」這事件屬乎上帝的啟示行動,而在這整個事件當中,祂必須始終是行動的主體。在巴特看來,這正是黑格爾及士萊馬赫的心理主義(以人類心理意識當中的『上帝』為上帝)及歷史主義(將教義的歷史或精神的歷史當成上帝的歷史)徹底缺乏的:他們始終將人在直接意義上當成認知事件的主體,磨滅了上帝作為絕對主體以及人作為客體之間的區別。
巴特堅定地否決了近代意識神學的心理主義及歷史主義:真信心乃「心理上的不可能性 (psychologische Unmöglichkeit),正如啟示是歷史上的不可能性 (historische Unmöglichkeit)」。28 這意思是,人類憑有限而墮落的心理,不可能生發對上帝的認識及信心,因為上帝是超越者;同時,上帝既是超越的永恆者,那麼,歷史就不可能將上帝啟示出來。
這就帶來《哥廷根教理學》所要處理的雙向核心難題。人們的確站在上帝的面前,但(一)「上帝如何能夠來到我們這裡,而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且(二)「我們人類如何能夠站在神面前,而我們之為人的存有卻不致改變」?29 這雙向難題帶來了《哥廷根教理學》的核心辯證,即上帝作為主體、上帝成為客體的辯證,以及隨之而來的啟示客觀可能性 (objektive Möglichkeit) 及主觀可能性 (subjektive Möglichkeit)。所謂啟示的客觀可能性,就是神來到世上成為被人認識的客體,而祂作為神之存有卻未曾改變的可能性──祂始終是對人說話的主體;所謂啟示的主觀可能性(人成為主體來認識神的可能性),就是人站在神面前,而其之為人的存有卻從不改變的可能性──人始終是啟示行動的客體。巴特用道成肉身的基督論探討前者,並用改革宗的經世聖靈論 (economic pneumatology) 來處理後者。30
2. 上帝的絕對主體性
正如士萊馬赫及黑格爾皆將「墮落」的教義詮釋為人與神之間的主-客體分裂,對巴特而言,啟示的主觀與客觀可能性難題也是墮落的後果。巴特借用當時在他與高嘉頓 (Friedrich Gogarten) 等人的圈子內頗為流行的我汝哲學 (Ich-Du-Philosophie) 術語,強調原初(墮落前)的神-人關係乃是「我與禰」(Ich-und-Du):在此關係中,上帝既非「祂」,更非「它」,而始終是「我」。31 強調上帝始終是 「我」,即強調上帝作為絕對主體的自存性:「『我即我之所是』 (出三14)……這位主體並不是在給自己下客觀定義,而是再次以祂自己為主體來定義自己。」32 然而,在墮落的世界上,上帝須成為被認識的「禰」,以客體型態自我隱藏,才有可能啟示祂自己:這世界不可能有上帝直接的臨在。
早在1915年,巴特於巴塞爾授課時即強調:「世界仍是世界。但神是神。」33 這句話代表了巴特神學生涯一以貫之的康德批判哲學出發點。34 然而,在《哥廷根教理學》中,「神是神」的神學公理不僅是康德的批判哲學,更借鏡於西方基督教的解經傳統。布許 (Eberhard Busch) 指出,在《哥廷根教理學》中,「『神是神』這宣告正是出埃及記三14當中上帝之名的意譯:『我即我之所是』」。35 在此基礎上,巴特反覆使用「純粹行動」(actus purus) 一詞來形容神在聖靈位格中的行動。36有趣的是,這專有名詞出自多馬主義,而巴特徹底拒斥其自然神學的進路。37 對巴特而言,士萊馬赫、黑格爾、十九世紀意識神學所犯最嚴重亦最基本的錯誤,就是採用自然神學來論述上帝(巴特所謂『自然神學』泛指一切以世界為出發點來論述神的進路),其結果就是以受造者的形象造出假神──這正是費爾巴哈所揭露的。巴特使用多馬主義的術語,是為了凸顯他與自然神學針鋒相對之處,並重新定義 「純粹行動」及出埃及記三14 的上帝之名。多馬主義認為,出埃及記三14 乃是在宣告上帝的純粹實動性 (pure actuality):上帝是完美的,因此祂沒有未實現的潛動性 (potentiality)。世界萬物都仍有潛動性,在被推動的時候某些潛動性就變為實動,唯有上帝是不動的推動者(Unmoved Mover)。
巴特拒斥多馬主義及亞里斯多德「不動的推動者」一說:對巴特而言,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從可見世界的因果及理性的第一原則來推論上帝的存有,須假設上帝與世界之間有本體上的因果連結,而這無異於否定上帝的超越性。巴特認為,這明顯違反了出埃及記三14。他稱聖靈的啟示行動(而非上帝的存有)為「純粹行動」,其實是用自然神學的術語駁斥自然神學,強調這節經文所揭示的上帝主體性:上帝的存有與世界並無因果關係;因果關係乃屬乎外在於上帝存有的啟示行動(Tat)與世界歷史的實動 (Wirklichkeit)之間。上帝始終是純粹行動的主體,就連進入歷史當中的主–客體隱藏性時,仍不改祂之為絕對主體的存有,因此在面向摩西的啟示事件中,祂自稱為「我即我之所是」。
3. 人的墮落:啟示的隱藏性
在此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當巴特用出埃及記三14來解釋「神是神」這神學公理時,他對《羅馬書註釋》第二版的思想作出了修正。《羅馬書註釋》第二版主張,神與世界之間無限本質的差異就意味,在這世界上,人對神的認識始終是不可能的,就算變為可能,仍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unmögliche Möglichkeit)。路許克 (Werner Ruschke) 如此解釋《羅馬書註釋》第二版的「基礎辯證」(Grunddialektik):「我們知道神是那位我們不認識的,是那位我們不可能認識的,因為神是神。」38 在第二版《羅馬書註釋》中,「人類沒有臨近神的可能性」,也不可能獲得對神的知識,因為對於世界而言,神是「絕對祂者」。39 這基本上就是康德批判哲學的立場:上帝若是超越的上帝,就不可能存在於人類直觀認知對象的範圍內。
然而,在《哥廷根教理學》中,人對神的知識已不再被形容為「不可能的可能性」,而是既成的後驗事實:「我們唯有知道啟示的事實,才能嚴肅地提出並討論啟示可能性的難題。根本上,我們只能後驗地 [a posteriori] 建構它。一切關於神如何能夠啟示祂自己的反思,事實上都只能是上帝已經自我啟示的『事後反思』[Nach-Denken]。」40
因此,當巴特用他從出埃及記三14所讀出的上帝絕對主體性來探討啟示的可能性時,布許正確地指出,「神的隱藏性不可與祂的超越性混淆」。41 對於原初受造的人類而言,上帝仍是超越者(巴特在《羅馬書註釋》第二版並未清楚闡明這點,時不時會混淆神的『超越性』及『隱藏性』),而伊甸園中的人卻直接站在那位超越的「我」面前,不需任何隱藏性作為啟示媒介。42 巴特認為,人的墮落在本質上就是將自己當成主體、將上帝當成客體,否定上帝的絕對主體性。
墮落之後,人所能認知的只有這世界以及其歷史上的事物。啟示之可能性的雙重難題即在於此。巴特提出:「當神真的將自己真實地啟示給我們時,這就預設……(一)神與我們相遇,且(二)我們站在神面前。就我們所處理的難題而言,這意味神乃是知識的客體,而我們是主體。神藉由在基督裡成為人,就成為了知識的客體。我們則藉由信心與順服成為知識的主體。」43
在這啟示的「雙重事件」中,神進入「主體-客體關係的隱藏行動」。44 換言之,絕對的主體將自己隱藏於客體性中(道成肉身),並將自己的主體性隱藏於啟示的客體(即受聖靈內在光照的人)中。然而,「隱藏」就是「非啟示」。弔詭的是,這「非啟示」卻正是神的自我啟示;反之亦然,「啟示」即「非啟示」。巴特反覆提及這「令人生畏的等式」:「啟示=非啟示」(Offenbarung=Nicht-Offenbarung)。45
如此,啟示作為非啟示還是真的啟示嗎?在《明斯特教理學》中,巴特用麥考馬克 (Bruce McCormack) 所謂的批判實存辯證神學來回答這問題:啟示真的是啟示,正因它乃非啟示。這辯證的批判實存主義並非哲學性或形而上的,而是對啟示之既存事實 (Tatsache) 的事後反思 (Nach-denken):
“至於一個人或有意或無意地委身於哪種哲學形式,完全不重要;那既存事實的亮光告訴我們,在知識論上皈依某種批判實存主義是完全無意義的──神之為隱藏的神正因祂是自我啟示的神,在祂的神性面前我們無法逃避祂的超越性而進入臨在性,反之亦然。這位上帝從來就不是那麼遙遠,因為祂就在我們身邊,而祂完全在我們身邊,正是因為祂離我們如此遙遠。祂是永遠不能成為客體的那一位,因為祂是神。如此,啟示是否就等於非啟示?46“
換言之,「我們看見、聽到、感受、摸著」的啟示,亦即「我們能夠內在或外在地感知的──那它者、相反的事物、第二個東西、一個客體、一個『我』──它不正是這個『我』(那『我即我之所是』的『我』)嗎」?47 巴特自答:「是的,正是,且始終如此。」48「啟示=非啟示」這等式意味,自我啟示的上帝 (Deus revelatus)與自我隱藏的上帝 (Deus absconditus)乃同一位上帝。49
巴特認為,士萊馬赫、黑格爾以及其後的意識神學在知識論上始終將人視為認知主體性、將上帝視為客體,並藉由這兩者間的終極一體性賦予上帝某種主體性,卻不曾正視上帝從未改變的絕對主體性,更未認清上帝主體與人類客體之間不可磨滅的區別。他們未曾發現,在啟示事件中,上帝始終是主體,因為「啟示=非啟示」。
4. 啟示的客觀與主觀可能性
巴特堅持,上帝主體雖成為受造的客體,但祂作為絕對主體的存有卻未曾改變;上帝主體與人類客體之間有不可磨滅的區別。他在《哥廷根教理學》中解釋:「神從不排除或撤回祂那不能排除也不能撤回的『我』。在祂的啟示當中,祂之為神的存有從未改變。但祂隱藏祂的『我』,以進入一個關係,在這關係當中,我們能夠有份於祂的自我認識,祂可以與我們相遇,我們可以站在祂面前。」50
換言之,道成肉身這自我隱藏的行動就是上帝自我啟示的行動,而這事件就成就了啟示的客觀可能性(神成為人類客觀認識的對象的可能性)。巴特認為,士萊馬赫「從下而來的基督論」僅將歷史的基督當成可知的客體,卻未處理超越的上帝在這客體中的自我隱藏,以致他的基督論正中費爾巴哈下懷,淪為「擬人法」以及「啟示的根本自然主義化」。51
然而,巴特既然不跟隨士萊馬赫發展一套「自然主義化」的基督論,而是接受道成肉身的基督論,那麼,他隨即會碰到下一個難題:墮落之人不可能直接認識神,因此,就連上帝進入歷史而成為知識的客體時,人類主體仍只能認識歷史的基督(成為客體的聖子),卻無法透過上帝的自我隱藏來認識永恆的基督(始終不變的主體)。
如此,啟示的主觀可能性何在?換言之,人怎能成為認識神的主體?而人作為知識主體,怎麼可能認識成為客體的神,並知道這位客體就是不變的絕對主體?巴特的答案已出現於稍早那段引文:惟有上帝真實地認識上帝,而墮落的人唯當「有份於祂的自我認識」時,才可能認識祂。
這概念似乎與黑格爾相近:黑格爾認為,人對精神的認識就是精神的自我認識,因為人即精神。此外,巴特所論述的神之自我認識,似乎更呼應了黑格爾的三一論。如稍早解釋過的,黑格爾提出,三一上帝在其自身的生命中即具有客體性。巴特在《教會教理學》II/1亦提出上帝的「第一客體性」(primäre Gegenständlichkeit),即內在於三位一體的客體性。52
巴特堅持,嚴格而言,只有上帝能認識自己為客體。祂首先在三位一體的關係中被祂自己認識,其次,才在外在於祂存有 (ad extra)的關係中成為被人認識的客體。上帝「第二客體性」(sekundäre Gegenständlichkeit:在祂存有之外成為被認識的客體)的基礎,乃是三一上帝的第一客體性:既然唯有上帝真實地認識上帝,那麼當神藉由道成肉身成為被人認識的客體時,其實是被自我隱藏於人類主體認知當中的聖靈所認識。53 雖然《哥廷根教理學》尚未提出第一、二客體性的術語,但無疑已有此概念:就基督論而言,神成為被人認識的客體,是因神「將祂的『我』隱藏於一個人性的『它』 或『他』」;就聖靈論而言,人能認識神所成為的客體,是因上帝聖靈「將自己隱藏於人類對這客觀實存者的看見、聽到、摸著,以及品嚐」。54
巴特此處與黑格爾的論述固然相似,但有一截然不同之處:黑格爾主張「人即精神」,但巴特強調,進入人裡面的聖靈始終是超越者,永遠不能與人劃上等號──聖靈主體與人類客體之間有不可磨滅的區別。因此,正如巴特使用多馬主義的術語跟多馬主義劃清界線,他也如此顯示自己與黑格爾的差異:「允許我用黑格爾的術語,神是絕對的靈 (Geist),是靈的純粹行動。就連祂作為聖子的靈,在最直接的臨在中,都仍是聖父的靈,遠在天邊。」55 在這句話當中,巴特一舉拒斥了多馬主義(『純粹行動』)及黑格爾的三一論。
5. 神的自我隱藏:啟示的間接性與客觀性
巴特堅持,就連聖靈的啟示行動都同時是神的自我隱藏(否則就會像黑格爾,將人與精神 [Geist] 劃上等號,因而落入費爾巴哈的懷抱)。巴特借用路德十架神學,論到由於神是神、世界是世界、人是罪人,啟示的獨一可能性就在於神的自我隱藏:上帝進入主-客體關係的隱藏性中,以向人啟示祂自己。 此外,巴特訴諸祁克果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指出黑格爾的辯證法將超越的三位一體變成「邏輯與形而上學的三位一體」,忽略了上帝在啟示行動中不變的主體性。56 巴特評論道:
“祁克果所說的太正確了。不論我們怎麼理解,他最深刻的洞見之一就是:主體者即客體者 (das Subjektive ist das Objektive)……。假如我們現在撞見的不是上帝的隱藏性,我們就有禍了!若神的自我隱藏真的是祂的啟示,若我們面前這道障礙同時也是可打開的門,若上帝要使自己被認識,那這就必須藉由上帝對其純粹的神性的隱藏,即祂的虛己……。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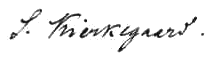
▲A signature of “S. Kierkegaard.”
此處所謂「主體者即客體者」意思是,上帝成為被認知的客體時仍舊是絕對的主體。意識神學在人類主體與上帝客體間試圖建立終極一體性,巴特跟隨祁克果,強調上帝主體與人類客體間有無限本質的差異。在《哥廷根教理學》當中,巴特對祁克果較為肯定,因為從後者的辯證法中,巴特找到了回應十九世紀意識神學的關鍵。他使用祁克果的術語,稱上帝的自我隱藏為啟示的「媒介」,「因著啟示,我們藉由信心所帶來的順服在基督裡知道,它只是一道面紗,是隱匿性[incognito],在其中那神聖的主體、那位『我即我之所是』、永生的上帝隱藏祂自己,並定意要被認識」。58 這就意味人對神的認識就像祁克果所說的,必然是「間接」的。59 同時,巴特強調,這認識雖是間接的──或者說,正因這知識是間接的──它乃是「正確」且「充份」(在知識論的標準上得以稱為知識)的知識。60
康德在第一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聲稱自己「必須藉由否定知識而為信仰存留空間」,61 二分「信仰」與「知識」,否定了神學的科學性之後,黑格爾、士萊馬赫,以及其後立敕爾、哈納克 (Adolf von Harnack)、赫爾曼 (Wilhelm Herrmann) 等人皆訴諸歷史主義及心理主義來重建神學的科學性,但始終無法像加爾文一樣宣告「信心」就是對上帝「堅定而確實的認識」:他們始終未能以上帝為人類知識的客體。
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當中訴諸傳統基督論及聖靈論來回應十九世紀意識神學,雖尚非他最成熟的論述,但至少採取了與意識神學截然不同的出發點,而這也是他後來發展基督中心論的出發點:神是神、世界仍是世界,但上帝已經說話 (Deus dixit),而信徒也已經認識上帝。從這出發點,巴特尖銳地提出,教理學必須確認上帝在啟示行動中的絕對主體性、祂在此事件中對於信徒作為認識主體的真實客觀性與可知性,以及祂在此自我施予的事件中自始至終保有的自存性及超越性,否則神學終將無異於人類學,基督教在本質上終將淪為偶像崇拜,而基督教神學將始終無法向費爾巴哈誇勝。
IV. 漢語神學與主體-客體辯證
在以上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巴特、黑格爾、士萊馬赫、費爾巴哈等德語神學家的知識論與母語息息相關:他們對「主體」與「客體」的分析,反映於德語及歐洲語言在文法上對主詞 (subject) 與述/受詞 (predicate/object) 的清楚二分。費爾巴哈非常清楚地用德語文法的概念來論述人性與神性:「某主體 [Subjekt,亦指文法上的主詞] 之所是, 完全在乎其屬性」,因此「述詞才是真正的主體[詞];而這就證明,既然關乎神的述詞都是人類天性的屬性,那麼這些述詞的主體[詞]其實亦為人類天性」。62 同理,如上所述,巴特在解讀「我即我之所是」 (出三14)時,也用這句話當中的主詞與主格述詞來強調上帝的絕對主體性。費爾巴哈提出,在文法上,主詞總是由述詞定義的。巴特則指出,這種文法關係只適用於受造者,但上帝不能由任何主詞之外的主格述詞來定義,因此,「我即我之所是」這句話的述詞乃是重複了主詞。
這種主詞-述詞的清楚二分,反映成中英教授所謂「西方哲學 …… 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與笛卡爾主義之主體-客體傳統,以及人-神二元論」,這種傳統所導致的知識論,使得西方的分析哲學方法無法直接適用於漢語的哲學文本。63 當代德國哲學家蘭克 (Hans Lenk) 也持此看法,指出漢語哲學的分析研究必須整合「本體論、知識論、語言哲學、文化哲學」等,並認為「對中國傳統之古典哲學文本的深入詳細研究」,可以補足西方「過份強調文法上主詞-受詞之區分對哲學的重要性」的「笛卡爾主義二元論的知識論帝國主義」。64
且不論蘭克對西方知識論的評價是否完全公允,他與成先生及許多研究東亞思想的分析哲學家、詮釋學及本體詮釋學專家都指出了一項幾乎無庸置疑的事實,就是漢語語法在主詞與受/述詞上的關係反映了東亞哲學本體論及知識論對主體與客體的理解:在主流東亞哲學及文化思想上,主體與客體並無柏拉圖-笛卡爾傳統那般清楚的二分。
如此,在東亞思想文化及語境中,巴特《哥廷根教理學》那套主體–客體辯證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呢?遵循東亞思想進路,拒斥所謂「笛卡爾主義二元論的知識論帝國主義」,對於漢語神學而言豈非更有助於將基督教融入東亞文化嗎?
本文指出,巴特對黑格爾及士萊馬赫的批判,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雖然士萊馬赫與黑格爾在哲學語言上仍依賴德文文法當中主詞與受/述詞的區分來論述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但就知識論及本體論的層面而言,他們實已揚棄了成先生所謂「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與笛卡爾主義之主體-客體傳統,以及人-神二元論」。本文已闡述了士萊馬赫與黑格爾之思想所主導的十九世紀意識神學的「主體轉向」,而成先生也指出,近代西方哲學已形成了拒斥柏拉圖-笛卡爾傳統之主-客體二元論的「反潮流」(anti-trend),並舉懷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及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為例。65 眾所週知,懷海德思想與黑格爾非常相似,而詹姆士所論述的神祕主義宗教經驗正是源於士萊馬赫。事實上,士萊馬赫與黑格爾正是成先生筆下這股近代至當代哲學「反潮流」的鼻祖:他們率先在康德對理性神學的批判之下,試圖以宣告人類意識與上帝意識的主-客體之終極一體性突破康德所造成的困境。成先生認為,此「反潮流」(現已儼然成為主流)的知識論是幫助西方人理解「中國人對於『知』的概念」的關鍵。66
換言之,十九世紀意識神學的知識論與東亞文化所理解的「知」,以及二者背後的主-客體終極一元論,皆非常相似。巴特已指出,在這種知識論的進路下,神學將不再以神為研究的對象。換言之,巴特的主-客體辯證對意識神學的挑戰,是漢語神學不可忽視的:漢語神學若採取主流東亞思想的主-客體終極一元論,那麼漢語神學必須嚴肅思考自身如何不致淪為費爾巴哈所謂的人類學。
知識論上的主–客體終極一元論,有時被稱為「主觀主義」或「主體主義」(subjectivism)。當然,以「主觀」一詞形容黑格爾或程朱理學,可能容易造成誤解。黑格爾所論述的精神是絕對的,而宋代理學亦認為,「道」、「天理」乃絕對而客觀,甚至是無限、自存的。 明道宣稱:「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原無少欠,百理具備」(程顥,《遺書》卷二)。
余英時先生論及明道這段借自荀子《天論》67 的論述時,認為「這是說『天理』(即『道』)作為宇宙根源的精神實體,本身是完滿自足的,人的一切作為…… 都對它無所增損……基督教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也是與此……相類似的擬想」。68 然而,二者雖有相似之處,但宋儒所謂的「天理」並非傳統基督教所論述的超越者,甚至不是柏拉圖的「理型」。
牟宗三先生論及同一段出自明道的引文,正確地指出「西方哲學中的實理,如柏拉圖的 idea,乃是由認識論的進路而把握,與儒家的性理自不同」。69 且莫論陸王心學所述之天理,就連宋代理學家亦認為天理與人性皆是一體的。牟先生繼續引用程顥《遺書》:「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裡來」(同上)。70 牟先生指出,這種天道性分相貫通的一元論與黑格爾非常相似:「此理普在於宇宙萬物而為每一物所完具……為什麼一花、一葉、一粒沙能夠表現宇宙?因為天理具有創生萬物而又內在於萬物的遍在性。」71

▲牟宗三先生相
人類之能認知天理,乃因天理非但永恆絕對而客觀自存,更存在於萬物及人之心性當中。這又與黑格爾的觀點相似。牟先生解釋:
“照黑格爾的辯證法,離開聖子講上帝,那個創造萬物的上帝只是上帝的在其自己 (God-in-itself),通過耶穌瞭解的上帝是上帝之對其自己 (God-for-itself)。聖父代表上帝之為客觀性原則,聖子代表上帝之 為主觀性原則。光講道體,那是道體的在其自己,是道體的客觀性意義。沒有這個道體,天地萬物沒有根。72”
然而,「光從客觀方面講道體是空洞的,只是客觀的、形式的話頭」。73 正如黑格爾在《宗教哲學》中強調個人必須在屬靈群體中將客觀精神實踐於歷史進程中,才得以與精神復和、自我認識為精神,牟先生解釋宋儒理學時亦提出,「要瞭解道體的具體而真實意義,在儒家,一定要歸于……從生活的實踐上來證實道體。」74
當然,牟先生並未忽視程頤、程顥、朱熹等人思想上的差異,但此三者確有共通之處。正如在黑格爾的現象學當中,對精神與歷史的本體論述乃是知識論的基礎,在二程理學當中,關於「天理」與「心性」相貫通的一元論亦是「格物致知」的出發點。故伊川:「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程頤,《遺書》卷十九)。
南宋晦庵亦然:「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熹,《大學》傳十之五『釋格物致知』)。
因此,黃俊傑教授指出,「人與自然界的萬物共構成為『一體』」的觀點,並「不僅是王陽明這樣主張」。75 黃先生解釋:「所謂『一體』是指『人』與『自然』是一種有機而非機械的關係,兩者之間是互相滲透的、共生共感的、交互影響的關係。」76 這是「東亞儒家的共識」,宋儒亦認為「『人』與『自然』共構成為不可分割的 『一體』」。77 基於這套本體詮釋學,宋儒提出「格物致知」,而這知識論並非柏拉圖-笛卡爾傳統的知識論所追求的客觀知識,即在主體與客體的清楚二分下,主體對客體的認識。
當然,對主流宋儒而言,「心性」與「外物」仍有區別,而天理相對於心性仍具相當程度的客體性,故須「格物」方能「致知」。然而,到了明代,王陽明龍場頓悟後宣告「心即理也」,「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陽明年譜》,戌辰年,卅七歲)。
王陽明拒斥朱熹的「格物致知」。他解釋道,「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之中,析心與理為二矣」(《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王陽明以「孝親」為例,反駁這套理學:假如「孝之理……在於親之身」而不「在於吾心」,那麼雙親過世後,「吾心」當中就不再有「孝之理」了嗎 (同上)?
在此我們注意到,王陽明的論證乃建立在一套關於「主體」與「客體」的語言分析上。他指出,朱熹二分「親之身」與「吾之心」:「孝之理」作為「吾心」所認知的客體,要不就「在於親之身」而外在於「吾心」之認知主體,要不就內在於「吾心」而與之等同。王陽明進而指出,「吾心」中的「孝之理」明顯不取決於雙親的存亡,因此,「孝之理」就不在「親之身」,而在於「吾心」。如此,「孝之理」作為「吾心」所認知的客體,其實就是「吾心」 這主體。
這套論述過程與費爾巴哈借自士萊馬赫的思想非常相似,結論也頗為雷同。費爾巴哈寫道:「在以無限者為對象的意識當中,意識的主體乃是以他自己天性的無限性為客體。」78 眾所週知,王陽明對儒家思想的詮釋在南宋已有前身,即陸象山的心學。其著名格言是:「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象山全集》,〈雜著〉)。這與士萊馬赫早期「對世界之直觀」(Weltanschauung)79 的思想頗為相似:「宇宙是在內在生命中被勾勒出來的,唯有透過那內在的,那外在的才能被理解」。80 換言之,心靈與宇宙的連結是直接的,而透過心靈對宇宙之直觀所帶來的感受,就是宗教上的敬虔。本文稍早解釋過,雖然士萊馬赫的《基督教信仰》不再使用 《演講錄》當中「宇宙」這類史賓諾沙主義的用語,但這種「心靈即宇宙」的思想所帶來的主觀主義意識神學知識論(以『直觀』與『感受』論述宗教『意識』)仍舊是士萊馬赫晚期神學的方法論主軸,即從客體與主體的終極一體性出發,反思、解釋教會當中的宗教意識(人對上帝的意識以及人的自我意識)。
在以上論述中我們看見,近代意識神學對於主體與客體之終極一體性的理解,與以儒家為主軸的東亞文化非常相似。不論在本體論、知識論、甚或更廣泛的文化思維層面上,兩者的進路皆頗為一致。這種神學進路,正是巴特《哥廷根教理學》主體-客體之辯證的批評對象。
V. 結論
上述始於士萊馬赫及黑格爾的十九世紀意識神學,皆在康德對理性神學的批判下,訴諸主觀主義來尋求神學的出路。牟宗三先生精闢地指出,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陰影下所建構那「無『客觀的妥實性』」的上帝,「是以宗教信仰中的上帝,或由純粹的宗教意識與敬虔來肯認」,而「這樣肯認了……即使是上帝罷,亦不必是基督教那個形態,很可以轉成中國儒家的形態」。81 換言之,牟先生認為,康德之後的十九世紀意識神學更為接近儒家思想,已然失去了基督教之為基督教的本質。
牟先生此處的分析與費爾巴哈不謀而合,而陳昭瑛教授注意到,費爾巴哈批評傳統基督教「對自然、世界、宇宙缺乏美學的直觀」,顯示傳統基督教與儒學思想的一大差異。82 換言之,基督教之為基督教,不同於儒家思想之處即在於基督教不接受「對世界的直觀」能夠成為認識上帝的進路。士萊馬赫將宗教約化為「對世界的直觀」,使得神學在本質上成為人類學,反而更接近儒家的人本思想。漢語神學若採取東亞哲學的主觀主義進路,以對自然、世界、宇宙的直觀來論述神,那麼如何避免投入費爾巴哈的懷抱,值得深思。
較之黑格爾,士萊馬赫更強調人與神之間的直接連結,二者之區別類似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黑格爾在描述人對精神的意識時,漸漸揚棄了「智性直觀」(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康德主義及後來德意志唯心論的術語,乃唯獨上帝才擁有的直觀)的範疇,但士萊馬赫始終將「直觀」作為他神學認識論的主軸。在後來的新更正教神學當中,士萊馬赫「對世界的直觀」一詞更成了普遍用語。
巴特批評道:「首先,我不贊成說 [這些關於創造] 的教義是為了要建立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基督教『對世界的直觀』。『對世界的直觀』的概念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人在特定的觀點下直觀這世界,最終極而至高的可能就是宗教、基督教的觀點。然而,人直觀這世界,但世界就是世界,就是他所直觀到的。這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世界仍是世界,但對於上帝的問題,或者至少對於合論 [Synthese]……對於必然性與偶然性之反論[Gegensätzen des Unbedingten und Bedingten] 的辯證總結 [dialektischen Schlußstein]的問題,仍然是無可避免的。」83
在此巴特一舉否定了黑格爾與士萊馬赫的進路,宣稱他們無法突破康德批判哲學對神學所設的困境。稍早提到,巴特1915年的名言「世界仍是世界,但神是神」一直被他用來表達康德在世界與上帝之間劃下的本體論與知識論鴻溝。在上面這段引文中,巴特指出士萊馬赫「對世界的直觀」的神學進路無法帶來人對上帝的真知識,而黑格爾對於歷史偶然性及精神必然性的辯證論述,亦無法突破「世界仍是世界」的困境。
當然,巴特在《哥廷根教理學》中用聖靈的實動解釋上帝永恆的揀選時,似乎對上帝存有的永恆性及上帝行動的永恆性賦予不同的定義,造成一些神學上的困難,而他在1936年出版的《上帝恩慈的揀選》(Gottes Gnadenwahl) 中,以基督中心揀選論重新詮釋了上帝的永恆行動與存有,用意之一即在於解決這困境(此課題已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在此不詳細說明)。84 在《教會教理學》II/1當中,巴特更提出上帝作為「行動中的存有」的概念,進一步釐清了上帝的存有與行動、永恆性與歷史性的問題。雖然在這些較成熟的著作中,主–客 體辯證的術語已不似在《哥廷根教理學》當中那般顯眼,但巴特始終堅持上帝在啟示行動與事件中的絕對主體性。在《教會教理學》II/2中,巴特提出「基督作為揀選人的神」85的概念,強調基督按神性說乃是揀選行動的主體。在這部以基督中心揀選論探究上帝論的著作中,巴特開宗明義宣告:「上帝論這教義若真的是基督教的教義,就必須…… 使人認識那主體為站在與他者的外在於祂存有 (nach außen)的確切關係中的那一位。這關係當中的客體並非上帝在自己的存有之外的實存性的一部份……上帝並未被迫進入這關係……祂從未在任何意義上受到這位他者的限制或強迫。」86 換言之,聖子藉由道成肉身的揀選行動進入這歷史關係當中而成為被揀選的客體時,其作為上帝之存有的主體性從未改變:基督是揀選人的上帝與被揀選的人,而在此關係中,祂作為揀選人的上帝的主體性始終是首要的。
從《哥廷根教理學》開始,巴特就認定十九世紀意識神學最基本的錯誤之一,即在於混淆了神與人之間的主客體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所謂「神學的主體轉向」是使基督教神學投入費爾巴哈懷抱的罪魁禍首。在《哥廷根教理學》當中,巴特一反意識神學的傳統,重新區分並界定了神與人之間的主-客體辯證關係,強調上帝在一切關係當中的絕對主體性,以及上帝主體與受造客體間不可磨滅的區別。如上所述,這套原則在他後來的神學發展中一直具有主導性的地位。且不論他晚期神學是否成功地突破了近代意識神學的困境並達到他所設的目標,至少他已指出十九世紀神學主觀主義失敗的原因,並為教理學設立了難以辯駁的目標,而這對於漢語神學的未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如本文所述,西方神學若未經歷十九世紀的「主體轉向」,那麼漢語神學或許還能天真地從東亞哲學的主觀主義尋求新進路。然而,巴特的主體-客體辯證已對任何試圖建立主-客體等同性或終極一體性的神學進路提出嚴肅的挑戰,使得漢語神學不得不思考自身語言文字及文化思維上可能遭遇的難題。巴特的神學不一定能為漢語神學提供出路,但他所提出的挑戰,是漢語神學不容忽視的。簡言之,巴特《哥廷根教理學》的主體-客體辯證提醒我們,漢語神學必須思考是否應該並且如何在神學思維及語言上確立神在啟示行動中的絕對主體性、祂在此事件中對於信徒作為認識主體的客觀妥實性與可知性,以及祂在此自我施予的事件中自始至終保有的自存性及超越性。對於漢語神學之為神學、漢語基督教之不失基督教的本質,巴特對意識神學所提出的批判以及他為基督教神學所設的這套目標皆值得借鏡。
(以下内容滑动查看)
注释:
作者简介

▲曾劭恺(英文名:Shao Kai Tseng,又名 Alex),加拿大籍,出生于中国台湾,2017年入选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曾劭恺老师本科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B.S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双主修物理及德文。 大学毕业后转入基督教研究专业,先后获加拿大维真学院(M.Div., Regent College)、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Th.M.,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MSt, DPhil, University of Oxford)。兼任学术期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A&HCI、Scopus等)编辑委员。著有英文专著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VP Academic, 2016)、《牛津手册》系列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专书论文等。
曾劭恺老师主要研究的学科为基督教思想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巴特研究、汉语神学、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研究、黑格尔研究、加尔文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研究、奥古斯丁研究等。
往期文章
曾劭恺 | 巴特的实动本体论:实体与进程的文法
曾劭愷|罪與人性 ——巴特實動主義對奧古斯丁罪論的重新詮釋
瞿旭彤|普遍與特殊:從蒂利希與巴特一九二三年的爭論看兩人神學立場與進路的差異
关注我们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编辑:Kimeikei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