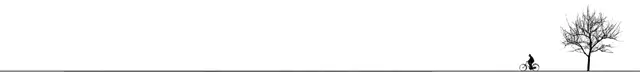上个世纪的中国,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想去哪里,想做什么,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运动”像天气,风云变幻。在1949年到1976年间,尤其密集,据说多达60余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整风整社、“四清”、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几乎把所有乡村社会成员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是领导者,一般农民群众是参与者,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则是斗争对象。一场场的运动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阶级敌人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村庄政治舞台上,充当群众运动的斗争对象、革命偏差的归罪对象和村民怨气的发泄对象。
我爸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就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接踵而至。
不幸的是,他的爷爷是当地的大富农。那位勤劳精明的老人,曾经早睡早起、克勤克俭经营下的马车、院子和水田,成了人民公敌的如山铁证。可怕的是,这运动可以株连,爹黑,儿子黑,孙子也黑,一家子的 “黑五类”。而且,斗争方式粗暴、野蛮、凶残,以伤害肉体、侮辱人格、摧残意志的方式操作着,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由此可见,在我爸本该天真无邪的年龄,邪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明目张胆地登台恣肆宣泄。在可以激情飞扬的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土改运动,摧残了乡村里像我爸的爷爷这样的旧精英;株连的合理化,严酷地训练了像我爸这些旧精英的子孙。
家道中落的感觉,我爸是从六岁有的。作为家里长孙,脖子上挂长命锁是基本配置。似乎一夜之间,所有金的、银的,都被摘去了。他懵懵懂懂看着发生的一切,稀里糊涂搬离了原来的大院,莫名其妙开始了劳作。
干不动重活,就去捡柴火吧。不到十岁,他已经独自进山了。有一次背柴时,因大雪封山,半个月被困在山里。他的腿跑遍了山里能躲人的地方,想找到进山放羊的羊倌儿,讨点吃的,结果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最后他用裤腰带扯成细带,在野兔出没的地方设了套,来猎取食物,烧光了所有拾来换钱的柴禾。等回家后,人生生瘦了好几斤,可过后他还心疼毁了的那捆求生取暖的柴禾。
十一岁时,家里割了韭菜,我爷爷给他做副扁担,让他挑着到县城里去卖,说:学人吧。我爸不到七十斤的小身板,晃晃悠悠地挑起这副过早撂给他的重担——尽管他的腿直打颤。至此,我爸的腿不但要跑山拾柴,还开始怯生生地挑担叫卖了。
贫与寒没有遏制成长的脚步,我爸的腿越来越长;十六七岁的路,虽然泥泞,却越来越远了。
尽管和成人一样劳动挣工分,加上拾柴和偶尔卖点小菜,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饥饿像个影子,时时尾随。于是,我爸决定起早贪黑偷作生意。在那时,这可是资本主义尾巴,每一位贫下中农都要果断铲除的,可饥饿驱使他还是打算铤而走险。于是,他的腿开始了从北到南倒买倒卖的路:把北边的菜和水果,运到百十里外的南边产粮区,换成粮食。
我爸曾经当笑话一样,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卖货时,几位“革命干部”发现了他。他骑车就逃,又遇大雨,路上泥泞不堪。跌跌撞撞中,他的腿不知蹬了多少圈,跑了多远多久。终于看到一个小村子,他慌忙拐进一户人家。车一支好,抬脚跨进门儿,看见炕上刚端上热腾腾的稀粥,他一把端起,说:“大爷,后头有人追我。”说完拿起筷子就吃。
那一家人愣住了,炕上的老人抬头一看我爸自行车上的东西,就明白了,说:“后生,没事,回了自己家了。”几乎是话音刚落,院里就闯进了那几位“革命干部”,“咣”一脚踹开了门,气势汹汹走到我爸面前。
老人喊到:“嘿!干甚了你们这是?”
“抓他这个小贩子!割资本主义尾巴!”
“甚?他是我外甥,给我送东西的,刚进门咋就成了小贩子了?”
我爸接茬就说:“闹了半天,你们是追我呢,我还以为你们也是跟我一样雨急赶路的。”
“革命干部”狐疑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屋里的人。大娘说:“哎,外甥还有假?年年他给我们送。”
就这样,他有惊无险躲过了那次追捕。
那条泥泞的路上,他那没命狂蹬自行车的腿,可以听到这个青年人心里的慌乱、惊恐和抗争。
我哥出生后,我爸考虑再三,认为囿在农村,连吃都是问题,做小买卖只有在农闲时才行,还得偷着藏着。所以,他决定出去干活。那时,“黑五类”“狗崽子”的身份照旧,哪有什么可选择的机会,只有去最危险的地方的资格——小煤窑。根正苗红的人,根本不会去受那份罪。那里有相对可观的工资和可怕的危险,没有外面激烈的阶级斗争,大家都是“黑五类”,都是一群苦人,同病相怜,没有人格尊严的欺凌。
一切都是最原始的采矿方式,作业条件低劣,安全没有保障。坑道只有一米多一点,我爸说他只能半猫着腰,蜷曲着腿,在坑道里爬,还要拖着一百七八十斤的煤。超负荷的劳作,险象环生的处境,是最直接与他们相伴的。
其间,瓦斯爆炸,矿井塌方……我爸目睹了二百多工友的伤残、死亡……历经多次危险,除了触目惊心,更多的是凄凉和无奈!
几年后,我爸觉得他再也不能去井下挑煤了,他想掌握一门技术。为了这个朴素的愿望,歇工时,他就凑到电焊师傅的身旁,看人家操作。师傅忙时,他就上去搭把手。师傅们高兴有人帮忙,也乐意指点他。他也机灵肯学,很快上手。
而立之年的我爸,虽然还在小煤窑,但已经不用下井。他的腿,支撑起了一个有技术的人。
在这个煤窑的十四年间,我的父母用他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盖起气派的大正房。

等我爸决定离开煤窑,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改革开放的风劲正猛。回村后,我爸除了盖房,也开始了他的自主创业路。租了大队的一间闲置房,开了他的机械作坊。每天进进出出、弯腰撅腚地忙着,粗声大气地吼着,和上门的顾客笑骂着……遇到合适的机会,还会抽冷子买进卖出做点生意。手艺加生意,我爸忙得紧。
只是遇到阴雨天,他的腿会提醒他:要变天了。他开始给这双辛劳多年的腿贴上膏药,用热水泡一下疲惫奔波的脚,和我们说说往事,吹吹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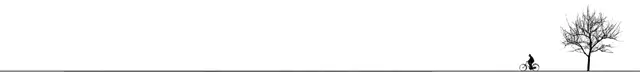
一晃多年,如今我爸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当年走路“咚咚咚”的铿锵跫音,不知什么时候萎了。今年,他又病了一场,住院近一个月才返家。疫情严峻,我无法到医院照顾,直到爸爸出院回家后,才回乡侍亲。一场大病,我爸被折腾得动作迟缓了,语言寡少了。但没有一般老人的那种忧虑负重,尽管三餐尚且食之无味,他仍然尽本分吃饭,也戒了烟酒,还积极锻炼,保持平静情绪和乐观态度。
每天晚上,我会服侍他洗脸洗脚。打来一盆热热的水,投毛巾进去,不要拧太干,就着热乎乎的水汽,给他擦脸。我爸抿着嘴,闭着眼,左右偏着配合我,还舒服地长吁着气。
待给他洗脚时,他会自己把裤腿挽高,伸脚进去泡上,还希望水再热些。我就在旁边一边续着热水,一边和他说着家常,话题起头五花八门,最终都会回到“峥嵘岁月”:那一次的艰难,那一天的不易,那一个人的恩情,那一个领导的赏识,那一回的危险……
泡着好一会儿了,我会说:爸,咱洗吧。我蹲下去,撩着水,给我爸洗脚踝,洗小腿。已经衰老的皮肤,裹着这一双腿,这一双从稚嫩走来、诉说着艰难的腿,这一双从泥泞走来、诉说着倔强的腿,这一双从黑暗走来、诉说着努力的腿,这一双从自主走来、诉说着乐观的腿,所诉说着的无形财产,实在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