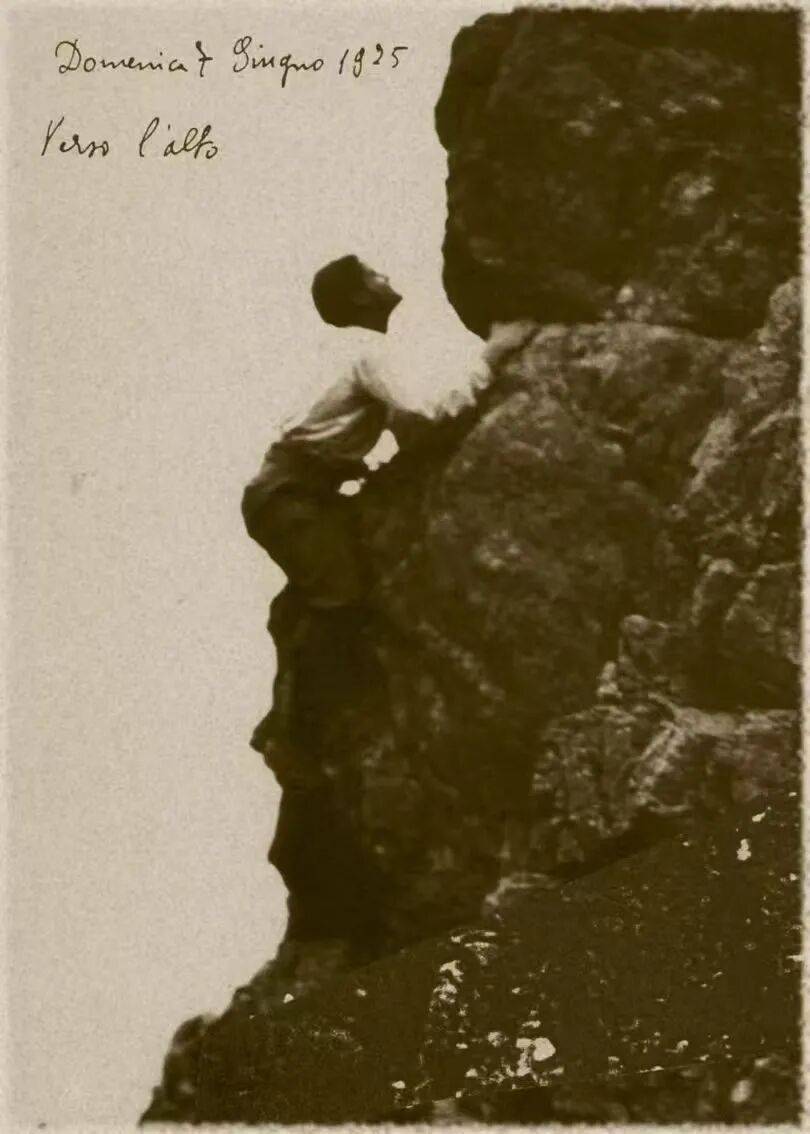
有一种人,叫衔命者。
他深知自己的天命,他衔着天命而来。他的天命就是求道、研道、传道、行道,他必尽心、尽力、尽意地完成自己的天命。凡天命以外之事,他不追求;凡因行天命遭遇的一切,他平静面对。
他认识天,也认识人。
认识天就是认识至高者。认识至高者既需要饥渴慕义的心,又需要至高者的浇灌——根本上是依靠至高者的浇灌。认识至高者依靠信,它是超越理性的,是必须体验的,但却是真实的。
认识人就是认识人性,认识人性在世界中的表现。认识人性,既需要理性,也需要体验;既需要读书,也需要做事;既需要外观,也需要内省。
由是之故,衔命者必须打通超验与经验,必须学会对症下药。
他必然面临无数没有现成答案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就存在人们心中,却是模模糊糊的,他只是把它们清晰地说了出来。他既是这些问题的提出者,又是这些问题的思考者,还是这些问题的解答者。
衔命者只崇拜至高者,而不崇拜任何人,讨好任何人。他将平视一切人,无论他是君王、富翁、明星、学问家,还是老百姓——他知道,老百姓并不比贪官高尚。他相信,凡不以至高者为唯一崇拜对象的,必崇拜形形色色的偶像,无论这偶像是肉眼能看见的存在,还是看不见的观念。
衔命者向人群走了过来。那些人,目光空洞呆滞,只有聚在一起抱怨时,才像个活物。他们叽叽喳喳,唉声叹气,活像一群秋后的蚂蚱。
“你们活得还像个人吗?”衔命者有些不客气地问道。
“他骂我们不是人,揍他!”甲号召道。
众人对衔命者怒目而视,恨不得吃了他。有人已经在挽袖子了。
“既然活得真有个人样,还抱怨什么呢?”衔命者反问。
众人没想到他会这么反问,倒有些泄气了,一时竟面面相觑起来。
“没人样又怎样?谁都没办法!”乙说。
“对,没办法。”众人附和。
“真没办法吗?”衔命者反问。
“认真说,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我们可以跑。”丙说。
“往哪里跑?天下乌鸦一般黑。”丁说。
“那倒也不是。我的朋友,已经跑出去不少了,他们都在劝我跑。”丙说。
“你有钱,可以跑,我们怎么跑?孟夫子不是说过吗:‘贫贱不能移’,哈哈。”丁说。
“嗨,哪里活不是活,凑合活着得了,想精想怪的,有毛用?!”戊说。
“不,不能这么说。我们先得把道理讲明白了,人生来就应该是自由的。康德不是说吗:‘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一个戴着圆框眼镜,面皮粉嫩,嘴唇很薄,书生模样的人挥舞着双臂,站在一个土台上,身边放着几本自己写的书。他自备了话筒,紧紧地攥住它,正准备发表一场演讲。
“打住。百无一用是书生,说那些空话有毬用?康德话说得漂亮,在国王面前不也装孙子吗?别想启蒙我,谁都不比谁傻。要说应该,我该回家做饭了。”戊说。
众人兴味骤减,都想散去了。书生讪讪,一时语塞。
“真就没希望了吗?”衔命者幽幽地发问。
“没有。”众人齐声答道。
“不!”衔命者斩钉截铁,故意拉高了声音。
“希望在哪里?”众人不屑地问。
“希望在我,在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之间的爱。”衔命者看众人茫然,补充道:“有爱,就有希望。爱,是世间最大的力量,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傻逼!”一个人骂道。
“傻逼!”众人齐声骂道。
“爱,就是光。至高者就是爱,就是光。光照进来,黑暗就会消失。相信爱的人多起来,光就会多起来。相信相信的力量,就能看见看不见的未来。”衔命者继续说。
“傻逼!”众人齐声骂道。
“朋友,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说完这句话,衔命者面带微笑,离开了众人。
“傻逼!”众人齐声骂道。
衔命者理解别人的误解、嘲笑,甚至攻击。因为,这就是人。他深知人无法改变人,改变人的,是至高者的大能。他不会把任何人的改变归功于自己,不会相信说服和辩论的力量,因为说服和辩论依靠的只是理性,而智慧超越理性、高于理性。
他跪倒在至高者的脚下,求他原谅他们:“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晓得。”他求他开启他们的心,擦亮他们的眼,赐给他们勇气。
他走向另一个人群,继续他的提问、反问、宣讲,接受他们的误解、嘲笑、攻击。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如是数年……
然而,竟然渐渐有人开始同情他了。
“你孤独吗?”有人问。
“不,我高兴得很,因为至高者与我同在。”他笑了,他知道一颗爱心已经被唤醒了。
渐渐有人开始佩服他了。
“你是个战士!”有人说。
“不,我只是个人。我只希望活成一个人,只希望大家都活成真正的人。”他说。
渐渐有人开始愿意听他讲,因为他们不仅听他说了什么,也看他做了些什么——他帮助人的故事渐渐流传开来了。
“什么叫一个真正的人?”有人问。
“就是恢复到被造时那样子,就是拥有至高者形象的样子。”他答。
渐渐有人相信他说的话了。在他身边,有了一群朋友,从三五个到几十上百个,再到成千上万个。他们团结在一起,成了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热烈地交流,同歌同哭,分工协作,相互造就。
他们都成了新的衔命者。
衔命者心中有大欢喜。他想,自己可以向至高者交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