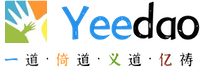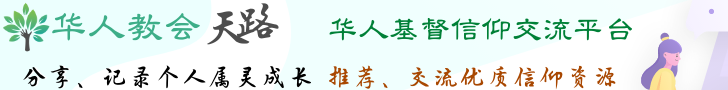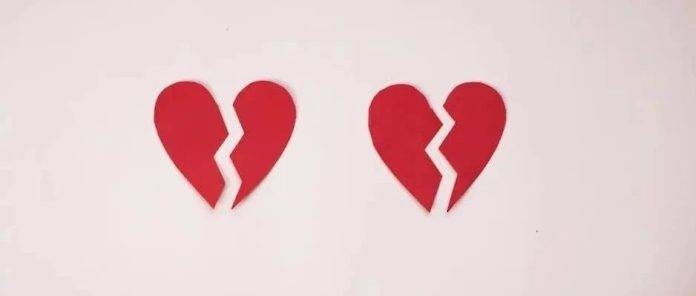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都会认真对待。以下我统一回复常见的几种反驳:
首先,我必须承认,上文的部分用语可能不太严谨,引起了大家的误解。比如,我用「受害者」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刑事案件。
比如,文章发布不久,就有读者质疑:如果你身边的人被性侵了,你还要强迫她饶恕对方?
这里作个清楚的声明: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报警。
当然,如果你非要找一些极端案例来反驳,我只能哑口无言。但我会认为这种反驳偏离了重点。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并且摆出一副长者的面孔,劝诫我:「一看你就没受过多大的伤害,你看看我所受过的伤……你这些话简直轻飘飘……」
首先,我必须向这位长者承认:我确实「图样图森破,有时拿衣服」(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但我不希望这场讨论最终变成「谁敢比我惨」的擂台赛。
而且,这种观点假设了一种荒唐的要求:如果你没有遭受跟他人同等的伤害,就没有资格劝勉他。
对此,我只能无奈地回答:「那位上了十架的人是这么劝的,我想他的资格是够的。」
其实我还想补充一句:那位的态度可比我严厉多了,因为他明确称呼那些不饶恕的人是「恶奴才」(太18:32)。
其他的反驳大同小异,总结起来就是:你跟他聊观点,他跟你聊态度。
也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对「施害者」的劝勉。我回答:「施害者的恶是明显的,人人得而诛之;受害者的恶是隐藏的,不易察觉,也更危险。」
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你独处的时候,要警醒自己的恶;你在群体中的时候,要警醒自己的善。」
正义感是个好东西,因为这表明我们在乎善恶是非;但我们也不得不警醒:很多暴行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作出的。
在上篇推文中,我说:在伤害发生时,受害者会面临更大的试探,因为他们天然地站在「正义」的一方。正是这一点让我担忧。
今天这篇推文仍然不是要劝勉「施害者」,而是「旁观者」。你也许会奇怪:当伤害发生时,旁观者会有什么试探呢?他又不是犯罪的那一方,他也不在这场恩怨之中。
旁观者所面临的试探与受害者紧密相关。上文提到,人在受到伤害后,会本能寻求宣泄,他会到处找不相干的人倾诉。这个时候,旁观者就被牵涉进来了。
设想一种场景:你的好朋友在教会中受到一位弟兄的伤害。她没有按照主的吩咐与当事人单独沟通,而是找到了你,因为你是她最信任的人。她声泪俱下地向你倾诉那位弟兄的种种不是。对此,你会怎么回应呢?
劝她想开点,饶恕那位弟兄?受害者在情绪当中当然不会吃你这一套。她也许会搬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样的醒世格言,让你哑口无言。
跟她一起背后骂那位弟兄?但如此,你也开始怨恨那位弟兄了,至少你会对他产生成见,尽管他并从未伤害过你。
结果是:不管你是想做个「和事佬」,还是想做「铁杆闺蜜」,都不合适。因为,你正处在试探当中。
我们都遇到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判断事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但是,在这种情形中,哪怕你竭尽全力保持公正,你的回答都是错的。
其实,不是你的回答错了,而是你的身份错了,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这个时候,唯一正确的回应是:在受害者向你倾诉时打断她,劝说她找当事人单独沟通。你要跟她强调:「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我无权评判。而且,你跟我说这些,让我也陷入试探之中了。」
作为旁观者,如果你不在一开始就制止这种行为,那么后果会很严重;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后果只会更加严重。再一次,正义感会让我们深陷试探。
也许一开始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苦毒会在人心里不断酝酿,带来肢体间的不信任和隔阂。而且,这种隐恶不会停留在个人心中,而是会扩散到整个教会共同体。
我认为,教会中很多的结党和纷争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结党纷争了。
一开始我只是怨恨伤害我的那个人,后来我开始怨恨那些帮「那个人」说话的人,后来我甚至会怨恨那些谁都不帮的「和事佬」。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通过找旁观者倾诉,我成功地聚集了一批与自己「同病相怜、休戚与共」的战友。
P.S. 我实在觉得,这一类的话题写成《魔鬼家书》的那种形式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