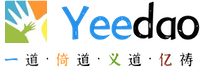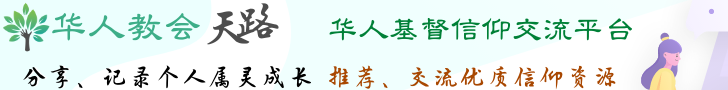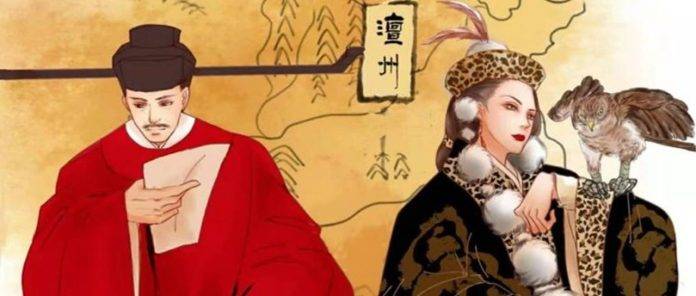本文选自“暮云漫谈上下五千年”第三季第十一课讲义。第三季课程已经上线,目前正在优惠中,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可以获取:

也可一次性获取全三季120讲课程(及先导课《秩序论》):

真宗赵恒即位,宋朝的皇位传承终于正常化。赵二赵光义北望的雄心与不甘,从他的政治布局可以看出一二,比如拔擢他以为偏鹰的寇准给儿子用:
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太宗曰“此官岂所以待准者耶?”,宰相请用为枢密院直学士、太宗沉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二年(989年)七月,擢虞部司郎中(阶官,从五品上)、枢密院直学士(职,正三品)、赐金紫、判吏部东铨。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但貌似鹰派的寇准,其真实想法或许更类似《三体》里的章北海。
他一生中的最高光时刻当然是澶渊之盟。那是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大举伐宋。
宋辽纷争的底层原因是天意和地理,中层原因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表层原因,第一,是赵二灭晋阳,而北汉与辽有约(侄皇帝不是白叫的),辽汉安保条约被触发。第二,赵二还想光复燕云十六州。他虽然武功不行,有生之年却也强行好几次北伐。高梁河那一次给他狂的不行——直到膝盖中了一箭。急火攻心的他随后还有意无意激死了侄儿。
后来得雍熙北伐(986年),理由更是莫名其妙。
几年前辽景宗去世,十二岁的辽圣宗登基,年仅30岁、著名的萧燕燕太后主政。《杨家将》里的萧太后就是这位。萧燕燕大名萧绰,自小聪明伶俐,美艳绝伦。嫁给景宗为后之后,皇帝身体不好,所以很早燕燕就已经开始治国理政。
但皇帝哪怕只有一口气,就有震慑作用。这一死,形势剧变。因为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早年遇害,无嗣,所以她没有外戚可以依靠。于是诸藩王重臣虎视眈眈,孤儿寡母岌岌可危。孤立无援的燕燕只能全力依靠并提拔汉臣韩德让。
据宋人史料记载,萧绰幼时曾许配给韩德让,未履行婚约就嫁给景宗。景宗死后,萧绰决定改嫁韩德让。而当时契丹的风俗也允许如此。她私下对韩德让说:“吾常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契丹>,据江少虞的记载,这些内容是路振于宋真宗时出使辽朝所得知的)。后萧绰派人秘密毒杀韩德让的妻子李氏。韩德让则无所顾忌的出入宫闱,出猎听政,两人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并排而坐,晚上则睡在一个帐篷里。圣宗对韩德让也以父事之。
但这些宋人野史的说法可能是企图丑化辽国皇太后,以达到毁坏其名声的目的。萧韩恋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类似文明太后与李冲(参第二季第24讲:《参合鲜卑》)。
总之,边关的雄州知州儒家好学生贺令图认为机会来了。第一,母仪天下之人公然有情人,成何体统!第二,这个光景似曾相识啊,权力交接,孤儿寡母,大乱将生,这不就是我们郭威、赵大两次黄袍加身的节奏?
于是贺令图上书赵二,要求北伐。所以以己度人的极品就是这一位了。赵二以他的见识,不出所料地大喜过望,发动了雍熙北伐。
殊不知,萧韩恋在蛮族那里根本就不是事儿。反倒这两位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强强联手。萧太后治国有方,赏罚分明,一方面笼络群臣,大家都加官进爵,另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大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她改变以前的种族歧视政策,对契丹人和汉人一视同仁,赢得汉人拥戴。韩德让也是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的全才。所以短短一两年,他俩就联袂稳定了辽国局势。
于是自以为得计的赵二这次倒了大霉。雍熙北伐惨败,杨业就死在这一次战争中。
到了景德元年,萧太后50岁了,辽国国力空前强大,她就旧恨新仇一起算,大举南征,给出的理由是当年默认的边界被柴荣夺去一块关南地,需要宋朝归还。
辽军所至,望风披靡,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很快就打到了汴京附近的澶州,又叫澶渊。
消息传来,真宗几乎崩溃。两个重臣王钦若、陈尧叟揣摩上意,趁机进言南迁。只不过两人一个认为应该迁都南京,一个认为应该迁都成都——两个地方分别是他俩的老家。所以书生那点儿心思,你想去吧。
只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要求迎击,公开说,谁再妄言,斩!同时要求皇帝御驾亲征。最后,真宗如同被绑架到了前线。他每天心惊肉跳,但听说宰相夜夜笙歌,宠辱不惊,皇帝才稍微安定。
其实寇准心里当然知道,远比本朝强大的赵大赵二年间都搞不定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猛的辽国,自己又怎么能打得过。但他深知以战求和的道理。之所以绑架皇帝一起来,就是让他背锅的,因为如果是自己带兵出征,然后议和,一定会被一贯“赢就一起狂,输了你来扛”的王钦若们骂为卖国贼。但如果是在皇帝主持下议和,大家就没话说,不至于像后世的李鸿章替慈禧背上骂名。
结果sd真的帮他,要把给挪亚时代的应许也给契丹和宋朝人民(“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此时辽国国号改为了契丹,这也是辽国最强的时候,以至于直到今日诸斯拉夫民族还称中国为契丹。但后来汉化久了,契丹又改回了辽朝,很快亡国。
契丹司令官萧挞览过于嘚瑟,在城下骑马奔跑骂阵,结果成了东亚歌利亚,被宋军用弩爆头(也有说是中了流箭),当晚去世。契丹士气大跌。
进退维谷的萧燕燕无奈之下,听说之前投降的宋将王继忠是真宗发小,就把他招来问策。王继忠虽然已在契丹定居,位高爵尊,但仍心念故国。近年战争中两方百姓生灵涂炭的惨状也深深刺激了他。于是他抓住机会,劝萧太后议和。
他告诉萧燕燕,契丹和宋一直彼此为仇,动不动就兵戈相见,结果导致两国都民不聊生,实在没什么好处。这样下去,两败俱伤。相反,如果两国肯罢兵议和,重修旧好,结为盟友,让百姓休养生息,双方都会从中获利,共同繁荣。
其实连年战争带来的财力、物力、人力消耗,萧太后和圣宗都看得十分清楚。现在听到王继忠的话,两人觉得议和的确很有必要。
寇准听说萧太后有意议和,正中下怀,决定利用现在军事上稍占优势的机会,促成和约。
于是他派曹利用为使者到契丹阵地议和。这次交涉的焦点是议和条约中宋朝每年应该向契丹提供多少财物。无论如何想回避战争的真宗对曹利用说:“只要能议和,一百万都行。”但是寇准叫住刚出门的曹利用吓唬道:“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算寇准没白吓唬,曹利用还真交涉成三十万。
曹利用回朝复命,真宗急切地让宦官问到底是多少。曹利用知道事情重大,要面奏皇帝,所以就对宦官只举了三个手指。没想到这笨宦官进去就给真宗上奏道:“举了三个手指,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大叫:“太贵了!”在外边等候接见的曹利用只听到真宗喊叫,所以吓得浑身发抖,满头冷汗,进去就给真宗磕头:“臣下无能,吃下大亏。”
真宗问:“到底是多少?”
“三十万。”曹利用跪在地上,浑身哆嗦。他当然没想到真宗对此回答喜出望外,下令重赏。
于是,契丹撤兵,两军合计几十万人的武力冲突被和平解决。两国首脑都具有通过交涉解决武力冲突的智慧和撤兵回朝的勇气。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使人和睦的有福了”。萧韩赵寇王等人都有政治家的智慧和度量,是和平之子,知道“妥协的艺术”。他们都不忍心因战争使民众受苦。这比能征善战更伟大。

就像旧约族长时代的以撒不若他的父亲和儿子有名有力,可他是和平之子,所以并不愧对圣约受约人身份。
经上记着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祂就赐福给他。(创廿六12)。以撒的丰收就是祂所赐的福。“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他们把以撒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填塞了。以撒为求和睦就离开那个地方,搬迁到基拉耳东南方的山上。以撒重新挖掘过去被亚伯拉罕挖掘但填塞的井,并且仍用他父亲所取的名来命名。
可是以撒的仆人挖了一个活水井后,非利士人又说这井是他们的。所以这井被称为埃色,意思就是说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宽怀大度,不争竞,就放弃了这口最有价值的活水井。他又重新挖井,但非利士人又来为井争竞。以撒给这第三口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
后来“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廿六22上)以撒给这井取名叫利河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雅巍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廿六22下)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作别是巴,直到今日。”(廿六32-33)
进化论和黑暗森林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必须恶性竞争。但以撒说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我们所有人。他的心胸和他居住的地方一样宽阔。
一千年前的东亚也足够大,可以同时容得下契丹和汉人。他们正确认识到了这一点。“澶”是“静水深流”的意思,所以在属灵意义上,澶渊好像别是巴,都是盟约之水(井)。被称作澶渊之盟的宋辽和约,直到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被撕毁为止,双方遵守了一百二十年。
宋朝方面最大的功臣当然是寇准。如果真宗到南方避难,那么宋朝会早一百二十年失去华北,因为宋朝在战场上获胜的可能微乎其微。寇准既回避了战争,还保全了国土,这需要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每年的无偿经济援助,防止了契丹对宋朝的侵略,性价比很高。
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是:
-
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
-
宋辽两国互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辽圣宗称李太后为伯母,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
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盟约缔结后,第二年,宋朝派人去辽朝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
后来王安石写过一首诗《澶州》赞美寇准: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
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
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
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之后一百二十年,宋辽休战,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不仅如此,岁币促进了贸易,契丹拿的钱大部分还是要用来买宋朝的货物,比如景德镇瓷器。从此中原产品在辽境大受欢迎,包括文化商品,于是契丹逐渐汉化为辽朝。
真宗继位当年光是钱币收入即达2,200万以上,另外布匹、粮食的收入还不计在内。国家和平发展经济就足以支付。那时,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约十万人左右),即需300万,就算没有战争,只是重兵防备一年的开支,也十分惊人。所以这笔经济账一算,30万哪里贵了!宋朝很划得来。
但后来的王安石(即便他赞美寇准)和富弼等人认为澶渊之盟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政府“忘战去兵”,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并且发展多年,非但没有收回燕云之地且每年还得给辽朝大量岁币是耻辱。
事实上这些泛鹰派,都生在澶渊之盟缔结后,他们未曾亲历战争的残酷,路径锁定的他们就开始用意识形态绑架朝野,愈演愈烈,终于间接、直接酿成靖康耻。
二战结束后,世界至今已有将近八十年的和平。这和平,能坚持到一百二十年吗?
和平之子寇准三度拜相又三度被贬,最终客死广东。寇准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一语成谶,他最后死在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远离家乡万里。
萧太后和韩德让则都享尽荣华,高寿而亡,死后也没有任何人清算诋毁他们。辽圣宗耶律隆绪20年后(1023年)建了一座佛塔,这是中国最北的一座塔,就在长春市农安县。不过他最大的功绩是救了千万人,而不是造了七级浮屠。
金庸写过的最大英雄是萧太后一支的萧峰,萧峰一生的最高光时刻并非聚贤庄或少林寺,而是雁门关,他用生命促成辽宋和平,完成了和平之子的使命。
和平之子如以撒、寇准等人,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出必要的妥协。
实际上,物质、利益和肉身的事,都是可以妥协和让步的,六尺巷显明邻舍之爱比建筑面积重要,主让彼得从鱼口得银交税显明邻里和睦比凡事较劲重要。
然而灵魂和信仰的事,是半步不能让的,因为灵魂高贵而脆弱,一旦破坏,人将失格。所以禁令之下,但以理依然开着窗户,一日三次跪祷,与素常一样(但六10)。
介乎两者之间的精神和良心层面,则很可能个人带领不同,而且sd也允许这不同。罗翔老师谈过为当事人辩护时,认罪减刑和坚持无罪之间的权衡,出于妥协,他会劝人选择认罪减刑,但若当事人坚持无罪,他也愿陪伴到底。十年浩劫时有长老被发配青海劳改,领导敬他,派他看管花生种子库。饥荒时代,这等于默许他可以不笼住嘴。但他的良心尺度是不可吃,最后也赢得了美好见证。
而耶利米遵守和西底家王的约定,不向他人谈及两人密会的全部细节(耶卅八),并不能算是说谎。虽然有些人的良心可能不允许他向任何人隐瞒任何事实。
良心自由就是在这个层面。因为真正的良心自由如彩虹之约一般,是个谱系。
所以妥协的尺度在哪里?分三个层面,就像那部电影《Eat, Pray, Love》的名字,要分物质、灵魂、精神三种情况:物质可以谈,灵魂没商量,自由看情况。
在此原则指导下,愿和平之君怜悯众生,在诸领域都赐下和平之子,能有寇准和萧燕燕一样的见识和仁爱。

或直接获取全三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