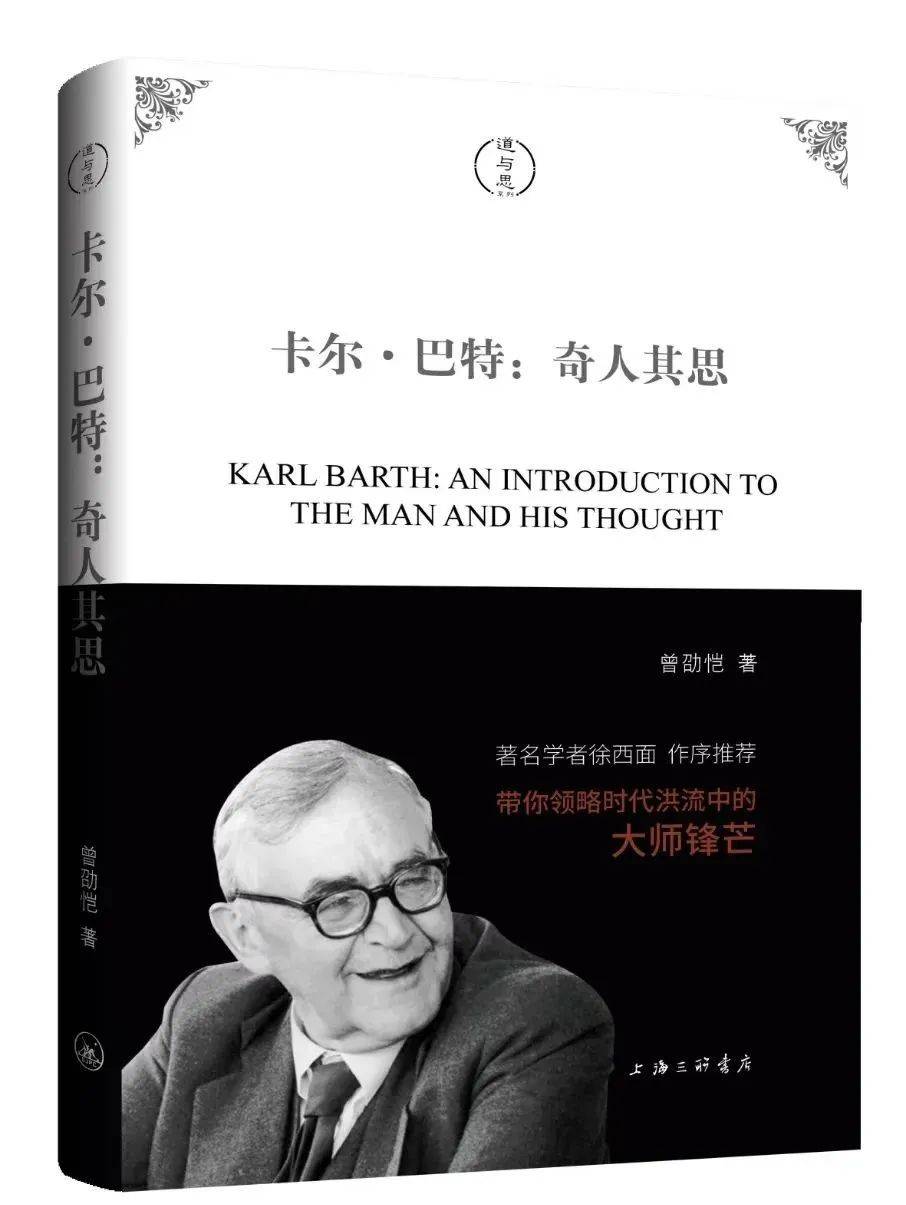译者前言:本章选自著名改革宗浸信会神学家迈克尔·里维斯(Michael Reeves)的导论性论著《你该认识的神学家:从使徒教父到21世纪》(Theologians You Should Know – An Introduction: From the Apostolic Fathers to the 21st Century)。里维斯老师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系统神学博士,执笔了不少针对平信徒的基础教育书籍,中译本中有脍炙人口的《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
本章讨论了广受争议的神学家卡尔·巴特。里维斯老师一方面为普通受众考虑,尽量简化了巴特的德国观念论背景,方便在哲学上涉猎不深的读者阅读;另一方面,他尽量根据巴特自身著作凸显巴特思想全貌,而非囿于一些二手文献论述(但里维斯也依然涉猎了不少巴特领域的研究专家,比如麦科马克[Bruce McCormack]、天主教著名神学家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等。甚至里维斯乐于从巴特原著阅读巴特,本身就有杭星格[George Hunsinger]“拒绝过度诠释的框架,回到巴特文本原原本本读巴特”的理念在背后)。里维斯也同样提到,给巴特贴上常见的“新正统”等标签,总体是误导人的;广泛阅读的细心读者可以发现,他的一些结论和一些尝试客观地理解和认识巴特、纠正一些对巴特的误读的福音派神学家颇为接近。
笔者之所以翻译这一章节颇有目的性。华人教会受困于闭塞的信息和大受限制的基础人文教育,常常在对人事物的判断上都有极大的片面性。“贴标签式定罪”“不问客观理据只问立场”“不求探索过程只求结论”“难以理性沟通”“模糊化、情感式思维,对人对事见到风来就是雨”“拒绝反省式的‘批判式思维’,却又热衷于背后(或心里)批评、论断人”“因个人局部的一些问题就将之全盘否定”,这些绝非只活跃在外邦人的“短视频文化”中,而是扎根在华人信徒的文化血脉里;再加上大陆教育极少有哲学史、思想史和历史反省的教导(这Western Education的核心内容多被某些政治教条替换、占据),“系统性思维”则更是匮乏少见,不少信徒对如何看待一位(似乎常提出不合圣经言论的)思想家颇为盲目,甚至于会出现“研究巴特(或任何非正统人士)就是异端行为/浪费时间”“范泰尔已经替我们读过巴特,我们无需再读”“说范泰尔对巴特有误读就是准备替巴特翻案,就是异端行为,是改革宗修正分子”这些荒唐可笑、毫无逻辑,只要稍微有一些学养就会嗤之以鼻的言论。乃至“范泰尔说‘巴特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异端’”这为范泰尔亲口否认的言论在华人群体中口口相传,而其来源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和微信小网文。
结合近期的一些极端公共事件,笔者惊恐地发现,纵使华人信徒受限于圣经的明确吩咐并不会有某些极端行为,甚至反对某些极端行为,但是其使用的逻辑和思考方式,其实和一些极端分子并无本质差异——以情感主义为主导,缺乏理性思维和看重客观理据的气质。当向他们细究为什么我们可以放下一些国家的战争罪咎不再追讨,比如德国就很看重战争罪咎,愿意认罪,但一些国家并不认罪,我们为什么在公共层面要原谅他们?不少信徒“茫若坠云雾”,或只是以一些福音原则强行解释一番。
笔者盼望,会陆续译出的这些文本,能让不少信徒从正面获益,不单是在神学上,也是在人文教育上;不单是在学识上抛砖引玉,也是在素质上培养平衡稳健的看见和品性。正统神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与不合圣经的思想互动中产生的。不少改革宗神学家自己就汲取了一些非正统人士的洞见,像加尔文面对当时已经被路德宗定为异端的欧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绝非鄙夷了事,而是发现其不少洞见值得深究,进而以此完善了“与基督联合”的教义,甚至是像西塞罗(Cicero)这样的外邦人,加尔文依然愿意引用他的诸多言语,修正提升;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也同样承认连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这样几乎颠覆了所有基督教传统教义的神学家也有深刻的见解,甚至为一些正统神学的发展指出了明路——为“位格”“信徒意识”“神学的科学性”和诠释学的厘清作出了巨大贡献。笔者盼望这些稳健而平衡的神学家的言行,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也使人悔改,不随意对自己未钻研过的人事物论断定调,以至于犯下“作假见证陷害人”的罪。
《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的信仰历程,以及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徒运动的历史,为读者了解16世纪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部精彩的导论,同时也引导人们重新思考五百年前的改教运动极其深远的意义。点击上方图片链接可以购买这本书以及相同主题的其他书籍。
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当今的神学领域鹤立鸡群。是否仅仅因为他在时间上离我们如此之近,所以才显得如此巨大/重要(titanic)?当然,要客观地评价一位巨人的特写是比较困难的,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巨人,主宰着上个世纪的神学。和所有巨人一样,巴特也让人害怕:他的巨著《教会教理学》(Church Dogmatics)有十三卷之多(尚未完成!),足以让大多数人急着去找二手文献或一些可以借之理解他的简短引述。因此,你会听到巴特被描述为 “新正统派 ”(neoorthodox)或类似的标签。这些标签通常既不准确,也没有帮助。然而,由于害怕接近巴特本人,学生们往往只能听到一些口号。事实上,不仅仅是学生,就连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也会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创造出巴特。这显然令巴特本人感到沮丧:
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为他自己也能够对那些他不认同的人(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进行高度尊重他们又复杂精微的解读。
巴特的生平
卡尔·巴特于1886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个牧师家庭,这个家庭在各个时代都不同寻常——它总体上持保守的神学立场。然而,张力很快产生了,在巴特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前往德国,在当时最伟大的自由派神学家门下学习:在柏林师从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在马堡师从威廉·赫尔曼(Wilhelm Herrmann)。不久后,巴特就被视为自由派神学的一颗新星,尽管他很快就会完全放弃这种神学,但这些年日对他影响深远。特别是赫尔曼,他是施莱尔马赫的忠实追随者;赫尔曼那对耶稣真实又深刻的爱显而易见,这深深地影响了巴特。
完成学业后,巴特搬到了日内瓦,成为一名助理牧师,并在那里首次深入研究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他甚至发现自己在加尔文曾经讲道过的讲台上布道,不过后来他写道,“恐怕加尔文会对我那时在他的讲台上所讲的道不太满意”![2]但仅仅几年后,他成为了萨芬威尔(Safenwil,位于苏黎世[Zurich]与伯尔尼[Bern]之间)的一个村庄的牧师,那时他的自由派神学才真正开始动摇。他逐渐意识到,告诉人们要敬虔并不是在帮助他们。
1914年,战争爆发,巴特震惊地发现他的自由派老师们支持这场战争。当看到他们将福音完全屈从于文化时,他对他们及其神学的信心受到了动摇。于是,“我逐渐回到了圣经”,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奇异新世界”。就像路德一样,这一切始于对《罗马书》的研究:在1916年的夏天,“我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用当时我能利用的所有资源来研读《罗马书》……我开始阅读它,仿佛我之前从未读过。”[3]这迫使他抛弃了所有旧有的神学遗产,并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巴特在《罗马书》上所做的笔记在1919年初出版,并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并不奇怪:巴特不再采用旧的自由派批判方法——通过重构的历史背景尘埃来过滤文本,而是想采用“逐字默示的古旧教义”(the old doctrine of Verbal Inspiration),让文本直接说话。[4]他以这种大胆的态度开始了阐述:
保罗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人,向他的同时代人讲话。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上帝国度的先知和使徒,保罗实际上是在向每一个时代的所有人讲话。当然,过去与现在、那里与这里的差异需要仔细考查和深虑。但这种考查的目的只能证明这些差异事实上是纯粹微不足道的。[5]
比如说,保罗讨论“犹太人对律法之态度”的内容,就适用于自由派对宗教性(religiosity)的观点。也就是说,自由派神学把宗教性当作通向上帝的阶梯。自由派神学认为,无需任何来自上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谈论并认识祂。
取而代之的是,巴特越来越主张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辩证的”(dialectical)关系。换句话说,上帝是绝对不同的。人与上帝、时间与永恒在本质上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谈论上帝。如果我们尝试这样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只是在(仿佛以很大的声音)谈论自己。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这一巨大鸿沟只有上帝自己能够跨越,而祂正是通过祂的道来实现这一点。因此,唯有在上帝的自我启示中,我们才能认识祂。
1921年,巴特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的改革宗神学教席,在那里,他的教学任务迫使他必须完成自己的“改革宗神学和历史”速成课程。有了对加尔文、茨温利、改革宗诸信仰告白和施莱尔马赫的新知识,他开始积累起一个真正可怕的神学武器库,可以用来向自由派神学开战。
四年后,巴特搬到明斯特任教,1930年他再次搬家——搬到波恩。就在那时,他开始阅读安瑟伦的著作,安瑟伦似乎为他澄清了一些思想。他从安瑟伦的格言 “信仰寻求理解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中看到,神学的构成必须不是以我们自己独立的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根据上帝所说的话,以信仰来思考和理解。[6]
20世纪50年代,瑞士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认为,在1930年前后,巴特的神学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巴特以前主张上帝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从那时起,他开始将这种关系视为类比关系(上帝与人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上帝命定的对应关系)。[7]巴特本人(虽然对此有所觉察)从未对巴尔塔萨的这一理论表示反对,因此该论点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部分由于布鲁斯·麦科马克(Bruce McCormack)对巴特早期思想的重新审视,[8]部分由于最近出版的许多巴特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未曾发表的材料,关于巴特神学具有真正转向的理论现在看来显得过于粗糙。他的“辩证”神学并不只是一个短暂的、不成熟的阶段。1930年前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一种澄清:巴特更抽象地称之为“道”的东西,从那时起就非常明确地成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具体的人——祂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
到20世纪30年代初,巴特已成为欧洲新教思想家的领军人物,并准备开始他余生几乎全部的工作:撰写《教会教理学》。然而,他刚刚起步,希特勒就在德国掌权,改变了一切。大部分德国新教迅速俯首称臣;但巴特没有,他认为这种屈服只是一种扎根上帝话语之外的神学的最新政治表现形式。为此,他很快就丢掉了工作。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除了带头创建一个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以抵制纳粹神学之外,巴特还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神学工作中。巴特看到的是,与其说现在是放弃深奥的神学以求快速反应的时候,不如说现在是为了恢复和捍卫福音而更加努力地从事神学工作的时候。
1935年,他刚被解除在波恩的教职,就被巴塞尔抢走聘用,于是又回到了故乡瑞士。他过去尽其所能继续向纳粹施压,但现在他的时间都集中在撰写《教会教理学》上。
艰苦的岁月、辛勤的工作和巨大的声誉很容易让人忽略巴特身上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那攀登阿尔卑斯山、热爱烟斗的纯粹人性。巴特充满好奇心且兴趣广泛,他对莫扎特近乎狂热的喜爱非常能够体现他的性格特点——莫扎特之所以吸引人,肯定是因为他与巴特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闪烁着光芒的、时常带着顽皮意味的玩乐精神。巴特认为,这才是神学家应有的样子:“在工作中毫无乐趣的神学家根本不是神学家。阴郁的面孔、沉闷的思想和乏味的说话方式都是不能容忍的。”[9]
1964年,巴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使他无法像以前那样工作。最终,他在1968年12月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天,他还为第二天要做的演讲写下了“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这句话,然后双手合十祷告。而这就是他的妻子内莉(Nelly)发现他时的情景——当然,背景中仍然播放着莫扎特的音乐。
注释:
[1] Karl Barth,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Otto Weber, Karl Barth’s Church Dogmatics (London: Lutterworth, 1953), 7.
[2] Karl Barth, Letter to F. J. Leonhardt, February 14, 1959, cited in E. Busch,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SCM: London, 1976), 53–54.
[3]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2), 264.
[4] Karl Barth,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18.
[5] Ibid., 1.
[6] 读过我在本书中关于安瑟伦的章节[第5章]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对安瑟伦的理解与巴特的理解颇为不同。(本书即《你该认识的神学家:从使徒教父到21世纪》[Theologians You Should Know – An Introduction: From the Apostolic Fathers to the 21st Century]。——译者注)
[7] H. U.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Ex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92).
[8] Bruce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6–1975; hereafter CD) II/1, 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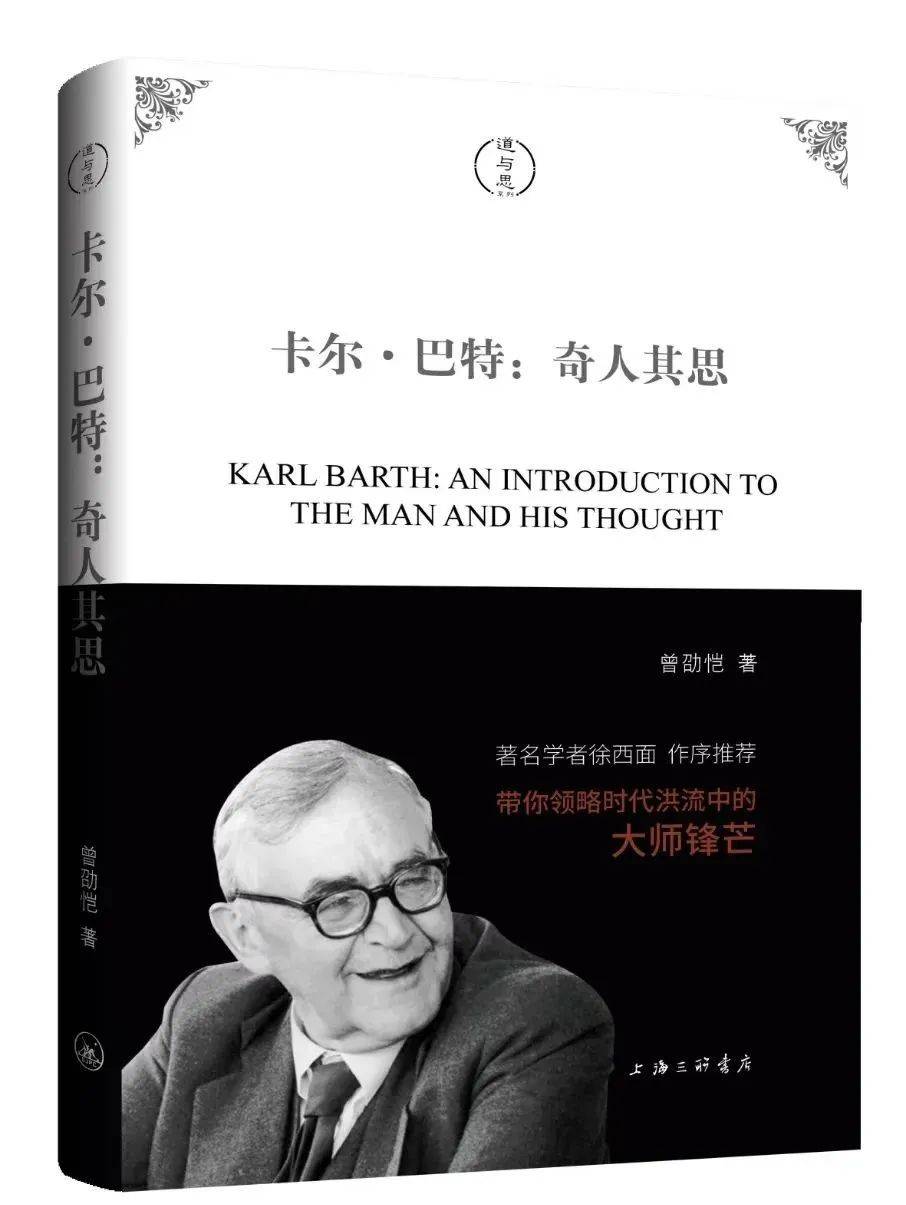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