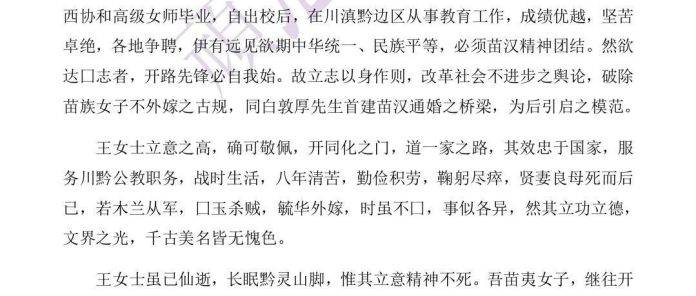阿卯革命老前辈张斐然先生的人生履历是很有意思的。基于某些客观因素,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潜藏”的故事,并不被更多人所知。
杨忠德先生搜集整理的《张斐然同志反抗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民主斗争的轶事》(见《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一文,是其遗稿部分,也是了解张斐然前期为革命事业和为民族事业奋斗的重要材料。
谈到为民族争取权利,张斐然与杨、白等人进行抗争的文字性描述,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那就是在贵阳的某次会议上,张斐然说“石门坎苗文”为拼音文字,是先进文字(今日的“石门坎苗文”(Pollard Script)是被如何对待的,大家心里明白),用以反驳当时当政者的“落后文字论”。
不过,笔者今日这篇小文,想要谈的是遗稿中谈到的有关白敦厚和王毓华之间的婚姻的问题。
白敦厚是汉族人,随杨森来到石门坎后就留下来执行任务,宣传“国家”文化。他在石期间与阿卯传道人王英的大女儿王毓华(成都读书回石)结识并结婚,被当时的地方报纸报道为威宁地区“苗汉通婚”首例,成为当时贵州省民族同化政策的“果子”之一。1945年王毓华离世,白后面找了花溪布依族陈为瑾为妻。
张斐然对此事的看法,其回忆文稿提到了一点:“白敦厚执行其主子同化少数民族的心不死,不久他的老婆(苗族)死了,给他向其主子谄媚取宠的机会又到了,就到处招摇撞骗,找少数民族女子结婚。”(《威宁文史资料》第二辑61页)
在他看来,白娶王毓华,还有陈为瑾,都带有“任务”性质,不纯是出于“爱”。
不过,张斐然1945年写下的《开辟石门坎的两位白先生》(《黔灵月刊》1945年5-6期,60-61页)一文,其对“苗汉通婚”一事确是高度认可和带有赞同的评价的。就单是对已故王毓华的评价,说她“破除苗族女子不外嫁之古规,同白敦厚先生首建苗汉通婚之桥梁,为后引启之模范”等等。
张斐然晚年的回忆和年轻时的记录,所思所想都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说互相矛盾。也许我们会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或者可能说民国时期张斐然只是为了“迎合”,并不是真心这样想……
总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份对同一事件(人物)的不同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去评判?
这个问题需要深思一下,但笔者目前一个粗略的看法就是:回忆稿有其时代背景左右,而1945年张所写下的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当时的一种真切的感受和想法。
此处暂停继续讨论,笔者想要转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苗族(阿卯)女生外嫁他族(尤其是汉族)所带来的一种族群内的认识和反思问题。
我们今日很难想象得到王毓华外嫁给白敦厚后,本族自己背后对她的“编排”和“造谣”对她以及她的家人的一种无形中的伤害有多少。不要觉得没有这样的事,那些年代久远的事我们或许很难探查清楚了,但活在当下,这样的事,我们今天也可能常会听到或者看到。
现今社会里,阿卯女生外嫁他族的也挺多,而且社会虽然看起来包容度更高了,但还是会存在一些的“风言风语”。著名微观史学者王笛先生就曾发专文说,短视频平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些民族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研究者也都开始了“短视频民族志”的书写。
阿卯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也非常活跃(其他平台笔者没有关注,不太了解),其中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外嫁他族的问题。女生们都从很多方面阐述了自己为什么嫁给汉族人的理由,而部分男生们则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来“阐述”(当然也会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的看待,但更多的则是有“指责”的意味在里面)自己的观点。
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友好的对话,而女生,则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受害者。一些被刻意编排出来的事会产生,并被宣传,传播到更多人的心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古代对这类信息的传播,往往局限于一个地方或者一小群人中间,但今日互联网如此发达,其传播更广,影响更大。
不久之前在一位老人家的资料那里,就看到过某位前辈留下的稿子,讲到的就是王毓华和白敦厚婚姻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说白如何虐待和欺辱王,并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威吓本族女性和防止本族女性再外嫁。因为一提到外嫁的结果,就可以举例:你看,王毓华就因为嫁给汉族,所以这样的“凄惨”。当她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心里也不免会思索许多,不会轻易外嫁。
笔者曾听一友人说起过一个故事,大概是谈起王毓华嫁给白敦厚后所遭遇的“凄惨”带给他人的不幸。故事梗概大致是,某阿卯人家的女儿嫁给一位汉族人后,由于被迫无奈,后来,改嫁给另一位阿卯男同胞,这样,家里人才放心下来。在这个故事里,王毓华外嫁所带来的“悲惨”命运,成为了迫使其女儿重新改嫁阿卯同胞的诱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笔者为寻找“答案”,近日拜读了王明珂的《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允晨文化,2021)、颜芳姿的《妖怪、变婆与婚姻——中国西南的巫术指控》(三民书局,2021)、张晓的《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商务印书馆,2018)三书。另外,曹端波的《侗族巫蛊信仰与阶层婚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和刘锋的博士论文《巫蛊与婚姻——黔东南苗族婚姻中的巫蛊禁忌》(云南大学、2005)等书和论文,也是要继续去阅读的相关著作。
笔者从王明珂的“毒药猫理论”和颜芳姿对侗族变婆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尤其是颜芳姿的研究,她在探讨侗族变婆与婚姻之间关系中,除了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外,还包括了深度的田野调查,使得其著作让人读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她本人作为曾嫁给侗族人的“外来者”,更是体会了一把“巫术指控”的意味。这两位的著作都探讨了非常多的问题,也很有启发意义,感兴趣者可以去阅读。
在关于王毓华“凄惨”故事的叙述中,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被污名化的阿卯女子外嫁的婚姻叙述,它所能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警戒本族人与他族之间的婚姻来往,以此也区分出“我族”与“他族”,同时也是一种封闭的自我保护机制。在社会紧张中,往往女人成为了“替罪羔羊”,成为了被抹黑的对象。这一切的一切,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存在,而不是简单的是非之分。
颜芳姿说:“变婆主要为侗族人提供了两个层次的社会界限:一个层次是透过变婆的骇人传说(变婆死后变化成猛兽攻击人类)来避免外地人在此处久留,另一个层次是保有侗人的血脉”(178页)。
针对阿卯女生外嫁,本族人又怎样去理解和阐述这些问题呢?作为阿卯女生,她们自己有怎样的想法?阿卯社会里又生出怎样的“故事”来诠释外嫁者?在今日我们认为的自由恋爱的社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时代下,本族外嫁,大部分人确实不再似从前那样有保守的观念。但似乎在今天的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很多人注定一辈子可能无法拥有自己的伴侣。尤其是贫困的阿卯地区,基于现实的考量,还有思想的改变等,许多人没能像当初他们的前辈那样,找到一个伴侣。面对这类情况,他们对于外嫁者所生出的一些“别样”想法又是些什么?笔者想,很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的田野,才能有一个比较有条理的回答了。
笔者的观念是:在当代的环境下,基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所能接触到的人,民族通婚已经是常见现象。他想找一个本族的,她想嫁一个他族的,是社会常态。某些基于民族主义的随意诋毁,笔者并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