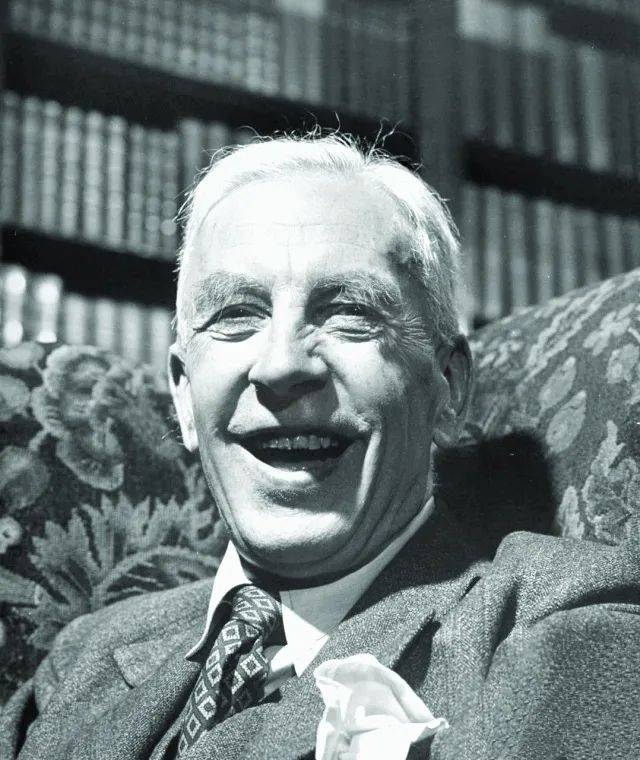
81.圣保罗曾经在奥伦特斯河和台伯河这样的内河冒险航行,急于穿越比地中海更辽阔的海洋。他在前往印度的第二次传教旅行时,搭乘一艘葡萄牙小帆船绕过好望角。之后,他进一步远游,在前往中国的第三次传教旅行中穿过马六甲海峡。这位不知疲倦的传道者又换乘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从加的斯(Cadiz)横渡大西洋,抵达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P611
匝评:上述叙述大多没有历史依据。
82.福音的本质越是具有革命性,越是要用熟悉而适宜的方式来加以表现。这样做势必要求传教士为福音脱去从自身文化传统里传承下来的外衣,要求传教士自己来判定传统的宗教表达中究竟何为本质、何为偶然。
这种策略的症结在于:传教士在非基督教社会传教,在消除一个障碍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教友设置了另一重障碍。在印度和中国,现代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就曾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传教士彼此猜忌争斗和梵蒂冈的保守成性,使这些人沦为牺牲品。然而,事实将证明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如果塔尔苏斯的保罗没有娴熟地脱去基督教在巴勒斯坦诞生时的地方性襁褓,罗马地下墓穴的基督教艺术家和亚历山大神学院的基督教哲学家永远不会有机会从希腊人的视角和观念来阐明基督教的本质,进而为希腊世界皈依基督教铺平道路。同样,在20世纪,奥利金和奥古斯丁宣扬的基督教,倘若不能去除它在历史旅程中接连在叙利亚、希腊和西方“驿站”停留时加上的外部标志,就无法把握如今摆在每一种现存高级宗教面前的世界性机遇。一种高级宗教如果听任自己“彻头彻尾地”带有转瞬即逝的文化环境的特征,注定会成为停滞和世俗的宗教。
如果基督教最终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就可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重现它曾在罗马帝国完成的壮举。罗马的交通系统促进了宗教交流,基督教得以汲取和承继接触到的其他高级宗教和哲学的精髓。P612-P613
匝评:宗教的外衣必须处境化,以适应各种文化环境,但信仰的核心必须坚守。
83.大一统国家的政府所在地成为宗教的沃土,因为这样的城市自成一个小世界。首都不仅有多种语言的居民,也包括各个阶层和民族的代表,它的城门连接四通八达的公路。在同一天之内,一位传教士可以在贫民窟和宫廷传教布道。如果他能得到皇帝的宠信,还有望调动帝国庞大的行政机构。尼西米(Nehemiah)利用在苏萨宫廷中的地位争取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保护耶路撒冷圣殿国家。16、17世纪,耶稣会神父千方百计在阿格拉宫廷和北京宫廷站稳脚跟,曾梦想凭借尼西米式的手腕为天主教会征服印度和中国。
实际上,首都的历史使命最终往往落实到宗教领域。直到本书作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华世界的京城洛阳仍然对人类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由于它曾是东周和汉朝的政府所在地的政治作用。从政治上说,洛阳无非是又一个尼尼微或提尔(Tyre)。洛阳至今仍有巨大影响,是因为它滋养了大乘佛教的种子,使大乘佛教适应了中华世界的文化环境,进而传遍整个中华世界。哈喇和林的废墟上也依然弥漫着无形的活力,正是在这里,13世纪时,西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中亚聂斯脱利教派和西藏喇嘛教的代表直接接触,这也是这个短命的草原城市昙花一现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
确切地说,以1952年的眼光来看,“永恒”罗马的创造者显然不是罗慕洛、罗穆斯或奥古斯都,而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君士坦丁堡,即所谓的第二个基督教罗马,享有远非一个大一统国家首都可比的地位,仍继续在当今世界发挥着影响,它是一位牧首的驻跸地,包括俄国教会在内的其他东正教教会的首脑,都承认这位牧首为“同侪之首”。P628-P629
匝评:很多国家的政治中心未必是宗教、文化中心。另外,作者这里对洛阳与哈喇和林如今地位的强调显然过于夸张了,根本不是事实。
84.伊斯兰教徒把《古兰经》和《圣训》记录的穆罕默德的圣言和法令奉为法律之源,这种法律不仅支配穆斯林社会自身的生活,还支配穆斯林征服者与最初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的关系。穆斯林的征服浪潮迅即席卷一切,穆斯林征服者新法律的公认原则却是无理性的,两者的结合造成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要从《古兰经》和《圣训》中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提炼出一种普遍的法律,这个任务十分荒谬,正如要在荒野中找到泉水,据说希伯来人曾向摩西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对于寻求法律养料的法学家来说,《古兰经》实际上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古兰经》关于穆罕默德在“希吉拉”之前从事非政治活动的麦加时期的章节,为务实的法学家提供的材料远比《新约全书》要少,这些章节几乎全都属于至关重要的宗教内容,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上帝的唯一性,谴责多神教和偶像崇拜。……
穆罕默德成为一个国家的首脑,他此后发表的言论大多涉及公共事务。然而,即使是麦地那诸章节,如果不是借助于外来的补充,恐怕也难以从中提炼出一种普遍的法律体系,这就像圣保罗的《使徒书》表演的同样的法学魔术。
在这种情况下,缔造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实干家抛开理论,自行寻求解决之道。他们借助于常识、模仿、共识和风俗,设法从中开辟一条途径。他们利用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倘若虔诚的教徒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材料直接源自先知,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如此掠来的材料中,罗马法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借鉴叙利亚省份通行的罗马法。不过,罗马法大概更多是通过犹太人的中介作用传入伊斯兰世界。
在穆罕默德的“希吉拉”之际,犹太法律已有悠久的历史。与伊斯兰教教法一样,犹太法律起源于冲出阿拉伯半岛北部大草原,闯入叙利亚原野和城市的游牧民族的惯例。为了应对同样突然而剧烈的社会环境变迁造成的燃眉之急,原始希伯来人像原始阿拉伯人一样,求助于“乐土”上的一个成熟社会的现行法律。
虽然《十诫》似乎完全是出自以色列人之手,以色列人的另一项法律,即受过教育者所知的“立约”(Covenant Code),却表现出受益于《汉谟拉比法典》的迹象。P636-P637
匝评:任何宗教经典都不能囊括人间律法,人间法律的制定还必须从经验出发。宗教经典为人间法律提供立法的原则。
85.货币的发明无疑有利于发行货币的政府的臣民,尽管这项发明给社会带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破坏性波动和高利贷的诱惑。但是,发行货币的政府才是更大的受益者。因为发行货币是一种“介入的行为”,政府由此至少直接而持久地与少数活跃、聪明、有势力的臣民建立起联系。货币的出现,不仅提升了政府的声望,还为政府提供了自我宣扬的绝好机会。P644
匝评:不仅货币,统一度量衡、文字等都有利于统治者。统治者还试图垄断对时间的定义,以帝王的年号纪年就是此意。
86.吉本曾经表示:“我已经描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这寥寥数语不仅概括了他的71章巨著的主旨,还表明他本人是塞尔苏斯和鲁提利乌斯的坚定支持者。
……吉本只是含蓄地提及上述观点,一位颇有声望的20世纪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ser)却直截了当地指出:
希腊和罗马社会乃是建立在个人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的观念之上,不论今世还是来世,全体国民的安全高于任何个人安全,并视之为行为的最高目标。公民从幼年时代起便受到这种无私理想的熏陶,毕生为公众事业服务,随时准备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崇高的牺牲面前退缩,就是只顾个人生存不顾国家利益的卑鄙行为。东方宗教的传播改变了这一切,它们反复灌输的是心灵如何与上帝相通,把灵魂的永恒拯救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与这个目标相比,国家的繁荣与兴亡不足挂齿。这种自私而邪恶的教义势必使信徒越来越疏远公众事务,只追求一己的宗教情感,蔑视现实生活,仅仅把现实生活看作是美好永生的初期阶段。芸芸众生把鄙视尘世、沉迷于天国冥想的圣徒和隐士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取代了无私忘我、为国家利益而生、为国家利益而死的爱国者和英雄的古老理想。在世人看来,尘世的城市贫乏可鄙,从而只关注九霄云外的上帝之城。
这样,人生的中心从现实转向来世。不论来世如何获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变使得现世遭受重大损失。整个政治机体濒于解体。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纽带松散了:社会结构趋于瓦解成个体,从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因为只有公民积极合作,自愿以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文明才有可能。人们不肯保卫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愿国家继续存在。他们热衷于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灵魂,他们把自己所处的物质世界视为邪恶之源,甘愿听凭这个物质世界毁灭。这种着魔般的妄想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中世纪末期,罗马法、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古代文学艺术的复兴,才标志着欧洲恢复了本土的人生和行为的理想,恢复了更为健全、更为勇敢的世界观。文明进步历程中的长期停滞就此终结。东方思想的入侵浪潮终于退却,而且还在继续衰退。P663-P664
匝评:这种指责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改教家倡导的天职观念在罗马帝国时就成为主流,反对基督教的声音就会减少。
87.我们曾在本书前面部分详尽地论证,早在基督教或任何一种在与基督教的竞争中落败的东方宗教入侵之前,希腊社会就已经衰落了。我们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高级宗教不应承担促成文明死亡的罪责,虽然这样的悲剧仍有可能发生。为弄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必须把研究范围从宏观领域扩展到微观领域,从过去的历史事实深入到人性的恒定特征。
弗雷泽的观点是,高级宗教本质上必然是反社会的。一旦人们首先关注的不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理想,而是以高级宗教为目标的理想,势必会损害文明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宗教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是否截然对立、水火不容?如果人们把个人的灵魂拯救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否就会危及文明的结构?弗雷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果弗雷泽的答案是正确的,也就意味着人生乃是一出没有精神净化作用的悲剧。本书作者认为弗雷泽的回答是错误的,因为它曲解了高级宗教和人类精神的本质。
人类既非无私的蚁群,也不是反社会的独眼巨人,而是一种“社会动物”。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人类才能表现和发展自身的个性。反之,社会无非是不同个体相互交往的平台。社会的存在有赖于个人的活动,个人也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再者,个人与同胞的关系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两者之间并无冲突。显然,在原始人的神灵幻想中,部落民与所崇拜的神祇之间存在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非但没有使部落民彼此疏远,反而成为最牢固的社会纽带。弗雷泽本人对原始人的研究表明,人对上帝的义务与对邻人的义务并无冲突。解体中的文明无不把独裁者奉若神明,以之作为新的社会纽带,足以证明这一点。是否像弗雷泽说的那样,“高级宗教”使得这种协调蜕变为冲突?不论理论上还是现实中,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人类追寻上帝乃是一种社会行为。如果基督救赎人类是上帝之爱在人世的体现,那么,既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竭力亲近上帝,就必然意味着追随基督的榜样,为救赎自己的同胞而牺牲自我。因此,尽力追寻上帝以拯救自身的灵魂与对自己的邻人尽义务,两者的对立纯属子虚乌有。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显然,与只追求世俗社会的美好社会目标、没有任何更高目标的世俗社会相比,人世间“战斗的教会”(Church Militant)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换言之,事实上,个人在现世的精神进步比任何其他方式更能促进社会进步。在班扬的寓言体小说中,朝觐者看不到通往善行生活的“窄门”,直到看见遥远地平线上的“亮光”。我们关于基督教的论断也适用于所有其他高级宗教。从本质上说,基督教与同类高级宗教并无二致,它们有如上帝之光照亮人类心灵的不同窗口,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窗口的透明程度不同,透过的光彩各异。P664-P665
匝评:此处的辩护存在瑕疵。因为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信徒都能平衡好俗世责任与属灵生活,的确有不少信徒不愿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从教义出发否认事实。汤因比这段论述有助于提醒信徒不要走偏。
88.只要从理论转到实践,从人性转到历史记载,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证明,宗教家实际上满足了社会的现实需要。我们若是列举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文森特·德·保罗、约翰·卫斯理或大卫·利文斯敦等人的事迹,也许会被指为提供不证自明的例证。因此,我们将列举被公认为异类,并且因此受到嘲笑的一类人,这类人不仅“醉心于上帝”,也是“反社会的”,他们既神圣又荒谬,被愤世嫉俗者所嘲笑。他们就是所谓“最不像好人的好人”,即基督教隐士,如沙漠中的圣安东尼、柱子上的圣西门。
很显然,这些圣徒离群索居,反而能够与人世建立起更为广泛、更为活跃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是他们依然做一个“尘世中人”、毕生从事某种世俗职业所无法企及的。他们一意静修,但对尘世的影响无远弗届,远远胜过皇宫禁苑里的帝王。他们与上帝神交、追求神圣,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比任何世俗政治层面的社会服务更能打动人心。P666
匝评:这是一些帮倒忙的例子,根本证明不了论点,反而给人留下把柄。这些离群索居的圣徒显然不会服兵役、抗击外敌入侵。
89.每一个现存文明的背后都有某种普世教会,一个文明的历史可以经由普世教会上溯到先辈文明。通过基督教会,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希腊文明;通过大乘佛教,远东文明可以上溯到中华文明;通过印度教,印度文明可以上溯到印度河文明;通过伊斯兰教,伊朗和阿拉伯文明可以上溯到叙利亚文明。P667-P668
匝评:汤因比对儒教缺乏必要的认识。事实上,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主要不是佛教,而是儒教。虽然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最多只能算半宗教。汤因比用西方人的宗教观念来套中国,全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90.到写作本书时为止,新兴的世俗社会经过长期努力,彻底挣脱西方天主教会蛹体,已有 250年时间。不过,我们显然仍可以把非凡而庞大的西方技术体系看作是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副产品。庞大的西方物质大厦的心理基础在于相信体力劳动不仅是人的本分,也给人以尊严:“工作就是祈祷”。这种信念彻底抛弃了把劳动视为平民和奴隶分内之事的希腊劳动观,这种新劳动观的树立,有赖于圣本尼狄克把劳动奉为神圣的教规。本笃会以这种劳动观为出发点,奠定了西方文明经济生活的农业基础。在此基础上,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通过合理安排的劳作建立起产业的上层建筑。世俗社会贪婪地觊觎这座由修士建造的巴别塔,最终直接插手干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起步的基础之一就是掠夺寺院。P669-P670
匝评:这种溯源其实还不够。其实可以追溯到耶稣而非本尼迪克。耶稣的职业就是木匠,而不是学者,可见上帝不轻视任何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