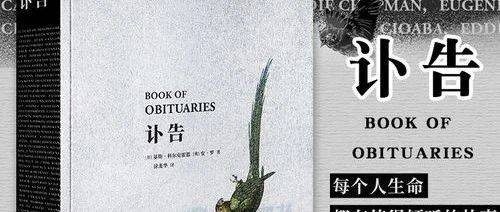阅读此文约6分钟。明天星期六(2024年1月6日)上午10点至12点,我将分享与这篇文章及标题相关联的内容。zoom号:852 0535 6860,密码:2023,欢迎有兴趣者转发周知并参加。
三年前的冬天,有一个人说完“我感觉不舒服”,就一命不起。那个人便是当今球王梅西的教练,我从大学时代起就欣赏的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经济学人》杂志“讣告”专栏作家安.罗的哀辞,也实在无由传达球迷在回忆1986年那个名为“上帝之手”的进球里,与他的死亡之间所连接在一起的悲欣交集。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你可以从十多册的《吴宓日记》里,看到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先生这句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所发出的近乎遗言的求告。这实在不是最悲惨的故事,留存下来的无一例外的,都有着“幸存者偏差”的特例——因为那个时代折磨致死的人间惨剧,是何其多也。很多痛彻心扉的人事消息于天壤间,随风而逝。
这样的遗嘱定睛于自己,自是无可厚非。别说一般人的遗嘱中,涉及大多无非是家产之分割,丧葬之丰俭。就是人臣贵如如张之洞,也只是“望你们勿忘国恩,不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当然他同时代的李鸿章则“更上层楼”,遗嘱里不忘向皇上提出匡扶社稷之策,“臣在九原,庶无遗憾”,“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读着这些得体的死别之辞,你能感受到他的效忠与偶像崇拜在哪里。
当然还有对死亡看得似乎更洒脱一点的,像陶渊明一样的《拟挽歌辞》三首,徐渭与张岱同写过《自为墓志铭》,都是当文学作品来写的,一心在意传世,与死时的挣扎大多无关。所以看起来好像在写别人的死亡,因为真正死亡的大锤还离得较远。他们死时的挣扎一同埋入时空里,倒是可从他们的同行元稹《遣悲怀》三首,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可略窥一二。前者的“唯将终夜长开眼,报达平生未展眉”,后者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使相逢应不识”,此等深情里透露出的绝望,常常被人忽略。此是人之共情能力低弱所致,否则就应该读得出他们内心里的至深绝望——而这种绝望是人类的悲剧,非仅元稹、苏轼同有,是我们所有人的无望。
但这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大前提,即人死如灯灭,所以人们是如此悲伤,甚至绝望到不能自拔。不过,如果有一个颠倒乾坤的事实,使你有十足的盼望与喜乐,你愿意来了解么?你说“哪有这等好事?”你死死地记得费尔巴哈带给你的砒霜:所谓宗教,就是人内在欲望的外在投射。我觉得他句话,若是加上“除犹太——基督教外”这个修饰性的定语,就会散发出真理的甘甜。更进一步说,我愿意你来了解有一个人不安排自己的后事——他虽然曾经死过却至今仍然活着——但他却安排了整个宇宙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后事,你愿意了解这份惊人的好消息么?你来看看安排了整个世界的后世之人,与这个世界为自己安排后世,写遗嘱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搜罗了近七百种关于死亡的中文书籍(含由外文翻译),也在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里整理过一系列关于死亡和信仰的书籍,以及近百种关于死亡的儿童绘本之书目(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刊布出来,以飨同好。自然特别愿意让人知道,死是众人的结局;按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可是我们这个族群忌讳谈死,且有不少人假装不死。当死临到自己至亲的时候,除了呼天抢地外,毫无准备,殊为遗憾。难怪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对死亡最没有准备的族群。但即便将自己的后世安排得十分得体,无比妥帖,中国也有这样的遗嘱推广机构,在西方正更是兴起逐渐被接纳的“安乐死”(又可名之曰“辅助死亡”)。但我们的后事真的是由我们自己安排,或者由我们的亲人们安排的吗?我愿意直接回答说,绝非如此。
2024月1月5日上午草就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