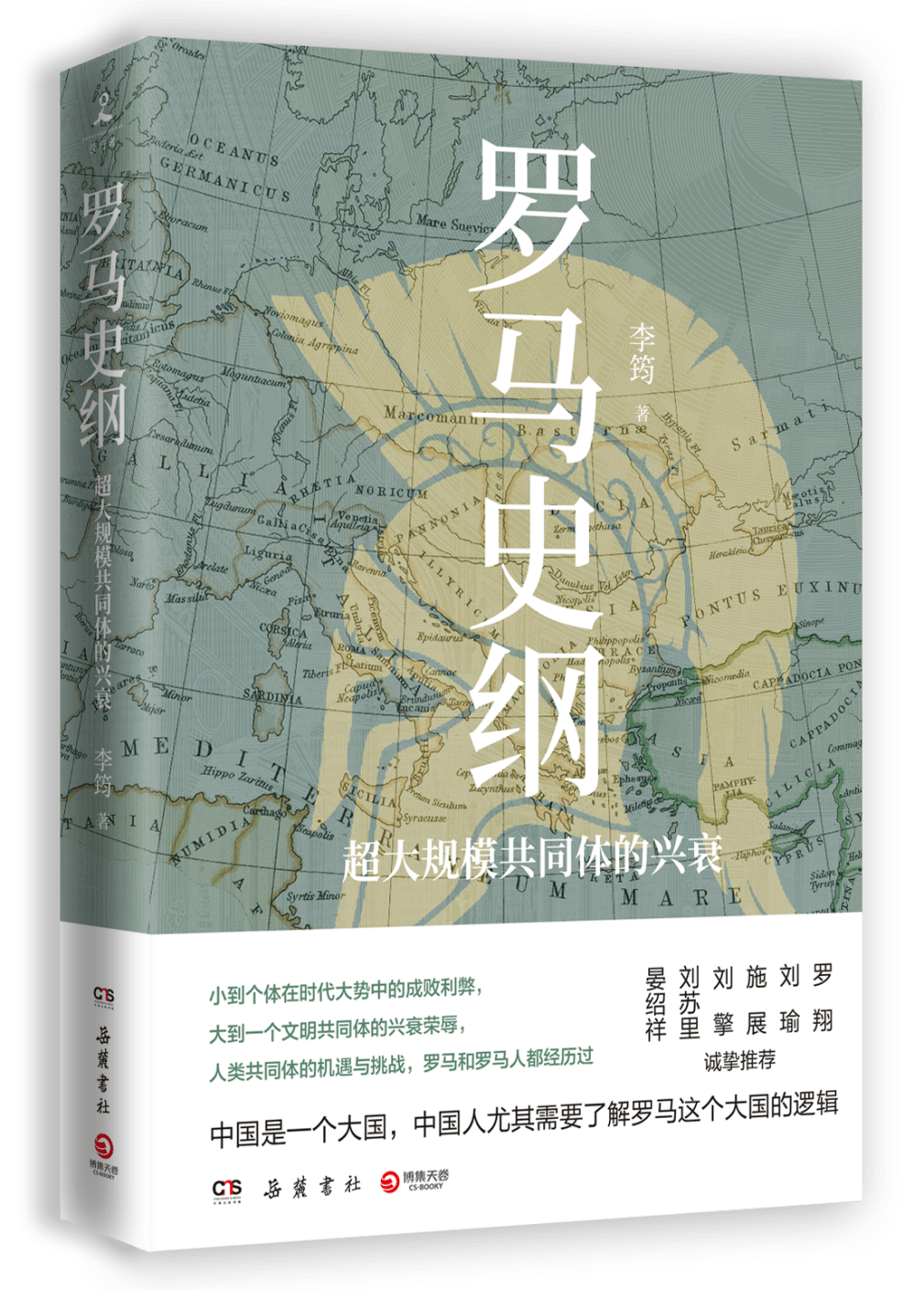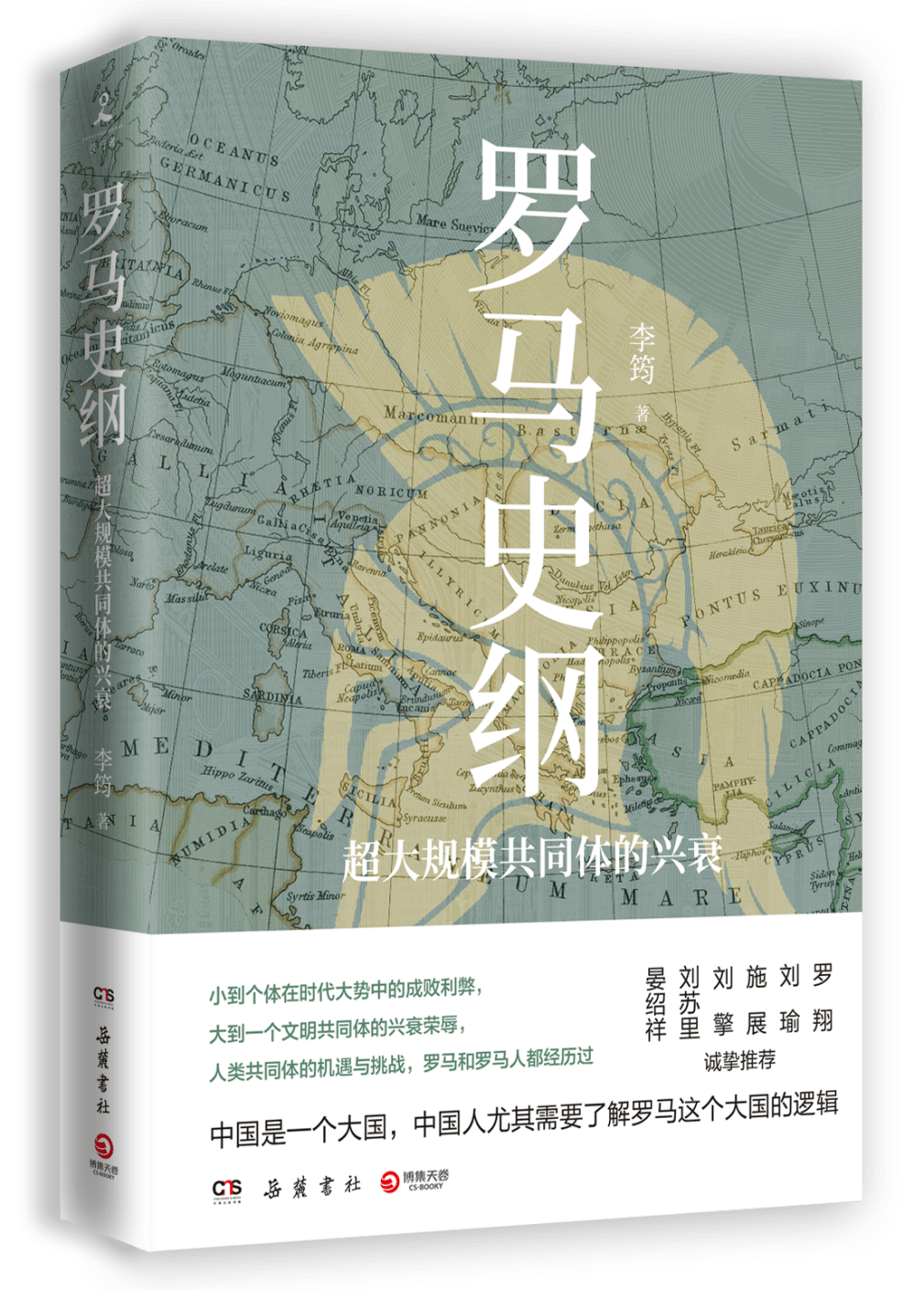大国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十多年来,民间学术团体——“大观”学术小组的研究一直聚焦于此。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国。你可以把这个学术团体的定位理解为一种前瞻的努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忧患意识使然。
近年来,这个团体中的学者纷纷走向前台,推出他们长期的研究成果,那就是用“史纲”体鸟瞰中西历史,并希望从中找到成败镜鉴。所谓“史纲”,“史”是历史,“纲”是逻辑。历史自有其运行逻辑,只是想看清并不容易。
先是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讨论中国历史的上千页学术著作《枢纽》赢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然后互联网学习平台“得到”强势力推“大观”学者开讲中西史纲。于是,施展推出了《中国史纲》,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推出了《西方史纲》《罗马史纲》,后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讲《中世纪史纲》。一般的传播做法是,“得到”上的课程讲完,同名图书随即面世。如今,读书界正在兴起对李筠教授《罗马史纲》的热议。
作为对西方和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的帝国,罗马的成功和失败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李筠会说是“共和”;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李筠会说“要让人愿意跟你玩儿”。
本次采访很长,我们以“罗马与中国”“罗马的治理技艺”“用罗马的思路看未来”为题,分上中下三部分刊出。
萧三匝:“大观”学术小组的研究方向定于超大规模共同体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为什么确定这个方向?
李筠:我们对学术界有自己的不满,觉得学术界对大的、宏观的问题谈得太少了,谈鸡零狗碎的问题太多了,大家找不到地方聊大问题,所以我们决定换一个玩法。先把整个世界跑一圈,把主要的大国都体检一遍,研究他们近代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古时候提供了什么元素,有什么包袱,近代史有什么曲折,有什么个性。把这个版图拼全了,才可以讲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之内。不是1840年以来,而是500年以来,在世界局势之中,中国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把时间拉长以后,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局促,才能把大势看得更清楚一些,对当下的很多问题也就没那么猴急了。
萧三匝:说白了,你们关注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李筠:当然。不过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按捺住直接研究中国的激情,先要把人家的历史和问题理清楚,不要直接对中国问题发言。把功课都做足了,才能讲中国的事。因为我们断定中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现象,不把药抓全了,不要轻易下手。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关心一个大国不光要繁荣富强,繁荣富强以后还能干什么,怎么才能干得好?
萧三匝:讨论帝国,首先就需要定义何为“帝国”,帝国与超大规模共同体是不是同义词?如果是,那么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也是超大规模共同体,是否也属于帝国?你说罗马帝国继承了罗马共和国的共和精神,那么帝国与共和国的本质不同体现在哪里?
李筠:“帝国”这个词的词源的意思就是统治权,而这个词在罗马共和时代就已经被普遍使用了。李维这些史家写共和国史的时候已经在频繁使用这个词了。如何运用这样一个庞大的统治权,罗马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了,因为共和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把我们后来归之于帝国的很多事做成了。比如武力的开拓,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这些共和国实际上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写书是想把帝国从狭义的语境中解放出来,研究超大规模共同体怎么治理。
如果非要较真帝国和共和国的区别,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中央机构。共和是一个贵族共治的局面,它的核心机构是元老院,世家大族、军功贵族一块儿商量怎么办国家的事儿。而帝国有明确的皇帝,是一人主持国政的格局,其他官员就变成了皇帝的打工者,不再像元老院那样和执政官平起平坐了,独裁的属性非常明显。
其实国大到一定份儿上,统治权的使用就越来越难任性。皇帝一个人实际上是管不了那么多事情的,没有队伍和系统,一个人耍不转。一个人无论是智力还是精力,都是不够用的,客观上就要求皇帝要把权力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这是任何国家做大了都会带来的必然要求。我探究的是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权力如何安排才是合理的、有效的、正义的问题。我通过讲罗马这样一个大块头,不光是讲历史,还要把政治学原理装进去,把政治学通则讲出来,因为罗马够大,玩得够高级。如果太小了,就那么点事儿,权力的运作也就没那么复杂。对中国来讲,小共同体的权力运作对我们没那么大的参照、对比和启示作用。
萧三匝:所以可以这么说,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但凡是大国,一定要蕴含共和的精神,否则玩不转。第二个层面,与其说你关注的是帝国,不如说你关注的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共同体,这是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可以抛开不同时期帝国概念的不同,比如罗马帝国它总有一个皇帝,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并没有皇帝,这两个帝国的概念又不一样了。回到帝国的概念的变迁,它是怎样发生的?
李筠:现代帝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织就帝国权力网络的工具大不一样,思路也就大不一样,战略也就要随之进行调整。但它毕竟是一个有核心的、有霸权主导国的同盟网络。帝国不是一个国家把其他国家全部吞并,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样,打下来,然后实行郡县制,全部格式化,这样的方式对全球性帝国的经营是不适用的,必须分层次、分梯度、分策略地安排各种盟友,形成一个庞大网络。现代条件下,交通和通讯的状况大大改善了,帝国的组织就比古时候方便多了。当然,有很多权力,因为交通和通讯的方便,反而变得秘密化了。原来是靠邮传来往,你靠罗马大道也好,我靠秦朝驰道也好,就那么些个官员,要控制那么大地盘,可用的手段有限。而现在市场经济发达了,很多技术手段大大的便利了,比如交通、通讯、金融,帝国的形成和运作反而隐秘化了。
萧三匝:其实大的共同体,达到两个目标就行,一个是秩序,一个是自由,这两个目标之间当然存在张力,做好平衡就行。我们单就超稳定性而言,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都属于帝国,其实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更加稳定。
萧三匝:我的意思是把从秦到清的中华帝国看成一个帝国,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很相似。从这个角度看,中华帝国的稳定性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我们有长期的帝国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学罗马帝国,我们应该学什么?
李筠:秩序和自由几乎是政治学和法学最想兼容的两个要素,兼容的方案和版本非常多,各有优劣。我觉得你高估了中国从秦到清稳定繁荣的历史。我把中国史理解为帝国版本的三次升级:秦汉是1.0版本,隋唐是2.0版本,宋元明清是3.0版本。它存在着一步步扩容、一步步复杂化、一步步升级的进程。从中央官制看,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更复杂的机构设置,随着帝国的扩张,中央官制复杂化、合理化、精密化了。秦汉只是整合了中国本部的文化,到了隋唐,随着佛教的进入,民族和宗教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这就不是秦汉的框架可以解决的了,所以隋唐扩容成2.0版本。到了清代,由元明积攒下来的多样性,比如西藏也进来了,蒙古也进来了,藏传佛教也非常重要,清代又实现了一次扩容。中国史是一个阶梯不断往上升级的过程。
虽然都是帝国,但罗马有一点是我们中国不传统具备的,我认为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罗马法。有了它,每个人都是法律主体,都可以享受法律的保护。即便这个人不是完整的罗马公民权的享有者,没有政治权利,没有资格选举元老院成员,但他拥有厚厚的罗马法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婚姻、继承、收养、买卖,这些重要的事情全都是有章可循的,受到帝国的保护。罗马帝国通过法律,把每一个人联进帝国的网络。而其他帝国,基本上都只是上层联接,不涉及下层。皇帝打下哪儿,你是国王,要不要服从我,如果服了,你就是我的属下,你的整个王国和部落也归附了。但这实际上是高层与高层之间建立起政治关系,民众之间并没有联接,一旦高层发生变动就麻烦了。比如成吉思汗死了,很多部落就会观望,捉摸到底是忽必烈厉害还是他叔伯兄弟厉害,帝国就开始松动了。所以通过军事征服所得到的庞大帝国非常不稳固,就在于它只是上层的军事同盟,没有办法铺到下层,很难给予普通民众真正的长治久安。
萧三匝:中国历代也有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罗马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比如大清律,它是自上而下的,没有顾及到每个老百姓的需求,而罗马法既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法律,又有照顾到地方不同情况的法律?
李筠:话分两头,先说中西法律的差别,然后再讲罗马的自治。总的来讲,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义务本位的,刑法为主体,不是说民法没有,但是占的篇幅并不多,民事主要交给了地方习惯去解决。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都是刑法为主,是非常刚性的。这样一个基本倾向,与中国长期以来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是契合的。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重农抑商,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怎样让农民安分地把田种好,是头等大事,而商业,从来就是被抑制的对象。商业带来的流动性,对于一个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国家一直抑制商人。如果商人被抑制,民法就长不起来。你这种事业我不赞成,我为什么要用法律来推进、保护、扩张你的地盘呢?当然是摁下去了。
而罗马恰好相反,它几乎从一开始贸易就非常发达,它必须通过贸易解决国内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罗马在很早的时候,粮食就不能自给,连吃饭都要通过长途贸易解决,当然就要推进贸易。所以它的民法如此发达,与它形成了古代最繁荣的市场经济直接相关。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就必须有民法。一个人即便没有罗马公民的投票权,罗马的民法权利也都是有的,生活就容易安顿。中国古代从来不是这样一个路数。这样的不同,导致中西政治存在基本政治逻辑上的差异。
萧三匝:那你是不是赞同某种程度的地理决定论?比如,农业文明区就搞中央集权制,而对罗马来讲,它的本土地盘很小,地中海沿岸国家也都很小,而且以商贸为主,所以它文明的基因就是商贸。
李筠:这个讲法对希腊是成立的,希腊是星星点点的城邦,粮食没有办法自给,所以普遍的贸易在地中海撒开。对罗马不完全成立,因为罗马一开始就像秦国一样,农民就是士兵,在罗马城周边,还是有平原让他们好好耕种的。当然,贸易因素在罗马的基因里也是很充分的。所以我认为地理的因素不应该看得过重,我们要用一个中间变量来看问题,就是“生存逻辑”。先民面对特定生存环境的时候,找到了什么样的活法来面对地理带来的各种环境要素,利用好它们,这套活法就是“生存逻辑”,它是有强大惯性的。
萧三匝:也就是说,罗马人找到了针对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罗马还是个比较小的农业国的时候,罗马人就比较朴实、勤劳,当后来它扩张到很大的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形成了共和精神,尊重各地法律、习俗。
李筠:小有小的办法,但是,小长大了恐怕要另想办法。从帝国扩张的路径上来讲,让被征服地区自治,是非常节省统治成本的办法。皇帝的征服,如果都像秦始皇那样,把被征服地区格式化,全部实行郡县制,县长都由皇帝派人来当,秦国的法律一定要落地到齐国临淄,事实上成本极高。彼此相距几千里,民情民风都不一样,皇帝推行刚性的法律和制度就得上手段,结果就是普遍的反抗。然后皇帝要派兵去维护秩序,养官养兵来执法,成本不就很高吗?如果全国都是这样,皇帝准备收多少税,养多少官和兵呢?当秦国变成秦朝以后,这样的高压态势统治全国,帝国没有办法持久,才经历二世,就崩溃了。所以刚性太强,实际上帝国根本不可能承受高昂的统治成本。
罗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不能硬管,只要你服从,好,你那里马照跑、舞照跳,你们原来怎么管就怎么管,有什么风俗我都不干预。但你要服从我的盟主地位,军事上必须认我是老大,不能偷偷地跟别人结盟。有了政治同盟关系,我可以给你提供安全保护,你自己不用养兵了,谁欺负你,我罩着你。你反而从养兵这个麻烦事里解套了,你就好好做你的生意,或者研究你的哲学,这不就挺好吗?你可以自治,还能得到保护,还能过上更文明的生活。那些蛮荒部落都没想到,原来日子可以过得如此美好,那他们为什么不跟罗马人过?
罗马人在这个过程中,最漂亮的做法是把人家的神都给安置好了。如果你到人家那里,明确告诉人家,你的神就是邪神、伪神,我来了就是要铲除你的神,那人家肯定誓死反抗,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就叫“不共戴天”嘛,人家肯定就跟你血战到底。罗马人到每一个地方都说,其实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某某神,只不过叫的名字不同。那些土著部落一听,也挺好啊,很容易归服。只要是多神教覆盖的地方,都和罗马兼容了,他们的神都进了万神殿,都有神位可以供奉。你想,你一个战败者,你的神庙不仅没有被铲除,你的神反而可以在罗马得到供奉,那你该多高兴啊。这样一来,宗教、军事、商贸都解决了,还可以跟罗马人学习过文明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加入呢?所以罗马征服的阻力就比较小,它编织那么大一个帝国,采取了把各方面成本都降得非常低的办法。
萧三匝:中国的王朝,越往后,越融汇异质文化。比如清朝皇帝统治汉人和蒙古人、藏人的方法就不一样,甚至按施展的说法,在清朝,北京是汉人的首都,承德是蒙古人和藏人的首都。
李筠:满清皇帝的确具有多元身份,他既是传统中原的皇帝,也是蒙古的大汗,还是藏传佛教里的文殊菩萨,什么都占齐了。这种玩法,在奥古斯都那里就有明确的思路。他打败埃及艳后以后,埃及不就并入罗马了吗?他就跟元老院讲,这个地方不能编成罗马的行省。因为埃及人一直相信法老就是神,罗马的宗教世俗化比较厉害,埃及人是不会相信这一套的,在埃及我们必须沿用法老的神权统治。告诉埃及人,罗马皇帝就是神,皇帝直接称神管理埃及,所以埃及就成了皇帝的特别行政区。其他地方也一样,只要这个地方够强大,文化传统够鲜明,宗教硬核够独特,在政治军事服从之下就主动地让它们自治。
萧三匝:帝国的最大特点是多元一体,或者说必须做到多元一体,你说的“一体”那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意思。
李筠:对。一个共同体可以分为好几层。比如清朝,最底层我们看见的是蒙古人在草原上奔驰,汉地主要是农民在农耕,儒生士大夫管着乡村宗族,西藏就是喇嘛管着信众,都不一样。中层是有结构性的互补的,汉地提供的是财政,因为农业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马背上的民族没有那么多财富,但蒙古人提供的是武力,骑兵异常勇猛。再说高层,儒家学说对定居的家族是非常有感召力的,只要定居农业,就信儒家。儒家不仅能安抚农民,它对最高级的制度设计也是言辞满满的,比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类,文献最丰富,故事最多。但这套故事去跟蒙古人和西藏人讲,人家不过定居农业的生活,从根本上就不会买你的账。蒙古人信长生天,统治者就要把萨满教这一套弄娴熟,宣称我就是大汗。藏人信藏传佛教,统治者就要借助它那个系统。西藏的黄教替代了蒙古萨满教占据蒙古人的心,当满清皇帝成为黄教里的文殊菩萨以后,实际上就掌握了蒙古人的信仰,所以他做大汗在宗教上是合理合法的。有了蒙古人的铁骑,清朝在军事上就是无往而不利的。所以,各大板块在帝国内部的功能是不同的,皇帝要把它像榫卯一样拼接在一起,拱顶石就是皇上,必须形成这种结构性的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