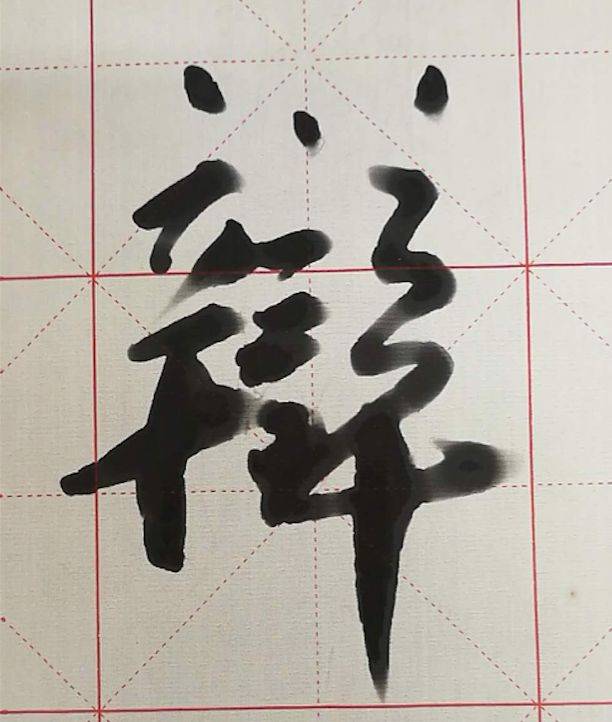
编者按:我曾在2017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发表三万余字学术长文《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此前,儒家网主编任重先生曾赠我一本《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并请我对此书进行评论,直言无妨。我认真阅读了此书,确有不得不说的看法,于是准备写作一篇长文,对书中几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主张进行回应。后来,有朋友看到我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建议我严密论证后发在学术期刊,于是有了在《文史哲》发表的机缘。我对上述几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评论,纯粹只是基于他们在《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这是一本纲领式的、宣言式的书)一书中的观点,并不涉及这几位先生在其他著作或文章中的观点。
在此文中,我对余东海先生的主要观点比较认同,因为他主张会通西儒。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久,余东海先生《中国历史精神》一书完稿,请我作序,并希望直言不讳。我答应了,很快就写好《极高明而道中庸》一文发给余先生。其中,对余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的观点既有肯定,也有委婉地批评。不过,我的批评不能让余先生信服,余先生遂作《关于<中国历史精神>与萧三匝先生商榷》一文驳之。后因余书一时未能出版,故我的序言及余先生的驳论此前并未发表。近日,余先生将两文发表在儒家网上,并“欢迎旧雨新朋和各界人士评判”我们二人之是非,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故也将这两篇文章刊发于我公众号,欢迎大家批评。
需要说明的是,我历来写序务求简短,很多话题未及展开,若读者诸君需要了解我对儒家的看法,可浏览我的《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一文及近日所发《萧三匝评现象级畅销书<枢纽>:抽干“中国”,必然失魂》。主要是由于时间原因,我未及回应余先生的驳论,不过我对儒家的主要观点,在上述两文中已经论述的比较充分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
萧三匝

方今中国,道德沦丧,社会失序,人心唯恐。于是有新儒家起,欲挽狂澜于既倒,振颓风而复清明,正人心以返圣域,拨据乱以至太平。
东海余先生著书逾十部,立论宗旨,不外两条:一,高扬仁本主义以救人心;二,兼采自由主义以救政治。发心至诚,言辞剀切,既如填海之精卫,又似啼血之杜鹃。真儒常以天下自任,东海庶几近之。若以性情而论,东海之刚直激越又与熊十力先生仿佛也。
今世儒者,常以儒家辩护士之面目出现,此实为现实环境所激。然万事过犹不及,辩护过头,则易将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政制美化,以至让读者生出中国古代社会乃黄金世界之感。更有甚者,设计未来政制蓝图而以复古为鹄的。如此辩护,既非事实,又违中道。如此建构,一反孔子与时偕行之旨,可谓刻舟求剑、荒谬至极。以上两种举动,事实上也将驱儒家之同情者一变而为反对者。以我看来,如此行事,虽为护儒,实属害儒,故不智。此类儒者,名为新儒,实则旧儒,或曰陋儒、伪儒。
中国文化之重光,必经扬弃之淬炼。换言之,舍“转化性创造”并无二途。此乃当今见识澄明者之共识,也应为儒家之共识。既为扬弃,固不能不对以儒家为主体之传统文化予以批判,而批判之目的,实为发扬、创造。故,有表彰儒家之儒家,也有批判儒家之儒家,二者皆不可或缺。基于此种认识,我曾撰三万余字长文《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针对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贬斥者有之,褒扬者有之。拙文对东海先生的定位为“儒之时者”,由此可见我对东海运思立说方向之认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儒学西学,道术未裂。东海先生力图沟通中西,可谓气象恢弘者也。有论者讥其“六经注我”,可谓浅薄之论,盖因古往今来之思想者无不“六经注我”,故王船山尝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也。
我与东海之主张也有不同,其不同处在于:东海主张以儒家之仁本为主、以自由主义力倡之自由理念及其制度为辅,而我以为不必分主辅,自然演进、融混或更利于未来之中国。当然,此种演进、融混并非排斥个人主观努力之谓。我未必能说服东海,东海也未必能说服我。然君子求大同而存小异,“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况且,当下并非自由主义与儒家分裂之时代,实为二者相互携手共进之时代。
历史乃中国人之宪章,如何解释历史乃中国历代思想者之责任。东海新著《中华历史精神》取经史互参传统,深入中国历史深处,“阐旧邦以辅新命”,勉君子奋起担当,其赤子之心,可不察乎?通观全书,批判与建构并重,故多有创发。比如,在前人“六经皆史”论基础上创生“六经创史论”、“儒家写史论”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东海此前有《大良知学》行世。要言之,东海在本书中再次高举起道德理想主义大旗试图唤醒国人之大良知,由此以告别丛林社会。
然我也有不得不献疑者焉。唤醒国人之道德良知固然重要,但道德理想主义也潜藏着危险。此种危险表现为对人性过于乐观,且以道德感代替历史事实,故东海之论述偶有逻辑不自洽处。比如,东海认为“只有善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他又认为三代以后之政治大致走了一条下行曲线。若其关于历史走势之判断为事实,则中国人这两三千年之善心、善行岂非在逐渐消失?既然如此,又如何证明二十一世纪此种“善”必然复归?
再如,东海认为儒家思想促进科技进步,此论实非我能苟同。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思想整体上表现为实用理性,实用理性重实用不重逻辑思辨,故中国本无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抽象原理),四大发明不过是技术(实用方法)发明。俗言“科技”一词,将科学与技术混同,其实不利于科学思维之进步。若就本书篇章布局来看,我所寄望于东海者,恰恰在最后一章,即中西汇通之理论思考,惜东海于此着墨不多,或此项任务已在或将在东海其他著作中深入阐发?
“极高明而道中庸”,然则中庸也难矣。东海“大醇”,或有“小疵”?献疑数言,东海当谅我唐突也。
关于《中国历史精神》与萧三匝先生商榷
余东海
一
对于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国人来说,本书“颇多异议可怪之论”。例如,儒家写史论、圣雄造史论、文化决定论、善动力论、仁者无敌论、邪不胜正论、良知造命论、中华偏统论、恶必愚弱论等等,估计都会让大多数人莫名惊诧。
萧三匝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对儒家颇有研究、对东海颇为欣赏者,但对本书一些观点也难以接受,在所惠序言中有所批评。他说:
“唤醒国人之道德良知固然重要,但道德理想主义也潜藏着危险。此种危险表现为对人性过于乐观,且以道德感代替历史事实,故东海之论述偶有逻辑不自洽处。比如,东海认为“只有善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他又认为三代以后之政治大致走了一条下行曲线。若其关于历史走势之判断为事实,则中国人这两三千年之善心、善行岂非在逐渐消失?既然如此,又如何证明二十一世纪此种善必然复归?”
关于“善动力论”,我在书中和《马恩给罪恶披上华丽的外衣》文中已予论证。这个观点与“三代以后之政治大致走了一条下行曲线”的看法并无矛盾。首先,三代以后之政治文明逐渐下行,意味着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逐渐下降,但只要是儒家王朝,都有一定底线。其次,“善动力论”可以表述为:文明是道德的光明。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此消彼长,文明整体上仍然处于进步状态。
关于人性,儒家既证悟本性至善,又深知习性易恶,故对人性既不会过于悲观,也不会过于乐观。对于人性之恶,儒家既诉诸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又主张制度规范和法律制约,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
对于人性、人生、社会和历史,儒生自有“贞观”。纵然有时悲观,也不会绝望。懂得历史规律和仁本主义历史观,懂得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易理,就能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并且借助黑暗成就良知光明。当然,盲目乐观也是肤浅的。儒生深知人类恶习之深重,深知文明上升之一波三折,历史发展之好事多磨。
萧先生谓:“东海余先生著书逾十部,立论宗旨,不外两条:一,高扬仁本主义以救人心;二,兼采自由主义以救政治。”这个总结不确。于道德和政治,仁本主义皆可挽救之,重建之。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一大思想体系,可以充当中华辅统,其民主制度之优点可以供建设新礼制时参考和汲取,但在仁本主义体系中,自由并无主义的资格。
萧先生谓:“今世儒者,常以儒家辩护士之面目出现,此实为现实环境所激。然万事过犹不及,辩护过头,则易将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政制美化,以至让读者生出中国古代社会乃黄金世界之感。”
此可以毋忧。儒者为儒家文化辩护,理所当然。以四书五经为准的儒家思想,本来至美,不用美化。至于传统政制,当然不适合现代社会,不能照搬,就像不能照搬西制一样。古制西制,好的地方都不妨为我所用。古制西制中没有的,只要有必要,还可以新创新建。强调“礼时为大”和“礼以义起”,反对“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的复古主义,正是儒家的制度精神。“儒家十诫”中,复古主义就是其中一戒。
古往今来附佛、附道、附耶的邪教都非常多,唯独没有附儒的邪教;古今中外多种学说宗教都曾经导出极权暴政,唯独儒家没有极权暴政—儒家王朝偶有暴君如桀纣周厉隋炀等,但都很快被革命或推翻。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儒家特别中正,正义性真理性至高无上。在儒家框架内,邪恶残暴的人物,即使占据君位,也脆而不坚或坚而不久,很快就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萧先生谓自由主义与儒家(仁本主义)可以相互携手共进,此言甚是。但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不能主次不分。王道中华,在文化上是一元化和多元化的统一:儒家作为立国精神和指导思想,拥有宪位和独尊的地位,这是一元化;中国诸子西方百家,包括各种宗教乃至邪教,都享有言论信仰自由,这是多元化。两者统一构成王道的有序自由,秩序品质和自由品质双优。
在文化品质上,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有高低之别。盖仁为人之本,仁性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因。仁本主义之下,内圣外王同归于仁,道德政治同本于仁。以仁为本,于个人可以成德成圣成就道德最高境界,于政治可以建设王道通往太平大同理想,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并重。比较而言,自由主义就逊色多了。
仁本主义政治是王道,道德资源特别充足,强调自由和秩序双优;制度为礼制,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保障:官员受到礼的约束,自由度较小;民众只受法律制约,自由度更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可以加一句:限之以法。礼制包括刑法。
仁本主义承认自由的重要性,内而追求道德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道德自由的最高境界;外而追求政治自由,《洪范》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的王道政治,可以给自由提供最好的保障。当然,自由和秩序两面一体,仁者追求自由和秩序双优。
自由主义追求的也是有序自由,但民主法治的制度品格远逊于礼制德治的制度品格,双方所能提供的秩序品格自有差别。而制度、秩序与自由,三者的品格有一致性。自由主义提供的自由,最好也有限。同时,作为自由主义哲学背景的个人主义,道德资源非常有限,可以培养善人,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
萧先生谓:“东海认为儒家思想促进科技进步,此论实非我能苟同。”关于原始儒家思想对科技进步有稳妥的促进作用,书中已有说明,兹不赘。
总之,儒家直面所有问题,包括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外部问题和自身问题。若儒家文化真有问题,历代圣贤绝不会执迷不改讳疾忌医;若历代圣贤真有问题,当代儒者也不应文过饰非遮丑掩臭。但若儒家文化和历代圣贤没有问题,儒者也不会故作谦虚清高态,坐视圣贤被误会。
二
萧先生谓:“有表彰儒家之儒家,也有批判儒家之儒家,二者皆不可或缺。”儒学当然可以批判,欢迎批判,不同儒生之间也会相互批判,但没有儒生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圣经圣人,因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在原则上,儒学是中学,不偏不倚,特别中正;是圆学,无缺无漏,特别圆满。她可以让个体成德成圣,圣德无极限,好上加好,圣而不可测之谓神;可以将政治导向王道,王道无止境,优而更优,直到全球大同。
别说自由主义及耶教,别说道家学说,连佛教包括大乘圆教也有软肋和罩门–政治即其软肋,即功夫练不到的地方。古今中外任何伟大的学说都各有软肋罩门,唯儒学没有,故《中庸》赞美“大哉圣人之道”,又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学是真正大圆满之学也。
说儒学圆满,是理论的圆满。在儒学的指导下,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都可以达到至高。圣境大中,王道至正,都是其他学派宗派指导不出来的。释尊老子极高明而未道中庸,未免逊于孔子;民主法治颇文明而又多弊端,毕竟低于礼制。
说儒学圆满,是天理良知的圆满,与某个人某件事的圆满并非一回事。不过,天下也有圆满的事和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乐尽善尽美,就是圆满;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也意味着道德人格的圆满。
所有儒家圣人,无论有位无位,都德性圆满,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集儒学大成,更是大圆满者。孟子赞:“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又引宰我子贡有若之言共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公孙卫》)难道孟子智不足以知圣人,或是故意夸大其辞?
儒学的圆满是本质上的圆满,是抓住了宇宙生命的本质,抓住了道德的最中心点,抓住了大象的全体,那就是乾元道心—两词同义,于天为乾元,于人为道心。对这个东西,老子只抓住了一半,所以他一方面很了不起,受到孔子高度推崇;一方面有破绽,不为孔子所皈奉。孔子抓全体,故能集大成。
佛教称佛陀说法之音为圆音。圆是缜密、周全、圆满义。儒家圣经圣言也可称圆音。孟子说仁者无敌,东海曰圣言无漏。圣经圣言中正圆满没有漏洞,是儒门共识。圣德大而化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圣境广大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古往今来没有比圣德更圆满的德、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人了。可以断言,看圣人有漏,必是看的人自己有洞。儒经圣言更没有糟粕。说儒经有糟粕者,恰恰是自己学术不精。注意,圣言无漏,仅指圣言,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言。他们的每句话每个观点,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和真理性,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其他儒言则未必,甚至贤人之言也可能有偏差,如孔门诸贤某些言论就不够中正。
除了圣学,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即使自圆其说,都是有漏之学,有大大小小的偏差或错误。理论上说不圆,实践中易出偏、出错甚至犯罪。而它们的个体或社会理想,或理想性不够,道义性不强,或难以付诸实践,属于空想。
儒家对圣言的推崇,对孔子的崇拜,是经过其良知验证的。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一些儒友认为儒学局限于人学,认为佛教大乘圆教才是真正的圆满之学,是受了佛教误导而丧失了文化道德自信。佛教虽为正教,终究有其宗教局限,高妙而不中正。说伏羲文王孔子和历代圣贤是菩萨应化世间、说孔子是儒童菩萨,又将儒家说为人乘,皆属宗教性的狡狯和自大。儒者一笑了之可也。
三
儒学即仁学,仁本主义学说。本书各种“奇谈怪论”,建立在一个更大的、根本性的“怪论”之上,那就是仁本主义历史观。
何谓仁本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仁是人类的尺度。归根结底,仁是人和万物的尺度。唯有仁,才是宇宙生命的本体、本位和第一性之“物”,唯有仁才有主义的资格,故称仁本主义。唯有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是最中正的,唯有仁本主义体系,才是衡量和辨别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最高标准。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详见东海《仁本主义》一书。
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脉相承,以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历史,是为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文化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文化意识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先进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落后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儒家社会发展较快,儒家受尊重程度、文化影响度与政治社会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意识有反作用。
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同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会发展总趋势: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和豪杰是历史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其五、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成德成圣,外成就人类的文明,内成就良知的光明。
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良知的光明度。
其六、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价值观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有阻碍作用。儒家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又以良知为人的尺度。归根结底,良知是最高价值标准。
上述理念在本书和东海正在创作的《这个故事》一书中,都有所说明和阐发。例如,禅让制和原始大同王道的实践,就从侧面证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并说明了唯仁史观的正确,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这可以说是“尧舜禅让”故事的一个意外收获。
又如,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春秋时鲁国穆叔的三不朽说,就是很好的解说。穆叔与晋国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可谓“不朽”。穆叔认为这只是“世禄”而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功立言,归根结底,无非立德,立德即成德。
唯仁史观的内容和理念,在本书儒家写史论、圣雄造史论、文化决定论、善动力论、仁者无敌论、道德造命论等等异议可怪之论中,都有相应说明和论证。
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文明和道德是血肉交融的关系。昧于中华文化,必然昧于中国历史;昧于历史,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历史,掌握历史精神,是深入中华文化、证悟道德真谛的重要途径。
太史公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春秋》精神、王道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也是萧三匝先生所说的救人心、救政治、救苦救难的精神,去恶消罪,莫此为重。盖罪恶与苦难成正比,能消去罪恶一分,就能化解苦难、提升幸福一分。
2017-3-5余东海于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