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从当事人公司的会议室走出时,才发现走廊里的灯都已经开了。
天黑了。走出大楼,车声如潮,黑夜的面纱掩不住雾霾带来的压抑感,人流匆忙,提着公文包徒步到地铁站,这一天已经接近尾声,但人们还未曾享受到宁静的黄昏,这就是北京。
十号线长春桥上车,北土城站倒车,八号线上,旁边一个可爱的小女人在用手机玩植物大战僵尸,她收集阳光,栽培向阳花,然后用豌豆射手和土豆雷构筑防线,那么地专注。我看着她在拥挤的车厢里自得其乐。
她让我想起初恋女友,那是一个几年前的夏天,初恋女友到兰州看我,我教她玩植物大战僵尸,性子急的我总是催促她指挥她,还说她笨,玩着玩着,她突然躲进洗手间哭,花了很久才哄她出来,她还不忘一边哭,一边谴责我。现在回想起那场面,依旧觉得她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孩子。然而物是人非,我们已经天各一方,她已身为人妻,并发誓永不见我。
不懂得为什么有些前尘往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烟消云散,就像我们总是觉得人生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却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尽头。在向她告别时,我眷恋着远方,立志于投身宏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去,而在离开她的两年多之后,我孤身在北京,为了生计做律师,像一只蚂蚁,乃至做自己想做的公众号都不得不发广告赚钱,是我努力不够能力欠缺的缘故,才沦落到如此地步么?
我的人生又能走到什么样的境域?时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畅想,时常被巨大的焦虑感控制着,像是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像是钻进了套子里的人,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来到北京,而直到现在,没有感觉到自由,更谈不上快乐,我是这个城市的囚徒。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有什么意义?等死去的时候,又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呢?
二
其实毕业前夕求职的目的地并不是北京,而是深圳,到北京只不过是为了倒车。在出发前,对比了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综合指标和律师执业环境,又考虑到北京办理律师执业困难重重,放弃了北京、上海和广州,选择了到开放和包容的深圳去,出发时身上只带了1500元现金,决心有两条:其一,绝不再向家里拿一分钱;其二,即使捡瓶子洗盘子也要坚持下去,绝不走回头路。给在深圳工作的初中同学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一下住处,告诉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强调自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
去深圳的车票在呼和浩特就已经买好,下午到北京,晚上就会上车,然而一个意外的工作机会让我留在了北京,而且就是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才收到这条拦我南下的微信,这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
那一天是2014年3月29日。
到11月,已经发了七个半月的工资,我也成为了一名实习律师,查了一下自己在北京新办的银行卡,到北京之后总收入是58068元人民币。

三
“一个从内蒙古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来到北京,去寻找他想要他的自由和理想,而以他现在的能力和智识,他得到的只是困惑、焦虑以及生活的窘迫。”
不知道采访我的记者会不会在他的稿件中这样描述我,然而这就是我的真实状态,台湾经典杂志拍摄蚁族专题的记者曾到我的住处—— 一个名为“双泉堡”的城中村。
结束拍摄走出城中村时,他提醒我说,人久住在这里会生病的,我清醒的知道这点,我也憎恨这里:垃圾乱丢,男人在夏天不穿上衣,各种纹身,村子里有好几家KTV夜场,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各色坐台女郎,她们经常在KTV门口和她们的客人告别,一副亲热的样子,像是依依不舍的恋人,就像这个城市的雾霾,令人作呕的虚空假面。
这个城中村真实的反映了我的生存状态,也让我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从农村的社会底层转变为城市的社会底层,而且是以漂泊者的身份,如果我在这座城市里死去,不会有人记得,不会有人哭泣,人们将匆忙而过,如这座城市的地铁,来不及为北漂母亲潘小梅哀悼,就沿着地下的黑暗继续前行,呼啸中无悲无喜。
四
来北京之后借过两次钱,第一次向一个朋友借了两千,第二次向两个朋友借了五千,还有一次从单位预支了五千元的工资,前几天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外债,并且给家人邮寄了五千元,同时资助一个西藏的藏族男孩读书,每学期一千元;给身陷囹圄的两位同道朋友各存了一千元,早些时候给另外一位宋庄艺术家的家人存了两百元,这三位朋友只见过其中的一位一面,他姓宋,湖北襄阳人,之前我们一直在网络上保持联系,在他被捕之前我们通电话,他还说要有些事情找我谈谈,说是个人私事,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出事了,想起这未成行的谈话,令人不免唏嘘世事难料,也颇觉遗憾心痛。
总有更糟糕的境遇,但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傅雷选择了自杀,马思聪选择了出逃,而他们三个都是普通善良的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必须为这种选择承受代价,也许他们的大多数同类乃至他们的家人都会将他们的行为视为愚蠢可笑的蚍蜉撼树,但即使是这种局面也不能让他们的受难打上半点折扣。面对这样血迹斑斑的现实,无力再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曾经在给艾某某的汇款单上留过这句话,曾经给姓宋的朋友邮过圣经,但是如今我面对他们的境况,所能做的,就是拿出一点钱。
大概是岁月让我变得保守,曾经激进地像一只眼红了的兔子,而如今,两手空空,站在北京的雾霾中,叹息这个世界有雾霾,也深觉自己心中也有雾霾。太多的时候,无限惭愧,我憎恨自己。
五
哥哥的腿被马踢断了,已经在医院里他住了四十多天,直到今天(2014年11月25日)才知道,父亲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曾经勇猛的像一匹狼的蒙古牧民在电话的另一头哭了。在一家私人接骨医院花了一万多元,耗费了四十多天之后,结果在去另外一家西医医院拍片时才发现,哥哥的骨头没有接上。
骑马者是我的哥哥,羊群是我家的。
牧区的生活很辛苦,不够浪漫。
我曾经为哥哥写过一首诗,名为:
《请你带我回草原》
老去的芨芨草
根部
母花纹蛇睡梦香甜
祖国的内蒙古草原
在牧人的吆喝声中暮色深沉
那最响亮的声音
来自瘦小的毕力格
他醉意浓浓,小脸儿通红
哼着老牧人们听不懂的情歌
红鬃马上骄傲的毕力格
是我亲爱的老阿哥
他一手拉扯大的羊羔卖掉时
他忍不住哭了
毕力格,毕力格
一个意为“聪慧”的蒙古名字
毕力格,毕力格
我亲爱的老阿哥
请你带我回草原
让我们像羊羔一样
在草原上撒个欢
愤怒于家人剥夺了我的知情权,今年哥哥已经因为身体原因住了一次院,家人也是隐瞒情况,后来实在是情况危急,姐姐才电话告知,也是因为那次,单位提前主动给我预支了工资。
哥哥上次生病家里花了几万,而今年内蒙古牧区的牛羊价格大跌,为了保值没有大规模出售,家里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现金存款。这次事出意外,父亲没想到在花费了一万多元之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他不得不给我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向我求助,大概是二十天前,他说自己去通辽市检查身体,让我帮他充100元话费,我当时故作慷慨地充了200元,却没想到家里出了事。
于是在2014年11月25日,我来北京之后第三次借钱了,我给朋友打电话,开口借一万,朋友爽快地要汇两万,我婉拒了,先借一万就好,自己身上还有一些。
其实借钱是一种验证、加深和巩固友谊的重要方式,这是我借钱两次之后的经验,也是我在第三次借钱时几乎毫不犹豫的原因。借钱也是一种激励,一种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你必须为了把钱还上去努力挣钱,在这之前还债的责任也决定你不能自杀,必须有个交代。对于夹缝中的北漂而言,借钱未尝不是一种防止自杀的有效策略。
六
经常想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然而知道贫穷已经扼住了自由的喉咙,必须为了钱,为了对家人的责任去打拼,乃至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去挣钱。钱是一个好东西,经济自由是自由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打算流浪,并且准备过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
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未来会是一个有钱人,会挥金若土,像雅典的泰门,或像曾经的鄂尔多斯人,曾经期许过待腰缠万贯时。
想走在路上放声歌唱,想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来一场穿越世界的旅行,有很多梦想,也未敢忘记最初的梦想和出发时的模样,虽然此刻在北京这座拥有两千多万囚徒的监狱服刑。
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而我不是海子,虽然也身陷这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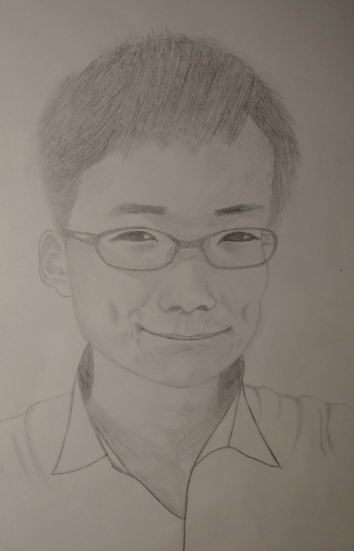

这是故乡的河流辉腾郭勒,意为“冷河”,这条小河最终注入渤海。

本文写于2014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