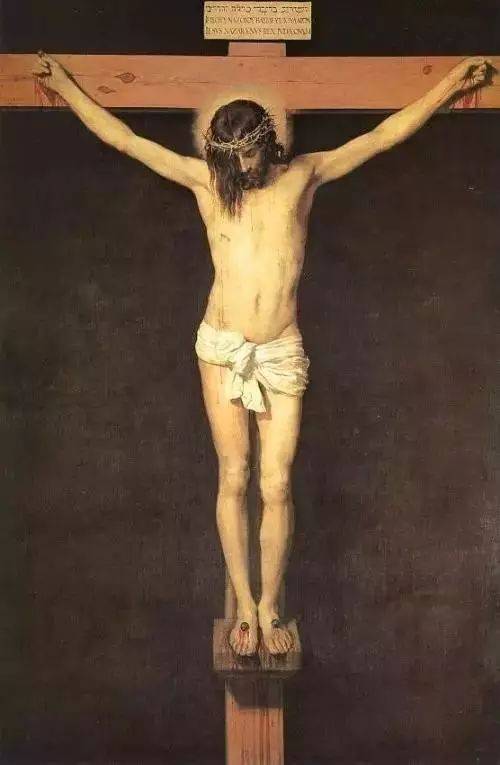
人生七十古来稀。若是强壮,我们或有机会活到七八十岁。
无论是新冠疫情、东航坠机,还是乌俄战争,都提醒我们坟墓里也埋葬着很多不满五十岁的人。
死亡不仅在肃杀之秋后,也可以在春天的任何时刻,它不受时间的限制,死亡的使者似乎就在我们的门外守候,可以随时推门而入。
我是1989年出生,与我同龄相识相熟的人中,就已经有四位去世了,而我还不到三十三周岁。
本科在读时,就有一个初中同学和本科同学因病去世,这两个女孩的生命停留在二十岁出头的年华。
初中同学是我暗恋过的女孩,初中时她就落落大方、身形窈窕,笑靥如花,记得初中时每见到她就莫名地心动和喜悦,至今仍感叹生命本身是何其地美好。她如同在春天被风吹落的花瓣: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本科时的那位女同学却总是忧郁,能感受到她的愁烦,我当时就爱读书,把克里希那穆提的那本《爱的觉醒》借给她,她还书时和我说:“你是想告诉我悲伤的终点是爱吗?”
“悲伤的终点是爱”是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当时哑然,心里感慨这真是一个悲伤的女孩,那么厚的书,偏偏挑出这一句。
后来她突然请假回家,再传来的却是她去世的消息,同学们都很意外,这是集体面对死亡的经验。记得在一个宿舍里,大家谈论这件事,一个感性的同学忍不住放声哭起来,其他人也都默默流泪。
我们不知道她去世的原委,至今仍感觉她只是远行走了,她的离世只是一个假消息,只是一个离开的借口。再询问老同学,说她当时已是肺癌晚期,手术失败了。
2021年,本科同班同学又有一位去世,他豁达,喜欢抽烟,大大咧咧,来自贵州的苗族。我是翻看他的朋友圈才发现他去世的,是他的妻子给亲友发的告知。
令我遗憾的是,之前他发微信给我,我没有及时回复,如今却已经是阴阳两隔。他是因为直肠癌去世。
我的亲哥哥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本来是我的学长,后来留级,成为我的同班,他学业成绩一般,常抄我的作业。
哥哥小学肄业,因为有一次语文老师课堂上念了他错字百出的作文,他感到被羞辱,小蒙古汉子的脾气发作,当场撕了作业本,与老师闹翻,后来就坚决辍学。
哥哥在2016年去世,还不到29周岁。那天凌晨我刚入睡,突然电话响,以为已经到清晨,是闹钟响了。清醒后看到是堂姑的电话,我当时就心里一惊,知道恐怕是哥哥病危,哥哥自2014年第一次心肌梗死发病之后就反复住院,之前就病危过,我接起电话,堂姑的声音犹豫:“晓明,你哥哥状态不太好”,她顿了一下,“你已经信主了,我就和你直接说吧,你哥哥刚刚没了。”

那夜我彻夜哭泣,凌晨五点时睡着了,六点醒来买了当天的机票,下午五点多,我终于赶到县城的殡仪馆。
那天晚上我围着哥哥的棺椁一圈圈地转,感觉阴间的门都是敞开着的。第二天早晨一个简单的仪式后,哥哥就被火化了。
我亲手抱着他的骨灰盒,安放在草原上挖出的坟穴里,看着人们铲土堆起坟丘。那个坟丘上,冬天覆盖着雪,夏天长着草。

如今春天到了,雪渐渐消融,草还在地下潜滋暗长。那片草原特别美,好过很多昂贵的墓地,虽然人生际遇差异万千,但是在死亡面前,我们是如此平等。
根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在去世前一直在听《葬花吟》,这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强人在面对死亡之时,也表现出他的软弱。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又去哪里呢?是否有审判呢?死亡之后只是尘土土,还是天国地狱之别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面对和思考死亡,更是有很多人忌讳谈论死亡,然而我要在春天里谈论死亡,因为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如同一句西藏谚语所言:谁知道明天和死亡,究竟哪一个更早到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