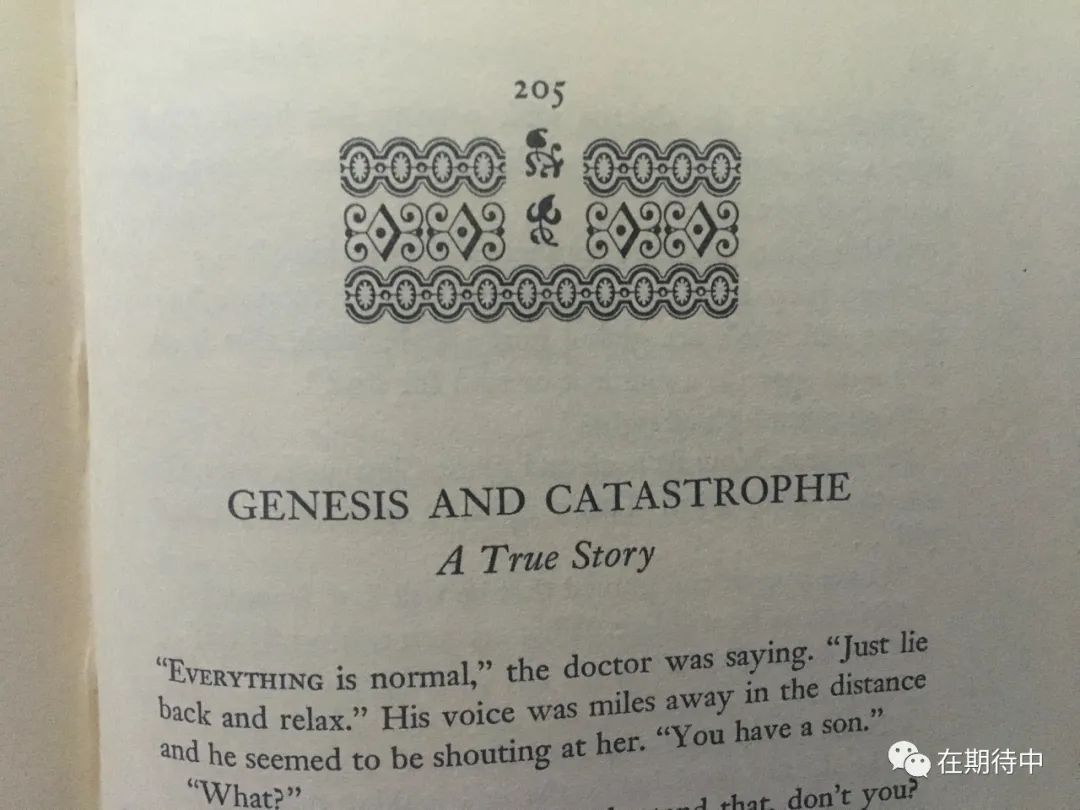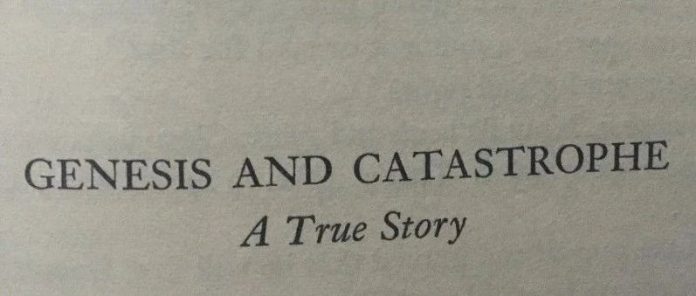起初与灾变:真事儿
“都正常,”大夫说,“好好躺着休息吧。” 大夫的声音似来自八荒之外又如此振聋发聩。“是个儿子。”
“啊?”
“你生了个大胖小子。能听懂吧,啊?大胖小子!你没听见他哭么?”
“他没什么问题吧,大夫?”
“他没什么问题呀。”
“那你让我看看他。”
“你待会儿就能看啦。”
“你确定他没问题吗?”
“我很确定。”
“那他还在哭么?”
“你先好好休息。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怎么不哭了,大夫?他怎么了?”
“你别激动,好么?一切正常。”
“我想看看他。你让我看看他呗。”
“您呐,”大夫一边拍拍她手,一边说,“您刚生了个健健康康的大胖小子。怎么我说话你还不信吗?”
“那内个女的站我孩子旁边儿干嘛呢?”
“你的宝贝儿,不得漂漂亮亮抱过来给你看么,” 大夫说,“我们给他简单洗洗,正常的。你消停会儿,行么?”
“你发誓我孩子没问题。”
“我发誓。来、来,快躺下休息吧。眼睛闭上。诶对,快眼睛闭上。对啦。这不好多了么。听话嘛……”
“我之前一直祷告啊我就祈祷他能活下来,大夫。”
“他怎么就不能活下来了?瞧你这话说的。”
“其他几个就没活下来。”
“啊?”
“我其他几个孩子一个都没活下来,大夫。”
大夫站在床边,低头看着这个年轻女人的脸,筋疲力尽苍白的脸。他从没见过这女人。这女人和她丈夫刚搬到镇上来。这是个边陲小镇,镇上旅店老板娘也在诊所,是来帮忙接生的。老板娘之前跟大夫说过,说这女的丈夫就在此地海关办公室上班,大概三个月前两口子突然拖着口箱子、拎着个包儿就来住店。那男的是个酒鬼,按旅店老板娘话说,是个牛气冲天、泼赖蛮横的酒饭之徒,但那年轻女人却是温柔敬虔。而且那女的心里很苦,从没笑过。跟店里住了这么好几周,老板娘就没见她笑过一回。再就是有闲话说那男的已经是三婚了,之前一个死了,一个跟他离了,因为他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这都只是些闲话。
大夫弯下腰,提了提被单,盖住女人胸口。“你别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轻言细语说,“你生了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生那几个当时也这么说的呀。但我全没了呀,大夫。就这么一年半时间,我三个孩子全没了呀,所以您真别怪我心里着急。”
“三个?”
“是啊……这是第四个了……四年了……”
大夫局促地挪了挪脚,光秃秃的地板,更显不安。
“我觉得您不懂我什么心情,大夫,是全没了呀,我那三个孩子,慢慢地就那么一个接着一个,没了呀。我现在眼前都还能看见他们呢。古斯塔夫的脸,我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真躺在我床边儿一样。古斯塔夫可招人爱了,大夫。但他总是病恹恹的。小孩子总是病恹恹的,但你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看着他们那样儿,可太受罪了。”
“我懂。”
女人睁开眼,盯着大夫看了好几秒钟,又闭上了。
“我小女儿叫艾达。她是圣诞节前几天走了。这不就才四个月前呢么。我多希望,你要是有机会能看上一眼艾达就好了,大夫。”
“你现在有个新生的宝宝啦。”
“可你知道艾达长得多漂亮么?”
“啊,”大夫说,“我知道。”
“你怎么能知道呢?”她大吼。
“我相信她肯定长得特别可爱。因为你刚生的宝宝也特别可爱。”大夫背过身去,从床边走开,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四月午后,潮湿灰暗,他能看见街对面的屋顶,还有硕大的雨滴打在红瓦上四溅开来。
“艾达才两岁呀,大夫……而且她长得那么漂亮,我早上起床给她穿好衣服,直到夜里把她哄睡上床,整天整天地我都看不够呀。我是又爱又怕,生恐她会遭什么不幸。古斯塔夫走了,我的小奥托也走了,就只剩下她了。有时我半夜爬起来,趴在她摇篮上,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就为了听听她是不是还有气儿。”
“你好好休息,”大夫一边走回床边,一边说,“请你好好休息,好么。”女人面无血色,煞白,口鼻周围还显些许青灰。几缕湿发垂挂前额,紧贴皮肤。
“她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又怀上了,大夫。艾达死的时候,这个刚出生的才怀上四个月。‘这个我不想要了!’葬礼之后,我大喊大叫:‘这个我绝对不要了!我送走的孩子够多了!’然后我丈夫……他在客人们中间走来走去,跟散步似的,手里还端着一大杯啤酒……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克拉拉,是好消息。’你能想象那画面吗,大夫?我们家老三才刚刚下了葬,他就端着杯啤酒杵在那儿跟我说他有好消息。‘今天我已经调去布劳瑙啦,’他说,‘所以你赶紧收拾东西吧。这对你来说也是个新的开始,克拉拉,’他说,‘你能去个新地方,而且换个新大夫。’”
“您先别说话了。”
“你就是他说的这个新大夫,对么,大夫?”
“没错儿。”
“那么咱这儿就是布劳瑙。”
“对。”
“我好怕,大夫。”
“不用怕。”
“我这老四能有多大机会活着?”
“你真不能再有这些想法了。”
“我控制不住啊。我敢肯定这就是个什么遗传,才导致我的孩子们都死了。肯定是。”
“你别瞎说。”
“那你知道奥托出生的时候我丈夫怎么跟我说的吗,大夫?他走进房间,看了看摇篮里躺着的奥托,然后说:‘我的孩子怎么个个儿全都长得这么瘦小、这么虚弱?’”
“他指定不能这么说。”
“他脑袋都凑到奥托摇篮里了呀,就像观察个小畜类儿似的,他还说:‘我意思主要是他们的品种为啥不能更优良一些呢?我没别的意思。’结果三天以后,奥托就死了。我们白天给他很快受了洗,当晚他就死了。接着古斯塔夫也死了。然后艾达也死了。全都死了,大夫……一转眼整栋房子都空了……”
“别多想了。”
“这一个也长得特别瘦小吗?”
“这个孩子正常的。”
“但个头还是小?”
“小是也许有点偏小。但个头小的经常比大个子更结实呢。您这么想啊,希特勒太太,明年这个时候他就该学走路了。想想这个,是不是心里舒服多了?”
她没应声。
“再想想,两年之后,他话匣子差不多就打开了,那话多的,能把你烦死了。对了,你给他取好名字了吗?”
“名字?”
“对啊。”
“我不知道。我不好说。我记得我丈夫说,如果是个男孩儿的话,我们准备叫他阿道夫斯。”
“那他小名儿就叫阿道夫呗。”
“对。我丈夫觉得阿道夫斯挺好,因为听起来像阿洛伊斯。我丈夫叫阿洛伊斯。”
“好得很。”
“诶不对!”她大喊,突然从枕头上蹭起来。“当时奥托出生了,他们也是问我这个问题,一模一样!你们急着问名字,就是因为他快死了吧!快,快给他受洗!”
“哎呀,您呀,”大夫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扶着她肩膀。“您完全误会了。我给你保证,你误会了。我就是个爱打听事儿的老人家,你别见怪。我就喜欢聊人的名字。我觉得阿道夫斯是个挺不错的名字。是我最喜欢的名字之一。来,看——给你抱过来了。”
旅店老板娘抱着孩子,高高捧在她丰满的胸口上,举步生风穿过病房,走到床前。“小宝贝儿来啦!”她声音洪亮,眉开眼笑。“亲爱的,你想抱抱他吗?还是我给你放你旁边?”
“他裹好了么?”大夫问。“这房间里可冷啊。”
“当然裹好啦。”
小婴儿裹着个白毛毯,严严实实,只露出个小小的粉红脑袋。旅店老板娘把他轻轻放在床上,挨着妈妈。“母子平安,诶,”她说,“你呀,你就好好躺着休息,好好瞧着你的宝儿,越瞧心里越美。”
“你肯定越看越喜欢,”大夫微笑着说,“你看看你的小宝宝多健康。”
“瞧这小手,多可爱呀!”旅店老板娘啧啧称叹,“瞧着手指头多长、多嫩!”
孩子的母亲却纹丝不动。她甚至连头都没转过去看一眼。
“快看呐,嘿!”旅店老板娘大喊一声,“他又不咬你!”
“我不敢看。我怕。我不敢相信我又有个宝宝了,而且他健健康康。”
“别犯傻了。”
慢慢吞吞地,这位母亲才转过头来,看着她身旁枕头上躺着的宝宝,看着这张小小的、出奇安谧的脸。
“这真是我的宝宝吗?”
“当然是呀。”
“啊……啊呀……他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大夫转身走到工作台前,开始收拾家伙什儿,装包。母亲躺在床上,目不转睛看着孩子,微笑轻抚,发出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安神。“哈喽,阿道夫斯,”她低声细语道,“哈喽,我的小阿道夫……”
“嘘!”旅店老板娘突然说:“听!我听见你丈夫来了。”
大夫走到门口,开了门往过道里看。
“希特勒先生?”
“您好。”
“您请进。”
一个小个子男人,穿了件深绿色制服,踱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房间,环顾四周。
“恭喜啦,”大夫说:“是个儿子。”
那男人蓄着连鬓胡子,几乎络腮,就像奥匈帝国那个弗朗茨皇帝的样式,身上浓浓的啤酒味儿。“儿子?”
“对。”
“他怎么样?”
“他挺好。您太太也挺好。”
“挺好。”这位父亲转身走向她妻子床前,说是龙骧虎步吧,又有点儿小心翼翼的样子,怪怪的。“那什么,克拉拉,”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捋捋胡须:“还顺利么?”他弯弯腰,看了眼孩子。然后往下更弯了弯。他就跟抽筋了似的,一下儿一下儿地往下弯腰,直到脸都快怼着孩子脑门儿了,不到一尺距离。妻子侧躺在枕头上,抬头盯着他看,眼里带着某种恳求。
“这小孩儿的肺可不简单,”旅店老板娘宣布:“你是没听到他刚出生那一嗓子有多亮。”
“但是……我的 神啊……克拉拉……”
“怎么了,亲爱的?”
“但是这个的个头比奥托还小啊!”
大夫快步上前。“这个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他说。
慢悠悠地,这位做丈夫的直起身来,背过床去,看着大夫。他似乎有些纳闷儿,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你骗我也没用啊,大夫,”他说:“我很清楚这什么意思。周而复始,一切又重演。”
“你好好听我说,”大夫说。
“你别——你知不知道之前那几个都什么情况,大夫?”
“其他几个,你就都别瞎想了,希特勒先生。给这孩子一个机会。”
“可他这么瘦弱!”
“爷们儿,他才刚出生呀。”
“就算是……”
“你这人干嘛呢你?!”旅店老板娘大喊道。“这么多废话你就是想这孩子死吗!”
“别吵!”大夫斥责。
母亲已然啜泣不止,继而失声抽噎,身体直哆嗦。
大夫走到做丈夫的身旁,一手搭他肩膀,耳语说:“对你媳妇儿好点儿吧,算我拜托你了,生命可贵啊。”说完重重捏捏他肩膀,然后暗暗把他推到床边。丈夫犹豫了。大夫使更大劲儿捏了捏,每根手指都在迫切给他递信号。最终,勉勉强强地,丈夫弯下腰,亲了亲妻子面颊。
“好啦,克拉拉,”他说,“别哭了。”
“我一直努力祷告,祈求他可以活下来,阿洛伊斯。”
“嗯。”
“这好几个月我每天都上教会,跪在地上求,求主赐这孩子生命。”
“是,克拉拉,我知道。”
“死了三个孩子了,我已经承受不了了,你还不懂吗?”
“懂。”
“这个必须活下去,阿洛伊斯。他必须,必须……哦 神啊,求祢怜悯他吧……”
(完)
——江文宇译自罗·达尔短篇小说集《亲亲》(“Genesis and Catastrophe: A True Story” from Kiss Kiss by Roald Da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