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与巴特
编者按
Barth-Studien
本文通过解读朋霍费尔对巴特的批评来理解巴特的“启示实证论”思想。作者首先指出,朋霍费尔理解的巴特没有把基督教与“此世”联系起来,巴特的启示观不能符合及龄世界的需要。随后,作者点明,巴特诟病一战时期德国神学家的神学以人为中心,他的启示观强调神人之间的鸿沟,这样一种“负面”的神学倾向促使巴特在道成肉身的概念上积极展开讨论。作者提出,巴特对耶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的双重肯定影响了对上帝神性的定义,这个问题长期困扰巴特,直到他在《教会教义学》第二、四册中清晰阐明,道成肉身并不影响上帝的神性。直到晚年,巴特依然坚持,启示并不发生在历史之内。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巴特强调的重点并非如此。巴特想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启示的谓词,而非相反。关于对作者相关观点的批判,参本微信公众号之前推送的吴国安博士的相关文章。
在评价朋霍费尔和巴特的“启示实证论”批评时,作者注意到并指出,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教会看作基督的身体,但在信仰群体中寻找启示,岂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返回了施莱尔马赫?这个未被作者解决的问题暗示了巴特和前辈之间复杂的思想关联,作者本人更是借这个问题表达了在“宗教多元”时代如何理解巴特的深思。
原文载于鄧紹光、赖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巴特神學的再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241-260。推送时已获道风书社和作者本人授权,在此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林子淳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引言
當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在《獄中書簡》表述他對非宗教性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的意見時,曾三次批評巴特犯上了「啟示實證論」(positivism of revelation)的謬誤(1944年4月30日、5月5日及6月8日)。1、 2可是,他本人卻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距德國被解放前不久,遭納粹德軍處決,未有機會澄清其說法,以致巴特亦歎謂:
現今他只遺留給我們他信中令人困惑的說法……譬如說,他從我的思想中找到所謂的「啟示實證論」,準確來說是甚麼意思,還有特別的是一種非宗教性語調的計劃可如何實現。3
然而,巴特在其後期著作中,卻有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嘗試回應朋霍費爾的批評。4 本文目的則旨在嘗試瞭解「啟示實證論」的意思若何、簡單回顧巴特啟示觀的發展、檢討此批評能否切中巴特的思想、以及巴特對此的回應。5
「啟示實證論」的意義
朋霍費爾使用「實證論」(positivism)的其中一個意思,是要指出巴特在未有清楚闡釋某些信念前,便要求人們視之為權威性資料「照單全收」,使得一些所謂啟示出來的觀念被貶損為「設定資料」(mere data, posita)而已。6 如朋霍費爾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的信中所說:
巴特是第一個開始批評宗教的神學家——這一直是他真正的大成就——但是他以啟示實證論者的教義來取代之,結果是說:「要么就接受,否則就留下」(Take it or leave it);例如「由童貞女所生」、「三位一體」等等,每一點在整體中都是同等重要和必要的部分,你必須把全部整體都吞下去,否則就都不吃。7
這裏所謂「設定資料」,是相對於有意義的「資訊」(information)來說的,意即那些所謂啟示的觀念只是一些抽空的材料罷了,沒有對人產生任何意義;更準確地說,是對這個「世界」不發生任何關係。普倫特(Regin Prenter)精闢地指出,每當朋霍費爾以「啟示實證論」來批評巴特以前,無不先讚許他與自由神學那種「宗教化」的福音決裂。8 朋霍費爾認為,其身處的是一個走向無宗教的時代,並且在他以前的一千九百多年來,基督教宣講與神學是建基於一個「人是信奉宗教」(religious a priori)的前設中。9 故此,自由神學與護教學的謬妄,在他看來,便是要在人的內心深處(inwardness)闢出一處地方,讓「宗教」可安然地穩立在其上,免受批評。可是,朋霍費爾認為,這種日子已悄然遠去,現在人所身處的是一個「及齡世界」(world come of age),「人是信奉宗教」此一立論不復存在,因此,他讚揚巴特說:
巴特是第一個人能看出這種錯誤,他認為,所有的努力(無形中駛進自由神學的海峽去),其目的只在清理出一塊地方好讓宗教居住,或讓宗教去和世界對抗。10
故此,他提出一種對基督教的「非宗教性詮釋」(religionless interpretation),即是說要尊重此及齡世界、並找出上帝與其之關係。11可是,他認為巴特雖然是在這方面的啟導者,卻沒有達致一個令他滿意的答案:
巴特是第一個在這方面動腦筋的人,他仍未達到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只是他已達到啟示實證論,這在本質上仍是一種保守主義!對沒有宗教的人,或對一般的人來說,這情形沒有甚麼新奇。12
因此,我們可簡單地總結,對朋霍費爾來說,巴特的問題是他仍未有把基督教與「此世」結連起來,一種沒有與此世結連的啟示依然未能符合及齡世界的需要。然而,若我們撇開及齡世界是否真需要一種與此世相連的信仰不談,巴特那種強調道成肉身的啟示觀真的仍與此世相離嗎?朋霍費爾的批評是否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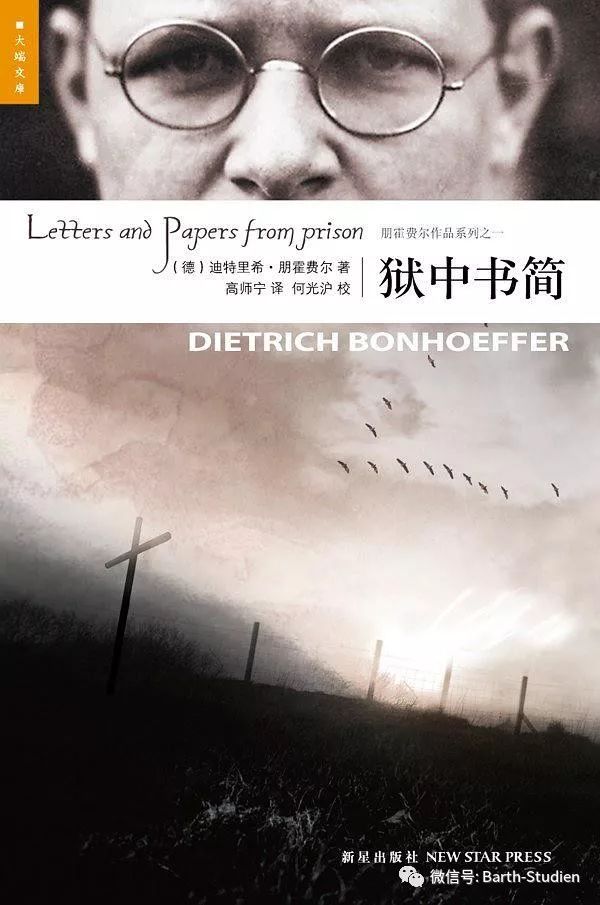
朋霍费尔著作书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巴特啟示觀的發展
《<羅馬書>注釋》(第二版)中的啟示觀
眾所周知,巴特與自由神學決裂的主要導火線,乃其大部分師長在第一次大戰前表明支持德國的戰爭政策,以致叫他將責任歸咎於他們所追隨的自由神學路線。13 當然,他們的政治取向與神學方法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在巴特看來,他們的問題乃是發展了一套以人為中心的神學。以人的意念來建構神學的結果,便是以人意代神意,故此便發展出各種各樣的弊端。因此,早於一九一六年,他已指出:
但是遵行他的旨意,意指要重新開始。他的旨意並非一種改正了的我們的旨意的延續,乃是以一「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來就近我們。我們的旨意並不能造就甚麼,除了最基本的再造(recreation)。14
因此在其《<羅馬書>注釋》(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中,巴特十分強調神人間的鴻溝,正如其名言日:「上帝在天上,而汝則在地上。」15 故此從人的一方永遠不能接近上帝,啟示永遠是從上帝一方作開始。
可是,人卻能對上帝有所領悟,即是說:本來是不可見的上帝使自己被人看見,但這又不能影響上帝原來的不可見性(unintuitability),否則,神人間的鴻溝便不能被維持,這怎樣可能?答案是耶穌基督:
「我主耶穌基督」是福音並歷史的意義所在。藉着此名,兩個世界交遇又分離,兩個平面相交,一個是被認知的、另一個卻不為人知……我們的世界在耶穌裏被另一個世界碰觸,被奪去其在歷史中、時間中或物質中的直接可見性……在歷史中,耶穌作為基督只能被辨認為問題或神話。作為基督,他帶來父的世界,但我們站在此具體世界中並不知道任何關於另一世界之事,也沒有能力知道甚麼。從死裏復活卻是一種轉變:在那點從上而下的顯明,又從下而上的作相應洞察。復活就是啟示:耶穌被顯明為基督,上帝的出現,上帝在基督裏被領悟。16
每當耶穌被宣稱為基督時,就是上帝啟示自己之時,17 但並非在歷史中作出啟示,乃是向歷史中的人開顯另一個世界,上帝的存在並沒有在時空中產生任何延伸。故,巴特說,復活並非一歷史事件。正因啟示永遠是「點對點」(point by point)的啟示,在復活中由聖靈開顯的新世界碰觸肉體的舊世界的情形,據巴特說,就如切線(tangent)碰觸圓周一樣。18 因此,在歷史中上帝的隱藏性依然被維持,也因此,巴特展開他對宗教的批評:
所有宗教都假設上帝將作事或已作事,並不在乎人赤裸地站在上帝面前並被他包裏的這「一刹那」。它們並不認為上帝感動人的這一刹那之前與之後是有所不同的,又或它們設想這「一刹那」依賴一些以往行為或會帶來繼後的行為。換句話說,它們看這「一刹那」某程度上可比擬人類行為。因此所有宗教皆負有對人之所是、所作和所有之事吹噓的可能性,就如人是神聖的。19
宗教的問題在巴特看來,就是人試圖在此世的時空裏尋找神聖的顯現。明顯地,這種把人的作為與宗教連結起來的說法,也是對以人為中心的神學建構方法的一種批判,是對自由神學的反動,這也是《<羅馬書>注釋》的最大特色。故在此著作中,巴特以為耶穌最大的貢獻並非正面的啟示上帝,乃是反面的隱藏:
他最大的成就是一負面的成就。他不是位守護……他不是位英雄或人的領袖。他亦非詩人或思想家: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你離棄我?……不管如何的客觀及普遍,在耶穌裏的啟示乃一弔詭。在作為基督的耶穌裏,上帝信實的應許被滿足,但因在他裏面所呈現的是最後的隱藏並最深奧的隱秘,故現在不是也永不會是一不證自明的真理。20
然而,這種強調上帝不可見性的傾向,在展開教義學討論時,顯然會成為阻礙多於貢獻,故巴特所需要的,是積極發展上帝可見性的討論——道成肉身的概念。
格丁根時期的發展
巴特第一次作教義學討論的嘗試是在一九二四年,當他在格丁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教授改革宗神學之時。在這時期,巴特依然十分強調神人間之間隔,「上帝就是上帝」這主題充斥於其講義。21 但為了發展其教義學的討論,巴特不得不檢討啟示的「客觀可能性」(objective possibility of revelation)22 及「主觀可能性」(subjective possibility of revelation),23 以致能符合人認知功能中的主客關係。24 所謂啟示的客觀性,就是要討論那位只能作為啟示的主動者的上帝,如何可成為人認知過程中的客體,答案當然也是耶穌基督:
上帝在其非啟示(nonrevelation)中啟示他自己,誠如他自己,不多也不少,完全的上帝,在其隱匿中與我們交遇,就是成為可見、可感與可理解的人。……但他真的表現出他自己。在這客觀條件上,啟示成為可能……但若上帝符合了這條件,上帝便除去了不可能性,使自己被聽被見於其啟示中。25
顯然地,把耶穌基督視為隱匿着的上帝,在巴特看來,不但不構成啟示的障礙,反倒為啟示的客觀性創造了條件,因為耶穌乃是在時空裏真實可被辨認的人。然而,在這客觀的人身上,上帝的神性依然被隱藏,因為上帝縱然成為了真實的人,卻不能憑表面被人認知,於是,他必須解釋人能從耶穌這人身上看到上帝啟示的條件,這就是所謂的啟示的主觀性:
上帝的第三位格聖靈,他的工作是激發我們的人性,使之在此弔詭中被抓住,叫我們能看見、聽見、接收並接受,就是使我們對上帝產生接受性,把我們置身於寓於基督裏的上帝面前,叫我們與上帝有團契。除了聖靈這種真實性外,其他建構主觀可能性的嘗試終必徒然。26
故此,巴特在其講義中依然大力抨擊宗教,而施萊爾馬赫(F. D. E. Scheiemacher)更成為他主要批評目標。27 至此,巴特對道成肉身的討論似乎已經完滿,上帝藉着這真實的人耶穌顯現於我們面前,但其神性卻又被隱匿起來,憑着聖靈的引領卻叫我們得以辨明。但相對於《<羅馬書>注釋》來說,不盡相同之處乃這位作為「完全的他者」的上帝不但只僅觸及到這歷史時空,其神性也灌注於耶穌這歷史人物身上,因為對巴特來說,上帝在隱藏中必然也是全然的上帝,不能是部分的上帝,否則,只能以上帝為主導的啟示便不可能;28 但耶穌的人性也必是全然的,否則,其隱匿性也不可能維持,29 可是,這卻產生了一本體論上的難題:作為全然的神又是全然的人的耶穌,其神性與人性又不能相混,卻要結連為同一主體(one subject),當中上帝的神性怎能不被影響?
米廖雷(Daniel L. Migliore)指出,這時期的巴特基本上認同於新教正統派的一貫主張,即受苦的主體為基督的人性,其神性並不能受苦以至死亡。30 然而,這種古老的看法並不能解決上述的複雜教義問題,以致在《格丁根教義學》(Göttingen Dogmatics 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出現了以下的奇異說法:
上帝是自由的主,這不只是在超越矛盾上,也是在超越其神性(deity)上。上帝是如此神性以致沒有被終止為上帝,而同時成為並願意成為非上帝。31
這句顯然在句子上矛盾,《格丁根教義學》的編者指出,巴特自己在稿上也打上了問號!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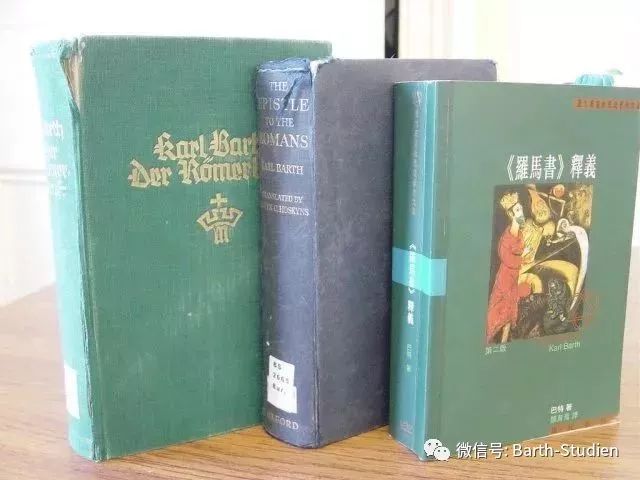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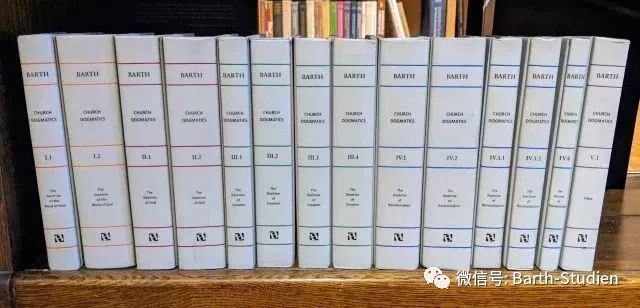
巴特著作书影
《教會教義學》之大成
當我們比較《教會教義學》(Church Dogmatics)第一、二冊與英文版的《格丁根教義學》第一冊時,會發覺二者在編排上並沒有太大的分別,33 但在仔細分析下,其分別雖小,卻是十分重要的,尤以對揀選的看法為甚。在兩部著作中,揀選都是被置於上帝的教義之下,並拒絕雙重預定論的看法,但在《教會教義學》中,耶穌基督同時作為揀選的上帝及被揀選的人得到非比尋常的發展,34 對於啟示論的重要性,乃在於有關道成肉身的難題得以解決。正如前述,在此以前巴特一直徘徊於處理神性如何與人性結合於同一主體中,而又在本體論上不被影響的困難中,但在《教會教義學》Ⅱ/2第三十四節,巴特明言:
在他之中,上帝將他自已與人結合起來。因此,人為了他的緣故而存在。靠着他,耶穌基督,為了他和向着他,宇宙被作為一個劇場而創造了,作為上帝與人交往和人與上帝交往的場所。上帝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類似地,人的存在本源地是他的存在。35
為何兩種存在的結合並不影響其中的神性呢?因為巴特認為,我們根本不應先預設有一種與人性無關的神性,這種在基督裏顯現出來、自限在具體肉身內的神性就是上帝自己的神性,是上帝自己在永恆中所選定的:
除了那顯於這具體決定與限制中他的存有,這在其永恆的存在中所作的初始抉擇以外,我們不能從上帝期盼其他的抉擇。36
故此,道成肉身並不影響上帝的神性,因為上帝的神性就是在基督裏附有人性的神性,以往的死結正是出於一種沒有根據的前設,要求神性與人性絕對的分離,巴特在《教會教義學》的第四冊對此說明得更清楚:
我們也許以為,相對於所有相對的東西,上帝能夠而且必須只是絕對的;相對於所有低下的東西,他是高貴的;相對於所有受苦受難的,他是積極鼓勵的;相對於所有的誘惑,他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相對於所有的普遍存在性,他是超越的;因而,相對於每一種屬於人性的東西,他是神聖的,簡而言之,他能夠並必須僅僅是「整個的另一個」。但是,這樣的信念被證明是相當的不可靠、腐敗和異端的,因為事實上,上帝確實是並在耶穌基督之中的。我們不能讓我們的那些設想成為標準,以此去衡量上帝能或不能做甚麼,或者以此作為基礎,去斷定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使自己變得自相矛盾。通過這樣做,上帝向我們表明,他能夠做到它,並在他的本性之內做到它。他顯示他自己為更加偉大、更加富有和更有威力的統治者,超過我們所曾設想的。我們關於他的性質的思想必須由此引導,而不是倒轉過來。37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思想上的轉變,教我們想起巴特在寫作《教會教義學》以前,曾出版了一部有關坎特布雷的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的著作《安瑟倫:信仰尋求理解》(Anselm: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書中一個重點正如書名所示:信仰尋求理解,並且巴特自認這是他最滿意的作品:
在這些年間我正在除去我內裏最後的哲學殘餘,那是較人性傾向的……基督教義的基礎與闡釋。實際上對此作最後話別的文本,並非許多人讀過,在一九三四年針對布倫納(Emil Brunner)的小書《不!》(Nein!),乃是在一九三一年面世,有關坎特布雷的安瑟倫對上帝論證的書本。在我眾名的著作中我對此最為滿意的……在此以前,我曾至少部分地為哲學系統的外殼(the eggshells of philosophical systematics)……所困擾。38
如此看來,這所謂「哲學系統的外殼」很可能就是一種對上帝教義先入為主的看法,也正因為以往被此困擾,巴特視一九二七年面世的《教義學綱要》(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為一錯誤的開始,39 要重新開始寫作一部《教會教義學》,也因此巴特高度讚揚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是少數留意到坎特布雷的安瑟倫對其影響的學者。40
可是,巴爾塔薩卻將這轉變視為巴特從辯證神學轉向類比神學的轉捩點,然而若類比神學的意思是從耶穌其人身上去尋找上帝的啟示的話,其實早於寫作《格丁根教義學》時這種方法已十分普遍,41 巴特當時所欠缺的只是一個單純從信仰入手的視點罷了。甚至我們可以說,巴特本身對於「辯證神學」或「類比神學」這些標籤並不十分關心,他在格丁根時更曾建議學生不要被「辯證」一詞所威嚇或過分使用它。42 再者,若有所謂「辯證神學」的手法,那麼它在《教會教義學》中也並不罕見,例如第二冊中巴特依然十分堅持上帝在基督裏的隱藏性:
在其啟示中,在耶穌基督裏,那位隱藏的上帝真的使自己可被領悟。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憑眼見(to sight),乃是透過信心(to faith)。不是在其存在中(in His being),但在印記中(in sign)……因為我們作為人看見並認知他,故我們能言及他。我們不能去除那帳幔而為之,就是沒有保留其隱藏性,或離開其恩典的奇蹟。43
故此,縱然巴特在晚年大談「上帝的人性」,但他並不以為自己是站在一個與早年對立的位置,對他來說,在耶穌其人身上啟示的上帝依然是那位「完全的他者」。44 亦因此巴特在《教會教義學》把時間分為被造時間(created time)、墮落時間(fallen time)以及啟示時間(revelation time),45 並不叫人意外,因為縱使道成為了肉身進入時空之內,他依然堅持,上帝並不在歷史時空中被人所辨認,啟示並非如其他事件般在歷史以內,反倒歷史是在啟示之內。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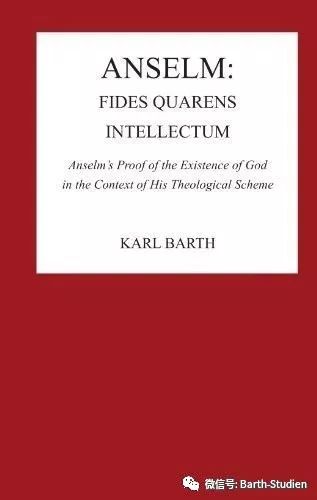

巴特与安瑟伦著作书影
評估「啟示實證論」的批評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清楚看見,巴特雖然以為上帝的神性真的藉着耶穌進入歷史時空裏,可是由始至終他仍堅持啟示並非在歷史時空裏發生,以維持上帝的隱藏性。如果「啟示實證論」的批評重點真的是啟示與此世相離的話,那麼朋霍費爾的說法肯定是正確的,因為這正正是巴特要維護的項目,故此,朋霍費爾在《行動與存有》(Act and Being)中一直質疑,在巴特這種「點對點」式的啟示觀背後隱藏着一種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ism)。47 相反,朋霍費爾要爭取的,正是上帝在此及齡世界的可見性,即在宗教(作為一種超越主義)被人拒絕後,為上帝在此世作啟示提出可能性,難怪巴特被他批判為在否定宗教後,仍舊傾向保守主義。
但朋霍費爾自己又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在《行動與存有》中有以下一段論述:
啟示的問題並非在於上帝有自由遠離我們,即是他的外在孤立性和獨立性(external isolation and aseity);而是他的趨近性(forth-proceeding)他所賜下的道(given Word),他規範自己自由的鏈結,就是他自由地規範自己於一歷史人物所表明的,把自己置身於人的位置上。上帝不是脫離人而自由(free from man),卻是為人而自由(free for man)基督就是上帝的自由之道(the Word of God’s freedom)。上帝在那裏(God is there)意指:不是在永恆的非客觀性(eternal non-objectivity)中,卻是(在尋找一刻)「可被擁有」(“haveable”),能在教會裏被掌握於他的道中。48
朋霍費爾的消解方法,就是直接把在世上可見的耶穌視為上帝在歷史中的客觀顯現,故此他認為,巴特把耶穌視作上帝的客觀實體這步是做對了,可是卻做得不夠徹底,仍舊把啟示置於歷史時空以外,這在及齡世界裏是不合時宜的。但在歷史裏可見的耶穌卻是一位受苦的上帝,故若信仰是參與在上帝的啟示中、那麼啟示的非宗教性詮釋便非一種內心深處的超越,而是在世上參與於他人的苦難中:
耶穌之關心他人乃是一種超越的經驗。這個脫離自我、至死不移的自由,就是耶穌的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堅強根據。信仰就是參與於耶穌本身(道成肉身,十字架與復活)。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並非人對超越存在、人對絕對權力或至善的宗教關係,那不過是對超越的一種偽造的觀念而已。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乃是藉着參與上帝本身而得的捨己為人的新生命。49
倘若我們只能以一種舍己行動來向及齡世界見證上帝,那麼,我們還可對上帝的本性作出任何表述嗎?可能!普倫特指出我們對於朋霍費爾所提及的「秘密的鍛煉」(Arkandisziplin)注意得並不足夠,50 且看以下的一段話:
我們將如何用世俗方式講解(或許我們已不可能再以一貫的方式來講這類話)上帝呢?在哪方面我們是非宗教、世俗的基督徒呢?又在哪方面我們是「那被選召」的教會(ekklesia))不認為自己是特別受寵蒙愛的人,卻看自己是完全屬於這個世界的呢?這樣基督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對象,而是十分不同的東西,他實在是世界之主了。然而這又指明甚麼呢?崇拜與禱告在一個全無宗教的情況下將有甚麼位置呢?是否秘密的鍛練,在次終極與終極的分別中(你以前已聽我談起的),可以獲取新的重要性呢?51
這段說話緊隨於對巴特批評為「啟示實證論」者,是一種保守主義的那段話之後,可見朋霍費爾自己或許也未能解決這疑難,而要設定一種「秘密的鍛煉」來盛載它。這種「秘密的鍛煉」會否與他自己所抗拒的「啟示實證論」有相和之處,以致他認為要把它置於隱秘處,免受及齡世界的鄙視與污染?
如此,巴特與朋霍費爾在啟示觀上的分別就只是把耶穌視為歷史上真實可見的啟示而已嗎?我們可簡單地宣稱,這種分別是微不足道的嗎?這又未必,因為這種分別帶來的意義是重大的。耶穌若被視為真實可見的啟示,那即表示上帝的存有真實進入了歷史中,甚至已化為可被人類認知的客體,而無需預設一超越的啟示區域,這就是上帝那為人行使自由的結果。然而,那位歷史上的耶穌已然成為過去,歷史學的方法也不能為其啟示作出可靠的保證,52 上帝的存在在今時如何仍可為人所認知?其實早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間,朋霍費爾已在其講師資格論文《行動與存有》給出他的答案:
啟示只能相對於教會來說可被想像,教會是由現今的信仰群體所組成,基督的死與復活在會眾中、為會眾被宣講。……因教會就是現今的基督,「基督存活成會眾」(Christ existing as congregation)。53
朋霍費爾運用了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的概念,54 使得基督的存有在今時仍可被人認知提出可能性。顯然,這種說法在早期的巴特思想中的確付之闕如,可是對於上帝愛人的自由的表述,卻在朋霍費爾去世後見於較後期的《教會教義學》第四冊中:
因為上帝在基督裏,這不是反對他自己的存在,或者與他自己相分離,他已經使他的神聖之愛的自由發揮作用,在這種愛之中,他是神聖自由的。因此他已經做到並顯示出他的神聖性質。他的不變性就在這一形式之中。……他自己能夠成為屬世的,創造出同樣屬於他自己的屬世形式:僕人的樣式(forma servi)以及它的原因;所有這些,都不放棄他自己的形式:上帝的樣式(forma Dei),他自己的榮耀,而是接納人的形式和原因,進而與屬他自己的(形式和原因)最完美地結合起來,接受這一世界的堅實性。……他的榮耀是愛的自由,在其中他行施和啟示了所有的一切。在這一方面,上帝的榮耀不同於人所想像的神那種沒有自由和沒有愛的榮耀。所有的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怎樣看待上帝的榮耀,以及上帝真實和尊貴的性質:不是武斷地構造他,而是從上帝的榮耀與耶穌基督的神聖品質的聯繫中推論上帝的榮耀。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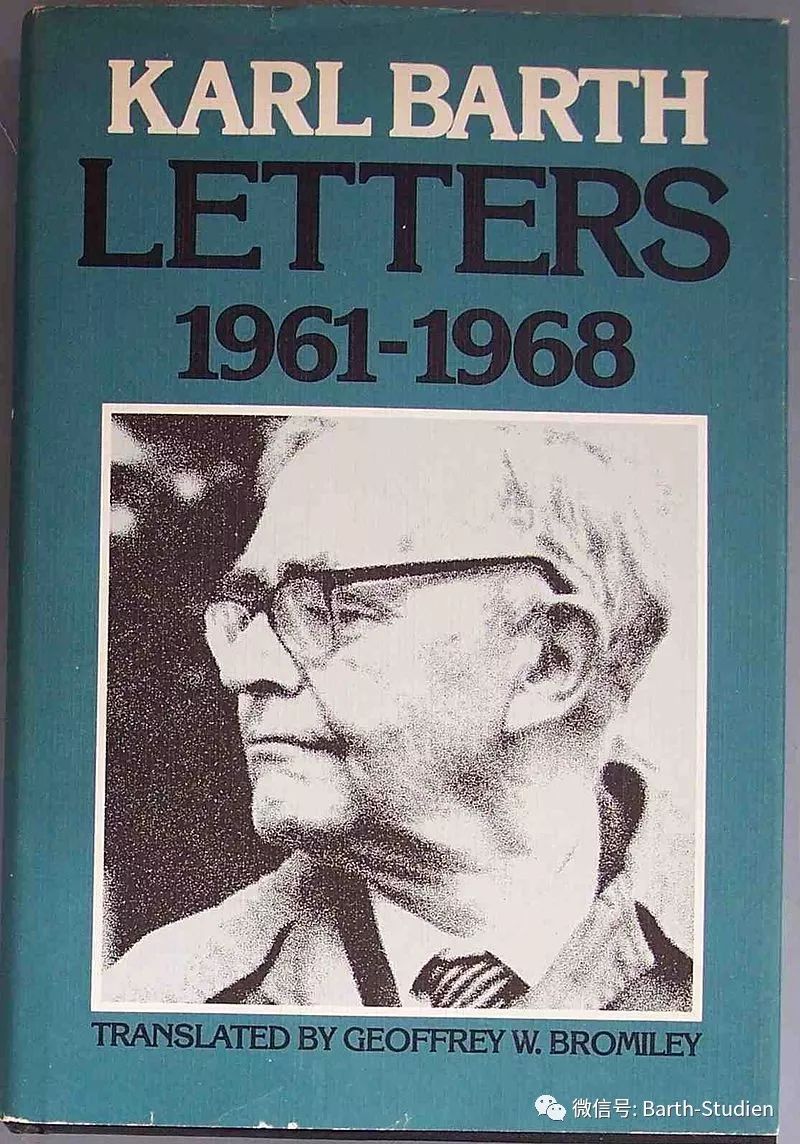
巴特书信集书影
在一九五六年的《上帝的人性》(The Humanity of God)中,巴特更似乎有意識地回應朋霍費爾的批評,譬如說:
這奧秘就是在耶穌基督的存有中我們真的遇見他;在他的自由中他真的不願意沒帶有人性,但與我們同在(but with us),並在同一種自由中不對抗我們,反倒無視我們的功價,卻為着我們(to be for us)——他實在的願意成為人類的伴侶,以及我們無所不能、憐憫的救主。56
還有一事,同樣從上帝的人性出發,在「及齡世界」中沒有嚴格的「圈外人」,只有那些認為自己是及齡的人……再者,若我們從此說起,只能有一些人並未確認及領悟到他們是「圈內人」。而且,從後者的意義出發,就算那些被認為是最確定的基督徒也必須重新認識到他們是「圈外人」。因此,根本無需為圈內人及圈外人而設任何特殊的語言。我們所有人都是此時此世之人。57
「我們」就是教會。教會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群體——那會眾,或用加爾文的說法——compagnie——那被組成、任命並呼召在世界中,藉着施恩的上帝顯現在耶穌基督裏的知識作他的見證,這知識是卑微的,卻因為是聖靈所創建的,故又是不被克勝的。58
這些說法,在認識朋霍費爾的批評後便沒有甚麼隱晦性。由於,巴特認為,揀選是在創世以先完成的,並且揀選的對象是人性(humanity)因此所有人皆有成為基督徒的潛在性,只在乎啟示對他是否發生功效:但對巴特來說,啟示又不是發生在歷史中,乃是「點對點」式的,故說根本沒有嚴格的「圈外人」與「圈內人」之分,59 反倒連基督徒也必須在每刻重新聆聽啟示的呼聲,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及齡世界那種非宗教詮釋的問題。
這樣,巴特解決了「啟示實證論」的批判了嗎?我看不然。如果由始至終地堅持啟示乃發生在時空以外,那為何在時空裏的人卻可言及上帝?巴特似乎想採納朋霍費爾的方法,故宣稱「我們」便是教會,以解決問題。可是,若他自己也斷言在時空裏的人必須每一刻更新,被在永恆裏的啟示激發,那他有甚麼理由老是堅持特定的一套基督論60以至啟示觀?這豈非一套不折不扣的實證論!故此,朋霍費爾觀點的重要之處,在於聖靈的工作是在歷史中繼續不斷的,故啟示在歷史中也得以更新,這便突顯了把啟示視為在歷史中可為人辨認之好處,使得在「此時」並「此世」仍可繼續得知並言說上帝的啟示,方法便是轉向信仰的群體——教會中去尋找。這裏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轉向信仰群體去尋找啟示是破解「啟示實證論」之出路,這豈非返回巴特所一直針對的施萊爾馬赫之路嗎?61 這是否就是巴特對施萊爾馬赫既愛又恨,又覺得自己與他的關係是沒完沒了之因?62
當然,在我們這個所謂「宗教多元」的年代,我們仍可再追問:若承認(聖)靈的工作在歷史中是自由的,那為何只有教會才是啟示的場景?其他宗教群體甚至非宗教群體有沒有得到神聖啟示的可能?但正如蒂利希(Paul Tillich)所分析的,他所做的是護教(apologetic)神學,而巴特的是宣道(kerygmatic)神學;63 又如巴特自己的著作所明示,是《基督宗教指引》64、《教會教義學》,故此是一套向教會以內宣講的神學,若我們把自己的興趣強加於其上來批評他,則可能有欠公允。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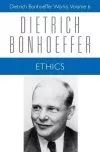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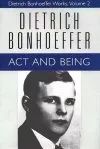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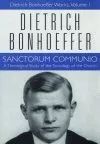
朋霍费尔部分德文版著作书影
注释
1.本文蒙賴品超教授指導並審閱,特此致謝。
2.Dietrich Bonhoeffer,《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ed. Eberhard Bethge;London & Glasgow: SCM, 1953),頁91、95、109。中譯可參許碧端譯,《獄中書簡》(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0),頁102、106、124。
3.Karl Barth,<巴特致赫倫布呂克的信>(From a Letter of Karl Barth to Landessuperintendent P. W. Herrenbrück, 21 December 1952),載Ronald Gregor Smith編,《及齡世界》(World Come of Age:A Symposium on Dietrich Bonhoeffer;London:Collins, 1967),頁90。
4.例如Karl Barth,《上帝的人性》(The Humanity of God;John Newton Thomas & Thomas Wieser trans;London & Glasgow: Collins, 1964)頁58-59。詳見下文。
5.普倫特也曾在《朋霍費爾與巴特的啟示實證論》(Dietrich Bonhoceffer and Karl Barth’s Positivism of Revelation)一文中檢討此課題,然而其討論只局限於巴特的《<羅馬書>注釋》(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第二版),本文則希望達致較全面的討論。見氏著,載Smith編,《及齡世界》,頁93-130。
6.Prenter,《朋霍費爾與巴特的啟示實證論),頁95。
7.Bonhoeffer.《獄中書簡》,頁95(中譯:頁106)。
8.Prenter, <朋霍費爾與巴特的啟示實證論〉,頁96。
9.Bonboeffer,《獄中書簡》,頁91(中譯:,頁101)。
10.同上,頁109(中譯:,頁124)。
11.同上,頁95(中譯:,頁106)。
12.同上,頁91-92(中譯:,頁102)。
13.見Karl Barth, <對施萊爾馬赫的不科學的結語>(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on Schleiermacher),載Clifford Green編,《巴特:自由的神學家》(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London: Collins, 1989),頁66-90。
14.Karl Barth,《上帝之言與人之言》(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28),頁24。
l5.Karl Barth, <第二版序言>(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載《<羅馬書>注釋》(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trans. Edwyn C. Hoskyns, London:OUP, 1933),頁10。
16.同上,頁29-30。
17.同上,頁29。
18.同上。
19.同上,頁111。
20.同上,頁97-99。
21.見Karl Barth,《格丁根教義學》(Göttingen Dogmatics 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ed. Hannelotte Reiffen;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Grand Rapids & Michigan:Eerdmans, 1991),卷I, 5.I(頁88)、5.Ⅲ(頁113、120)、6.Ⅱ(頁134、134注5)、16.Ⅳ(頁368-369)、18.Ⅱ(頁446)。
22.同上,6.Ⅱ,頁140-141。
23.同上,7.Ⅰ,頁168及以下。
24.巴特對於人認知功能的看法,顯然受到馬堡新康德學派(Marburg Neo-Kantianism)的影響,詳見Bruce McCormack,<序言Ⅰ:馬堡背景資料>(Prologue I:The Marburg Background),載氏著,《巴特的批判性實在論辯證神學》(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Oxford:Clarendon, 1995),頁31-77。
25.Barth,《格丁根教義學》,6.Ⅱ,頁140。
26.同上,7.Ⅱ,頁177。
27.同上,7.Ⅲ,頁181-191。然而巴特對施萊爾馬赫的批評未必恰當。
28.同上,6.Ⅱ,頁138。
29.同上。
30.Daniel L. Migliore,〈卡爾·巴特的首次教義學講課:基督宗教守則>(Karl
Barth’s First Lectures in Dogmatics: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載Barth,《格丁根教義學》,頁LⅢ。有興趣的讀者可比較:Barth,《格丁根教義學》,17.Ⅳ,頁408;及Karl Barth,《教會教義學》(Church Dogmaties;G. W. Bromiley & T. F. Torrance ed;Edinburgh:T & T Clark, 1975)Ⅳ/2,頁357的說法:「根本上是聖父上帝在其奉獻及差遣其子中受苦,就是在其自我降卑(abasement)中。」
31.Barth,《格丁根教義學》, 6.Ⅱ,頁136;英譯文如下: “What if God be so much God that without ceasing to be God he can also be, and is willing to be, not God as well.”。
32.同上,6.Ⅱ,頁136注8。
33.麥考密克(Bruce McCormack)甚至以為,巴特是誇大了《教會教義學》第一冊輿《格丁根教義學》的分別,參McCormack,《巴特的批判性現實辯證神學》,頁441-448。
34.有關二者簡單的分別可見於Miglioer,<卡爾·巴特的首次教義學講課>,頁XLV-XLVIII。
35.Barth,《教會教義學》,Ⅱ/2,頁94。
36.同上,Ⅱ/2,頁50。
37.同上,Ⅳ/1,頁186。
38.Karl Barth,《我的思想如何轉變》(How I Changed my Mind; Edinburgh: The Saint Andrew Press, 1969),頁42-44。
39.Barth,《教會教義學》,Ⅲ/4,頁xii。
40.Karl Barth,《安瑟倫:信仰尋求理解》(Anselm: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Anselm’s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the Context of his Theological Scheme; trans. Ian W. Robertson;London:SCM, 1960),頁11。
41.可參米廖雷的簡介;Migliore,<卡爾·巴特的首次教義學講課>,頁XXVII-XXXIV。
42.參Barth,《格丁根教義學》,13.Ⅱ,頁309。
43.Barth,《教會教義學》,Ⅱ/1,頁199。
44.Barth,《上帝的人性》,頁37。
45.Barth,《教會教義學》,Ⅰ/2,頁47及以下。
46.同上,Ⅰ/2,頁56及以下。
47.參Prenter,《朋霍費爾與巴特的啟示實證論》,頁125。
48.Dietrich Bonhoeffer,《行動與存有》(Act and Being;ed. Wayne W. Floyd, Jr.;trans H. Martin Rumscheidt;Minneapolis:Fortress, 1996),頁90-91(強調出於原作者)。
49.Bonhoeffer,《獄中書簡》,頁165(中譯:頁196)。
50.Prenter, <朋霍費爾與巴特的啟示實證論>,頁101-102。
51.Bonhoeffer,《獄中書簡》,頁92(中譯:頁102-103)。
52.當時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與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等人的著作已廣為人知。
53.Bonhoeffer,《行動與存有》,頁110-111
54.同上,頁111。
55.Barth,《教會教義學》,Ⅳ/1,頁186-187。
56.Barth,《上帝的人性》,頁50。
57.同上,頁58。
58.同上,頁63。
59.這種說法教我們想起有關巴特是否有普世論(universalism)傾向之爭論。其實,巴特自己並不以為普世論有甚麼問題(參Barth:《上帝的人性》,頁61-62),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巴特所說的普世論是針對啟示而說的,與救贖論不一定有關係,他對個別的人會否得救根本不甚關心,甚至以為這問題不應被列為神學議案,而指出這正是改革宗提出雙重預定的錯謬之處,這也是筆者在此把universalism譯為「普世論」而不作傳統的「普救論」之因。參Barth《教會教義學》,II/2;以及Barth,《格丁根教義學》,18.1-Ⅳ。
60.從巴特的啟示觀看來,他務必要採納一套近乎亞曆山大利亞的西里爾(Cyril of Alexandria)的基督論,以保證基督是在一個主體(one subject)內擁有兩個特質(two natures),聶斯脫利(Nestorius)那種兩個主體(two subjects)相合的說法是不能滿足他的神學建構的。這也解釋了為何他要擁抱迦克敦信經(Chalcedonian Creed)的基督論,甚至覺得茨運利(Ulrich Zwingli)的基督論比加爾文(John Calvin)的較危險,因為前者有更貼近聶斯脫利思想的傾向。參Charles T. Waldrop,《巴特的基督論》(Karl Barth’s Christology; Berlin, NY & Amsterdam:Mouton,1984),頁18-37;及Bruce MeCormack,<從他超奠基主義的觀點看啟示與歷史>(Revelation and History in Transfoundationalist Perspective: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Epistem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a Schleiermacherian Tradition),載《宗教期刊》(The Journal of Religion178/1[1998]),頁28。
61.有關施萊爾馬赫神學進路的中文簡介,可參賴品超,<從上萊馬赫看基督教神學與宗教學〉,載《建道學刊》10(1998),頁81-108。
62.參Barth,<對施萊爾馬赫的不科學的結語>,頁89-90。
63.田立克(又譯蒂利希)著,龔書森、尤隆文譯,《系統神學》(台灣: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93),頁4-11。
64.《格丁根教義學》德文原著名字正是Unterricht in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65.在巴特處身的年代,顯然「宗教多元」仍未為一受廣泛關注的論題,但可順帶一提的是,其實巴特也不全然否定啟示在其他宗教中的「可能性」,但這欲並非他的關注,例如Barth,《格丁根教義學》:6.Ⅲ,頁149-152;Barth《教會教義學》,I/2,頁381-382就顯示出這種見解。
作者简介

林子淳,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主任兼研究員。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主任;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兼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師、名譽副研究員;中華神學人協會秘書。主要研究興趣:神學及哲學詮釋學、現代神學、基督教思想史、神學處境化問題。著有《哈貝馬斯與漢語神學》(與張慶熊合編,香港:道風書社,2007)、《多元性漢語神學詮釋》(香港:道風書社,2006)。
往期文章
章雪富|内在三一和经世三一:论卡尔•巴特和T.F.托伦斯的三位一体神学
瞿旭彤|普遍與特殊:從蒂利希與巴特一九二三年的爭論看兩人神學立場與進路的差異
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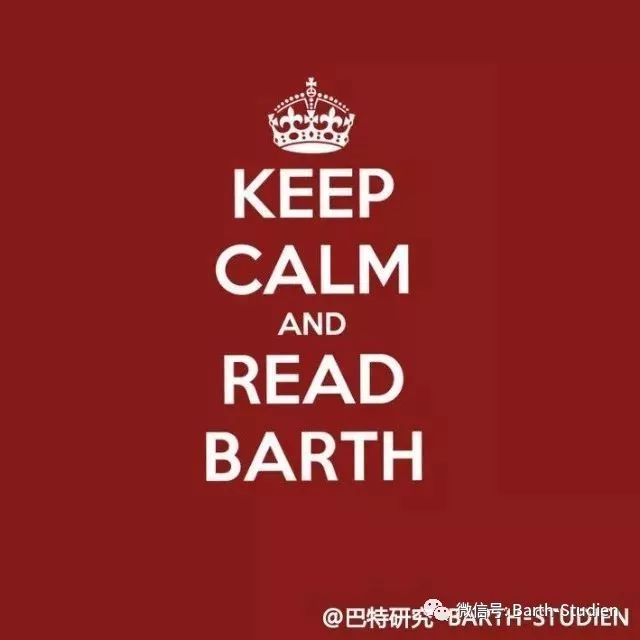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Imaginist、Lea、Vanci、语石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