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加西亚·马尔克斯
编辑修订/ 阿信
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校长胡安·本图拉·卡萨林斯是我儿时的朋友。完全没有当年老师们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把孩子们都当成地位平等的大人,对我尤其关照,课堂上提问我的次数比别人多,还教我如何回答得言简意赅。他允许我把校图书馆的书带回家,其中的《金银岛》和《基督山伯爵》成了我坎坷岁月中的精神食粮。我如饥似渴地读,想知道下一行发生了什么,又不想知道,生怕精彩戛然而止。
读完《一千零一夜》和这两本书之后,我永远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百读不厌的书才值得去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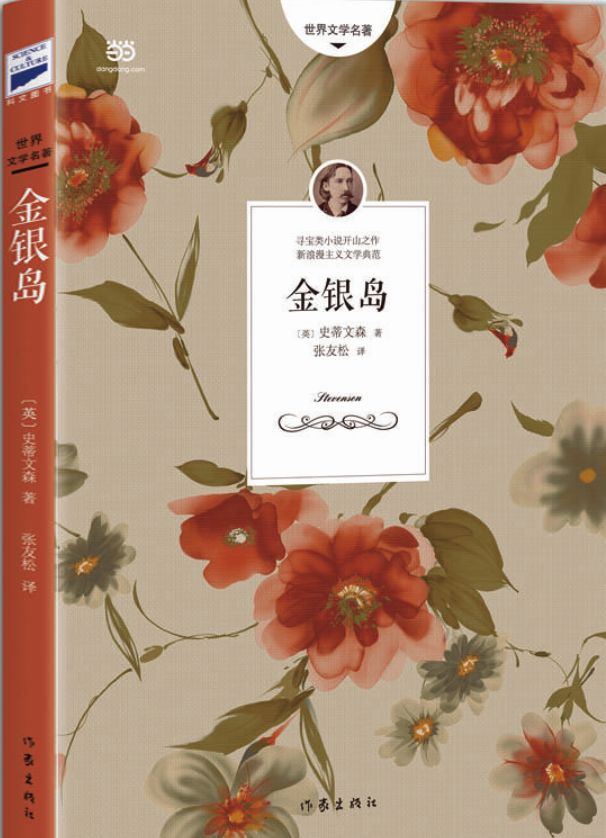
关于《唐吉坷德》的阅读过程,有必要另起一段。此书远不及卡萨林斯老师所言那么震撼,游侠骑士睿智的长篇大论我看不下去,侍从的糊涂话和混账事一点儿也不好玩,简直让我怀疑:此书非彼书。但我告诉知己,博学的老师不可能推荐错。我像一勺勺吃药那样,很努力地一页页读啃。到了中学,《唐吉坷德》成了必读书,我又试了好几次,还是不可救药地厌恶。直到朋友劝我把书放到厕所,方便时翻一番,我这次着了魔,从前往后,从后往前,反反复复地读,意犹未尽,直到能整段背诵。(《活着为了讲述》P124)
进入圣若瑟中学后,嗜书占用了我的业余时间和几乎所有的课堂时间。我能背出哥伦比亚所有脍炙人口的诗作,以及西班牙黄金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佳篇,其中很多诗也出现在正在学的中学课本里。以我的年龄,这些脱口而出的知识让师长们恼火。他们在课堂上刁难我,而我总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他们难辨真假。梅西亚神父说:“这孩子爱咬文嚼字。”他其实想说:“这孩子没法儿忍。”我从不刻意去记,读三四遍,诗歌佳作自然铭记于心。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就是教务长奖给我的,因为我非常流利地背出了加斯帕尔·努涅斯·德阿塞的五十七节八音节十行诗《眩晕》。
课堂上,我明目张胆地把书放在膝盖上读,没挨过批,只能说是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缘故。(真正的好老师啊!——阿信)
我不务正业,忙得很欢。奇怪的是,关注我的老师从不关注我糟糕的拼写。妈妈不同,我的信,他会藏几封吊爸爸的胃口,其余的修改后再寄还给我。有时,她会表扬我语法有长进,用词得当。只可惜两年过去了,成效甚微,拼写问题遗留至今。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字母不发音,有时两个字母发一个音,还有那么多没用的规则。(P142)
我的拼写始终过不了关;稿子至今还会吓坏校对,好心的校对只当是打字员的错,聊以自慰。(P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