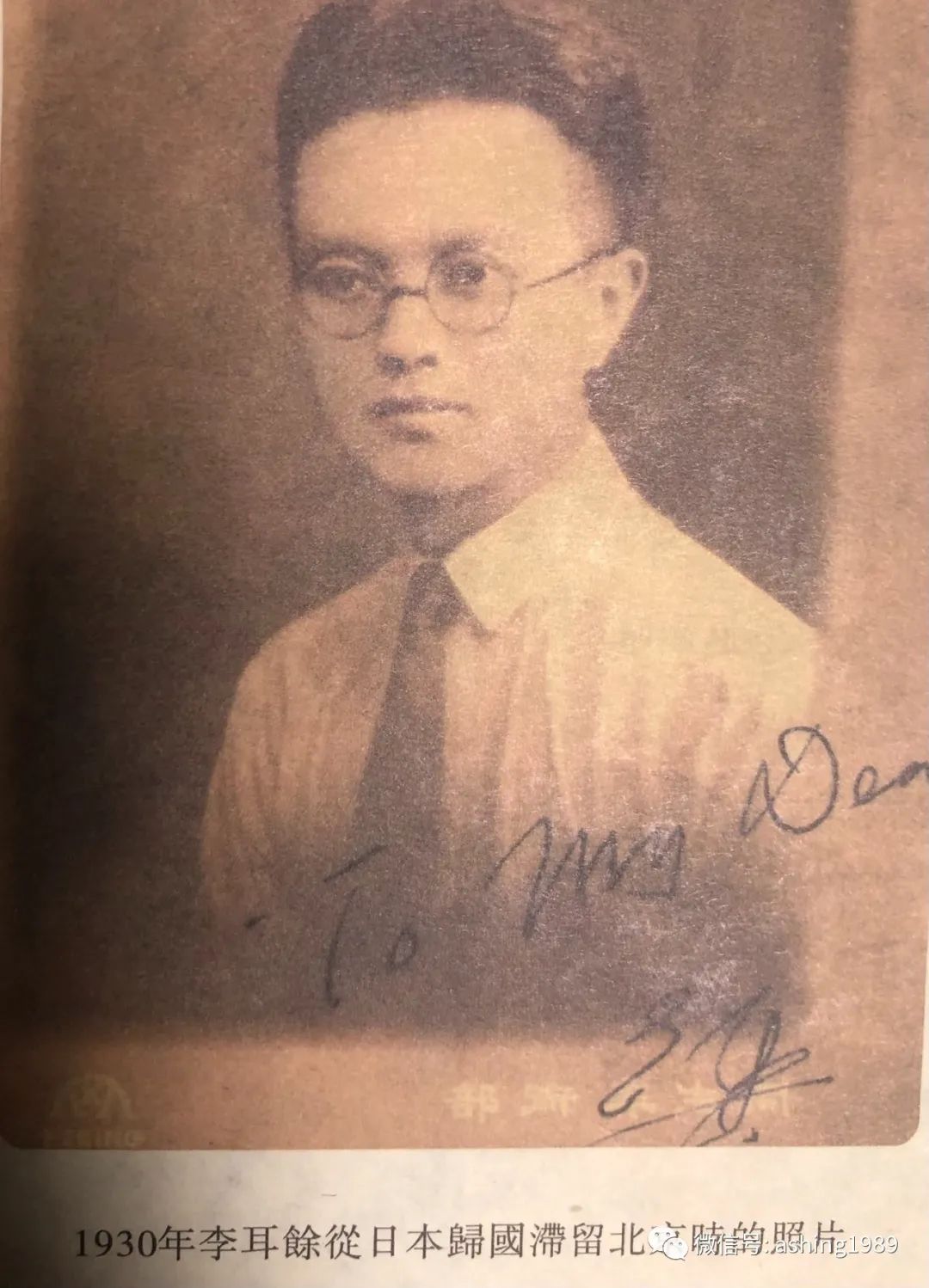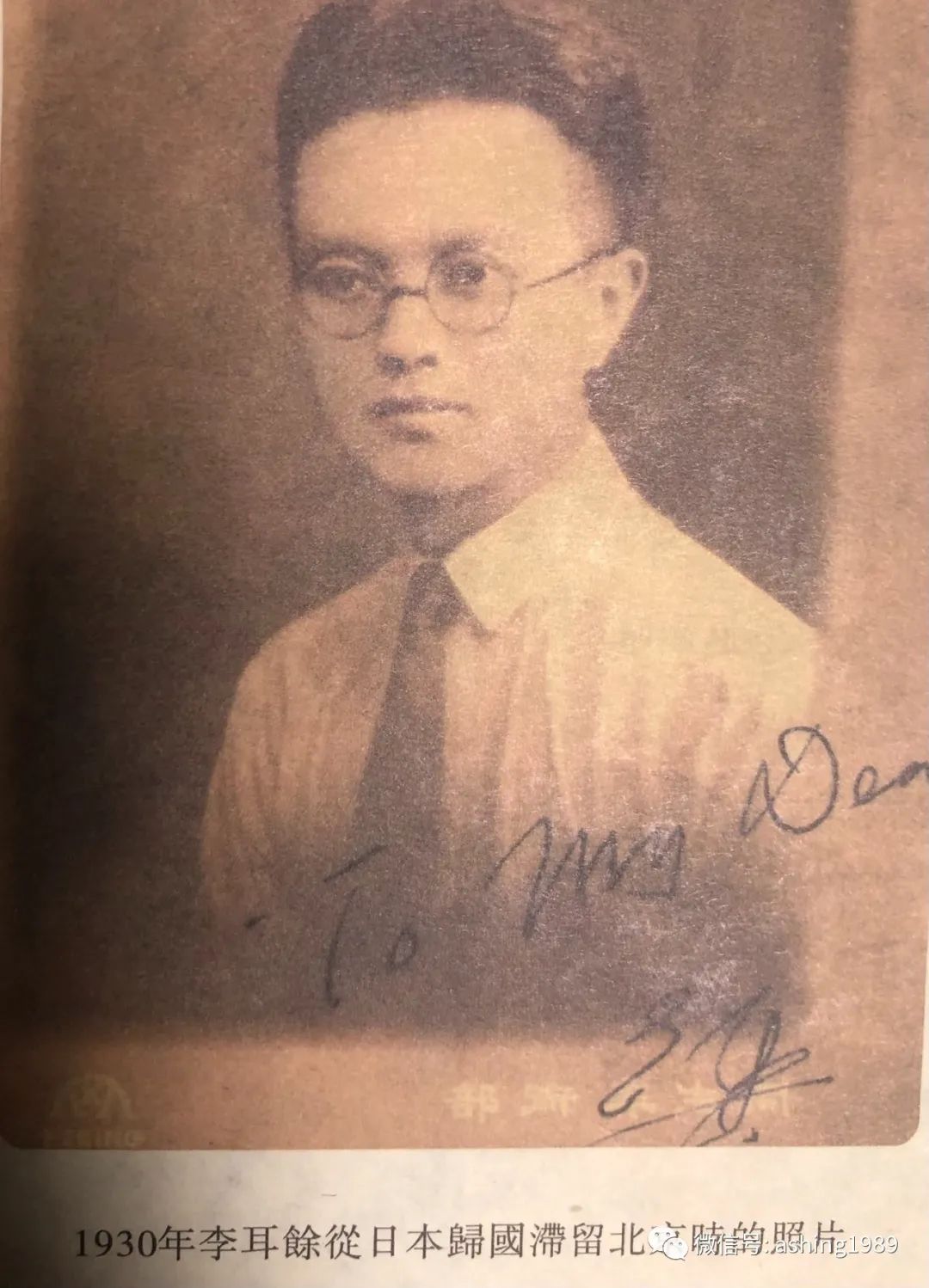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致母亲节
我清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革命时代所有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卷上去,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拉兹,长大了一定要当法官,当了法官才能保护妈妈”……这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极右、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最后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小腿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和伟大领袖同一天死的。居委会说不准办追悼会,反革命分子怎么可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办追悼会呢。
不能在院里搭灵棚,妈妈只好在屋里摆上照片,用棉被和布条把门窗捂紧,低低清唱了外公喜欢听的京剧片折子戏《断桥》。
妈妈在剧团里本来是唱全本《玉堂春》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再后来就只许演偷公社苞谷的地主婆。这算幸运,有成份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押上高高的板登坐“喷气式”,双手反剪,被人从后面踹翻凳子,整个身体向前猛摔出去。目睹此景,妈妈就活在巨大的不安里,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她这种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喷气式,要么下放藏区。终于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种是往电瓶里灌注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可自幼闻惯水粉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重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怕被粗布工装磨伤脖子,下工后还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扔掉丝巾,开始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大声说笑的女工中。她学习岔着腿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听到粗俗的玩笑,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三是重返小时候住过的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她父亲是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归国。归途中在对马海峡突遇风浪差点死掉,并先后在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时还被关麟征邀去黄埔军校兼任文职教官。那时文人富裕,外公拥有三进院落,养活着整个家族。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她常央求勤务兵带着她去后花园捉麻雀,撒把米,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把细绳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跳舞鞋,学上海来的顾太太那样踮起脚尖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好生活的标志,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烟火熏黄的房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夏天,黄桷兰香得人睡不着觉。待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又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一夜风暴,就刮掉了燕子窝。我妈记得那天晚上枪声不断,就像爆豆子一样。等天光大亮,才知道父亲在凌晨开始的全城大抓捕里被带走。全家也被扫地出门,母亲带四个孩子四处漂泊,低声求人,终于在宁夏街一间铁皮和竹混搭的棚里安身下来。
我妈说,那时饿得天都变成了青色的。那是缺糖的表现。她母亲让孩子们脱了棉衣棉裤躺床上保存体力,她从棉裤里掏出棉花做成小孩冬鞋,把毛线衣拆了勾成小圆帽,上街叫卖,一天能挣五六个烤红薯。命是保住了,但几天过后眼见棉花掏空、毛衣也没了……外婆卖血已无血可卖,正想跳沙河自杀,忽在河边听说鹅卵石可以卖钱,建军工厂用的,飞快返家带着我妈跑到沙河边,扑嗵跳下去。正是冬天,母女俩在刺骨沙河捞着石头,开心地捞着,数着冰冷的石头,像数着滚烫的烤红薯。
我妈总说:那时我才八岁,我这老寒腿就是那时落下的。
我妈之所以能进剧团,也是因为饿。那天听说到宁夏街排队可以领馒头,她飞快跑去却被流浪汉们挤出来,见不远处有个队列人少、干净,便挤进去……几个军人打量她,让她抬腿试柔韧性,又让唱歌,我妈就使劲唱起“燕子,燕子,你轻轻地来,燕子,燕子,又开心地走……”这是她在民国时基督教幼儿园里学来的,领头的军人沉吟一会儿,说了声“好,你来西南军区文工团吧”……
从此我妈每天都能吃上馒头了,还常偷回家,举家一起唱“燕子,燕子,你轻轻地来……”。几年之后,她的母亲便走了,走时两腿奇痛,低声叫着我妈的乳名“咪娃,咪娃,我痛啊、痛啊”。多年以后我妈都断定:那就是下沙河捞石头落下的病。
这个国家的命运左右着所有女性的命运,命运一边摧毁着她们,一边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作为黑五类的我妈下放到街办厂后,一直梦想重回舞台,可是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嗓子。那天,为了给一个赶急路的司机电瓶充电,她手忙脚乱忘带口罩,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剧团,她能唱全本的《玉堂春》,当年在春熙大舞台选角,她师傅花想容曾这么夸赞:
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晌,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我知道,这是在告诉我,失去舞台梦想的她开始着手实现第二个梦想了。她很想让儿子穿着体面衣服去上课,背漂亮的双肩书包,像同学一样吃着早餐面包,可她实在没钱。那天我因为没有白球鞋,老师禁止我参加校运会排练,让我滚回家。我妈像一头愤怒母狮冲到学校大吵一架,面目狰狞……她用全家积蓄给我买了白球鞋参加了第二天校运会,然后辞去月薪30多块的街办厂工作,办起成都第一家私人幼儿园,其实,就是帮别人带孩子。
那是一段艰辛岁月,无数夜晚,我看见我妈蜷伏在孩子们的床边,疲惫打盹,她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她每晚睡不安稳,至今患有严重失眠症。洁癖的她坚持每天给孩子们换洗干净衣服、熨烫平整。她说,“孩子们是我的体面,带到街上、公园,孩子们体体面面,生意也才好”。
可渐渐地,能翻出漂亮云手的手指,因天天洗衣物变得关节粗大、变形,曾在春熙大舞台走过曼妙台步的身材,也不可逆转地变形、丑陋。我妈眼角下垂,视力下降,因长期神经紧张,胃部也出现了问题。
终于一月能挣到两千块钱了,那天,妈妈带我去成都饭店吃了西餐,在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看着高岔,她突然害羞地悄悄问我:妈妈的边岔是不是开得太高了,妈已经老了呢。
我妈不可阻挡地老了,失去重回舞台的梦想,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也十分渺茫。我不知何时才能让她实现第三个梦想,住进带花园的房子。我是如此没出息的儿子,只能借钱买一处便宜的远郊顶楼,在屋顶上种了些花花草草。
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身体已大不如前,高血压和骨刺常折磨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她说: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告诉我,这是安慰我。这样的粗心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悄无声息地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脑溢血,医生说只有30%的生存机率。
那天晚上,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我向苍天发誓,一定要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奇迹发生,我妈竟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儿啊,我梦到院子里种了好多的花,花香真是浓啊,浓得把我抬起来了,我就在香味中飘啊,飘……
我不假思索跳槽到收入更高的报社,交了一套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但我仍没办法帮她实现第三个梦想:在缱绻如梦的花园里,让妈妈夏天嗅到黄桷兰,秋天闻到桂花香,在发黄的屋檐下,看燕子们飞去飞来……
那一年,致力于打造中产阶级梦想的我,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新殖民地风格”的装修。我感到妈妈隐隐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瓣了,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只能盆栽些花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央空调又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她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刚在阳台上吊一声嗓子,保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楼提醒:太婆,有人提意见了……
她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提出能不能换到一楼住,种点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不打农药,比菜市场新鲜。可是一楼贵十几万,我哂然“你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说话了,默默听我阐述“新殖民地风格”的理念和艺术气息。后来,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转述:这新殖民地风格啊,其实跟殖民地不是一回事,很先进的。
于是,我定期带她去已不复旧时模样的红墙巷。她会指着某处说:看,这以前是四姑家的前庭,这是孙师长的后花园,这是外公的书房,每晚他都让外婆从窗户放下吊篮,买些醪糟汤圆、红油抄手,全家宵夜。那青石板路啊磨得亮亮的,能照见天上的月亮,斜对面土司的女儿太美了,可是总对着月亮梳头,也不怕白天忧愁……她念念叨叨,我就带她去旁边宽巷子吃醪糟汤圆、红油抄手,买些时令的花儿,她嗅着嗅着,眼神就变得年轻起来,亮晶晶的,但仍固执地说“如今的黄桷兰,真是没以前香了……”
我妈越老还小了,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打扑克,还常常偷牌,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并没发觉她的儿子已偷走更多的好牌……有时我看不下去,悄悄把好牌塞到她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又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红墙巷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隔着镂空窗檩偷看大人们跳交谊舞,留声机里的黑胶唱片总有周璇唱的歌曲……她总重复这些故事,我并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感叹今不如昔……
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教科书里那种慈祥厚重的母亲。她只是一个没落大户人家的女子,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骨子里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她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包括红墙巷的院子。她翻看发黄的照片总念叨“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去念想她最好的时候,在春熙大舞台挥动长长的水袖,浅唱低吟“花光月影宜相照”“当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嗟叹之间,徒增伤感。
她一生的经历让她无比敏感,心思细得可以穿过针孔,能聆听到针掉在地下的声音。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激荡变幻,命运多舛,只好追忆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浪漫,年华似水、抽刀难断。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让她保持重回红墙巷的幻想,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像一块砖、一块砖在修砌着一间大房子,让她真地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原文 05/15/2006母亲节,李承鹏于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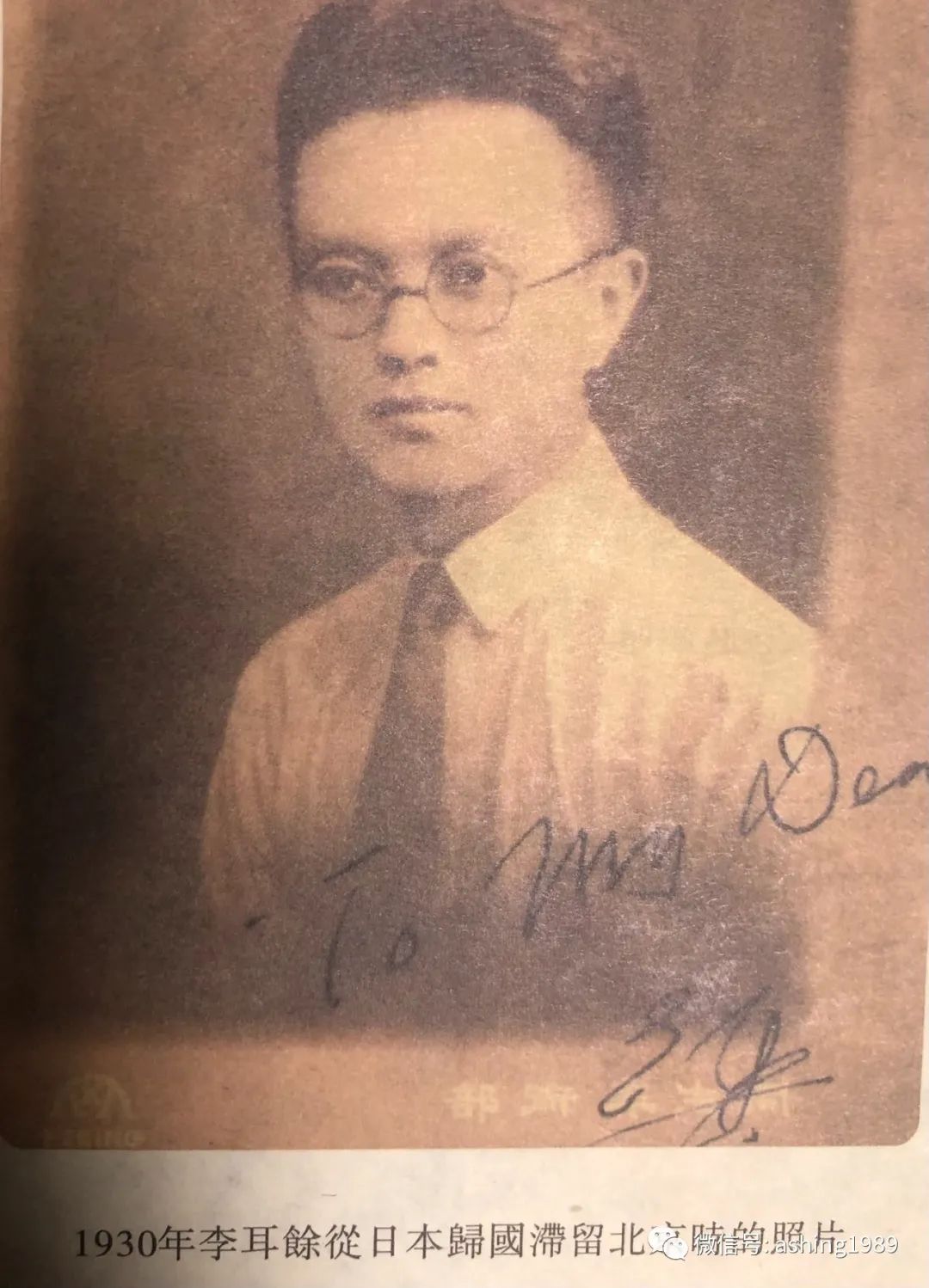
李承鹏外祖父李耳余先生

李承鹏外祖母(游绍琴)游凤之
《落叶》——李承鹏外祖父李耳余先生遗稿
阿信注:该书孔夫子旧书网有售,已很稀少,欲购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