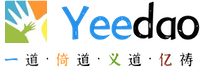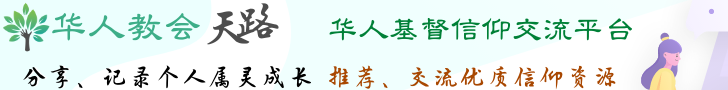北美灵修作家唐慕华女士,在她《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一书的序言里,分享她写作的初衷。有一年,她家的书房需要加建新的屋顶,雇来的年轻修房顶工人花了两个月时间,最终结果却是屋顶仍旧不断漏水。如此一来,这个修屋顶的年轻人就可以不断地索要更多的费用来修补漏水问题。
后来,唐慕华找到了另外两位工人,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令大家极为惊讶的是,漏水的问题竟然是那位年轻工人有意为之的。唐慕华感叹:现今还能够找到好的修屋顶的工人吗——一个熟悉自己的工作,完全能干、诚实而且可靠的工匠吗?整个社会——政府、商界、社会服务界、建筑界——我们都极度需要具有诚信和道德品格的人,需要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好的人,我们庆幸他们遍满社会,而这些德行怎样可以塑造出来呢?
前两天,家里要来客人,太太出门买一些瓜子水果。回来后,我看她脸上有些困惑,就问是怎么回事。她拿起一包瓜子给我看,说这么少一点东西怎么会收了我三十多块钱?我拎起来也觉得不大对劲。她就到储物间把东西重新称重,才发现果然是不够数。
过了一会儿,我在家里打扫,见她人回来了,太太说,那个卖瓜子的女人一直骂我,说我脑子有问题,东西拿走了,当时怎么不注意,总之就是不肯重新算一算究竟需要多少钱,太太人也很坚决,一直等到卖东西女人的丈夫过来,知道什么情况后,赶紧称重,给太太赔礼道歉,退回了多收的的一部分钱。
那条街上,虽然都是看上去老实本分的农民在摆摊,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玄机。很多人的秤不准是常有的事,而且卖的农产品很多并不是自家种的,无非是批发来的菜还当成是自家种的卖个高价钱。遇到小年轻,尤其是领着孩子不方便的妈妈,这些人更是有恃无恐,明明你只要三块钱的青菜,她能够最后给你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让你多买一些才算是诚心如意。
卖牛羊鸡鸭的,都说自己是散养的,喂的都是五谷杂粮,实际上,很多养殖户为了降低成本,怎么舍得全部喂粮食?都是用饭店讨来的泔水拌饲料喂,真正放心的农产品他们都留给自己家孩子吃,根本不够分的。
行走教育群里,Doris分享了自己考驾照的经历,一下子让不少朋友产生了很深的共鸣。在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你考过驾照,都能感受到那种挥之不去的屈辱。教练没耐心教你,脾气大,甩脸色给你看,都是家常便饭。也有的人看得比较属灵,从教练没有耐心的角度看到自己平时对待孩子也是这么苛刻,不近人情。
还有做企业的,我们有一位爸爸,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打拼做起了一家电器自动化公司。盛弟兄很有想法,经常想着怎么通过企业这种方式给社会带来价值,以信仰见证生命的道。但是这么多年,他经常感慨所遇到的现实:企业感叹找不到合用的工人,社会上却有一大批年轻毕业生没有工作机会。这种矛盾常常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我举的例子都是个案,而且都比较偏重于负面的例子,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恐怕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现实。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信任的根基。所有这些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混杂在一起,我们真的是要惊呼,难道社会发展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自以为科技力量足可以使我们强大到可以和神相提并论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找不到几个好的理发师,本分的农民,买水果的小贩,和有耐心有智慧的教练,合用的大学毕业生。

【出差在外的盛总,早晨还依然坚持和女儿连线,一起晨读】
这次游学,我们专门来到绍兴,去鲁迅先生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转一转。为了给孩子们提前做好功课,太太特意在车里播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朗读音频。我听得入迷,觉得鲁迅先生的童年真的是充满了乐趣和活泼泼的力量。回过头来,我们哪每一个人的童年不都是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可是为什么如今的我们竟然全都落得了中年闰土的那副模样?
鲁迅先生当年看到的是吃人的文化,他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是他对孩子对年轻人的那份发自心底的爱。“救救孩子”,别让这个世界成为培养恶魔的地方,别让人性的高贵与健朗,在文化的酱缸里被染成漆黑。
到了绍兴市区,城市的繁盛、热闹如一幅画卷展现在眼前,我们停好车,看车的老师傅见我们一家竟然有四个孩子,立刻上来和我们攀谈,夸我们夫妻很了不起,国家应该奖励你们之类的绍兴话,我听得似懂非懂,只好连连点头表示感谢。
我们没有去鲁迅文化街区,避开了小红书的热门推荐,像往常一样,带孩子都进了街边一家农贸市场。和我住的小区相比,这里的物产实在是丰盛,东西摆放得也很有讲究。孩子们看得都很仔细,一会问这是什么鱼,一会儿问那是什么菜。走到卖梅干菜的一个摊位前面,一个拄着双拐的阿姨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从哪里过来,想吃点什么。我见她的摊位上有成罐的香榧,有高山茶和自家做的散装梅干菜,每一样都买了一些,总过花了一百五十元。阿姨说她们家自己有香榧园,有茶园,见我们孩子多,临走时又送了我们两袋香榧路上会给孩子们吃,我们加了微信,付过钱以后就和阿姨告别了。
这个社会会变好吗?梁漱溟晚年如此发问。我想,任何对中国社会有半点清醒了解的人,都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危机和压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和教育机构,先不说能不能培养出精英人才,伟大人物,最起码的,那些散发着平和、良善、知足、乐观的平凡的普通人,究竟该怎么培养呢?或者说,你愿意自己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出路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牵动国人神经的大问题。但我们有信仰的父母,期待孩子的,是将来不仅可以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更是期望在他们特定的职业中,他们能够成为不一样的理发师,不一样的厨师,不一样的卖水果的小贩。当他们服侍的对象站在他们面前时,他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而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把他们看成是任人宰割、需要极力吹捧的消费者。
那些代代相传的行当,是有师承的。而今呢?教育本来的意图不就是培养人、转变人、使其能够形成特定的人生信念吗?倘若我们的教育能够真正做到有益于整个社会和个人,就不能那么急功近利和短视,一名优秀的理发师、厨师的培养,远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恢复圣经对人类来自何方,因何受造,将来去往哪里的神学性信念,以抵抗来自文化与传统的那些致人死命的宰制。
这次出门,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放着我最喜欢的一本小书,德国大哲学家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皮珀说:
从事职业教育当然需要接受训练,而训练乃是一种偏于某种特殊导向的专业培育,尽隶属于人类和世界的某个部分。教育的导向是整体全面性的,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会知道这个世界的整体运作模式,教育牵涉了人类全体,因为人乃“无所不能”(capax universi),人能理解一切事物的存在现象。(第32页)
当代教育对于评估结果的痴迷,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实际上,如果你的人论出了问题,如果你看不出人性的奥秘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靠着真理的启示,那么你就永远无法摆脱认识论的盲区。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是洞穴里的穴居人,直到那位道成肉身者来到,我们才意识到生命原来如此尊贵容不得半点糟蹋。这个社会会好吗?靠着人类的意志,绝无可能,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要说,凡事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