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作家中,论幽默,刘震云要是排第二,没有人能排第一。就算是从古代算起,我这论断也大致不差。因为,中国作家天生缺乏幽默感,中国幽默文学几乎不值一提。在我看来,中国式幽默,本质上不过是嘲讽。嘲讽与幽默是不同的,嘲讽是高高在上地觉得别人可笑,幽默是深感自己和别人一样可笑。从这个角度看,钱钟书是嘲讽,刘震云是幽默。至于老舍和林语堂,既非幽默,也非嘲讽,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已。
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幽默传统?因为“文以载道”,文学是教化工具,所谓“政者,正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怎么能嬉皮笑脸、不正经呢?按“大学”八条目,“诚意”、“正心”正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啊。然而,陈义太高,多数人就做不到,所以,道德理想国里就盛产假正经、伪君子,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只不过它常常以荒诞的面目出现。
刘震云在文学上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看成是从不同方向向假正经和伪君子投枪。从早年的《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到近年的《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再到这部新作《一日三秋》,刘震云呼唤的不过是一个“真”字。或许在他看来,若无“真”,“善”不过是伪善,“美”不过是丑而已。
刘震云曾告诉我,他不追求语言上的幽默,那是浅层次的幽默,他的做法是搬运现实生活,即通过对生活进行剪裁、变形、组装,让小说的结构自然呈现生活的荒诞。这是一种经得起咂摸的幽默,越咂摸越感到幽默;这是一种初看平淡无奇,细想可笑,深想可悲的幽默。刘震云不想逗你笑、取悦你,而是要引你思、刺痛你。
有时候,刘震云把这层写作用意隐藏;有时候,他选择把话挑破。比如《一日三秋》,19万字的书稿,共分五个部分,最后一部分只有46个字:“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以下无)”这就如同是刘震云在带着读者策马狂奔,走到尽头,却是悬崖,虽然浓雾弥漫在深山巨谷,好在悬崖边竖着一个大牌子,上书“前方死路,赶紧下马”。
浮世绘
让我们先回到小说的叙事。
延津县有个豫剧团,团里有三跟台柱子:陈长杰、李延生、樱桃。三人曾上演一出名剧《白蛇传》:陈长杰演法海,李延生演许仙,樱桃演白娘子,都演得好,都是角儿。
戏里,李延生和樱桃是恩恩爱爱的两口子。戏外,白娘子樱桃却成了法海陈长杰的老婆。为啥?因为年轻时的陈长杰爱讲笑话,把樱桃逗得哈哈大笑,李延生老实,不会讲笑话。但李延生和陈长杰是朋友,经常一起喝酒、吃猪蹄。李延生娶了戏迷胡小凤。
后来,剧团倒闭了,两家人各过各的,李延生和陈长杰还是朋友。没想到的是,婚后的陈长杰越来越不爱讲笑话,两口子都觉得“没劲”,开始经常吵架。最后,就因为一把韭菜的口角,樱桃居然自杀了。人们都说是陈长杰逼死了樱桃,就如同法海害死了白娘子,陈长杰只有带着三岁的儿子明亮去了武汉,自己在火车上当司炉工。
樱桃的阴魂附在了李延生身上,她要李延生带她到武汉见陈长杰。原来陈长杰把樱桃葬在了县城南关的乱坟岗上。半年前,那里又葬了一个强奸杀人犯。在阴间,那死鬼不仅强奸樱桃,还当鸡头,让樱桃当妓女接客,他收嫖资。樱桃要陈长杰回延津给她迁坟。李延生要不答应樱桃的请求,樱桃就不从李延生身上出来,那就意味着李延生很快就得死。李延生不得不带着樱桃去武汉见陈长杰。
樱桃的阴魂跟着李延生去了武汉,却临时变卦,决定不走了。因为她看见了儿子明亮,就想跟儿子在一起,天天照顾儿子。她爱儿子,不想让自己的阴魂附着在儿子身上,而是附着在儿子随身带的一张她的照片上。
那时候陈长杰已经娶了秦家英,两口子虽然谈不上有多恩爱,但也还亲密。樱桃天天住在家里,只有儿子知道,她原本也希望与陈长杰、秦家英一家相安无事。但她毕竟曾经是陈长杰的女人,晚上见陈长杰夫妻干柴烈火,就起了嫉妒心,作起祟来。秦家英后来发现了明亮母子的秘密,就偷了樱桃那张附魂的照片,交给道姑马道婆去作法,扎得樱桃遍体鳞伤、生不如死。
受难中的樱桃给儿子托梦,让儿子去救她。明亮找到了马道婆的住处,发现母亲的照片已经千疮百孔,被针扎透了。樱桃告诉儿子,她浑身上下都是伤,火烧火燎的,只有把她照片放进水里,才能疗伤。明亮把母亲的照片扔进了长江,没成想,樱桃的阴魂立即幻化成戏中的白娘子,唱起了控诉法海和许仙的唱段。很快,一个浪头打过来,樱桃就被大浪卷走了。
少年明亮惊恐不已、肝肠寸断,他在寻找机会逃离母亲遇难的武汉。后来,爱他的奶奶去世了,他回延津奔丧,却决定打死都不回武汉了。陈长杰无奈,只得把明亮托付给李延生一家抚养,他每个月背着秦家英给李延生邮寄孩子的生活费,明亮也开始在延津念小学。
明亮上到高一就辍学了,因为秦家英发现了陈长杰偷偷给儿子寄钱的事儿了。秦家英不是不愿意抚养明亮,也不是不愿意让陈长杰给儿子寄钱,是觉得丈夫不跟自己商量,十几年都把自己当外人,因此震怒非常。结果是,陈长杰断了儿子的生活费供应,李延生夫妻也很快就改变了对明亮的态度,明亮就主动搬出了李延生家,去“天蓬元帅”饭店当了学徒,学炖猪蹄。
明亮26岁时娶了马小萌。马小萌在中学时曾被继父性侵,为了逃离家庭,先是在“天蓬元帅”当了两个月服务员,后来去了北京打工,据说还是当服务员。五年后,马小萌发了财,回到延津,开了个服装店。再次见到明亮,两人聊起过往,同病相怜,就结婚了。
一年后,延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丑闻,所有人在一夜之间都知道了马小萌当年在北京不是做什么服务员,而是当了鸡。丑闻起因于当初跟马小萌一起当鸡的的香秀见马小萌发了财,向马借钱,马不借,香秀一怒之下,就把马小萌在北京当鸡的名片复制了撒到全城各处,那名片上有马小萌搔首弄姿的照片。
明亮小时候逃离了武汉回到家乡,现在不得不带着老婆再次逃离延津。他们逃到了西安,历经艰辛,先是卖菜,被人欺负,后来用马小萌在北京挣的脏钱开了炖猪蹄馆子,没想到生意越来越好,明亮成了成功人士。
陈长杰在临死前见到了儿子明亮。因为要给爷爷奶奶迁坟,明亮后来又回了一趟延津,其间种种故事且按下不表,用“恍若隔世”来概括就够了。
《一日三秋》是一部浮世绘,写尽了人世的虚无和悲凉。但我不得不说,如果仅止于此,它不过是一部通俗的,以宣扬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市井小说罢了;如果仅止于此,它就并不比明清市井小说高明多少,这样的刘震云也就不值一提了。
刘震云之所以是刘震云,在于这部小说的主题不在因果报应,而在于追问笑话到哪里去了。换言之,中国人的幽默感到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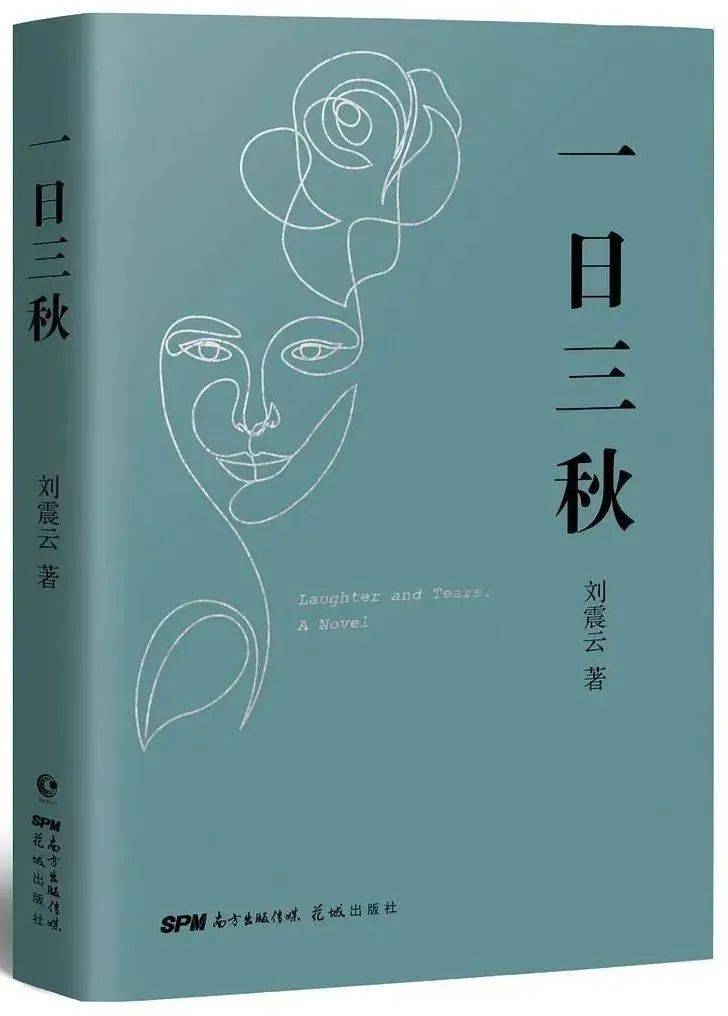
什么是笑话
陈长杰和李延生这对朋友,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有感于自己人生的失败,说了同一句话:“我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在《一日三秋》里,刘震云念兹在兹的,正是人们不懂得怎么说笑话,反把自己活成了笑话。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笑话对于人生的意义,所以被笑话压死了。
小说的第一部分《花二娘》只有五页,但相当重要,它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花二娘的故事是这样:三千多年前,花二娘与花二郎相约逃难到延津渡口见面,但她没等到花二郎。花二娘后来就化成了一块石头,再后来又变成了一座山。花二郎、花二娘都是喜欢幽默说笑的人,没了笑话就没法活,没想到花二娘死等郎君,倒把自己活成了笑话。花二娘死后就成了精,由于天性所致,常常就钻进延津人的梦里,向人讨要笑话。你要是能讲出笑话来把花二娘逗乐了,花二娘就送你一个红柿子吃。你要没把她逗乐,“她也不恼,说,背我去喝碗胡辣汤。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呢?刚把花二娘背起,就被花二娘压死了。或者,就被笑话压死了。”
很显然,刘震云在这里用的是一种修辞,那些被花二娘压死的,不是笑话本身,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快活,就被愁闷压死了。正如陈长杰、李延生、樱桃在《白蛇传》戏里经常唱的“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既然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快活,当然最后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一日三秋》的主角是谁?不是陈长杰、李延生、樱桃,也不是明亮,而是花二娘,因为正是她决定了人的生死。
我在上面复述小说梗概的时候没有提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表面上看,樱桃是死于因与丈夫陈长杰的口角而自杀,真相却是,她是被花二娘压死的。在跟李延生去武汉的路上,在李延生的追问下,她告诉了李延生实情:当年樱桃与陈长杰因为一把韭菜吵架,陈长杰摔门走了,樱桃大哭不止,后来就睡着了。倒霉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花二娘进了樱桃的梦中,要樱桃给她讲笑话。樱桃正在伤心,哪有心思讲笑话呢?于是给花二娘唱了一出《白蛇传》,越唱越悲切,直唱到“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才完。弄得花二娘也伤心起来,樱桃的死期也就到了。“我这才想起花二娘来梦里的目的,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便说,二娘,不消您动身,我先走一步吧,拿跟绳子上了吊。”
小说中,另一个被花二娘压死的是开羊汤馆的吴大嘴。吴大嘴成天板着脸,不拘言笑。一次,花二娘来到吴大嘴梦中,向他讨要笑话,吴大嘴哪会讲笑话,就被花二娘压死了。搞笑的是,生前严肃的吴大嘴,死后却变得油嘴滑舌了。原因是,阎王出台了一项新政,凡被笑话压死的人,如能改过自新,刻苦上进,一口气给阎王他老人家讲五十个笑话,这人就可以转生。但是,这五十个笑话必须是一句话就能把人逗笑的顶级笑话。所以,被笑话压死的鬼都疯了,为了早日转生,都在天天苦练笑话,吴大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进步神速。显然,就连阎王也讨厌愁闷鬼。
但也有人成功接受了花二娘的考验,这个人就是明亮。花二娘曾两次来到明亮梦中讨要笑话,明亮两次都给花二娘讲了让花二娘满意的笑话。
明亮第一次讲的笑话是:
“一个女孩,当了五年鸡,和几千个人睡过觉,但跟一半人没有办过事,你知道为什么吗?”
花二娘:“这不可能啊,人家把钱白花了?”
“因为,男人中间,有一半是阳痿呀。”
这个笑话是马小萌告诉明亮的,说的是马小萌当年在北京做鸡的亲身经历。明亮无耻地讲了老婆的脏事来换命,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大笑话。
第二次,花二娘来到明亮的梦中讨要笑话,明亮却跟花二娘讲道理。花二娘翻脸了。
“我希望你也明白一个道理,我出门是来寻笑话的,不是寻道理的。”
明亮恐惧了,灵机一动,讲了一个与道理有关的笑话。
“道理当然糊弄不了您,但道理可以糊弄许多人。在生活中,许多道理也是假的,可天天有人按真的说,时间长了,就成真的了;大家明明知道这道理是假的,做事还得按照假的来,装得还像真的;您说可笑不可笑?还不如梦里真呢?”
花二娘听到这个解释,反倒笑了。
“让道理成为笑话,总显得有些没劲,还不如你上回说的黄色笑话好玩呢。”
什么是笑话?天天都讲真真假假的道理、不说人话就是笑话,天天都像在演戏就是笑话。这样说来,花二娘要求的其实不是笑话,而是要人像人一样过日子,像人一样说话罢了。
笑话的生成逻辑
笑话是如何生成的?换言之,为什么陈长杰、李延生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诗无达诂。”作为小说家,不能把话说白了,需要读者在阅读小说家的闲笔点染时体悟作者的深意。事实上,刘震云已经多次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引导读者去琢磨问题的答案了。
在与明亮交谈时,明亮怪花二娘总是向延津人讨要笑话,逼得延津人成天胆战心惊。花二娘的回答是:
“说起来,我也是万般无奈呀。来延津前,我是一个会说笑话的人,不需要别人给我说笑话;来到延津之后,变成一个乞丐,别的乞丐是讨饭,我是讨笑话;没有笑话喂着,就活不下去;你以为一到晚上,是我非要到大家梦里找笑话?错了,不是我,是有一个人,附到我身上,一直附了三千多年。”
又说,“是他,非要把生活活成笑话。”
明亮追问这个人是谁,花二娘的回答是“天机不可泄露”。
“他也知道,是他早年留下的病根,非用笑话才能治愈,让我陪他玩了三千多年,可到现在病情也没好转,他也心里有愧呀,可他说,他也做不了主呀。”
又说,“你说,这件事本身,是不是也是个笑话?”
请注意,作者不断在提醒读者,花二娘来延津已经三千多年。我相信,这不是“贾雨村言”,必然有所指喻。我们不妨追问,是什么像鬼魂一样附着了延津三千多年呢?当我们把盐津置换成华夏,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相当明朗了。很显然,刘震云笔下的延津绝不是现实中的那个县城。
花二娘把话说了一半,足够玄乎。这是全书第三部分的结尾,到第四部分,刘震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再次点染。他补叙了花氏宗族的故事。
花大爷原是古时西北地区冷幽族最会说笑话的人,他领着族人到了活泼国,给活泼国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讲笑话,赢得了举国欢迎。于是活泼国国王邀请他们留下来定居生息,他们就留下来了。
话说十年过去,国王驾崩,四儿子继位。谁知四儿子不喜欢笑话,改国号为“严肃”。新国王登基,开宗明义:
“从此,希望大家都严肃起来。”
又说,“让嬉皮笑脸见鬼去吧。”
这时有大臣出班上奏:“现国内有一冷幽族,整日挑唆大家嘻嘻哈哈,怎么处置?”
新国王:“嘻嘻哈哈败坏民风,嘻嘻哈哈败坏人心。”
又说,“这是深仇国和大恨国蓄谋已久的阴谋,这是他们派遣的第五纵队。”
下令屠城。官军连夜围封冷幽族,该族男女老少一百多口子,如砍瓜剁菜一般,脑袋都被剁了下来。花大爷临死前说:
“谁能想得到哇,当年给老国王说笑话时,数他笑得欢。”指的是新国王了。
“原来是装的,全天下数他会装。”
“这是老国王也没有想到的。”
“我说了一辈子笑话,这才是最大的笑话。”
冷幽族被屠杀,只有花二郎、花二娘逃了出来。花二郎其实已经逃到了延津渡口,但吃鱼时听到一个笑话,大笑,就被鱼刺给卡死了。花二娘呢,痴痴等了花二郎很多年,最后化成了一坐山。
活泼国新国王为什么推崇严肃,并改国号为“严肃”?因为只有庄严才能产生神秘感,而笑话非但不能帮助国王装神弄鬼,起到的作用反而是解构。换言之,冷幽族人要是长期住在严肃国,他们必然成为那个说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
细想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刘震云其实在别处已进行数次点染。比如在说及陈长生、樱桃婚后为何“没劲”时,他说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男人,陈长杰性能力不行了;再比如经马小萌亲自讲述、明亮复述的那个事实——“男人中间,有一半是阳痿呀”。
如果读者能联系上述引文进行拼图,我想对笑话的生存逻辑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了。至于延津人如何才能摆脱花二娘这座山的重压,刘震云虽然没有明说,但我想,找到病根就找到了药方。
至于《一日三秋》的写作技巧,限于篇幅,恕我不能细谈了。在我看来,评论像刘震云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不宜过多着眼于所谓技巧,因为大匠求道,小匠求技。事实上,刘震云一直是中国当代最具哲学家品质的作家。中国作家要实现超越性突破,着力点也不在技巧的模仿或创造,而在对大道的探寻。
不过,在此,我还是愿意指出《一日三秋》的两点写作手法:一是《一日三秋》激活而且深化了中国的志怪小说传统;二是善用镜头闪回,举重若轻、以轻写重。比如,写明亮的一生,刘震云就只选取了三个时间节点:当年(六岁)、二十年后、又二十年后。看似只写了几个片断,实则什么都写了。正所谓“一日三秋”,这个书名本就体现了举重若轻。
刘震云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他想写一本《鸡毛飞过四十年》,因为他早年有一部名篇就叫《一地鸡毛》。突然想到,《一日三秋》不就是《鸡毛飞过四十年》嘛!
刘震云为什么要说笑?刘震云为什么爱说笑?因为人间很多事太可笑,也太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