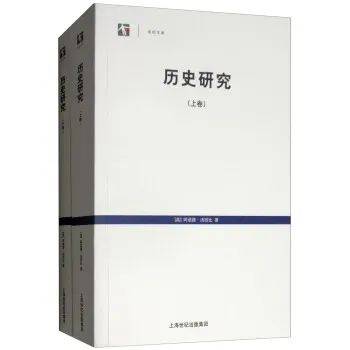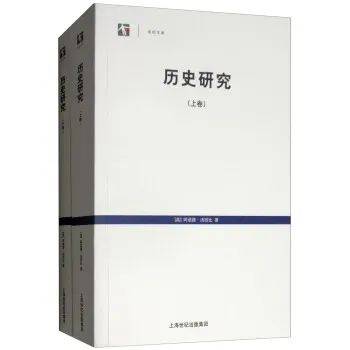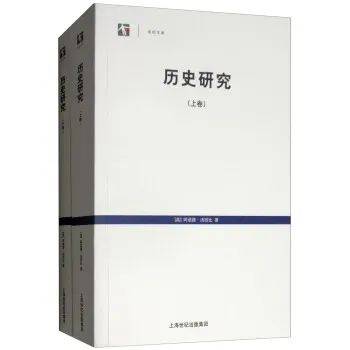51.内部无产者以冷淡甚至是满意的姿态看待降临于少数统治者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内部无产者会用积极的热情接受征服他们的少数统治者。在把犹太人囚禁起来的新巴比伦尼亚帝国的波斯征服者那里,“再世的以赛亚”用流利的演说表示了欢迎。200年以后,巴比伦人自己又在欢迎希腊的亚历山大把他们从阿契美尼王朝的束缚中拯救了出来。P384-P385
匝评:中国老百姓帮助八国联军与此同理。老百姓的想法是:国非我之国,其亡与我何干?
52.当一个解体社会被迫接受某些外来的设计者来为自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时,这就说明,本地少数统治者已没有任何能力和创造力了,对这种过早的衰老不可避免的惩罚是令人耻辱的被剥夺公民权。那些来执行少数统治者职责的异族自然会滥用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在任何由异族建立的统一国家中,所有本地的少数统治者都降格到内部无产者这个等级。蒙古或满洲的可汗、奥斯曼的君主、莫卧儿或是英国的奎沙伊汗德会发现酌情雇佣中国的文人、希腊的法纳尔人、印度的婆罗门为他们服务是很方便的,但这件事掩饰不了这些代理人业已失去灵魂和地位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从前的少数统治者同他们曾经蔑视的内部无产者一起沦落,我们很难设想解体的过程会仍旧按照正常的路线进行。
在现代印度社会的内部无产者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者暴力与温和的两种不同反应,一种是在孟加拉革命者中好战派进行的屠杀,另一种是由圣雄甘地倡导的非暴力运动;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更为古老的一些历史:在许多宗教运动开始出现时,这两种相反的趋势会同时出现。P386
匝评:即便在同一宗教运动中,也会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
53.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我们发现知识分子,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两种文明发生了接触,并且其中的一个文明正被为另一个吸收为内部无产者。我们还可以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观察到另外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所有人都赞同并理解的: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不幸的。
这个联络的阶层忍受了杂交品种的先天不幸,他们不属于父母的任何一方。知识分子受本民族的憎恨和轻视,因为这一阶层的存在就是他们的耻辱。尽管它出现在人民中间,知识分子仍然是外来文明讨厌而又不可避免的活生生的暗示,既然没有办法不接近外来文明,就只好迎合它。当法利赛人碰到税吏时,奋锐党遇到犹太国王希律时,他们都会想到这件事。还有,知识分子不仅在本国得不到热爱,它费力所掌握的其他国家的风俗和诀窍也得不到那些国家的尊重。在印度和英国交往的早期历史中,英国统治者为自己管理方便而培养的印度知识分子是英国人的共同笑柄。这些“巴布”英语越是流利,那些“先生”就越是讽刺和嘲笑那些不可避免的语音瑕疵;这类嘲笑即便出自善意,也都是伤人的。知识分子只好遵从我们对无产者定义的双重标准,他们“在”但是“不属于”两个社会,并且他们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在他们历史的初期,他们可能会安慰自己,对这两个社会来说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安慰甚至也被剥夺了。在人力作为商品的社会里,对供求的调节差不多超出了人类的智慧,到了一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要忍受生产过剩和失业的不幸了。P395-P396
匝评:知识分子注定是“丧家狗”(客观描述,无贬义)。知识分子要告别焦虑,必须找到永恒的家园,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54.像希腊拥有爱奥尼亚史诗一样,在英格兰有条顿史诗、在爱尔兰有斯堪的纳维亚萨迦。斯堪的纳维亚萨迦同阿斯加德关系密切,英格兰史诗——主要流传下来的著作是《贝奥武夫》——它同沃坦及其神圣随从联系在一起,正如荷马史诗同奥林匹亚众神密切联系在一起一样。实际上,史诗是外部无产者反应中最有特点也最杰出的产物,这是他们的苦难留给人类的唯一恒产。古往今来,没有哪个文明创造的诗篇可以同荷马史诗“永远引人入胜的精彩和无与伦比的深刻”相媲美。
我们提到了史诗的三个例子,在这个名单中添加更多的史诗,并且说明每一个例子都是外部无产者与文明发生冲突时的反应也是毫不费力的。例如,《罗兰之歌》是叙利亚统一国家欧洲这边外部无产者的作品。11世纪时法兰西半蛮族的十字军突破了安达卢西亚的倭马亚哈里发的比利牛斯防线,这一事件造就了一件艺术作品,此后,这部作品成为所有用西方世界地方语言写作的诗作的祖先。显然,从历史的重要性和文学价值上看,《罗兰之歌》胜过了《贝奥武夫》。P411
匝评:史诗是书写反抗外来文明的英雄的,这也是中国无史诗的原因。史诗把英雄神化,以激起民族自慰心理,缓解焦虑。
55.所有的统一国家,无论是外来人的还是本地人建立的,通常都被当地人怀着感谢和顺从(如果不是带着狂热的话)接受了;至少从物质意义上说,它们同先前的混乱时期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不知好歹的新王”,简言之,动乱时期和关于动乱时期恐怖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成为过去而被遗忘了,而现状——统一国家的力量已遍及全社会时——却在不考虑它的历史联系的情况下被当作一件事情来加以判断。在这个阶段,本地人和外来人的统一国家的命运便分道扬镳。不管其真正的价值如何,本地人的统一国家越来越受到国民的欢迎,而且对他们的生活来说,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外来人的统一国家则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它的国民越来越不喜欢外来人的特性,也越来越对那些已经完成的和可能仍在为他们履行的有益服务视而不见。P419-P420
匝评:除了本地统治者和外来统治者,还有作为代理人的统治者,后者在本质上是外来统治者。
56.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外来的火花在“高级宗教”赢得皈依者时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障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内部无产者疏远了它正在脱离的解体社会,它在寻找新的启示,那正是外来火花所提供的,它的新鲜使之富有吸引力。但在此之前,这个新的真理必须为人们所了解;只有有人完成了必要的解释工作,这个真理才能发挥其影响力。天主教之所以能在罗马帝国获得成功,是因为从圣保罗开始的四五百年里,教会神职人员努力地把天主教教义翻译成希腊哲学术语,按照罗马文官制度模式建立了天主教的教阶制,甚至还把异教的节日转变为天主教的节日,并用天主教对圣徒的崇拜取代了异教的英雄崇拜。相反,在中国的传教士执行了梵蒂冈的命令,导致了基督教在那里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果圣保罗犹太化基督教的反对者真的如“使徒行传”和早期保罗使徒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会议和冲突中都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远行踏上异教徒的土地时,希腊世界皈依基督教的事业也会变得遥遥无期。P423
匝评:基督教如何处境化是个大问题,必须分清基本教义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千万不能教条主义。
57.在希腊世界的解体过程中,基督教所有不成功的竞争对手都希望在希腊的土地上成功地推动自己的传教事业,在外形上他们按照希腊人的审美标准重塑了神的形象。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希腊化不仅在外表而且是实质上的。只有基督教用希腊哲学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教义。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一种希腊化的理性宗教,它的创造性特征源自叙利亚,用阿提卡方言代替阿拉米作为《新约全书》的语言工具是它的预兆,因为这种复杂语言的词汇里有大量的哲学内涵。
在对观福音书中,耶稣被看做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信仰贯穿并深植于第四福音书中。但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又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是上帝创造性的道。这种表述不是那么明确,但很含蓄,人子和上帝的道是同样的:人子作为道就是把人子的创造性智慧与神的目标视为一体,把道看做人子,就可以把道人格化为圣父之外的另一个人。同时道的哲学一跃而为宗教了。
用哲学的语言来宣传宗教的方法是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来的传家宝。正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公元前30—公元45年)播撒了种子,两百年后,斐洛的同胞基督徒克莱门特和奥利金却有了极为丰富的收获。可能也在同样的方面,四福音书的作者获得了圣道的想象,他把这个想象同人格化的上帝合为一体了。毫无疑问,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教哲学家也是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教父们的先驱,他被引导着穿过希腊语言的大门,走上了希腊哲学之路,因为毫无疑问,在斐洛居住并进行哲学探讨的城市里,阿提卡方言变成了当地犹太居民的日常用语,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希伯来文甚至是阿拉米语的掌握了,这些犹太人不惮把他们的《圣经》翻译成异教徒的语言,从而玷污了它。然而就犹太教历史本身来说,这位基督教哲学的犹太长老却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他从残余的摩西法典中推出柏拉图哲学的创造性成就,对犹太教来说却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P469-P470
58.最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尽管新神话出自异邦源头,希腊长老们的神学和哲学在本质问题的论证上却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柏拉图那里接受的,几乎没有做什么修改。这样的联合可以让我们推测,柏拉图寻找的要代替旧神话的东西同不那么完美的基督徒的基督教信仰就没有多少冲突……从所有的线索看,可以推测柏拉图自己隐约地察觉,显灵就要出现,他的寓言是一个预言。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警告雅典人在他之后还会有其他的精神证人为他的死复仇,在别的地方,他还承认基于哲学的推理和高度的想象,除非仁慈的上帝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是无法知道正确的真理。P473
匝评:柏拉图是一个开道的先驱。因为有柏拉图、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就为基督信仰在希腊化的罗马帝国的落地准备了条件。所以奥古斯丁要融合基督信仰与柏拉图主义。
59.在文明瓦解的最后行动中,各种哲学都消失了,高级宗教却继续存在下去,并且把他们的希望寄予未来。基督教幸存了下来,挤开了新柏拉图派哲学,这一派哲学在抛开理性时并没有找到生存的万应灵药。实际上,在哲学遇到宗教时,宗教一定会繁荣,而哲学一定会衰落。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相遇,也不能暂时停顿以观察为什么哲学的失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问题。
那么是怎样的弱点注定了哲学同宗教应战时总是失败呢?致命和根本的弱点,也是其他弱点源头的就是缺乏精神活力。活力的缺乏使哲学在两个方面都有缺陷。它降低了哲学对群众的吸引力,还阻止了那些感觉到哲学吸引力的人们投身到为了哲学的利益所做的宣称工作中去。的确,哲学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精英的偏爱,“少数适合的人”,正如自命不凡的诗人认为自己作品流传之少就是他诗歌优秀的证据。……
所以哲学在最佳的状态时,也比不上宗教的活力,它只能仿效或是模仿低级信徒的弱点。在塞内卡那个时代,宗教气息时刻使希腊知识分子轮廓清晰的大理石雕像充满活力,到埃皮克泰图斯时代时,很快地失去了活力,在马可·奥里略之后,成为乏味的虔诚,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在两头落空。他们放弃了对理性的追求,也没有找到精神之路。当他们不再试图成为圣人时,他们不是圣人,而是古怪的人。朱利安皇帝从苏格拉底转向了第欧根尼哲学模式——从传奇式的第欧根尼而不是从耶稣中产生了圣西缅苦行者及其他追随者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确,在这个悲喜剧的最后一幕,柏拉图和芝诺的追随者承认他们自己大师的不当之处和不足为训,放弃自己的立场,转而以内部无产者为榜样,这些无产者是排除在贺拉斯的听众之外的凡夫俗子们最真诚的恭维。最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克乌斯和普洛克洛斯都算不上哲学家,而是虚构和不存在的宗教的教士了。对教会事务和宗教仪式的充满热情的朱利安本来是他们计划的执行者,一旦他的死讯传来,他以国家名义支持的教会组织马上就瓦解了,这证明一个现代心理学派创建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重大的改变从来不会自上而下,它们总是来自下面……(来自)这个国家中备受嘲弄而又默默无闻的人——这些人不像许多大人物,他们较少地受到学院式成见的影响。P473-P475
匝评:哲学为什么干不过宗教?因为哲学诉诸人的理性,而宗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理性永远干不过情感。当某个宗教并不反对理性而只是超越理性时,哲学更会完败。
60.先从例外说起,我们可以注意到,政治统治者有时会建立一个教派,这个教派不是真正宗教感情的表现,而是伪装成宗教的某种政治观点:例如伪宗教的仪式表达了对政治统一的渴望,这个社会已经尝尽了动乱时期的困难。在这样的境况中,已经赢得民心的并被他的臣民视为救星的统治者可能会成功地建立一个教派,而他本人、他的政府机关以及他的王朝都会成为崇拜的对象。
这种绝技的典型例子是罗马皇帝被奉为神灵。然而对恺撒的崇拜证明是不可共患难的教派,同“救民于水火”的真正宗教背道而驰。在2—3世纪之交罗马帝国第一次崩溃时,它并没有幸存下来,随之而来的这些重整旗鼓的军人皇帝开始在他们自己声名狼藉的帝国神灵之外再想出某些超自然的影响力。奥勒里安和君士坦丁乌斯·克劳路斯在抽象而又普遍性的太阳崇拜的旗帜下招募军队,一代人之后,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转而效忠内部无产者的上帝,这个上帝证明自己比太阳神或是恺撒更有影响。
……“恺撒崇拜”这样的蛛丝马迹还可以在其他的统一国家中找到,安第斯、埃及和中国。这样的考察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即由政治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的教派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即使这样的教派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而在形式上是宗教的,即使他们与群众的真实情感相一致,他们也没有在暴风雨后幸存下来的能力。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例子,政治统治者试图推行的宗教只不过是有宗教伪装的政治组织,但却具有真实的宗教特征,在这个领域,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已经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尝试的实例。然而,在这些例子中成功都有一个条件,即按照这样的方式推行的宗教一定是一个“强者”——至少能触动这个政治统治者少数臣民的灵魂——而且正好具备这个条件才会获得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当一种宗教通过政治当权者的努力成功地强加在所有臣服于这个统治者的人民的灵魂中时,这个宗教虽然赢得了世界的一部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所有可能成为或是维持统一教会的希望。P476-P477
匝评:人造的假神为什么终将丧失人的信仰?因为造神者和被造的假神追求的都是现实的世俗利益,而真神在人间毫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