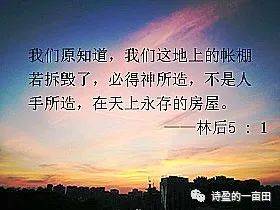八月的家乡,成了火焰山。
虚弱的身体架不住这40度高温天天烘烤和一天24小时空调房呆着,小病几天还在慢慢适应。
终于不用天天测核酸了,可那头疾控中心短信依然在提醒我要去测核酸,只好找社区的网格员报备暂离,回去时再找他报备才能进小区。
这大数据时代,像个巨型的网,无人能漏网。
母亲为了迎接女儿远归,酷暑高温下多跑了两趟菜场,右脚就起了大大的水泡,跟烫伤似的,此起彼伏的长。
姐姐请了假,一早带母亲去医院看,现在没有儿女陪伴的老人,看病真是艰难,被各种码困住,茫然无措。母亲说:“幸好有儿女在身边,不然心慌慌的。”
父亲洗了葡萄颤颤巍巍地递到我面前,在我身边坐下。一会儿睁着眼,一会儿又闭上眼睛,很疲乏的样子。
“老汉儿(四川话老爸的昵称),你眼睛咋又闭起了?又打瞌睡了?”
“不是的,我眼睛不舒服,左眼缝的线扯起扯起的,医生说跟肉长到一起了,扯不脱了。”
“那你右眼是好的,啷个也闭起?”
“闭起舒服些。现在看东西都是重影,因为左眼闭不拢。”
“那我给你买个单眼眼罩,把病眼遮住,看会不会好些?”
“要得嘛。”
说着说着,他的口水长流下来,完全没有感觉,我赶紧递过一张餐巾纸。父亲一边擦一边厌烦自己:“老了,咋成这个样子了嘛?”
姐姐带父亲去看过,说是当年脑瘤术后的后遗症,治不了。还有术后面瘫导致的左眼角膜溃疡,医生为了治好这溃疡,把父亲的左眼给缝上了,只留了一条缝,就是这条缝,让他视物模糊又干涩难受。可也只能是忍耐。
上午大半时间,父亲陷在客厅的沙发里,电视声音大大开着,有时他呆若木鸡的坐着,像是遗忘了什么,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更多时候他闭着眼睛睡着了,我悄悄去关电视声音,他又醒了。
“英儿,你教我画画嘛!不然挺挺坐着没事干也难受。”
“要得,我教你画简笔画吧!”
“我想学画国画”
“你不是在练书法吗?又忘了?”
“哦,真是搞忘了!”
现在我的书桌成了父亲的,上面堆满了笔墨纸砚,横七竖八的在书桌上躺着,他不允许母亲收捡他的东西,因为母亲收捡完之后又常想不起放哪了。
趁着父母冗长的午睡时间,我拿着几个大垃圾袋,将堆在客厅及书房里的各种过期保健品和不用的杂物,全部扔掉。总感觉怎么扔都扔不完,这个家已然在老去的路上了。
每天午后安静时光里,我都在整理书柜和旧物,年轻时没时间看买来存着,计划等退休后再慢慢读的书皆老旧泛黄,抽出一套《追忆似水年华》,打算慢慢翻完,再整理些经典名著捐给山区图书馆,给那些买不起书的孩子们。
父母午休完推门出来,母亲赶紧垃圾袋里翻翻,看有没有扔掉宝贝,父亲直接来一句:“你干脆把老汉儿也拿去扔了!”
便想起陈年趣事,父亲那时壮年气盛脾气暴躁,冲母亲发完火见母亲三天不理他,就来央求儿女们帮忙说和,哪知儿女们都心疼母亲,又正好借机修理一下父亲的臭脾气,家里除了我,个个都领教过父亲的雷鸣电闪,批得父亲自觉理亏就会来句:“你们几个把老汉儿抬到河里扔了嘛!”
记忆是鲜活的历久弥新的,在儿女的脑海里。而父母的记忆已日渐飘散如烟淡去,留也留不住,却又竭力想留住。
包括想把我这远嫁的女儿,留在身边长住,似乎唯有如此,他们才放心,将来我老了,身边不缺亲人照应。
“不是说好了两个月的吗?”
“至少呆三个月,才准走。”父亲耍赖:“你回来一趟多不容易?在这个家你是熊猫。”
太阳落山后,母亲去扔垃圾,不过十分钟的时间,父亲就不停在念叨:“你妈妈扔个垃圾,咋扔这么久?还不回来?”
父亲一早去理发,过了半小时,母亲的电话也会追过去问:“老头子,你咋还不回来?”
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就活成相依为命。想起一早乘飞机离开自己的家时,熊猫先生在身后喊:“你要准时回来啊!”
一张宽大的床上,母女夜话。母亲感叹:“人老了,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做点事就觉得累,都没力气给你按摩!看你的小腿细成啥样了!老妈好心痛!”
我说久病的人不也一样老的快嘛!都要接受!也要学会放手!
这世上哪有永远的家?能把爱留住,带着爱离开,就已是幸福的人了。
熊猫先生的公众号:
打赏二维码——谢谢你的鼓励与支持!